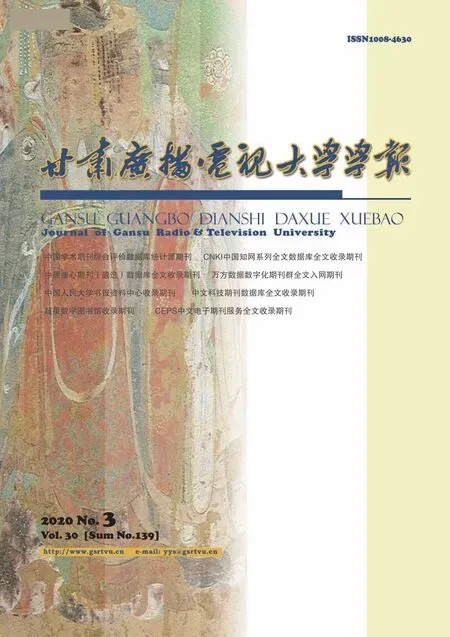論《史記》中母親形象的悲劇色彩
王愈
(復旦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史記》開創了我國以人物為中心的文學表現形式,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小說和戲劇的始祖,具有高超的寫人藝術。《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不僅鮮明,而且豐滿,在以男性為主的歷史世界中,也有眾多的女性形象。在這些女性形象中,包含著一組母親形象,她們身上籠罩著濃重的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帶有特定時代環境下的悲劇色彩。通過分析這些人物形象,可將其悲劇色彩分為如下四類。
一、家國利益沖突下的悲劇色彩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1]1677戰火紛飛的年代,生命如同露珠一般,轉瞬即逝,人的命運不可預知。吳起手下這位卒母的丈夫正是為國捐軀、曝骨荒野的烈士,而她的兒子或許亦將同他的父親一樣,客死他鄉,永難相見。在那個戰亂頻發、刀光劍影的年代,作為一個母親,她所面臨的是一種喪夫之痛和失子之憂,她無法預測孩子的生死,面對未知的恐懼,她只能在惶恐不安的煎熬中度日。這位卒母,正是億萬士卒家庭中女性形象的縮影,是家國利益沖突下的犧牲者。卒母的遭遇已然令人同情,而她那痛徹心扉的啜泣聲,更是彰顯了人物本身的悲劇色彩。
還有《史記·趙世家》中位高權重的趙太后。趙太后疼愛自己的幼子,不愿讓他成為他國人質,從而陷于危險境地,于是“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1]1435此時,觸龍深知太后心理,但為了國家利益,他還是對太后循序漸進地勸諫,終于使太后改變初衷,救趙國于水火之中。可以看出,趙太后是一個開明的女性:她聽取忠言,以家國利益為重而舍棄天倫之樂,終救國家于危難之間。而對于自己的女兒,趙太后則在其出嫁之時抱著她的腳后跟為她哭泣,惦念她嫁往遠方。女兒出嫁別國,自然是為了鞏固江山社稷,永葆國家基業。趙太后作為一個關乎國家利益關系的重要人物,身處政治高位,不得不為國謀劃。因此,在家國面前,她必須舍棄小家,放棄過同平常人一樣普普通通卻樂在其中的生活,放棄享受其樂融融與天倫之樂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為一個母親,她并沒有完全的自主權,并不能真正保護自己的兒女。因為她是太后,必須為國家謀利益,她的一言一行都要服從國家利益,她的首要任務是綿延國祚,而不是保證自己兒女的幸福與安全,從這點來看,趙太后何嘗不是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母親呢?
眾所周知,趙括是“紙上談兵”的主人公,秦趙長平之戰,他因空有理論而無實戰經驗,平白葬送了自己和四十萬同胞的生命。千百年來,“紙上談兵”使他成為眾人口中的笑柄,但人們并未因此貶嘲趙括的母親,而是贊揚與欽佩這位遠見卓識、深明大義的女性。《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記載:“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愿王勿遣。’”[1]1876趙括母親深諳趙括的秉性和缺點,在對比分析趙括與其父親趙奢的特點后,敢于公開兒子的隱秘,指出兒子用兵之道的弱點,希望趙王收回令趙括為將的成命。她不僅關心兒子的性命,更關心趙國的命運,她站在民族立場上,表現出一個卓絕女性對國家深深的關懷。她的智慧是“從人生的細節洞見人性弱點,并且是從國家從百姓的角度去觀照國家存亡的大智慧”[2]。可是,趙王最終并未采納她的建議,仍然派趙括出兵,她因此發出了一聲飽含無奈與絕望的嘆息:“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1]1877在嘆服趙括母親敏銳洞察力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同情她的遭遇。這位母親無疑是最無奈、最悲痛的人:縱然她再聰明、再有先見之明也敵不過君王的一句圣旨,不能使家國利益得以兩全。
二、犧牲自我的悲劇色彩
為奪取政權,劉邦和項羽上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楚漢之爭。劉邦知人善用,項羽剛愎自用,垓下一戰,劉邦戰勝項羽,奪取政權,已是歷史的抉擇。而在那個年代,就有一位睿智而崇高的母親,深諳歷史大勢,以死來堅定兒子跟從劉邦的政治決心,她就是王陵之母。《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項羽怒,烹之。陵終與高祖定天下。”[1]1603王陵的母親處在項羽的強勢壓迫下,仍沒有向項羽妥協,因為她深知項羽嗜殺成性、驕傲自大,也深諳劉邦寬厚仁愛,將來必能取得天下。為了不使兒子受到牽連,亦不使其有所顧忌,她選擇用死亡堅定兒子的忠君之心。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一位崇高而剛烈的女性所具有的品質:不畏強暴、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以及對兒子深切與無私的關愛。她以母親的直覺、母性的剛烈堅定了兒子依漢擊楚的政治抉擇,體現著悲壯與崇高的審美范疇。
另外一個犧牲自我的母親,不像王陵母親那樣悲壯和激烈,但仍然值得一提,她就是介之推的母親。介之推是晉國國君晉文公的救命功臣,但當晉文公回國登基、論功行賞之時,卻將他忘記了。介之推于是打算功成身退,到山中歸隱。《史記·晉世家》中記載了母子倆商量歸隱一事時的對話:“‘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1]1322可以看出,介之推之母無疑是希望兒子能夠光宗耀祖、飛黃騰達的,但是,當她聽說兒子不愿同朝中佞臣相處而企圖歸隱時,卻未加反對,而是“與女偕隱”,認同并堅定兒子歸隱的決心。介之推的母親舍棄了能使自己榮耀顯貴的生活,為的只是讓兒子保持高潔的品格。“正是因為有如此深明大義的母親,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潔之士。”[3]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品格高尚的母親仍然未躲過命運的殘酷:最終母子隱遁深山,葬身火海。這確實是一段慘烈的史實:母親以犧牲自身利益堅定兒子的選擇,用生命的代價保持兒子的獨立人格,可謂用血淚譜寫了一支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
三、成為政治斗爭犧牲品的悲劇色彩
在《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呂不韋列傳》中記載了秦始皇的母親。兩千多年來,人們常常視秦始皇母為生活糜爛、禍國亂家的反面形象,然而,作為一個母親,在她的身上也有著難以言說的無奈與痛苦,彰顯著濃重的悲劇色彩。秦始皇母因嬴政即位而貴為太后,變成秦國形式上的最高統治者,但秦始皇母子所面臨的形勢卻是十分嚴峻的:嬴政尚小,太后無任何根基,處于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下,他們的政權隨時都有倒臺的可能。因此,為了鞏固母子的權威與地位,太后與呂不韋私通,為的正是尋求呂不韋的支持。在此期間,呂不韋的勢力日漸膨脹,不久便成為秦始皇母子的潛在威脅。面對危局,太后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借機拉攏扶植嫪毐來制約呂不韋。在太后的提攜下,嫪毐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就成為可與呂不韋分庭抗禮的重要力量。而此時,太后那久被政治壓抑到谷底的內心情感竟被嫪毐激起,與其生下了兩個兒子。于是,嫪毐憑借著與太后的特殊關系和自身的地位積極培植私人勢力,企圖發動政變。在這危險時刻,秦始皇發現了嫪毐的陰謀,先發制人,鏟除了嫪毐集團。處在盛怒之下的秦始皇,毫不猶豫地處死了兩個年紀尚幼的同母異父胞弟,而此后,他同母親的關系也是名為母子,實同路人。縱觀秦始皇母親的一生,可謂辛酸至極:她中年喪偶,為了兒子的江山,不得不忍辱負重,以身事人;雖貴為國母,卻無力保護自己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兒子之間刀劍相向、骨肉相殘的煎熬。她雖在秦始皇年幼時竭力為其穩住江山,卻始終不能使秦始皇理解自己。最終,她只能在深深的孤獨與悔恨中度過自己的余生[4]。可以說,秦始皇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斗爭犧牲品。
四、異化的人性悲劇色彩
除了敘述正面的母親形象之外,司馬遷還塑造了一些反面的母親形象。她們有的專橫殘忍,有的玩弄權術,有的糊涂偏私,有的利欲熏心……在她們身上體現的是異化的、畸形的母愛,她們失去了人性中的真善美,釀造了一幕幕人性墮落和道德淪喪的悲劇。
在《史記》中,司馬遷僅為一位女性專門作了傳,她就是呂后。呂后以一位女性政治家的角色立于男性史林之中,其身份之尊貴自不待言。但同時,她也是一個典型的處在傳統社會政治中心的母親,她深知“母以子貴”的道理,并以此將自己的兒子同其政治目的牢牢地綁縛起來。呂后,用其一生踐行著“母以子貴”的觀念,并因此獲得了顯赫的權利與地位。然而,一件事情的背后往往顯露出它的另一面,呂后的做法固然使她達到了政治目的,但政治同人性的締結,終究使得她的母愛呈現出異化的狀態。呂后百般呵護其子劉盈,為的就是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馳”[1]1918,這是后宮女性誰也無法擺脫的命運。呂后深知此理,故在劉邦因她年老色衰而將萬千寵愛集于戚夫人一身之時,她更加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與權利。而此時的戚夫人,年輕貌美,恃寵而驕,對呂后的政治利益構成了不小的威脅。同樣深知后宮規則的戚夫人,憑借其受寵日加的籌碼,整日在劉邦枕邊啼泣,想讓劉邦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于是,一場爭奪皇位的斗爭在呂后和戚夫人之間展開。呂后雖不及戚夫人得寵,但她懂得謀略,知道運用政治手段獲得寵幸大臣的扶持,最終獲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事情并未就此結束,處在勝利喜悅之中的呂后,依然對戚夫人懷恨在心。因擔心戚夫人東山再起,威脅她的政治地位,呂后竟使用慘無人道的“人彘”刑法將其殺害。然而,呂后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她運用謀略和權術千方百計守護的兒子,卻偏偏毀在了自己的權謀之下。目睹生母的殘暴,劉盈提心吊膽,惴惴不安,他開始放任自我,整日“日飲為淫樂,不聽政”[1]274,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五年,劉盈終因不堪重壓,與世長辭。權力異化了呂后,也異化了她的母愛,她不僅將自己推向陰冷黑暗的內心深淵,更將兒子的錦繡前程毀于一旦。殘毒陰險的呂后,失去了人性的真善美,她正是政治權欲支配下,人性與母性異化的一個悲劇。
同樣處在政治漩渦之中的母親還有《史記·晉世家》中的驪姬。驪姬倚仗獻公的寵愛,利用各種手段使自己的兒子奚齊成為太子。她在獻公面前極進讒言,詆毀陷害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致使申生自殺,其他公子流離失所,嚴重危害了晉國的社會秩序。然而,君王駕崩之后驪姬終因失去倚靠而無法在男權社會的政治里生存,兒子和自己被殺。驪姬畸形的母愛使自己墮入人性深淵,并最終難逃悲劇的命運。
呂后、戚夫人和驪姬的生平不禁使人扼腕。男權政治下,女性身份卑微,個人價值與地位的獲得,同其兒子密不可分。身處后宮的她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寄希望于兒子,讓兒子成為她們立足后宮的工具。她們需要做的,就是參與政治斗爭,為其子謀劃未來,因為她們深知子貴母貴、子榮母榮的道理。社會的悖論,性別的不平等,將她們推向殘酷而慘烈的政治斗爭,迫使她們從一位仁愛的母親一步一步走向異化的深淵,不自覺地深陷其中,成為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
五、結語
憑著對歷史的尊重、對女性的尊重,司馬遷突破了傳統歷史觀念的束縛,把這些母親清晰地融入《史記》,讓她們得以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他筆下的母親以不同身份、不同姿態、不同處事方式亮相,風姿有別,各有特點。無論是濃墨重彩還是簡筆勾勒,司馬遷都力爭展現她們最具個性的一面。她們身上所籠罩的悲劇色彩各有各的不同,卻都令我們為之動容。正面的母親形象身上,有著和諧的精神生態、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健全的心靈世界,身處悲劇色彩籠罩下的她們,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閃耀著人性之美;而在反面的母親形象中,我們透過她們的行動,可窺視到種種異常行為背后暴露的社會現實,從而悲嘆使母愛異化、人性異化的男權政治。《史記》中的母親群像,包含著司馬遷對人性和歷史的思考,這些傳記作品中展現的濃重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不僅是其進步歷史觀的體現,也是他面對天道是非的詰問與抗爭。千百年來,當讀者閱讀這些作品時,也深深被這些母親形象所打動,思索著生命與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