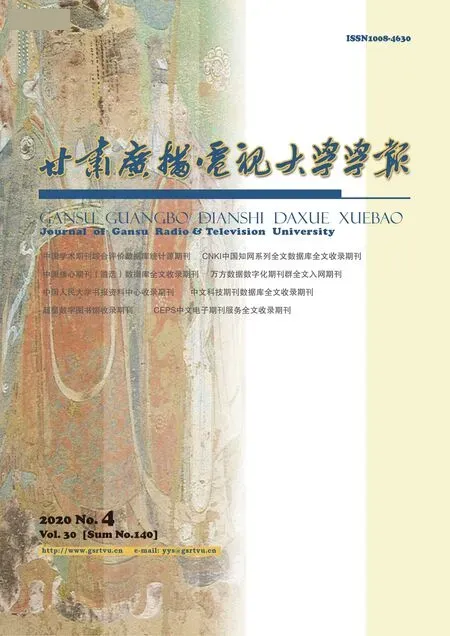敘事藝術中的沉默與發聲
——讀王小波《青銅時代》
周啟星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研究生院,北京 102400)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壇生態中,文學已然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寫作傾向,個人化現象較為明顯,文學流派漸趨式微,文學不再鮮明地呈現出某種集體意識,而是以作家的個性化寫作立場和風格贏得評論家及大眾讀者的注意力。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的集體出現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文學正走向敘述的成熟,但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現代稿酬制度以及網絡文學的興起,作家們大多對宏大歷史的書寫采取繞行的態度,或將其作為敘事大背景鋪陳在個人化的敘事視角之中。而王小波的敘事藝術呈現出多重時空背景和人物分層,看似眾聲喧嘩且令人眼花繚亂的敘事技巧背后,是作者面對文學生態所作出的選擇,敘事控制中表達自己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態度。
一、多重敘事的自由與集中
王小波小說中獨特的敘事方式和結構特點——多重的敘事結構及表達立場,并非是他所有小說敘事構篇的常規手法,而只散見于他的少數幾篇小說之中,但卻有著完整而臻于成熟的藝術呈現。這樣的敘事特點在王小波的早期小說《綠毛水怪》中初露端倪,到了小說集《青銅時代》(收錄《萬壽寺》《紅拂夜奔》《尋找無雙》)中,則顯示出一種自覺的刻意追求。
讀王小波的小說,不難感覺到他的筆下灌注著一種似閑散任意,實嚴肅誠懇的格調,使讀者自以為可以很切實地把握他的思維,但卻又實在無以言喻。造成此種狀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小說在敘事上的多重表達,真實與虛假交織網羅以及文本情節的隨意跳躍往往容易使人動搖自己的立場而迷失在小說的多重世界里。
在《綠毛水怪》《紅拂夜奔》和《尋找無雙》這三部小說里,都出現了一個名叫“王二”的人物。王二作為小說人物貫穿在王小波的絕大多數作品中,而他們的多處陳述又常帶有作者直接發言的性質,他常以非人格化的觀點來申訴具有作者人格化的言論,彼時或可將他視作作者的替身。正如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一書中所提出的:“在他(作者)寫作時,他并不是創造一個理想的,非個性的‘一般人’,而是一個‘他自己’的隱含的替身。”[1]80誠然,所有的描寫都不可能是客觀的,因為描寫本身便是一種自主觀出發的行為,文學更不可能全然做到所謂客觀、非人格化。那么,讀者進入文本的過程,其實是辨別作者所說的話的過程,尋找王二何時充當了作者的第二自我,何時只純粹作為故事中人的身份而存在。但即使王二時而承擔了作者的一部分意識,他與作者仍舊遠遠不可混為一談,不過,我們未嘗不可以從王二這一人物及他所牽連出來的整個故事世界,來探看布斯所說的“隱含作者”。王二不僅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作者還將敘事的工作推給了他,那么他勢必蘊含了“隱含作者的精華和思想規范的核心”——“風格”“基調”“技巧”[1]83三者的一部分。
王二在敘事中擔任了三重角色。第一,故事的敘述者。王二是以第一人稱“我”自稱的,他在故事中講述著別人的故事,以一個近乎全知的視角進行敘述。第二,故事的參與者,即他自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在《綠毛水怪》里王二的篇幅很少,是旁觀者與傾聽者。在《紅拂夜奔》中“王二”這一形象,則幾乎平行于故事的主人公紅拂與李靖而存在,這就形成了故事的雙重營構。作者把講故事的人推到了臺前,并且講故事的人也同時參演著故事,變成了故事中的一個主人公,甚至牽帶出了他周邊的世界。在《尋找無雙》里王二出場的頻率比較少,但也同樣兼任著講述與參演的雙重身份。第三,作者的代言人。在王小波的小說里,作者并不是客觀地只講述不發言,也不是讓人物通過正常可靠的渠道講出作者想講的話,讓讀者感覺不到是作者在發聲,而經常是作者搶過敘事者的話筒自己發聲。此時,王二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甚至可以將他的聲音當做隱含作者的聲音。
這樣的小說敘事結構看似閑散,但作者的控制方式和控制力度卻表現得自由而強勢,作者既給了敘事者所述故事中的純粹主人公一個話筒,又給了敘事者一個話筒,同時自己還在幕后握有一個話筒,并且操控著話筒的發聲時間、音量以及話語的虛實。比如《紅拂》中王二雖以第三人稱有限視角,講述著李靖與紅拂的情緣糾葛、王二與女友小孫的生活,而講述的內容和幅度卻被作者控制著。由于并非全知視角,便給分析、評論留下了可能和空間。在《青銅時代》中經常會出現作者以王二的話筒發出的對事件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立場有可能不同于故事中的純粹主人公,這種立場到底是王二的還是作者自己的又很難分辨。能明顯地感覺到的是,敘事者越位兼任了主人公,作者打破了沉默發表議論,這便造成了多重敘事表達的局面。
二、敘事控制的表達及其效果
多重敘述的小說技巧給文本帶來了超越單一敘述場面的繁復效果。
首先,文本跳躍一方面帶來了情節分裂和時空錯位,造成故事主人公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感,而作者的控制也在同時消彌著這種距離感。
比如《紅拂》有很大的篇幅只講李靖與紅拂,語言較為現代化,并時常涉及某些現代物質語詞,單線敘述之流暢冗余過之,使讀者幾乎要忘記了王二與小孫的故事線,但是李靖與紅拂告一段落之后,文本又轉回到王二與小孫。唐朝、當代,李靖紅拂、王二小孫就這樣互相穿插并行,兩條線分屬于中古與現代,他們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毫無聯結的可能,但是作者通過講述視角的轉換和文本的跳躍,使他們在小說中相遇。這種敘述轉換和跳躍的手法也可見之于王小波其他的小說中,其方式或是講完一個完整事件后的直接跳躍,或是因同一個話題將兩條線上的人物相提并論,通常以后者居多,以至于很巧妙地彌合了時空之間的距離,消除了跳轉之間的突兀。如《尋找無雙》中有這樣一段:
大家就高叫:“魚玄機,沒出息!怎么能講這種話!!”魚玄機回嘴道:“真是豈有此理!你們怎么知道該講什么話!……難道你們都上過法場,被絞過一道嗎?當然,當然,講這些話不對。最起碼是很不虛心啦”。
據我表哥說,死刑犯中,原來有過一些很虛心的人。……還有一位老先生,被判宮刑。當眾受閹前他告訴劊子手說:“我有疝氣病,小的那個才是卵泡,可別割錯了。”他還請教劊子手說:“我是像豬挨閹時一樣呦呦叫比較好呢,還是像狗一樣汪汪叫好。”不要老想著自己是個什么,要想想別人想讓咱當個什么,這種態度就叫虛心啦。[2]576
這是由魚玄機被處死時的場景轉移到王二表哥的講述,牽引的線索是“虛心”這一話題,這樣的跳轉無疑是完美的,盡管時空跨越非常之大,但是讀者絲毫感覺不到它的不合理,作者正是通過敘述者的聯想進行故事上的穿梭,而這種穿梭并不是空無依傍的,其內部有著緊密的邏輯關聯。
其次,眾聲喧嘩的噪音事實上合成一種背景輕音,從而突出作者獨立意志的獨白。
王小波自覺的思辨思維與包容意識,決定了他的小說是營造眾聲喧嘩的話語場,正調與反調相碰撞,主調與雜音相伴生,甚至是多種互相抵牾的聲音的“不齊聲”合唱。巴赫金在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提出了“復調”的概念,即小說中“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3]4,代表不同的價值觀念以及情感態度,這正是王小波小說的結構模式。所不盡相同的是,王小波小說中的各種聲音并不擁有獨立平等的地位,也不是“直抒己見的主體”[3]5,而是在作者統一意識的支配下彼此爭勝,或是妥協。而在文本多種表達的背后,讀者總能聽到一個作者的話語意志,而它是單一,也是實質性的“獨白”。
在王二自白式的解說中,讀者實際上可以判斷出作者的臧否意向。多種聲音的爭論無非只在同一層面上,可以看做一個問題的幾個方面,作者可以提供選擇,也可以表明自己的選擇,但最終擺出來的卻是整個問題,多個聲音其實是一個合音。
在小說《尋找無雙》中,無雙存在的證明以及無雙下落的探明過程久經波折。作者演繹了宣陽坊各位老板的反應變化、王仙客從懷疑到堅定的過程,讓各種不同的聲音同時顯現。最終王仙客知道了無雙的下落,但也說“我估計王仙客找不到無雙”,“尋找無雙”的過程是一個探尋真理的隱喻。實際上,王小波在這篇小說里借尋找無雙之題發揮,揭露智慧被愚弄、真實被掩蓋的遭遇[4]。
再次,通過主體間不同聲音的表達造成觀點同等地位的假象,在控制敘事中限制道德判斷。馬克·科里在《后現代敘事理理論》一書中選取了《愛瑪》和《化身博士》的例子來說明“通過敘事視角控制距離的敘事原則是用以控制道德判斷的一種手段”[5]130,將敘事者與敘述內容之間的結構距離轉化成道德距離。而《化身博士》中“把時間距離當成道德距離”[5]131則是這一手段的一種變型策略。
王小波的小說除了利用第三人稱的敘事視角以及時空上的距離來限制對人物的道德判斷之外,還通過敘事弱化人物的性格形象。小說中的人物在敘述中升華為多種理念的呈現以供選擇,這未嘗不可視作是王小波利用控制敘事來控制道德判斷的一種創造性策略。他放任文本中的各種觀點,組織觀點之間的爭論,但最終不給出明確的裁決。對于人物的各種行為或思想,小說中并無明確褒貶,以致小說只限于理智及概念上的爭論,并不涉及道德層面的批判或褒揚。
《尋找無雙》通篇涉及到事物存在與合理性的問題,這一點在小說中表現為王仙客與眾老板之間的分歧對立。無雙是王仙客的表妹,但由于早年失散,王仙客只好苦苦尋找。由于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無雙的身份,宣陽坊里的各位老板先后把魚玄機和彩萍當成無雙來糊弄王仙客,而實際上他們是先讓自己相信這兩個女人就是無雙,再讓王仙客相信她們就是無雙。
他(孫老板)有一種很生動的思想方法,雖然我不這樣想問題,但是我對它很了解。……該無雙(彩萍)不清不楚,把她當真的就不合理。但是她又在大院子里吃香喝辣,作威作福。你樂意看到一個假無雙在吃香喝辣,還是真的在那里吃香喝辣?當然樂意她是真的——所以就讓她是真的好啦。這樣倒來倒去,什么不合理的事都沒了。[2]616
在孫老板們的世界中,事物存在與否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合理性判斷,他們自覺消除不合理的事物,同時賦予存在的事物一個自以為合理的理由。而王仙客則堅定地相信客觀的存在,鍥而不舍地尋找無雙,最終從羅老板的口中逼問出了無雙的下落。對于無雙是誰以及她究竟存在與否,王仙客與眾老板與其說是把持著兩種觀念的人物群體,倒不如說是他們已虛化成兩種不同的世界觀的象征物。
此外,老板們毫無理性地從現實出發隨意改變觀念認知的思維方式,以致于歪曲理念,枉顧真理。但作者在小說中沒有在情節上對其施以懲罰,也沒有通過王二之口進行道德批判,而只是將其具象化地加以解說,讓讀者看清其本質,進行自由選擇。亦是借敘述者之口對事理進行剖析,消除文本距離引發同情,以限制道德判斷。
三、敘事訴求的隱與顯
任由多種論調自由爭論,而不明確表明作者的好惡傾向,同時限制作者對小說中人物的道德判斷,這在文本表面似乎是作者對待思想的民主態度,但小說中是否真的沒有蘊含作者明確的傾向?作者又是否真的中立而不倚?這顯然是值得懷疑的。
從容掌握判斷及立場選擇上的“隱”與思想精神上的“顯”,讓讀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文本所表達的內涵及其價值,這是王小波敘事的一大意圖。以低調寬松的姿態表達極具個性化的精神訴求,營構自由民主的敘事場來實現自己主觀的精神意志是其小說的特色。而王小波最終的創作意圖在于表達自己對現實以及某些超越現實的事物的看法,又不致成為道德說教或者單純的判斷。
在敘事方式上,王小波創造了王二的角色代替他間接敘事,實際上就把作者的發言位置后撤,敘事視角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自由轉換,小說中的“我”并不完全代表作者,讀者與作者的距離不即不離。被敘述者可以反思,敘述者可以反思被敘述者的反思,而作者可以通過對這兩者的有效調動進行更深層的思考,自由地出入文本,隨時選擇沉默或發聲,構成遞進式的“看與被看”的關系。作者在創作的同時監視著自己的寫作,自覺地把握著隱與顯的分寸。若要沉默則全交由被敘述者推動情節或者發出聲音,有時也讓敘述者越位制造情節;若要發聲便經由王二之口說話,第一人稱的表達又容易引起話語主權的模糊,所說的話到底是出自作者還是王二難于分辨。這反映出王小波對話語權威的回避態度,也是作家對于主觀表達有意規避的寫作姿態,防御的卻是作家內心強烈的自我意識。王小波選擇這樣一種含蓄的方式與他個人在文革中的經歷,以及20世紀90年代整體的文學生態環境有莫大關聯。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生態,顯示出一種對于主流話語權的自覺回避,更加傾向于個人性格邊緣敘事,即使是諸如陳忠實、賈平凹、蘇童、余華等當代主流文學圈的作家們,也大都選擇將社會宏大歷史作為虛化背景,而進行個人化或者地域化的小視角邊緣敘事。文學的大主題記錄與干預現實的功能,相比于此前的“歸來者作家群”、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時期較為減弱。主流文壇內的作家對于歷史和現實敘事態度的選擇,也影響到了王小波在文壇中發聲的方式。王小波在小說中使用的敘事策略,表明他自居于主流文壇之外的邊緣位置,來進行個人化的言說。
而市場化的寫作對于忠實于寫作本身的作家來說有著不容忽視的沖擊。寫作不再是作家全然主觀的事業,而必須考慮到讀者的審美需求,以及怎樣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甚至不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讀者。這意味著作者很難隨心所欲地說自己的話,而是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把握言說的技巧,讓自己說的話有人聽,并且愿意聽。面對市場化的寫作生態,王小波的敘事策略是在小說中制造多重敘事分層、時空跳躍以及充滿知性的觀點穿插,散發出個人的寫作魅力,贏得一大群的閱讀追隨者,也就爭取了一定數量的話語對象,以此進行具有接受可能的發聲行為,最終實現他從容地表達自我的敘事目的。
“隱”是一種敘事策略,正如李銀河說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天真爛漫嘴無遮攔的孩子,他解釋及揭示的對象正是世故的大眾習性,民族性的思維弊病。崇尚至高的理性,用理智來面對現實人生,沖破所有被社會積淀成破壞人類真誠本性的教條規則,是他鋒芒所指。“隱”的目的是為了“顯”,這兩種敘事技巧的嫻熟運用,在文本中虛擬了一個民主的敘事場域,以敘事者身份轉換的方式自由表達。此外,敘事視點在虛構的歷史人物與當代人物之間往復推拉,既創造了一種別樣的歷史書寫范式,又以歷史指涉當今,擔當起“批判現實”的知識分子的責任[6]53,在獨立的精神世界中呼吁民智與理性,重建價值判斷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