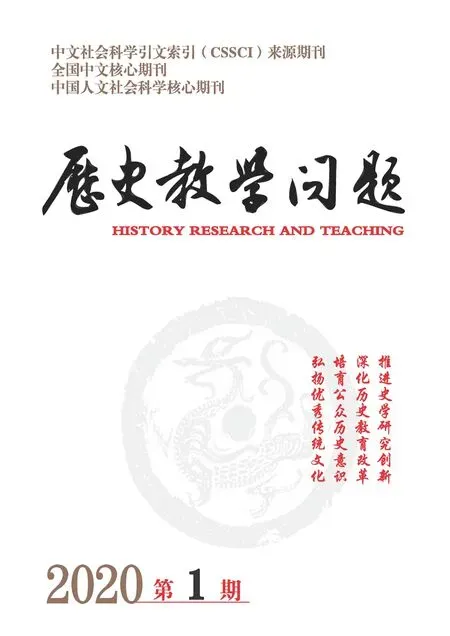記憶的戰爭與戰爭的記憶
——有關20 世紀中期中國的回憶與書寫
唐 小 兵
對于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及其紛爭,構成了當下中國人自我理解和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參照。記憶從來就不僅僅關乎過去,它更關乎對當下現實的理解與詮釋,更影響著對于未來的想象與展望。阿倫特曾言: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類將不能達到縱深。①阿倫特:《何為權威》,《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譯林出版社,2011 年,第89 頁。對于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闡釋,在近十多年來成為知識界與公共文化界的熱點。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 年》、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傅國涌《1949 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等著作都或從宏觀的歷史變遷、或從知識人的微觀生活等視角共同構建了我們的“一九四九”記憶。而本文從幾冊風行一時的公眾史學作品和回憶錄切入,來檢討有關這段內戰歷史的“記憶之爭奪”,以及在當事人社會體驗中的歷史真實,從而從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政治文化的視角進一步深化對于20 世紀中期中國的理解與闡釋。
一、“信史”與“痛史”之間
“‘卡空’里‘胡子’多,②據張正隆研究,偽滿時期,日本人在城邊修了條環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長春圍城期間,這條圈道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真空地帶,老百姓叫“卡空”。國民黨往外趕,共產黨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夾在“卡空”里餓死的。詳見張正隆:《雪白血紅》,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第505 頁。搶吃的。一口井他們霸著,怕老百姓給喝光了。莊稼地也霸著,誰也不準進。白天晚上打槍。我有個侄女婿不聽邪,也是餓急眼了,晚上想弄點毛豆,去了再沒回來。人們擼樹葉子吃,成牲口了。樹沒皮沒葉,草剩個桿,有的地方桿也不多了。嘴都吃綠了,人都吃綠了。一家一堆,擠擠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里呆著。鍋呀,盆呀,車子,被子,活人,死人,到處都是。8 月,正是最熱的時候,日頭那個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窩雞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著爛著,骨頭白花花的。有的還枕個枕頭,骨架子一點兒不亂。人餓了,開頭腳沒根,渾身直突突,冒虛汗。餓過勁了就不覺餓了,暈暈乎乎,飄飄悠悠,像騰云駕霧似的,不覺得難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東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搶。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沒有。能說話時,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一聲聲都像是‘餓呀’、‘餓呀’。沒聲了,眼睛有時還睜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沒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睜了,還喘氣兒,像睡著了,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燈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著還像笑模悠悠的,更嚇人。”①張正隆:《雪白血紅》,第505—506 頁。這是長春圍城的幸存者之一于連潤在接受軍旅作家張正隆口述訪談時回憶起的場景。饑餓、死亡、尸體等各種慘絕人寰的景觀,經過歷史書寫者的筆觸,將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不幸與痛苦,直觀而觸目地呈現了出來。這是被宏大歷史所有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小人物的歷史。
作為另一種歷史親歷者的國民黨憲兵王鼎鈞,在其晚年著述的名噪一時的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部《關山奪路》中如此評鑒其初讀張正隆此書的震撼:“長春圍得久,東北垮得快,我們身不由己,腳不點地,離東北越來越遠。長春圍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圍城的詳情所知無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饑餓慘象,前所未見。古人所寫不過‘羅雀掘鼠’、‘拾骨為爨、易子而食’,張正隆以現代報道文學的手法,用白話,用白描,用具體形象,為人間留信史、留痛史。人類歷史的進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輔相成,視野遼闊,寄托深遠。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么多,到底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②王鼎鈞:《關山奪路》,三聯書店,2013 年,第207 頁。“信史”是就歷史真相而言,“痛史”則是就經歷了歷史變動的個體的命運和苦難而言,以及后人讀史時與前人心靈相通而感同身受的那一份苦痛。前者突破謊言回歸真實,后者拆解偽善重建道德,形成不同代際之間的情感和倫理上的連帶感。
戰爭與革命是20 世紀中國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題,而對戰爭與革命的歷史書寫和歷史記憶,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性的命題,而同時是中國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的歷史、進而很可能刺激記憶領域的紛爭與沖突的導火線。任何對歷史的表達,都隱含著一種對現實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試圖突破歷史記憶固有框架的書寫,往往會引發公眾和政府層面強烈的反響或反彈。《雪白血紅》在20 世紀80 年代的末期出版,幾乎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卻因為龍應臺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現在世人的眼前。龍應臺以一個作家的敏銳和文化名人的號召力,將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東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當代華人世界的感覺世界之中。然后,龍應臺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親愛的,我百思不解的是,這么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么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道、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為什么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于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么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么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③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 年,第200 頁。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個小插曲,而這本轟動一時的作品主要是通過文獻梳理、歷史遺跡尋訪和口述訪談等多種形式,還原或重構了國軍將士(包括遠征軍)在亂世中的命運,尤其此后被歷史刻意遺忘的一面。
作為“戰敗者”的后代(其父龍槐生系國軍將官),龍應臺試圖為被歷史敘述遮蔽的這群人爭回一個應有的紀念位置:“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么,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④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扉頁。龍應臺試圖站在一個人道主義的立場和非戰的立場,為一切戰爭的失敗者和受害者提出一種控訴,但“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是什么?它是一個基于現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諸人權)的普世價值,還是個人因參與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具有尊嚴的特殊性內涵,龍應臺語焉不詳;再者,龍應臺將內戰時刻的國共紛爭造成的犧牲與苦難(這種內爭很難在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之間劃出一道明確界線)與抗日戰爭過程中的南京大屠殺、反法西斯戰爭的列寧格勒保衛戰并置在一起進行討論,以后者在公共領域和國家層面大規模的歷史記憶來映照前者的被“遺忘”,就等于抹殺了不同類型的戰爭之間的差別性。這種“以失敗者為榮”表面上是以對“弱者”和“卑賤者”的人道主義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但其實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緣、團體的身份認同為核心而構建了承認的譜系,其中隱含了一個未必能夠不證自明的預設:失敗者天然就代表正義。
歷史記憶更深刻地指向為父輩討還一個歷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際之間的記憶傳遞和一個民族的心智結構。阿倫特曾言:“回想過去和從消散中收聚自我在這里等同于‘懺悔’。引導我回憶、收聚和懺悔的不是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對存在源頭的追尋,追尋‘創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記憶超出了跟動物共有的感覺能力,逐階上升,趨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達‘記憶的營地和宮殿’。”①阿倫特:《愛與圣奧古斯丁》,王寅麗譯,漓江出版社,2019 年,第97 頁。對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國共雙方也同樣致力于各自記憶宮殿的建造。長春圍城,在國共兩方的記憶里呈現的是幾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對國民黨而言是屈辱體驗,對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凱旋。這凱旋中間又夾雜著“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開掘這段歷史的真實面相。與記憶相對應的是遺忘,但正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所言,遺忘并非純粹“消極性”的心靈生活,而“遺忘研究給歷史學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歷史:原來我們所能了解的歷史史實,不過是被種種力量篩選過的、幸存下來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實,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們的記憶庫之外了。我們無法了解的那些,有相當一部分是前人認為不應該或不值得為后人所了解的。我們不知道的過去,固然可以稱為失憶(amnesia),或曰歷史記錄的空白,但這種失憶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遺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積極行為的結果,是符合前人預期的”。②羅新:《遺忘的競爭》,《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 年3 月8 日。對長春圍城,或者更廣泛的20 世紀中期中國的內戰史,我們都可以從“記憶”與“遺忘”的雙重視角去探測。有時候“記憶”與“遺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強迫遺忘而另一方就要強化記憶,有時候記憶與遺忘是相生的,在遺忘“非正義的戰爭暴力”的前提下發揚勝利者的記憶,有時候勝敗兩方都是刻意要從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歷史的痕跡,讓民眾“積極地遺忘”甚至不去觀看某部分歷史區域的真相。自然,民眾和知識人并非木偶,他們有時候會從這重重歷史記憶和遺忘構建的“存在之網”中掙脫出來,去復原對歷史的真實感知。
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陸兩個歷史學者那里引發了完全不一樣的回應。已故歷史學家高華為此書撰寫的長篇評論《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縱橫捭闔,文采斐然,將臺海兩岸在1949 年前后的大變動,從政經大脈絡和歷史人物小視角展開分析,結合龍應臺的記述將“悲情一九四九”的歷史內涵及其后續影響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出來。高華對此書評價極高,認為該書的基本特點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復雜,場面宏大:從1949 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臺到臺灣,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③④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領導者》總第34 期,2010 年6 月。高華進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價值觀,來反思1949 年由國民黨政府的大失敗而引發的國內一部分人群的大遷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龍應臺在書中著力描述了被意識形態宏大話語長期遮蔽的一個個歷史場景,討論了一系列與1949 年相聯系的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但是她不直接評判那場內戰的是非功過,而是重點敘述那些內戰的犧牲者及1949 來到臺灣的人群,對他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④高華抽繹出龍書的價值核心是“普世價值”,而其歷史觀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觀”,并充分肯定這種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歷史敘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導的意識形態敘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華看來,龍應臺將“內戰的是非功過”的價值評判懸置了起來,因而是在一種人道主義心情之下的歷史寫作,將所有戰爭的受難者與幸存者都放置在歷史記憶的天平上同等地書寫。但龍應臺自身又特別標舉其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那么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是龍應臺認同失敗者的價值、思想與行為,還是僅僅因為他們是戰爭中的敗者因而容易被賦予同情的視角?如果如龍應臺所言,戰爭無所謂勝負,那么何以她又旗幟鮮明地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種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和聚焦小人物的歷史敘事中試圖實現歷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強烈地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國之哀與國共兩方中選擇站隊。這豈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高華對這個癥結有精彩的詮釋(未知龍應臺本人是否同意):“國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使自己猶如空中樓閣般的脆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1949 年初陳誠奉蔣介石命接掌臺省主席一職后,痛定思痛,宣稱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臺之理念,從‘三七五減租’著手,將社會基礎夯實,開始新的出發。顯然,臺灣以后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與其失敗相聯系的,龍應臺不會為國民政府1949 的大流亡而驕傲,她是為臺灣人從失敗后站起來,又開出新價值而自豪。”①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專治“1949 之學”的史家林桶法在一篇討論國民政府播臺影響的文章中說:“經過60 年后如何看待1949 年?從歷史脈絡而言,1949 年的逃難潮為臺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移民精英,無疑對臺灣是一股動力。許倬云在檢討1949 年前中華民國結構上的缺失時提到:‘這結構的上層在1949 年移植于臺灣,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品質不差,我指的是農復會、臺大、經濟部,這些干才,他們在臺灣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比大陸上好。’”②林桶法:《1949 年的迷思與意義》,《思想: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2009 年第13 期。楊儒賓也指出:“臺灣無從選擇地接納了一九四九,接納了大陸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負皆收。結果短空長多,歷史詭譎地激發了臺灣產生質的飛躍。但獨坐大雄峰,誰聽過單掌的聲音?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人員因素也因進入臺灣,才找到最恰當的生機之土壤。在戰后的華人地區,臺灣可能累積了最客觀的再生的力量,其基礎教育、戶政系統、公務體系的完整都是中國各地少見的。”③楊儒賓:《1949 禮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34—35 頁。
相對于高華對《大江大海》的極度推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楊念群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很尖銳地抨擊龍應臺在該書中的歷史觀為“炮灰史觀”:“所有戰爭,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并不是靠單純的人道主義告誡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龍應臺這位年近花甲、見多識廣的‘小紅帽’在踏入歷史叢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與她觀點相左的狼外婆,但結果是‘小紅帽’太強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洶涌的修辭順利擊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島山打根集中營里虐殺國民黨軍戰俘的臺灣監督員,與血戰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線國民黨軍隊,密集沖鋒不顧死活的解放軍士兵,統統變成了飄散到戰爭塵埃中的悲情線偶,由歷史的偶然所操控,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峽的恢弘敘事,揭開的是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口’,讓他們血跡斑斑地盡情噴灑,然后任由記憶的血水灌流進當代人麻木的心里。為被踐踏、被侮辱傷害的失敗人群立傳,結論當然是戰爭根本沒有什么勝利者。當交戰搏殺的暴力被不論輕重、不分界線地指責,任何戰爭的意義都會從此徹底消解,‘炮灰論’剎那間炸出人們的眼淚,‘正義論’對勝負的書寫當然就會在淚水中變得模糊不清。”④楊念群:《龍應臺炮灰史觀的煽情與闕失》,共識網,2013 年12 月15 日。換言之,在楊念群看來,這種訴諸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的歷史敘述,所構建的其實是在本質上無差別的悲情故事,等于是完全消解了戰爭的意義,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說獻身戰爭的將士的生命主體性。每場戰爭的卷入者都成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戰場上死過一次的當事人,還得在歷史記憶的領域以“復活”的方式在“生命意義和價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楊念群質疑龍應臺在搜尋史料并構建歷史敘述的時候,自動剔除掉了那些與其“人道主義的立場”相悖的證據,從而也就失去了真正進入歷史的可能性。
這觸及的其實就是面對20 世紀中國的中期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各執己見的個體經驗的書寫與記述究竟是會推動歷史和解還是其實在阻礙歷史的和解?歷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戰爭創傷如何撫平?我們是否能在具體地理解投身戰爭的個人的心情與境遇的基礎上來討論個人與時代的相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著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歷史記憶和歷史書寫在人際、代際、黨際之間的對話與和解中應該和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吳乃德在一篇討論二二八事件的文章中曾如此談及歷史記憶的真實性與模糊性之間的關系:“為了和民族當前的想象和渴望產生共鳴,歷史記憶必須加以剪裁。‘記憶’和‘歷史’因此經常不完全重疊。‘集體記憶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對某一個事件作歷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復雜性,是從疏離的立場、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觀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體記憶則將歷史中的模糊加以簡單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簡化的、甚至錯誤的歷史記憶,不論它負載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訓和啟發,顯然違反理性社會對真實的追求,而且也將不斷受到歷史學者、后代,特別是不同立場者的挑戰。同時,模糊的歷史記憶或能點燃某些人的熱情,卻必然失去對其他人的號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場的團體具有不同的歷史經驗,模糊的歷史必然無法成功地營造共同的歷史記憶。而共同的歷史記憶卻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或許——只是或許——如某些歷史家強調的,‘除非歷史記憶以學術標準為基礎,否則我們對記憶的責任只是一個空殼。’”①吳乃德:《歷史記憶中的模糊與未知》,《思想》2012 年第21 期。
龍應臺似乎也意識到了歷史寫作的局限性。她在書中坦承:“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國土,那么復雜的歷史,那么分化的詮釋,那么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么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語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達呢?……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以偏概全’的歷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②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74 頁。吳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歷史記憶”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歷史被裁剪、壓制、刻意引導、遺忘等之后形成的“籠統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體的歷史變動之中其實很難給其行動一個道德上的裁斷。這隱含的一個預設是歷史書寫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對自身在道德、價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這種偏向可能導致的對歷史認知和歷史闡釋的誤導,應該存有一份冷靜的反省。③Timothy Brook 教授也曾指出過:“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準則,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識。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出錯誤的觀點來抨擊過去的歷史參與者或現在的讀者,而是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準和條件以便進行研究。”詳見氏著:《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譯,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281 頁。史華慈曾說,歷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對“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義上的復雜性”。龍應臺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回看歷史,并且意識到了自己只能相當個人化地傳輸“以偏概全的歷史印象”,但其為“失敗者”寫痛史的心志過于強勁,為父輩做傳的心情過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記了其回溯歷史的初衷而抹掉了歷史與人性的復雜性。越是充滿對復雜性的理解的寫作和記憶,就越不可能讓讀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數的讀者試圖從歷史中捕撈的記憶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認同與情感。人在歷史長河試圖打撈的往往是他翻轉的身影。這就是歷史與記憶之間永恒的張力。
作為戰敗者的國軍,對于臺灣島的本土居民而言,卻又是強勢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層層弱者,這就導致正義與倫理的界定變得異常艱難。在前引許倬云等人認同的大陸上層精英引入臺灣的積極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來,卻是強烈地壓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的政治參與。
筆者曾經在討論中國大陸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歷史和解”問題時提出:“對于社會共同體的自我更新和文化傳承來說,讓記憶呈現出來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別艱難的事情。記憶自然不是為了煽動仇恨,而歷史寫作更非如此。記憶更多的像一個民族的自我療救,而講述本身也成為一種不斷修復一個社會集體創傷的獨特形式。”④唐小兵:《讓歷史記憶照亮未來》,《讀書》2014 年第2 期。我想,這個議題對于兩岸知識人、政治人物和民眾而言,具有相近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所以應該在一個更為寬廣和縱深的視野里來開掘其價值、探尋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二、歷史與理性之間
對于1945—1949 年之間的戰爭記憶,或許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超過有著國民黨憲兵身份后來轉為作家的王鼎鈞的回憶錄《關山奪路》。此前對于這部分歷史的絕大部分記憶來自知識人的書寫,包括對這段歷史的重構,也相當部分是以知識人為對象的,比如錢理群《天地玄黃:1948》、傅國涌《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或者是一些史家的研究性著作,比如蔣永敬、汪朝光、楊奎松等人的專著。《關山奪路》從一個軍人的經驗和視角出發,將抗戰結束到中共建政之間的這段歷史描述得極為真實生動,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教授所言:“作為歷史學者,我對文學家寫的回憶錄素來比較警覺甚至排拒,而《關山奪路》卻讓我感到意外的驚喜。文學的求美、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解,王鼎鈞先生以回憶錄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來。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平心靜氣,卻觸及靈魂。”①王奇生:詳見《關山奪路》封底推薦語。王鼎鈞在《關山奪路》的后記里談及他寫這部回憶錄的原則:“我寫《關山奪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這四年(指1945—1949)的經驗太痛苦,我不愿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寫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②王鼎鈞:《關山奪路》,第272 頁。因此,王鼎鈞對臺灣的“反共文學”、大陸在文革結束后的“傷痕文學”都不認可,認為這些都太膠著于個體的生活經驗。就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而言,王鼎鈞認為歷史寫作不應該僅僅是“自傳”,而應該是以自我為媒介來為自身“受想行識”的時代立此存照,尤其是為“一代眾生的存在”以及20 世紀“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留下可靠的記憶。依照王鼎鈞先生的自述,《關山奪路》在寫作結構上隱含了“對照”“危機”和“沖突”的線索,全書讀下來確實讓人酣暢淋漓而處處又別有洞天發人深省。《關山奪路》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冊,整套回憶錄在有關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中位置極為重要,從不同視角和側面展現了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起承轉合。高華教授生前曾撰文如此評述:“王鼎鈞這套書的前兩本寫作者的青少年時代,后兩本橫跨戰后的1945—1979 年,緊扣冷戰歲月國共的熱戰和武力對峙,以‘人、歲月、生活’為經緯,用簡練優美的文字,寫盡被時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艱辛、蒼涼和辛酸,又跳出個人局限,在時局大動蕩中展現人與時代交融的復雜狀態。而作者在當時或事后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彌足珍貴,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個人自傳,具有豐富的思想性,故此書既有歷史價值,還有很高的思想價值。”③高華:《他何以選擇離開:王鼎鈞〈關山奪路〉讀后》,《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08 頁。
就其大體而言,《關山奪路》一個最重要的角度就是“歷史的反思”,或者說從理性的視角出發來思考國共成敗之因果。這可以說是整部回憶錄的“主線”,而這種反思和議論又往往建立在作者個人的經歷和直觀感受基礎之上,所以不會顯得空洞抽象。例如國共兩黨行事方式的差異,王鼎鈞在講述了內戰時期的很多歷史現象后說道:“國民黨辦事‘執簡馭繁’,社會組織已經形成,已經運作,國民黨順應這種運作,依賴由運作產生的樞紐人物,掌握樞紐就掌握了社會。地主是佃農的樞紐,資本家是工人的樞紐,校長是學生的樞紐;一個校長等于全校學生,一個地主等于全村佃戶,一個廠長、董事長能抵他旗下一千個工人。國民黨注意拉攏這些人,重視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也偏重照顧這些人的利益。共產黨不怕麻煩,反方向而行,它搞‘農村包圍城市’、‘小魚吃大魚’。它結合貧農,不要地主;它結合工人,不要資本家;它結合學生,不要教育部長。一部總機下面有一千具電話,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電話機不通。它在全民抗戰的號召下,理直氣壯地去組織學生和農民,因為上陣打仗要靠多數,不能靠少數。等到民眾組織成功,軍隊訓練成熟,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當務之急是一齊動手摧毀那些樞紐,重組社會,痛快淋漓!”④王鼎鈞:《關山奪路》,第188 頁。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窺見在王鼎鈞的認知世界中,國民黨是依賴社會中上層的具有保守特質的精英主義政黨,而中共卻是依靠底層大眾的具有激進性質的反精英主義政黨,前者依托于社會固有結構來運作,而后者卻要制造出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這確實把握住了兩黨在社會層面上的差異。⑤詳見王奇生、唐小兵《20 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中的相關討論,《東方歷史評論》2013 年第4 期。亦可參閱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一書。王鼎鈞在南京時曾與蘇北、魯南的難民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對于中共土改的具體運作過程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中共要徹底改變這個社會,第一步,它先徹底掃除構成這個社會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優勢,第一是財產,第二是世襲的自尊,兩者剝奪干凈,精英立時變成垃圾。人要維持尊嚴,第一把某些事情掩蓋起來,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釋,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脫褲子’,脫掉他的褲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財產,他從此必須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經參加革命,親友也和他劃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滅。”⑥王鼎鈞:《關山奪路》,第65—66 頁。
前述是兩黨對地方精英的態度和方式的差異,而對于青年學生而言,王鼎鈞在書中著墨也不少。在他的記憶中,左翼文學的敘事,對于處于苦悶中的青年尋找人生和國家的出路形成了一種極有吸引力的敘述。據其回憶,“我們那一伙文藝青年,得意的時候讀老舍,老舍教我們冷諷熱嘲、幸災樂禍;失意的時候讀魯迅,魯迅替我們罵人;在家讀巴金,巴金教我們怎樣討厭家庭;離家讀郁達夫,他教我們怎樣流亡,怎樣在流亡中保持小資產階級的憂郁,無產階級的堅忍,資產階級的詩情畫意。”①②③④⑤⑥⑦王鼎鈞:《關山奪路》,第116 頁,第118 頁,第119 頁,第167 頁,第78 頁,第78 頁,第92—93 頁。文學如何與政治結合形成一種對青年人的影響力,王鼎鈞也有深入的洞察:“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令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面,讀書會揭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違法而不公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臨門一腳。”②而左翼文學在青年讀者那里召喚出來的集體心態,王鼎鈞也始終記憶猶新:“這些大作家以及他們的詮釋者、鼓吹者,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他們咒詛權力財富,制造困局,顯示改進無望,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毀滅的快感。”③王鼎鈞認為,正是這些牽引人心的左翼圖書和讀書會,與中小知識青年在大時代的命運的碰撞,才激發出波瀾壯闊的學潮。學潮塑造英雄如書中所云的于子三,但更多的青年學生卻在學運中喪失學業、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在王鼎鈞看來,青年是內戰時期兩黨爭奪的對象,也是兩黨爭相利用的工具,這一段話無比沉痛:“‘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里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志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么狹隘的視界,多么簡單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殘酷的判斷,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報。如果是現在,我會說,學潮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④在政黨與青年之間,王鼎鈞選擇站在青年一邊,而在弄潮兒與沉默者之間,王鼎鈞選擇站在沉默者一邊,在歷史事實與人文理想之間,王鼎鈞選擇站在理想這一邊。
作為回憶錄的《關山奪路》在歷史敘述上展現出了幾重張力,而這些張力或者說敘述困境的存在,恰恰豐富了作者的敘述層次,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對讀者固有的認知歷史框架構成了挑戰。從對國共兩黨成敗之因果的探尋來說,王鼎鈞對作為失敗者的國民黨及其軍隊似乎并沒有同情,他費了最多的筆墨試圖尋找強弱轉化之道。就戰敗的日本與國民黨、蘇聯軍隊三方而言,他對于作為勝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義上的認同,反而有意選擇對戰敗者的“尊嚴”做更多的記憶與書寫。因此,王鼎鈞的歷史記憶的價值基點就不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邏輯(當然,縱覽全書,他始終對弱者、失敗者有同情感),也不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霸道邏輯,這就提出了一個饒有意義的挑戰:面對20 世紀中期的戰爭記憶,我們的立足點究竟應該歸置在何處?這場戰爭能夠用正義與非正義來嚴格區分敵我雙方嗎?道德的模糊性與情感的強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攪拌在一起,沖擊著我們理性的堤壩。比如書中第一部描述的抗戰勝利后“日俘日僑”這一節文字,作為戰敗者的日軍勉力維持其體面和尊嚴,保持著整潔和秩序,沒有悲情吶喊,更沒有搖尾乞憐,以至于作者說“無論如何,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⑤而與之相對照,王鼎鈞對國民黨軍隊持負面的評價:“戰地軍官,軍權至高,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換一個新官位,他的部下經過改編整訓,槍口換個方向,不是死在這個戰場上,就是死在那個戰場上,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優于’那樣的軍人。”⑥而作為戰敗者的家屬,日本女性通過出售物品、叫賣食物來維持生活,換回回歸日本的旅費,順從中介人的擺布為中國軍官提供性服務從而為日本男人維持尊嚴。
而與之相應的是,作為勝利者一方的表現卻讓人齒寒。據王鼎鈞敘述,美國用原子彈轟炸了日本廣島,蘇聯這才出兵攻入東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蘇軍繼續推進,占領東北全境七個多月,劫走的工業設備價值美金20 億元,劫走的金塊價值美金30 億元,劫走偽滿時代的紙幣軍票,回頭套購物資。在東北境內發行紅軍票97 億元,敲骨吸髓。王鼎鈞寫到這里情不能自已:“蘇聯大兵在火車電車上公開奸淫婦女,中國女子剪發束胸,穿著男裝,沈陽的朋友曾經把他太太變裝的照片拿給我看。這樣的軍隊,這樣的勝利,居然還允許有這樣的紀念碑!蘇聯在東北的行為沒有國格,然而中國的國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東北人的屈辱。”⑦這究竟應該算是弱者的悲哀還是強者的悲哀?王鼎鈞的歷史記憶充分地展現了面對歷史時人的情感倫理的復雜性。從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來說,中國的抗戰自然是正義的,但這種正義并不能保證在此之下中國軍民的舉止行動就是合乎正義或者倫理的,而作為戰敗者的日軍及其家屬,在這場戰爭記憶之中,似乎并不是被同情的弱者,卻成就了“弱者的尊嚴”,仿佛成了應該被戰勝者一方來尊重的對象。勝利并不天然象征正義,而失敗也并不必然代表屈辱。王鼎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對人的理解、態度和情感,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嗎?我們可以在一種消泯了個人的國家身份的前提之下,認真地對待歷史中每一個具體的個人嗎?對戰爭的歷史記憶能夠構造我們與那個時代之間內在的連帶感嗎?如果超越了控訴史學或者成王敗寇史學,那么史學又有怎樣的意義?當我們順應這種對失敗者進行充分理解甚至尊重的邏輯之后,反思和批判是否就會成為搖搖欲墜的空中樓閣?換句話說,對戰爭各方的記憶,其能夠抵達的歷史目標和道德目標究竟應該是什么?
東北戰局是決定國共兩黨勝負之關鍵,從1929年到1948 年的20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元老齊世英負責東北黨務,對抗戰后東北政局變遷之內情不乏洞察。他生前在接受沈云龍等人的口述訪談時說,中共過去在東北的組織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張家父子時代就絕不優容,張作霖在北平就曾抄過俄國大使館、殺李大釗。就是日本進占東北也是反共,而偽滿又是執行日本的命令。“我們在那里辦黨務知道得最清楚,因為過去知道他們的力量微不足道。俄國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東北淪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當、方法不對,也須承認。尤其勝利后,東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傾向中央,只要中央給點溫暖或起用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樂意為國效勞。可惜中央處置不當,事與愿違,終給共產黨以機會,利用東北的富源、人力、物力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打到廣東。我們今天痛定思痛,是應該自己反省的。”①《齊世英口述自傳》,齊世英口述,沈云龍、林泉、林忠勝訪問,林忠勝記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 年,第192 頁。而在齊世英看來,戰后最大的用人不當就是讓江西籍官員熊式輝做東北行營主任長達兩年,對此,齊世英講述起來也是痛心疾首:“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部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聿明、孫立人合作。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熊式輝本人也搞了幾手,以后在香港、曼谷糟蹋了不少,就是連現在在美國的某人(姑隱其名)也是出了事用人頂替才跑掉的。而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于不能收容偽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②《齊世英口述自傳》,第190 頁。這與前引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中的敘述、觀察與分析恰可互證,東北之失,主要不在中共,而在國民黨自身的失誤和貪腐。一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一為國民黨普通憲兵,但都系這場戰爭的親歷者,有著沉痛的教訓和追問的動力,都彌漫出一種歷史反思的理性之光。
但在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教授那里,對故土東北的記憶,則更多的是彌漫著一種難以遏止的情感。她曾在接受上海《東方早報》的長篇訪談中如此闡釋過其歷史觀:“可惜的是,中國人到現在,因為歷史的傷痕和記憶,有太多的人需要不斷地解釋自己的過去、自己的生命歷程、自己的選擇,否定自己過往的生活。這是很令人傷感、很浪費的人生。”③明鳳英:《臺灣知名學者齊邦媛訪談:潭深無波〈巨流河〉》,《東方早報》,2013 年3 月14 日。在膾炙人口的回憶錄《巨流河》中,齊邦媛在引述了父親對東北戰局的追憶和反思后,如此表達其從一個女性視角的感慨:“‘溫暖’,在東北人心里是個重要的因素,那是個天氣嚴寒、人心火熱的地方,也是個為義氣肯去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東北全部淪陷,我父親致電地下抗日同志,要他們設法出來,留在中共統治里沒法活下去,結果大部分同志還是出不來。原因是,一則出來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則,九一八事變以后大家在外逃難十四年,備嘗無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漂泊,從前東北人一過黃河就覺得離家太遠,過長江在觀念上好像一輩子都回不來了。三則,偏遠地區沒有南飛的交通工具,他們即使興起意愿,亦插翅難飛。這些人留在家鄉,遭遇如何?在訊息全斷之前,有人寫信來,說:‘我們半生出生入死為復國,你當年鼓勵我們,有中國就有我們,如今棄我們于不顧,你們心安嗎?’”④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第325—326 頁。這段敘述既有理性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從情感視角出發對歷史的審問,尤其是對于那些東北子弟的出路及其困境的探討,充滿了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在這些敘述的背后,作者似乎代其父親背負著一種強烈的倫理虧欠感和負疚感。
結 語
人類學家王明珂曾經指出:“歷史不只有一種聲音;許多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人群,都在爭著述說自己的過去,爭著將自己的過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為當代的社會記憶,以抹煞他人的記憶。在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有些人可以向社會宣揚自己的過去,有些人的過去被社會刻意發掘、重建。這是對過去的詮釋權之爭,也是認同之爭,權力之爭。”①王明珂:《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1996 年第3 期。對于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無論是官方主導的歷史記憶,還是民間自發的回憶錄、口述史,或者作家、學者的歷史寫作,都試圖將自身對于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理解和認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這種寫作和記憶的情感動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義的價值立場,或者基于對歷史成敗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評悲憫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責理性化的反思,將淹沒在歷史結構和行動中付出生命的個體。尤有進者,有些學者甚至會認為關于這個時段的更多私人化歷史記憶(比如這些年大量出版的回憶錄、口述史等)的出現,非但不能推動人際、黨際、代際之間的和解,反而會進一步撕裂中國社會,導致歷史記憶的價值共識難以構建。②這部分的思考,得益于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博士的一次深入討論,謹致謝意。而就對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苦難的認知與記憶而言,我們自然不能停留在對于政治和戰爭悲劇的控訴層面,而應該深入歷史的肌理,將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背后的潛在的結構性因素挖掘出來,這才是歷史記憶和歷史寫作的更高境界。歷史記憶或者歷史寫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每個人摸到的雖然只是一個“片面的局部”,卻不乏深刻的具體性,而當每個歷史回憶者和寫作者意識到自己可能是“盲人”(會有個人的偏見、知識和信息的限制、表達能力和記憶能力的欠缺等),而大象卻是一個難以被一次性完全觸摸的整體的時候,他就會相對謹慎、謙卑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寫作。對20 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無論是龍應臺的歷史寫作,還是王鼎鈞的歷史記憶,都不乏在當代中國的公共生活中通過引入歷史資源來進行啟蒙的動力,這里特別值得深思的一個有價值的主題就是:價值啟蒙是否必須以尊重歷史真實為前提?揆諸歷史與現實,我們會發現啟蒙與歷史之間存在永恒的張力,而這種張力和困境引發的爭執甚至沖突也經常在當代中國的公共生活中掀起驚天巨浪,攪動人心。或許,這才是我們追溯、檢討和寫作這一頁歷史的時候不得不小心對待和處置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