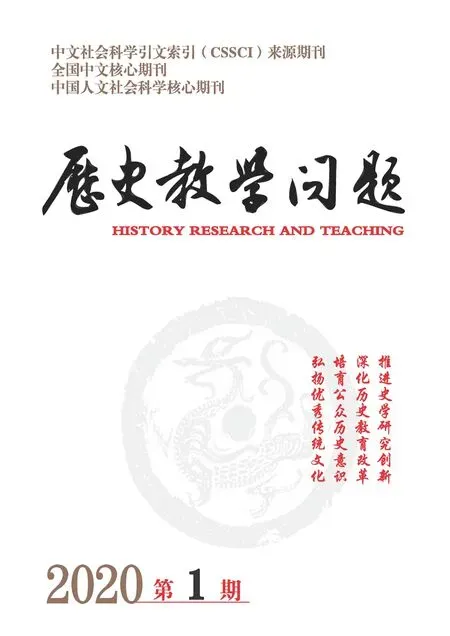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研究與反思
王 若 穎
1928 年,陳東原撰寫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著作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反對壓迫婦女的產物,它開創了中國婦女史研究。①在《中國婦女生活史》問世前,徐天嘯《神州婦女新史》于1926 年出版,但其影響力與代表性遠不及陳著。《中國婦女生活史》的問世意味著開始專門有學者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來審視中國婦女的生活,而且它是第一部真正富有影響力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著作,中國婦女史研究自此開端并且繼續發展。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婦女史研究集中圍繞婦女解放運動問題進行并且出現了一大批相關史料編纂成果和研究專著,研究成果可謂豐富多彩。②鄭永福、呂美頤:《60 年來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大象出版社,2013 年,第258 頁。20 世紀90 年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再次有所突破,當時先有一批海外學者采取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婦女史。③當時以高彥頤(Dorothy Ko)、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曼素恩(Mann Susan)、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賀蕭(Gail Hershatter)為代表的一批海外學者將社會性別理論引入中國婦女史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轉變不僅強調重新發現婦女的歷史,同時也要求將男性以及兩性的互動放入研究視野中,有關中國婦女問題的歷史研究因此開始從婦女史研究轉向性別史研究。新的研究強調應用社會性別理論并且開拓了研究范圍、豐富了研究內容、挖掘了更深層次的研究意義。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很快被譯介到國內,緊接著性別研究成為了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范式并且最終促成了中國新婦女史研究開花結果。④“新婦女史”是指改革開放后興起的具有西方女性主義色彩和新社會史特征的婦女史,參見鄭永福、呂美頤:《60 年來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第257 頁。如果說傳統婦女史研究在歷史中重新發現了婦女,那么新婦女史研究則更注重探究和反思女性的歷史背后所隱藏的問題及其意義。因為研究方法根本不同導致新、舊婦女史研究存在分歧,傳統婦女史研究通常對女性群體做整體性研究,而新婦女史研究則發掘具有特點的女性小眾群體做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深描,例如明清時期的賢媛才女等等。因此中國婦女史研究前后呈現割裂狀態,這樣會妨礙中國婦女史研究學科的整體發展。⑤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中已有關于女工、女學生和女伶等等成功的研究范例,但那些研究對象大都是在晚清之后才出現的、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因此很難將她們與中國傳統女性做更多的聯系,這種現象正是筆者所謂中國婦女史研究發展的割裂與阻礙。那么應該如何開展新的研究并且推動中國婦女史研究繼續發展?下文將以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為例,分析和討論研究中國婦女史應該如何把握宏觀問題意識、采取合適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并且嘗試為解決現存的問題提出建議。
一、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
研究婦女史能夠幫助人們在歷史中重新發現婦女并且重新認識她們,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也不例外。“母親”一般是對承擔了生育職能的女性的統稱,所謂生育職能指的是生產和養育孩子的兩種行為,大多數女性自懷孕開始自覺承擔起這兩種職能,但也有一部分母親們或只承擔了二者其一。雖然現實生活里并不僅僅是母親來承擔撫育后代的責任,例如費孝通的雙系撫育理論就強調父親的撫育職責和作用,但只將“母親”作為一種婦女史的研究對象、將“母親”的定義和內涵框定在婦女史研究的范圍內,則可以將“母親”視為一種承擔了生育職能的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母親”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女性所擁有的個體身份角色,它賦予了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而且“對生命的呵護與持守,這是女人共同的東西,盡管做起來是一個人一個人獨立完成的”。所以“母親”也是女性的一種群體身份角色。直到今天由女性承擔生育職能作為一種社會性別分工和勞動分工仍舊沒有發生改變,母親一直受到各種文化的贊美,這種對女性的肯定在人類共同且漫長的父權制文化中顯得例外,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更是如此,因為在中國這個地方母性是高于女性的。①李小江等:《女人:跨文化對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03、404 頁。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就是要挖掘“母親”作為個體身份角色所承載的女性生命故事,同時研究“母親”作為群體身份在歷史中反映出的女性的整體命運。而且進行任何有關中國婦女問題的歷史研究并不是要僅僅填補女性的歷史失落,而是要實現重新認識、解釋歷史以至重寫完整的兩性同創共享的中華史的目標。②杜芳琴:《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6 頁。
目前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研究通常涉及女子教育、生育育兒、國家干預和文化建構四個方面。有關女子教育的研究主要討論賢妻良母主義和母性教育問題,其中有關賢妻良母主義的研究最多,因為它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們最早提出的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思想主張。呂美頤認為“賢妻良母”曾是中國女性的傳統形象和生活的基本范式,但直至1905 年左右才真正形成一種在社會上流行的概念,賢妻良母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衍生物,但它不僅要求女性要繼續履行傳統賢妻良母的義務,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義務、為善種強國做貢獻。③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爭論》,《天津社會科學》1995 年第5 期。余華林認為盡管賢妻良母主義在五四以后遭到批判,但人們無法否認母職和母性對于女子的重要性,因此人們還是主張以尊重母職、提倡母職為中心的新觀點來代替賢妻良母的舊觀念。④余林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賢妻良母主義”論析》,《人文雜志》2007 年第3 期。針對母性教育的研究一般是從思想淵源、教育實踐和學生態度三個方面開展的。叢小平認為近代女子教育植根于前近代女學傳統,早期女子教育主流的推動力是民族主義與傳統母教觀念的混合物,無論是精英還是國家均接過傳統女學中以母教繁榮家族的觀念引導女性接受教育。⑤叢小平:《從母親到民國教師——清末民族國家建設與公立女子師范教育》,《清史研究》2003 年第1 期。簡姿亞認為尊崇賢妻良母主義的女學實際上在構建新母性神話來替代舊母性神話,母性依舊被視為女性最重要的天職,母性依舊在遮蔽和剝奪女性的其他豐富多樣的生命需求。⑥簡姿亞:《近代新母性神話的建構:從身體解放到人格獨立——以辛亥時期女性媒介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2013 年第2 期。有關教育實踐的研究相對較少,通常是對學校實施的家政或家事課程進行考察。張麗研究發現清末女子初小就有家事課程,民國成立后家事科目成為女子教育的特色,內容涉及手工、園藝、縫紉、刺繡、烹飪和育兒等等,家事科目隨著女子教育的發展日臻完善并最終被正式納入了高等教育體系。⑦張麗:《民國時期學校家政教育初探》,華中師范大學2008 年碩士論文,第16 頁。徐婷婷對金陵女子大學的研究注意到其下設的家政系共分為三個方向:家庭藝術、兒童教育和營養學,家政系師資陣容強大且注重實驗和實習活動,學校希望學生能用系統的科學知識去管理家庭事物,進而管理社區乃至社會的事物。⑧徐婷婷:《文化沖突視角下的金陵女大研究》,曲阜師范大學2015 年碩士論文,第21 頁。有關女學生如何看待母性教育的研究最少,一般研究者們都默認女學生是母性教育被動的接受者,但也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馮慧敏認為母性教育的重點是培養女學生的家政技能而不是增長她們的職業技能,這會造成她們與男學生間的差距,最終導致畢業后難以就業,女學生群體成為了被動的受害者,而且母性教育促使人們認為即使是受教育的女性還是更適合回歸家庭,這本身不利于女子的發展,因此母性教育越來越受到女性的質疑與反對。①馮慧敏:《民國時期女子職業問題研究——以〈婦女共鳴〉為中心的考察》,河北大學2011 年碩士論文,第35 頁。
有關生育育兒的研究主要包括生育衛生、節育運動和生育觀念轉變三個方面,生育衛生研究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醫療衛生制度改革中有關分娩衛生的問題,何江麗研究了近代北京的生育衛生,發現直至1913 年以后北京地區才開始一面取締舊的產婆和接生方法,一面訓練新的助產士和提倡新法接生,再造“國民母親”要求將女性身體從屬于衛生的控制,國家話語企圖更嚴密地籠罩女性身體,以最終完成生育行為的社會化過程。但事實上市政機構未能將生育的過程嚴格置于行政管制之下,生育衛生仍然基于女性的自主選擇。②何江麗:《再造“國民之母”——近代北京生育衛生研究》,《歷史教學》2014 年第8 期。趙婧研究了近代上海的生育衛生,具體包括西方產科學的建立、以助產士替代舊產婆、分娩衛生的醫療化問題。她發現近代上海的分娩衛生改革使得時人拋棄了舊的生育觀念、認可分娩衛生是保護母性的有效手段,但本質上市政機構強調分娩衛生仍出于健全母體產生健全兒童的需要,所以在民族主義話語中,婦女的身體與健康只有在作為母性的一種具體表現時才有意義。③趙婧:《近代上海的分娩衛生研究(1927—1949)》,復旦大學2009 年博士論文,第26 頁。節育運動研究關注國家如何倡導改變民眾的生育觀念,俞蓮實重點以北京、上海、南京為例研究民國城市生育節制運動,重點介紹了運動在三地開展的情況,她認為生育節制運動實質上是用科學的手段構建現代母親角色,推動社會認同母職的重要性,同時這也造成母親養育子女的責任越來越重,但母親的社會地位和權利卻沒有因此而上升,最終導致意識形態的“母性”和女性主體經驗的“母性”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反差,以母性自由、生育自主權的獲得、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性別秩序的建立為主要目標的真正的生育革命并未實現。④俞蓮實:《民國時期城市生育節制運動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為重點》,復旦大學2008 年博士論文,第350 頁。有關生育觀念轉變的研究經常與節育運動的研究聯系起來,陳文聯認為五四時期接受生育節制思想的社會基礎較之此前廣泛得多,生育節制思想的內涵也不斷得以完善和提升,但民眾生育觀的現代化仍然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需要進一步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環境。⑤陳文聯:《近代中國生育節制思潮的歷史考察》,《中南大學學報》2007 年第2 期。另外,相關研究共同注意到了近代中國女性為履行母職所肩負的重擔,例如李揚的研究指出不同于父教重于母教的傳統,近代中國母親不僅要擔負起生育的責任,還被要求去學習各種新式的育兒知識,這無疑對母親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近代中國女性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新式母親必須要有足夠的能力,而在現實生活里很多女性因此陷入了困境。⑥李揚:《歧路紛出,何處是歸程?——民國時期知識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上的兩難選擇》,《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6 期。
有關國家干預的研究主要針對社會公育、社會保障與慈善救濟事業進行考察。社會公育的研究是考察國家如何通過舉辦公共事業幫助女性分擔母職,研究者們首先注意到社會公育思想的萌芽,潘曉飛認為近代中國兒童公育思想萌芽于戊戌維新時期并促生了近代兒童公育制度,但近代兒童公育思想片面強調公養和公育而不符合中國國情實際,無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⑦潘曉飛:《清末民初“兒童公育”思想研究》,安徽財經大學2013 年碩士論文,第38 頁。近代中國母親們的利益更依賴于公育制度的實踐,當時最普遍的實踐形式是舉辦公立幼兒園或托兒所。趙宇靜研究了清末民初幼兒教育機構的興辦狀況、師資情況和幼兒教育團體對兒童公育事業發展的推進。⑧趙宇靜:《清末民初幼兒教育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8 年碩士論文,第58 頁。王含含研究了南京民國政府時期城市幼兒園教育的實施情況,內容包括機構設置、機構性質、發展成果與啟示。⑨王含含:《南京民國政府時期的幼兒園教育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4 年碩士論文,第92 頁。馮蕾研究了戰后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托兒所以及戰后上海的兒童教養組織的情況。⑩馮蕾:《戰后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托兒所研究(1945—1949)》,上海師范大學2014 年碩士論文,第77 頁。社會保障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多,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有關保護母親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出臺及其實施情況。劉秀紅研究了1912 年至1937 年女工生育保障問題,發現通過婦女團體的推動和女工群體的主動爭取,女工最終獲得了南京政府頒布的《工廠法》在立法上對她們生育權益的保障。①劉秀紅:《社會性別視域下的民國女工生育保障問題(1912—1937)》,《婦女研究論叢》2015 年第6 期。張茂梅對清末民初中國婦女的法律地位進行研究并且分析了女性作為孕婦和母親在近代中國實施現代立法的整體過程中所受到的保護。②張茂梅:《試論清末民初中國婦女的法律地位(1901—1926)》,廣西師范大學2001 年碩士論文,第29 頁。有關慈善救濟事業的研究最少,一般只在整體研究中順帶論及有關母親的問題,相關研究都將國家對孕產婦的衛生指導、設立幼兒公育設施、舉辦兒童教育事業視為社會慈善救濟事業的一部分,這樣就與前述很多問題的研究有所交叉和重疊,只是相關研究更加突出和強調各項事業和措施的社會公益性質。
近代中國母親不僅會受到國家權力的規訓,還會受到文化的建構,馬川川對中國的母親文化進行了研究,但他的研究只是梳理了近代有關母親問題的思想潮流的產生及其嬗變,缺乏對有關母親的文化建構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③馬川川:《近代中國母親文化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3 年碩士論文,第210 頁。目前更多相關研究集中于考察近代女性報刊是如何建構有關母親的文化的,研究者們注意到報刊能夠通過傳播育兒知識幫助女性勝任母親的角色,同時女性讀者會主動參加報刊上相關問題的討論來表達她們承擔母職的感受。④陳瑤:《民國上海知識女性的家政生活——以〈婦女雜志〉(1915—1931)為中心》,上海師范大學2015 年碩士論文,第100頁。因此有一些研究指出女性在文化建構母親的過程中不是全然被動的,只要有適當的機會她們就會主動爭取自身的話語權并且參與到文化建構母親的過程中去。⑤馮劍俠:《女報人與現代中國的性別話語——以20 世紀30 年代“新賢良主義”之爭為例》,《山西師大學報》2014 年第5期。還有一些研究注意到“母親”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議題,近代中國隨著五四之后興起了一批廣為社會關注的女性作家,有關母親的文學形象、議題和作品也隨之陡然增加,女性對于“母親”的書寫反映出她們通過主動參與文化建構母親的過程完成對自我、性別以及生命的認知和表達。⑥此類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穎、盧升淑和朱凌的研究,具體研究內容可參考王穎《論中國現代女性小說中的“母性”命題》,《東方論壇》2011 年第4 期;盧升淑《現代婦女作家文本里孤獨、無力的母性——試論張愛玲、楊絳、蘇青、林徽因的母性書寫》,《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0 年第3 期;朱凌《“母性”的現代重構與結構——論張愛玲小說中“母性”形象的叛逆》,《東方叢刊》2005 年第3 期。
二、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反思
前述梳理了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研究的現狀,其中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突出的問題是目前已經有很多關于思想流變、制度革新、風俗改良和社會運動的考察,但很難在具體研究內容中看見鮮活的人,特別是本該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母親”往往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被忽略了。事實上絕大多數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研究成果只能被歸類為政治史、經濟史或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真正能夠稱作婦女史的研究成果很有限,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現有研究成果大都沒有采取和應用婦女史的研究視角、理論和方法,甚至針對該問題的新婦女史研究還是空缺的,目前急需填補這項空白。另外,新婦女史研究應用最普遍的三種基礎理論是女性主義、社會性別和后現代主義理論,因此在開展相關研究之前應該先熟悉這三種理論。首先,女性主義是20世紀早期開始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的主流社會中產階級婦女反對性別歧視、爭取男女平等的思潮。⑦蘇紅軍:《第三世界婦女與女性主義政治》,《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三聯書店,1995 年,第22 頁。書寫女性主義歷史意味著要詳細說明婦女的規范是如何被強加、被遺漏、被置換、被再強加或可能被廢棄的。⑧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沈齊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3 頁。其次,社會性別(Gender)是相對于生物性別(Sex)而提出的概念,它可以被視為自然的“性”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它通過在經濟、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建立起多層次的規范來確立男女各自在社會中的角色、位置和地位。⑨鄭永福、呂美頤:《社會性別制度與史學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4 年第3 期。瓊·斯科特(Joan W. Scott)將社會性別理論引入歷史研究范疇,她認為研究社會性別是要探究形成性別差異的全過程,這樣才能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結構、權力以及物質分配的特點,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重寫了歷史。①鮑曉蘭:《美國的婦女史研究和女史學家》,《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第79 頁。另外,福柯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對于女性主義最具有影響力,特別是知識權力形成理論和身體理論,前者旨在說明權力的實施創造了知識,知識本身又產生了權力,知識等同于權力;后者指出軍隊、學校、醫院、監獄、工廠這些機構為了增加自身力量,用紀律和懲罰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紀律與懲罰的實施就是為了制造馴服的身體。②李銀河:《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潮》,《哲學研究》1996 年第5 期。筆者強調掌握這三種基本研究理論是因為中國婦女史研究已經進入了以性別研究為新范式的新階段,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必然要做新婦女史研究,因為新婦女史研究能夠將研究視角真正放在“母親”身上,做新婦女史研究不僅有助于在歷史中發現“母親”,更有助于探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背后所蘊含的歷史意義。當然基礎理論應用于研究實踐過程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理清開展研究的理論基礎即弄明白采用什么理論更有益于實現研究目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應該如何具體開展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新婦女史研究呢?第一,可以用女性主義理論為指導確立母親為直接研究對象,還要以以母親為中心的研究視角和立場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第二,可以用社會性別理論為指導明確研究要探討的是社會性別秩序的轉變以及這一轉變是如何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的,并且借此探究近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權力是如何建立和運作的,這是各種具體問題的研究共同著眼的根本問題。第三,還可以用后現代主義理論為指導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母親們受到了怎樣的權力規訓和文化建構,還要反思女性自身對此的感受和態度。另外,在研究時需要注意到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特點及相應社會條件的變化,還要將不同歷史階段的問題聯系起來做比較分析。還需要注意到中國由于國土面積遼闊、人口龐大、民族多樣,造成不同地域的經濟、文化與風俗習慣歷來差別很大,加上近代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通商口岸城市和全國其它地區之間(特別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異更加突出,所以由于地理范圍不同而造成的差異狀況必須在研究時特別注意并加以考量。最后,研究還應該要關照現實,因為有關母親問題的研究正好緊密聯系著現實生活,2016 年1 月1 日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正式施行,國家開始鼓勵女性生育二胎,有關母親的作用、責任和地位的問題自然也被擺到了國家、社會和所有人的眼前,“如何幫助女性成為一名好母親?”成為了家庭、社會與國家共同需要思考、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現實的需要會促使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尋找有用的經驗加以借鑒,因此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歷史研究責無旁貸地需要增加一份關照現實的考量。
反思研究現狀能夠發現,目前真正缺少的不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的研究,而是將母親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新婦女史研究。應該如何突破這樣的研究現狀呢?筆者留意到,已經有學者做出了嘗試并且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果,2018 年4 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者盧淑櫻的研究專著《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書,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共分為四個章節,前三個章節研究了近代中國牛乳哺育的興起過程及其與近代中國母親的關系,最后一個章節探討了牛乳哺育問題背后折射出的近代中國母親的內心世界和她們所承受的歷史命運。縱覽整本書,作者以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哺育方式的轉變作為切入點,研究發現近代中國牛乳哺育的實現是近代中國嬰兒哺育方式轉變的結果,女性對個人、身體以至家庭制度的覺醒,為她們棄母乳、改用牛奶埋下了伏線。作者認為女子教育和就業問題導致婦女角色與母親角色的分離,這就意味著女性可享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種發展加速了哺兒方式的改變。盧淑櫻還認為哺育方式的轉變對于近代中國女性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這一改變幫助女性解放了一部分母職,這一改變會與傳統父權思想產生碰撞,這種碰撞與沖突越發突顯了社會上男女兩性對婦女角色期望的分別,最終掀起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別秩序對母親角色的重塑。③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年,第237、239 頁。雖然盧淑櫻在書中花費了相當多的篇幅來研究牛乳哺育在近代中國社會傳播和實現的過程,但她沒有僅僅局限于這個具體問題本身,而是借此將研究目光最終牢牢鎖定在接受和選擇牛乳哺育的母親們身上。作者特意以最后一章的內容來壓軸討論有關近代中國母親的問題,整本書研究的核心問題和最終的落腳點是通過分析牛乳哺育問題來探討近代中國母親所受到的社會性別秩序的重塑,因此這本書是將母親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新婦女史研究。這樣的研究在筆者目前所關注到的研究中還是一個孤例,所以特意在此將這本書作為一個最新的和成功的研究示范加以詳細介紹。
盧淑櫻在這本書中得出的最終研究結論是:婦女的哺兒經驗反映了在建立現代新型國家之際,國族主義及科學話語代替了儒家學說繼續規范著婦女的思想、行為和身體。理想母親形象與實際母親經驗的差距反映出,在現代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兩性對母親角色的分歧意見,縱使20 世紀前期中國的政治、社會及文化變動為婦女帶來不少機遇,但她們始終未能突破母親角色的傳統框架。這樣的研究結論看似有些悲觀卻非常具有價值,因為它不再迎合和默認過往的相關研究一致對近代中國婦女解放事業作出的全盤肯定,而是客觀看待和分析了中國女性在近代歷史中的真實處境。盧淑櫻的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國女性在五四運動以后被社會新文化教育要追求自我解放并且成為新女性,但同時她們又不可能拒絕個人家庭需求、社會性別文化傳統和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對于女性提出的生育要求,因此近代中國女性被國家、社會和所有人默認既要成為新女性也要成為新母親,從而導致女性需要承擔的母職越來越沉重。盧淑櫻的研究結論不僅新穎而且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她的研究充分證明了筆者前述針對中國近代母親問題做新婦女史研究應該采取的意識、視野、理論和方法的思考是能夠成立和實現的。但是一本書的研究內容畢竟有限,也不可能盡善盡美,特別是盧淑櫻的研究只是從牛乳哺育這一個方面來論證近代中國母親所受到的社會性別秩序的重塑,顯然還不夠充分并且顯得不夠有說服力。可是研究任何問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盧淑櫻的研究應該被視作一個突破,除此之外,應該期待更多針對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新婦女史研究能夠得以全面展開和深入發展。
三、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意義
梳理和反思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研究是為了推動相關研究的繼續發展。那么,重視和強調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有什么意義呢?首先,從促進婦女史研究發展層面來說,研究母親問題能夠觀察到一直以來為婦女史研究所忽略的歷史面相與細節。近代中國社會在男性知識分子們的號召和主導下尋求婦女解放事業的發展,而近代中國女性受惠于婦女解放事業的整體發展,具體表現為近代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能夠接受教育、自由戀愛和結婚、參加工作獲得經濟獨立甚至參與政治或軍事活動等等。但已經有一些研究指出,近代中國社會為了解放女性而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也會給女性帶來負擔和痛苦,例如19 世紀末中國社會興起的禁纏足運動,讓很多已經纏過足又需要重新放足的女性飽受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負擔和折磨,雖然這并不足以否定禁纏足運動本身的正確性和積極意義,但為爭得婦女解放事業整體發展而犧牲一小部分女性利益的做法在近代中國的很多人眼中是具有合理性的,這種觀念甚至得到后世很多婦女史研究者們的認同,因此更多類似禁纏足運動的消極影響這樣的問題就會在婦女史研究過程中被掩蓋,這樣做研究不僅無視了近代中國女性在歷史中的真實處境,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女性為歷史發展做出的奉獻和付出的代價。所以那些被既有研究忽略掉的中國婦女的歷史的另一面應該予以認真地梳理、分析與反思,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采取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開展新的研究,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恰恰是一個理想的題目。其次,從研究的宏觀意義層面來看,就如同著名女性主義研究學者李小江指出的:“你問女人有沒有共同的東西,我以為是有的,至少有兩點:一是自然的,就是生育;另外是歷史的,就是女人都曾經是‘第二性’,這也是女人不同于男人的最根本的差異。”①李小江等:《女人:跨文化對話》,第204 頁。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正是要借由這種女性共同的并且無法為時代所割裂的生命體驗和歷史記憶,去探究婦女群體內部和代際之間延續和共享的一種歷史及其所承載的力量和意義,做這樣的研究有益于彌合新、舊婦女史研究之間的分歧并且改變兩種婦女史研究彼此割裂的現狀。更重要的是,書寫有關母親的歷史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不僅僅是女性)從歷史中獲取有益的經驗并且加以借鑒,在人類文明固有的文化傳統里習慣將女性稱頌為生命之母、國民之母、文明之母,但所有的贊美只是在建構理想的“母親”,只有客觀地面對和反思有關母親們的真實的歷史的時候,人們才會意識到女性需要的不僅僅是對母親的理想頌歌,女性更需要的是國家、社會和所有人對于母親真正的理解、尊重和幫助,而這一切可以并且應該從研究有關母親的歷史開始。
最后,進一步說明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對促進中國婦女史和近現代史研究發展的意義并且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論。如果說近代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發展為絕大多數女性帶來了福音,那么近代中國母親們是否也一樣得益于此?從古至今絕大部分女性基于自然的性別分工必須成為母親并且承擔母職,因為近代中國女性一般結婚較早,而女性婚后一旦懷孕生子就將承受各種作為母親的責任與壓力,那么有多少女性在成為母親之后還能夠繼續享受婦女解放運動所倡導的受教育的權利、就業的權利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呢?如果近代中國女性被疲勞地束縛于母職,這能否說明無法解放母親的婦女解放運動對于全體女性的幫助是有限的呢?《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書的結論給出了一種回答:“二十世紀現代國家針對各階層的母親重申她們必須履行育兒責任,以達至治家興國、強國強種的目標,在‘雙重負擔’下職業婦女的解放可以說是虛假的。”①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第237 頁。這是唯一且正確的答案嗎?客觀地說僅僅憑借一本書的研究而得出的答案肯定是不完善的,那么就需要對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做出更豐富更細致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更多樣和更可靠的答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發展的積極成果是不容否認的,這是歷史事實,同時這也為既有中國婦女史研究所證明過了,因此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借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去質疑和否定近代婦女解放事業發展的成果,而是利用研究這個問題讓人們能夠以更全面的視角觀察近代中國婦女的歷史,這樣做也會促進中國婦女史研究更加以人為本。
本文主旨就是要說明和強調,目前我們需要更多有關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新婦女史研究,我們需要去認真聆聽母親們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留下的聲音,因為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其實就是在研究我們所有人共同的“母親”。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最終目的是要突破社會性別制度的遮蔽與限制,從而去發現母親們以及更多女性的生命力與價值,由此也昭示出了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意義所在及其一直以來的研究目標和發展方向。同時,審視和研究近代中國母親的歷史還會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提供全新的視角、思路和答案。自1898 年戊戌維新變法運動開始,梁啟超等晚清的有識之士們就將女性視為實現民族“強國保種”的對象,繼之,近代中國社會倡導婦女解放事業發展的男性知識分子們一直強調女性的生育價值對于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性。那么,在近代中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是如何肯定、重塑和利用女性生育價值的?在近代中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國家權力是如何規訓母親和母職的、社會文化又是如何建構母親和母職的?近代中國社會的女性作為母親是否接受、配合和參與了國家權力的規訓和社會文化的建構過程?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夠理解和說明社會性別秩序的重構在近代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影響,這正是研究近代中國母親問題的新婦女史應該做出的終極思考,這也是研究該問題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所在。另外,研究近代中國母親的歷史還有一種特別的現實意義,那就是,知道歷史給予過母親怎樣的價值、地位和意義,才能夠警醒和指導當下社會應該如何幫助女性更好地面對“成為母親”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