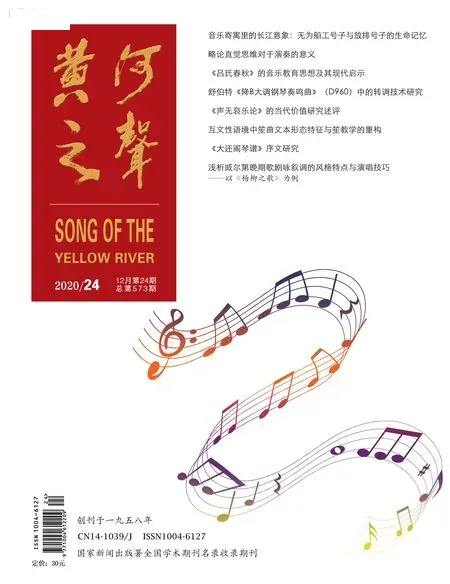論民族民間舞《詠荷》的創新藝術表現
彭子依 / 龔易男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民族民間舞在作品題材方面越來越重視進行更為廣泛的探索和嘗試去表現更為豐富的抽象和深刻的情感題材。因此其在舞蹈、音樂、音舞結合等方面都突破了傳統的較為單一和傳統的風格,呈現出創新藝術表現特點。《詠荷》就是一個比較有開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在炎熱夏天中荷花帶給人們一絲清涼,舞蹈清新脫俗,荷花扇在優美的舞姿中來回轉動……
《詠荷》的舞蹈類型屬于熱情的膠州秧歌,當地民間又稱“扭斷腰、三道彎,是漢族民俗舞蹈的三大秧歌之一。”[1]秧歌“本是南方勞動人民插秧所唱的勞動歌舞,隨著南北方商業貿易的往來傳至北方,同時吸收北方雜劇精華形成的新藝術形式。”[2]膠州秧歌分為小戲秧歌和作為主要舞蹈部分的小調秧歌,主要舞蹈動作有“‘翠花扭三步’、‘撇扇’、‘小嫚正反三步扭’、‘棒花’、‘丑鼓八態’等”[3]。膠州秧歌音樂是民族調式,以徵調式為主,輔助以商調式及羽調式的交叉調式,表現形式為別具特色的打擊樂演奏及嗩吶牌子曲和民歌小調。
一、題材的創新藝術表現
一個作品的藝術品位首先在于對題材的創新藝術表現。舞蹈《詠荷》題材來自“荷花”,描繪了荷花從綻放到風雨摧殘到盛放的整個過程。以電閃雷鳴象征民族斗爭中的壓迫,以荷花雨后綻放象征中華民族戰勝艱難困苦,重獲新生。但不同于其他大量舞蹈作品表現“荷花”作為花的清純柔美,《詠荷》可以說是用膠州秧歌的剛柔相濟表現荷花大氣豪邁的氣質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另一方面,《詠荷》不拘泥于傳統的中國民族民間舞擅長于情感表現的特點,作品還表現出“荷”雅致的藝術性與厚重的文化底蘊。因此可以說舞蹈《詠荷》對民族民間舞蹈的題材進行了創新的藝術表現。
二、舞蹈音樂的創新藝術表現
舞蹈《詠荷》的音樂《凌波仙子》選自著名作曲家史志有創作并獲中國時報年度民族音樂銷售排行榜第一名的民樂原聲大碟《水蓮》。音樂蘸取“蓮”之靈氣與風骨,運用六種不同音色的主奏樂器來表現六種著名中國蓮的曼妙風華。“花與樂的巧妙結合,使得六首曲作充滿了生動、細膩的表現力,將琴、簫、琵琶、柳琴、曲笛、笙、箏、排簫等樂器的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一一說出蓮花亭亭生妙香、超然于紅塵的絕美心田,說出賞花人那臨風觀蓮、了卻俗慮、更向清靜去的無限情思。”[4]“淩波仙子”是荷花、水仙等水養花卉的別稱。明代大才子唐寅的《詠蓮花》:“凌波仙子斗新裝,七竅虛心吐異香。”音樂主題描繪和表現的也正是舞蹈《詠荷》的情感。作品融合了中國傳統民樂的古典韻味與現代編配的藝術感染力:琵琶空靈的音色在樂隊深沉的效果的烘托下仿佛人與自然的對話;濃郁的民族氣息與時尚風格的巧妙融合又讓觀眾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和無窮無盡的聯想。
舞蹈《詠荷》的配樂在《凌波仙子》的基礎上重新創編,增加了以打擊樂民族鼓為主奏的節奏性的發展部,以及將人聲和音導入音樂的且轉調為G 羽調性的結束部。曲調方面用交叉調式的變化增加了情緒表現的空間。打擊樂演奏與交叉調式的調性布局讓舞蹈音樂充分尊重了膠州秧歌的音樂風格。音樂的節奏與旋律快慢結合且變化多端,在音色方面達到了完美融合的境界。舞蹈音樂的配器糅合了個性的民族樂器,現代的電聲樂隊以及經典的管弦樂隊,在豐富了音樂的音色的基礎上又巧妙解決了琵琶、曲笛這些傳統民族樂器音色的過于個性化的問題。音樂的曲式結構突破了傳統的民族音樂作品較為常見的單線條的一維結構,而是采用了復三部曲式的創新的立體結構。各個樂段的銜接揉入了旋律疊入、節奏性發展和復調織體等多種寫法,在節奏、調性、織體、配器、風格等方面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對比與發展,從而使得音樂整體既有極強的新意,又有較好的觀眾接受度。音樂對情緒的立體性的營造也突破了傳統民族音樂較為平面的情緒發展,達到了創新的發展高度,使得“凌波仙子”的情感與形象更為立體和豐滿,帶給觀眾強烈的精神震撼。
三、舞蹈語匯的創新藝術表現
音樂前奏開始時,舞蹈家雙膝并齊跪坐,向左下旁腰,左手背在腰間,右手握扇平蓋在頭頂,宛如荷葉靜立在水中央。在聽到第一聲鳥鳴后,右手將扇子緩緩抬高。在第二聲鳥鳴時,舞蹈家快速輕挑扇子,身體隨之迅速立起又落下,像清晨的露珠打在荷葉上的微微顫動一樣。緊接著,舞蹈家再次立直身子,同時左手拎起平架至胸前,隨后微微向前推動,身體面朝天空向后倒下,右手將扇子從頭頂前劃過然后平端。之后舞蹈家的頭干脆地面向一方位,右手手腕翻動將扇子蓋向一方位,右臂帶動身體,保持攤扇從一方位劃至七方位,然后扇子留住,立身挑胸時緩緩收回右臂,右手由握扇變為夾扇,將其從右下顎平滑過臉頰。一套動作下來,好像是婷婷荷葉在與微風、露珠的舞蹈后再次平靜了下來。
呈示部主題樂句音樂主題第一個音引出舞蹈家一個翻扇,右手夾扇,手心朝上,身體再次坐回自己的腳跟上,左手背在腰間。隨后舞蹈家右手慢慢拎起扇子,掌心向上推開扇子,露出臉來,然后慢慢仰面下胸腰,扇子平攤。緊接著音樂下半句,舞蹈家一個翻腕將扇子拎起,劃過天空蓋下到身體正前方后再次提臂,在頭上方變為攤扇落在身體右側,左臂隨著右臂的擺動架至胸前,同時右腿向后撤半步,重心移到左腿上。然后舞蹈家緩緩轉向七方位,身體隨之立起,左手推掌,右手收臂將扇子攤在后腦勺處。
主題第二樂句,舞蹈家含胸,扇子由后腦平劃到胸前,然后干脆地拋向二方位,身體坐在右腿上,左腿微微彎曲,整個人向二方位延伸。然后舞蹈家緩緩轉向八方位,右手收臂將扇子平架在頭右后方脖頸處,左手順著下顎抹過后貼著左耳,右腿站起左腿隨后跟上,半腳掌踩地,身體近乎背對觀眾。舞蹈家雙臂同時水平延伸,左手向后穿,右手攤扇向前送。主題第二樂句后半句,舞蹈家左腳收回,一個快速的波浪腰,雙臂保持伸直垂下再舉至頭頂,然后右手帶動扇子經過胸前劃下后再舉起約四十五度,左手推掌姿勢架在胸前,身體面向五方位下旁腰回卷。像是筆直的花莖因為突然掉落的露珠而彎了彎腰。隨后舞蹈家順勢繞扇,身體向左轉一圈,將扇子從身前劃下然后又一個翻扇的同時舉到頭頂上方,左腿小腿輕輕向后一踢然后小碎步先向一方位再向八方位跑幾步,扇子慢慢抹下來。
接下來的對比段,舞蹈家的舞蹈動作開始有對比,左腿吸腿跳的同時收扇豎直從耳邊伸到頭頂,隨后含胸下落,面向五方位將扇子從胸前推開。緊接著舞蹈家一個翻身,右手抱肩,然后又反方向再翻身,接上經典的膠州秧歌的步子——右腳上步腳跟著地,腳尖帶著身體向右擰,然后再左腳上步,身體與腳尖一起向左擰。對比段第二句,舞蹈家雙臂一起從身體左側劃向身體右后側,重心從左腳向后移到右腳上,然后右手將扇子從身體后面拎起,左手從下巴穿出,兩臂又同時向前劃下,兩手握扇翻身后下垂,隨后兩手從身體兩側拎起在頭頂快速繞扇,同時上右腳跑向舞臺右側。然后舞蹈家一個穿手隨后反方向轉一圈,左手向前平舉,右手將扇子搭在左臂上,小碎步向后退。
接下來音樂進入過渡樂句,舞蹈家開始一套過度動作:向右轉向一方位,左手慢慢放下來,右手慢慢收扇,然后隨著音樂的拍點頭靈巧的轉向八方位,然后下一拍右腿和右手胳膊肘順邊向上提,然后左腳落地,在上右腳的同時右手將扇把指向八方位,然后立即向右轉身,身體面向八方位,隨著音樂的節點兩手握著扇骨開扇。然后舞蹈家又立即向左轉大半圈面向二方位,將扇骨貼在平舉的左臂上,再次向舞臺的六方位后退。
再現段舞蹈家向七方位上右腳,扇子向斜上方拋去,身體跟上轉兩圈后面向二方位下蹲,左手背在腰間,右手握扇平蓋在頭頂,然后隨著音樂站直身體并且將右手伸直露出臉來。
作品《詠荷》的舞蹈語匯充分發揮民族民間舞膠州秧歌的身韻來強調“荷花”的中國特色,另一方面又在動作組合與結構安排上巧思妙想不落俗套,從而使得該作品突破了民族民間舞傳統的表現力的限制,達到立體化的創新的舞蹈藝術表現效果(見圖1)。

圖1:舞蹈《詠荷》
四、道具運用的創新藝術表現
舞蹈是在音樂與燈光,道具與舞美服飾等多種藝術形式的支持下通過特定的舞蹈語匯來表現和表達主題情節與情感的綜合藝術。道具作為舞蹈不可分割的主要輔助工具往往在被用來增強舞蹈的表現力和感染力的方面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舞蹈帶給了道具生命的氣息而道具反過來加強了舞蹈的情感表現。梳理舞蹈表演與舞蹈道具相互作用的運用關系,用準用巧合適的舞蹈道具能達到一舉多得、意蘊無窮的藝術效果。
舞蹈道具大致可以分為以表現生活情趣為主的生活性道具,以表現詩情畫意為主的寫意性道具和以表現借物抒情為主的象征性道具。《詠荷》中道具荷花扇的運用主要是一種對寫意性道具的創新性運用。
膠州秧歌女子獨舞《詠荷》所用道具為秧歌舞蹈中運用較多的扇子,“與傳統的民族民間舞蹈所用扇子不同的是《詠荷》中的扇子被設計成獨特的能三百六十度打開的一面為草綠色一面為玫紅色的雙面大折扇。完全展開后草綠色那面酷似一片荷葉而玫紅色那面神似一朵盛開的荷花。”[5]作品前半段重點展現草綠色扇面而將玫紅色的扇面折藏在內側面。舞蹈家身著飄渺的綢緞綠衣,扇子在手中就如伸展開來的荷葉。扇子不斷舞動的多姿多態的扇花恰到好處的配合舞蹈家曼妙的身姿,撇、抖、繞、甩、開合等舞扇動作完美融合了舞蹈家手中之扇與肢體動作。舞蹈中段音樂聲夾雜著雷雨襲來,舞蹈家從舉扇旋轉過渡到席地側身半躺,右手持扇將荷葉邊半垂下來擋在身前,翠綠的姿態仿佛荷塘中舒睡著一位含苞待放的荷花仙子。之后舞蹈家隨著音樂漸漸站,臉側枕著扇面緩緩立身旋轉,用飄逸的扇尾勾勒出優美的弧線仿佛荷葉在隨波蕩漾。接著舞蹈家一個盤扇含胸,快速將扇子展開到三百六十度并翻扇將玫紅的扇面展露出來同時雙手托扇將扇子舉到最高,此時舞蹈家肢體連同荷花扇好似翠綠的枝干一朵嬌艷的荷花盛開在觀眾面前。燈光漸明之后進入最后高潮部分,舞蹈家持扇旋轉、跳躍,宛若陽光下灼灼生輝生意盎然的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給予了我們一種詩情畫意的審美感受。《詠荷》運用寫意化改造的扇子塑造荷葉荷花的形象,結合編導、舞蹈家巧妙編排和運用,將觀眾帶入一種寫意的詩情畫意的審美境界。
在民族民間舞蹈《詠荷》當中寫意性道具“荷花扇”不僅惟妙惟肖的模仿了“荷花”的形象,更展現了作品的審美特征和主題思想,讓觀者感受到“如畫的意境,如詩的感情”。
結 語
民族民間舞蹈《詠荷》仿佛是一首民族斗爭精神的詩篇,給觀眾的內心帶來了強烈的震撼。舞蹈在題材、音舞結合、舞蹈語匯、道具使用等方面進行了充滿意蘊和張力的創新藝術表現,使得整個作品在藝術表達的廣度和深度方面達到了新的高度,為新時代民族民間舞蹈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