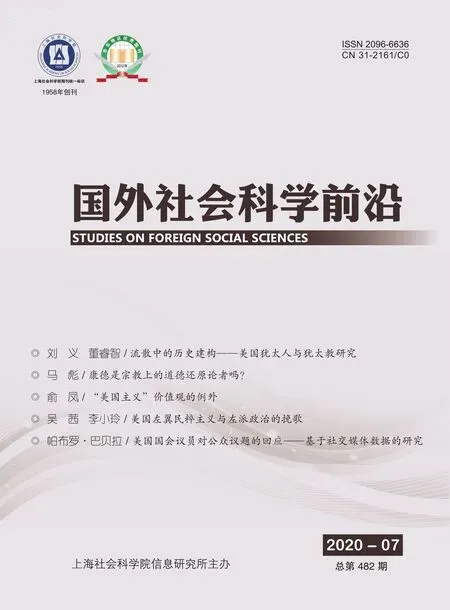康德是宗教上的道德還原論者嗎? *
馬 彪
內容提要 | 康德思想體系中的道德與宗教之間究竟具有何種關系,一直是后世學者較為關注的話題。由既有的研究文獻來看,可以粗略地分為兩種,即道德還原論和非道德還原論。基于“公設之信仰”這一前提,主張“道德還原論”的克朗納認為,沒有道德就沒有宗教,道德是宗教得以可能的前提與基礎。與此不同,主張“非道德還原論”的龐思奮則斷言,宗教雖說來自道德,但前者的領域顯然比后者的領域要大得多,道德只是宗教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兩者不是互為涵攝的關系,更不能將它們等同視之。然而,縱觀康德思想,尤其是結合他對哲學、神學以及宗教之關系的系統分析,我們將會發現,康德既不完全贊同由哲學(道德)的路徑對宗教來加以單獨考察,也不完全贊成單由神學(啟示)的路徑來詮釋宗教,相反,他認為應該在哲學與神學的對話或商榷中漸次趨近于宗教的真理與智慧,進而將這一真理與智慧注入民眾的心智之中。康德的這一論斷對后世宗教哲學影響深遠。
一、引 言
如所周知,康德在其一生的著述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宗教這一主題,而對這些文本稍有涉獵的讀者當不難發現,康德的宗教思想與其道德學說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確立并延伸開來的,離開后者,前者將無從談起,用康德自己話說,我們對于一個最高存在者之存在的信念是建立在道德法則之上的,沒有道德,宗教的存在絕無可能。沿著這一思路,后世不少學者認為,康德將宗教進行了道德還原,或者說康德的宗教思想無非是偽裝了的道德而已,這一主張最為有名的代表為里夏德·克朗納(Richard Kroner)。與此相對,有的學者則主張,不能將康德哲學中的宗教思想簡單地還原為道德,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巨大的,道德為宗教之基,但它本身并不就是宗教:道德只是宗教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兩者并不完全一致,這一立場的代表李秋零教授①比如,李秋零教授在《道德并不必然導致宗教》一文中指出,道德與宗教之間雖說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卻根本不存在康德所說的必然性的聯系,康德把信念與知識領域剝離開來,以此來為信念騰出地盤,實際上也就是把宗教信仰劃歸了自由的領域,宗教信仰就是一種自由選擇的結果。參見李秋零:《道德并不必然導致宗教:康德宗教哲學辯難》,《宗教與哲學》2013 年第2 期。和龐思奮(Stephen Palmquist)教授②Stephen Palmquist, Does Kant Reduce Religion to Morality, Kant-Studien, 1992, vol. 83, pp. 149-169.。在我們看來,這后一立場較為可取,但也不是沒有缺陷,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康德傾向于采取由神學與哲學、信仰與理性,以及啟示與道德之爭論或商榷的方式來詮釋宗教,進而將宗教中所包含的真理與智慧注入民眾的心靈。表面上來看,康德所做的努力是在啟示神學之外,開辟一條以理性或道德為基礎的解讀傳統宗教的研究理路,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并不能由此得出康德定然拋棄傳統的理解宗教的探究方式。誠如艾倫·伍德(Allen Wood)所言,康德雖然對基督教教會信仰持有異議,但這并不意味著他要完全棄絕所有的神秘啟示、歷史奇跡,以及偶然事件。康德對基督教的批判,并不包含哲學家本人要粉粹其智識世界的意圖,也不以摧毀其思想王國為目的。不可以設想康德會游離這個智識世界,就像他不會遠離他的故鄉哥尼斯堡的周邊一樣,而完整的和全面的考察可以發現,康德的哲學事實上幾乎把基督教思想的傳統王國完好地保留了下來。①[美]艾倫·伍德:《康德的理性神學》,邱文元譯,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6 ~7 頁。基于此,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考察“道德還原論”的基本內涵,重點討論德國哲學家克朗納與此相關的基本立場;其次,刻畫“非道德還原論”的觀點,側重闡述龐思奮的主要論點;最后,具體分梳筆者對此一問題的一點見解,即嘗試在理性和信仰、自由和啟示的商榷或對話的基礎上解決道德與宗教之間的疑難問題;文末,再對上述議題之彼此勾連、密切相扣的關系作一總結歸納。
二、道德還原論
毋庸置疑,在康德之于宗教的態度這一理解問題上,克朗納的道德還原論與龐思奮的非道德還原論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兩種立場,在一定意義上,它們至今依然統治著人們對康德宗教思想的認知。而要辨別清楚康德宗教思想的真實主張,我們必須先要破除這兩種既有的詮釋理路。鑒于非道德還原論是針對道德還原論而發的,因此,在介紹前者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后者作一簡單梳理。因為,相較其他的解讀而言,道德還原論不只是在時間上較為據先,而且在影響上也比非道德還原論深遠,對它的梳理不僅有助于我們厘清后世學者對康德之宗教學說的詮釋脈絡,更有助于我們把握康德之宗教思想的本質特征。
克朗納是由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一視角來探討康德哲學中道德與宗教之關系的,這位出身于德國的新黑格爾主義者認為,在康德龐大的思想體系中有著一以貫之的根本原則,即道德法則,它是其他一切領域得以可能的基石:“道德領域指向了一切存有與一切存在之終極基礎。”②[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70 頁。道德法則不僅超越了自然的必然性,甚至超越了道德自身的規范性的領域,總的來說,它是有著相對于所有其他存在的優勢,指向了那終將統一感性領域與超感性領域的“元一”(a transcendent One)。對克朗納而言,道德法則之形而上的要求不單是命令我們自身與外在自然都約束于理性之下,它甚至認定我們的信仰也無法逃脫這一原則。誠然,基于道德上的理由,我們不能把自然同時建構(constituting)在道德領域之內,畢竟它與后者還是有著質的差異的,但為了滿足理性的需求,我們必須尋求一更高的綜合來統攝兩者。對于這一最高綜合的尋求,康德并不是在理論理性中作出的,而是在道德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一至高的綜合就是上帝。由康德的思想理路來看,他的哲學精神最終是要走向宗教的,而宗教與上帝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是道德。
克朗納承認,當康德斷言就算是上帝也要依從于道德法則,而不是道德法則依從于上帝時,他的確遭遇到了不少的質疑。因為,一方面,康德深信宗教必然出自道德,它不過是道德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而已;另一方面,康德也似乎潛在地透露,上帝要比道德法則高得多。如此一來,康德的哲學思想就被兩種難以結合而又彼此糾纏的基調決定著,這兩種基調始終威脅著其學說體系的完整性與系統性。不過,對于這一點,克朗納亦不感到特別難以處理,他認為,在康德的道德世界中,道德法則其實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上帝ordoordinans(發布命令),它是我們道德行動中作出秩序安排的命令者:“上帝乃是道德的律令,它的意志表達作為吾人的良知之呼喚(the voice of our conscience),它的詛咒表達作為吾人內心的懊悔,而它的愛表達為一純粹的心靈的凈福。”①[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74 頁。而我們除了對道德法則的服從之外,根本沒有別的途徑事奉上帝,也沒有別的方式來榮耀上帝了。大多時候,康德被人們視為反基督教的思想家,如果我們強調良知作為道德及宗教的最高法庭的話,那么康德無疑走向了傳統神學的對立面。之所以如此,乃是與道德法則作為立法者的自律這一特性密不可分。就我們能夠體現與踐行純粹實踐理性這一點而言,“道德法則的立法者(legislators)并不是上帝,而正是我們自己,我們服從于道德法則并非為了上帝,而是為了我們自己”。②[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75 頁。在克朗納看來,人的道德法則以及基于這一認知前提之上的自由,不只是免于自然及其規律的自由,而且也是完全外在于超自然力量的自由,任何外在條件都不可能對作為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施加確定不移的影響,也不可能摧毀它的尊嚴。康德以前,從來沒有哪位思想家像康德這樣如此的褒揚、彰舉人自身,賦予人以如此高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人,雖來于自然,但又超越于自然,而使得這一超越得以可行的基礎,就是它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超感性的道德領域,在這一領域中,人的觀念與上帝的觀念是如此接近,到了幾乎重疊的地步,以至于上帝也要仰賴道德。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克朗納的詮釋理路基本符合康德的思想演進過程。當然,康德是由道德這一概念確定無疑地推導出上帝的存在,還是“宛如”(als ob)推導出上帝的存在也還是有爭議的。比如,漢斯·懷興格(Hans Vaihinger)就認為,康德哲學中的宗教誠然源自道德,離開道德的宗教是無法想象的,但基于道德的上帝只是“宛如”存在,而非客觀實存。在其扛鼎之作《“宛如”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s if’)之第三部分“康德‘宛如’方法的使用”(Kant’s use of the ‘as if’ method)一節中,③針對懷興格的“宛如”哲學,牟宗三嫡傳弟子盧雪昆教授亦有詳盡的批判,具體可以參見:盧雪昆:《康德的自由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404 ~413 頁。懷興格曾經指出,康德哲學中的上帝之出于道德的論述雖說可行,但不十分可靠,因為按照康德的論證,對上帝的信仰只不過是一些道德上的需要,上帝只是一個道德觀念而已,作為一種實踐上的假設,上帝只是好像存在而已,至于上帝是否確然存在,歸根到底還是有待進一步說明的。④Hans Vaihinger,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trans. By C. K.Ogde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en Paul Ltd, 1911, pp. 271-318.
針對懷興格的這一詮釋,克朗納斷然否定,他的反駁主要有兩點:第一,康德不會說謊,一個擁有像康德這般智慧和道德境界的人如果在說什么的話,那么他必定是當真如此想的,因為他的所有著作與行為都證實了他的虔敬與誠摯;第二,作為自然與自由之統一的上帝信念是康德整個哲學體系的應有之義與必然結果,上帝雖然無法給予思辨上的證明(demonstrated),但可以在道德上被確證(assured)。道德上的確證之所以比思辨的證明更有說服力,在于它不僅具備了后者的確定性(certainty),同時還具備了后者所不可能有的尊嚴性,而正是這一點,使得道德法則可以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因為理論上的理由是可以被反駁的,假如上帝存在是出于理論的證明,那么它隨時可以遭到質疑,畢竟理論與其相關的推論都是容易犯錯的。而一旦把上帝的存在置于道德法則之上,則將是無法駁斥的,因為要否定上帝,除非事先否定道德法則及其效力,但對康德而言,這即等于人要否定自己是人,因此是絕對不可能的。①[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78 ~79 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基于道德而被公設的上帝,與我們作為理性且道德的存在者一樣都是確實地存在著的,從根本上而言,我們自身也是不能在思辨的層面上得以證明的,我們也是在道德的意涵上得以確證或被設定的,因此任何對上帝之實存的否定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對人自身之實存的質疑,而這一點在康德看來是不可想象的。
表面上看,立足于康德的人格與文本,克朗納給出的反駁似乎無懈可擊,其實并非如此。我們先看看他的第一個反駁,這一反駁沒有任何邏輯的力量,幾乎全是情感的說教,這與其說是在論辯,不如說是情緒的宣泄,此誠不足與之辯。第二個反駁完全立足于康德的既有文本,著重強調的是上帝之公設(Postulate)與人之道德法則之間的理性的事實(Factum der Vernunft)關系。作為道德信仰之事,上帝的存在雖沒有知識上的普遍性,也決不能由理論的角度來考察或證明之,但它卻有著道德上的實在性,它的這一實在性是奠立在人的自由意志這一層面,進而落實到道德法則這一理性的事實之中的。反駁這一點,等于否認人的理性的規定性,而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斷言人是理性的存在者,與其說是康德的哲學主張,不如說是他的道德信念。
較于第一個反駁,克朗納的第二個反駁存在一定的說理依據,基本符合康德的哲學精神,的確也為他的宗教出于道德的主張給出了合理的辯護。然而,即便如此,作為一個認真、負責的學者,克朗納并沒有由此就對康德哲學中的疑難視而不見,也沒否認康德之倫理思想與其宗教神學之間存在沖突問題。相反,他采取的態度是直面這一議題,承認康德在一定程度上被他自己的“公設之信仰”這一學說所累:上帝觀念失去了固有的尊嚴與權威,而道德的嚴肅性與崇高性亦受到了危及。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克朗納認為,康德必須采取這一理路,這是康德道德哲學的應有之意,因為“道德”一詞本身就意味著掙扎與沖突,一旦擺脫這一品性,道德的價值亦將不復存在。用克朗納自己的話說:“道德之世界堅決不屈地要求與其目標之間存在著一種持久的張力,這一障礙一旦被取消,則道德意志將失去其真正的力量,如果這種張力與這些障礙被抽出,則道德法則本身將失去其意義。”②[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81 頁。
不難看出,無論克朗納的道德還原論如何努力完善其立論基礎和論證方式,它都不得不面對或承認一個問題,即完全從道德視角來解釋宗教將會遭遇很多困難:一方面,作為被道德所公設的上帝,似乎沒有獲得其應有的神圣地位;而另一方面,與上帝隔離的道德,也貌似失去了其崇高的威望。結果,上帝與道德法則都變得曖昧不清,它們同時都顯得既超出于對方之上,又獨立于對方之外,都顯得既絕對又不絕對。③[德]里夏德·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關子尹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83 頁。之所以如此,我們認為,克朗納雖說看出了病理癥候,但沒有勘出這一癥候的真正病根——康德不是一個宗教上的道德還原論者。凡是對這一問題視而不見者,都沒有真正理解康德及其道德宗教思想。
三、非道德還原論
雖不是最早、但卻較為全面考察這一問題的學者是香港浸會大學的龐思奮。他認為,判斷康德是不是一個宗教上的道德還原論者,須首先看一看何為還原論,它包含什么內涵,在此基礎上才能具體對康德的思想作出診斷與判別。如所周知,龐思奮在1992 年發表于《康德研究》(Kant Studien)雜志上的《康德把宗教還原為了道德嗎?》(Does Kant Reduce Religion to Morality?)一文,具體區分了兩類還原論,即闡釋性的還原論(explanatory reductionism)與消除性的還原論(eliminative reductionism)。其中,前者是指“在某個領域之外,根據一個單一的、但卻可以遍及各處的要素來對這一領域相關的東西做出必要、合理的說明。”①Stephen Palmquist, Does Kant Reduce Religion to Morality, Kant-Studien, vol. 83, 1992, p. 129.以心靈與大腦的關系為例,龐思奮認為,心靈可以對某些大腦現象加以說明,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大腦與心靈等而視之,或者僅靠心靈就能夠對一切大腦現象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兩者相關但不相同。與此相仿,康德哲學中道德與宗教的關系亦是如此。道德能夠對某些宗教問題給予詮釋,然而,這不等于說道德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解釋一切宗教議題,可以說,道德是真正的宗教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相反,后者即消除性的還原論則徑直以道德代替了宗教,道德是自足的,它不需要其他方式的介入就可以對宗教給予徹底地、事無巨細地說明,在此意義上,克朗納就是這一還原論思想的典型代表。毫無疑問,這一種理解方式是有問題的。針對這一立場,龐思奮以《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一書為核心文本提出了自己的反駁,他的反駁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龐思奮認為,人們以“道德宗教”這一名號來概括康德神學思想的做法易于產生歧義。我們知道,較早將康德的有關宗教的思想界定為“道德宗教”(moral religion)的學者是美國的艾倫·伍德,早在上個世紀70 年代,他就由道德宗教的視角闡釋了康德的神學思想。②伍德曾在20 世紀70 年代出版了兩本大作《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與《康德的理性神學》(1978),分別闡述了他對康德宗教學說的看法,扭轉了自海涅以來的偏見——認為康德哲學尤其是他的宗教哲學是對基督教的反動這一立場——給予康德宗教研究以全新的方向。當然,伍德的觀點也不是一貫的,他對康德宗教思想的解讀可以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階段,兩者并不完全一致。具體可以參見Allen Wood,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78; 以及Allen Wood, Kant’s Moral Relig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70.當然,龐思奮不反對由道德的維度來介入宗教的研究,但是他尤為強調的是,康德以理性為基礎、以道德為核心的研究方式,并不排斥其他的探討途徑與研究方法。以《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為例,康德彰顯“純然理性”的目的,只是想嘗試一下或者做一個實驗,看一看單是以“純然理性”來詮釋宗教究竟可以達到何種程度,或者用康德自己的話說,他這里要做的是,要在那啟示給人的宗教文本即《圣經》中憑借理性也能夠被認識到的東西。相反,如果人們誤認為單憑理性而不需要啟示就可以解釋宗教,那就太過自負或僭妄了,因為康德并不否認“宗教的學說畢竟有可能出自超自然感動的人們”③[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6 頁。這一事實。對于這一點,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一文的題名中,我們由康德刻意選擇的兩個德語單詞即“界限”(Grenzen)與“純然”(blossen)里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界限”這一語詞來說,依龐思奮之見,德語里面有兩個表示“劃界”的詞語可以動用,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曾做出過清晰地說明:“界限(Grenzen)(在廣延的存在那里)永遠以在某個確定的場所之外被發現并包圍這個場所的一個空間為前提條件,限制(Schranken)并不需要諸如此類的東西,而僅僅是就一種量不具有絕對完備性而涉及該量的否定。”①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nnen,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GmbH&Co, 2009, s. 130.顯然,康德用的是第一種意義上的劃界,他把所要研究的領域喻為了一個空間,比如宗教就是這樣一個場所,它可以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人們完全能夠由不同的側面對其加以考察,而康德所要做的就是由純然理性的視角來探討之,雖然他并不反對在理性之外以別的方式對此加以研究的可行性。在某種層面上,康德其實是贊同由不同視域來對宗教加以研究的,因為只有如此,這一研究才是完備的、系統的,也才不會墮入“限制”的劃界那種不完備的、不系統的否定性研究之中而無法自拔。總的說來,“界限”的指向是領域的邊界(territorial boundaries),而不是絕對的限制(absolute limits)。其次,就“純然”②具體闡述可以參考朱華甫:《欲成義人,先做善人:康德對道德與宗教關系的處理》,《現代哲學》2010 年第3 期。而言,康德對它的選用也是十分講究的。按照龐思奮的分析,很多英譯者就沒有充分考慮康德遣詞造句的良苦用心,徑直將blossenVernunft 翻譯為Reason Alone③Theodore Greene and Hoyth Hudson,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0.或Mere Reason④Allen Wood and George di Giovanni,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不可否認,這些譯作或有所得,但是其不足也是明顯的,它們不僅忽視了blossen 一詞的普通內涵,也錯失了原作的精微之義。龐思奮主張,最佳的翻譯應該是Bare Reason,因為Bare 不僅囊括了Alone 與Mere的意涵,而且還將其與《純粹理性批判》中的Reinen Vernunft 之間的區別闡釋得較為清晰,因為所謂的“純然理性”指的不是那些不夾雜經驗的純粹理性,純粹與否對它而言不是重點,畢竟它不涉及對思辨知識的考察,此處所要強調的是它在不牽涉其他方面、而單由理性這一方面來對某一事物進行研究的意思。不難看出,康德從理性與道德的角度詮釋宗教的做法,并不意味著他要排斥其他的解讀進路,然而,一旦我們誤解了康德的這一解釋方式,則將必然得出道德還原論的結論來,顯然,這并不符合康德的旨意與哲學精神。
其次,從康德對宗教這一范疇的理解來看,龐思奮主張,信仰與“純粹的理性宗教”是康德眼中真正宗教的一體兩面,兩者彼此相關,不可分割。⑤Stephen Palmquist, Does Kant Reduce Religion to Morality, Kant-Studien, 1992, vol. 83, p. 133.康德一貫認為,道德或“純粹的理性宗教”不就是真正的宗教本身,但它卻是真正宗教的內核與底色,宗教中的其他非道德的部分誠然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它們有助于或能夠促進人的道德提升。換句話說,康德認定真正的宗教包含兩個構成要素:一是神恩、信仰等啟示神學的內容,二是自由、理性等道德神學的內容,兩者雖然并存在于宗教之中,但后者要居于優先地位。需要指出的是,道德的優先地位絕不意味著它在結果(或目的)系統中的完備性。正像一座大樓的地基一樣,它本身是自足的,而且優位于地基之上的樓體建筑,但是如果沒有樓體建筑,地基要想實現其終極目的與結果也不太可能。道德與信仰、啟示的關系亦是如此,道德可以導致宗教,但只靠它自己還不行,必須有道德之外的附屬存在物和它一起才能構建成真正的宗教。因此,“就作為‘基礎’(ground)而言,道德是自足的,它只需要我們的實踐理性即可;但就‘結果’(consequence)來說,我們必須超越道德才有可能希望找到‘第三者’作為橋梁以彌補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的鴻溝,而在這個《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中,這個‘第三者’就是宗教。”⑥Stephen Palmquist, Does Kant Reduce Religion to Morality, Kant-Studien, 1992, vol. 83, p. 133.依龐思奮之見,試圖將宗教還原為道德的“克朗納模式”顯然忽視了上述“基礎”與“目的”的這一區分,沒有看到我們只能在道德之外才能抵達幸福這一最終目的。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我們不超越道德進而在宗教的層面上到達經驗的實在性(empirical reality),我們就無法完成“我可以希望什么”這一要求與目標,因為說到底,“我可以希望什么?這是實踐同時又是理論的,以至于實踐方面只是作為引線而導向對理論問題以及(如果理論提高一步的話)思辨問題的回答”,①[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612 頁。而在龐思奮看來,這一目標只能在既綜合了經驗思辨又包含了道德實踐的宗教中方能實現。
簡單比對一下即可發現,“非道德還原論”比“道德還原論”要優越一些,也較為容易地解決了康德思想中道德與宗教的關系。就“基礎”層面來看,它承認宗教源自道德,道德是宗教的基底;然而,就康德所要實現的目標與“結果”而言,它又主張單靠道德不足以完成“人的希望問題”,必須超越道德,立足于宗教的立場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因為這里不僅僅涉及道德的議題,還涉及道德之外其他建制或輔助問題。如此說來,按照龐思奮的看法,我們只有從兩個不同的維度,即“基礎”維度和“結果”向度來對待道德與宗教之復雜關系。現在,如果說龐思奮所作的解讀是正確的,那么這會不會導致一個騎墻的局面:即康德在回避問題,沒有對道德與宗教何者據先的問題給予最終的解答,面對困境,他一會跳到“基礎”層面一會跳到“結果”或目的層面,而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當在龐思奮教授所作努力之上再前進一步,進而在哲學學科與神學學科之關系的層面中對此重新加以審視。
四、基于哲學和神學對話之上的道德宗教
須事先明確的是,康德對宗教的態度不是模糊的、騎墻的,而是確定的、一以貫之的,這種一貫之道就是在神學與哲學的商談與爭論中將真理與智慧一一注入民眾之心的過程,既不能簡單地將宗教還原為道德,亦不能完全拋棄道德任性(Willkür)隨意地解讀,相反,在對宗教之解經釋義的過程中,兩者都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用康德的自己話說,他所做的努力只是一種商榷,即“神學專業和哲學專業的學者們之間的一種商榷,是為了確定,宗教怎樣才能純潔而又有力地注入人們的心靈”。②[德]康德:《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12 頁。為了更有效地踐行這一思想,實現上述目標,康德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中又引入了兩種宗教解讀方式,即圣經神學(biblischen Theologie)的詮釋方式和哲理神學(philosophische Theologie)的詮釋方式,③[德]康德:《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6 頁。而在《學科之爭》(Streite der Fakult?ten,1798)中他又進一步發揮了這一主張。
在《學科之爭》一書中,康德將圣經神學等同于了以信仰為核心的神學學科、高等學科,而把哲理神學視作了以道德為內核的哲學學科、低等學科,并分別對兩者的性質、職責,以及研究范圍作出了較為詳細的分梳。④在《學科之爭》中,康德明確主張將“圣經神學”等同于“高等學科”與“神學學科”,而將“理性神學”等同于“低等學科”與“哲學學科”。參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34 頁。作為由政府背書的圣經神學,它以《圣經》為權威,其規章制度完全來自于一個在上者的任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的學說。與此相對,哲理神學則以民眾自己的理性為基礎,在這里,理性按照本性是自由的,不接受任何某種視之為真的命令[不是crede(你要信),而僅僅是一種自由的credo(我信)]。①[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13 ~16 頁。此處,神學與哲學之間的區分是相當清楚的,一個訴諸于信仰、啟示;一個訴諸于理性、道德。“我們一旦把兩種不同的事物混為一談,使其相互交錯,就對它們中的每一個特性都不能形成任何確定的概念。”②[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20 頁。非常明顯,面對宗教這一課題,康德主張可以存在兩種解讀方式,那就是神學的方式與哲學的方式,兩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圍,誰也不能越軌,否則必當造成混亂,進而取消各自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比如,康德就曾明確反對神學對哲學之理性概念的調用,因為一旦這么做,它在某處程度上就會損害政府的權威、插手了哲學學科的內部事務,而哲學學科則將毫不愛惜地拔光神學所有從理性借來的耀眼的羽毛,按照平等和自由的尺度來對待它。因此,康德建議,神學最好小心謹慎,不要與哲學學科陷入不匹配的婚姻,而是要對它敬而遠之,以免自己規章的威望被它自己的玄想所損害。③[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19 頁。
面對上面的論述,某些康德專家也許會提出反駁說,康德誠然提出過神學與哲學通過商榷的方式來共同詮釋宗教的主張,但是康德似乎沒有真正地執行他的這一方案,因為他在《學科之爭》中處處表現出他要以哲學的解讀方式來統合甚至取代神學的解讀方式,有時他的這一傾向表現得還特別明顯。④Lawrence Pasternack, Kant’s“ Appraisal” of Christianity: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ure Rational System of Relig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53, 2015, pp. 485-506.例如,在《事關釋經原理的指責及其答復》一節中,有人就認為康德的解經釋義原則都是哲學學科的判斷,在這里,哲學顯然干涉了神學的事務。對此,我們的回應是,要想正確理解康德的立場,需要仔細辨析一對核心概念,即哲學上的邏輯在先和神學上的時間在先。
按照邏輯在先的觀點,哲學的解釋應該先于神學的解釋,因為依康德之見,一切釋經一旦涉及宗教,都必須按照在啟示中作為目的的道德性的原則來進行,如果沒有這一原則,則要么在實踐上是空洞的,要么干脆就是善的障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除了通過我們自己的理性同我們說話之外,我們不理解任何東西,因此,就我們的理性的概念是純粹道德的,因而是確實可靠的而言,除了通過它們,一種向我們頒布的學說的屬神性,不能通過任何東西來認識。⑤[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44 頁。相反,由時間在先的立場來看,我們對宗教的解釋必須由啟示、奇跡等開始。康德指出:“在基督的時代,為了不顧猶太教的對抗,率先開創一個揚棄世上一切訓誡的純潔宗教,并把它傳播到廣大民眾中去,奇跡和宣示秘密是必要的。在這方面,許多kata anthropon(人為的)論據也是必要的,它們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價值。”⑥[德]康德:《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44 頁。康德認為,純然理性的信仰必須以這一神學的歷史性信仰為前提,之所以如此,應該為之負責的是人性的軟弱,原因在于,作為理性存在者,我們知道我們應該通過一種道德上善的方式來事奉上帝,但是與此同時,作為感性的存在者,我們也知道對上帝的信奉并不在于行動的道德價值,而在于虔誠地順從以討上帝的歡心。由于世界的每一位偉大的主人,都有一個特殊的需要,即為自己的臣民所崇敬和通過臣服關系來頌揚,沒有這些東西,它就不能體察它的命令在信眾中所造成的影響。與此相對,我們作為臣民,不管多么理性,也總能在對上帝的啟示與神跡中感到一種直接的滿足。因此,就宗教的信仰而言,我們發現,事先產生的不是純粹的道德宗教概念,而是事奉神靈的宗教概念。①[德]康德:《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90 ~91 頁。在此基礎之上,真正、純粹的宗教信仰方能漸次展開。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神學對宗教的闡釋理應優于哲學的詮釋,因為從時間上來看,是神學先于哲學最早促生了宗教的萌芽與開展。不過,要想在更深的層次上把握這一點,我們還須重新回到康德對“理性主義”“自然主義”“純粹理性主義”,以及“超自然主義”的界分,只有理解了這一組概念的內涵,我們才能真正把握康德思想中哲學、神學和宗教之間的復雜關系。
按照康德的理解,理性主義這一概念強調的是人的義務先于上帝的誡命,或者說“在能夠承認某種東西是上帝的誡命之前,就知道它是義務”。②[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56 頁。換句話說,先有了人的義務,然后才有上帝的誡命,從邏輯上來看,前者先于后者,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熟悉康德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實在康德哲學中“人的義務”和“上帝的誡命”兩者是一回事,只不過是看待這一問題的視角略有不同而已。而在這里,康德之所以如此界定“理性主義”,顯然是在信仰和理性何者優位方面,將側重的砝碼放置在了理性天平的一端。與此同時,康德把“自然主義”理解為“否認超自然的上帝啟示的現實性”,③[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56 頁。這一界定中的“現實性”指的是那些可以在感官世界得以證明的客觀存在,凡是能夠得到經驗確證的——不管是證實還是證偽——概念,都可以稱之為現實性,而當“自然主義”拒絕承認上帝啟示這一現實性的時候,它無非是說,一切違背自然規律的事件都應一律排斥,因為它們無法用機械的規則加以說明,在此意義上,它們都是不能被我們所理解或把握的東西。再次,是所謂的“純粹理性主義”,對于這一概念,康德的界定是,它允許超自然的啟示,但同時又主張認知這一啟示對于宗教而言并不完全必要。與自然主義不同,純粹理性主義并不否定那些違背自然規律現象的存在,甚至是允許它們的發生的,但是有一個條件限制,即對于那些啟示我們是無法認識的。基于理性的立場,上帝的恩典也好,自然的奇跡也罷,或許它們都是有的,但我們不認識它們,或者至少對于宗教來說并不重要。可以看出,較于自然主義,純粹理性主義在對待非自然現象或反自然現象時是比較寬容的。與自然主義的那種對自我的自信有所差別,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純粹理性主義不是一味的堅持自我,反對與自己對立的他者的可能性,而是反身而誠,首先反思自身的有限和不足,至少是認知上的有限和不足。最后,是超自然主義,它的立場是對超自然啟示的信仰是宗教所普遍必須、不可或缺的要件,④[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57 頁。沒有啟示的宗教是不可思議的,信仰是宗教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上述4 種立場的區分,人們不禁要問,康德本人秉持的是哪一種立場?針對這一點,爭議較大,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許是由于現實社會環境的原因,在那個對宗教議題特別敏感的時代,出于安全的考量,康德對上面4 種立場的描述著墨也不甚多,而只是說,理性主義必然由于它的這一稱號,自動地就把自己限制在人的洞察力之內了,因此它絕不會作為自然主義來否認啟示的存在,既不會否認一種啟示的內在可能性,也不會否認一種啟示作為引導真宗教的手段的必要性,因為對于這一點,沒有一個人能夠憑借自己的理性而有所斷定。因此,就某種層面而言,存在爭議的問題僅僅涉及純粹的理性主義與超自然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分歧上。康德這一論述雖說較為難懂,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一點端倪。基于康德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出,較于自然主義、純粹理性主義,以及超自然主義,理性主義的范圍是最為寬泛的,因為它只表明了一點,即相對于上帝的啟示而言,理性在先,信仰在后;自然主義則徑直否定啟示,自然世界沒有超自然事件的地盤;而純粹理性主義雖然主張自然世界允許啟示,即啟示可以是“現實的”,但同時又主張認識這一啟示對于宗教而言不太必要;與此不同,超自然主義斷言,自然世界中的啟示對宗教來說,極為必需,不可或缺。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針對上述4 種主張,康德雖然明確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但從上面的簡單解讀中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4 類概念并不是并列關系,而是總分關系,即后三者都堅持了理性在先,啟示在后的理性主義立場(如果存在啟示的話),所不同的或有爭議的是如何看待啟示在自然世界的地位問題:自然主義根本不接受所謂啟示;純粹的理性主義承認啟示對理性神學具有外在、偶然的促生作用,也就是說,沒有歷史啟示,道德宗教不可能迅速產生并得以充分確立;而超自然主義則認為,基于理性之中的宗教,需要歷史啟示這一必要的、內在的喚醒作用,否則它將永遠沉眠于理性的臂彎,得不到蘇醒之日。可以看出,自然主義因為完全棄絕了啟示的作用,自然不再是康德的選項,那么在純粹的理性主義與超自然主義這兩者之間,康德傾向于哪一立場呢?①Chris Firestone, Kant and Theology at the Boundaries of Reas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 152.對這一問題,“康德沒有裁斷”,②Chris Firestone, Kant and Theology at the Boundaries of Reas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 152.也沒有給出具體的答案,而是模糊地指出:“有爭議的問題僅僅涉及純粹的理性主義和超自然主義在信仰事務上的互相要求,或者涉及一方或另一方認為是唯一真宗教所必要并且充分的東西,或僅僅是偶然的東西。”③[德]康德:《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141 頁。其實,康德之所以給出這一貌似不太令人滿意的答案,也委實不是他的過錯,由于這一問題超出了人們的理性界限與理解范圍,對此,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能付諸闕如。
對我們來說,雖然康德是支持純粹的理性主義還是超自然主義的立場,還不甚清楚,也無法弄清楚,但是他所給出的上述區分,卻對我們理解其宗教思想,以及把握神學與哲學之爭執意義重大。我們看到,康德并不否認神學立場在詮釋宗教中的重要價值,啟示與信仰在解經釋義中的作用與地位斷不可少,亦不可替代。雖然就邏輯的起點而言,理性的、道德的哲學態度無疑是解讀經書的根本立場,也是宗教得以奠定的基礎,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由時間的起點觀之,這一理性的、道德的宗教要么接受啟示對理性的外在的、偶然的促生作用,要么接受歷史信仰對理性的必要的、內在的喚醒作用,可是不論哪一種,都離不開神學這一關鍵的誘因與影響。在此意義上,我們很難說在詮釋宗教的向度上神學就比哲學弱,畢竟離開神學的誘導與啟發,真正的哲學意涵上的解讀也是空無著落的,根本無法實施。
因此,在此意義上我們很難說在宗教詮釋上神學就比哲學弱,畢竟離開神學的誘導與啟發,真正的哲學意涵上的解讀將根本無法實現。對康德而言,在追求真理與智慧的道路上,哲學是以理性與自由的方式走向宗教的,而神學是以上帝之道與靈神的方式趨近宗教的,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彼此不可取代的方式,離開了哪一個都不行,這里不存在彼此替代,相互貶低的問題。準確地說,哲學與神學這兩門學科之間的爭執不是一種沖突,①Chris Firestone, Kant and Religion: Conflict or Compromise? Religion Study, vol. 35, 1999, p. 151.誠如我們上面曾提到過的那樣,康德在1794 年10 月12 日致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信件(草稿)中就已經坦陳過他的真實想法,即他的那些宗教作品之所以被寫出來,只是作為“神學專業和哲學專業的學者們之間的一種商榷,是為了確定,宗教怎樣才能純潔而又有力地注入人們的心靈。這種理論當然不會被普通公眾所注意,如果要對學校教師和教會的教師講授這一理論,那就需要政府的批準。但是,建議給與學者們以自由,這并不傷害政府的智慧和權威。”②[德]康德:《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12 頁。無論以何種方式來解讀宗教,康德的目的都不是完全將宗教還原為道德,因為他始終承認那種由政府背書的高級學科即神學的存在,康德的真正旨趣在于借助哲學與神學之間的這一商榷行動,將宗教中所體現的智慧與真理合理有序地注入人們的心田。在康德看來,哲學與神學的差別僅在于它們的解經釋義的方式與手段中,而不是在解經釋義的目的與意圖上,就神學與哲學對宗教的詮釋而言,其途雖殊而其歸則同,都是為了達致真理與智慧。
五、結 語
綜括前述,就康德是否為宗教上的道德還原論者這一主旨來說,道德還原論與非道德還原論從兩個不同的層面給出了不太完全一致的看法。克朗納由“公設之信仰”的角度出發,的確可以疏解康德哲學中的部分疑難問題,也基本符合康德道德神學的論證邏輯與演繹方式,但基于這一立場,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擺脫康德思想體系中“道德意志”與“宗教信仰”之間的悖論與沖突,而這一悖論與沖突的存在幾乎可以動搖康德哲學的根基。面對這一解讀困境,龐思奮由康德成熟的宗教作品即《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出發,提出了他自己的獨到見解,以消除康德哲學中道德與宗教之間的矛盾。從宗教之所從來的基礎而言,宗教來自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宗教,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由結果或整體的層面來看,宗教領域要比道德領域寬的多,后者有著前者無法涵蓋的機制與功能,道德只是宗教得以可能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兩者并不完全等同。不可否認,龐思奮的看法極富洞識,也給人以極大的啟示。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龐思奮對康德的解讀難免給人以模棱兩可的印象,即在面對道德和宗教何者據先的問題上,康德是較為重視基礎層面還是結果層面總是舉棋不定,頗難決斷。然而,當我們由康德哲學的某一枝節中跳出,縱觀他的整體思想,尤其是結合他對哲學、神學,以及宗教之關系的系統分析,我們將會發現,康德既不完全贊同由哲學的路徑對宗教來加以單獨考察,也不完全贊成單由神學的路徑來詮釋宗教,相反,他認為應該在哲學與神學的對話或商榷中漸次趨近于宗教的真理與智慧,進而將此真理與智慧注入民眾的靈魂之中。用康德自己的話說,他既沒有貶低啟示信仰,也沒有高抬道德理性,畢竟后者亦有不足,比如惡產生自何處,惡怎么過渡到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不是理性只身所能完成的了的。③[德]康德:《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12 頁。毋庸置疑,康德的這一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爭議亦不小,僅就這一點而言,它就值得我們一再詮釋和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