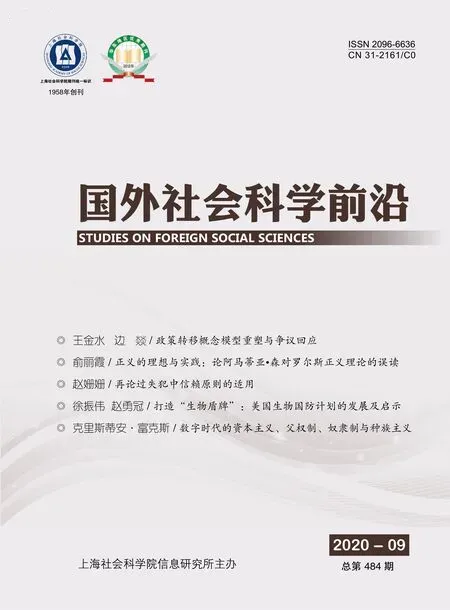正義的理想與實踐:論阿馬蒂亞·森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誤讀 *
俞麗霞
內容提要 | 正義的理想與實踐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政治哲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近期得到了很多探討。阿馬蒂亞·森區分了兩種正義進路:先驗正義進路和比較正義進路。他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屬于先驗正義進路,對于減輕現實生活中的不正義和增強正義無意義。他推崇比較正義進路。森誤解了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錯誤地給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貼上了先驗正義的標簽。森的比較正義進路只能有限地推進正義,而且并不能保證在任何時候都能促進正義。森的比較正義局限于狹隘的比較評估,相比之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包含了一種更廣的比較評估。推進社會正義或全球正義都離不開理想正義理論的引導。
正義的理想與實踐的關系是政治哲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近期得到了很多探討。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理想的正義理論很抽象,與現實相距遙遠,因而與現實無關,不能引導人們實現一個公正的社會。他們盡管同意某個社會是不公正的,但懷疑正義理論具有引導人們實現公正社會的作用。與國內領域的正義理論相比,全球正義理論的引導作用似乎更值得懷疑。與這種現實生活中對理想的正義理論的懷疑相一致,有一些學者也認為正義理論與促進現實社會的正義無關。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區分了先驗(transcendental)正義進路和比較正義進路,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屬于先驗正義進路,沒有實踐意義,重要的是減輕現實生活中的不正義和增強正義。1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探討以下兩個問題:森的比較正義進路是否真的可以促進正義?正義的實踐是否與正義的理想無關?下文將說明,森誤解了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錯誤地給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貼上了先驗正義的標簽。更重要的是,森的比較正義進路只能有限地推進正義,而且并不能保證在任何時候都能推進正義,正義的推進離不開正義理論的引導。全球正義的推進同樣如此。
一、先驗正義進路和比較正義進路
森倡導比較正義,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視為先驗正義,力圖用比較正義進路取代先驗正義進路,實現正義理論范式的轉變。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10; 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vol. 31, 2017, pp. 261-270; 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 2011, pp. 297-315.森反對構建完美的理想正義理論,追求完全公正的社會,倡導在實踐中減少不正義和增強正義。1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ix.近期,森似乎不再使用先驗正義進路和比較正義進路這對術語,而是使用社會契約論進路和非社會契約論進路這對新術語。他似乎沒有說明更換術語的原因。“社會契約進路對應于先驗進路”,非社會契約進路對應于比較進路,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不同,是“更具有比較性、更以實現為導向、更行為化和全球性,并且更加認識到不偏不倚的推理的可能多樣性”的正義進路。2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1, 2017, pp. 261-270;Amartya Sen, Reason and Justice: The Optimal and the Maximal,Philosophy, vol. 92, 2017, pp. 5-19.但是,所用術語的變化沒有影響他的兩條正義進路的實際含義和正義理念,因而本文仍沿用先驗正義進路和比較正義進路。3Amartya Sen, Reason and Justice: The Optimal and the Maximal, Philosophy, vol. 92, 2017, p. 19.
在森看來,先驗正義進路源于社會契約論傳統,洛克、盧梭、康德等是這個傳統的代表,經由羅爾斯的發展成為當代政治哲學的主流。先驗正義進路也被森稱為先驗制度主義,因為它追求關于公正社會的完美理論,專注于制度安排,預設了所有人都服從制度安排的理想行為。先驗制度主義“只是試圖識別出就正義而言不能被超越的社會特征,因此它關注的不是對可行社會的比較,所有這些社會可能都缺少完美的理想。這種探究的目的是識別出‘正義’的本質,而不是找到判定一個選項與另一個相比‘不那么不正義’的一些標準”。4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森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只關注制度的公正,除了要求個體支持公正的制度以外,不關注個體行為的公正。5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2014, pp. 243-244.森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屬于先驗制度主義。相比之下,比較正義進路專注于人們的實際行為,其代表包括斯密、孔多塞、馬克思和密爾等。森是當代社會選擇理論的倡導者,認為這種理論發展了比較正義進路。森反對先驗正義進路,批判了當前在政治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羅爾斯式的正義理論,這種理論把正義作為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6Chandran Kukathas, On Sen on Comparative Justice,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 16, 2013, pp. 196-197.
森對先驗正義進路提出了兩種批評:理論的可行性批評和冗余性批評。在他看來,先驗正義進路在理論上不可行,人們即使在不偏不倚和開放的環境下也不可能就唯一一套正義原則以及完全公正的社會制度理論達成一致看法;7森的第一種批評的理由并不清晰。有學者指出,森有時認為,由于正義原則的理由是多樣的,人們不能就唯一的完美先驗正義理論達成一致看法;有時又似乎認為,完美的先驗正義理論是不可能的。森對三個孩子爭一支笛子的例子所作的說明并不能支持他的觀點。參見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 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p. 33;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15。實踐理性的運行只需要一個比較正義的框架,在可行的正義提升方案之間作出比較,并不需要確立一種完美的正義情境,完美的正義理論是多余的。8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8-10.下文的探討將圍繞森所區分的兩條正義進路展開。
二、先驗正義進路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的確是不合理的。然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否屬于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推進正義是否不需要理想的正義理論?巴勃羅·希拉韋特(Pablo Gilabert)指出,實際上很難找到一個政治哲學家會接受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1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42.有學者指出,森對先驗正義進路的批評并不適用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2Anthony Simon Laden, Ideals of Justice: Goals vs.Constraints,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6, 2013, pp. 205-219.還有學者認為,森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視為先驗正義,原因是把“先驗”(transcendental)理解為“超驗”(transcendent),3超驗訴諸的是無條件、沒有應用性的理想。參見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vol. 13, 2014, pp. 241-263。關于“先驗”和“超驗”在康德及其他哲學家的思想中的區別,參見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9~1010頁。誤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追求的是完美的正義,并且是一種“不可能被超越的完美情境”。完美的正義原則還對“所有可能的社會后果作出完整和傳遞性的排序”。森還認為,羅爾斯探索的是完全公正的社會,不對可能出現的社會進行比較,不關注最終會出現的社會。4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9.森關注的是實踐中不正義的減少和正義的增強,他認為,羅爾斯為完全公正的社會構建的完美的正義理論與此無關。或許對于森而言,完美的正義理論“超越了人類存在的限度”,因而是不實際的。5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2011, p. 302, pp. 312-313.
艾倫·托馬斯(Alan Thomas)指出,森認為羅爾斯追求的正義理論是完美且不可能再完善的,森的這種正義觀點是柏拉圖主義的,意味著存在外在于時間和歷史的正義原則。這里,森誤解了羅爾斯的“完美”的含義。托馬斯認為,羅爾斯的“完美”不是指正義原則的內容是理想的,沒有再完善的可能,而是指原則與實現之間的一致。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采用了反思的平衡方法,要求在正義原則和深思熟慮的判斷之間進行相互調整,目的是獲得一種合理的正義觀念。羅爾斯只是把他的正義理論視為一種正義理論,而不是森所批評的那種不可能再完善的完美正義理論。6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2014, pp. 248-250.勞拉·瓦倫蒂尼(Laura Valentini)指出,反思的平衡是一種靈活的方法,根據這種方法,沒有哪種假定、原則或主張是理所當然的,有關正義信念的固定點只是暫時的,正義原則和信念都是可以修正的。7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2011, pp. 312-313;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18, pp. 42-43.因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可以修正的,而并非是不可再完善的。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不屬于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反而更符合有學者所說的正義的實踐進路。正義的實踐進路并不滿足于構建完美的正義理論,而是涉及引導行動的規定性主張,試圖將正義的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相結合。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與有的學者所說的正義的認識進路接近。根據正義的認識進路,正義是一種哲學理想,只強調評價性主張,不關注實踐中的可行性。8Naima Chahboun, Three Feasibility Constraints on the Concept of Justice, Res Publica, vol. 23, 2017, p. 434;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9;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還有學者把正義的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稱為道德上的可期待性(desirability)維度和可行性維度。9Pablo Gilabert, From Global Poverty to Global Equality: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38-239.可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追求的是理論和實踐、或可期待性和可行性兩個維度的結合。這幾乎與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相反。在森看來,先驗正義進路只關注理想的正義理論,不關注實踐。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試圖結合理論和實踐,這也體現在他的現實主義的烏托邦觀念之中。他認為,政治哲學的一種作用是“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限度”的現實主義烏托邦。現實主義的烏托邦包含正義原則和可行性兩方面,并試圖使兩方面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在他看來,正義的實踐進路的關鍵是如何確定可行性的限度。1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7, pp. 11-12, pp. 12-23;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5; 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11.他指出:“事實不能限定可行性的限度,我們或多或少可以改變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許多其他因素。因此,我們必須依賴猜測和想象,并盡力論證我們想象的社會世界是可行的,可能真的會存在,如果不是在現在的話,那么可能會在更適當條件下的未來的某個時候。”2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 羅爾斯的這個觀點似乎可以支持全球平等主義的可行性。但是,這個觀點有多種解釋,有的解釋未必能支持全球平等主義的可行性,參見Laura Valentini, Justice in a Globalized World:A Normative Frame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0-41。此外,嚴格的正義理論的實現未必總是不可能的,這與相關行動者的動機和其他方面的能力有關。希拉韋特這樣寫道:“烏托邦圖景可能會阻礙或增強人們的行動動機,這取決于如何處理這些圖景。”3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48.正義理論是否具有實踐上的可行性還與它自身的特點有關。有學者指出:“一種理論與實踐無關可能不是因為它過分樂觀,而是因為它嚴重悲觀,或者因為它既不樂觀,也不悲觀,而僅僅是與眾不同。”4Robert Jubb, Tragedies of Non-Ide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1, 2012, p. 233.
森把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作為先驗正義進路或先驗制度主義的一個典型例子。有學者認為,先驗正義進路包含了三個假設:正義意味著完美正義,通過合適的制度實現;正義是我們希望實現的一種狀態;一些專家在告訴我們實現正義所需的制度和行為的要求方面具有權威性。5Anthony Simon Laden, Ideals of Justice: Goals vs.Constraints,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16, 2013, p. 206;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7.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不是由專家設定某種完美的正義圖景,然后把它作為一種狀態來實現。下文有關反思的平衡的討論將會說明這一點。接下來,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不是森所批判的先驗制度主義。
森批評先驗制度主義的原因之一是它只關注制度,不關注人們的實際生活。根據作為公平的正義,人們在原初狀態中開誠布公地討論大家都能接受怎樣的正義原則。根據有的學者的解讀,羅爾斯正義理論的主題是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公民或行為者之間的關系。這樣一來,作為公平的正義的核心不是一套制度、程序或結果,而是公民間的平等關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公民之間的關系結構,包括個人生活和集體生活,因而制度與人們的生活不是截然分開的。可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非只關注制度,而是同樣關注人們的實際生活。如果正義的主題是人們之間的關系,那么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具有調解人們之間的關系,包括調解人們有關正義對話的功能。森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把正義視為某種需要促成的某種東西,這是把正義視為一個工程問題。但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并不持這種正義觀。此外,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中,正義原則不是僅僅由專家決定的,公民也參與了正義原則的商討。因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不包含上文提到的先驗正義進路的第三種假設。1Anthony Simon Laden, Ideals of Justice: Goals vs.Constraints,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16, 2013, pp. 207- 210.森忽視了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的商討和接受過程,而把他的正義理論視為完美的正義理論。總之,森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視為先驗正義是對后者的正義理論的誤解,把自己所認為的先驗進路的很多缺點強加給了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三、比較正義進路與理想正義理論
讓我們在這部分考察森所倡導的比較正義進路是否可以真的促進正義以及正義的提升是否不需要正義理論。比較正義進路在不同的社會選擇方案之間進行比較,從而減少不正義或增進正義。森認為,對于制定合理的政策或構建合理的制度,識別出完全公正的社會安排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因而,完美的正義理論是冗余的。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 他又認為,國內或全球正義理論的用處主要是在社會選項間作比較,而不是確立完全公正的社會或理想的社會制度,參見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 vol.31, 2017, p. 265。可見,森有時又承認正義理論在比較評估中有作用,但這種正義理論不應是理想的。那么,森的正義理論是一種介于理想和應用之間的理論?對于森,作比較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不需要確定一個完美的樣本。比如,比較兩幅名畫的好壞不需要首先確定一幅最完美的畫;比較兩座山峰的高低不需要首先知道珠穆朗瑪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3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1- 102.然而,這類比較與在各種減少不正義或增強正義的方案之間作比較并不完全一樣,后一種比較不像森認為的那樣簡單。我們在對事物進行比較時必需依據一定的標準。比較各種選擇方案的優劣,確定哪種方案更能減少不正義或增強正義,不可避免地要參照正義原則。我們只能準確無誤地減少已知的不正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價值觀,所以我們不是白板”。4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 p. 43.實際上,前一種比較也離不開一定的標準。森有關兩幅名畫的比較暗含了比較所依賴的標準或原理,人們對于畫作的優劣實際上已有確定的標準。一幅最好的畫是一些原理的具體化,確定這樣一幅畫有助于對兩幅畫的優劣作出評判。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一個比森的山峰高低稍微復雜點的情形:如果我們要攀登世界最高峰,我們就必須知道目前珠峰是最高峰,然后在幾種可能的路線方案間作出評估,找出一條較好的路線。5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45; A. John Simmons,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8, 2010, p.35; 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 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 p. 34.
人們能夠識別的是最嚴重的不正義,并要求優先減輕這類不正義。這似乎是常識。然而,即使是減輕或消除最嚴重的不正義也不像森所說的那樣簡單。人們并不是天生就能識別出哪些現象或行為屬于嚴重的不正義,比如奴隸制。奴隸制是嚴重的不正義,這是人們根據一定的標準作出的判斷。森把世界上存在的“饑餓、貧困、文盲、酷刑、種族主義、對女性的壓制、任意監禁或醫療排斥”視為嚴重不正義。他認為,比較正義可以減少這些嚴重的不正義(不人道),比如預防饑荒、阻止酷刑、提供基本醫療保障。6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xi- xii, pp. 96-103.然而,壓迫、性別不平等,甚至奴隸制的減輕或消除是人類經長期奮斗而取得的道德進步成果,人們將這些在歷史上存在過的現象視為不正義經歷了一個過程,并非從一開始就把它們視為不正義,而且這些嚴重的不正義并未完全消失。人類社會奴隸制的廢除、性別平等方面的進步、反種族隔離以及反殖民主義的勝利是經由曲折的過程取得的重大道德進步。1Lea Ypi, Global Justice and Avant-Garde Political Agen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3-164.這些嚴重的不正義是最嚴重的不平等。當前一般的正義理論都把這些嚴重不平等視為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侵犯。隨著社會的發展,其他一些現象可能也會被視為不正義。森的比較正義僅限于在那些可以帶來“立即和明顯”的正義的方案之間作比較評估。2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52.對于森,我們判斷社會是否公正只需要以這些嚴重不正義為參加標準,而不需要參照完美的正義理論。3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2011, p. 300;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3.
然而,森的比較正義不能脫離理想的正義理論。森在多種選擇方案之間所作的比較評估只能參照既有的正義標準進行,實際上默認了這種或那種正義標準。恰如森自己所言,比較正義進路在已存在或有可能(feasibly)出現的社會間進行比較。4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 森對“可能”的理解或許有些狹隘,與其他學者對可行性(feasibility)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下文的探討會涉及這一點。比較正義的一個問題是不能引導人們實現包含更高要求的正義,不能根據更高的正義原則改造社會。希拉韋特指出,理論上的高要求與實踐上的高要求相關聯,正義理論有助于我們批判現狀,確定增強正義的長期目標。人們對正義的探索是一項永遠在進行之中的任務,必然會超越立即和明顯的正義提升,引導人們在認知層面和實踐中不斷追尋高要求的正義,減少不正義。離開了對理想正義理論的探索,我們可能會向我們本可以認識和減輕的不正義屈服。5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p. 44 - 47.
還有的學者指出,正義并不總是與評估選項相關,在現實生活中,作選擇的情況是很少的。比如,選舉屬于評估,但是,即使我們有幸可以選舉,大部分政治活動也都與選舉無關。很多時候,政治應該設定正義的理想,而清晰的正義理想有助于比較評估。有時我們離開了正義的理想就不知道什么是不正義。我們通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才深刻認識到社會制度的不公正是嚴重的不正義,逐漸接受了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這個理念。森的比較正義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不能診斷不正義。森認為,診斷不正義與比較正義無關。“但是,對某事不公正的原因的診斷本身就是伸張正義……(森)力圖以形式方法代替評價性方法,這使他的理論不適合任何一個政治目標的實現。”6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 p. 43.希拉韋特指出,確定支撐完美社會的正義原則與有關不完美社會的評價相關。我們的比較評估比較的是“描述性”特征,但是,“價值性”標準決定了哪些描述性特征是重要的。7這就說明,正義原則包
7 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45. 希拉韋特分析了完全公正的社會和正義在五個方面與森的比較評估相關,文中提到的是第一個方面,其余四個方面為:第二,完全公正的社會和正義原則對各種方案間的比較評估具有啟發意義。盡管各種方案都不可能是完美正義的體現,一些方案難分高下,但根據完全公正的社會和完美的正義原則,我們可以對這些方案進行有限排序,這樣可以排除那些侵犯基本人權(比如,嚴重貧困和獨裁統治)的方案。第三,比較評估有時很復雜,不根據高要求的正義理論,我們可能會作出不準確或者錯誤的評估,盡管正義理論不能列出所有供比較的情形,或者我們有時并不需要作全部比較。第四,正義理論有助于批判現狀,增強政治上的可行能力,在認識和實踐上提高把握增強正義和減少不正義的能力,為未來的改革做準備。第五,高要求的正義理論具有激勵和動員人們設定政治議程、開展政治行動以增進社會正義的作用。參見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 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vol. 15, 2012, pp. 46-48。含的價值觀讓我們在比較不同的正義或不正義狀況時知道應比較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比較評估不是森的比較正義進路所特有的,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也利用比較評估。希拉韋特指出,森的比較正義采取的是一種狹隘的比較評估進路,但是,比較正義應采用一種更寬廣的進路,以融合理論抱負和實踐導向。在他看來,森所區分的先驗正義和比較正義進路彼此并不對立。羅爾斯的實踐正義進路屬于這種更廣的比較進路,它不限于在立即可行的增強正義的方案之間進行比較評估,而是比較評估不同的理想正義理論和實施這些理論的不同方案以及不同的促成短期轉型的政治變革的非理想過程。這些比較評估過程包含了種種非理想的妥協和局部改善,但不放棄可能的深層變革。這種比較評估結合了有抱負的規范目標和動態的政治可行性。這種廣義的比較可以區分原則、制度和實踐,并且區分實施過程中所包含的改革策略;它還可以包括處于擴展之中的“政治行為、知識和想象”的長遠謀劃,而不是局限于對明顯公正和可行的增強正義的方案的短期比較。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所采用的反思的平衡方法包含了比較評估。希拉韋特運用這個觀念解釋了這種更廣的比較正義進路:有關政治行為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政治審議要求我們修正正義原則,在有抱負的長期社會轉型要求和短期政治行動之間進行反復的相互調整和平衡。1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p. 51-52, p. 55.
此外,森的比較正義進路忽視了正義原則和它的實施之間的區別。實現正義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會包含多維度的比較評估,包括識別困難節點,區分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以及實現長期正義目標所必須履行的動態責任,等等。2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5, 2012, p. 51.我們可以把正義目標實現的過程中分階段推進的正義視為過渡正義。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不僅探討了理想正義,也涉及了非理想正義。過渡正義是羅爾斯的非理想正義。過渡正義的目標是為過渡到理想正義作準備,創造使理想理論變得適用的環境,或者說,是為可能實現的完美的公正社會識別政策,3D. C. Matthew, Rawls’s Ideal Theory: A Clarification and Defense, Res Publica, vol. 25, 2019, p. 560.而不是判斷哪種方案更公正。森的比較正義與羅爾斯式的過渡正義之間有差異,前者是在幾種增強正義的方案間選擇一個更公正的方案,后者以完整的正義即以對正義的完全服從為目標。過渡正義的目的是最終實現完整的正義,推進過渡正義的政策是根據理想正義、由理性的政策建議者制訂的。相比之下,森的比較正義局限于在幾種社會方案之間進行比較,不以實現最終的正義為目標。羅爾斯式的正義理論也進行比較,但比較的是實際的行動環境與有利于正義的環境之間的差距,并據此給出行動建議。這種正義理論在不利環境和有利環境下都能給出建議。因而,不應在理想正義理論與不現實的烏托邦正義理論之間劃等號,有時前者是否能實現還取決于行動者。圣雄甘地、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或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把一些理想正義變成了現實。4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2014, p. 254.
羅爾斯的過渡正義是追求完整的正義目標過程中經歷的若干階段,而森的比較正義則滿足于當前環境中比較正義的結果,不追求完整的正義目標,甚至會阻礙完整正義的實現。有時,減輕局部不正義可能并不會有助于整體正義目標的實現。1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2014, pp. 254-255.A. 約翰·西蒙斯(A. John Simmons)注意到,消除一些嚴重不正義可能經常會促進理想正義目標的實現,但是,我們不能保證其他減少或消除不正義的情形也是如此。他還指出,如果我們放棄理想的目標正義,接受任何比較正義的成果,或者專注于處理一些特定的不正義,那么我們可能會使政治實踐不受任何系統性理論的指導。2A. John Simmons,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8, 2010, pp. 22-24.在托馬斯看來,森的比較正義會給一個社會如何從不正義狀態過渡到正義社會提供錯誤的建議。這是森的比較正義和羅爾斯式的正義理論之間的一種實質性差異。3Alan Thomas, Sen on Rawls’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2014, p. 257.羅爾斯的非理想正義是為了實現長遠的正義目標,對實施政策或行為有三方面要求:道德上是否允許、政治上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有效性。4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9.
在西蒙斯看來,我們至少有兩種評估一項政策的政治可能性和可能的有效性的方式。根據第一種方式,我們考察這項政策是否消除了它所要處理的特定不正義,并且考察這項政策與實現理想正義之間的聯系。這兩種做法會產生不同的后果。一項政策可能會減輕或完全消除一種特定的不正義,但卻會推遲或阻礙正義的實現,或對于實現理想正義的最終目標而言,這項政策比其他溫和的政策要糟糕。第二種評估方式將政策作為完全消除所有社會不正義的策略。羅爾斯式的非理想正義支持的是第二種評估方式。好政策有助于實現完整的正義目標。他還注意到,在一些情況下,比如當一種特定的不正義屬于社會結構的嚴重不正義時,一項能完全消除這種不正義的政策可能也是消除所有不正義的最好方式。5A. John Simmons,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8, 2010, pp. 21-22.西蒙斯注意到,羅爾斯式的非理想正義理論有時為了推進正義,可能必須先后退一步。假如非正義理想只給出一種符合過渡正義的政策,即有助于實現完整正義的目標的政策,為了確定哪種狀態更公正,我們就無需在這種政策可能實現的社會狀態和現狀或其他狀態之間作比較。6A. John Simmons,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8, 2010, p. 23.在這種情況下,森的比較正義就不起作用了。此外,西蒙斯指出,不受理想正義引導的非理想正義是盲目的,會受有關不正義的判斷的擺布,從而會作出任何改變。7A. John Simmons,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8, 2010, p. 34.羅爾斯說明了理想正義與消除當下的不正義之間的關系:“一種理想的正義觀念必須具體說明必需的結構性原則,并且指明政治行為的總體方向。如果背景制度缺少這種理想形式,持續調整社會過程以維持背景正義就沒有理性基礎,消除現存不正義也沒有理性基礎。因此,理想的理論規定了一個完全公正的基本結構,是非理想理論的一個必要補充。沒有理想的理論,變革的期望就缺少目標。”8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Expande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85.
四、森的正義進路與全球正義
森的全球正義觀與他的正義理念密切相關。他承認全球范圍內的相互依賴,支持全球正義。他指出,正義要求的倫理基礎是普遍的,應在全球范圍內減輕不正義和增強正義。9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 vol. 31, 2017, pp. 261-270.與他倡導比較正義進路相一致,森的全球正義是比較正義。他的全球正義的要求高于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他敦促消除一些“無法容忍”(outrageously)的不公正安排,但不要求一個完全公正的世界。1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那么,哪些不公正安排是無法容忍的?森提及了奴隸制、對女性的壓制、酷刑等這些嚴重不正義。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xi-xii, p. 96.全球正義應消除或減輕這些不正義。此外,他還認為,全球正義應處理貪心、貪婪和腐敗問題。3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 vol. 31, 2017, p. 266.然而,減輕或消除這些不正義在多大程度上增強了全球正義?當代大多數全球正義倡導者都會同意這些嚴重不正義的消除或減輕的確會推進全球正義。但是,他們有關全球正義的爭論超越了這些最嚴重的不正義的消除,爭論的核心問題變成了全球正義是否要求全球分配平等。森認識到,一個消除了奴隸制、解決了大范圍的饑餓以及掃除了文盲的社會離先驗正義所要求的完全公正還很遙遠。他會同意一個公正的社會不應只是沒有奴隸制的社會,但他不支持先驗正義所包含的平等的自由、分配平等等要求。4Amartya Sen, What Do We Want From a Theory of Justice?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03, 2006, p. 217; 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 2011, p. 305.可見,他的比較全球正義的要求過低。
森認為,當代政治哲學中主流的正義理論是先驗正義,先驗正義進路限制了正義的范圍,把正義限制在國家內部,體現出偏狹性。羅爾斯和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的正義理論都屬于先驗正義進路,反對全球正義,將正義限制在國家內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羅爾斯并不完全反對全球正義,只是反對把他的平等主義分配正義擴展到全球范圍,因而他反對的全球正義是全球平等主義。內格爾的確反對全球正義。但是,這兩位哲學家反對全球平等主義或全球正義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采用了先驗正義進路。當前其他很多政治哲學家支持全球平等主義,要求將羅爾斯的國內平等主義正義擴展到全球領域。有的學者指出,羅爾斯、內格爾和其他學者反對把平等主義分配正義擴展到全球領域不是因為他們堅持先驗正義進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認為全球領域中不存在與國內領域相似的社會關系,平等主義不適合應用到全球領域。5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5-26; 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 2011, pp. 309-310;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mas Nagel,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Philosophy and Public Aヵairs, vol. 33, 2005, pp. 113-147.
當前很多政治哲學家都支持全球正義,但是全球正義處于激烈爭論之中。全球正義爭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全球正義是全球平等主義還是全球充足主義,或者說,是要求把羅爾斯國內平等主義擴展到全球范圍,還是滿足于保障所有人的基本人權或者其他要求。但是,限于篇幅,筆者在這里不展開探討一些學者反對將平等主義分配正義擴展到全球范圍的原因。就森而言,他忽視了全球正義爭論的現狀。從森的視角看來,當前很多全球正義理論都采用了先驗正義進路。接下來,讓我們探討森認為先驗正義進路限制正義范圍的原因。
森認為,羅爾斯式的先驗正義限制正義范圍是由于其偏狹性,即不能聽取不同社會中人們的各種聲音。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在程序上是狹隘的,原初狀態設定了一個封閉社會,體現的是一種封閉的不偏不倚,只局限于聽取本社會成員的聲音,不考慮其他社會成員的聲音。相比之下,開放的不偏不倚可以考慮來自其他社會的冷淡觀察者的意見。正義理論的客觀性要求開放的公共推理。1Amartya Sen, What do We Want from a Theory of Justice?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03, 2006, p. 235;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 125-126, pp. 149-152; 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 vol. 31, 2017, p.264.森要求就全球正義開展由不偏不倚的觀察者參加的全球對話和全球公共討論。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1.他沒有正確地理解作為公平的正義以及獲得這種正義的原初狀態。在有的學者看來,森和羅爾斯兩人對公平的解釋不同:森把羅爾斯的公平理解為不偏不倚,而羅爾斯自己將公平解釋為互利。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機制的一個作用是探討一個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組成的社會的正義原則。這個社會是一個公平的合作體系,原初狀態中各方探討的正義原則是互利的。社會的公民是正義探討的參與者,他們之間是互利關系。不偏不倚是對裁判的要求,而裁判并不參與正義原則的探討。3Anthony Simon Laden, Ideals of Justice: Goals vs.Constraints,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6, 2013, p. 216. 有學者剖析了森的公開的不偏不椅觀念存在的其他問題,如: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 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pp. 40-42。對于全球正義,重要的是把互利關系擴展到全球范圍,使全球正義原則的探討考慮合理的批評聲音。4另一方面,這也說明森和羅爾斯的觀點并不完全對立,而是存在可以結合的地方,參見Anthony Simon Laden, Ideals of Justice: Goals vs. Constraints,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6, 2013, p. 217。此外,原初狀態貫徹了個體的道德平等這條基本道德原則。但是,一個包容社會之外的所有人的公開和公共的推理并不必然承認這條基本原則,會允許各種不可調和的立場,最終不會達成有意義的正義共識。5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2011, pp. 311-312.森聲稱,公共辯論包含的聲音越多,辯論最終就會越自由,對他人就會越尊重。事實上,由于森不承諾基本的道德平等,他的公共辯論沒有立場。6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 pp. 42-43; Amartya Sen,What do We Want from a Theory of Just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 103, 2006, p. 235.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設置與全球正義并不沖突,全球正義理論的構建可以利用或參照這種設置,每一個人都應成為全球正義探討的平等互利的參與者。
森推崇比較正義進路,強調減輕現實中的不正義或增強正義,倡導通過公共辯論來確定不正義。從他的角度看來,公共辯論不需要正義理論,全球正義的公共辯論同樣不需要全球正義理論。然而,森的公共辯論很難開展,或很難取得有關正義或不正義的共識。有學者指出,在公共辯論中,我們經常會遇到試圖讓別人理解我們認識到的不正義或理解他人認識到的不正義的情境。但是,由于森排斥他所認為的先驗正義,認為沒必要厘清正義的理想,實際上我們很難在上述情境中將辯論進行下去。7Kristina Meshelski, Amartya Sen’s Nonideal Theory,Ethics and Global Politics, vol. 12, 2019, p. 43.這就表明,公正辯論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理想的正義理論,從而超越森膚淺、經驗性的比較正義。恰如瓦倫蒂尼所注意到的:“作為個體,我們經常對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有深信不疑的信念,但是,我們沒有幫助我們檢查這些信念彼此間是否融貫以及理解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首要標準。作為集體,我們經常對什么是公正或不公正存在分歧,并且,當我們同意把一些行為或現狀斷定為公正或不公正時,我們總是會將它們進行不同的排序。”8Laura Valentini, A Paradigm Shift in Theorizing About Justice? A Critique of Se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27,2011, p. 307.這樣看來,森倡導的有關全球正義的公共辯論離不開全球正義理論的引導。
森指出,有關全球正義的公共討論的合適主題可以包括“如何增加安全、降低風險、擴大人類自由、控制不平等以及消除赤貧”。森還提及了其他需要解決的全球正義問題,比如,饑荒、全球性營養不良、全球性流行病、嚴重的人類不安全和苦難、全球經濟危機、全球變暖,等等。在他看來,人們應在公共推理的基礎上探討消除或減輕這些全球不正義。森認為,全球正義的公共推理應廣泛、系統化和信息化,應盡量移除公共討論的壁壘。1Amartya Sen,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Justic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ヵairs, vol. 31, 2017, p. 269; Amartya Sen,Reason and Justice: The Optimal and the Maximal, Philosophy, vol. 92, 2017, pp. 17-18.然而,森盡管倡導公共辯論,但排斥理想的正義理論的參與,這樣的公共辯論很難開展并獲得成效。這是不是他自己沒有深入參與全球正義爭論的一個原因?
他的比較全球正義與當前以是否要求全球分配平等為核心問題的全球正義爭論相距甚遠。他的比人道主義要求更多的全球正義是否支持全球充足主義并不清晰,他也沒有說明減輕那些嚴重不正義的程度。希拉韋特指出,盡管森支持全球正義,但他有關全球正義的探討令人失望,草率地否定了以社會契約進路(原初狀態)構建的平等主義全球正義,2Pablo Gilabert,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Justice, 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Ideal Theor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15, 2012, pp. 54-55.即否定了他所批判的先驗正義進路。
五、結 語
根據上文的探討,我們看到,森誤解了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給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貼上了先驗正義進路的錯誤標簽。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不僅僅關注或滿足于構建理想的正義理論和完全公正的社會,而是同時關注正義的理想和實踐。脫離了理想的正義理論,森所倡導的比較正義進路只能減輕或增強已知的明顯或嚴重的不正義。真正的比較正義包含的比較性評估離不開理想正義所設定的標準,即使嚴重的不正義的判斷也是根據正義的標準作出的。森的比較正義進路是一種狹義的比較進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則包含了一種廣義的比較性評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所采用的反思的平衡方法很好地體現了正義的理想和實踐的結合以及廣義的比較性評估。森的比較正義只滿足于減少眼前的不正義或增強正義,在一些情況下可能會阻礙長遠正義目標的實現,可能不利于任何政治目標的實現。比較正義可能會使社會變得保守,一些人止步于制定和實施只有助于減輕眼前的不正義和增強顯爾易見的正義的社會政策,喪失根據正義的理想進行社會改革的機會。
盡管森支持全球正義,但是,他的比較全球正義只滿足于減輕嚴重的全球不正義,實現僅高于人道主義的全球正義目標。他錯誤地認為包括羅爾斯在內的一些政治哲學家反對全球正義的原因是由于采用了先驗正義進路,而先驗正義把正義的范圍限制在國家或社會內部。他倡導通過公共辯論探討全球正義,傾聽其他社會成員的聲音,但是,我們看到,由于他反對理想的正義理論,不支持個體的道德平等,他的公共辯論很難進行下去,或者不會達成任何全球正義共識。可能由于他反對理想的全球正義理論,森自己并沒有深入參與當前在很多政治哲學家之間展開的全球正義爭論,忽視了全球正義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全球正義是否要求全球分配平等。可見,他的全球正義觀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