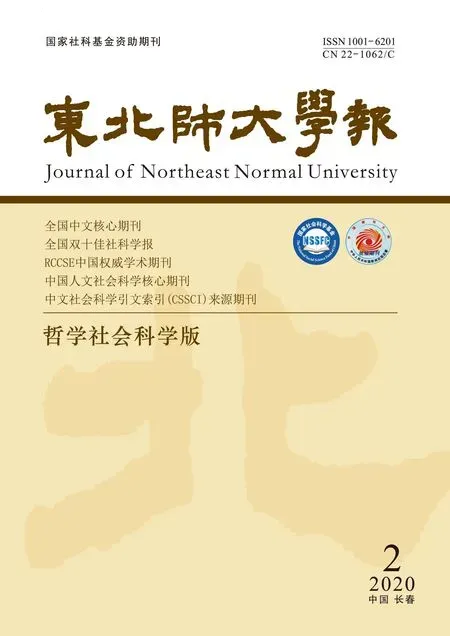中國新詩人稱代詞的詩學內涵與現代性發生
倪 貝 貝
(江漢大學 期刊社,湖北 武漢 430056)
“人稱”的說法源于英文中的“personal pronoun”,意為“身”:說話的一方是“第一身”,聽話的一方是“第二身”,說話和聽話之外的是“第三身”。故人稱代詞也叫“三身代詞”[1]。王力指出,“就英語而論,‘人稱’這個詞是有語病的,因為‘it’并不是‘人稱’而是‘物稱’。就中國古代語而論,‘其’和‘之’有時候雖是‘人稱’,然而有時候也是‘物稱’,只有就現代中國語而論,‘人稱代詞’這個稱呼總比較地適宜,因為咱們只有‘我’‘你’‘他’,雖偶然用‘他’字指物,但是可認為把物‘人化’了。”[2]從這個角度而言,人稱代詞應屬于現代語言學才有的概念范疇。邢福義將人稱代詞定義為“對人物起稱代作用的代詞”[3],同時,人稱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動態語素參與到語言交際活動中。由此,人稱代詞的基本性質被細化為三個維度:其一,人稱代詞具有稱代功能;其二,人稱代詞不僅指代言語交際雙方,還指代與之相關的隱匿第三方;其三,人稱代詞與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密切相關。
人稱代詞指代具有能動性的實體人物或對象,故與其他詞類相比更多體現出主體性表現功能。“我”“你”“他”等人稱的背后,隱藏著人的主體意識和認知以及人物觀察視角的存在。基于上述主體多重性特質,在文本敘述中一個人稱可以分裂為多個主體,“敘述者的話語本身就含有第二個或不斷變換著的第三個隱秘的敘述主體,它可能是在敘述者后面的那個文學主體——作者,也可能是在敘述者前面的那個文學主體——主人公”[4]106,兩者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巴赫金將作者和主人公在文本中的易混淆關系劃分為以下三種相處模式:1.主人公控制作者,作者須通過主人公的眼睛來觀察世界;2.作者控制主人公,主人公是作者情緒意志的反射;3.主人公本身就是作者[5]。當“主人公掌握作者”情況出現時,敘述人稱與主體人物人稱分離,主人公的自我意識超出了作者意圖的控制范圍,成為與作者對等的主體并與之產生對話,由此,多聲復調的特征在作者與主人公各自獨立的主體意識裂縫及沖突中產生。如果說人稱代詞的主體性在文本內部反映為作者與主人公的二元狀態,那么在文本之外,則因讀者對主體人物的主觀代入使文本呈現為“說者為‘我’,聽者為‘你’,被談論者為‘他’”[4]116的三角式對話關系。人稱的多重指向與切換使文本的敘述方式趨于復雜多樣化。敘述者越主動地在敘述過程中隱匿自身存在而將主體人物自覺呈現在大眾面前,讀者就越容易忘卻其接受者身份,并發揮主動性感同身受地進入文本與主體人物產生互動,使讀者自我與文本主體人物“我”趨于合一。從這個角度而言,正是敘述者(作者)、受述者(主體人物)、讀者的三維互動,進一步擴大了人稱的主體性表現功能。
從本質來看,人稱代詞是一種用于社會交際的語言符號。作為交流活動中專門指向主客體的詞匯類別,人稱代詞被賦予了強烈的對話互動性。在語言交際中人稱代詞雖用以表達個體情感態度,實際寄予了外界他者對自我認同及肯定的訴求。“‘我’這個概念本身就預設了‘你’的存在”[6],“我認為/感覺”的個體闡述其實展現的是“我希望你也這樣認為/感覺”的潛在對話關系。人的主體獨特性正是通過與他者的對話性交流得以實現。正如羅蘭·巴爾特所言,“人稱代詞是一種‘指示性符號’,它本身把約定性的關系和存在性關系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我只能借助一種約定性規則才能表示其對象。”[7]人稱代詞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下形成了自身完善的詞匯系統,主客體的情感表達與信息傳遞須在人稱既有的語言框架和范式中完成;另外,人稱代詞也作為區分主客體身份的符號出現。人與人之間信息交流的需要促使主客體分離,由主體對信息的施予傳達到客體對信息的接受反饋的回環實現,才意味整個對話過程的真正完成。在語用交流過程中,人稱代詞的詞匯體系呈現出流動更新的態勢。有些人稱逐漸被棄用,如文言人稱“自”“己”、稱謂名詞“寡人”“不才”等;與此對應,新的人稱開始占據常用位置,如現代女性第三人稱代詞“她”、指物代詞“它”的出現。人稱代詞大量涌入新詩的詞匯語法體系,是中國新詩在語言形式上異于古詩的一個突出標志。其在漢語詩歌中從古代到現代的演變以及彰顯出的現代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詩言說方式的變革,值得引起重視。
一、現代新詩中人稱代詞的形成與確立
自先秦起,人們的語言活動中已開始出現人稱代詞。據考據,殷墟甲骨文記載的常用人稱代詞包括第一人稱“我”“余”“朕”,第二人稱“汝”“乃”“爾”,第三人稱“之”“其”[8]。經兩漢魏晉至明清時期的發展,人稱代詞的詞匯及其用法更為豐富,不僅增加了“卬”“吾”“而”“戎”“若”“厥”“彼”等三身代詞,同時將諸多稱謂名詞納入進來。據粗略統計,人稱代詞在各歷史階段的大致面貌如下:

表1 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稱代詞發展概況(1)本表依據崔希亮對人稱代詞的斷代分析結論所制,見:崔希亮.人稱代詞及其稱謂功能[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0(1):46-54.
可見,古漢語人稱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自成一套詞匯體系。但就其在古詩中的表現而言,總體呈現出一種“由顯到隱”的發展態勢。
在古詩詩體形式成熟完備以前,人稱代詞作為抒情主人公的發聲者及代言人,在集體創作和早期文人創作的詩歌中常常可見。在集體創作中以《詩經》和樂府民歌為代表,其中既有第一人稱抒發內心感受的詩作,也不乏第一人稱與第二、第三人稱之間的對話交流,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小雅·采薇》)“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魏風·碩鼠》)“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東門行》)文人創作中以《楚辭》和先秦至兩漢時期的文人創作為代表。如屈原《離騷》在人稱的使用上詞匯豐富且數目繁多,包括第一人稱“朕”“余”“吾”“我”、第二人稱“汝”“爾”“君”、第三人稱“其”“之”“彼”等,涵蓋了當時大多數人稱代詞的用法。先秦至兩漢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與文化語境,以及詩歌形式較為自由多元的松散范式,使得文學主體的精神表達具有較為開放的空間,而主體呈現也會表現出特有的限度。歷代民間詩歌從精神主體到詩歌形式的不拘于詩歌規范束縛的自由姿態,決定了詩歌人稱代詞表現的多樣形態,當然也只會處于一種較為簡單的呈現樣式。
而當詩歌創作技法日益成熟并形成特有的審美范式后,人稱代詞在古代詩歌中急劇減少。表現之一是人稱代詞的多樣化形態向較單一化發生轉移。以唐代為界,不難發現唐以前的詩歌在人稱代詞的詞匯選擇上遠多于唐以后。以魏晉時期的詩歌為例,就有“我”(“彷徨忽已久,白露粘我衣。”曹丕《雜詩》)、“吾”(“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王粲《七哀詩》)、“余”(“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嵇康《幽憤詩》)、“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蔡琰《悲憤詩》)、“汝”(“官作自有程,舉筑諧汝聲!”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子”(“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陸機《赴洛道中作詩》)等三身代詞和“君”“妾”(“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曹植《七哀》)等稱謂名詞的交叉使用。對比之下,唐以后的詩歌(尤其是近體詩)多用稱謂名詞來指代人稱,三身代詞使用甚少。由此帶來詩歌人稱的第二個變化:由直指轉向屈指,人稱代詞在詩中的直接占位演變為隱匿到詩后。從創作觀念來看,唐以來的詩歌趨向于追求人與宇宙、自然合一的忘我境界,由此帶來詩歌從早期自由直白的情感抒發向含蓄敦厚的古典審美意境的轉變。此外,唐以后的詩歌體例日趨純熟,必然要求詩歌創作遵守嚴密的格律規范。為滿足詩歌嚴格的字數限制與對仗性的工整,人稱代詞及虛詞等能夠為讀者于詩外意會而又不影響詩意表達的詞匯自然被剔除到詩句之外。
清末民初時期是一個社會急劇變革與轉型的歷史階段。受時代思潮和外來新事物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無論是在思想觀念還是內容題材及語言表達上均呈現出與傳統古詩相異的趨勢。詩歌創作相比以前更為注重個人的存在,不再刻意隱匿人稱。至“五四”時期,對個體精神的彰揚達到高潮,人稱代詞開始大量涌入現代新詩。必須看到的是,無論是人稱代詞自身詞匯、句法、語用等語言形式的變革,還是其在新詩中的發展成型,均非輕而易舉、一蹴而就,而是在社會文化因素的參與下,經過長期地選擇、較量、淘汰與磨合后最終形成。
清代以降,詩人對人稱代詞的態度從有意回避逐漸轉為欣然接納。根據清至近代詩歌在人稱代詞上的使用情況顯示[9],“我”“吾”“汝”“爾”“君”的使用最為普遍,同時也有“余(予)”“老生”“老夫”“臣”“諸君”“儂”“郎”“妾”“女公子”等人稱的摻雜使用,表現出人稱代詞的使用頻率增多、各式新舊人稱代詞雜糅并存、傳統人稱逐漸向現代人稱過渡轉化的特點。
以黃遵憲的《今別離》為例,這首詩以古樂府的形式將傳統離別相思主題與西方現代科技術語融為一體,頗受時人關注。值得關注的還有其中多個人稱代詞的疊加使用。詩中既以“妾”“君”等稱謂名詞來自稱和他稱(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營造出傳統古詩含蓄纏綿的古典意境;也運用“我”“汝”這樣的三身代詞構成你我之間的交流互動(如“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使詩歌初具現代意味的對話性;此外,自稱代詞“我”和稱謂名詞“妾”的互換疊加(“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使詩歌中的主體性意識得以初步彰顯。可以說,近代詩人對詩歌人稱代詞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古詩含蓄蘊藉的審美傳統,使詩歌語言風格開始轉向明白曉暢,同時為人稱代詞在新詩中的進一步發展和定型奠定了基礎。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推動下,古代漢語長期秉持的語用傳統被打破,現代漢語的語法思維模式逐步建立。現代白話文的誕生,對傳統文言文句式表達產生巨大沖擊,隨之使古代漢語交際中的典雅化人稱日漸被現代漢語的日常化人稱取代。“五四”前后新詩在人稱代詞的取舍上具體呈現出以下幾種態勢:
其一,除了“君”“卿”等少數不確指稱謂仍有保留使用以外,古詩中常見的“賤妾”“老夫”等傳統稱謂名詞大部分已走向消亡,而“俺”“你老”“大家”等富于方言特色的人稱代詞取而代之在新詩中出現。如胡適的詩作《示威》:“俺做事一人擔當,/怕死的不算好漢!”《人力車夫》:“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平民學校校歌》:“大家努力做先鋒,/同做有意識的勞動!”現代口語化人稱的進入,使詩歌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從貴族化、典雅化向大眾化、平民化的傾向靠攏。
其二,復數人稱詞綴“們”和第二人稱“你”入詩,可謂現代漢語人稱代詞在“五四”以來的詩歌表達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古詩中無直接可用的復指人稱,只能在三身代詞后加上“輩”“等”構成復指性稱謂,如“吾輩”“爾等”,指義含糊不明。現代漢語以“們”作為復數詞綴,使復數人稱用法趨于規范。此外,不同復數人稱語義上的細微差異對詩歌表達產生了相異效果。以“我們”和“咱們”為例,王力認為,雖同為第一人稱復指,“咱們”把對話人“你”包括在內,“我們”則不包括對話人:“咱們=我+你(或再和別人),我們=我+他或他們(但沒有你在內)”[10]。試比較以下兩例詩句:胡適《示威?》:“咱們天橋瞧熱鬧去。”以口語化人稱“咱們”表述詩中人物話語,將主客體的距離拉近,顯得親切生動,符合初期白話詩歌淺顯直白的語言要求。馮至《別離》:“我們招一招手,隨著別離/我們的世界便分成兩個。”運用的人稱代詞是“我們”,目的在于描述一個基本的事實,并未邀請對話客體的參與,相比“咱們”要正式且語氣更為客觀化。在第二人稱的處理上,古詩多采用特定的稱謂名詞或敬語(如“君”“子”“公”“翁”等)在主客體之間造成疏離感。由此一來,形式上在場與主體產生交流的客體實際上是并不在場的他者,“‘我’和‘你’的關系本質上仍然不過是‘我’和‘他’的異在關系”[11],整首詩其實仍是主體個人情感體驗的抒寫。新詩直接以“你”來稱呼對話客體,抹去了主客體的不對等身份差異,營造出一種平等交流與情感互動的氛圍,使詩歌實現由獨抒性靈向現代開放對話模式的轉型。
其三,第三人稱代詞在詩歌創作中出現分化。在早期白話詩里,無論是指代女性(如胡適《病中得冬秀書》:“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總常念他,這是為什么?”)還是指代事物(如周作人《小河》:“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多以“他”統稱之。這種第三人稱“他”通用的局面在現代新詩語言的日趨成熟中迅速被打破。一方面,現代文化語境促生了諸多新的第三人稱詞匯,較有代表性的如“她”“伊”[12]、“牠”“它”等。詩人在詞匯選擇上的不同偏好,使新詩中的第三人稱單數客體呈現多樣化特征。另一方面,女性第三人稱代詞“伊”“她”相繼被提出或創立,并在使用過程中出現相互抗衡的現象。而“詩歌對文字簡潔的高度要求,其達情的特別需要,象征似表達的慣用手法等,都為女性代名詞的‘她’提供了無限廣闊的用武之地。”[13]經過語言學者、詩論家的論爭及社會大眾文化的長期考驗,“她”取代“伊”被多數現代詩人用于詩歌實踐,“她”字的女性指代意義最終被確立。
經前人長期的探索與反復實踐,“五四”以后至三十年代新詩的人稱代詞詞匯體系基本定型并走向規范化,形成以現代漢語三身代詞、無定代詞和復指代詞為詞匯來源,以“我、你、他/她/它們”為主要人稱來指代詩歌主客體的人稱范式。從詞匯類型及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新詩在人稱的選擇上相對減少。而在表達上,詩人靈活運用人稱的多重變換,在新詩中打破抒情主體與符號他者之間的藩籬[14],借用他者發聲或運用不同聲音之間的沖突、對話,產生面具化發聲的戲劇性效果,使詩歌內涵開始趨于復雜化。
通過對漢語詩歌中人稱代詞的線性梳理我們發現,中國新詩中的人稱代詞是在各種文化因素和語言土壤的培育下積淀生成的。大體而言,現代漢語詩歌人稱代詞主要有兩大詞匯來源,一是對古代漢語語用和文學創作中的人稱及稱謂的挪用與改造;二是在吸收各類方言和外來詞匯的基礎上借鑒衍生出人稱代詞。
新詩中人稱代詞對古代漢語詞匯的改造集中表現為以下方面:首先,運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將古漢語中原先不屬于人稱代詞的詞匯借用過來,賦予新的詞性意義,使其成為新詩中的常用人稱。如“她”字并非現代詩人劉半農所創,而是古已有之,在《說文解字》《淮南子》《六書故》等古文獻中皆有記載,可看作“姐”的別稱。劉半農的貢獻在于,借用“她”這一古字的字形而摒除其原有古義,使之成為現代漢語中專為女性(包括具有女性氣質的事物)所用的第三人稱代詞。又如“們”字最初見于宋代,但“并不單純表示復數,只簡單地作為人稱代詞和某些指人的名詞的詞尾”[15],經現代漢語的發展改造,在新詩中專用于復指。其次,對傳統稱謂名詞加以繼承與變革后使用,在初期白話新詩中表現尤為明顯。如“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中的“卿”(胡適《希望》(譯詩))、“緊緊的跟,緊緊的跟,/破爛的孩子追趕著鑠亮的車輪——/先生,可憐我一下吧,善心的先生!”(徐志摩《先生!先生!》)中的“先生”,都是古代漢語中表示身份稱謂的名詞,在新詩中均被借用為人稱代詞甚至直接從其演變而來,相當于第二人稱“你”。可見古代漢語人稱及稱謂詞匯是我們考察中國新詩人稱代詞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它為后者的發生提供了傳統型參照和成長空間。
除此之外,方言和外來詞匯的刺激也構成了現代新詩人稱代詞的靈感來源。表現之一是不同的語言成長環境對詩人在人稱上的選擇造成影響,如江浙、安徽等地南方詩人胡適《瓶花》、馮雪峰《花影》、汪靜之《蕙的風》、應修人《小小兒的請求》等詩作對“伊”的偏愛,使該人稱成為早期白話新詩中一個重要的語言符號。為表現地方性的風土人情,詩人也會有意識地入鄉隨俗,將當地的方言土語融入詩歌語言,使其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色。如北京、河北、山東等地喜用“咱們”“您(你老)”“俺”等口語化人稱。反映到新詩當中,如傅斯年《咱們一伙兒》:“太陽,月亮,星星,鬼火,——/咱們輪流照著,/叫他大小有個光,/咱們一伙兒。”卞之琳《春城》:“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鷂鷹/在馬德里蔚藍的天心,/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見您哪/京都!”阮章競《漳河水》:“戲鼓咚咚響連天,/唱盡古今千萬變。/唱盡古今千萬變,/沒唱過俺女兒心半片!”形成淺白自然、平易近人的語言風格。表現之二,外來詞匯和語法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拓寬甚至改變了現代文人的構詞思維。英語詞匯“she”的翻譯難題,推動了現代女性第三人稱代詞“她”的產生。與此對應,物主代詞“it”也需要有一個詞來指代,由此出現了“牠”“它”“祂”三字作為中性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競爭。古代漢語中,“它”和“他”被視為同一個代詞的兩種不同的書寫形式,到現代始被錢玄同、陳獨秀等人主張用于指代中性第三人稱。“祂”的創立,則用于指稱上帝、耶穌或神,也指代不在性別范圍內的第三人稱。經過社會大眾文化的反復實踐,“它”字最終脫穎而出取得勝利,新詩中以“他”指代物性第三人稱的局面被打破,人稱開始趨于規范化使用。
二、人稱代詞的“現代性”與“詩性”
從早期漢語語用及古代詩歌、民間歌謠中的情感和信息傳遞來看,古代漢語人稱代詞很少直呼具體主體或對象人物,而是將主體的社會角色與心理定位隱藏其中,呈現出“曲折代指”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常見的表現形態:(一)用表示人物關系和身份的詞來替代人稱,如“翁”“妾”“君”等;(二)在具體語境中用尊稱、敬稱或帶有感情色彩傾向的稱謂名詞進行自稱或他指,如“令堂”“老夫”“賤內”“豎子”等;(三)借用比擬性事物來喻人,對所指人稱的褒貶態度通過借指的事物來傳達,如《紅樓夢》第十五回北靜王借用李商隱的詩“雛鳳清于老鳳聲”,即是用“雛鳳”來稱贊賈寶玉人才品格的出眾。因此就指向功能而言,古漢語人稱代詞實現得并不明確——它們往往并非指向人物對象本身,而是通過某種社會倫理關系的約束來確立自身存在的依據。
現代漢語人稱代詞摒棄古代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構詞方式,以直指性、確指性的指代詞替代古代漢語的含蓄隱晦式稱呼:用于自指的通用第一人稱“我(們)”取代“吾”“朕”“鄙人”“不才”“晚生”等,大大縮減了需依托特定語境來使用的稱謂詞的數量,使人稱代詞的用法趨于規范,將語用中對稱謂背后的身份標識的關注轉移到話語本身的意義上來;第二人稱“你(們)/您”取代“君”“汝”“卿”“子”等,使隱含尊卑關系的不對等交流轉變為平等性對話;第三人稱“他/她/它(們)”取代“其”“彼”“之”等,弱化了客體對象的虛指內涵與不確定性,使語言表述與意義指向更為明晰、準確。從古代“吾”“予”“爾”“汝”“其”“之”等到現代“我、咱(們)”“您、你(們)”“他、她、它(們)”“人家”“自己”等過渡轉變,不僅體現了古今人稱代詞在詞匯選擇運用上的異同,更折射出二者在文化趨向和社會心理上的巨大差異。與古漢語人稱相比,現代漢語人稱代詞被賦予了前者無法類比的現代性。
首先,現代漢語的語法結構及句法形式催生了現代漢語人稱代詞語法占位的自由化。古代漢語表達受文言文句法的束縛,人稱代詞的數目龐雜且用法各異,故在詞匯選用上極為嚴格講究。如第一、二人稱“吾”“汝”用于主格和屬格,“我”“爾”多用于與格和賓格。第三人稱“其”僅用于屬格,“之”只用于與格和賓格[16]。與此不同,現代漢語在簡化人稱代詞詞匯數量的同時也減少了語法對人稱占位的限制,使其得以呈現多樣化的表現形態。如常用的三身代詞“我、你、他/她”既可以用作主格:“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徐志摩《為要尋一個明星》)、“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戴望舒《雨巷》),也可用作賓格:“那是去年的我!”(胡適《如夢令》)、“那燈下是我在等你”(饒孟侃《招魂》),還可以與其他詞匯組合構成偏正或兼語短語做定語或狀語:“我聽見你的真珠的淚滴”(穆木天《淚滴》)、“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胡適《“應該”》),等等。人稱代詞的多種占位可能性,為現代漢語交際和創作提供了自由靈活的表達途徑。
其次,現代漢語人稱代詞的“去身份化”特征促使其指代對象呈現多元化。由于摒除了內在社會化標識,不同于古代人稱“朕”只適用于君王[17]、“妾”作為女子對自己的謙稱等用法,現代漢語人稱代詞很難僅從詞匯的取舍來判斷話語主體或指代對象的身份,而要結合具體的語言環境作具體分析。如“她”作為女性特指第三人稱代詞,可稱呼戀人:“她是羞澀的,有著桃色的臉”(戴望舒《我的戀人》),可指代母親:“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汁之后,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可喻指富于女性化氣質的事物:“新嫁娘最后漲紅了她豐滿的龐兒,被她最心愛的情郎擁抱著去了”(郭沫若《日暮的婚筵》)。由于語言環境的不同,同一人稱代詞因可以指向多種主體行為人被賦予了頗具包容性的豐富情感內涵。
最后,現代漢語人稱代詞的普遍性適用原則引導語言表義走向理性客觀化。古代漢語人稱代詞因有主體社會意識的潛入,帶有明顯個體情感傾向[18]。與之相異,就詞匯本身來看,現代漢語人稱代詞與名詞、動詞、介詞類似,均表現出語言學純粹科學化的中性色彩,這使其在交流運用中得以理性客觀地展開敘述。以書信為例:
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于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于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胡適《致陳獨秀》)
同為與友人之間的書信交流,上述二者因人稱代詞的不同選擇呈現不同效果。前者以“吾”自稱,以“足下”敬稱對話人,在情感態度上拉開了說話人與對話人間的距離,謙恭有余而親密不足,潛意識里透露出拒絕與對方作深入交流的信號。后者以“我”自稱,以“你”指代客體對象,其間還摻雜了共同主體“我們”。整個敘述過程客觀平和,敘述主體要傳達的信息不因人稱的主體傾向性導致情感上的誤讀或偏差,交流主客體及讀者的關注重點不在于由人稱代詞引發的情感推動力,而在于敘述事件本身。
現代漢語人稱代詞在文學創作活動中隨處可見,反映在不同文體上又各有偏重:小說注重情節的生動與曲折性,作者的意圖與情感傾向往往通過人物直接發聲或讀者的介入來實現,故多采用“作者代入人物”的第一人稱或“作者與讀者旁觀人物”的第三人稱視角來展開敘述;散文重視內容的寫實性,人稱一般帶有作者自述的痕跡;戲劇由于涉及多個人物關系和場景對白,具有多人稱對話視角轉換的特點。和上述文體相比,詩歌因自身特殊的表現形式賦予了人稱代詞獨特的詩性特征。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稱代詞在詩歌中擔任顯在或潛在抒情主體的角色。自先秦起,詩歌就有“詩言志”“詩緣情”的傳統,抒情性是詩歌區別于其他文體的重要特質。無論是人稱代詞相對隱蔽的古詩,還是以彰顯人稱作為主體性解放之標志的現代新詩,其間都有一個抒情主體的存在。前者如“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其間隱含著送客人“我”和故人“你”的情感互動,詩人對友人的情意通過隱匿的抒情人稱“我”望江惆悵的畫面予以呈現。與此相比,新詩尤其強調突出個體的生命體驗,人稱代詞在新詩中的使用,不僅是為了滿足詩歌內容與形式表達的需要,更是詩人自我主體意識張揚的體現。如郭沫若在《鳳凰涅槃》所傾訴的:“我們歡唱!/我們歡唱!/一切的一,常在歡唱!/一的一切,常在歡唱!/是你在歡唱,是我在歡唱?/是‘他’在歡唱?/是火在歡唱!”作為承載主體人物發聲的代言者,詩歌中的人稱代詞呈現出多樣化的表現形態:以“我”為情感主體,交雜以“我們”“你”“他”等多個抒情人稱,極力凸顯個體情感的宣泄抒發。
其二,人稱代詞在詩歌中起到完善詩歌內容和結構形式的重要作用。詩歌作為一種文字簡短凝練而又包含豐富情感內蘊的文學樣式,在句式組合和遣詞造句上要求極為精密。古詩講究“以字煉意”,盡量在一首詩內實現每個字詞的高度準確表達。這種對文字的嚴苛程度在其他文學體裁中是少見的。當人稱代詞作為詩歌的語言要素之一,其語法占位就獲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與不可替代性。無論是“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衛風·氓》)中的人稱代詞“我”“爾”,還是“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她的溫存,我的迷醉。”(徐志摩:《“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中的人稱代詞“我”“她”,都是既擔任著詩歌的抒情主人公角色銜接詩歌內容,又作為詩歌字句的必要組建因素保證詩歌結構的完整,無法刪去或用其他詞匯類別來替代。
其三,人稱代詞有助于詩歌審美表達的有效完成。基于詩歌“言簡意深”的文體特征,其在文字工具上每一次大的調整與變革,均有可能不同程度地突破乃至重建詩歌原有的審美范式。表現在人稱的運用上,從“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古詩十九首·冉冉生孤竹》)人稱代詞由“我——汝”的對等關系向隱含尊卑等級的“君——賤妾”轉變,從側面印證了古詩由自由開放向規范典雅的審美追求的演變。在以自由的散文化詩體為主要創作形式的現代新詩中,人稱代詞的大量使用更成為詩人實驗現代白話新詩語言表現力的有效工具。這一點在率先使用白話語言作詩的白話新詩派那里得到體現。如胡適《一念》:“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我”作為獨立個體以一種平等的視角與宇宙對話;劉半農《一個小農家的暮》:“灶門里嫣紅的火光,/閃著她嫣紅的臉,/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他銜著個十年的煙斗,/慢慢地從田里回來……他還踱到欄里去,/看一看他的牛,/回頭向她說:/‘怎樣了——/我們新釀的酒?’”詩中場景在“他”和“她”兩個視域之間轉換,最終在“我們”這里重合,多個人稱在詩中轉換并置,營造出戲劇性的詩意表達效果。
現代漢語人稱代詞的頻繁使用,已成為“五四”以來新詩中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歷史成因,以及人稱代詞在新詩中占位所帶來的詩歌審美形態及功能轉向等一系列問題,值得細致深入地探討。在對中國新詩人稱代詞的現代性發生作歷史性還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語言活動本身是一個流動發展的動態過程,而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則從不同側面促發了現代漢語人稱代詞在新詩中的涌現,新詩人稱代詞詞匯體系的形成,是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后現代詩人自覺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