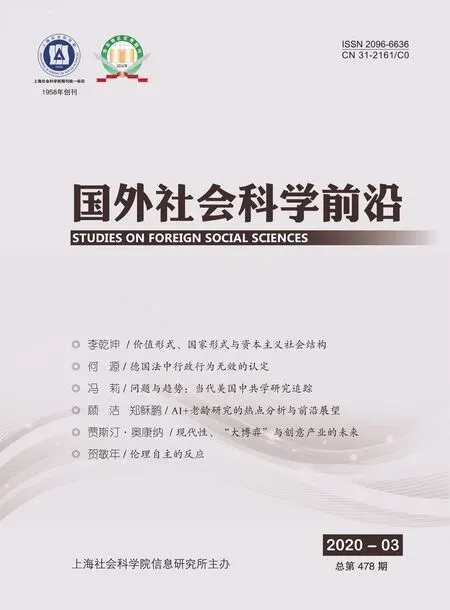現代性、“大博弈”與創意產業的未來 *
賈斯汀·奧康納
內容提要 | 中國目前成功加入了全球創意產業的“增長”敘事,但在實力增強的同時,中國也與美國開展了競爭,尤其是在具有全球價值的技術設施領域。在被美國視為“超級對手”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之爭。如何借“冠狀病毒暴發”在全世界帶來的喘息機會,認真思考何為“美好生活”,如何“共同建設美好生活”,是中國當下大有可為的命題。西方現代性強調“進步”與“增長”所制造的生態危機,需要中國以東方智慧,提供不同的道德理性來加以平衡。
現在看來,質疑中國的體制是否能打造一個“創意經濟”,已經是過時的觀點。當然我們可以說,一個擁有14 億人口、收入在持續提高、服務業持續發展、國內消費持續增長的國家,總是會有一個龐大的文化產業在為其服務。中國的互聯網防火墻并不像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所說的那樣,是白費勁地把果凍釘在墻上,而是為自己堪稱優秀的數字平臺建設打下了基礎。我們再也不能用“要么轉型,要么出局”這樣的兩難困境來描述中國了——這個國家已經成功地與創意產業不斷“增長再增長”的故事融為了一體。在有關“創意產業”的敘事中,唯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那些有可能阻礙這一“產業部門”發展,或是對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產生限制的議題。這對英國(尤其是脫歐后)、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尤其是德國、法國和荷蘭)等希望進入中國市場,也歡迎中國對其投資的國家來說,顯得尤為重要。然而這對美國來說,沒那么重要。美國仍然是全球文化產業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目前仍處于由它的五大科技企業巨頭臉譜網、亞馬遜、蘋果、奈飛、谷歌(FAANG)等在全球的成功所帶來的亢奮狀態之中。對美國來說,中國在內容上還談不上“威脅”——事實上,所有人都認為中國的軟實力,即便在東亞地區也是不溫不火的。關鍵點在于,中國在數字平臺構建了屬于自己的龐大市場;此外,中國的數字通訊技術已經開始進入西方國家基礎設施的核心。
雖然“軟實力”這一概念將大家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內容上,但美國在全球文化產業中的主導地位依賴于它對一些基礎領域的控制——商業、技術和法律等。美國通過打造蒂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在談論石油產業時所提到的“技術層面”來控制文化產業,也就是“一套表面上看互不相關但實際上暗中協調的規定、一些精心計算過的安排、各種五花八門的基礎設施以及為了控制對象和資源流動所設計的技術程序”。1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London: Verso, 2011, p.40.被限制進入全球最大的市場是一回事,感覺你對某項具有全球價值的重大技術設施的控制權被某個國家削弱了,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當創意產業那些過分樂觀的經濟師們正在歡迎一位新成員加入他們的“全球增長俱樂部”時,美國開始喊停了。2有關“全球增長俱樂部”,參見Stuart Cunningham and Terry Flew,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2019, pp.146-163.雖然有人會對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戰”中一些細節感到不安,但這些不安最終都會平息在美國兩黨已經達成的共識上:“中國一直在作弊,再也不能讓它搭順風車了。”中國開始同時扮演以下幾個角色:一是“敵對帝國”的角色,該角色在20 世紀30 年代由德國和日本扮演過,后來又由蘇聯扮演過;二是需要被馴服的“經濟對手”,就像《廣場協議》簽署前的日本和20世紀90 年代的歐盟;三是“敵對文明”的角色,譬如石油危機后的中東。作為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地緣大國、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對手、一個截然不同的文明體,中國具有成為美國超級對手的所有條件。
1792 年,當隨外交使團抵達中國之后,馬戛爾尼伯爵(Earl Macartney)的副手喬治·斯湯頓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2 歲的兒子開始學習中文。勤奮的托馬斯·斯湯頓(Thomas Staunton)作為非正式翻譯人員,開始了他研究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漫長生涯,并于1823 年和他人一起創立了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1840 年,在英國下議院那場關于是否要發動“鴉片戰爭”的著名論戰中,托馬斯·斯湯頓爵士強烈支持對中國開戰,聲稱如果允許中國人焚燒廣州倉庫這樣的侮辱行徑存在,會對大英帝國的聲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3Harry G.Gelber, Opium, 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Britain’s 1840-42 War with China,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95.他可以被看作有條件近距離了解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但又對中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表達憎恨的西方學者或旅居者的第一人。中國具有的悠久文化,可能很少有外國人能夠馬上完全適應,但這并不會影響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好感與理解。然而,當他們的國家與中國的關系緊張之際,其中有些人會感到有必要站出來,說一些警告的話。目前西方國家反華言論的激烈程度——尤其在英語文化圈——達到了1989 年之后的最高水平,而那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西方與中國的經濟融合程度,遠不及今天的水平。這些反華言論的主導修辭是“快醒來吧,中國的快速發展正在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給全世界帶來不可控制的影響”。在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當“歷史終結”以后,資本主義被認為是通往增長、進步和現代性的唯一道路,中國的快速發展只會讓它在美國的“良性主導”下逐漸融入現代化的全球社會。現在,我們被催促著正視這一想法的天真,“我們被欺騙了,被搭了順風車,現在我們必須超越對‘錢包’的關心,看到我們的基本價值觀正在再次受到威脅這一事實。”這樣做的目的和結果是,把大家緊緊封鎖在“我們的”價值觀之中,這些價值觀與“他們的”有著根本的不同。
西方人早已學會了用滿不在乎的口氣談論“政權更迭”。在代表著西方現代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4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是象征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所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等奠定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的原則。——譯者注核心地帶以外,他們對類似事情一直是如此處理的。在“基本價值觀”的范疇內,我們有一整套政治、經濟、行政和技術安排,這些是不能被觸及或是受質疑的,它們只能被出口,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器。當下甚囂塵上的所謂“認清中國”,就是要接受那些最愿意站出來堅決反對中國的政客,就是要把他們對西方價值觀的傳播當作不言而喻的真理。類似情況以前也發生過,而且發生過好幾次了。
在這本書中,我們通過“創意產業”這一概念,勾勒出對“現代性”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這兩種敘事,不斷地互相交織和分離,有時和諧有時沖突,然而不知何故,如同復調音樂一般,它們最終抵達的是同一個“現代”目標:進步與增長。這兩種與現代性有關的、至少從18 世紀中期以來就開始為人類帶來生機與希望的敘事,今天正在走向終結。直到目前為止,西方和中國都還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一結局,也不知道這對他們各自來說,可能意味著什么。西方資本主義提供的是一個實踐起來將產生最多問題的版本:它的帝國夢,現在集中于一種具有掠奪性質的全球化的新形式,其中沒有任何有關多極化、多樣性、多重性或互惠性的理想。正是對上述這些理想的追求,全世界開啟了一個“后歷史”的黃金時代。正如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言,我們已經從全球化的“正向”發展階段轉向了“負向”發展階段。1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眼下,仍然相信“進步與增長”的中國,正在猜想“現代性”能夠以某種方式,克服它為自己制造的挑戰。2019 年,根據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正式上映。在這部電影中,因太陽即將毀滅而對地球造成的生存威脅,被人類以推進引擎將地球移出運行軌道、駛向另一個星系而得以解決。停止地球自轉所引發的海嘯和地震,摧毀了地球上的一半人口,活下來的人也有很多無法被容納進地下生存空間。電影中的中國工程師運用各種科技手段,拯救了地球和人類的未來。片中人物的態度是:為了保證人類物種的延續,拯救行動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目前,中國仍然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市化進程、大規模投資科技研發等,作為繼續通往現代性的道路。這一“現代性”由中國共產黨提供保障,也將進一步鞏固它在這個國家的領導地位。
從全球來看,資本積累體系對文化領域展開毫無顧忌的吸納,這一過程是從20 世紀90年代開始加速的。在世紀之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符號交換系統開始受到計算機“算法”的控制,導致一種“超加速”的積累過程,該過程只有通過對個人數據的大規模提取才能實現,而“監控”是這一過程的“暗物質”副產品。這樣一個過程,對社會及其象征秩序、公共領域、言論的理想情境、理性對話的可能性等諸方面,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并且日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上述這些領域,在西方和中國都處于一種重構的過程,但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一過程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進行的。在中國,代表著“象征秩序”的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2“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主義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譯者注而西方則被各種不和諧的嘈雜聲充斥,震耳欲聾。
數字平臺及其所推動的“算法治理”存在著嚴重問題,即資本體系對個人價值的提取程度越來越高、侵入性越來越強。誠然,對那些關注“社會工廠”問題的人來說,他們所感到的是一種一直在進行的、不斷從生活世界中提取價值以滿足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不公。正如羅安卿(Anna Lowenhaupt Tsing)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總是能不斷地從“前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以及“后資本主義”等各種社會形態中提取自己想要的價值。3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然而,問題并不只在于不平等的“價值提取”,以及其中所可能存在的對生產者生活世界的扭曲與破壞。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把文化系統逐步簡化成“商品邏輯”,這一做法對“社會”自身具有極大的破壞性。這樣的做法越來越阻礙了社會原本具有的、將“文化活動轉變為知識”的能力。這就是伯納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說的“符號性貧困”(symbolic misery),1“符號性貧困”是法國哲學家伯納德·斯蒂格勒在《論符號的貧困:超工業時代》中所提出的概念,指在超工業時代,大多數人的美學探索精神被市場營銷學所營造的美學禁錮,失去了真實感知,以及與世界聯接和表達自身的能力。——譯者注他借此所要表達關注的是:我們人類作為有思想的存在,在表達自身對于意義的深層需求方面,正在表現出“集體無能”。在“商品化”和“算法”的控制下,逐步瓦解了的文化系統,導致他所說的“對知識本身的否定”。這是虛無主義的一種當代表現形式。
我們該如何克服這一困難,是一項緊迫的任務。我們不可能沿著陳獨秀所說的“飛矢”2此處化用陳獨秀語句:“人類文明之進化,新陳代謝,如水之逝,如矢之行。”出自1916 年1 月15 日《青年雜志》第1 卷第5 號《一九一六》。——譯者注抵達未來——那是一條在想象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有關“進步”的“直線”。如果我們要避免在極端右翼學說影響下逐步蔓延開來的“黑暗啟蒙”,及其所帶來的倒退,那么我們對當下所謂“進步”的否定,就不能只是一次否定,還應該是對“啟蒙”的一次徹底的重新評價。我們需要在“理性”被壓縮為一個機械的、工具性的外殼以前,再一次向大家宣揚“理性”所具有的延展性與開放性。3關于“徹底啟蒙主義”這一概念,參見Arran Gare,The Arts an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Gaining Liberty to Save the Planet, The Structurist, vol.47/48, 2007/8, pp.20-27.在18 世紀末的歐洲,藝術曾經有過一個特殊的“現代使命”,藝術具有表達和“消化”工業和民主現代性為人們所帶來的深刻沖擊的能力——這就是藝術的“世界相關性”。4也被翻譯為“藝術與世界的恰當關系”。參見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rmative Defiance, Breda: Avans Hogeschool, 2016.對于藝術這一至今仍緊迫存在的歷史任務,目前各國正在大力發展的以“消費”、“算法”與“產業數據”為核心的“創意產業”,不僅沒有提出解決方案,而且日益成為人們在提出“藝術的歷史使命”時所面臨的重大阻礙。
一種經過重新思考的“現代性”,不會僅從歐洲和歐洲內部一個角度來進行論述。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起源于公元前800 年—前200 年世界“軸心時代”的亞洲宗教與文化,為我們今天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要的、具有全球視野的人道主義,提供了重要的道德理性。5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我們在本書中討論了:中國的“儒家”傳統以一種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的方式,構建了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其中有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加以利用的資源。我們對中國早期現代性中“非西方知識”的討論,表明這些“非西方知識”曾試圖為中國探索一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后殖民主義、激進的女權主義和生態主義的思想與實踐,都曾經對中國近代這些有關“現代性”的討論進行了再審視,這些思想仍有可能為我們走出當前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指導。也許更加具有爭議性的是,我們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資源、它所經歷的革命世紀,在中國社會發揮著重要的轉化作用。無論中國未來發生什么樣的改變,這一改變需要以中國自己的方式實現,而不必服從以美國意愿為中心的規則。
中國真正的變化不會發生在民眾騷亂與地緣政治沖突相關聯的地方。發生在大國邊緣的這些沖突,很快就會被卷入互為對手的大國間的政治斗爭之中。吉卜林在其小說《吉姆》(Kim)中詳加闡釋的“大博弈”理論6“大博弈”(The Great Game)特指19 世紀中葉—20 世紀初英俄帝國的中亞爭霸戰。這一說法因英國小說家吉卜林的作品《吉姆》而流傳開來。——譯者注自有其生命力,也許像“冠狀病毒暴發”這樣的挑戰,正是對這一理論的最新回應。并不是像西方媒體所報道的那樣,這次暴發“暴露”了中國政府缺乏透明度或者是它的“無能”,而是在突然安靜下來的城市里,曾經由經濟機器不停運轉所造成的永不停歇的勞作,突然被按了“暫停鍵”,人們也許會因此而有時間來認真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真正基礎?當然,人的生命與生存需要得到優先考慮,在這場疫情中,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政府的能力——當它和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積極配合檢疫隔離的普通群眾一起行動起來之后。但在疫情中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也值得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省思:在向老百姓承諾了安全與繁榮之后,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還有哪些需要加以改善的?
在藝術與文化的幫助下,通過特定形式實現的意義、知識與情感上的交流,必將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根本性變化的一部分。這也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所開創的自由民主精神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服務的中國人民的持續影響的一部分。在中國社會的日常空間,需要打開一個富有自我責任感的新空間,這或許是中國當下所需要的一種進步。這需要中國在追求“經濟增長”之外,人們能以自己的方式、以文學與藝術的方式,提出和探索“何為美好生活”的問題。
像中共這樣一個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過磨煉的共產黨組織,沒有理由做不到這一點。但它需要重新把自己正在推動的現實與作為行動依據的意識形態框架及根源聯系起來。它所擁護的馬克思主義在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國此后試圖在現代化的層面與西方加強溝通——“看看我們,我們也實現現代化了!”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主政者與市場經濟學家一起蹬“雙人車”,他們共同探索能帶來“進步與增長”的技術。在整個世界的發展前景越來越不確定的當下,中國可以敞開大門,積極探索并完善自身的發展道路,為全世界共同需要的巨大變革,帶來更多可能性。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世界對這種變革的需求,正在變得日益緊迫起來。中國可以與東西方也在尋求這種變革可能性的人聯合起來。如果它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它就真的可以宣稱自己繼承了“紅色創意” 的衣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