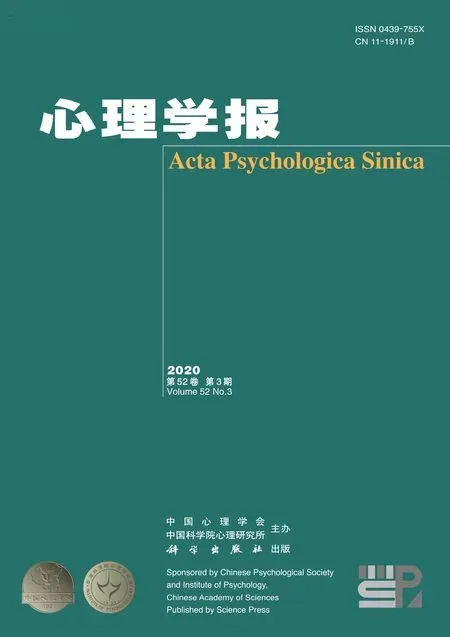信任以稀為貴?下屬感知被信任如何以及何時導致反生產行為*
陳 晨 張 昕 孫利平 秦 昕 鄧惠如
(1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廣州 510275) (2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 香港 999077)
(3廣東金融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 廣州 510521)
1 問題提出
在當今日益多元化的組織結構中, 信任(trust)作為工作環境中人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被認為是降低組織運行成本、提高團隊效率的關鍵(李新春, 2002; 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Yao,Zhang, & Brett, 2017)。過去20多年里, 信任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陳閱, 時勘, 羅東霞, 2010; 秦昕, 鞠冬, 2011; de Jong, Dirks, & Gillespie,2016; Dirks & Ferrin, 2001; Schoorman, Mayer, &Davis, 2007)。信任是指一方愿為另一方的行為承擔傷害的意愿(Mayer et al., 1995)。當個體預期對方所采取的行為對自身十分重要時, 不論個體是否有能力監控另一方的行為, 個體越愿意承擔對方行為可能帶來的傷害, 其對另一方就越信任(Mayer et al.,1995)。現有研究發現, 上司對下屬的信任會對下屬工作態度與績效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段錦云, 田曉明, 2011; 韋慧民, 龍立榮, 2009; 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輇, 鄭曉明, 2007)。
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 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feeling trusted)反映了下屬感知到上司愿意為自己(即下屬)的行為承擔傷害和風險的程度(Baer et al.,2015)。信任與感知被信任是兩個相關但不等同的構念(Brower, Lester, Korsgaard, & Dineen, 2009)。目前, 感知被信任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現有研究發現, 下屬感知到被上司信任不僅能夠提升下屬的組織自尊與工作績效(Lau, Lam, & Wen, 2014),還會提高組織責任規范與組織績效(Salamon &Robinson, 2008)。可見, 傳統智慧與現存大多數研究都認為, 下屬感知被信任對下屬自身及組織都是有益的。
然而, 下屬感知到被信任一定是有益的嗎?本文認為, 以往研究夸大了被信任的益處而忽視了其潛在成本, 被信任可能導致的消極影響并未被充分挖掘。事實上, 目前已有少量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王紅麗, 張筌鈞, 2016; Baer et al., 2015)。例如王紅麗和張筌鈞(2016)發現, 下屬感知被信任會加重其工作負荷與工作壓力, 從而增加下屬的情緒耗竭。新近研究初步反映出下屬感知被信任的潛在危害,但目前僅集中于個體資源角度, 關注感知被信任對員工壓力與情緒耗竭的影響, 并未能完全刻畫出被信任可能的負面影響(Baer et al., 2015)。鑒于此, 本文從一個全新的視角——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探討了感知被信任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反生產行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指個體有意實施的、對其所在組織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具有或存在潛在危害的行為(Spector et al.,2006), 是常見的員工負面行為, 會給組織帶來巨大損失(張永軍, 廖建橋, 趙君, 2012; Bennett &Robinson, 2000; Ju, Xu, Qin, & Spector, 2019; Zheng,Qin, Liu, & Liao, 2019)。鑒于信任在組織中的重要作用, 探討感知被信任潛在的負面影響, 挑戰了被信任總是好的這一主流研究假設, 能夠為感知被信任的研究提供更加全面且辯證的視角, 同時也將目前對其危害的認識從資源保存拓展到其他方面。
為解決上述議題, 本文擬基于自我評價理論(Markus & Wurf, 1987)和信任相關研究(de Jong et al., 2016; Fulmer & Gelfand, 2012; Lau et al., 2014),探索感知被信任如何以及何時導致員工反生產行為, 以期打開感知被信任消極影響的黑箱。自我評價理論認為, 個體會受到所處社會環境和社會信息的影響, 不斷進行自我的認知和評價(Korman,1970), 并形成相應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 Gecas,1982); 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又會進一步影響其態度和行為(Pierce, Gardner, Cummings, & Dunham, 1989)。根據自我評價理論, 上司的信任是員工在職場中所獲得的重要社會信息, 對員工的自我概念有重要影響(Mishra & Mishra, 2012; Pfeffer, 1998)。由于信任在組織中具有特殊、稀缺等屬性(Graen & Uhl-Bien,1995), 這便向員工傳遞出獲得上司信任的人是稀有而獨特的信息, 從而促使員工產生自己是獨特、稀缺的自我評價和自我概念, 引發心理權利感(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Campbell, Bonacci, Shelton,Exline, & Bushman, 2004), 即個體覺得自己相比于其他同伴, 應該得到更多或應該受到特殊對待的即時感受(Campbell et al., 2004; Qin, Chen, Yam, Huang,& Ju, 2019; Yam, Klotz, He, & Reynolds, 2017), 進而導致反生產行為增加。此外, 本文還進一步探討了上述作用的邊界條件, 提出了員工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綜上所述, 本文擬從自我評價視角探討下屬感知被信任對其反生產行為的內在作用機制及其邊界條件(如圖 1)。本文將為感知被信任、心理權利感和反生產行為的研究做出貢獻, 進一步揭示感知被信任的消極影響的作用機理。

圖1 理論模型
1.1 自我評價理論與下屬感知被信任
自我評價理論指出, 個體自我評價的形成受到他所處社會環境及社會信息的影響(Markus & Wurf,1987; Pettigrew, 1967), 尤其是當信息來自組織中重要的人員(例如領導), 并且信息內容是對其積極的評價時(Gecas, 1982; Turner, 1978)。結合信任相關研究來看, 領導是員工在職場中社會信息的重要來源(Salancik & Pfeffer, 1978), 且信任反映出領導對該員工積極的評價, 因此, 當員工感知到被上司所信任時, 他更可能將這一信息用于自我評價過程,基于此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則會進一步影響他的知覺、態度與行為。綜上所述, 自我評價理論為本研究解釋下屬感知被信任后的知覺與行為提供了適宜的理論視角。
1.2 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
基于自我評價理論(Markus & Wurf, 1987)與信任相關研究(Lau et al., 2014; Mayer et al., 1995), 本研究提出, 下屬感知被信任會引發下屬的心理權利感1本研究將心理權利感定義為一種狀態類變量(state-like variable),指個體覺得自己相比于其他同伴, 應該得到更多或應該受到特殊對待的一種即時的感受(Campbell et al., 2004; Yam et al., 2017)。雖然以往的研究傾向于將心理權利感視為一種穩定的特質類變量(Harvey & Martinko, 2009), 但近期的心理學和管理學研究已經逐漸開始將其概念化為可以瞬時波動的狀態類變量(例如,Vincent & Kouchaki, 2016; Qin et al., 2019; Yam et al., 2017; Zitek,Jordan, Monin, & Leach, 2010)。基于此, 本文將心理權利感定義為一種狀態類變量。。信任反映了一方愿意為另一方的行為承擔脆弱性的程度(Mayer et al., 1995), 行為表征包括能力依賴與信息披露等。相應地, 感知被信任則反映了個體知覺到對方愿意承擔風險、暴露其脆弱性的程度(Baer et al., 2015)。
對員工來說, 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具有重要象征意義, 這意味著他的能力、品格等得到了上司的認可, 成為了上司的“圈內人”, 并會在績效評價、職業發展等方面獲得競爭優勢。然而上司往往只會對團隊中的少數成員給予信任(Chen, He, & Weng, 2018;Graen & Uhl-Bien, 1995), 即對員工來說, 來自上司的信任具有獨特、稀缺的屬性, 從而向員工傳遞出獲得上司信任的人是稀有而獨特的這一社會信息。由于自我評價的過程受到社會比較的影響(Pettigrew,1967), 個體感知到自身所擁有的事物(或屬性)在組織中的普遍性程度會影響其自我評價過程(Ditto &Jemmott, 1989; Jemmott, Ditto, & Croyle, 1986)。尤其是在個體擁有某些好的事物(或屬性), 而這一事物(或屬性)又較為稀缺時, 他們在進行自我評價時往往更傾向于夸大這一稀缺性, 從而拉大自身與他人之間的區別(Goethals, 1986; Sherman, Presson, &Chassin, 1984)。基于此, 當員工感知到被上司信任時, 他們會認為與其他團隊成員相比, 自己具有更強的能力或更高的品格, 能夠為組織做出其他成員無法做到的獨特貢獻, 是組織中稀有的存在, 即形成稀缺、獨特的自我概念。而個體對自身稀缺性、獨特性的感知則是影響個體心理權利感的重要因素, 員工在組織中稀缺性與獨特性的自我概念越強,便越可能引發其心理權利感(Emmons, 1984; Raskin& Terry, 1988)。綜上所述, 由于來自領導的信任具備稀缺、獨特屬性, 下屬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可能引發其心理權利感。據此, 我們提出:
假設1: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其心理權利感正相關。
1.3 心理權利感與反生產行為
個體的心理權利感與其膨脹的自我認知(Levine, 2005)和自我中心取向(Harvey & Martinko,2009)息息相關。這一膨脹的自我認知和對報酬獎勵、人際互動等方面存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會引發個體互惠觀念的扭曲, 進而更有可能導致個體采取消極行為(例如反生產行為)進行回應(周如意, 龍立榮,賀偉, 2016; Jordan, Ramsay, & Westerlaken, 2017;Naumann, Minsky, & Sturman, 2002)。以往研究表明,心理權利感所導致的行為結果可以通過公平理論的視角進行解釋(Huseman, Hatfield, & Miles, 1987)。雖然員工通常期望自身在工作中的投入產出比是公平的, 但心理權利感會破壞這一知覺過程(Huseman et al., 1987)。心理權利感較高的人往往傾向于對自己持有過度積極的認知, 認為理想的結果要歸功于自己的付出, 因此期望能夠獲得與自我付出相匹配的回報, 這種膨脹的自我認知和對有利結果的自我歸因讓高心理權利感的人堅信他們應該獲得比他人更多的所得或受到更大的優待(周如意, 龍立榮,張軍偉, 2018; Harvey & Martinko, 2009), 而不考慮他們實際的績效和貢獻。因此, 當這種膨脹的期望未被滿足時, 個體便可能產生不公平感, 由此采取具有破壞性的反生產行為來抵消這種未滿足感和不公平感(Campbell et al., 2004; Qin et al., 2019;Yam et al., 2017)2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種情況下, 員工采取反生產行為并非是出于自利的目的(Trevi?o, Weaver, & Reynolds, 2006), 而是因為他們真的堅信自己被虧欠了, 反生產行為只是他們與團隊及團隊成員“扯平”的一種方式。對高心理權利感的個體來說, 反生產行為恰恰是他們對工作所得所采取的公平回應, 盡管他們所期望的工作所得是有偏差的、被他們的膨脹的自我認知和自我中心取向所導致夸大了的。。相關實證研究證實, 當個體具有更高的心理權利感時, 他們更有可能將自己的需求置于他人之上(Harvey & Martinko, 2009), 表現得更加自私, 更少幫助他人(Zitek et al., 2010), 以及更有可能采取越軌行為(Levine, 2005; Qin et al., 2019;Rosenthal & Pittinsky, 2006)。據此, 結合假設1, 我們提出:
假設2:下屬心理權利感與下屬反生產行為正相關。
假設3: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增強下屬心理權利感, 進而誘發其反生產行為。
1.4 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調節作用
根據前文所述, 心理權利感的產生與下屬基于感知被信任所形成的稀缺、獨特的自我概念有關,而這一自我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取決于下屬如何看待所在團隊中的信任, 即下屬感知到的自己從上司處獲得的信任在團隊中的稀缺程度。雖然從整體上來說, 組織中上司對于下屬的信任都是稀缺的,但某些情境下(例如, 上司自身的信任傾向較低或授權較少的團隊), 下屬可能會更加感受到領導信任在團隊中是稀缺的。當個體對所處團隊中上司信任的稀缺程度知覺越高, 也就意味著擁有這一信任的員工在組織中越特別, 此時下屬感知到被上司信任便更有可能引發他/她對自身稀缺和獨特的評價,進而更可能引發心理權利感。相反地, 在某些情境下(例如, 上司自身的信任傾向較高或自我管理型的團隊), 下屬知覺到信任的稀缺程度相對較小,由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所帶來的下屬對自己是特別的這一知覺也隨之變弱, 下屬的心理權利感也會隨之減弱。據此, 我們提出:
假設4: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會調節下屬感知被信任與下屬心理權利感的關系。具體來說,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 下屬感知被信任與下屬心理權利感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 上述關系不顯著。
結合假設 3與 4, 本文進一步提出被調節的中介假設:
假設5: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會調節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影響其反生產行為的間接效應。具體來說, 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 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下屬心理權利感影響其反生產行為的間接效應顯著; 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 上述間接效應不顯著。
1.5 研究概覽
本研究采取多種研究設計、多樣本的方法來檢驗研究模型, 共包括兩個實驗研究(研究 1、2)和一個問卷調查研究(研究 3)。這種全景式研究方法有利于為研究假設提供更加豐富且有利的實證證據(Chatman & Flynn, 2005), 進而有助于建立研究的內部和外部效度(Ju et al., 2019; Qin, Ren, Zhang, &Johnson, 2015)。
2 研究1:感知被信任對心理權利感的實驗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樣本
在研究1中, 我們通過本文作者的校友網絡招募115位來自中國不同企業的全職員工參與實驗。在實驗參與者中, 47%為女性, 平均年齡為 28.7歲(SD= 7.70), 參與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6.3年(SD=1.33), 平均在企業的任期為3.92年(SD= 5.58)。參與者來自不同行業, 包括制造業(14.8%)、銀行業(16.5%)、建筑業(19.1%)和其他(49.6%)。
2.1.2 實驗設計與實驗程序
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感知被信任組(n= 58)或控制組(n= 57), 并被要求回憶一件自己與上司在完成工作任務時的具體情境。回憶完成后, 我們要求參與者對這一互動過程進行描述。
感知被信任的操縱程序。本研究采用關鍵事件法對感知被信任進行實驗操縱, 該方法被廣泛用于社會心理學與組織行為學的實驗操縱中(Aquino,Tripp, & Bies, 2001; Bobocel, 2013; Liang et al., 2016)。具體而言, 在操縱組(即感知被信任組), 我們讓參與者回憶一件他/她在完成一項工作任務過程中,上司表現出對他/她信任的事情。為更好地喚起參與者的回憶, 我們同時提供了幾個事例作為參考, 要求參與者所回憶的事例包括但不限于所提供的事例。事例基于感知被信任的量表(Mayer & Gavin,2005)題項改編而來, 例如“你的上司讓你在對他/她很重要的工作上發揮作用”“你的上司依賴你對工作相關問題的判斷, 且認為沒有必要監督你的工作”等。操縱組被試所描述的內容示例如下:“7月末, 在與客戶溝通完其與借款人數千萬元借款合同糾紛的基本案情后, 我用一天時間草擬了一整套訴訟方案, 先后就四項重要議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 上司看完我的方案后, 表示完全沒有問題。其后, 上司放心的讓我與客戶獨立溝通, 在解答客戶數輪問詢后, 我們得到客戶的委托, 由本團隊代理本起訴訟, 協助上司創收近百萬元。”
在控制組, 我們讓參與者回憶一件他/她在上司的指導和帶領下完成工作任務的事情3本研究將控制組設置為“低程度的信任”組而非“不信任”組, 是因為“信任與不信任并非是一個構念的兩端, 信任的反面不是不信任” (Lewicki, McAllister, & Bies, 1998, p.448)。信任與不信任是兩個不同的維度, 兩者有共通之處, 即都暗含著對對方行為的預期(expectation)。但信任是積極的預期, 預期對方會做出對自己有益的行為; 而不信任是消極的預期, 預期對方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Lewicki et al., 1998)。因此, 根據這一觀點, 本研究將控制組設置為低程度的信任組, 即上司需要指示和監督下屬, 不會與下屬分享敏感信息等。。相關事例根據感知被信任的操縱事例對應編制而成, 例如“你的上司要求你聽從他/她的指導來解決對他/她很重要的問題”“你的上司相信自己對工作相關問題的判斷, 且認為有必要監督你的工作”等。控制組被試所描述的內容示例如下:“有一個重要的會議需要制作 PPT, 我制作了初稿之后, 上司審閱完就指導我修改, 完成修改版本之后, 我上司還是要求我將PPT直接傳給他進行再修改, 并在涉及財務商務敏感問題上沒有指導我, 而是選擇自己編制。”
在回憶任務完成后, 我們請參與者對他/她所回憶的情境進行描述, 并詳細描寫出事件發生的過程。操縱結束后, 我們要求參與者繼續完成一項無關的描述任務(即邀請被試描述他們通常在周末會做什么)作為填充任務(Berger, Meredith, & Wheeler,2008)。隨后, 參與者完成一份包括測量心理權利感、操縱檢驗及參與者人口統計學變量的問卷。
2.1.3 測量工具
本研究盡量采用以往研究中使用過的成熟量表進行調查, 以確保測量工具具有較高的信效度。在研究 1與研究 3中, 對于英文量表采用 Brislin(1980)的標準方法進行翻譯和回譯, 以保證測量對等性。除非特殊說明, 本文3個研究中的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點量表進行計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心理權利感:采用Campbell等(2004)編制的心理權利感量表。該量表共包含9個題項, 例如“老實說, 我覺得我比其他人更值得嘉獎”, 本研究測量了參與者當下的感受,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為0.84。
操縱檢驗:根據Mayer和Gavin (2005)編制的信任量表改編。該量表共包含10個題項, 例如“我的上司會讓我在對他/她很重要的工作上發揮作用”。本研究中將其改編為“在我剛剛所回憶的事件中, 我的上司會讓我在對他/她很重要的工作上發揮作用”,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0.81。
2.2 研究結果
2.2.1 操縱檢驗
我們首先對實驗操縱進行了檢驗。t檢驗結果顯示, 操縱組的參與者所感知到被上司信任的程度(M= 3.48,SD= 0.48)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參與者感知到被上司信任的程度(M= 3.18,SD= 0.41),t(113) =3.62,p< 0.001, Cohen’sd= 0.67。因此, 研究 1 對感知被信任的操縱成功。
2.2.2 假設檢驗
我們采用 t檢驗進行假設分析, 結果顯示感知被信任組的參與者心理權利感水平(M= 3.15,SD=0.56)顯著高于控制組參與者的心理權利感(M=2.94,SD= 0.42),t(113) = 2.24,p= 0.03, Cohen’sd=0.42。因此, 假設1得到驗證。
研究1的結果表明, 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能夠增強其心理權利感。通過研究 1, 我們建立了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其心理權利感之間的因果關系, 但研究1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盡管我們的理論推導并不特別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但我們的研究樣本均來自中國, 缺乏普適性。因此, 為了解決樣本局限性問題, 進一步驗證我們研究結論的普適性與穩健性, 我們通過 Amazon’s Mechanical Turk(MTurk)平臺招募了來自美國的全職員工作為被試,對上述研究結果進行了重復驗證, 此外, 我們還進一步檢驗了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在其中的調節作用(即研究2)。
3 研究2: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調節作用的實驗研究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樣本
在研究2中, 我們通過MTurk平臺招募了145名來自美國的全職員工參與實驗4本研究共151名被試參與實驗。為保證填答質量, 參考以往研究(Liang et al., 2016), 我們在問卷中設置了質量控制題項(即“請選擇‘非常同意’”), 我們排除了未通過該題測試的被試; 此外, 我們還排除了完全無關的描述(例如, 亂寫無意義的文字、描述其他非工作場景中的事項等), 最終獲得分析樣本為145人。最終的有效樣本來源在人口統計學變量方面與被排除的無效樣本相比, 沒有顯著差異(p > 0.10),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樣本損耗性偏差。。以往研究表明,通過 MTurk平臺收集的數據與方便抽樣收集的數據相比, 具有類似的心理測量特征(Buhrmester,Kwang, & Gosling, 2011; Qin, Huang, Johnson, Hu,& Ju, 2018)。每位被試完成實驗后可獲得0.4美元報酬。實驗參與者中女性員工占50.30%; 白種人占73.10%, 非洲裔/西班牙裔/拉丁裔人占 14.48%, 亞洲裔占 8.96%, 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占2.76%, 其他0.70%。被試的平均年齡為36.92歲(SD=10.21), 平均的受教育年限為15.79年(SD= 2.67),平均在公司的工作年限為7.28年(SD= 7.26)。參與者來自多個行業, 其中醫療保健業占13.79%, 信息技術業占11.72%, 教育業占13.10%, 其他61.39%。
3.1.2 實驗設計與實驗程序
我們首先邀請實驗參與者報告他們感知到的所在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 隨后的實驗程序與研究1一致, 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感知被信任組(n=73)或控制組(n= 72), 并接受與研究1相同的感知被信任的操縱程序。操縱組被試所描述的內容示例如下:“我在公司資源室值班, 我的上司讓我自行管理和關心使用資源室的客戶。她會讓我自己選擇與客戶之間進行哪些活動或互動, 盡管她也喜歡做決定。她非常信任我在沒有她直接監督的情況下讓我自行與客戶進行活動。”控制組被試所描述的內容示例如下:“我需要為一個特定的 106項目寫一份關于聯邦應急管理局審查的報告, 因為我以前沒有完成過類似的項目, 我的上司給我發了電子郵件,告訴了我項目編號, 然后給了我這個項目要遵循的要點。第二天, 我又收到了她發來的另一封郵件,內容是關于這個項目核對的, 我要把目前為止完成的內容發送給她, 這樣她就能確保我是按照她在前一封郵件中列出的具體格式來做的。”
在實驗操作之后, 參與者完成填充任務, 填寫包括測量心理權利感、操縱檢驗及人口統計學變量的問卷。
3.1.3 測量工具
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改編自 Vincent和Kouchaki (2016)的感知到創造力的稀缺性量表。該量表共包含3個題項, 例如“在我的工作團隊中, 被上司所信任是罕見的”,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為0.92。
心理權利感:與研究 1一致, 本研究采用Campbell等(2004)編制的心理權利感量表,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0.90。
操控檢驗:與研究 1一致, 本研究采用根據Mayer和Gavin (2005)的信任量表改編的10題項量表來進行感知被信任的操縱檢驗,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為 0.82。
3.2 研究結果
3.2.1 操控檢驗
與研究1一致, 我們首先對實驗操縱進行了檢驗。t檢驗結果顯示, 操縱組的參與者所感知到被上司信任的程度(M= 3.61,SD= 0.61)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參與者(M= 2.96,SD= 0.68),t(143) = 6.11,p<0.001, Cohen’sd= 1.00。因此, 研究2對感知被信任的操縱成功。
3.2.2 假設檢驗
我們采用一般線性回歸分析(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進行假設分析, 具體結果如表 1所示。在表1的模型1中, 我們將感知被信任與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對心理權利感進行回歸, 結果顯示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正相關(β= 0.28,p=0.03), 因此, 假設1得到驗證。

表1 研究2一般線性回歸結果

注:an = 145。0 = 控制組; 1 = 感知被信任組。*p < 0.05, **p < 0.01, ***p < 0.001。
在表1的模型2中, 我們進一步將感知被信任與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交互項納入到回歸方程中, 結果顯示, 該交互項與心理權利感正相關(β=0.29,p= 0.01)。簡單斜率分析結果表明, 當參與者感知到所在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 感知被信任對其心理權利感有顯著增強作用(b= 0.59,t=3.42,p= 0.001); 而當其感知到所在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 感知被信任對其心理權利感沒有顯著影響(b= ?0.04,t= ?0.26,p= 0.80), 二者的差異顯著(b= 0.64,t= 2.59,p= 0.01)。因此, 假設4得到驗證。為更加直觀地表示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調節變量的均值加減1個標準差作為分組標準, 分別對個體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高和低的情況下, 感知被信任與否與心理權利感間的關系進行了描繪, 具體如圖2所示。

圖 2 研究 2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在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之間的調節作用
研究1和2為被試感知被信任對其心理權利感的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因果證據, 并且檢驗了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對上述關系的調節作用。這兩項研究都驗證了理論模型的內部效度, 但都受到了外部效度的限制。因此, 我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研究3)通過多時間點、多源的問卷調查來擴展我們研究結論的外部效度, 并同時考慮下屬的反生產行為,對整體研究模型進行檢驗。
4 研究3:全模型問卷調研
4.1 研究方法
4.1.1 樣本及程序
研究3為實地問卷調研。本研究采用多源、多時間點的取樣方式。研究通過國內幾所大學的校友網絡招募參與者。通過這種方法, 本研究邀請了來自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員工及其直接上司, 增加了樣本的廣泛性, 提高了調查結果的外部效度。在 T1時間點, 由下屬評價自身感知被信任程度、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心理權利感及人口統計學變量。T1時間點共邀請208位下屬參與調查, 回收192份問卷(回收率為92.31%)。在T2時間點(一周后), 由參與T1調查員工的直接上司評價其下屬的反生產行為。T2時間點共邀請62位直接上司參與調查, 回收 60份問卷(回收率為 96.77%)。為了提高問卷的填答質量, 激發填答問卷的積極性, 本研究為每位下屬每次調查均提供5元人民幣作為報酬, 為每位上司每次調查均提供8元人民幣作為報酬。與此同時, 我們在問卷的指導語中強調了問卷嚴格的保密性, 以及真實作答的重要性。在將多源、多時間點的問卷逐一進行匹配, 剔除明顯缺失重要變量的樣本后, 本研究最終獲得 60份有效的上司問卷(問卷有效率為 96.8%), 以及 187份有效的下屬問卷(問卷有效率為89.9%)。平均每位上司評價3位下屬。
在樣本結構方面, 被調查者中 65.8%為女性,平均年齡為27.8歲(SD= 6.8), 平均的受教育年限為15年(SD= 1.9), 平均在公司的工作年限為3.1年(SD= 4.0), 員工與其直接上司共事的平均工作年限為2.3年(SD= 2.7)。此外, 被調查者來自多種類型的職位和行業。其中, 22.5%的被調查者從事行政相關工作, 18.7%從事市場相關工作, 8.0%從事技術相關工作, 16.0%從事財務相關工作, 以及34.8%從事其他類型的工作。在行業結構方面, 20.3%的被調查者來自制造業, 15.0%來自服務業, 9.1%來自銀行業, 21.4%來自信息技術行業, 以及34.2%來自其他行業。
4.1.2 測量工具
感知被信任(T1):與研究 1相同, 本研究采由Mayer和Gavin (2005)編制的信任量表改編而來的感知被信任量表,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為0.84。
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T1):與研究 2相同, 本研究采用由Vincent和Kouchaki (2016)編制的感知到創造力的稀缺性量表改編而來的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量表,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為0.89。
心理權利感(T1):與研究 1相同, 本研究采用Campbell等(2004)編制的心理權利感量表,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0.91。
反生產行為(T2):采用Spector等(2006)編制的反生產行為量表。該量表共包含 10個題項, 例如“該下屬故意浪費公家物品”。由員工的直接上司對其進行評價,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為0.92。
控制變量(T1):根據以往研究(例如, Penney &Spector, 2005; Zheng et al., 2019), 本研究控制了下屬相應的人口統計學變量,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以及與直接上級的共事時間, 以排除這些因素的影響(Bernerth & Aguinis, 2016)。本研究控制了性別因素是因為相對于女性, 男性更加激進(aggressive),更容易做出有侵略性的行為和反生產行為(Gonzalez-Mulé, DeGeest, Kiersch, & Mount, 2013)。本研究控制了教育水平是因為教育水平比較高的人, 認為不道德的行為是難以接受的(Browning & Zabriskie,1983)。本研究還控制了年齡和與直接上級的共事時間, 因為Berry, Ones和Sackett (2007)的一項元分析發現, 年齡和任期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反生產行為有影響, 例如, 年齡較低、任期較短的員工,反生產行為更多。因此, 控制這些變量能夠使本研究排除可能的解釋因素, 得到感知被信任所增加的預測效度(Bernerth & Aguinis, 2016)。
4.1.3 分析策略
由于本研究的數據結構是嵌套型數據(反生產行為由一個領導評價多個下屬, ICC1 = 0.70,p< 0.001),本研究采用多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HLM), 通過Mplus 7.0對數據進行了分析(Bryk &Raudenbush, 1992)。具體來說, 感知被信任、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心理權利感為個體層面變量(individual level), 反生產行為在理論上雖然是個體層面變量, 但由于同一領導評估多名下屬導致存在嵌套性問題, 具有個體層面(individual level)和團隊層面(group level)的方差變異。因此, 雖然整體研究模型在個體層面, 但本研究仍選用HLM進行分析,以排除反生產行為由于領導評估帶來的團隊層面的方差變異。參考以往研究(例如, Gong, Huang, &Farh, 2009; Zheng et al., 2019), 在檢測Level 1預測因子的主效應時, 對 Level 1預測因子使用原始尺度或總值中心化(grand-mean centering)處理都是合適的, 因此, 我們將所有核心解釋變量在放入回歸模型前均進行了總均值中心化處理(Hofmann, Griffin,& Gavin, 2000)。由于本研究總體的團隊規模較小,難以有效估計 Level 2的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Theall et al., 2011), 我們將斜率設置為固定斜率(fixed slope)。此外, 本研究采用了RMediation的方法檢驗理論模型中的中介效應(Tofighi & MacKinnon,2011)。為了檢驗被調節的中介效應, 本研究采用了Edwards和 Lambert (2007)的調節路徑分析方法,計算調節變量在高于1個標準差和低于1個標準差水平上時, 自變量通過中介變量影響因變量的間接效應的大小。

表2 研究2描述性統計和變量間相關系數a
4.2 研究結果
4.2.1 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是變量描述性統計表, 展示了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4.2.2 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檢驗感知被信任、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心理權利感、反生產行為 4個變量之間的區分性,本研究使用Mplus 7.0對上述變量進行了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首先, 我們對各量表的題項進行了打包(parceling)。由于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核心構念間的區別, 而不是構念中題項之間的相互關系, 因此對題項進行打包是合理的處理方式。與先前研究一致(例如, Zheng et al., 2019), 對于多維度的變量, 我們根據概念的維度進行打包, 即將感知被信任的測量題項(即基于認知的信任和基于情感的信任)和反生產行為的測量題項(即針對組織的反生產行為和針對人際的反生產行為)均分別打成兩個包; 對于單維度量表,我們根據平衡題項與構念的方法(item-to-constructbalance method; 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2002)進行打包, 即將心理權利感打成三個包。結果顯示, 假設四因子模型對數據的擬合結果較為理想(χ2= 34.58,df= 29, CFI = 0.99, TLI = 0.99, RMSEA= 0.03, SRMR = 0.04), 且其擬合優度顯著優于其他模型(其他模型擬合的具體結果可聯系本文作者獲得), 表明這4個變量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構念5本研究的CFA分析結果是個體水平的分析結果, 考慮到反生產行為數據結構的嵌套性問題, 我們將反生產行為設置為多水平、其他變量設置為個體水平進行了多水平 CFA檢驗(Dyer,Hanges, & Hall, 2005), 四因子模型結果如下:χ2 = 153.02, df =72, C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8, SRMR = 0.06。。
4.3 假設檢驗
假設1預測, 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正相關。從表3的模型2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水平、與直接上司的共事時間之后, 感知被信任對心理權利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 0.17,t= 2.37,p= 0.02), 假設1得到了驗證。
假設2預測, 下屬心理權利感與其反生產行為正相關。從表3的模型5中可以看出, 心理權利感對反生產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 0.04,t= 2.12,p= 0.03), 假設2得到驗證。假設3進一步預測, 心理權利感在感知被信任與反生產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為了檢驗中介效應, 本研究通過RMediation檢驗了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的路徑系數, 以及心理權利感與反生產行為的路徑系數之間乘積的顯著性。結果顯示, 心理權利感的中介效應顯著(b= 0.01,SE= 0.005, 95% CI = [0.001,0.015]), 假設3得到驗證。
假設4預測, 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正向調節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的正向關系。從表3模型4中可以看出, 感知被信任與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交互項對心理權利感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b=0.18,t= 2.72,p= 0.01)。簡單斜率分析發現, 當參與者感知到所在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 感知被信任對其心理權利感有顯著正向影響(b= 0.30,t=4.34,p< 0.001); 而當其感知到所在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 感知被信任對其心理權利感沒有顯著影響(b= 0.03,t= 0.34,p= 0.73), 二者的差異顯著(b= 0.27,t= 2.72,p= 0.01)。因此, 假設4得到驗證。為更加直觀地表示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調節變量的均值加減1個標準差作為分組標準, 分別對個體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高和低的情況下, 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間的關系進行了描繪, 具體如圖3所示。
假設5預測, 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正向調節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正向影響反生產行為的間接效應。被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表明,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均值加1個標準差),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影響其反生產行為的間接效應顯著(b= 0.01,SE= 0.01, 95% CI =[0.0003, 0.027]); 當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均值減 1個標準差), 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影響其反生產行為的間接效應不顯著(b= 0.002,SE= 0.01, 95% CI= [?0.005, 0.010]); 兩者的差異顯著(Δb= 0.01,SE= 0.01, 95% CI = [0.0002,0.028])。因此, 假設5得到驗證6我們還對研究3進行了一系列補充分析。首先, 為排除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由于對變量采取不同的中心化方法而獲得的這一潛在干擾, 我們對核心變量采取組內平均數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ing)處理后進行了重新分析。結果表明, 在進行組內平均數中心化后,本文所提假設依然成立(補充分析的具體結果可聯系本文作者獲得)。其次, 我們檢驗了在控制“感知被信任—領導成員交換(LMX)—反生產行為”這一積極中介路徑作用的基礎上, 我們模型所假設的感知被信任的消極效應是否依舊成立。結果表明, 在控制了上述積極中介路徑后, 本研究所提假設依然成立(補充分析的具體結果可聯系本文作者獲得)。。

表3 研究2 HLM分析結果a
5 討論
5.1 研究結果

圖 3 研究 2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在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之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基于自我評價理論的視角, 檢驗了下屬感知被信任對其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結果發現: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引發下屬的心理權利感進而增加其反生產行為, 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在這一過程中起調節作用。當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高時, 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影響其反生產行為的正向中介效應顯著; 當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較低時, 上述中介效應不顯著。
5.2 理論意義
本研究對于信任、心理權利感與反生產行為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理論意義。首先, 本研究通過探索感知被信任的潛在黑暗面, 挑戰了目前信任相關研究中“信任總是有益的”這一主流假設。現有絕大部分研究都表明, 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會為下屬個體及組織帶來積極影響(孫利平, 龍立榮, 李梓一,2018; Brower et al., 2009; Lau et al., 2014; Salamon& Robinson, 2008), 并且大部分研究通常從社會交換的視角, 去驗證信任作為一種社會交換關系, 對員工產生的積極效應, 例如增加工作績效、組織公民行為(Brower et al., 2009)、提高工作滿意度(Lester& Brower, 2003)等。然而, 目前文獻對信任的積極影響的廣泛研究, 可能使得大家過度關注積極的一面, 忽略感知被信任潛在的成本。因此, 本研究聚焦于感知被信任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 通過自我評價的視角, 以及深入分析信任的稀缺屬性, 揭示出了下屬感知到上司的信任可能帶來的負面的結果,即本研究發現, 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會引發下屬心理權利感, 進而增加其反生產行為。本研究通過對感知被信任消極作用的探討, 為理解下屬感知被信任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更辯證的視角。更進一步地, 本研究對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其反生產行為間的內在作用機制及邊界條件進行了深入挖掘, 為打開下屬感知被信任與下屬非倫理行為間的黑箱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解釋視角與實證證據。目前僅有的對于感知被信任的負面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從員工資源保存視角進行的探討, 認為感知被信任引發了下屬工作方面的壓力(例如角色負荷、工作壓力), 進而導致其情緒衰竭升高、工作績效下降(王紅麗, 張筌鈞, 2016; Baer et al., 2015)。本研究則從一個新的視角——自我評價的視角——進行了探索, 發現感知被信任還可能導致下屬膨脹的自我知覺(即心理權利感), 進而增加其反生產行為。此外, 本研究還進一步探討了上述效應的作用邊界, 發現當下屬感知到組織中信任的稀缺性越高, 感知到的被信任越可能內化成下屬的自我概念, 進而進一步增強其心理權利感與反生產行為。上述結果從個體自我評價的理論視角, 為感知被信任為何以及何時能夠導致下屬的反生產行為提供了全新的解釋, 豐富了感知被信任的相關研究, 也回應了Bare等人(2015)關于“加強對于感知被信任及其重要作用機理相關研究”的呼吁。
其次, 本研究發現了引發員工反生產行為的新的領導行為因素。以往研究表明, 領導消極的人際對待行為(例如苛責管理、不公平行為等)往往是導致員工采取反生產行為的重要前因(Bennett & Robinson,2003; Ferris, Spence, Brown, & Heller, 2012; Tepper,2000, 2007)。而本研究則發現, 在某些情境下, 領導積極的行為(例如信任)也可能引發下屬的反生產行為。通過識別與檢驗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新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反生產行為領域的相關研究。進一步, 本研究也豐富了心理權利感的相關研究, 拓展了對員工心理權利感前因的探討。以往研究表明, 當員工自身采取某些行為(例如, 被迫做出組織公民行為; Yam et al., 2017)或是遭受他人的消極對待行為(例如, 被不公平對待; Zitek et al.,2010)時, 往往會引發員工的心理權利感。而本研究則發現, 當員工感知到其所接收到的積極信息極其稀缺時, 他人所傳達的積極信息(例如, 領導的信任)也可能引發其心理權利感。通過識別組織中影響員工心理權利感的重要前因, 本研究對于心理權利感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5.3 實踐意義
本研究的發現對管理實踐也有著重要的啟示。首先, 本研究啟示管理者需注意下屬被信任后可能導致的消極影響。由于信任具有能夠讓員工在組織中更有自信、形成更高的基于組織的自尊、提高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等諸多方面的好處, 上司要信任員工似乎已成為目前管理者們的共識。而過度推崇信任的重要性與好處、過度鼓勵上司信任下屬, 可能存在一定的隱患。管理者需要注意當充分信任一位下屬時, 該下屬可能無意識地形成膨脹的自我認知, 產生較高的心理權利感。而這種“自己應該獲得更多所得和特殊優待”的感覺可能導致下屬的期望無法被滿足, 又進而增強其反生產行為, 對組織利益造成損害。因此, 上司需要注意到, 自己出于好意的信任行為也可能會帶來一定的隱患。當上司更完整地理解被信任的管理現象后, 可以及時發現、調整和控制組織中的不良傾向, 從而幫助上司更有效地管理團隊和組織。
其次, 本研究啟示管理者需注意對極少數下屬賦予信任。當上司賦予極個別的下屬以信任時, 該下屬感覺上司的信任十分稀缺, 而自己卻能夠得到如此稀缺的資源, 下屬感覺自己更加的特別, 產生了更高的心理權利感。這種被強化的心理權利感很可能會進一步損害組織利益。相反, 如果上司對團隊中的很多下屬都賦予信任時, 該下屬感覺上司的信任并不是稀缺的, 從而緩解這一負面影響。因此,為了降低下屬產生優越感的可能性, 上司需盡量避免只信任極少數的下屬。
最后, 本研究啟示管理者正確分析和看待員工的反生產行為。上司如果觀察到員工的反生產行為通常會歸因于員工的人格問題, 而鮮有進一步分析員工為何產生扭曲的心理狀態。除了客觀的不公平等現象導致員工的反生產“報復”行為, 員工無意識的自我膨脹也可能會導致這樣的行為。當員工自我膨脹時, 員工自發產生心理權利感, 認為自己值得更好的, 而外部環境無法滿足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因而做出反生產行為。因此, 領導者需要深入分析員工反生產行為的成因, 從更多的角度(例如, 避免僅對極少數員工賦予信任)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降低和緩解員工反生產行為。
5.4 本研究優勢、不足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具有較多優勢, 例如采取多種研究設計(實驗設計、問卷調查)、多種調研樣本(中國樣本、美國樣本), 進而增加了研究的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希望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解決和探討。第一, 由于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兩個變量是下屬心理層面的變量, 難以通過他評進行測量, 因而本研究的研究3可能存在潛在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問題。研究 3中調節作用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弱共同方法偏差效應。此外, 研究1與研究2利用實驗研究方法檢驗了下屬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之間的因果關系, 證實了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一影響。然而, 未來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來控制上述變量之間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例如將感知被信任與心理權利感的測量分隔時間段測量, 或是考慮長時數據研究等。此外, 本文研究2的美國樣本是通過MTurk平臺招募的, 通過網絡平臺招募的被試存在一定的模糊性(Cheung, Burns, Sinclair, & Sliter, 2017)。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在美國實地招募全職員工進行實證檢驗, 從而為本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提供更充分的實證證據。
第二, 本研究僅探討了下屬感知被信任對下屬心理權利感和反生產行為的影響,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索感知被信任其他可能的消極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區別于上司信任下屬, 下屬感知被信任站在下屬的角度, 是一個新的探索信任的角度。未來研究可以更多地探索感知被信任帶來的消極影響及機制, 從而為信任領域提供更為全面的發展。例如,下屬感知被信任也可能會導致下屬的地位提高, 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 下屬可能會采取損害其他同事的策略, 進而損害組織利益。此外, 當下屬擁有非常稀缺和珍貴的資源——信任時, 下屬可能擁有更高的“權力” (power), 導致其在行為和決策時更為冒進, 甚至做出濫用權力的行為。具體來說,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Pfeffer & Salancik, 1978), 下屬擁有團隊或組織中稀缺的無形資產, 比其他成員有著更多的權力, 而擁有權力一方往往會做出趨近性(approach)的行為或決策(Keltner, Gruenfeld, &Anderson, 2003), 帶來潛在的消極影響。這些其他的潛在中介機制和消極結果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第三,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下屬感知被信任的消極影響,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同時探討感知被信任的雙刃劍效應及其作用邊界。本文研究3的補充分析結果表明, 在控制了 LMX的中介路徑后, 感知被信任通過引發下屬心理權利感進而增加其反生產行為的中介路徑依然成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感知被信任對下屬可能存在雙刃劍作用。例如, 下屬感知被信任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增加了下屬的感恩, 進而通過提高工作績效、增加組織公民行為來回報上司; 而在另一些情境下則可能更多地增強下屬的心理權利感, 進而增加反生產行為。其中, 下屬自戀水平、感知到公平性等變量可能在上述關系起到了重要的調節作用, 決定了兩條路徑作用的相對大小, 希望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第四, 本研究主要基于靜態視角來探索下屬感知被信任的陰暗面, 然而有關領導行為的新近研究已經發現, 領導行為除了在整體水平上存在個體間差異以外, 在時間維度上還表現出一定的波動性(Ju et al., 2019; Qin, Ren, Zhang, & Johnson, 2018)。因此, 未來研究可在時間動態的視角下分析感知被信任的陰暗面。此外,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對于領導?下屬這一互動關系來說, 僅僅關注互動中的某一方往往很難解釋領導為何會區別對待團隊成員(例如, 倫理型領導行為; Qin, Huang, Hu, Schminke,& Ju, 2018), 或是為何團隊成員表現出某些特定行為(例如, 員工建言行為; Xu, Qin, Dust, & Direnzo,2019), 同時關注領導、下屬互動雙方的匹配研究則能更好地回答上述問題。基于此, 未來研究可以關注領導感知給予下屬信任與下屬感知被信任的一致性的影響。例如, 當二者不一致時, 下屬感知到的角色清晰度越低, 進而增加工作壓力與情緒衰竭。
最后, 本研究主要從下屬自我知覺的角度來探討, 下屬主觀感知到自己在團隊內所獲得的上司信任程度如何影響其自身的自我概念、心理狀態及行為反應。然而, 由于上司對下屬的信任在團隊中本身是非均勻分配的, 因此, 客觀上每個下屬所獲得的上司信任在團隊內部也存在相對差異, 這一客觀上的組內相對差異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下屬在團隊內所獲信任的情況。因此,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慮, 基于每個團隊全體成員的取樣, 采用組內平均數中心化的方式獲取下屬在團隊內感知被上司信任的相對位置(Bliese, Maltarich, & Hendricks,2018), 進而更加客觀地探討下屬感知被信任在團隊內部的社會比較過程(Hofmann & Cavin, 1998)。另外, 由于本文的研究團隊規模較小(平均團隊人數為 3), 難以有效測量和反映團隊層面的關系,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在團隊層面上探討上述關系(Bauer, Preache, & Gil, 2006), 例如, 不同團隊中,心理權利感的中介效應有著怎樣的差異; 感知被上司信任和心理權利感之間的關系是否隨著團隊的不同而變化等。
6 結論
本研究基于自我評價的視角, 探討了下屬感知被信任的黑暗面。通過實驗設計, 以及多源、多時間點的問卷調查, 本研究發現, 下屬感知被信任通過提高下屬的心理權利感進而增加了下屬的反生產行為。這一影響機制又受到下屬感知到信任的稀缺性的調節作用, 當感知到信任稀缺性較高時, 下屬感知被上司信任通過心理權利感正向影響反生產行為之間的間接效應顯著, 當感知到信任稀缺性較低時, 上述間接效應不顯著。這一研究為探索感知被信任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辯證的視角,同時為探討員工心理權利感、反生產行為的前因研究提供了新的實證證據。
致謝:作者感謝《心理學報》主編、編委和各位匿名評審專家給予的建議性意見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