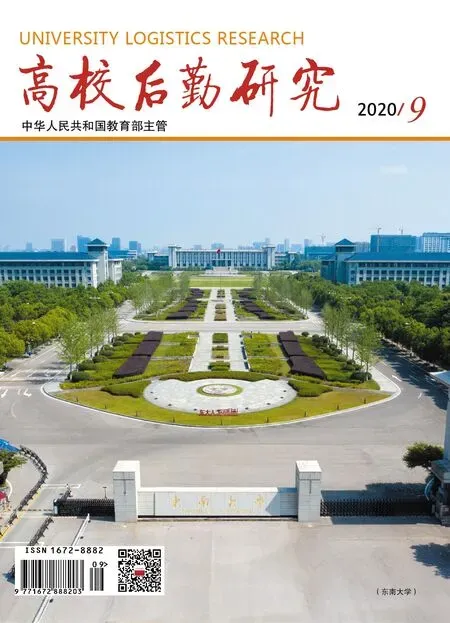大學綜合化發展的內涵與理性探析
俞俏燕
大學綜合化發展的內涵與理性探析
俞俏燕
[杭州師范大學發展與改革處]
大學由學科單一向學科多樣再向學科綜合方向發展,已成為當前我國各類高校發展的普遍現象,由此也帶來高校學科布局雷同現象。本文從大學綜合化的內涵和本質入手,梳理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和學科發展內在邏輯,認為大學綜合化發展是必然趨勢,但真正的綜合化發展卻是個遵循大學發展規律的自然過程。因此,在綜合化過程中應理性處理好學科綜合化的“自然性”與“必然性”、學科門類的“齊全性”與“綜合性”、學科發展的“綜合化”與“特色化”這三對關系。
單科性院校;綜合性大學;綜合化發展
大學由學科單一向學科多樣再向學科綜合方向發展,是當今世界各國高等學校發展的基本趨勢。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始,英國自20世紀60年代后,澳大利亞和我國臺灣地區于近四十多年來都在積極推進多學科性大學和綜合性大學建設。自20世紀80年代始,我國高校的綜合化發展趨勢也日趨明顯,原先旨在面向社會各行業、各部門辦學的單科性院校發展到今天基本已“變異”。今天的單科性院校除了保留其1952年院系調整遺留下來的,能體現單科性院校類型的名稱外,其學科門類早已發展成為多科性甚至綜合性,“千校一面”的綜合化學科布局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
歷史與現實地看,綜合性大學較之單科性院校的確具有較大的優越性,但綜合性大學的優越性究竟源自其本身的內涵與特征?還是源自其與社會發展、知識更新、時代變革的某種契合?是否所有的單科性院校都有必要發展成綜合性大學?從單科性院校發展到綜合性大學又要經過怎樣的過程和繞過哪些誤區?這都需要我們從源頭上來解答。
一、綜合性大學的內涵與特征
(一)綜合性的內涵和本質
何為“綜合性”?現代漢語詞典把“綜合性”解釋為:(1)把分析過的對象或現象的各部分、各屬性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2)將不同種類、不同性質的事物組合在一起。系統論把“綜合性”看成是事物間內在有機聯系和辨證統一的關系;創造學把“綜合性”當作是一種創造,即把不同信息要素,或把原來無邏輯關聯的知識要素重新有序組合,形成新的結構,產生新的功能。以上無論哪種解釋都說明從組合到綜合需經歷量到質的躍變,一般程序為:(1)先將一些相關的或不相關的事物集合在一起,為它們提供相互作用的機會與環境;(2)研究方法體系,促進事物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滋生與發展,使之形成有機系統;(3)提供各種有利的條件,促進該系統產生新質[1]。因此,綜合化過程實質也是組合——系統——創新的過程。
大學的綜合性實質包含三層含義:第一層為具有相對齊全的學科門類,實現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跨越設置,這也是綜合化的表層含義;第二層為學科的綜合化與學科間的融合性,具有合理的學科群;第三層為整體化的知識教育,包括專業的綜合化設置、人才培養的綜合化、課程內容的綜合化等。這三層含義間有遞進關系,第一層是實現大學綜合性的第一步驟,第二層是對第一層的深化,第三層又是前兩層的深化,也是大學綜合性的終極體現。因此,從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實踐來看,學科門類的齊全只能證明高校具備綜合性的第一個步驟,即實現了學科的組合,后者的綜合化與整體化往往才被看成是大學綜合性的重要標志。
(二)綜合性大學的特征和優勢
與單科性院校相比,綜合性大學最突出的特征除具備較為齊全的學科門類、密集的本科專業布點外,還在于擁有能交叉融合的多學科和數量眾多的各領域學者。因此,綜合性大學的優越性在于:其一,能夠利用學科結構綜合優勢,實現跨學科合作,能迅速組織各學科專家進行多領域的大型綜合研究,既解決社會發展和科技更新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綜合性問題,又快速推動知識創新,發展新興學科;其二,能充分發揮綜合教育的作用,營造多學科融匯的學術環境,構建綜合素質培養和學科交叉的人才培養環境和機制,培養大批復合型人才,滿足社會不同行業需求和人全面發展的需要;其三,有利于爭取更大的資源投入,拓展辦學領域,同時又能通過整合,充分發掘和優化現有教育資源,提高大學資源運用效率,提升辦學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其四,有利于構建高品位的校園文化。[2]綜合性大學因為具有多學科的學術氛圍,有效增強人文精神、科學精神及創造性思維能力,從而優化人才培養環境。
二、大學綜合化發展的必然性
人類教育走過了這樣一條道路:占絕對優勢的古典文科教育——古典文科教育傳統受到動搖、科學教育逐漸興起——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過渡平衡——科學教育獨領風騷,人文教育備受冷落——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趨于融合。綜合性是現代教育的需要。大學綜合化發展不僅僅是大學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文明向前進化、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需要。
(一)源于社會生產方式發展需要的綜合化
大學走上綜合化發展道路是社會專業化分工、大工業化生產的產物。在社會分工水平較低的時代,學校教育主要內容為統治人才所需的人文知識,勞動者的培養則僅融于社會生產實踐活動中。實科教育雖孕育于中世紀的行會學校和學徒制度,但其完整體系的建立則是在17、18世紀較早發生產業革命、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的英國、法國和德國。至19世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結構得到升級,以培養高級實用技術人才為辦學宗旨的單科性院校和少數多科技術院校出現,并很快成為這個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流模式。20世紀后期新科技革命引發的產業結構升級使單科和多科院校開始出現種種弊端和危機。據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學生認為上大學的主要原因是通過對某個專業領域的學習取得一份職業。
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生產系統已由“剛性”變成“柔性”的知識創新系統,只掌握生產過程某一環節的專門技術,已不足以承擔新產品的生產使命。單科性院校單一的學科設置已遠遠滿足不了復雜技能輸出的社會需求,其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對社會發展的促進能力在知識經濟時代已開始走向衰退。而綜合性大學因具有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所要求的人才庫和知識創新源,而具有更大的潛在和現實優勢,于是研究性和綜合化便成為單科性院校發展的戰略路徑和發展目標。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把推進單科和多科大學的綜合化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策略,綜合化成為當今大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
(二)源于科學發展的綜合化
量子論的奠基人普朗克曾深刻指出:“科學是內在的統一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質,而是由于人們認識能力的局限。”古代科學是綜合之學問,所有關于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知識統一包容于哲學母體中。相應地,古典高等教育多以通識教育為主;到近代,人們進入以分化研究為主的認識階段,大大推進了人們對客觀事物內部的認識和科技的發展。然而,自然界、人類社會內部存在著有機聯系,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呈現出彼此的不可分割性、綜合性、系統性和完整性。因此,當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無法靠一、兩個科學分支來單獨解決時,人類又逐步進入以整體化為主的科學認識階段。但這個階段綜合了前兩個認識階段的優點,一方面現代科學比近代科學發展得更精細、更專尖,科學分科也越來越細,科學體系結構呈樹狀繁衍;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學科界限,由往昔的單兵作戰模式發展為學科協同作戰整體。這并不是簡單的歷史回歸,而是各分支學科在充分研究各自領域的中心部分后,與其他學科接壤的邊緣地段拓展基礎上的統一,也即高度分化基礎上的高度綜合。
大學學科劃分很大程度上受科學知識劃分的影響,學科知識也開始向兩個方向縱深發展。其一是高度分化。單是近10年來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已達500余門之多。其二是高度綜合和集成。現代科學的綜合化、整體化發展使得不少科學分支都需要從其他科學分支的理論、技術或方法上汲取靈感或營養,以便形成發展的新動力。這也使得學科交叉呈現更大跨度的趨勢,有力推動了大學學科設置的綜合化。據統計,到上世紀80年代,新興交叉學科總量已達到2581門,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其中文理交叉學科近300門[3]。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已不限于同門類,交叉融合的深度、廣度以及速度加大加快,學科正朝著在一個領域內不斷深入同時又在多個領域綜合交叉的整體化方向發展。世界一流大學都在傳統學科外設置其他學科。如牛津、劍橋、哈佛等新建了科學技術類學科;麻省理工學院、德國工業大學則增設人文社科類學科。很多大學在學科設置綜合化的同時,也紛紛建立了各種跨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不僅解決各種綜合性的實際問題,還將原屬不同院系、互不相干的學科緊密聯系起來。
(三)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模式導向下的綜合化
現代大學發展史顯示,大學遵循著“綜合—分化—綜合”的發展路徑在發展。中世紀大學起初都為單科,如意大利的薩萊諾大學以醫學為主,波隆那大學以法律為主。從今天的學科分類上說,這些大學都為單科性大學。再如1150年成立的巴黎大學,最初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學校發展而來,以研究神學而聞名。1200年巴黎大學法規規定教學包括神學、文學、法學和醫學四科,由此巴黎大學成為當時科目最齊備的大學,被譽為“世界大學”、“大學之母”。后來,一般大學都開設文學、法學、醫學、神學四科。
以單科性技術學院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偏理工型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等也經歷了從單科性到多科性再到綜合性的發展歷程。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麻省理工學院一直是純工科的技術學院。今天的麻省理工學院除了工科本科專業聲譽全球,其經濟學和語言學在全美高校中名列第一。加州理工學院也如此,原先單純的工科院校,發展到今天也涵蓋了理學、文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麥克×居里1988年對40所著名大學比較研究后得出結論,在影響大學聲譽發展的諸多因素中,專業方向數的多少是作用最大的因素,專業數少的學校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和努力。美國另一位學者沃克溫1989年對86所具備博士學位授權資格的公立大學進行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4]大學本身就具有學科集聚性特征,大學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其學科設置往往不再以單一的學科存在,而成為不同學科的集合,這也使得大學似乎具有一種天然地、自發地、努力地將學科體系變得更為全面的傾向。
三、大學綜合化發展的理性認識
大學綜合化發展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綜合化發展實質卻是一種復雜的全局性運作。綜合化進程中的院校不僅需要正確把握綜合性大學的內涵與特征,還要在回應教育外部環境時保持敏捷,更要在學科門類趨向齊全的過程中堅守自己的傳統與特色。正因為此,大學的綜合化歷程并非一帆風順,需理性認識以下幾對關系,避免因顧此失彼而產生種種負面效應。
(一)大學綜合化的“自然性”與“必然性”
學科單一的大學走上綜合化發展道路是必然的,但這個必然卻又是個“自然”的過程,并非人為“突然”而成。首先,大學綜合化發展應循國家產業結構的發展而自然發展。大學向綜合性大學的發展雖然是一定社會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走向高度綜合化的必然反映,但它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與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相對應,順應單科到多科再到綜合的自然發展過程;其次,大學綜合化發展應按學科內在發展邏輯而自然發展。大學的綜合化需依據原有辦學特色與傳統,在加強傳統學科的基礎上,選定與之相關、容易互相促進的重點學科,然后再根據學科間的相關性,由近及遠地形成合理的學科群,使大學真正走上綜合化發展道路。
(二)大學學科門類的“齊全性”與“綜合性”
在從學科單一向學科綜合的發展過程中,學科門類的齊全性常被當作是否成為綜合性大學的重要衡量標志。大學的綜合性確實離不開學科的多樣化和齊全性,但學科門類齊全也不等于學科綜合,多科性并列不等于學科融合和協調發展,多學科只是為學科的融合提供了可能[5]。綜合性強調的是學科之間的關聯性,是學科間的交叉、滲透性,以及學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共生性。不同的學科同居一校,如“老死不相往來”,并不能實現綜合性。因此,判斷一所大學是否具備綜合性大學的性質與特征,并不在于其學科門類一定要齊全,而在于其學科設置是否能構建一個合理的學科群,是否能促成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和融合,是否有利于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是否能給予學生全面而整體化的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
(三)大學學科發展的“綜合化”與“特色化”
“綜合化”與“特色化”并非一對矛盾體。大學的綜合化并不是要拋棄其原有的特色。“綜合化”是通過學科的綜合化拓展高校的辦學領域和發展方向,進一步培育和發展新興學科,開辟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科學研究領域。“特色化”則是實現大學辦學定位,使學校長期穩定發展并不斷獲取和形成競爭優勢的戰略手段,其核心也是學科與專業的特色化。可見,“綜合化”更側重于發展型戰略,而“特色化”則更側重于競爭型戰略。[6]“綜合化”與“特色化”屬于大學發展戰略中的兩個層面,綜合要以特色為導向,特色又要以綜合為基礎,二者共同推動高校的整體發展。因此,大學在綜合化過程中絕不能只追求學科的綜合,而拋棄學科的特色,否則就是拋棄學校的競爭力。
大學綜合化是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綜合性大學自身的內涵與特征使其比單科性院校更具優越性與競爭力。但這種競爭性與優勢又并非與生俱來,而是源于社會生產方式的變更與演進、科學技術由分化走向綜合等一系列內外因素的變動。因此,真正的綜合化發展是個自然過程,“突然”的綜合化發展必定會帶來種種負面效應。單科性院校在綜合化發展過程中不能僅停留在學科齊全這一表層上,綜合化發展也并不是要摒棄原先積累下來的傳統與特色,而要將兩者結合,共同推進學校的發展。
[1]郭桂英 方洪錦. 對多學科合并大學“綜合性”的探討[J], 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05):59.
[2]王英杰. 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1-62.
[3]別敦榮 徐警武. 我們為什么要辦綜合性大學——兼論重點理工大學文科發展戰略[J].高等教育研究,2000(06):94.
[4]蔡克勇. 21世紀中國教育向何處去[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55.
[5]龐青山 曾山金. 高校合并的四個不等式[J]. 機械工業高教研究,1999(03):17.
[6]李立國. 大學辦學綜合化與特色化的內涵及其關系研究[J]. 中國高教研究,2008(02):17.
浙江省教育廳一般項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大學專業調整機制研究——以杭州師范大學綜合化轉型實踐為例”(Y201635339)
(責任編輯:盧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