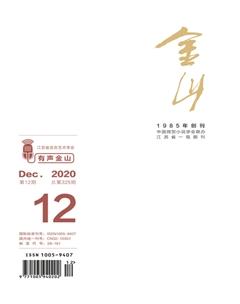有意味的小說
顧建新
汪曾祺曾提出,要寫出有意味的小說。什么是“有意味”?題材的新穎、情節的奇巧、人物的鮮活、意蘊的深刻、語言的生動……都是。
中國作協會員、內蒙古著名作家王炬創作過長篇、中篇、短篇,近期致力微型小說的創作,作品多次在大型期刊上發表,并獲過多個獎項。最近他一氣寫了幾篇關于“羊”的小說,給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他自己承包了四個牧場,經常去蒙古草原,因此對牧民和放牧生活非常熟悉,這,就給他的小說帶來了得天獨厚的創作契機和別人所不能模仿的嶄新的題材。
這三篇小說,都令人讀得津津有味。
首先是生動誘人的細節。如《詭異的牧工》中寫一個牧民老葛:
他剛進場的時候,正好是牧場氣候最惡劣的時候,氣溫零下三十多度,風很大,夾著雪粒,打得人都站不住,其他牧工都是把羊群趕出來,又躲回來喝茶,到了傍晚再去把羊群趕回圈里來。只有老葛,頭戴著一頂長毛的狗皮帽子,腳上穿著一雙厚厚的氈靴,在牧場里一站就是一天。他早晨喝四碗奶茶,用刀把凍肉削在碗里,再吃點果條什么的,然后裝上幾把炒米就出發了,中午在寒冷的牧場吃幾把炒米,等晚上回來吃個晚飯,不到七點就躺下,等半夜十二點又起床去羊圈看羊,而且有幾次半夜接羔子,一干就是幾個鐘頭。他不說話,只有萍姐主動和他說話,他才應答幾句。
這是一幅難見的“風中放牧圖”:細膩獨特的牧民形象,艱難的生活和人物不屈的拼搏,歷歷在目。我們對草原的認識是從歌中來的:“草原就像綠色的海,氈包就像白蓮花。”牧民生活并沒有那么浪漫和愉悅。正因為作者有深刻的體驗,才使我們看到了真實的另一面,從中感悟生活的真諦。
其次,是獨特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陶愛哥》《詭異的牧工》兩篇是直接寫牧民的。
《陶愛哥》中的主人公“陶愛哥”的形象很特別。小說在開篇時,就為人物出場設計了一個很特殊的矛盾:羊群轉場時,因為小羊身上沾上了機油味,媽媽就認不出他們了。其后果非常嚴重:小羊因不能吃奶面臨死亡;大羊的奶放不出來,易得乳腺炎。在人們束手無策的關頭,陶愛哥出場了。作者這樣寫,頗有深意:采用的是“危難處方顯英雄本色”的寫作方法,使人物一出場,就給人卓爾不群之感。此其一。第二,主人公用的方法也很不一般,用唱歌,輕易解決了母羊媽媽不認小羊的難題,寫出了人物的神奇。第三,更有出奇之處:他竟謝絕了事先談的三千元的酬勞,只要了一只小尾細毛母羊。有人說,這是因為牧民認定了這只羊是他妻子的化身。這正是神來之筆:寫出了牧民獨特的思想、獨特的情感。沒有對他們深刻的了解,就難寫出這樣的情節、這樣出奇的作品。這篇小說,分為三個層次:但絕不是平行的滑動,而是逐層推升的態勢,最后達到了高潮。
《詭異的牧工》緊緊抓住“詭異”做足了文章,達到了一種“紙短情長”的藝術效果。小說的篇幅不長,卻讓人讀之難忘。誠如我們前面所引的,這個老葛頭對放牧兢兢業業,不辭辛勞。但通過放錄像,卻發現了他有一個奇怪的舉動:不停地打一只很貴重的進口公羊。為什么會有這個令人難解的反常的行為?小說最后揭出:他在毆打這只羊時,嘴里不停地叨念:打死你這個張建剛,讓你搶我的老婆。原來,他是把羊當成了假想敵,在它身上發泄不滿。小說沉重地寫出了一個小人物難堪的生活際遇: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卻解決不了,甚至無人訴說,只能采取這種無奈的做法,結果是悲慘的:被開除了,失去了工作的機會。小說通過“這一個”,實際寫出了處于社會底層的一群人的悲慘處境。
《再一次告別》是專寫動物的。寫一個叫陶陶的女子,把羊當成了媽媽。兩人相依為命。當不能不離開時,羊竟然死了,讓人動容。使我們聯想到,這種深情超過了人類,這篇小說,讓我們某些人自嘆不如,感到羞愧!
我很早提出:寫動物,必須寫出人性。王炬的小說,嚴格地遵守著這一原則。我希望王炬能繼續寫草原的羊,寫出獨特,寫成系列,一定會讓更多的讀者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