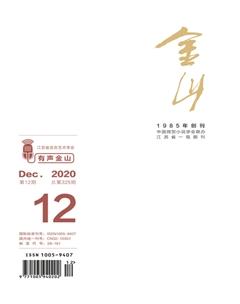愛上一座城
編者按:
1945年12月25日,二次大戰結束后的第一個圣誕節,賽珍珠向美國有關人士發出了圣誕賀卡,告誡人們不要忘記在亞洲和世界上還有成千上萬饑餓的、無家可歸的戰爭孤兒。這不是一張普通的圣誕賀卡,這是一張充滿人間大愛的圣誕賀卡,字里行間流露著賽珍珠的博愛情懷。
70多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賽珍珠所做的一切,影響了無數有識之士,著名作家顧堅先生說: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起賽珍珠,并有意無意地追尋著賽珍珠的腳步——寫我的故鄉,寫故鄉大地上的農民——那些可愛的鄉親,他們的辛勞、他們的淚水、他們的自足和歡喜。
和大多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鄉村孩童一樣,我對“鎮江”這個地名有概念首先來自于民間故事《白蛇傳》。許仙和白素貞人妖孽愛,被鎮江金山寺法海和尚覷破,藏許仙于法座之下,白蛇娘子帶領小青蛇前來尋夫,法海不許,白蛇娘子惱怒之下水漫金山,并搬來四海龍王與蝦兵蟹將幫忙,法海則搬來天兵天將對付,最終將白蛇壓在杭州雷峰塔下。不知為什么,孩子們對故事中的法海和尚非常厭惡,而對妖精白娘子和小青則充滿了同情,這大概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能,反感那種專門破壞他人愛情和幸福的家伙,至于受鎮壓的是人是妖,他們才不管呢!
“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余胥。”因為金山寺有個討厭的法海和尚,在我幼稚的心靈里,對鎮江的本初感覺竟不太美妙——好在不久便獲得了扭轉。
我家的隔壁是大隊民兵營長顧想田家。彼時的村官與現在的情形大相徑庭。顧想田家和基本群眾一樣窮困;夫妻倆參加生產隊勞動,同樣為填飽老少一家子的肚皮殫精竭慮。如果說顧想田家有什么殊異的話,就是屋里有一領蚊帳是用美國飛行員的降落傘改成的,那是他在朝鮮戰場上的戰利品,復員后獲準帶了回來。白絲綢質地的降落傘改成的蚊帳潔白華麗,摸在手上冰涼水滑的,就是放在宮殿里也不過分,可惜支撐在低矮昏暗的土坯茅屋里,真的是暴殄天物啊。確實,顧想田家窮得連一盞玻璃罩子燈都沒有,三個孩子種存、種英、種華也是穿得破破爛爛。1974年冬天的一個黃昏,有位穿著藍色工裝、背著鼓鼓囊囊旅行包的陌生人摸上他家的門,晚飯的時候整條巷子都聞得見燉肉香和歡聲笑語。原來這個姓李的中年男人是顧想田抗美援朝戰場上的生死戰友,部隊打散整編后兩人中斷聯系,現在李師傅通過多方打聽得知顧想田的地址,專門從鎮江坐車坐船,逶迤了一天一夜趕了過來,兄弟相見,擁抱執手,淚眼婆娑,訴不完的別后衷腸。明珍嬸子生怕怠慢了貴客,把腌了過年的咸豬頭燉了一大鍋,還請了大隊支書和大隊長來作陪。
第二天早上李師傅便匆匆趕回去了。吃中午飯的時候,明珍嬸子捧著我從來沒見過的蜜餞送到我家里來,告訴我母親,說想田昨晚和李師傅睡在一起,兩個大老爺們笑笑哭哭、哭哭笑笑談了一夜。早上起來打了五個雞蛋的蛋茶待客,然后下面,李師傅只吃了兩個蛋和面條就走了,把剩下的三個蛋留給三個孩子。說到這里明珍嬸子抹開了激動的眼淚,說今年老人孩子們過年都能做一身新衣了,李師傅不但帶來了好幾塊布料,臨走時還硬丟下四十塊錢和二十斤糧票。“他是拎著滿包來,拎著空包走的,我送他幾斤花生都不肯要,說帶走了過年孩子們的零嘴兒就沒有了……還說以后年年都來……”至此,我十一歲的少年心中突然徹底地轉變了對于“鎮江”的消極印象,老法海不重要了,老法海只是個神話人物,而這個來自鎮江的李師傅是活生生的人,是不忘戰友情的善良的人,是給他人提供無私援助的高尚的人!
果不其然,次年春天李師傅又來了。這次帶來了更多的禮物:有座鐘、半導體收音機,還有諸如手電筒、罩子燈、塑料搓板等日用品,還有老人吃的京果粉和京江臍點心;當然還有孩子們吃的蜜餞和糖果,讓整條巷子的孩子們嘴里甜了好幾天。村民們都說李師傅是顧想田家的恩人。
大學畢業后,我先在農村從教,后下海來到揚州從事服裝批發生意。每到南方進貨,都從瓜洲輪渡過鎮江,竟一回未能停駐——直到2005年初冬才真正做了一次鎮江訪客。
此時我已棄商從文,成為揚鎮兩地作家協會組織的第一屆“雙城會”采風成員。鎮江方面組織得十分妥當,座談前安排我們游覽了江城主要名勝。踏上金山寺印著苔痕的斑駁石階,我聯想起孩提時聽到的白蛇傳說,沒來由加快了腳步,仿佛一不留神身后便會洪水漫天;待登上山頂,俯瞰遠處城市萬千人家,心里又在想:在哪一棟樓房或哪一條幽深的胡同里,住著顧想田的生死戰友、那個給我的童年帶來江南甜味的李師傅呢?
就在這次鎮江采風中,我接觸到了“賽珍珠”這個名字。在文學上半路出家的我感到匪夷所思——這塊土地上曾經生長過一位金發碧眼高鼻梁的美國女兒!1892年出生的賽珍珠剛三個月便隨傳教士父母離開美國,來到中國,在鎮江的老百姓當中一天天長大。她上著中國的私塾,讀著中國的圣賢書,中文成了她的第一母語,在某種意義上她成了一個地道的鎮江女孩。她熱愛鎮江,熱愛中國文化,一直到十八歲才回到美國接受大學教育,然而大學畢業后又重返中國,嫁給一個有農業專長的美國青年,夫唱婦隨,從而更深更廣地接觸了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這為她以后從教之余開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鄉村基礎。1931年,她寫出了長篇小說《大地》,一舉成名,以典型的懷舊筆觸講述中國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土地是農民的生命,也是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作品中充滿了對落后中國和底層農村的同情、憐憫和真誠。1938年,已回國定居的賽珍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這些年來,我一直認為賽珍珠之所以獲得諾獎,和她獨一無二的中國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和中國式的文化體驗、文化儲備分不開。雖然用的是英文,她的寫作卻是實實在在的中國寫作,而她又是現實主義的,是寫底層寫農村寫農民的,她的腳步一直站在堅厚的中國大地上。這個喝著長江水長大的女子一輩子都在為中國說好話,甚至她的離世都跟中國有關——她對中國充滿了深情,沒有中國,就沒有賽珍珠。鎮江是賽珍珠真正意義上的故土。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起賽珍珠,并有意無意地追尋著賽珍珠的腳步——寫我的故鄉,寫故鄉大地上的農民——那些可愛的鄉親,他們的辛勞、他們的淚水、他們的自足和歡喜。無論是《元紅》《青果》《黃花》,還是《愛是心中的薔薇》和《運河逐夢》;甚至是抗戰題材的《火苗》,描寫的也是一組抗爭不屈的農民群像。我寫著這些一路走來,心里十分踏實,因為我站在闊大的鄉土背景中,站在堅實的農村大地上。我有時甚至突發異想:我的寫作是不是發端于孩提時代聽到的那個“水漫金山”的愛情神話?我心中的愛意培育是不是跟鎮江那位有情有義的李師傅有關?至于我的寫作軌跡和表達取向,則在上面說過了,肯定的,跟那位鎮江的女兒——賽珍珠脫不了干系。因為愛上人,所以愛上城——因為愛上了白素貞,愛上了李師傅,愛上了賽珍珠,我愛上了一座江城——鎮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