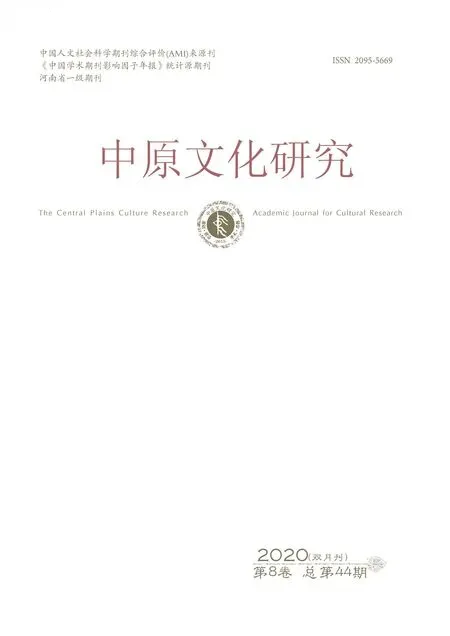神熊意象與中華文明探源*
胡建升
西方人設定了討論文明起源的三個標準,即文字、青銅器與城市。如果依照西方這一文明標準,商代才是華夏文明與文化的開始,因為甲骨文是在安陽殷墟發現的,而且甲骨文中有殷商的文字證據。我們通常所說的中華文明5000年,依照西方這一標準,最多只有3000 余年。可見,拘囿于西方人的標準來討論中華文明探源問題,就會顯得捉襟見肘,無法展開。因此,只有暫時擱置西方關于文明的三個標準,才能重新去理解和發現中華文明起源的本土特質與核心要素。
一、文化大傳統與神熊文化之根
文學人類學重視田野調查,尤其重視立足中國本土素材,結合考古出土實物與物質圖像來提煉中華文明與華夏精神的文化基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扎根中國本土的文化大小傳統理論。將史前無文字時期的文明與文化傳統稱為大傳統,將文字出現以后的文明與文化傳統稱為小傳統。如果將西方文明的文字標準放置在文化大傳統的新型理論視野之下,就可以發現,西方關于文明的相關概念及其標準,其實質乃是文化小傳統的文明觀念與文化精神,不足以涵蓋文明在大傳統時期的文化意義。
文學人類學依據大小傳統的文化理論,相應提出了N 級編碼理論,將無文字時期的文化大傳統編碼稱為原編碼(或元編碼),即一級編碼與文化基因;將甲骨文與金文出現以后的文化編碼稱為二級編碼,將先秦經典的文化編碼稱為三級編碼,將秦漢以后文人的文字書寫至今天的各種文字文本稱為N 級編碼。如果將西方關于文明的文字標準放置在N 級編碼體系中,也可以發現,西方關于文明的定義與范圍極為狹小,其重視的是二級至N 級編碼的文字書寫形式,而忽略了大傳統文化時期的文化基因與原初編碼。
如果立足于文化大傳統與N 級編碼理論來探究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最為重要的是要重視文化文本。文化文本與文字文本不同,前者是以出土實物與史前物質圖像為主的文本形式,后者是以文字書寫為主的文本形式。從時間關系來看,前者是史前無文字時期的重要遺留物與文明痕跡,后者是文字出現以后的歷史記錄與書寫形式,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文化貫通與文脈傳承關系,但前者屬于史前先行出現的特殊文本形式,后者屬于后來崛起的流行文本形式,不能因為文字文本的出現,就完全陷入文字文本中心主義,而忘記了在文字文本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文化文本。相較而言,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只有據源析流,才能源流分明,條理有序。為了彰顯文化文本的文化基因與源頭功能,只有暫時擺脫文字文本的局限,才有利于開啟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大傳統新模式。
在文化大傳統、N 級編碼與文化文本等諸多理論新視野中,中華文明探源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距今10000年至文字出現的3000年之間)提煉和總結出中華文明的核心文化要素。葉舒憲近來提出,在文化大傳統時期,存在一種被歷史敘事所遮蔽的玉石神話信仰(玉教),他認為,玉石文化與玉禮器是文化大傳統時期的核心文化要素之一。
同時,深入史前無文字的大傳統文化時期,在玉器、陶器、骨器、漆器等諸多出土器具之上,都存在著一種極為普遍的“制器唯象”“制器尚象”的文化現象。在文字還沒有出現以前,神話意象已經成為具有優先表達意義的符號功能,也可以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要素。
為了展示神話意象在文明探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我們以神熊意象為例,聯系與中華文明起源相關的幾個方面,展示神熊意象在建構中華文明起源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為探討文明起源、國家制度、文化認同等諸多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視野。
動物熊是自然界的猛獸,早在幾十萬年前的洞居時代,猿人就已經獲得對熊的神性知識,熊具有冬眠與復蘇的生理習性,由此,將熊與宇宙氣運、大地母親的季節物候聯系起來,形成熊是宇宙物候節奏的神性信使的神話認知。從遼寧金牛山猿人洞穴遺址中同洞出土的28 萬年前的猿人頭骨與熊頭骨,到同洞出土的大約3 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人骨與熊骨,都展示了人熊之間的信仰觀念與神話幻想故事是具有長時段的文化積淀。在牛河梁紅山文化的女神廟中,廟頂部有一只完整的泥塑神熊,底部有泥塑神鷹,這種神話結構為我們探索神熊意象與中華文明起源奠定了文化大傳統的神話真知①。隨著中華文明的逶迤到來,古老的神熊認知與文化記憶也就以神話關聯與支配動力的方式滲透到文明制度之中[1]。
二、三皇之首伏羲:神熊創世與文明起源
伏羲是華夏人文始祖,這是一種文化共識。唐代司馬貞在《史記》“正義”中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并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2]1司馬貞在《三皇本紀》中將伏羲、女媧與神農列為三皇。
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出土文獻《楚帛書甲篇》云:“曰故(古)大熊包戲(伏羲),出自囗(震),居于睢囗。厥囗,囗囗囗女。夢夢墨墨,亡章弼弼。囗每(晦)水囗,風雨是于。乃取(娶)囗囗子之子,曰女(媧),是生子四。囗是襄而,是各(格)參化法(度)。為禹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騰)傳(轉),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陽)氣百(魄、陰)氣,以為其疏,以涉山陵、瀧、汩、益、厲。未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步以為歲,是惟四寺(時):長曰青干,二曰朱四單,三曰白大橪,四曰□墨干。千有百歲,日月夋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備(侐)。四神乃作,至于覆(天蓋),天旁動,捍蔽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囗思(保),奠四極,曰:非九天則大(侐),則毋敢蔑天靈,帝夋乃為日月之行。共攻(工)囗步十日四時,囗神則閏,四□毋思,百神風雨,辰祎亂作,乃囗日月,以傳相囗思。又宵又朝,又晝又夕。”[3]董楚平認為:“帛書甲篇是很標準的創世神話,在現有的中國先秦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還沒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確的創世神話。”[3]在楚帛書的創世神話中,天地尚未形成,宇宙處于混沌的狀態之中。楚帛書認為,混沌之中,首先誕生的是“大熊伏羲”,猶如混沌之中生出太一,可見,大熊、伏羲與太一處于創世神話相同的結構位置。此后再有伏羲、女媧結為夫妻,生了四神。這個過程可以看成是由太一、太極分化出陰陽,然后由陰陽產生四象。四神開辟天地,才有了大地與天蓋。這樣才有四時、四方、日月星辰和五木等。
在楚帛書中,為何大熊成為宇宙化有的太一狀態的文化象征?這可能跟大熊冬眠與復蘇的生理習性有關。大熊進入黑洞,開始了漫長的冬眠,黑洞就成了混沌未開的原始象征。第二年春天,大熊蘇醒,從黑洞之中爬出來,就猶如鑿破混沌的天帝太一。從楚帛書中的大熊伏羲,轉變為伏羲女媧二元結構的伏羲,就好比是由太一結構分化為真陽與真陰的二元結構。楚帛書的文化結構為:大熊伏羲(太一)—伏羲與女媧(陰陽兩儀)—四神(四象)—大地天蓋日月四時四方等。神獸大熊成為華夏創世神話的最為核心的文化基因,相當于太一、太極的中心位置,是人類鑿破混沌、迎來光明的帝象之先。
《易緯·乾鑿度》記載:“黃帝曰:‘太古百皇,辟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知生化柢,晤茲天心。念虞思慷,慮萬源無成。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行。’”注云:“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也。”[4]1《易緯》是漢代學者的文字文本,但依舊保留了早期大熊創世的神話敘事。首先,有熊氏伏羲通達了“天心”,所謂“天心”,就是舍棄作為個體存在所具有的各種人為思慮念想,通達了宇宙之初的道體神性,然后才達到了宇宙之初的混沌狀態,這就是“萬源無成”。然后,從混沌之中,有熊氏生發出“物”。這種“物”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太易”“太極”的文化過程,才形成“乾坤”天地,然后才有萬物的有形存在出現。將《易緯》與楚帛書中的創世神話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兩者具有相同的文化結構,大熊伏羲與有熊氏伏羲都成為宇宙混沌的創世者。神熊意象成為華夏創世神話中創世神的重要符號。
作為創世之神的大熊伏羲與有熊氏伏羲,隨著“雌雄”二元觀念的出現與形成,“熊”就常常與“雄”通用,這種文化符號的通用現象,就開始遮蔽了作為太一狀態的創世神話。《釋名》:“熊者,雄也。”《皇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陳,作瑟三十六弦。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皇。后世音謬,故或謂之宓犧。一號雄皇氏,在位一百一十年。”[5]607伏羲由“大熊”“有熊氏”,變成了“雄皇氏”,而“雄”不過是陰陽、雌雄二元結構中的一個因素,作為太一狀態的創世神結構就被人遺忘了。
三、五帝之首黃帝:神熊意象與帝車制度
在西方文化中,北斗星被稱為大熊座,以熊意象來比擬天體中的星象。在東方文化中,北斗星又被比喻為帝車。《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斗。”[2]1291所謂帝車,就是天帝巡視宇宙時所乘坐的神車(見圖1)。神車所到之處,就是天帝所到之處。可見,在天體星球中,北斗星成為天帝所至的標志性符號。北斗星斗柄所指代表了天地氣運變換、自然節氣轉變的重要標志,這與神熊的冬眠與復蘇一樣,都是自然季節物候的靈使。
《史記》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也成為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之一。梳理相關文獻發現,黃帝出身于有熊氏,乃是受到北斗星精所感而生,其坐擁有熊之國,居軒轅之丘,還以軒轅為號。《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于壽丘,長于姬水。龍顏,有圣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5]611-612《河圖握樞》曰:“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大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5]612總結黃帝的文化符號,可以看出:一是與熊有關,如有熊氏與有熊國;二是與北斗有關,如北斗星精感化而生,是北斗在人間的化身;三是以帝車為號,軒轅即車,居軒轅之丘,猶如天帝居住在帝車之上。
可見,在人文始祖黃帝的身上,匯聚了作為自然宇宙節氣轉換的天地靈使符號,如天上的北斗與地上的神熊,還有運載天帝的帝車。北斗是天帝的化身,神熊是大地母親的標志。帝車成為天帝與大地母親自然運轉的運載工具形式。黃帝之所以是黃帝,有著極為神奇的神話結構:神熊—北斗星精—帝車,而這三個標志性的意象符號又有共同的神話價值,即都是宇宙神圣天帝與大地母親的有形顯現。

圖1 北斗帝車畫像,山東嘉祥武梁祠

圖2 熊與帝同車(正面圖),春秋,1998年甘肅禮縣圓頂山1號秦墓出土②
在甘肅禮縣圓頂山1 號秦墓出土的青銅車上有一人一熊(見圖2),中間之人應該是天帝的形象,熊為太一的形象,天帝與太一居于青銅車的中央。車體周邊四隅是四鳥與四獸,形成了以天帝與神熊為中心的神話空間結構。聯系上面黃帝的神話結構可知,青銅車猶如帝車,承載著天帝與神熊太一,也形象地講述了自然宇宙氣運的季節物候故事。
四、大禹建熊旗:神熊意象與國家旗幟制度
旗幟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民族國家的集體信仰。建立國家民族的旗幟,就是樹立一個國家集體的核心信念,由此形成集體行動的文化方向。同時,為了區別旗幟,通常在旗幟上標示一定的標志物,諸如日月星辰等,以此展示旗幟的空間秩序與權力關系。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華夏文明最早的建旗制度應該是從黃帝開始的。《列子·黃帝篇》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虎為前驅,雕、鹖、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6]84黃帝在炎黃之爭中,為了嚴肅軍隊紀律,統一指揮,組織了以神獸為形象的軍隊,建立了以神鳥為標志物的旗幟。清代學者黃奭所輯的《河圖稽耀鉤》載:“黃帝之生,先致百狐。有蚓長十二丈。幼好習兵,長善攻戰。問之于風后曰:‘夫帝之旗何如乎?’風后曰:‘予高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朱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旗;中央法黃龍,曰常也。’”[7]5《河圖》中風后向黃帝提出建立“帝之五旗”,按照東、西、南、北、中的順序,分別是青龍旗、白虎旗、朱鳥旗、玄蛇旗與黃龍旗,五方的旗幟標志物各不相同。從中心意象與四象、四靈來看,文化小傳統中的黃帝建五方旗明顯受到漢代五行觀念的影響,中央黃龍意象彰顯了神龍意象的文化崛起。
出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容成氏》中記錄了大禹建五方旗的事跡,其云:“禹聽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略矢。田無蔡,宅不空,關市無賦。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實之,乃因近以知遠,去苛而行簡。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夫。是以隸者悅治,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請貢。禹然后始為之號旗,以別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禹然后始行以儉:衣不鮮美,食不重味,朝不車逆,舂不毇米,宰不折骨。制服冕黻。禹乃建鼓于廷,以為民之有訟告者鼓焉。”[8]264-267大禹執政3年之后,可謂政通人和,四海之內的其他部落紛紛前來請貢,以表示對大禹政權的臣服之意。大禹為了區別自己的中央位置與其他的請貢部落,開始建立五方旗制度。同時,為了表明朝廷的司法公正,還配套實施廷鼓制度。五方旗制度是從視覺符號方面建立空間權力秩序,建立廷鼓制度是從聽覺符號方面建立國家懲治處罰法律制度,從而保障了國家秩序與中央權力的有效性與正當性。
大禹建立五方旗,在選擇旗幟的符號標志物方面,也使用了特殊的神話意象。東方旗幟上是太陽,西方旗幟上是月亮,南方旗幟上是蛇,北方旗幟上是鳥,中央旗幟上是熊。中正之旗代表的是大禹的中央集權,四方之旗代表的是臣服的四方部落。大禹選擇了“熊”作為中央權力的神圣標志物,彰顯了“熊居中央”的古老文化記憶與史前原型編碼。
在河南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上,用綠松石鑲嵌出一種神獸的形象,我們認為,這種神獸與夏代王朝的神物崇拜與宗教信仰有關,尤其與夏代君王的旗幟圣物有關,就是神熊意象。銅牌上的神熊,與中正之旗的神熊,正好勾勒出中華文明第一個王朝的神話信仰標志物,都用神熊意象來展示國家的神圣權力。
到了周代,依舊保留了“熊虎為旗”的古老傳統與神圣信仰。《周禮·春官·司常》云:“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9]859在“熊虎為旗”中,盡管“虎”也開始成為旗幟的重要意象,但是“熊”的核心標志地位依舊沒有改變。許慎《說文解字》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從其聲。《周禮》曰:率都建旗。”[10]170許慎在解釋“旗”的時候,就直接用“熊旗”來解釋,可見,“神熊意象”與旗幟制度具有一種對等互稱的關系,說到旗幟,是指“熊旗”。劉熙《釋名·釋兵》云:“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為旗,旗,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旃,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熊虎為旗。旗,期也,與眾期期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11]18253劉熙區別了天子旗幟、諸侯旗幟、三孤旗幟與軍將旗幟。他認為,天子是建日月常旗,諸侯是建交龍之旗,三孤是建赤色之旗,軍將建熊虎之旗,可見,隨著社會復雜化程度增加,旗幟制度也出現各種等級分化。作為國家集體的神熊意象,開始淪落為軍隊部門的旗幟符號了。
結論
在無文字的大傳統文化時期,各種不同材質的器具與器物上的神話意象極為豐富,充分體現了史前時期“制器唯象”的神話思維與文化編碼,甚至可以說,神話意象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重要符號標志。
在大熊伏羲的創世神話中,大熊扮演著太一的神話角色,太一伏羲與女媧形成二元結構,他們結婚之后,才產生了四神,然后才有四神開天辟地,創造天地日月萬物。可見,神熊作為太一化身的神話意象直接推動了宇宙世界的誕生,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最為原始的創世神。
在人文始祖黃帝的神話中,黃帝誕生于北斗星精,居于有熊之國,號為軒轅,將北斗帝車與神熊意象融為一體,神熊與天帝乘坐帝車,依據自然宇宙的運化節奏,成為天父與地母最佳的物候信使。只有理解了神熊與北斗的宇宙信使身份與神話認知,才能理解黃帝為何是北斗星精所生,黃帝為何成為有熊國君,為何以軒轅為號。可以說,北斗為天帝的使者,神熊為地母的信使,黃帝為人間的圣靈,它們共同承載了宇宙自然物候的氣運變化。
旗幟是國家制度的象征,也是集體信仰的標志。大禹建立五方旗,中央的旗幟圖騰物或符號標志物是神熊,二里頭出土銅牌飾上的神獸也是神熊,神熊意象成為中華文明第一個王朝的神圣之物,神熊信仰成為建立國家五方旗幟制度的支配動力。
在大傳統文化時期,青銅器還沒有到來,玉器就扮演著文明起源的核心物質要素。文字還沒有出現,各種出土器具之上的神話意象就成為文明起源的原始動力與文化文本。要探尋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發掘華夏文化的精神實質,必須從大傳統文化時期的神話意象與文化文本入手,才能逐漸揭開中華文明的本土特質,才能理解諸多作為文化現象存在的文明形式與國家制度。只有理解了文化大傳統時期神話意象的原型編碼與文化基因,才能真正揭開中華文明與國家起源所潛藏的支配動力與精神信仰。因此,史前神話意象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要素之一。
注釋
①2019年8月30 日至9月1 日,筆者參加遼寧省朝陽市德輔博物館召開的“國際熊文化研討會”,有幸聆聽郭大順先生回憶當年發掘牛河梁女神廟時的真實情景。9月1 日下午,筆者還跟隨郭先生參觀牛河梁女神廟遺址,詳細了解了女神廟出土泥塑熊與泥塑鷹的神話現場。具體可參閱楊樸、楊旸:《牛河梁女神廟的真相再揭秘——記文學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一次對話》,《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1 期,第1-7 頁。②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禮縣博物館:《禮縣圓頂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 期,圖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