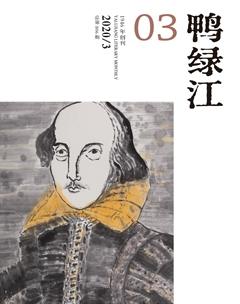在日本也不得安寧
1月15日,中美之間達成了第一階段的經(jīng)濟貿(mào)易協(xié)議,各國的股市都出現(xiàn)了大幅度上升。但僅僅一周以后,武漢就遭到猛烈病毒的折騰,使中國首次經(jīng)歷了一個安靜的春節(jié)。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問題被西方稱為“黑天鵝”事件。“黑天鵝”本來是金融用語,直譯的話,就是事先無法預測的重大事件。事實證明,新冠肺炎的確像一股亂氣流,給中國自身和世界帶來了超乎預料的沖擊。
生活在東京的我,從1月22日開始,日子過得幾乎一模一樣。早晚看新聞,白天看微信和朋友圈。有關于新冠肺炎的各種情報鋪天蓋地。這使我想起了德維爾寫的小說《瘟疫與霍亂》。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數(shù)千人喪生,整個香港陷入恐慌。葉森奉命前往研究疫情。他碰上了一場科學競賽,他的對手是日本科學家北里柴三郎,香港的醫(yī)院全力配合北里,給他最好的設備與器材,但卻不給葉森任何資源,甚至不愿意提供病死者的尸體。與葉森隨行的神父買通停尸間的看守者,偷了幾具尸體出來,讓葉森在臨時搭建的簡陋茅屋做研究。我挺喜網(wǎng)上的這段評價:“在書中還具有人類必須永無止境與各類‘瘟疫對抗的寓意,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禍患,包括書中提到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人性的斗爭、自然土地的開發(fā)等。此外法語中有一句話是‘在瘟疫與霍亂間選擇(choisir entre la peste et le choléra),意指兩難的抉擇,本書亦借用這樣的意涵,指涉書中科學發(fā)展的兩難:科學一方面能戰(zhàn)勝瘟疫,但也能使瘟疫迅速在全球散播;科學能改善人類處境,但也可能成為戰(zhàn)爭的武器,造成大規(guī)模傷亡。”
在這場瘟疫面前,我一直像一個隔岸的旁觀者。我一直認為國內(nèi)的現(xiàn)實不會比想象的要壞。不管怎么說,我所認識的國內(nèi)朋友中,還沒有一個人染上新冠肺炎。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把新冠肺炎當一回事。
到了2月6日,我突然覺得不對勁兒了。早上的新聞聯(lián)播說日本國內(nèi)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已經(jīng)有37人。但中午的報道說已經(jīng)飆升到45人。僅僅在一天里,數(shù)字更新了兩次,與巨型游輪“鉆石公主號”有極大的關系。來龍去脈如下:1月20日,一位80歲的男性乘此游輪從橫濱出發(fā)去香港;22日在鹿兒島下船參加了集體活動。25日,該男子再次乘游輪;2月1日抵香港后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問題是,跟該男子一起參加活動并乘同一輛大巴的人有42人。而且,游輪中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戴口罩。2月3日,“鉆石公主號”從香港返回橫濱。因為80歲男性的原因,日本政府決定對游輪上的乘客進行檢疫。102個樣本中,確診有20人被感染。為此,日本政府決定禁止游輪靠岸,對船上所有乘客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隔離期間,因活動范圍小,時間也有限定,以至于有人形容游輪為海上流動監(jiān)獄。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還有二百多人的檢疫結果沒有出來。就現(xiàn)在的感染倍率來說,被感染的人數(shù)可能會直線上升。再說“鉆石公主號”,事件中有一個令人擔心的地方,那就是游輪在那霸停留后,有22人留在了那霸。也許那22人中也有被感染者。
我覺得應該買口罩的時候,家附近的藥店已經(jīng)沒貨了。據(jù)說都被中國人買光,被寄到中國去了。不過沒關系,日本人家里永遠閑著一兩盒口罩的。
住在池袋的朋友告訴我,她不敢輕易上街,也不敢輕易去飯店了。因為池袋是東京的中華街,遍地是中國人。兒子的籃球隊本打算在3月初開聯(lián)誼會,地點臨時從池袋的中國飯店改到學校附近。
1月16日和24日,我曾在家里接待過從中國來玩的幾個朋友。但家里人告訴我:一段時期內(nèi),不允許帶剛從中國那邊來的人到家里來。
每頓飯都在家里自炊了。
消毒水不離身了。
洗手洗三分鐘了。
這一切都緣于恐懼。
文藝復興時期彼德拉克在信中寫道:“我寧愿自己從未誕生:沒有天庭的閃電,沒有地獄的烈火,沒有戰(zhàn)爭或任何可見的殺戮,但死亡彌漫。有誰見過如此可怕之事嗎?”
在這場瘟疫面前,沒有人是局外人了。
2月7日。是我覺得最難受的一天。早上打開微信,好多人的朋友圈忽然看不到了。群里圈里都是李文亮的名字和燃燒的蠟燭。毛尖的《為李文亮哭吧,但是》接近刷屏。瘟疫以來,我第一次覺得心痛得喘不上氣來。
除了一個中國患者死在菲律賓之外,所有的死者大都集中在武漢。有的日本學者說,新冠肺炎是低毒性高傳染。在理論上,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新型病毒性感冒,及時控制好癥狀就頂過去了。那么湖北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呢?因為貽誤了疾控的最佳時機,病毒已大面積蔓延,醫(yī)療資源不夠用了。但是,早在12月30日17時48分,李文亮在一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中就已經(jīng)發(fā)布信息,稱“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yī)院急診科隔離”。這本來是社會中最自然的警報器。如果世界上有“如果”的話,讓我們可以回到那個時間,重新面對,也許李文亮和那幾百人不用死。
這次新冠肺炎事件,最受影響的不僅是中國經(jīng)濟,也有國際形象,同時激發(fā)了民眾的權利意識。災害應對中真正重大的考驗,歸根結底也許是在行政管理。“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災難面前,我們應該仰仗的兩樣東西是,相信科學和對大自然的敬畏。
同樣是2月7日,一條微博刷屏。關于《中國新聞周刊》的兩份專刊。17年前SARS,封面寫著:我們還要為SARS付出多少?17年后,同樣的疑問再次發(fā)出:我們還要為新冠肺炎付出多少代價?
我不知說什么好。我先前一直說人死了不該過于難受,動物死了才會動心,但我卻想為李文亮和632名死者哭泣。每天,死者的數(shù)字都在繼續(xù)上升,而太陽卻會照常升起。我的悲傷好像陽光下的影子,藏也藏不住。
作者簡介:
黑孩,女,曾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學》編輯,1986年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出版短篇小說集《父親和他的情人》《傻馬駒》,散文集《夕陽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華麗》《故鄉(xiāng)在路上》,長篇小說《秋下一心愁》《櫻花情人》《惠比壽花園廣場》等。在《收獲》《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小說選刊》《思南文學選刊》《作家》《山花》《鐘山》等雜志發(fā)表作品。現(xiàn)定居日本,在日本期間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雨季》、長篇小說《惜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