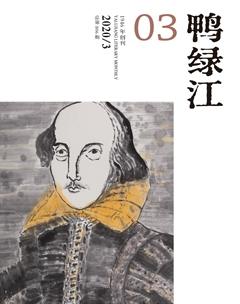疫期雜感
在寫這些文字的此刻,我置身于廣州家中。我的同事已經上班,和我一樣有外出接觸史的,都在家隔離。我1月22日乘高鐵路過武漢,仍有人上下車,并坐在我的身邊,而23號,武漢就封城了。那一瞬間,方才和大部分人一樣意識到:這次的情況嚴重了!2月5日,我從外地坐飛機回到廣州。乘坐地鐵,發現曾以每日人流量達到四十萬人次而“稱霸世界”的體育西站,也只有寥寥數人上下車。每節車廂零零散散有五六個人,戴著口罩,低頭盯著手機一動不動,宛如雕塑。
我一開始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和蔬菜,但蔬菜經不起放,發黃變質,隔幾天還是得出門購買。廣州的商業秩序還是不錯的,小區門口的幾家超市正常營業,紙巾、雞蛋和水果被放置在門口的顯眼處。隨著疫情的持續,出門所能見到的人越來越少,包括冒著風險在小區散步透風的人也越來越少。小區門口的保安對每次出入的人用紅外體溫器測量體溫,那姿勢猶如近距離射擊。人們被分隔,焦慮在蔓延,恐怖在激增。廣東的感染人數在持續增長,確診人數僅次于湖北,成為全國感染位列第二的省份。常規的時間流逝被裝上了剎車裝置,空間的封閉更是加劇了這一點。我們通過互聯網不斷地閱讀著關于疫情的每一篇報道,朋友們會發信息打電話,交流關于本次疫情的復雜感受。
瘟疫時期的生活,肯定才是真正同質性的,與戰爭狀態的確非常相似。我們都被裹挾進去了,無論身體是否染病,我們的精神都是病態的,都已經感染了病毒釋放出的恐怖信息。病毒并沒有因為對它的種種認知(比如基因序列、感染方式)而降低它的神秘色彩,它反而展現出更加強烈的神秘性,這讓人們不再持有一種穩固而傳統的生命觀念,我們應當持有一種更加開闊的“大生命觀”。那些被我們停留在口號中的“生態”,是如此真切地和每個人性命攸關。生態并不在遙遠的巴西雨林,就在我們的呼吸當中,無數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將我們和巴西雨林緊密相連。
作為寫作者,在這種情形下,肯定不會忘記那些讀過的經典文學作品,比如《瘟疫年紀事》《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等等,不勝枚舉。我在這里想著重提到一段話。在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他和他的人》里邊,他說道:“在瘟疫的日子里,他的人寫道,有一些人出于恐懼,把一切都丟開了——他們的家、他們的妻子、孩子,顧自飛快地逃離倫敦。一旦瘟疫過去,他們的行為就會為人所不齒,無論從哪方面看他們都是懦夫。但是,我們忘記了面對瘟疫時需要喚起的是什么樣的勇氣。這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氣,也不是抓起槍打死敵人的勇氣,而是挑戰騎著白馬的死神的勇氣。”這段話仿佛就是為我們今天而說的。
從文學的角度如何理解疾病與文學、疫情與社會的關系,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思考視域。在我看來,疾病及其結局的死亡,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不同的疾病類型,讓我們意識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比如傳染病,讓我們直接面對人的社會屬性;比如外傷,讓我們直觀看到身體受到傷害的殘酷性;比如癌癥,顯示生命系統本身所出現的障礙,是一種生命系統的限度性結局。沒有任何東西像疾病這樣能使人完全深入地專注于自己的感受,認清生活的真實境遇。正是因為疾病,我們自以為完全屬于自己的那個可以靈活移動的身體,終于跟社會價值觀以及復雜的社會關系產生了無比密切的關系,我們這才真切地意識到,這個身體的自由原來是如此有限而脆弱。
除卻我剛才提到的那些直接以疾病命名的作品,事實上,在我看來,至少一半以上的文學作品都和疾病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沒有疾病,便沒有文學。《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咯血決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劇,《三國演義》中曹操的頭痛癥與他多疑多思的性格也是一體的。因此,疾病對文學來說是百分之百的隱喻與象征,文學不可能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正如沒有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的人生。疾病會在任何層面上改變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學的敘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闡釋和轉變的功能。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并非是要解構疾病在文學中的功能,它恰恰是以文學的方式針對現實層面中疾病在道德方面的過度闡釋,以及相應的歧視與壓抑。換句話說,將疾病的道德色彩通通剝離那是生物學而非文學,文學是以悲憫與共情重建疾病與道德的關系。
我們所謂的“高科技”也愈加顯現出它的局限性。“新冠病毒”無疑是對目前的“高科技”的一種嘲笑。我們在人工智能、5G、自動駕駛等等科技背景下,感受到的人類科技已經開始創造魔法般的奇跡。但一場瘟疫,跟幾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樣,輕易就給“科技社會”以致命一擊。這讓我想到愛因斯坦說的一句特別有名的話:“在生物面前,我們的科學技術就像原始人一樣。”我們如何理解人類本身,依然是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我們從文藝復興開始,人變成了判斷萬物的尺度,到了今天,在某些極端環保生態人士眼中,人類與動物的存在又來到了同樣的尺度上。人的限度在哪里?人的本質何在?這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迫切的核心問題。在量子物理學的視野中,人是觀察者,這種觀察本身會影響數據的測量,也就是人跟世界之間其實是不可劃分成毫無關系的主觀和客觀,那只是一種宏觀上的錯覺罷了。我想,我們在文化層面也是同樣的,我們得理解我們自身作為觀察者跟實踐者的雙重角色和身份。
疫情還是會改變我的寫作與讀書計劃。被疫情的信息牽引,這是一個當代人最基本的情感方式。病毒是肉眼看不見的,但信息在占據你的眼睛,并無限接近病毒的某種真實狀況。你在其中獲得絕望和希望,從而體會到生命的尊嚴與脆弱。在今天,瘟疫及其信息的瘟疫都是我們需要雙重承受的。因此,我又翻開了《鼠疫》,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這是一本堪比疫情防治指南的小說,尤其是關涉我們心靈瘟疫的部分。書中說:“鼠疫會使城市發生變化,也不會使城市發生變化。”我們能夠識別并記住那些變化與不變嗎?此前我在讀庫切的新書《耶穌的學生時代》,這里的耶穌又是一個隱喻,里面講的是一個孩子如何被引導著認識這個世界。我們其實一直都處在這樣的境地,各種話語自始至終在引導我們。我們從各種話語中得到了建構主體的養料,但同時也必須跟各種話語做斗爭,這便是主體的判斷與選擇在持續影響主體的生成。一個人認為自己成熟了,成長與己無關了,這是最為可怕的想法。《耶穌的學生時代》和《鼠疫》一起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人的境況竟然是如此復雜、多變和琢磨不定,文學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2020年2月25日
作者簡介:
王威廉,先后就讀于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文學博士。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生活課》《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譯為英、韓、日、俄等文字。現任職于廣東省作家協會,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廣東魯迅文藝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