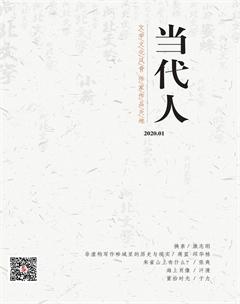“換”難之中見“親”情(評論)
作為賈大山的親傳弟子,康志剛深諳短篇小說的創作三昧——短小精悍、以小博大、簡約而不簡單。正所謂短篇雖短,五臟俱全,其短篇新作《換親》便采用“主題套盒”的敘事手段為我們完美地演繹了“芥子納須彌”的文學辯證法。
就情節層面而言,小說可一言蔽之,即一場荒唐“換親”事件引發的人間悲劇:村里有個姑娘叫小素,長得好看又善良,正值談婚論嫁的年齡,卻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個中原因不在小素,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小素的哥哥小海一直討不到媳婦,長期的精神負擔最后轉化成了生理上的疾病,哥哥突然間落下個耳背的毛病。于是,母親銀珍心里盤算著以換親的方式同步解決兒女的婚姻問題。正在猶豫不決之際,女兒又在打麥場出了事,生產隊隊長小亮子仗勢欺人,把她給糟蹋了。這可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為了最大程度上降低“損失”,母親迫不得已只能倉促將小素嫁給了一個瘸子……
從上述的表層故事梗概中,我們不難看出,小說《換親》儼然是一出具有鮮明現實批判色彩的“社會悲劇”。僵化、森嚴的等級觀念與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無情地吞噬著花樣的年華,腐蝕著人們純凈的心靈,甚至差點扼殺了青春的生命。作者康志剛在小說中并未點明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但從打麥場、生產隊、成分、貧農、解放腳、粗布褂等這些極富年代感的詞匯中,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推斷出,這是一個發生在“文革”前后的鄉村悲劇。魯迅先生曾說過,悲劇就是將人生中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而書寫“社會悲劇”的目的在于“揭出病痛,以引起療救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講,《換親》中無疑表達著對時代浩劫的控訴,寄托著農村女性對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渴望與呼喚,甚至還隱含著對特殊年代中鄉村權力結構和社會生態的揭露。
然而,《換親》并非是一篇單純以揭示和批判為旨歸的“問題小說”,換句話講,小說的敘事著力點不在于呈現社會問題,而更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情感變化與心靈悸動。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換親》在“社會悲劇”的外殼之中其實還蘊藏著一出“性格悲劇”。作者并沒有全然將母親銀珍塑造成一個重男輕女、鐵石心腸的“扁平人物”,而是抱著“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去極力呈現她在困境中的糾結、猶豫、掙扎與無奈。小說中交代:“成分不好的閨女,倒是不愁嫁人,從前年開始,也就是小素剛滿二十歲時,就有媒人來提親了,卻都被母親銀珍婉言謝絕了。”與其說母親是在待價而沽,試圖以“饑餓營銷”的方式為換親之事做前期“市場調研”,毋寧說她是在祈禱上蒼,期盼并幻想著兒子小海能夠在女兒小素出嫁前順利討到理想的媳婦,進而從根本上避免“換親”事件的發生。可是,造化弄人,事與愿違。母親的“等待計劃”終因一場突如其來的“打麥場事件”而宣告徹底破產,并導致“換親計劃”被迫啟動。如果說,在“等待計劃”中母親更多考慮的是兒子的婚事,那么,“換親”之舉則著實是在為女兒未來著想。試想一下,一個成分不好,又慘遭惡霸強暴的姑娘,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今后的命運將會如何。由此可見,母親銀珍此前的“優柔寡斷”和后來的“孤注一擲”,都是出于一個平凡母親本能的、發自內心的舐犢之情。
小素同樣是一個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姑娘,逆來順受、聽天由命,這也注定了一場“性格悲劇”要在她的人生中上演。母親多次回絕媒人的提親,小素并未像《傷逝》中的子君那樣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而“只恨自己命苦”;當得知自己即將被許配給一個瘸子時,她也只是無助地“抬起頭來望了母親一眼”;到了結婚當天,小素原本有機會像《家》里的鳴鳳一樣“以死明志”,然而最終還是順從了家長的意愿,“坐到了來接親的自行車上”。以五四新文學以來的“啟蒙”和“革命”視角來觀照小素,她顯然是一個被吃人的封建思想和殘忍的鄉村惡俗所戕害的犧牲品,然而,從人物自身的情感邏輯出發,小素向命運的妥協,與家人的和解的過程,恰恰折射出一個柔弱的鄉村少女身上最可貴的品質——善良。從這個意義上講,小素的“性格悲劇”何嘗不是一次破繭成蝶的痛苦蛻變。
因此,我個人更愿意將《換親》視為一篇由人物驅動而非情節驅動的“成長小說”。作者筆下人物的“成長性”是以他們自身的性格缺陷為前提條件的,或者說,正是性格上的“局限性”構筑了人物心靈的“成長史”。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小說通過小素、大娘這一老一少兩個女性形象搭建了一組“鏡像參照系”。
作者分別從這兩個人的視角去觀照對方,從而形成了一種奇妙的“互看”:在小素心里,大娘如同一個為愛堅守的老兵,“一個女人,就這么孤零零地生活幾十年,一直在等待一個男人,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耐力呀”;而在大娘眼中,小素就像一朵被暴風雨摧殘的花蕾,“遭天殺的呀,好好的一個閨女,就這么被糟蹋了”。
這既是兩個孤獨靈魂的惺惺相惜,也是兩代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慰藉。正是在彼此間的“看”與“被看”,“同情”與“被同情”之中,兩個人物逐漸合二為一,構建起人生歷程中的兩個生命階段。作者借助一個“梳頭”意象巧妙地實現了兩者的融合:大娘用深紅色桃木梳子梳理著花白的長發,“就這么從美麗的少婦,梳到了年老。她又想到了她自己。每天早晨,她也是這么梳頭的;可是,以后誰來看自己梳頭呢”。就像小素不解于大娘為何要固執地守寡幾十年一樣,多年后人們也會困惑為何小素最終選擇了聽天由命。畢竟,“有些謎語,要猜一輩子的!”正是由于有了大娘作為鏡像參照,讀者才得以窺探到小素的“隱秘成長”。試想一下,如果小素在結婚之日選擇一了百了,那么對于整個家庭來說無疑意味著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哥哥的婚事、母親的心血將就此化為烏有。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小素的抉擇是逆來順受,是自我放棄,是與命運的和解,毋寧說它是忍辱負重,是痛苦的涅槃,是類宗教意義上的犧牲與普度。
如果你是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質詢者,或許會發現小說《換親》演繹的不僅是一場“社會悲劇”和“性格悲劇”,同時還是一出“命運悲劇”。我們不妨重新找尋一下悲劇生成的根本原因——上文提到,母親選擇“換親”,實屬無奈之舉,直接誘因是“打麥場事件”,而導致“打麥場事件”發生的根源是家庭的“成分問題”,而“成分”的形成源于大伯為國民黨軍隊效力的“黑歷史”,然而,真正吊詭的是,大伯的“黑歷史”僅僅源自一場荒唐的偶然遭遇——“被抓兵”,也就是說,小素及其家人的人生悲劇都源起于命運所開的一個小玩笑。世界的荒誕性以及人作為存在本身的“被拋擲感”由此噴涌而出。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還藏匿了一個精致的存在主義的“內核”。正是由于這個“內核”的存在,小說的文學空間和審美向度得到進一步擴展與豐富。薩特一聲令下:“存在先于本質。”作者筆下的人物瞬間掙脫了性別、身份、地位等諸多社會性定義的束縛,而被還原成了一個個赤裸裸的“存在”本身,這就為讀者角色代入、情感共鳴提供了必要的契機與可能。于是,我們才會在閱讀小說時莫名地感覺到,自己仿佛并非只是一個置身事外的苦難旁觀者,同時也是感同身受的故事“劇中人”,透過特殊年代中小素一家人的悲劇人生,我們也切身地體會到一種普適性的、無差別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劇性命運。
常言道,患難之中見親情。“換親”之難,折射出的恰是隨著現代化進程而日漸式微的傳統親緣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換親》不是在“控訴”,也不是在“啟蒙”,而更像是在為即將消逝的宗族秩序與親情倫理獻上的一曲挽歌。
(趙振杰,中國評論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河北省作家協會,主要從事中國當代作家作品評論及90后文學現象研究。文學評論文章散見于《文藝報》《文學報》《小說月報》《文藝評論》《青年文學》等刊物,著有文學評論集《螢火微光:文學的散點與聚焦》。曾獲《人民文學》首屆“近作短評”金獎、第十三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第十屆河北省文藝評論獎。)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