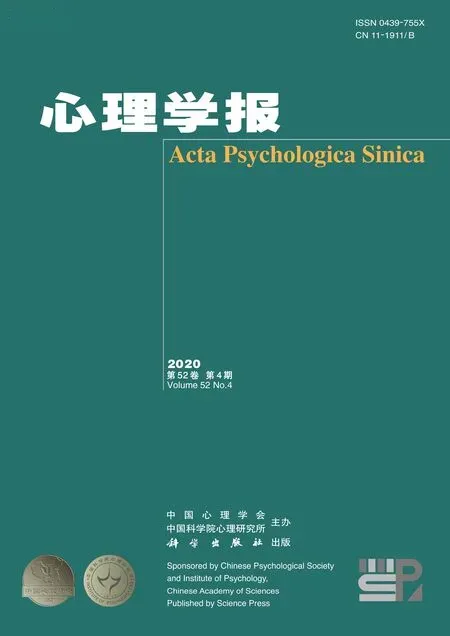概念加工深度影響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
王叢興 馬建平 鄧 玨 楊眾望 葉一舵
(福建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福州 350000)
1 引言
隱喻(metaphor)是指用概念上非常不同的事物來描述另一種事物的語言手法, 其研究存在類比(analogy)、范疇(categorization)、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三種立場或視角(Holyoak &Stamenkovi?, 2018)。概念映射立場的學者將隱喻置于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框架之下(Barsalou, 2008; Gibbs, 2006; Wilson, 2002; 殷融,蘇得權, 葉浩生, 2013), 認為隱喻是習得和理解抽象概念的深層心理機制, 在主觀理解中發揮著重要作用(Lakoff & Johnson, 1999; 王锃, 魯忠義, 2013;殷融, 葉浩生, 2014)。
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認為, 抽象概念系統在隱喻映射結構中屬于目標域(target domain)成分, 其意義需要個體通過身體感知運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來理解和把握(Lakoff & Johnson, 1980), 并認為概念隱喻是單向的, 如我們在語言表述上只會使用具體的概念來表達抽象的概念。但是, Lee和Schwarz (2012)卻認為, 概念隱喻既存在語言現實性, 也存在心理現實性, 概念隱喻理論只能解釋概念隱喻產生過程中的語言現實性, 卻不足以解釋其具體運用所形成的心理現實性。而同樣基于具身視角, Barsalou (1999)提出的知覺符號理論(Perceptual Symbols Theory,PST)卻能對這種心理現實性進行良好的解釋, 該理論認為抽象概念并非零散的、孤立的進行符號表征, 而是在神經上與感知運動區域緊密相連。因此,通過始源域概念和目標域概念不斷的聯合使用, 與之相對應的兩個腦區間也不斷的相互作用, 從而建立了跨域的神經聯結, 隨后它們通過在神經上不斷的共同激活從而形成隱喻聯結的心理現實性。此外,在一個隱喻中, 對于激活和映射的關系, 魯忠義、賈利寧和翟冬雪(2017)認為, 如果個體對身體的感知運動經驗的激活影響了對抽象概念的認知, 說明目標域有一種指向始源域的映射, 反過來便可以說明始源域有一種指向目標域的映射。
具身道德(embodied morality)觀認為道德概念的習得是基于身體經驗的, 身體的自然結構及其感知運動系統塑造了道德認知和行為, 同時道德認知又反過來影響了個體對環境的經驗和感知(陳瀟,江琦, 侯敏, 朱夢音, 2014; 閻書昌, 2011; Yu, Wang,& He, 2016)。已有研究發現, 道德概念與顏色(Sherman & Clore, 2009; 殷融, 葉浩生, 2014)、明暗(Banerjee, Chatterjee, & Sinha, 2012)、潔凈(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 Zhong,Strejcek, & Sivanathan, 2010)、大小(魯忠義, 郭少鵬,蔣澤亮, 2017)等均存在隱喻聯結。有力證明了道德概念與具體的身體感知運動經驗密切相關。
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來自于身體和所處的自然物理環境、文化經驗及其相互作用,并在構建抽象概念意義時具有核心作用(Gibbs,2006; Lakoff & Johnson, 1999)。Williams, Huang 和Bargh (2009)認為個體會在身體對空間感知的基礎上形成身體圖式(body schema), 并通過架構(scaffolding)映射到抽象概念上從而形成隱喻聯結,獲得對抽象概念的意義。空間方位存在不同的圖式結構, 由于人類身體的構造特性和對重力等因素的感知, 對垂直(上下)、水平(左右)、前后空間圖式結構的運用異常普遍(楊繼平, 郭秀梅, 王興超,2017)。目前, 道德概念的方位隱喻研究主要集中在垂直空間隱喻理解上, 其研究發現:道德概念與垂直空間存在隱喻上的聯結, 并且在不同意識程度的實驗范式下還會表現出不同的特性(Hill & Lapsley,2009; 賈寧, 蔣高芳, 2016; 魯忠義, 賈利寧 等,2017; Meier, Sellbom, & Wygant, 2007; 王锃, 魯忠義, 2013)。但是, 對水平方位在道德隱喻表征中的作用卻研究較少。
在西方文化中, 左右在隱喻構建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研究認為利手與情感效價(affective valence)存在密切的關聯, 左右手使用的不對稱性對個體表征信息的偏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成人會更偏好利手空間方位的刺激物(Casasanto, 2009), 兒童更喜歡將心愛的玩具放在利手空間方位處, 而將不喜歡的玩具放在利手相反的空間方位處(Casasanto,2011; Casasanto & Henetz, 2012)。另一些研究則表明語言習慣和文化環境塑造了水平方位隱喻表征,如個體對政治黨派(如民主黨和共和黨)人物圖片的加工會導致其注意力向特定的視野區域(左、右)偏移, 這說明了抽象概念的加工會引起相應水平方位表征的激活(Mills, Smith, Hibbing, & Dodd, 2015)。此外, Mills, Boychuk, Chasteen和Pratt (2017)等使用語言分類任務(英語/荷蘭語), 發現被試的注意力在水平方位上的偏移易化了隨后出現的相容條件詞匯判斷速度, 表明水平方位也能影響個體對相關詞匯的加工。這可能是由于美國人經常使用左、右來對相應概念進行描述和概括, 并在反復使用過程中產生了特定的隱喻聯結。
可見, 西方的研究發現水平方位隱喻的來源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身體感知運動經驗, 二是文化因素和語言習慣。Casasanto (2009)的整合隱喻結構觀(Integrated 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認為, 個體的感知運動經驗和語言文化習慣在概念隱喻中同時發揮著作用。而英語中更有“right”這種既表達“積極”又表達“右”的詞匯, 并可能在其二元論的文化中又發展出“消極”與左的表達習慣。在漢語環境中,我們雖與其具有相同的利手身體特異性, 在生命早期的感知運動經驗上體驗相似, 但文化傳統和語言習慣上卻大相徑庭。
在漢語環境中, 楊繼平等(2017)在對道德詞和左右方位隱喻的研究中發現, 被試對水平方位左側出現的不道德漢語詞匯的反應速度顯著的快于水平方位右側。對此, 楊繼平等(2017)認為:在傳統文化中, “無出其右”常用來指代個體道德高尚, “旁門左道”等指代個體品行拙劣, 因此道德與不道德應該分別與空間右、左存在隱喻聯結。但事實上關于左、右的效價指向在傳統中并非一成不變, 在不同的朝代和歷史背景存在差異。《老子》記載:“吉事尚左, 兇事尚右”, 說明在春秋時期人們有一種左好右壞的價值觀, 而在明朝莊嚴場所中, 禮儀要求座次及排序都須以左為尊, 因此在漢語文化中左右效價的關系具有二重性(王希杰, 2004)。此外, 現代人的語法規則和空間表征與傳統相比變化巨大,書寫規范和禮儀要求等均不可同日而語, 其傳承和因果關系值得商榷。在漢語的書寫和口語表達中,遵循“言有序”的語言規則, 經常先表達積極概念,后表達消極概念, 如:“善惡”、“好壞”、“對錯”等等, 這種語言表達的順序性, 總是積極的在左、消極在右, 是否對水平方位構建道德概念產生一定的影響呢?
綜上, 雖然西方的理論觀點與實證研究普遍認為道德與右、不道德與左存在隱喻聯結, 但這是基于感知經驗和語言文化習慣的一致性。中外文化畢竟存在差異, 漢語環境下其研究又是非常薄弱的。如只有楊繼平等(2017)的一項研究對其進行了探究,使用的方法較為單一, 其實驗結果只得到了不道德與左的隱喻聯結, 并不足以支持“道德與右、不道德與左存在隱喻聯結”這個結論, 另外,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漢語“言有序”的書寫規則感受的異常普遍, 這與利手身體特異性的感知運動經驗是相悖的。基于此, 我們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之間是否具有隱喻聯結?如果有,又是怎樣的?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隱喻過程中始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映射是雙向的, 這符合知覺符號理論對概念隱喻心理現實性的解釋(He, Chen, Zhang, & Li,2015; Lee & Schwarz, 2012)。在漢語環境中, 道德概念與垂直空間表現出了映射的雙向性, 個體加工道德概念可以影響對垂直空間的感知, 而對垂直空間方位的激活能夠影響個體對道德概念的認知(賈寧, 蔣高芳, 2016; 魯忠義, 賈利寧 等, 2017)。但這種雙向性并不總是能被探測出來, 如魯忠義和賈利寧等(2017)的研究就發現, 在迫選任務下對道德詞匯的加工會影響隨后的垂直空間方位希臘字母的偏好, 而在分離式空間Stroop范式中, 并沒有發現道德詞匯對垂直位置的字母判斷產生影響, 并認為隱喻映射是不平衡的, 受到實驗范式意識性的影響。
事實上空間 Stroop范式是一種條件自動化范式(Bargh & Tota, 1988), 而不是絕對的無意識(魯忠義, 郭少鵬 等, 2017), 被試在實驗過程中同樣對道德詞匯進行了有意識的加工, 實驗范式所要求的意識性并非“全”或“無”的關系。首先, Lakoff和Johnson (1999)認為, 基于具身認知的概念隱喻是無意識的, 個體是通過感知運動經驗和文化因素的無意識影響, 借助隱喻對復雜概念進行把握和理解,使用“意識”和“無意識”對概念隱喻進行表述并不恰當。其次, 對意識與否界定模糊, 目前學界對于如何區別意識與無意識尚存在巨大的爭議, 在操作中缺乏強有力的依據。因此, 道德概念與垂直空間的隱喻聯結在兩種范式中所表現出的不同, 更有可能是個體對概念的加工深度造成的。加工水平理論認為, 深度的編碼加工會產生更強的刺激痕跡(Craik& Lockhart, 1972), 加工深度是對概念的神經激活程度而言, 在信息編碼中, 個體的隱喻聯結是內隱的、無意識的, 但隨著始源域和目標域的加工深度加強, 腦區神經得到大范圍的激活, 這種隱喻聯結便可以體現出來。已有研究發現, 情緒概念的加工深度, 決定了其與情緒面孔之間隱喻聯結的強度。在較淺的加工層面, 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單向的, 而在較深的加工層面, 兩者的關系是雙向的(劉文娟,沈曼瓊, 李瑩, 王瑞明, 2016), 這為我們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意義。
以上研究表明, 概念加工深度影響了道德概念與垂直空間的隱喻聯結, 在深概念加工深度下, 道德概念與垂直空間之間隱喻聯結較強, 因此映射是雙向的, 而在較低的概念加工深度下隱喻聯結較弱,則只能探測出一種方向的映射。那么這是否適用于水平方位呢?在這里我們提出第二個問題:不同概念加工深度是否會影響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另外, Huang, Tse和Xie (2018)的研究發現, 在Stroop任務中, 對明暗-效價方向判斷時能夠發現隱喻一致性效應, 而在效價-明暗方向判斷時卻未發現這種效應(實驗 1), 但是在加入 go/no go操作的Stroop范式中卻發現了該效應(實驗3)。而在啟動范式中, 在兩個方向的判斷中均發現了隱喻一致性效應(實驗 2), 因為在這兩個實驗中非判斷域信息都被預先激活, 并據此提出了激活假設(activation hypothesis)。該假設認為具體概念的加工要快于抽象概念的加工, 并且隱喻一致性效應的產生取決于具體(或抽象)信息在對抽象(具體)進行判斷之前是否被預先激活。但是, Huang等(2018)的研究只是說明了非判斷域的激活深度在效價概念明暗隱喻聯結中的作用, 卻并未探討判斷域概念加工深度對隱喻一致性效應的影響。那么, 是否隱喻聯結的產生不僅取決于非判斷域的概念有無被預激活, 還取決于判斷域概念一定深度的加工呢?因此, 我們將在接下來對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的實驗中對此進行驗證, 以求進一步豐富激活假設, 這是本研究所要說明的第三個問題。
為此, 我們首先進行了實驗 1, 采用了王锃和魯忠義(2013)的迫選任務范式, 該實驗要求被試在在思維層面對道德詞匯進行空間迫選, 在充足的時間內對詞匯的語義信息和空間的知覺信息進行了加工, 實驗 1主要是一種探索性實驗, 為后續的系列實驗提供一定的參考。隨后設計了實驗2、實驗3和實驗4, 均采用楊繼平等(2017)的空間Stroop范式, 以往的空間Stroop范式中都是將道德和不道德詞匯水平呈現, 這極有可能造成被試從左到右的閱讀效應, 從而影響實驗結果, 因此本研究詞匯為豎直呈現。實驗2在空間Stroop任務中添加了任務要求, 要求被試對目標詞匯進行效價判斷前, 先勻速穩定的將其出聲閱讀, 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其概念加工深度。閱讀的聯結注意模型(Seidenberg,2011)認為對詞匯的加工包括最底層的詞形加工,以及加工深度更深的語義加工和語音加工, 故在語義加工的基礎上加入語音加工能夠進一步加深對目標概念的加工深度, 因此實驗2是一種較深加工深度的實驗。而實驗4將道德效價判斷改為真假詞判斷, 真假詞只對目標詞匯的字形知覺特征進行了一定的加工, 對詞匯的語義、語音加工是微弱和不充分的(劉文娟 等, 2016; Seidenberg, 2011), 因此是一種淺概念加工深度的任務。而實驗3采用標準的空間Stroop任務, 要求被試對出現在水平方位的道德詞匯進行效價判斷, 這涉及一定的語義加工,但其概念加工深度要淺于實驗2, 且深于實驗4, 并將其定位為中等概念加工深度的實驗。
此外, 如果實驗2、3、4發現道德概念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受概念加工深度的影響, 并且在實驗4中未發現隱喻聯結。我們將進行實驗5和實驗6進行補充驗證, Huang等(2018)認為, 啟動范式對非判斷域的激活水平強于Stroop范式。因此, 實驗5參照了Mills等(2017)的空間啟動范式, 在實驗4的基礎上預先激活了空間知覺信息, 并通過記錄在知覺空間啟動下真假詞判斷任務的表現, 探究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理解中目標域向始源域的映射情況。實驗6參照了魯忠義等(2017)的分離式空間Stroop范式, 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啟動詞匯, 通過記錄在詞匯啟動下字母分類任務的表現, 探究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理解中始源域向目標域的映射情況, 在該實驗中, 如果對道德詞匯的字形加工能夠激活相應的水平方位表征, 那么在真假詞判斷后, 就會易化對相容水平方位的字母(p、q)判斷速度。
2 實驗1:迫選任務中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2.1 目的
探究在意識思維中, 個體理解道德抽象概念時是否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若存在這種隱喻聯結, 那么在迫選任務中, 要求被試將道德詞或不道德詞放在水平方位的左側或者右側時, 被試會顯現出一定的偏好。
2.2 方法
2.2.1被試
本實驗共有33名大學生(含研究生)參與, 其中男生11名, 女生22名, 平均年齡為24.25歲 (SD =2.59)。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2.2.2實驗材料
首先從道德概念相關文獻中初選道德詞(如勤勞、善良)、不道德(如惡毒、欺騙)雙字詞和中性詞(如水杯、儀器)各 30個。35名在校大學生或研究生對這些材料進行等級為1(非常不道德) ~ 9(非常道德)道德效價評定, 按照道德效價得分從中挑選出道德詞和不道德詞各 20個, 其余的作為實驗的練習材料。道德詞的得分(M = 7.31)與中值5進行單樣本t檢驗, 結果差異顯著:t(19) = 18.99, p <0.001, 說明所選道德詞匯具有明顯的道德效價。不道德詞的得分(M = 2.20)與中值5進行單樣本t檢驗,結果差異顯著, t(19) = -28.14, p < 0.001, 說明所選不道德詞匯具有明顯的不道德效價。根據《現代漢語研究語料庫查詢系統》進行詞頻分析, 結果顯示,道德詞(M = 0.0103)、不道德詞(M = 0.0115)在詞頻差異上不顯著, t(38) = 0.64, p > 0.05。此外還對詞匯的筆畫進行了評定, 道德詞的筆畫平均數 M =17.50 (SD = 4.63), 不道德詞的筆畫平均數 M =19.05 (SD = 3.53), 對比結果表明t(38) = -1.19, p >0.05, 因此道德詞和不道德詞的筆畫數沒有顯著差異, 說明實驗材料符合實驗要求。
2.2.3實驗設計與程序
實驗采用 2(詞匯類型:道德詞、不道德詞) ×2(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被試內實驗設計。因變量是被試把道德詞或者不道德詞分別放在火柴人左側或者右側的個數。
本研究采用紙筆測驗進行。實驗首先給被試呈現一副圖畫(如圖 1), 圖畫中心呈現一個火柴人,火柴人的左右手兩側各呈現一個帶有指向箭頭的圓框, 并要求被試將出現的詞匯按照個人偏好將其放入左手邊或者右手邊的圓框, 放入左手側圓框則選擇A選項, 放入右手側圓框則選擇B選項, 并且A和B選項分別在每個詞下同行左右呈現。

圖1 紙筆測驗圖
2.3 實驗結果
共有33名被試參加了實驗1, 所有被試均符合實驗要求。實驗數據使用SPSS 22.0進行統計分析,描述分析見表1。
對被試將道德屬性詞匯放在左右水平方位的個數進行卡方獨立性檢驗, 結果顯示:水平方位和道德類型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χ2(1) = 140.12, p <0.001, η2= 0.23。之后, 我們對交互作用作進一步的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在道德詞水平上, 水平方位具有顯著的簡單效應, χ2(1) = 77.39, p < 0.001, η2=0.34, 說明當被試看到道德詞時, 選擇將其放置于空間左側的個數顯著多余右側的個數。在不道德詞水平上, 水平方位同樣具有顯著的簡單效應, χ2(1) =63.06, p < 0.001, η2= 0.31, 說明當被試在對不道德詞進行迫選時, 選擇將其放置于空間右側的個數顯著多于左側的個數。

表1 迫選任務中將詞匯放置于左右水平方位的個數
2.4 討論
實驗1的結果表明, 當要求被試對看到的道德詞或者不道德詞進行空間偏好迫選時, 被試傾向于將道德詞放置于空間左側, 而將不道德詞放置于空間右側。這個結果雖然證明了在深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 但聯結情況卻與前人的結果并不一致, 如楊繼平等(2017)的研究顯示在Stroop范式下, 不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右側存在隱喻聯結。但我們不能就此推翻楊繼平等(2017)的實驗結果, 因為紙筆測驗對實驗的精度控制有限, 受諸多無關因素影響較強, 需要更精密的實驗來進行證明。為此, 實驗2、3、4擬采用Stroop范式, 從三種不同的加工深度梯度進一步來探究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聯結情況, 及其受概念加工深度的影響。
3 實驗2:較深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3.1 目的
探究在統一使用Stroop范式時, 較深概念加工深度條件下, 個體理解道德抽象概念時是否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若在此等條件下,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具有隱喻聯結, 那么在要求被試對出現的目標詞進行道德詞性判斷, 如道德詞或不道德詞出現在相應的空間方位(左側、右側)時就會出現隱喻一致性效應, 導致反應速度變快。
3.2 方法
3.2.1被試
本實驗共有28名大學生(含研究生)參與, 其中男生13名, 女生15名, 平均年齡為24.00歲 (SD =1.19)。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3.2.2實驗材料
道德詞和不道德詞材料同實驗1。
3.2.3實驗設計與程序
實驗采用楊繼平等(2017)的空間 Stroop范式,并加入了閱讀詞匯的任務要求。實驗在60 Hz刷新率的 14英寸 IPS電腦顯示器(1980*1080)上進行,實驗中屏幕背景為白色, 程序采用 E-prime 2.0軟件編制。在實驗中被試端坐在距屏幕55 cm處, 實驗開始前向被試呈現指導語, 先在屏幕正中間呈現一個 800 ms的注視點“+”, 然后會在水平方位左側(距屏幕左側邊沿 25%處)或者右側(距屏幕左側邊沿75%處)隨機出現目標詞匯, 詞匯為黑色30號宋體, 豎直呈現。要求被試在看到目標詞出現時,先穩定勻速的將其讀出, 隨后對其進行道德詞性判斷, 道德詞出現時按“F”鍵、不道德詞出現時按“J”鍵, 按鍵會在被試間進行平衡。詞匯不設置限定呈現時間, 每個試次結束后顯示 500 ms的空屏。40個實驗詞匯分別在水平方位的左側和右側各呈現一遍, 因此正式實驗中包含了80個試次。
在正式實驗開始前會先進行至少8個試次的練習, 練習詞匯材料來自評定后沒有被選入正式實驗的材料。每個練習試次結束后會出現1500 ms的反饋, 反饋內容包括詞匯判斷的正誤情況和反應時,而正式實驗中并沒有反饋。在練習結束后, 被試如果清楚實驗任務和操作則按“Q”可以進入正式實驗,如果不清楚則必須按“P”鍵返回重新進行練習。
3.3 實驗結果
共有28名被試參加了實驗2。為確保統計處理結果的有效性, 刪除3個被試的實驗數據(2人違反實驗程序, 1人詞匯判斷中正確率低于75%), 并對25名被試數據進行一定的篩選:刪除被試在詞匯判斷中的錯誤反應數據, 以及各被試在每個項目中反應時超過平均數2.5個標準差的極端數據, 共86個(總數據量的4.3%)。實驗結果在SPSS 22.0錄入并處理, 描述分析見表2。

表2 詞性判斷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差
對詞匯判斷的反應時進行2×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第一個是以被試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 F1,第二個是以項目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F2。結果顯示:詞匯類型(即道德詞、不道德詞)的主效應顯著,F1(1, 24) = 34.43, p < 0.001, ηp2= 0.59, F2(1, 76) =24.78, p < 0.001, ηp2= 0.25, 表明被試對詞匯判斷速度, 道德詞要快于不道德詞(反應時分別為, M =866.10; M = 930.40); 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主效應不顯著, F1(1, 24) = 2.60, p = 0.120, F2(1, 76) =1.33, p = 0.252; 詞匯類型×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在被試為對象分析中顯著, F1(1, 24) = 8.53, p = 0.007,ηp2= 0.26, 而在項目為對象的分析中不顯著 F2(1,76) = 2.55, p = 0.114。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 在道德詞匯條件下, 水平方位簡單效應顯著, F1(1,24) = -34.16, p = 0.003, ηp2= 0.31; 左側方位的道德詞反應時要顯著低于右側方位的反應時(反應時分別為, M左= 846.37; M右= 880.53); 在不道德詞匯條件下, 水平方位的簡單效應不顯著, F1(1, 24)= 1.11, p = 0.304, 左側不道德詞的反應時與右側無顯著差異(反應時分別為, M左= 933.44; M右=922.30)。
3.4 討論
實驗2采用了添加了任務要求的空間Stroop范式, 以提高其概念加工深度。在水平方位隨機呈現目標詞匯, 要求被試對出現的詞匯進行穩定勻速的出聲閱讀, 隨后進行道德判斷, 同時不限定反應時間。結果表明, 被試對道德詞的判斷速度明顯快于不道德詞, 與以往的研究相同(殷融, 葉浩生, 2014;楊繼平 等, 2017)。對此, 楊繼平等(2017)認為這是一種對不道德的注意偏向, 個體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對威脅自身的消極事物的注意優勢分配。也有研究者認為, 這是因為對道德概念的體驗與人的動機趨避系統相關, 消極刺激激發了回避動機, 而積極刺激激發了趨向動機(劉文娟 等, 2016)。更重要的是, 我們發現了詞匯類型和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這表明在較深的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此外, 被試對左側出現的道德詞反應速度顯著快于右側, 即在道德詞上發現了隱喻一致性效應; 而在不道德詞上, 卻沒有發現這種隱喻一致性效應, 這可能是不道德詞的注意偏向或回避動機, 在一定程度上掩蔽掉了其隱喻一致性效應, 導致不道德詞出現在左側和右側的反應速度無明顯差異。
4 實驗3:中等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4.1 目的
通過去除Stroop范式的任務要求, 從而降低概念加工深度。在此等概念加工深度中, 個體在構建道德抽象概念時是否借助了水平方位的表征, 即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是否存在隱喻聯結?因此, 實驗3同樣采用空間Stroop范式, 探究此等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情況。
4.2 方法
4.2.1被試
本實驗共有30名大學生(含研究生)參與, 其中男生15名、女生15名。平均年齡24.33歲 (SD =2.52)歲。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4.2.2實驗材料
實驗所用道德和不道德材料同實驗1。
4.2.3實驗設計和程序
實驗設計與程序同實驗 2, 但不要求被試在詞匯出現時進行出聲閱讀, 并且詞匯限制3000 ms的最長反應時間。
4.3 實驗結果
共有30名被試參加了實驗3。為確保統計處理結果的有效性, 刪除2個被試的實驗數據(1人違反實驗程序, 1人詞匯判斷中正確率低于75%), 并對28名被試數據進行一定的篩選:共刪除數據 195個(總數據量的8.71%),刪除方法同實驗2。實驗結果在SPSS 22.0錄入并處理, 描述分析見表3。

表3 詞性判斷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差
對詞匯判斷的反應時進行2×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第一個是以被試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 F1,第二個是以項目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F2。結果顯示:詞匯類型(即道德詞、不道德詞)的主效應顯著,F1(1, 27) = 27.16, p < 0.001, ηp2= 0.50, F2(1, 76) =16.93, p < 0.001, ηp2= 0.18, 表明被試對詞匯判斷速度, 道德詞要快于不道德詞(反應時分別為, M =764.14; M = 802.90); 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主效應不顯著, F1(1, 27) < 1, F2(1, 76) < 1; 詞匯類型×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顯著, F1(1, 27) = 4.76, p = 0.038,ηp2= 0.15, F2(1, 76) = 5.46, p = 0.022, ηp2= 0.07。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 在道德詞匯條件下, 水平方位在被試分析上簡單效應邊緣顯著, 在項目分析上不顯著, F1(1, 27) = -22.58, p = 0.074, ηp2= 0.11, F2(1,76) = 1.95, p = 0.167; 左側方位的反應時要明顯低于右側方位的反應時(反應時分別為, M = 752.85;M = 775.43); 在不道德詞匯條件下, 水平方位的簡單效應不顯著, F1(1, 24) = 14.83, p = 0.178, F2(1, 76)= 2.60, p = 0.111; 道德詞的反應時與不道德詞的反應時無顯著差異(反應時分別為, M = 810.31; M =795.48)。
4.4 討論
實驗3采用標準的Stroop范式, 在水平方位隨機呈現目標詞匯, 并要求被試對出現的詞匯進行道德判斷。結果表明, 被試對道德詞進行判斷的速度明顯快于不道德詞, 這與實驗1的結果一致。更重要的是, 我們發現了詞匯類型和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 這表明在中等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此外, 被試對左側道德詞的反應速度顯著快于不道德詞, 產生了隱喻一致性效應;而對不道德詞卻并未發現左側反應時和右側的顯著差異, 這與實驗2的結果一致。
5 實驗4:較淺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5.1 目的
通過真假詞判斷任務, 探討在較淺的概念加工深度下,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是否存在隱喻聯結。如果存在這種隱喻聯結, 那么在要求被試對出現的目標詞進行真假詞判斷, 如道德詞或不道德詞出現在相應的空間方位(左側、右側)時就會出現隱喻一致性效應, 導致反應速度變快。
5.2 方法
5.2.1被試
本實驗共有28名大學生(含研究生)參與, 其中男生11名, 女生17名, 平均年齡為22.50歲 (SD =2.49)。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5.2.2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包括40個真詞(道德詞與不道德詞各20個)和40個假詞, 真詞材料同實驗1。假詞材料從相關的文獻附錄中挑選, 并經過 32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對其進行評定, 按照評定等級為1~9 (1代表完全是假詞, 9代表完全是真詞)進行評分。40個假詞的平均得分M = 2.25, 隨后將其得分與中值5進行單樣本 t檢驗, 結果差異顯著, t(39) = -14.183,p < 0.001, 因此材料符合實驗要求。此外, 真詞的筆畫平均數M = 17.00 (SD = 2.78), 假詞的筆畫平均數M = 18.28 (SD = 4.14), 對比結果表明t(78) =-1.62, p > 0.05, 因此真詞和假詞的筆畫數不存在顯著差異, 滿足實驗要求。
5.2.3實驗設計和程序
實驗采用3(詞匯類型:道德詞、不道德詞、假詞) × 2(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被試內設計。要求被試對出現的詞匯做真假詞判斷, 其余實驗程序要求同實驗2。
5.3 實驗結果
共有28名被試參加了實驗3。為確保統計處理結果的有效性, 所有被試在真假詞判斷中正確率均高于75%。并對28名被試數據進行一定的篩選:共刪除數據 246個(總數據量的 5.49%), 刪除方法同實驗2。實驗結果在SPSS 22.0錄入并處理, 描述分析見表4。

表4 詞匯分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差
對詞匯判斷的反應時進行3×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第一個是以被試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 F1,第二個是以項目為隨機變量的方差分析F2。結果顯示:詞匯類型的主效應顯著, F1(2, 26) = 13.60, p <0.001, ηp2= 0.34, F2(2, 154) = 18.22, p < 0.001, ηp2=0.19, 表明被試對詞匯判斷速度, 道德詞要快于不道德詞和假詞(反應時分別為, M = 886.44; M =921.35; M = 939.57); 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主效應不顯著, F1(1, 27) = 1.87, p = 0.18, F2(1, 154) =2.30, p = 0.13; 詞匯類型×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1(1, 27) < 1, F2(1, 76) < 1。
5.4 討論
實驗4采用結合真假詞判斷的Stroop范式, 在水平方位隨機呈現目標詞匯, 并要求被試對出現的詞匯進行真假詞判斷。結果表明, 被試對道德詞進行詞類判斷的速度明顯快于不道德詞, 與實驗2和實驗3一致, 即存在對不道德詞的注意偏差或回避動機。但卻并沒有發現詞匯類型和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 也就是說道德詞或不道德詞出現在水平方位相容的位置時, 并沒有影響詞類判斷的反應時, 但先前的實驗發現道德概念和水平方位是存在隱喻聯結的。因此, 這表明在較低的概念加工深度的Stroop范式中, 無法探測到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而根據激活假設, 實驗 4和實驗 2、3具有相同的空間方位條件, 因此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不僅取決于非判斷域概念的預激活深度,還取決于目標概念的加工深度。
6 實驗5:較淺概念加工深度空間位置啟動條件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6.1 目的
實驗5在實驗4的基礎上, 加強了空間方位的預激活深度, 采用啟動范式, 探討在較淺概念加工深度條件目標域指向始源域的映射方向上, 水平方位與道德概念是否存在隱喻聯結。如果存在這種映射方向的隱喻聯結, 那么啟動左右水平方位就能影響隨后對道德屬性詞匯的判斷情況。
6.2 方法
6.2.1被試
32名在校大學生(含研究生)參加了此次實驗,其中男生17名、女生15名, 平均年齡20.97歲 (SD= 2.57)。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6.2.2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包括40個真詞(道德詞與不道德詞各20個)和40個假詞, 真詞材料同實驗1。假詞材料從相關的文獻附錄中挑選, 并經過 42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對其進行評定, 按照評定等級為1~9(1代表完全是假詞, 9代表完全是真詞)進行評分。44個假詞的平均得分M = 1.69, 隨后將其得分與中值5進行單樣本 t檢驗, 結果差異顯著, t(43) = -170.14,p < 0.001, 因此材料符合實驗要求。從中選取40個假詞作為正式實驗材料, 另外4個假詞作為練習階段的材料。
6.2.3實驗設計和程序
實驗設計和因變量指標同實驗4。實驗程序參照了Mills等(2017)的啟動范式, 在60 Hz刷新率的19英寸IPS電腦顯示器(1280*1024)上進行, 在每個任務前都會在屏幕水平方位的左側(25%處)或者右側(75%處)隨機出現視覺線索 750 ms, 要求被試在該線索出現時將視線偏移到線索方向, 視線偏轉夾角為 9.54°, 隨后線索消失并在該線索處出現一個詞匯。其余實驗程序同實驗4。
在正式實驗開始之前會要求被試先進行 16個試次的練習, 練習標準與先前實驗一致。
6.3 實驗結果
共有32名被試參加了實驗3。為確保統計處理結果的有效性, 所有被試在真假詞判斷中正確率均高于75%。并對32名被試數據進行一定的篩選:刪除詞匯判斷中極端數據共 216個(總數據量的4.22%), 刪除方法如實驗2。實驗結果在SPSS 22.0錄入并處理, 描述分析見表5。

表5 詞匯分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差
對詞匯判斷的反應時進行3×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 詞匯類型主效應顯著, F1(2, 30) =36.11, p < 0.001, ηp2= 0.54, F2(2, 154) = 60.76, p <0.001, ηp2= 0.44。被試對詞匯判斷速度, 道德詞要快于不道德詞和假詞(反應時分別為, M = 621.97; M =640.71; M = 681.45); 水平方位主效應不顯著, F1(1,31) = 2.80, p = 0.104, F2(1, 154) = 2.09, p = 0.150(反應時分別為, M = 644.74; M = 651.35)。詞匯類型×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1(2, 30) = 1.37, p =0.261, F2(2, 154) < 1。
6.4 討論
實驗5在實驗4的基礎上, 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 先在屏幕上啟動空間線索, 隨后在同樣位置呈現詞匯, 要求被試判斷該詞匯的真假。實驗結果發現, 被試對道德詞匯反應速度更快, 這與先前的實驗結果一致。但是詞匯類型與水平方位并不存在交互作用, 也就是說加強水平方位預激活深度并沒有影響隨后的道德概念的加工速度, 因此并沒有發現目標域向始源域的映射。此外, 在真假詞判斷任務中并沒有發現道德概念水平方位的隱喻一致性效應, 表明在非判斷域得到預激活, 而判斷域概念的加工深度太淺時, 未能發現其隱喻聯結。接下來,我們還要探討在另一個方向上的隱喻映射情況, 采用同樣的真假詞判斷任務來對詞匯進行概念加工。如果該方向上同樣不存在隱喻映射, 那么則可以說明真假詞判斷任務對詞匯概念加工深度較淺, 無法達到隱喻聯結所需的激活程度。
7 實驗6:較淺概念加工深度詞匯啟動條件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7.1 目的
采用啟動范式, 通過真假詞判斷結合字母判斷的組合任務, 探討在淺概念加工深度始源域指向目標域的映射方向上, 水平方位與道德概念是否存在隱喻聯結。如果該方向的隱喻映射是存在的, 那么啟動道德屬性詞匯就會影響隨后水平方位上的字母判斷速度。
7.2 方法
7.2.1被試
28名在校大學生(含研究生)參加了此次實驗,其中男生15名, 女生13名, 平均年齡20.71歲 (SD= 3.13)。實驗被試均為右利手, 無閱讀困難,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7.2.2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同實驗5。
7.2.3實驗設計和程序
實驗設計和因變量指標同實驗5。實驗范式參照了魯忠義(2017)的分離式空間Stroop范式, 并結合了真假詞判斷任務。實驗在60 Hz刷新率的19英寸 IPS電腦顯示器(1280*1024)上進行, 實驗中屏幕背景為白色, 程序由E-prime 2.0軟件編寫。在實驗中被試端坐在距屏幕55 cm處, 并全程通過儀器固定下巴和額頭。實驗開始前向被試呈現指導語, 在每個試次中, 先在屏幕正中間的位置呈現一個500 ms的注視點“+”。隨后在屏幕中間豎直出現一個詞匯, 詞匯為 30號黑色宋體。要求被試在看到詞匯時盡可能快而準確的判斷所出現的詞匯是真詞還是假詞, 真詞按“W”, 假詞按“O” (按鍵在被試間進行了平衡), 詞匯最長顯示時間為3000 ms。按鍵之后詞匯消失, 然后會隨機在水平方位的左側(25%處)或者右側(75%處)出現一個字母(字母是“p”或者“q”), 被 試視角偏移夾角為9.54°。要求被試在該字母出現時進行判斷, 是“p”則按“P”鍵, 是“q”則按“Q”鍵(字母在項目間進行了平衡), 字母最長顯示時間為3000 ms, 按鍵反應后字母消失并呈現1000 ms的空屏。80個詞匯分別在屏幕水平方位兩側各呈現一遍, 因此正式實驗包含160個試次。
在正式實驗開始之前會要求被試先進行 16個試次的練習, 練習標準同先前實驗一致。
7.3 實驗結果
共有28名被試參加了實驗4。為確保統計處理結果的有效性, 所有被試在真假詞判斷和任務字母分類任務中正確率均高于75%。并對28名被試數據進行一定的篩選:刪除在詞匯判斷和字母判斷中的極端數據共 287個(總數據量的 6.41%), 刪除依據同實驗2。實驗結果在SPSS 22.0錄入并處理, 描述分析見表6。

表6 字母分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差
對字母判斷的反應時進行3×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 詞匯類型(即道德詞、不道德詞、假詞)的主效應不顯著, F1(2, 26) = 1.75, p = 0.184,F2(2, 154) = 1.12, p = 0.329。表明被試對詞匯的反應并沒有影響隨后的字母判斷(反應時分別為, M =644.55; M = 634.88; M = 647.97); 水平方位(左側、右側)的主效應顯著, F1(1, 27) = 13.59, p = 0.001, ηp2= 0.34, F2(1, 154) = 7.70, p = 0.006, ηp2= 0.048 (反應時分別為, M = 652.54; M = 631.25)。詞匯類型×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1(1, 27) < 1, F2(1, 154)< 1。
7.4 討論
實驗6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啟動道德屬性詞匯,隨后呈現字母并要求被試對其進行分類判斷, 結果并沒有發現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交互作用, 即并沒有發現道德概念影響水平方位上的字母判斷。說明在較淺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中未發現始源域向目標域的映射。這說明即使是采用啟動范式, 也需要對目標域和始源域進行一定深度的激活, 才能發現相應的隱喻聯結。
8 總討論
本研究通過6個實驗從不同角度探究了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的聯結和映射情況, 實驗1發現個體更喜歡將道德詞置于左側空間方位, 而將不道德詞置于右側空間方位, 即在思維層面存在“道德與左”、“不道德與右”的隱喻聯結。實驗2、實驗3和實驗4采用Stroop范式發現, 在較高和中等概念加工深度,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 而在較低的概念深度下未發現隱喻聯結。實驗5和實驗 6進一步采用啟動范式在較低概念加工深度下,未發現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8.1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聯結的心理現實性
實驗1采用紙筆測驗, 要求被試對給出的詞匯進行左右水平方位的迫選, 結果發現被試對道德詞進行選擇時, 將其放置于空間左側的個數顯著多于空間右側的個數, 對不道德詞進行選擇時, 被試將詞匯放置于空間的右側的個數也顯著多于放置于空間左側的個數。由此我們可以發現, 被試在迫選中更偏向于將道德與左、不道德與右聯結起來, 因此在思維中存在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但實驗結果與前人的研究并不一致。如楊繼平等(2017)采用空間 Stroop范式就發現, 存在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理解的心理現實性, 但只體現在不道德層面, 且不道德與左聯結, 在道德層面并不明顯。實驗1不能得到與之一致的隱喻聯結, 可能與選取的實驗本身有關, 因為紙筆測驗相較于實驗室實驗, 在變量控制上并不嚴密, 可能受到諸多無關因素的影響, 在實施過程中精密度和嚴謹性都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實驗2、3和4都采用了與楊繼平等(2017)相同的空間Stroop范式, 探究在較深、中等、較淺概念加工深度情況下,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的心理現實性。實驗2和實驗3的結果均出現了詞匯類型和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 這表明在較深和中等概念加工深度下,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的心理現實性, 表現為道德詞在空間左側的判斷速度顯著快于空間右側, 這部分支持了實驗1, 但與楊繼平等(2017)的研究結果相反。
此外, 結果還顯示了這種隱喻聯結只體現在道德詞層面, 即發現了道德與左的隱喻一致性效應;而在不道德詞上, 實驗2和實驗3的結果均顯示不道德詞在空間左側的反應時與空間右側無顯著差異, 但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在空間右側不存在不道德與右的隱喻聯結, 因為實驗2和實驗3均顯示詞匯類型和水平方位顯著的交互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對不道德詞匯進行判斷時, 其注意偏差或回避動機與不道德與右的隱喻一致性效應同時發生了作用,從而對其隱喻聯結產生了干擾。還有可能是不道德與右的隱喻聯結比較微弱, 需要更大的被試量才能得到顯示, 如從實驗2和實驗3的結果來看, 被試雖然對不道德詞在空間左側和右側的判斷速度在統計學意義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但空間右側不道德詞的反應速度均快于空間左側(實驗 2反應時分別為, M = 933.44; M = 922.30; 實驗3反應時分別為,M = 810.31; M = 795.48)。因此, 不道德可能與右存在隱喻聯結, 但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
因此本研究通過實驗1、實驗2和實驗3發現存在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理解的心理現實性, 表現為左表征了道德、右表征不道德。但為什么本研究得出的結果與以往的結論相反呢?我們認為主要存在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 楊繼平等(2017)認為被試從左到右的閱讀習慣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的實驗造成影響, 將道德詞匯的左右呈現改換為豎直呈現, 這也是除實驗材料和被試外最明顯的區別。但垂直呈現的雙字詞間距很小, 在視線偏移的視角上只有 0.03°, 遠小于左右水平視角偏移的 9.54°, 垂直視角的偏移不太可能對水平方位的啟動造成巨大影響。另外, 在以往道德概念垂直空間隱喻的研究中, 詞匯水平位置的呈現并沒有對實驗造成影響(賈寧, 蔣高芳, 2016;魯忠義, 賈利寧 等, 2017)。我們認為垂直方位跨維度影響水平方位的可能性更小, 而水平呈現可能直接對水平方位啟動造成干擾甚至沖突, 同時, 漢語雙字詞因為其獨特性, 必須承認在視覺呈現時無法避免這種閱讀效應。其次, 這也可能是個體差異造成的, 已有研究表明左右與時間存在隱喻聯結, 一般將左表征為過去, 而將右表征為未來(金泓, 黃希庭, 2012; 李金星, 王振宏, 2015), 而不同的個體對過去和未來的情感效價是存在差異的, 如對過去有較好的情感體驗, 那么當道德詞出現在左側時,反應時會更快; 而如果對過去有著消極的情感體驗,那么在不道德詞出現在左側時, 可能反應更快。這一點也需要進一步的探究。
因此, 我們認為存在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的心理現實性, 表現為道德與左、不道德與右,并且這種心理現實性可能受個體因素的影響。
8.2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隱喻聯結構建的二重性
實驗1、實驗2和實驗3的結果與西方的研究結果的并不一致, 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源于左右水平方位在表征抽象概念中所體現出的二重性。Casasanto (2009)提出的整合隱喻結構觀認為, 個體的感知運動經驗和語言文化習慣在概念隱喻中同時發揮著作用。對右利手而言, 在個體成長的早期,因為習慣性的使用利手對空間進行感知和經驗, 可能會用右側方位來表征積極概念, 而用左側方位表征消極概念。這可能會對個體早期道德概念系統的構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因為基于利手的人們最初與環境互動過程所產生的感知運動經驗是具有普適性的。但后天的語言使用習慣和傳統文化因素對隱喻同樣具有很強的影響(葉浩生, 2017), Boroditsky(2000)也認為, 語言文化中詞匯使用和表達習慣的重復, 是特定感知運動通路和抽象概念隱喻聯結的關鍵。因此, 在右利手文化里, 早期左右水平效價的隱喻建構上是類似的, 但不同的是在后來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習慣的塑造下, 左右空間可能在漢語環境下表現出了一定的獨特性。
一方面, 我們語言中存在“無出其右”、“旁門左道”這樣的表達來支持右好左壞的隱喻觀點(楊繼平,2017), 另一方面也存在“穩操左卷”、“左券在手”等表達來支持左尊右卑的隱喻觀點, 在生活中我們更多的也會使用像“左右為難”、“左右逢源”這些詞匯來表達一種躊躇、摸棱兩可的情感, 這顯示了左右道德效價在日常使用過程中的“中庸”和泛化。王希杰(2004)也認為在傳統文化中, 左右所代表的情感效價具有二重性, “左右之爭”在學術界至今沒有一個明確且一致的結果。其次, 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視“言有序”這一語言書寫規范, 并且中文雙字詞一般將重要的、積極的書寫在前面, 而將次要的、消極的書寫在后面, 如“好壞”“尊卑”、“對錯”等, 因此詞語排列的先后順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左右的道德效價表征, 而西方詞匯在表義上具有整體性, 并沒有類似的表述習慣。目前漢語的書寫規范是從左到右, 所以可能存在一種道德在左、不道德在右的語言使用習慣, 并在此基礎的重復使用進一步導致了這種隱喻聯結的心理現實性, 而這與利手所習得的情感效價并不一致。
而實驗6中被試對水平方位右側的字母判斷速度顯著快于左側字母, 這表明在不涉及到漢語道德概念加工時, 個體表現出了一種右快左慢的利視特點。但為什么在之前的實驗中并沒有發現這種情況呢?即這種利視現象為何只在字母判斷而非漢語詞匯判斷中出現呢?這可能體現了左右空間在漢語隱喻表征中的二重性, 個體在成長過程的早期通過利手感知運動經驗來構建積極或者消極情感, 而在對漢語的習得和使用過程中我們又建構了另一套隱喻系統, 這也就意味著并非所有語言的隱喻表達習得的方式都與身體特異性有關(Lakoff,Johnson, 1999)。隱喻的形成具有層次性和復雜性等特點, Lakoff和Johnson (1980)認為存在于文化中的價值觀經常存在著沖突, 而具有表現的優先權則取決于個體所處的亞文化以及特定的價值觀。中國文化復雜多樣, 在對抽象的道德概念進行建構時某一種隱喻傾向可能會占據主導權, 這可能受諸多因素的影響。
8.3 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受概念加工深度影響
實驗2、實驗3和實驗4分別在較深、中等、較淺三種概念加工深度下探究了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情況。不同概念加工深度的實驗范式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這符合加工水平理論的觀點, 即在語言認知過程中, 不同的加工水平意味著不同的理解效果(Craik & Lockhart, 1972)。根據閱讀的聯結注意模型(Seidenberg, 2011), 對詞匯的概念加工存在詞形、語音和語義三種, 其中詞形加工是最淺顯的概念加工, 語音和語義都屬于較深的概念加工。因此實驗2加入了語音閱讀的任務要求增強了對目標詞匯的概念加工深度, 而實驗4加入真假詞判斷, 是典型的詞形加工任務(劉文娟 等, 2016),這削弱了對目標詞匯的概念加工。實驗3采用標準空間 Stroop范式要求被試對道德詞匯的效價進行判斷, 這是一種半自動化的加工深度。已有研究顯示對詞匯的情緒屬性進行判斷會導致一定深度的概念加工, 在這種加工層次下, 被試對詞匯有一定的語義加工(Hyde & Jenkins, 1973), 因此實驗3要求被試對詞匯的效價判斷屬于一種中等深度的加工。
實驗2和實驗3結果都顯示了詞匯類型與水平方位的交互作用, 而實驗4結果沒有顯示這種交互作用。這表明在較深、中等概念加工深度下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 而在較淺的詞形概念加工深度下, 并沒有顯示這種隱喻聯結, 說明這種隱喻聯結受概念加工深度的影響。Huang等(2018)提出的激活假設認為, 具體概念的加工要快于抽象概念的加工, 并且隱喻一致性效應的產生取決于具體(或抽象)信息在對抽象(具體)進行判斷之前是否被預激活。而實驗 4與實驗 2、實驗 3均為空間Stroop任務, 都對水平方位有相同的預激活, 但是實驗4卻沒有發現相應的隱喻一致性效應, 這說明對非判斷域的預激活于隱喻聯結而言只是一個必要條件, 判斷域的激活深度對隱喻聯結的產生也同樣重要。Huang等(2018)的研究還發現啟動范式相較于 Stroop范式, 因為對非判斷域有更深的加工,導致隱喻一致性效應更易出現。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實驗5在實驗4的基礎上, 在真假詞判斷之前加入了與之一致的空間啟動線索, 進一步增強非判斷域的預激活深度, 并未發現隱喻一致性效應的出現。而實驗6先通過真假詞判斷在較淺的詞形加工深度下啟動道德詞匯, 隨后對出現在水平方位的字母進行類別判斷, 結果也未發現隱喻一致性效應。這進一步佐證了我們的觀點, 即是否出現隱喻一致性效應, 不僅取決于非判斷域概念是否預激活,還取決于對判斷域概念的加工深度。也就是說, 至少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同時取決于目標域和始源域的概念加工深度。而由于空間信息往往加工速度更快, 因此對抽象概念的加工深度顯得更加重要, 這進一步豐富了激活假設的內容。
此外還需注意, 道德詞既包含了道德效價, 同時也包含著情緒效價, 情緒作為一種主觀上的體驗,伴隨著道德認知過程(李瑩, 張燦, 王悅, 2019)。已有研究表明個體對道德情緒的加工顯著快于其對道德認知的加工, 說明了在道德效價判斷任務中,基于直覺性的情緒加工是一種自動化的加工, 而道德認知的加工需要進一步的語義加工才能得到充分理解(Zhai, Guo, & Lu, 2018)。那么在真假詞判斷任務中, 被試對道德概念可能具有相應的情緒加工,而情緒感知與身體特異性有關, 但實驗4、5、6均未發現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 說明道德情緒可能在漢語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中不具有核心作用, 對詞匯概念加工加深可能是加強了道德認知, 從而影響隱喻聯結。這進一步表明在漢語環境下, 道德概念水平方位的隱喻更多基于語言習慣和文化因素, 而非身體特異性。
綜合本研究的6個實驗, 我們認為道德概念水平方位的隱喻關系是否能夠被明顯探測到, 其關鍵在于對始源域和目標域概念的加工深度。概念加工深度越深, 就能激起并喚醒更大程度和范圍的神經元, 從而導致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聯結強度增加。因此在不同的概念加工深度下, 個體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的隱喻聯結存在差異。
9 結論
(1)道德概念與水平方位存在隱喻聯結, 左表征道德、右表征不道德。
(2)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表征受到概念加工深度的影響。
(3)豐富了激活假說, 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隱喻聯結同時受始源域和目標域加工深度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