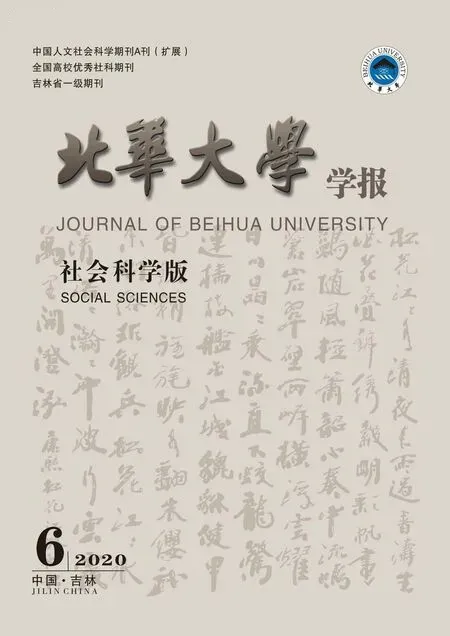清代打牲烏拉采參問題研究
王雪梅
為壟斷東北地區豐富的物產資源,清政府在烏拉地方建立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作為專門為皇室進貢東北土特產品的專業生產機構,隸屬于內務府管轄。“溯查本署旗仆,系我朝太宗文皇帝御基由來本處,以圍獵貂皮,刨挖人參,進寶納貢。”[1]14康熙二十一年(1682)跟隨康熙帝東巡的高士奇記:“虞村居人二千余戶,皆八旗壯丁,夏取珠,秋取參,冬取貂皮以供公家及王府之用。”[2]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建立于順治十四年(1657),宣統三年(1911)隨清朝統治滅亡而撤銷。存續期間,其大宗采捕產品東珠、鱘鰉魚、蜂蜜和松子一直進行生產,其他種類的貢品采捕,不定時進行。只有人參生產比較特殊,在衙門成立之前即已進行,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到乾隆十五年(1750),“烏拉地方捕牲壯丁采取人參,有名無實,嗣后采蜜三百戶停其采參”[3]8168,至此,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采捕人參使命正式結束。打牲烏拉采參是清代享有特權的專業采參機構,組織模式、管理模式都很特殊,其采參生產開始和結束與清代參務政策調整息息相關,對其相關內容進行闡釋十分必要。
一、打牲烏拉采參的組織模式
打牲烏拉采參的生產者是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壯丁,這些壯丁以珠軒為單位組織生產。珠軒為滿語,意為打牲烏拉包衣下的食糧人戶。進行采捕生產的時候,各珠軒的打牲丁在衙門官員帶領下,進入山林和江河進行采挖捕撈。順治十八年(1661)規定,打牲烏拉設33珠軒,每珠軒設壯丁20—26名,雍正七年(1729)定每珠軒設壯丁不得過30丁。[3]實際上,珠軒內部構成的人數是不固定的,最少為5人,最多為30人,一般為11—14人。珠軒的負責人為珠軒達(窩鋪長),采參生產時,由窩鋪長或副窩鋪長帶領牲丁進行。
順治年間,牲丁尚無明確的采捕任務分工。順治四年(1647),打牲烏拉有12個珠軒參與采參,其中男丁166名,婦女159名;[4]95順治七年(1650),采參男丁243名,婦女230名;[4]116順治八年(1651),鑲黃、正黃、正白三旗33個珠軒參與采參,采參牲丁共計471人。[4]120-122康熙五年(1666),“打牲烏拉增設六個捕魚珠軒。從此,打牲烏拉珠軒按照所擔負捕貢任務的不同,分為采珠珠軒和捕魚珠軒兩大系統”[5],但采參牲丁沒有成立單獨的珠軒系統,從大類上說,隸屬于采珠珠軒系統。
打牲烏拉的采參牲丁兼任采蜜,采蜜和采參的具體分工,會根據需要隨時調整。“查康熙五十二年因米鹽庫蜂蜜貯積議奏,將打牲烏拉采蜜丁一百五十名,令其一年采蜜,一年刨參”[6]227,這種牲丁隔年挖參的模式一直持續到雍正五年(1727)。該年因“現有漢人進蜜,足可敷用,相應將打牲烏拉所進蜜貢,從此裁撤,而采蜜之丁,著盡行刨參等因”[1]90,但第二年,“因漢人交蜜稍覺不敷供用,仍令打牲烏拉遵照將以前采蜜一百五十名丁內,揀丁五十名采蜜,循例進送等因。”[1]90至雍正七年(1729), “打牲烏拉一百五十丁內,令一百名刨參,五十名仍采蜜,伊等內每年更換行走,其刨參丁現有幫丁,每人準其兼帶二名,所給刨參丁參票內添注幫丁之名,以為證驗。既添幫丁,相應每票一張加參六兩,額定征參三十兩,若有額外多交,照定例勸賞,若不足治罪”[6]253,此次調整是打牲烏拉采參人數調整最大的一次,采參人數增加到300人。幫丁制度的實行實際上減輕了采參牲丁的負擔,原來每牲丁采參數額是24兩,增加幫丁之后,3人采參額數是30兩,人均采參數額是10兩,牲丁負擔大大減輕。采參人丁300人的編制也一直持續到打牲烏拉采參使命的結束。
乾隆十三年(1748),打牲烏拉采參事宜交吉林將軍兼辦之后,吉林將軍改派兵丁進行挖參,相比打牲壯丁來說,兵丁挖參經驗不足,地理不熟,挖參收獲缺額很大。乾隆十四年(1749),打牲烏拉只上交人參835兩,較定額3 000兩缺額2 165兩之多,最終導致了采參牲丁的徹底裁撤。“乾隆九年起至十三、四等年,因呈進之參,不敷額數,準吉林將軍衙門咨文內開,由內閣抄出大學士公等議奏,將挖參之三百人裁撤,歸并捕珠丁內,一律捕差,如東珠、蜂蜜,采捕足數,以贖罪愆”[1]42,這些采參牲丁歸入了采珠牲丁的行列。
從順治到乾隆初期,打牲烏拉采參牲丁不斷調整的過程,可以看出清廷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這一專為皇室服務的專屬機構管理不斷制度化、規范化的過程。從順治年間對牲丁的寬泛管理,到康熙、雍正年間對牲丁管理體系制度化的形成,也能夠折射出清朝入關后統治不斷穩定,皇權不斷加強的政治統治過程。
二、打牲烏拉采參的管理模式
打牲烏拉牲丁采參數量定額、牲丁待遇等管理,也經歷了從寬泛到制度化管理的變化過程,與其人員組織管理過程相一致。
順治年間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之前,內務府對于牲丁采參的數量定額沒有具體規定。據《盛京內務府順治檔》統計,順治四年(1647),打牲烏拉牲丁166名,采參398斤2兩,平均每丁采參2斤6兩;順治八年(1651),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牲丁471人,采參375斤5兩,每人采參12兩。康熙五十六年(1717),對打牲烏拉所交人參設定額數,規定每丁每年交人參1斤8兩,上三旗150丁,交人參225斤。雍正七年(1729),清廷對采參牲丁進行了調整,100名采參丁,每名配2名幫丁,牲丁加幫丁一共交參30兩。這樣打牲烏拉每年所交人參數額就是3 000兩,合為187斤8兩(16兩為1斤),至此3 000兩的交參數額成為定數。雍正十一年(1733),總管內務府統計,“都虞司打牲烏拉牲丁刨得年例應交人參三千兩,余參三百七十一兩五錢,蘆須一百八十八兩,按斤數應得人參二百十斤十一兩五錢,蘆須十一斤十二兩,稱驗較年例應交人參數外余出人參二十三斤三兩五錢,蘆須十一斤十二兩。”[7]這個定額成為常例,一直持續到打牲烏拉采參任務的結束。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部分年份交參數量,如表1:

表1 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部分年份交參數量統計
據表1可知,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采參限定數額之后,至乾隆十一年(1746)之前,打牲烏拉牲丁所交人參基本能按定額繳納,偶爾缺額也不大。但乾隆十一年(1746)只交參810兩,缺額2 190兩后,乾隆十三年(1748)采參事宜交給吉林將軍兼辦,乾隆十四年(1749)又缺額2 165兩,第二年,打牲烏拉終止了采參生產。
順治時期,打牲烏拉采參牲丁的待遇采取實物補給方式。采參牲丁以珠軒為單位,對采獲的人參分別給予馬、牛、大毛青布、小毛青布、粗布的賞賜。每采人參1斤,獎給大毛青布2匹,13斤人參可獎勵1匹馬,10斤人參獎勵1頭牛,順治四年(1647)“大番珠軒采得人參二十七斤七兩,除獎給一匹馬抵銷十三斤人參外,其余的十四斤七兩可獎與毛青布”,“塔比亞珠軒采得人參三十斤二兩,除獎與一頭牛抵銷十斤外,尚有應獎與毛青布的二十斤二兩”。[4]95順治六年(1649),打牲烏拉12珠軒一共采得人參162斤4兩,“尼康珠軒共采人參十七斤十兩,每斤應給予二毛青布,共給予三十五毛青布一庹,以上總計三百二十八毛青布二庹。倘給大毛青布每斤應給二,如給小毛青布每斤應給三。”[4] 112
康熙五十六年(1717)額定參額后,采參的獎勵以丁為單位實行。“每丁額征人參一斤八兩,多交一兩者,賞毛青布一匹,缺額者,每人參兩錢,鞭責一。”[3] 19205采參丁多采人參獲取毛青布的獎勵一直持續到乾隆時期,乾隆六年(1741),打牲烏拉上三旗共刨得人參191斤4兩,珠軒頭目劉查寶、副頭目蔣德五十五人刨送人參較數額多出六十兩,共計賞給毛青布六十匹,由廣儲司發給。[6]243對未完成挖參數額的打牲丁并連帶衙門官員都會受到處罰。雍正五年(1727),“查對應解參數自康熙五十三年初次解過人參四百十五斤,后于五十五年解人參一百十六斤,因其甚少,始行奏準限定額數。”[6]228對于所交人參額定數量的不足,清廷認為是處罰措施不夠嚴厲,導致打牲丁藏匿刨挖人參不上交,因此制定了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刨參之丁每票定額交參1斤8兩,打牲丁“缺少一兩以下者鞭五十,二兩以下者鞭一百,二兩以上者枷號四十日、鞭一百”,領催、窩鋪長對于本旗牲丁應交數額,“缺少六斤以上至二十斤者,將該管領催、窩鋪長各鞭八十,二十一斤以上至三十斤者鞭一百。此外更有缺少者鞭一百,革其領催允當打牲壯丁”;對于上三旗牲丁應交數額,“將應交人參二百二十五斤之內,缺少二十一斤以上至三十斤者,將該管翼領驍騎校各罰俸兩個月。此外更有缺少者,以二十斤為一分,加增每一分罰俸兩個月,缺少一百斤者各降一級,罰俸一年。”[6]228
對于缺額極大的年份,處罰則至打牲烏拉總管。乾隆十一年(1746),總管綏哈那任內只上交了人參810兩,缺額達2 190兩。[6]253“綏哈那應交參三千兩,內缺少二千一百九十兩,合計于十分內缺少七分以上,應將綏哈那照此律杖一百。系公罪,應降四級調用。查綏哈那有加一級,應銷去所加一級抵現降一級,仍降三級。系內府人員,照例免其調用,加罰俸三年。”[6]254綏哈那因此次貢參缺額一事受到處罰,雖未免去總管之職,但乾隆帝對綏哈那的工作能力和信任出現了危機,“乾隆十三年奉旨,打牲烏拉采人參事繁,總管一人,不能辦理,交吉林將軍兼辦。”[3] 19198
由于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十四年(1749)打牲烏拉衙門采參數額較少,乾隆十五年(1750)清廷取消了打牲烏拉衙門的采參生產,但把未完成交參定額的原因歸結到參丁身上,“乾隆十五年議準,蜜戶內采參丁三百名,多將所得人參竊與官領信票之人,以致欠缺參額,改令采捕東珠,效力贖罪,毋庸一例給予珠丁錢糧,將其所得東珠存記,如果所得東珠一等者多,再令該將軍奏請賞給錢糧。”[3]16037參丁雖然轉為珠丁,但卻沒有與珠丁享有同等的例行待遇,要靠采捕更好的東珠才能獲取錢糧賞賜。清廷簡單地把打牲烏拉人參缺額原因轉嫁到參丁身上,并制定了懲罰措施,反映了參丁地位的低下。
三、打牲烏拉對私采人參的管理
清統治者為實現對人參的壟斷,對私采和私販人參實行嚴酷的刑罰和嚴密的管理制度。順治時期,對于偷采人參的組織者,拿獲就要殺頭,其他相關人員也分別予以處罰。順治十五年(1658)“有偷采人參者,將帶至之頭目斬決,余眾治罪。又議準,旗下人偷采人參者,枷一月,鞭三百,牲畜及所得之參,一并入官。官民家下人有犯,其主知情者,本犯枷一月,鞭三百,參與人畜皆入官,其主問偷盜之罪。不知情者免議。本犯枷兩月,鞭一百,牲畜財物入官,若其主知情詐稱不知者,加等治罪,家人入官。”[3] 8187乾隆十一年(1746), “嗣后拿獲過冬偷刨之民人、家奴開戶人等,無論己未得參,一體刺面。民人遞籍,交地方管束,照盜竊例,不時點查。”[8]
除制定嚴酷的刑罰以震懾偷參行為外,清廷在參山附近的交通要道設置卡倫負責對私參的緝拿。“各駐隘要,以杜飛飏人參,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等事。”[9]乾隆十年(1745)又定,吉林所屬打牲烏拉地方,附近參山之四道梁子、咯薩里、那木唐阿、長嶺子等四處,設立臺卡,每卡官一員,兵十名,每月更換。[3] 8176在這些常規的檢查站之外,打牲烏拉衙門的官員也有緝拿私參的職責,乾隆二年(1737),打牲烏拉派出左翼協領那什以及正黃旗、正藍旗等佐領、驍騎校等8人帶領164名兵丁去上河等處查拿私采人參者,共搜得人參642兩6錢。[10]如果緝拿私參不力,對相關人員也要給予處罰。“其巡查管轄等事派翼領一員、驍騎校一員,將刨參丁嚴行稽查,若有隱匿交不足數不行查出,被旁人首告等情,將前往之翼領、驍騎校一并議處。”[6] 253
四、打牲烏拉采參終結的原因
清廷雖然從人參采捕、管控等各方面制定了嚴厲的措施,以確保對人參資源的獨占,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人參采集還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結束了,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自然資源的日益減少,使得人參采集越來越困難。入關之前,人參就是女真人重要的經濟產品。明代中后期,受明人溫補思想影響以及女真南遷自然生產條件的改善和此時黨參的衰落,為女真人采參業發展提供了極好的契機。女真人通過人參、東珠、各種動物皮毛等土特產品與明朝進行交換,以致“民殷國富”。“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人參的產量和銷量都是相當大的,可以說是野生人參采挖史和貿易史上的鼎盛時期……在這個時代里,每年人參的具體產量,雖然尚無文獻可資精確統計,但大體上每年都在五、六萬斤以上。”[11]50入關之后,基于統治者對人參一以貫之的重視和江南溫補文化的盛行,[12]20社會對人參的熱情只增不減。但人參不同于一般的漁獵產品,其生長周期特別長。而女真人對人參的采集速度遠超過人參的生長速度,以致造成人參資源日益枯竭。
入關后,清廷對東北人參實行壟斷和封禁政策,并且采取各種極為嚴厲的措施控制私參,但私參屢禁不止。“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于饑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余人。”[13]52康熙三十三年(1694),“去寧古塔、烏拉等處偷挖人參之人一年將及三四萬,馬牛羊達七八萬。前去挖參無業之人,在山內居住一年,需帶食米七八萬石。”[14]64這些私采人參數量較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盛京附近抓獲姚兒道、德琳偷刨人參2 700斤,從商人手中繳獲人參7 631斤,從盛京拿獲628斤。[15] 622康熙五十三年(1714),吉林將軍孟俄洛在松花江上游色勒、薩穆西、訥殷等處,抓住偷參之人802人,查獲人參7 825兩,參節、參須644兩。[15]977
官、私對人參的大量采挖,造成人參資源日益枯竭,從采參的參山不斷往北推進的過程可見一斑。“歷史上人參分布的最大區域,北自北緯52°,南至北緯39°,西起東經115°,東至東經135°……在這樣一個遼闊的人參分布區內,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幾個最重要的人參盛產地,即遼陽以東至鳳凰城,渾江流域之額爾敏、哈爾敏流域,松花江上源及輝發河流域,吉林周圍地區,寧古塔周圍地區,烏蘇里南部地區,綏芬河流域,共計七個重點地區。從歷史發展來看,人參產區的開發發展是自南而北,自西而東,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11]142清初始行的八旗分山制“大部分參山在柳條邊墻的東段至長白山之間,其次則為吉林地區,寧古塔至呼蘭間則較少。參山的分布反映了清代早期參場大多在盛京的東北部至吉林交界的地區。”[11] 80但是經過數十年的官私大量采挖,這些參山資源日益減少,康熙“甲子、乙丑已后,烏喇、寧古塔一帶,采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13]52隨著原有參山資源的枯竭,清廷不斷往北尋找新的參源,康熙二十三年(1684)烏蘇里江上中游一帶發現了新的參源,人參采挖逐漸轉向烏蘇里江地區。
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起至乾隆十一年(1746),“烏蘇里內,必欣、牛曼、阿庫里等山業已連刨參三十余年,看此三年,多寡不等,俱不能足額。山場荒蕪是實。”[6]252面對這樣的困境,清廷采取了系列措施:一是制定了更加嚴厲的禁令,加強皇室采參管理。康熙四十八年(1709)議定:“寧古塔、瑪彥窩哩別派、綏哈河、伊拉莫河等處地方所產之參,專備上用,不準常人采挖”[3]8164;二是嘗試采取歇山和輪采政策。雍正八年(1730)“烏蘇里、綏芬等處參山,開采二年,停歇一年。其停歇之年,在額爾敏、哈爾敏地方開采”[3]8164,乾隆九年(1744)烏蘇里等參山,試開二年,停止一年;或連刨三年,歇山一年。[3]8164隨著參源的減少,清廷雖然多次下達歇山輪采的禁令以及加強對東北封禁的管理,但功效甚微,最終歇山輪采不了了之。人參資源的枯竭,使得打牲烏拉衙門牲丁采參日漸困難,最終結束了采參生產。
第二,新采參渠道的開辟,擴大了采參規模,提高了采參數量,為內務府提供了更多的參源。清初人參采挖以官方壟斷形式進行,官采人參除了打牲烏拉壯丁采參外,還有盛京內務府采參、王公貴族采參、八旗兵丁采參等幾種形式,其中八旗兵丁采參為皇室采參的補充形式,是非常態的采參模式。康熙二十三年(1684)取消八旗分山制,八旗貴族采參的特權也隨之取消。在參山資源逐漸減少和私采難以控制的局面下,清廷不得不把壟斷的人參資源對民人開放。
康熙五十三年(1714),發給富商王修法等八千張參票,允許他招募刨夫八千人采參,清廷想利用政府掌握的參票權力既能控制人參采挖,又能獲利,但采參效果并不好,康熙六十一年(1722),停止了這種嘗試。雍正帝繼位后,對康熙末年實行的招商刨采制進行了改革。雍正元年(1723)“采參雖經嚴禁,盜挖不能除。與其肆令盜挖,莫如定制收課”[3] 8166,正式向民間發放參票,每票交參2兩5錢,征銀20兩,多采人參收取稅銀。雍正二年(1724),改為每票征參24兩,銀4兩。雍正四年(1726),改為免交銀兩,一律交參,烏蘇里、綏芬河采參交參26兩,奉天交參24兩。雍正八年(1730),又恢復了招商刨采制,對烏蘇里、綏芬河等處參山,官放參票,招商刨采,1萬張參票,可以雇傭刨夫1萬名,每張參票收參16兩,其中10兩交官,6兩留商。[3]8167乾隆九年(1744)清廷為了避免商人作為中間環節的弊端,改“招商刨采”為“官雇刨夫”采參,“盛京、吉林、寧古塔等處行放參票,因招募商人承辦,私弊較多,官票放不足額,嗣后改官雇刨夫……無論旗民,均準給票刨采”。[3]8167由此,盛京、吉林、寧古塔陸續設立官參局負責地方采參事宜。
參務制度的改革,使清官府獲取的人參數量極大增加。乾隆五年(1740)大商人范毓斌承辦東北參務,“與奉天、吉林烏拉、寧古塔三處共放出參票四千五百六十二張,應納人參四萬五千六百二十兩。”[14]170除了所放參票收入之外,內務府所獲人參還包括各地繳獲的私參,以雍正十一年(1733)為例,據總管內務府統計,收到奉天商人郭正義所放官票2 822張,應交人參28 220兩,實際收到人參1827斤4兩,佐領雅思哈拿獲人參149兩8錢5分;寧古塔拿獲人參71斤6錢,打牲烏拉牲丁刨得人參210斤11兩5錢,以上四次送到人參2118斤12兩3錢。[7]有了這樣數量眾多的人參可以選用,打牲烏拉衙門采參職能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了。
第三,內務府人參庫存的積壓,不再需要打牲烏拉提供人參。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牲丁和八旗士兵所采人參,主要是交給內務府以供給皇室滋補及藥用,作為清宮珍貴的物品,也用于對有功大臣的賞賜,剩余的交給戶部,由戶部送交崇文門監督變價銷售。
清宮廷用參質量要求高,管理嚴格,清宮太醫院用參都有詳細的檔案記錄。根據太醫院檔案記,“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止,皇貴妃人參湯用過人參三兩一錢,噙化人參用過人參三兩一錢,湯藥內用過人參八錢。”[16] 86雍正十三年(1735),太醫院共用人參為230斤。[16] 76
清廷實行招商刨采和官雇刨夫制度后,獲取人參數量大幅增加,導致了內務府人參積壓,積壓的人參由內務府發往江南地區變賣。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把內務府積壓的1 024斤10兩5錢人參交給曹頫、李熙、李文成分為三份運往江南售賣;[17]雍正時期,繼續把內務府積壓的人參南運售賣,而內務府變賣人參在乾隆朝已經是制度性的措施。[12]187之所以內務府能在人參貿易中充當重要的角色,“最主要的原因是內務府收藏人參的茶庫的庫儲人參無法消耗每年所囤積的人參,所以必須將多余的人參賣至民間市場。”[12]188
皇室用參的滋補、醫用以及賞賜需求數量有限,內務府人參又大量積壓,超過皇室用參需求,因此從打牲烏拉衙門直接獲取人參的特供需求也就不強烈了,也導致了打牲烏拉人參采挖生產的終結。
人參是女真人重要的生活和生產物資,其與東珠、貂皮等漁獵產品都是女真崛起的重要物質因素,“本地所產有明珠、人參、黑狐、玄狐、紅狐、貂鼠、猞猁猻、虎、豹、海獺、水獺、青鼠、黃鼠等皮以備國用。撫順、清河、寬甸、叆陽四處關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賈,因此滿洲民殷國富。”[18]人參不同于東珠和各種動物皮毛,其醫藥價值和經濟價值相對更為顯著。入關前,女真貴族對人參就實行壟斷經營。入關之后,清王朝將人參管理納入了國家管理體系當中,不斷強化壟斷管理,設立了專業采參組織進行人參生產,反映了清朝入關后皇權不斷強化的過程。從打牲烏拉采參、王公貴族采參、八旗兵丁采參到官參局的設立,各種采參模式的不斷調整,既反映了清代初期人參管理的變化過程,也是清代中后期人參采捕政策調整的依據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