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考上985的寒門學子
朱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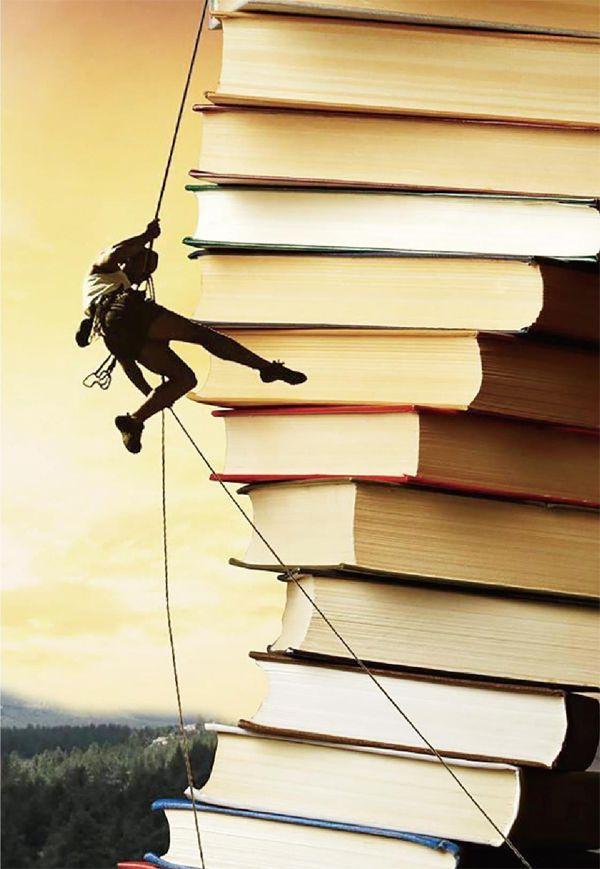
走出去了,然后呢?
從小到大,胡月聽得最多的一句話:“爸媽一輩子都要在這個村莊了,你要自己走出去。”她深知這一句話里面藏著多少期待。
胡月家在內蒙古的一個貧困村,那里常年干旱,村民們通過種植一年一季的農作物為生。農閑的日子里,父親會到建筑工地里當水泥工,將家里年收入維持在兩到三萬的水平。
2014年的高考,胡月考上了廈門大學,是鎮上成績名列前茅的大學生。但她還是不滿意,“比平時低了三四十分”。唯一的遺憾是,如今她當上了北漂,躺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想起了當年選專業的情景——當這條人生路上重要的分叉口來臨時,身旁沒有人能給她指導,耳邊只有來自老師的告誡:選學校比專業、城市重要。
2018年,江西贛州的洪磊通過了華南理工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最后的面試關頭,教授拋出了自動化和機械工程兩個專業的橄欖枝,他選擇了“看起來更厲害”的機械工程專業。
選擇只是一念之間,影響卻格外深遠。他們出身寒門,走進了985的校門,希望和迷茫,得意和失意,是高考后未完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
洪磊今年大二,八月初,他忙著準備疫情期間欠下的各科期末考試,期末周是他大學最“痛苦”的時刻。
從江西南部城市贛州石城縣的家出發到廣州,他要先搭四個小時的大巴,轉兩趟車,到達贛州火車站;再坐上時長七個小時的普快列車,來到人聲鼎沸的華南省會。在他看來,學校所在的城市,和家所在的縣城差不多,只是“物價貴了點”。
他對未來仍十分迷茫,但言語間透露著“未來可期”的松弛感。他在班上成績“不好不壞”,
“不是最勤奮的那批同學,但也不是不學無術”。讀了兩年機械工程后,洪磊總結,這個專業的課程內容就是難度很高的力學,同專業的學長建議,“未來不要走純機械方向,實在太難了。”
胡月是當年村里唯一考上985學校的大學生。六年前,她只身一人,扛著國家助學貸款,來到離家2400公里的海濱城市。父母過去反復叮囑的“走出去”,是她小學至高中12年學習生涯中最大的動力。如今,她真的走出來后發現,外面的世界雖然不會再讓她像過去一樣“黃土滿面”,但也并非如想象中的繽紛多彩。
廈門全年溫和多雨,與內蒙古冬天的嚴寒干燥有很大的反差,胡月不適應。此外,專業上的學習讓這位本不滿意被調劑命運的人感到崩潰。因分數不理想,錄取后她被調劑到了一無所知的生物學專業。她不喜歡去實驗室,也厭倦課本上枯燥的生物知識。大一下學期始,她向學長學姐打聽專業未來的就業前景,卻感覺更加迷茫。
獲取而來的信息讓她明白,專業對口的出路無非是幾種:一是在國家部門的生物、海洋所擔任公務員;二是繼續深造,走科研道路;三是通過海外留學等途徑提高學歷后,回國當高校講師、輔導員。胡月對此有不少憂慮,不管是哪條道路,失敗的可能性都不小,“家庭承擔不起我今后失敗的成本。”
錢在胡月這里,是她做出大小決定的首要考慮因素。大學四年,為了不在出門聚餐時花錢,她沒加入任何社團。五一、十一小長假,她不敢與同學結伴外出旅游,只呆在圖書館里安靜看書。
連升學、擇業等重要的人生決定,她都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作為家里的長女,胡月總認為,自己要早日擔起養家的責任。即使擁有獲得獎學金讀研究生的機會,她仍然要考慮再三。
胡月的遲疑和糾結不是偶然的。《中國青年研究》的一篇文章曾經顯示,寒門大學生容易預見新環境對自身造成的“威脅”,導致其自我控制出現下滑和失焦,從而會對學習和生活產生不利影響。
曾經有一段時間,對專業前景的憂慮太深,胡月認為自己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她把自己封閉起來,斷絕與外界的接觸。最長的一次,手機關機了一個星期。負面情緒壓得人喘不過氣,她開始逃課,到圖書館一個人待到天黑。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開始整宿地失眠,清晨起來枕巾被幾大片淚漬沾濕。
“好好讀書”
相反,洪磊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初中三年,他在縣中學的尖子班上名列前茅,也因此獲得到贛州一中念高中的機會。但是,為了“講義氣”,也為了離家近,他留在原學校,與很多到市重點中學念書的同學“分道揚鑣”。
縣城中學雖然在資源上不如市里中學,但洪磊更喜歡其中的氛圍,“輕松也很快樂”“還有時間與朋友出去逛逛”。
父母也沒干涉洪磊的決定,準確來說,他們并不清楚兒子的學習情況。他們只知道,洪磊從小成績就好。全年在東莞市務工的兩人,每年只回家一次。大多時候,他們會塞錢給留在家里的老人,有時還給初中的洪磊和弟弟報周末補習班。
洪磊記得很清楚,他是在“非典”來到那年被父母由廣東送回到贛州,由爺爺奶奶撫養。他并不清楚這其中的緣由,三歲前的記憶也十分模糊。但是,他堅信自己與留守兒童不一樣,他從未感受過來自家庭的愛的缺失。
“你認為你和別的留守兒童不一樣在哪里?”洪磊想了半天,強調這是一種不可言訴的安全感。最后,他好不容易擠出一句話,“我的爺爺奶奶很開明,從來告訴我的都是要‘好好讀書。”
“好好讀書”,也是胡月上學期間聽到好多次的話。但說這類話的人,更多是出自學校里的老師,帶給胡月的是壓迫感。
從小村莊考入縣城高中的尖子班,胡月一入學就感受到與他人的差距。英語已經比別人落后一大截,敏感的青春期讓她也開始在意同輩的目光。至今都讓她感到窘迫的是,家里過去沒錢給她添置新衣,一個冬天只有幾件換洗衣物。最夸張的一次,胡月一個月都在穿同—件外套。連班里的男生都止不住問她:“那么久了,你都不換衣服嗎?不覺得臟嗎?”
年級越高,胡月就越自卑。她唯一能抓住的希望就是父母強調的“走出去”。因此,考試成績是她心情的晴雨表。考試失利時,她會陷入無盡的自責,責備的理由也是相似的:“你沒有全力以赴,你要怎么樣走出去?怎么對得起父母的養育之恩?”
有時候,胡月甚至覺得,連“好好讀書”她都做不到了。尖子班上總有比她更勤奮的人,大家都在攢著力氣相互較勁。從高一開始,學校每周需要上六天半的課,每日在校時間超過15個小時。即使如此,班上仍有部分每天熬夜到兩點、第二天六點就來到教室學習的人。
高三是胡月最焦灼的時候。班級“晾曬式”的管理辦法讓她時不時情緒崩潰:每次周考出成績后,班主任會當眾念各科分數排名,并將全班各科成績粘貼在走廊墻壁上。胡月還清晰地記得,到了高三后期,每回老師在班上念排名,只要在名單上“從下往上數”,就會很快找到她的名字。
改寫的命運
高考后,命運就能被改寫嗎?胡月與洪磊的回答都是一致的肯定。
洪磊用了個假設,“如果沒有高考,我現在是什么樣?”停頓了幾秒后,他的結論是,“不管怎樣,都不會比現在好。”
洪磊的朋友圈里,分享的全都是大學里的消息,有學院機械結構設計大賽的比賽通知,也有英語四六級模考預告,更多的則是各類社團舉辦的節日。他很少分享生活照片。少數的兩張是2019年上半年的折紙作品,配文寫道,“自己折的菠蘿,好開心”。20個面的三角形拼成了菠蘿形狀的手工,放在白色的石階上,像一個能討小孩歡喜的皮球。他說,平日就喜歡做這類無用功。
在不喜歡的專業里打轉,胡月的擔子則重了很多,她為此還進行過接近一年的心理治療,心理醫生告訴她:“人要學會和自己和解,接受每個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不過,不管她與現實撞得如何鼻青眼腫,她也從未告訴父母在學校里的狀況。這是她的習慣,因為“告訴了他們也沒用”。從小到大,農民出生的父母都沒法在她做重大決策時給出意見。
畢業后,胡月來到北京,加入了一家與原專業“不搭邊”的上市公司,但是工作一年多后仍然感慨,“看不到上升空間”。疫情期間,公司大幅裁員,她也選擇了辭職,并且開啟了長達四個多月的待業狀態。
待業的時間里,她給互聯網公司投簡歷,每天自學C語言,但她明明對互聯網興趣有限,不愛刷抖音,更不愛看同齡人都在刷的美妝博主,她自嘲“天生落伍于互聯網潮流”,這樣的日子漫長而充滿煎熬。
胡月最終選擇了與自己和解,在意識到失業的焦慮日復一日地彌漫四周后,那種大二時患上抑郁癥的前兆——“全身乏力”的狀態又回來了。她不再逼迫自己終日學習C語言,聽從了父母在電話里的規勸,“回家吧,別在北京漂了。”
“找到工作后,我要準備考老家的公務員,考不上就再考一年,不行就再來一年。”
摘自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