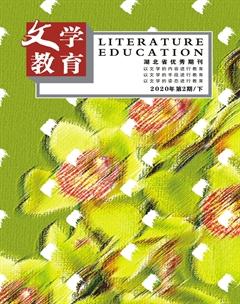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看《白鹿原》與《百年孤獨》
內容摘要: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出發,通過閱讀《白鹿原》和《百年孤獨》兩部經典著作,對著作中多名女性角色的比較和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兩部小說的思想和理念,構建一個多元、互補和平等的社會關系,消除二元對立,對于促進女性健康、建構兩性平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社會具有促進作用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 女性角色 比較 評析
20世紀60、70年代,歐洲世界婦女第三次浪潮中誕生的生態女性主義的和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的興起和發展,將生態環境與女性問題兩個話題愈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弗朗索瓦·德·埃奧波尼(Franc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并指出在自然和女性之間產生著天然的聯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由于女性與自然在孕育生命等方面有著內在的聯系,使得女性更接近于自然。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是為消除男性中心主義和提升女性地位。由于歷史、政治、宗教等的關系,男性的意識、心靈和精神占社會主導地位,形成了一個貶低女性和自然的以男性主導的世界觀。一直以來,男權社會對生態的破壞和掠奪,與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和統治十分相似,生態女性主義批判男性對自然的強制掠奪和對女性的壓迫,但實際是將女性和自然作為一個整體放在了男性的對立面上,這沒有消除二元對立,而是建立了新的二元對立。西蒙·波伏娃認為女性與男性相同,也有社會公平的訴求。女性和男性在生理上是不同的,但是女性可以超越她們的生物特性,把她們從生物繁殖命運解放出來去爭取作為人的價值。(西蒙·波伏娃:195-196)
一直以來,不論是文學還是影視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相似的:順從和孝順,是賢惠的妻子、溫順的兒媳和慈祥的媽媽,這讓女性在自我定位上都遵從和努力讓自己成為相似的妻子和母親。女性天性和母性使女性具有溫柔和善良的品質,但這不能就讓女性活在社會建立的犧牲和奉獻的固化角色中。女性不應是男性的附屬,但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只能被動接受,甚至從未思考過自我需求,任何的反抗都會遭受到更強烈的抑制和壓迫。中國傳統女性這種逆來順受、犧牲、奉獻和隱忍的“好品質”,一次次反抗失敗后的結果。
《白鹿原》和《百年孤獨》兩部經典著作在創作背景、國家和所處社會環境等均有不同,作者在塑造著作中的女性形象十分相似但角色的命運卻又有著極大的差別。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出發,對兩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分析、對比。通過對其中女性角色的再次解讀和分析,實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關注女性在社會中的公平訴求,把女性從傳統角色中解放出來,重構一個平等、去中心化的社會,讓男性對女性的奉獻和犧牲不再習以為常,讓女性對家庭和社會所作的一切得到認可,讓女性擁有主動權和話語權,讓女性能夠更多的參與到社會中,得到應得的認可和尊重。
蘇爾蘇拉與吳仙草
烏爾蘇拉是《百年孤獨》中整個布恩迪亞家族的靈魂人物。作者對烏爾蘇拉的最初描述是她整日忙碌,辛勤勞作,“她身材嬌小,活力充沛,嚴肅不茍,是個意志力堅定的女人”。烏爾蘇拉是家族的靈魂,勤勞、樸實,她不僅是稱職的家庭主婦,照顧丈夫,養育兒女,同時種植瓜果,飼養家畜,經營糖果,關愛整個家族和村莊,正是她的辛勞支撐著整個家族,并推動整個村莊發展。
在《白鹿原》中與烏爾蘇拉形象相似的是白嘉軒的妻子吳仙草,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代表。最初的仙草是靈氣十足,受過良好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體”。與烏爾蘇拉相比,吳仙草不必辛勤的勞作來照顧整個家族,但生活在封建社會的仙草要守本分,做一個乖巧的媳婦兒和稱職的妻子,跟著婆婆學紡線織布,細心照顧丈夫,生兒育女。
烏爾蘇拉與仙草是順從的。作為家族實際掌權者的烏爾蘇拉,擁有絕對的權威,但面對丈夫的各種要求時,還是容忍和妥協。擴展家業的牲口、做本錢的金幣都在丈夫的苦苦哀求下,化為烏有,蘇爾蘇拉只能用更加辛苦的勞作來滿足丈夫的要求;新婚之夜的仙草有過遲疑、猶豫,但最終還是順從了,作了一個稱職的媳婦應做的,對丈夫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拒絕的。
烏爾蘇拉與仙草都將丈夫、孩子和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烏爾蘇拉一生辛苦勞作支撐整個家族,甚至在早已失明的情況下,僅憑借對東西的位置、氣味等的記憶,準確“看到”所有東西的位置,到處管事干預,是害怕自己被認為已經無用了。仙草染上瘟疫后,還“像往常一樣平靜溫潤地招呼出門歸來的丈夫”;病重后,也還是沉著冷靜地安排著一切,更是要做到盡善盡美;失明后,還“歉疚不堪地說:‘誰給你跟老三做飯呀?”在仙草看來,她的職責就是給照顧丈夫的衣食起居,如果不能做到,那就是失德,不是稱職的妻子。
烏爾蘇拉與仙草所作的一切似乎都是應該的,男性理所應當地被母親、妻子照顧,女性理應奉獻,而自身的需求卻從未顧及,也無人關心,沒有得到過關愛和照顧。
田小娥與麗貝卡
田小娥《白鹿原》中一個悲劇人物。年輕的田小娥渴望正常情感,勾引長工黑娃,本以為此后可以跟黑娃過上踏實的生活,但兩人的結合卻沒有得到黑娃父親鹿三和族長白嘉軒的認可,被趕出家門的二人居住在村東頭的破窯洞里。雖然得不到族人的認可,但對小娥來說,能夠與心上人在一起,“安安寧寧,吃糠咽菜”也是幸福的。但因黑娃鬧農協,逃出村子,拋下小娥一人。在不被族人認可的情況下,小娥為了生存投靠鹿子霖,又被鹿子霖利用,作為報復白嘉軒的工具去勾引白嘉軒的兒子白孝文。
《百年孤獨》中的麗貝卡相比田小娥來說,她有追求幸福的自由。麗貝卡是烏爾蘇拉的遠房表妹,在一次舞會后,麗貝卡愛上了意大利鋼琴技師皮埃特羅。但婚禮遭到好姐妹阿瑪蘭妲的各種阻撓一直未能舉行,最終這對戀人之間的激情逐漸淡去,麗貝卡與哥哥阿爾卡蒂奧結婚。這樣的結合同樣也遭到了烏爾蘇拉的反對“不可想象的失禮,永遠不肯原諒”,并禁止他們再邁入家門。這對新人在公墓對面租了一間小屋,唯一的家具是一張吊床,過著簡單的生活。
田小娥與麗貝卡一樣,只想與心愛的人過踏實,穩當的日子,不論是跟鹿子霖還是跟白孝文,都是要生存,求自保而不得已,但最后還是一再被利用,被拋棄。田小娥不像麗貝卡那樣“擁有沖動心性和熾熱情欲,擁有無畏的勇氣”,但即便小娥再大膽,有追求幸福的勇氣,對中國千百年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們來說,對田小娥的種種亂倫行為是無法接受的,最后黑娃的父親鹿三殺死了這個讓鹿家和白家兩家蒙羞的女人。
白靈與蕾梅黛絲
《白鹿原》中的白靈自小生得水靈可愛,是父親的心頭肉“稀欠的寶貝女兒的要求難以拒絕”,當別人家女孩都學紡線的時候,白靈卻在父親的帶領下走進學堂,引得“村里人一街兩行圍住看稀罕”。父親對白靈的寵愛可謂是超過了一般,因父親以不安全為由拒絕她進城學習的請求時,白靈自己跑到城里上學,并對來帶她回家的父親以死相逼,父親只是默許了她的行為“一句話沒說就回到原上來”。
白靈叛逆的是在奶奶、父親等家人的寵愛下形成的,從小可以像男孩子一樣自由成長。《百年孤獨》中的美人蕾梅黛絲也是自由的,但她的自由是單純、簡單和最基本的,二十歲還不會讀寫,不會使用餐具,整日赤著身子在家里走來走去,她似乎永遠停留在童年時代,生活單純簡單,自由自在。而白靈的自由從開始時的被一家人“寵慣著”,到后來接觸進步思想,追隨愛人的步伐加入共產黨,當白靈聽到“‘同志那聲陌生而又親切的稱呼時”,那種激情注定白靈將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一名革命者。
蕾梅黛絲與白靈相同,都熱愛自由,但白靈接受教育,通過學習,對世界形成了自己的認知,敢于大膽追求愛情和為信仰奮斗。白靈是新時期女性的代表,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為追求理想而努力和斗爭,在為推動社會進步中流血犧牲,正是女性意識覺醒的表現,在斗爭和改革中實現自我價值。其反叛意識和批判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女性,白靈短暫的一生,是中國婦女擺脫傳統封建禮教之束縛,邁向思想現代化歷程的標志。(張鐸,2014:136)
生態女性主義不僅是一種文學理論,更是一種社會運動。通過對兩部著作中女性角色的分析,能夠讓女性對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認識,并產生真正的自我認同,在面對種種挑戰時,不斷修正,不斷完善,展現女性的睿智,重建自己的社會身份,從男性的附屬中解放出來,掌握自己的命運,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從物質、生活和精神等各方面獲得自由,在社會生活中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范曄(譯),南海出版公司,第2版(2017)
[2]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強,譯.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195-196.
[4]張鐸.女性意識的覺醒—揭示《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6)
基金項目: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基礎科研項目“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白鹿原》與《百年孤獨》女性角色的比較與評析”(20101184831)
(作者介紹:辛冀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英語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