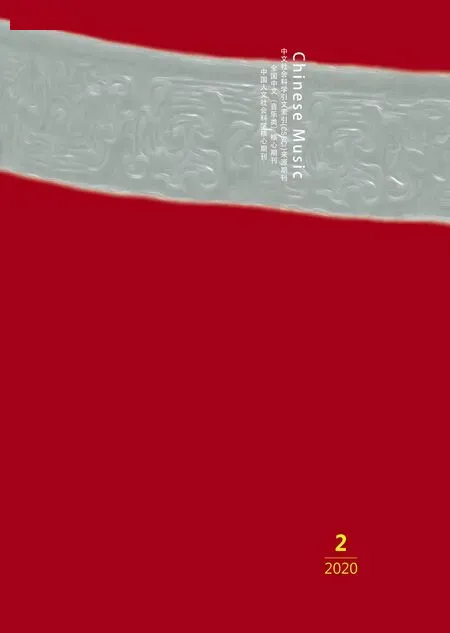風格樂派林立 爭艷走向未來— 中國第六屆西方音樂史年會綜述
2019年11月9-11日,中國第六屆西方音樂史年會在中國音樂學院召開。11月9日上午九點,在中國音樂學院國音堂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中國音樂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李秀軍教授擔任主持,全球音樂教育聯(lián)盟主席、中國音樂學院院長、第六屆西方音樂史年會組委會主任王黎光教授和中國西方音樂學會會長、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以及上海音樂出版社代表嘉賓楊海虹發(fā)表精彩致辭。王黎光教授在開幕詞中指出:“任何學術都應從比較開始,有比較才有哲學問題的提出,才有價值觀的提出。‘中國樂派’無法脫離全球音樂而獨生,對中國而言,全球音樂文化格局既是西方文化全球化之結(jié)果,也是中國文化世界化的契機。希望中國的西方音樂學者們從西方音樂的角度、從比較的角度,多關心、多關注‘中國樂派’的建設。引入先進的西方文化用以激活本土文化,從而引入創(chuàng)新,推動整個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本次年會從西方音樂研究的角度去破解‘中國樂派’的存在和建設的價值,希望這是一個重要的拐點,是一個理論上的新舉措。我們在進行中國音樂研究中只有不忘本來、吸收外來,才能走向更具魅力的未來。”
三天中來自國內(nèi)外的125名學者在兩個分會場做了精彩發(fā)言,他們以“西方音樂的風格流派”為主題,就西方音樂流派的成因、特點和影響,西方音樂流派的橫向和縱向比較研究,西方音樂風格史研究,西方音樂流派的經(jīng)典作品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地闡釋和研討,并對“西方音樂視野下的中國樂派”的建設、發(fā)展進行了有益探索。
一、西學前沿—歷史敘事的新思路
年會中一些資深學者對西方音樂史學科的發(fā)展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觀點,他們通過解讀史實,對西方音樂史研究進行新角度的介入和重新思量,從純理論探索向各個層面的音樂文化研究進行深入拓展,提出了對于學科發(fā)展具有一定前瞻性及國際性的觀點。
中國音樂學院李秀軍教授在其發(fā)言《21世紀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需要關注的思考問題》中,指出目前我們西方音樂研究中存在的兩大問題:我們一方面需要一定數(shù)量的西方音樂史學科中不同領域的有影響和具代表性的文獻,另一方面,我們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圍內(nèi)還沒有更多地引起對方專家的足夠關注和重視。并指出應該從基督教與西方藝術音樂的關系與問題,西方藝術音樂的文化特征問題,西方藝術音樂與歐洲各國各民族樂派間的交流與關系,西方音樂研究與研究者的“身份”關系問題,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五個方面去深入地思考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所面臨的歷史問題。
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教授的主題發(fā)言《德意志音樂崛起與發(fā)展的原因和啟示》,從歷史角度和宏觀視角再度回顧和反思德意志音樂的發(fā)展歷程。他提出,德意志音樂發(fā)展的引擎動力應是馬丁·路德,他是德意志音樂的重要奠基性基石。德意志民族長期分裂的割據(jù)局面,從某種角度促成了德意志音樂在各地的發(fā)展和發(fā)達,德意志作曲家群星璀璨,他們形成了各自鮮明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共同推動了音樂的發(fā)展,并保持了德意志音樂的高水平運作和整體文化氣氛的烘托與助力。其結(jié)論為:德意志音樂的一大特點是音樂從來不是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邊緣性娛樂,而是精神生活中的主體建構(gòu)成分之一,音樂文化也是他們的主流文化之一,并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
中央音樂學院班麗霞副教授在《先鋒派與音樂政治》的發(fā)言中提出:在描述20世紀西方音樂的幾個關鍵詞中,“先鋒派”(avant-garde)這一概念的歧義性絲毫不亞于“后現(xiàn)代主義”。在英美音樂學領域,先鋒派與現(xiàn)代主義基本同義,當學者試圖強調(diào)某位作曲家大膽突破音樂傳統(tǒng)時,便會換用“先鋒派”作為一種修辭。這種不加區(qū)分地混用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將一些持不同美學觀點和身份立場的作曲家混為一談。班教授指出,與先鋒派文學與視覺藝術相比,先鋒派音樂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以薩蒂與凱奇為例,真正沖擊藝術體制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音樂在歷史先鋒派運動中的邊緣性與溫和性,使其對音樂體制的沖擊微乎其微。當下,盡管先鋒性的實驗音樂依然存在,但已失去昔日的社會否定性,而退卻為后現(xiàn)代多元音樂文化中的一個維度。
浙江師范大學李晶教授在其發(fā)言《十九世紀“女性救贖”主題歌劇的創(chuàng)作特征與意義詮釋》中,通過對貝多芬的《費德里奧》、韋伯的《魔彈射手》、貝利尼的《諾爾瑪》、威爾第的《茶花女》、古諾的《浮士德》、瓦格納的《漂泊的荷蘭人》六部作品的分析與比較發(fā)現(xiàn),作曲家們?yōu)榱耸谷宋镄蜗笈c救贖主題相關聯(lián),在結(jié)構(gòu)布局、場景設置、人物關系、調(diào)性布局、動機設計、主題旋律、核心唱段、配器手法等各方面呈現(xiàn)出共通的處理方式與考量。19世紀歌劇“女性救贖”主題的出現(xiàn)并非一蹴而就的偶然現(xiàn)象,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鋪墊的。在西方音樂歷史上,可以看到“原罪”和“救贖”觀念在西方音樂中的強烈影響。
二、西方音樂風格流派:多元視角下的審美關照
西方音樂風格流派的多角度研究是本次年會的主題。與會學者從西方樂派史料的統(tǒng)計分析入手,厘清其發(fā)展脈絡,反思其機制成因,總結(jié)其風格特征,多角度、多層面地對西方音樂風格流派進行了深入討論,展現(xiàn)出多元的研究角度和廣闊的學術視野。
上海音樂學院孫國忠教授的發(fā)言《關于樂派若干問題的思考》指出,“樂派”通常指一個群體,而且這一群體中的作家、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風格或觀點受某一個人物或某種(共同)理念的影響。從這一特定意義來講,構(gòu)成“樂派”的作曲家群體是指在某種具有共識的(基本)藝術思想或創(chuàng)作理念下形成的音樂創(chuàng)作者的“聚合”,這種具有共性的“聚合”允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群體中的個人思想與具體的創(chuàng)作訴求。以此界定為參照,西方音樂史上的“樂派”是一個有特定指向的概念,而每一個“樂派”的形成與發(fā)展又有其歷史層面和藝術維度的獨特性。因此,對“樂派”的認識與解讀必須結(jié)合對西方音樂史特定藝術語境和創(chuàng)作背景的理解。嚴格地講,只有搞清楚“樂派”概念的明確含義及意義指向,其運用及對相關研究問題的闡釋才能真正顯示音樂史論話語的詮釋效力和學術價值。
上海音樂學院陳泓鐸教授的發(fā)言《論西方當代音樂中的流派及影響》,集中論述了西方當代音樂中的“樂派”及其影響。他對西方當代音樂中的“樂派”進行了梳理,對其一般概念做了概括,并辯證地指出西方當代樂派以特殊的音樂觀念和技法作為立派依據(jù)有失偏頗,樂派意識在西方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中央音樂學院呂常樂副教授的發(fā)言《北德樂派音樂風格形成的啟蒙思想與宮廷文化語境》從啟蒙運動所倡導的“回歸自然”與人文主義精神對“北德樂派”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思想的深刻影響,柏林宮廷的文化環(huán)境與作曲家音樂創(chuàng)作的密切關系,以及“北德樂派”音樂創(chuàng)作與理論著述對“情感風格”的體現(xiàn)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上海音樂學院博士后楊珽珽的發(fā)言《“非西方”視角觀當代音樂流派—頻譜音樂之過去—現(xiàn)在—將來》向我們展示了20世紀與21世紀當代嚴肅音樂創(chuàng)作所面臨的文化轉(zhuǎn)向和“聲音轉(zhuǎn)向”,給中國當代音樂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所提供的比對與參考。他指出:“21世紀已不再是‘西方文化中心’世界,傳統(tǒng)的國家、民族、地域等簡單歸因式單一思維,已無法面對這樣全球化的進程。只有以開放且積極的姿態(tài),對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多維視角的觀察與分析,才能深入理解這個瞬息萬變且多元融合的世界。”
中國音樂學院殷霞副教授的發(fā)言《自我表達與二十一世紀民族樂派》,分析了19世紀與20世紀民族樂派在“表現(xiàn)自我”方面呈現(xiàn)出的不同狀態(tài)。“文化中的歐洲中心已經(jīng)處于逐步消解的狀態(tài),更多不同類型的國家表現(xiàn)出建設民族樂派的傾向。20世紀民族樂派的諸多力量在表現(xiàn)自我的時候,與19世紀西歐國家的‘本能化民族性’和東歐國家的‘刻意化民族性’有所不同,它更尋求于自身專業(yè)音樂所具有的相當高度的獨特道路。”她認為,這是一個文化發(fā)展趨向于全球化、多元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前所未有地在“表達不同的聲音”的時代。我們應以“21世紀民族樂派”的態(tài)度在音樂領域表達我們的聲音,而“中國樂派”就是這樣一種努力建設的成果。
南京師范大學陳新坤副教授的發(fā)言《論新德意志樂派的形成》從社會語境、哲學觀念和音樂訴求三個方面對新德意志樂派的形成、意義及影響進行了分析和定位。此外,海外學者俄羅斯格涅新音樂學院博士宮子惠的《20世紀藝術的主要風格趨勢及其在蘇聯(lián)音樂中的表現(xiàn)形式》、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碩士孫嘉琦的《第二新英格蘭學派的藝術歌曲創(chuàng)作》、巴黎索邦大學博士杜超《抄襲之爭:瓦格納〈漂泊的荷蘭人〉與迪冀〈鬼船〉》、英國約克大學張亞歐博士《“邊緣性”視域下的布里頓室內(nèi)歌劇〈螺絲在擰緊〉》的發(fā)言,讓我們看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更開放的視角。中國音樂學院副教授康嘯則以新的視角論述了“新德意志派”與瓦格納的關系,著重分析了“新德意志樂派”的深層含義,并辯證地論述了瓦格納在其中的重要影響。其論證嚴謹,展現(xiàn)了中國青年音樂史學家的較高的學術水平。
三、作為文化研究范疇的西方音樂史
本屆年會展現(xiàn)了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跨學科的研究視角,一方面體現(xiàn)了中國學術研究的開放性心態(tài)和包容性思維,以及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當代音樂史學科跨學科研究的大潮流和趨勢,學科與學科之間發(fā)生關聯(lián)的可能性越來越多地在音樂研究中體現(xiàn)。
中央音樂學院劉經(jīng)樹教授在《跨文化音樂學》的發(fā)言中指出:“跨文化不僅破除了西方中心論,也給音樂民族學提供了更寬泛的角度。奧爾蒂斯歷史觀下的古巴文化,指多種民族文化在古巴的交融體。音樂民族學在考察有移民或殖民地因素的地區(qū)文化時,應該站在跨文化的高度,來考慮各個民族在文化里的反映,它是在這些地區(qū)產(chǎn)生的全新文化。”他的發(fā)言站在跨文化的高度看歷史,破除了歷史編纂學中始終貫穿的西方中心論。
福建師范大學葉松容教授在發(fā)言《“文化自覺”理論視域下的西方19世紀民族樂派》中認為,文化自覺,尋求其作為人類社會共同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普適性意義,進而豐富了西方19世紀民族樂派音樂的文化內(nèi)涵,并將“文化自覺”理論賦予世界性的意義。他以費孝通倡導的“文化自覺”理論為視域,以接受美學為立論出發(fā)點,探尋西方19世紀民族樂派音樂的解釋意義,揭示了西方19世紀民族樂派音樂創(chuàng)作中所蘊含的理論關注點。
上海大學音樂學院洪丁教授的發(fā)言《印象主義的風格濾鏡:西方音樂史學流派研究的一種反思》從文化互文及接受史角度出發(fā),通過對印象主義音樂風格在歷史中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并觀察這一流派形成的內(nèi)在及外部因素。他不僅界定概念中的印象主義“理念原型”,還指明這一流派在歷史發(fā)展中被賦予的層層風格濾鏡。
上海音樂學院伍維曦副教授在《被建構(gòu)與想象的樂派—以19世紀法國政治與音樂為例》的發(fā)言中,以19世紀法國政治體制與音樂活動的關系(尤其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來說明“文化樂派”的發(fā)生機制及其與主流音樂風格的關系,并為未來我國學院派音樂文化事業(yè)的建設提供參照與啟示。
中央音樂學院劉小龍副教授的發(fā)言《對貝多芬〈田園交響曲〉標題性特征的跨界闡釋》論述了貝多芬為這部交響曲賦予文字標題的創(chuàng)作目的和內(nèi)心矛盾,進而對作曲家藉此表達的獨立藝術觀念進行跨界闡釋。中央音樂學院潘瀾教授在其發(fā)言《論西方音樂風格的雙重特性—技術性與藝術性》中,借助哲學、歷史學、音樂學等人文學科理論,探究西方音樂風格技術性與藝術性雙重特性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他通過實例對樂譜進行認知與感知的分析,同時結(jié)合傳統(tǒng)的樂譜技術和音響分析,對音質(zhì)音色、音勢動態(tài)、韻律、聲音層次等各個要素之間的關聯(lián)性加以研究,從而將音樂風格的藝術性注入技術性中,并使藝術性有了較為可信的技術性分析作為依據(jù)。他希望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研究,使人們能夠同時關注音樂風格的多種維度,削弱技術模式化程度,更加關注音樂風格藝術性方面的研究,從而讓西方音樂風格既具有理性的認知,又具有人性的感知。
中央音樂學院何寬釗副教授在《連續(xù)性、總體性還是間斷性、偶然性—對文藝復興音樂中兩個問題的歷史哲學分析》的發(fā)言中提出了兩個問題,15世紀意大利為什么不是引領者?半音主義為什么曇花一現(xiàn)?并對問題進行了哲學性的分析。他指出:“人文主義作為一個總體性的時代精神,生發(fā)于意大利,意大利理當在各個領域擔當引領者。然而在音樂領域,意大利卻并未成為引領者。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預設,在間斷性的反思和批判性精神拷問下,上述現(xiàn)象便與歷史主義的總體性相抵牾,構(gòu)成一種深刻的歷史悖結(jié)和裂縫。文藝復興的‘半音主義’和19世紀晚期的半音化具有明顯的區(qū)別,后者是這條連續(xù)性上的有機展開,而前者則是這股連續(xù)性上的小小岔道,不符合向調(diào)性音樂邁進的連續(xù)趨勢,難以構(gòu)成和聲演變軌跡上的有機一環(huán),于是曇花一現(xiàn)。”
會中大量論題涉及“作為文化研究范疇的音樂史”,展示了近年來西方音樂史發(fā)展的新方向,即通過對作品、作曲家文化遺存的研究,深入人類文明內(nèi)部探尋文化問題。這也是西方音樂史學界對打破學科藩籬,吸收其他學科研究成果,進行交叉學科研究的呼吁所做出的積極回應。
四、西方樂派視野下“中國樂派”的本位、傳承、融合發(fā)展思路
中國近代發(fā)展的百年中,西方音樂理論與實踐中的行為活動秩序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與指導。文化交流的目的,在于互通有無,在于關注借鑒外來理論的本土化問題和具體語境,形成文化互補。更深層的意義則在于引入外國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從而引入創(chuàng)新,推動整個文化的發(fā)展。本屆年會通過研究西方音樂流派的孕育、傳承、演變、繁榮、衰敗過程中的潛在規(guī)律,梳理音樂與政治、藝術家與贊助人、流派傳播與市場經(jīng)濟、流派領袖與追隨者、流派演變與觀眾接受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自我、認知自我,依托“一帶一路”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契機,將西方、東方各民族音樂的經(jīng)典納入我國音樂學科發(fā)展之中,用以構(gòu)建“中國樂派”。這是本屆年會的核心要義。
杭州師范大學王晡教授在主題發(fā)言《風格、樂派和“中國樂派”》中,厘定風格的概念及構(gòu)成要素,樂派及其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音樂極簡史,維也納古典樂派等論題。他認為用風格來定義音樂歷史是有價值的,風格史是一種有效的史學方法。他指出,新世紀就史家治史的基本理念、史著與音樂客觀存在的關系、作品在音樂史中的地位而言,風格史仍然是最符合歷史實際、直截而明晰的一種音樂史類型,這種觀念也是研究風格與流派、學派、樂派之間關系的基礎。
中國音樂學院博士后鐘卓文的主題發(fā)言《我國在和聲民族理論進程中對蘇俄學派的的接受》,通過梳理我國在和聲理論民族化進程中對蘇俄和聲學派的接受歷史,從政治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因素、美學思潮等多個層面探討并論證不同時期我國對于蘇俄和聲理論的接受契機及深層次原因,從中總結(jié)中國音樂學者自我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并為之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理論依據(jù)。
西南科技大學田彬華副教授在其發(fā)言《中國樂派時代何以自處?》中,分析了研究西方音樂的中國學者的學術定位。他指出:“爭論是否有‘樂派’的存在沒有多少意義,積極地構(gòu)建參與才是勇于承擔學科責任和擔當?shù)捏w現(xiàn)。其中,作品、作曲家的研究是最為關鍵的。對我國近代以來經(jīng)典作品的重新審視過程中,需要脫離各種有意無意地外在遮蔽和干預,從藝術角度重新進行經(jīng)典化構(gòu)筑—‘經(jīng)典’也需要被主動構(gòu)建。”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畢明輝副教授在《“中國樂派”如何登場?》的發(fā)言中指出:“中國當代尤為強調(diào)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我們有必要細致研究西方樂派產(chǎn)生、發(fā)展、興盛、漸落的歷史過程,從中總結(jié)經(jīng)驗。除音樂作品本體研究外,其相關理論研究,尤其是對有關‘樂派’的產(chǎn)生、發(fā)展、變遷等精神層面的軌跡予以梳理并總結(jié)經(jīng)驗,都應是我們所關注的內(nèi)容。”
中央音樂學院姚亞萍教授在其發(fā)言《音樂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中,分析了音樂現(xiàn)代性的三個階段后指出,“樂派”是一個音樂現(xiàn)代性現(xiàn)象,后現(xiàn)代時代已經(jīng)不可能產(chǎn)生樂派。隨著大師時代的終結(jié),作曲范式難現(xiàn),音樂不再代表某種群體(或階層)的意志,樂派失去了生長的土壤。“中國樂派”是作為西方之外的另一個參照提出的,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后現(xiàn)代現(xiàn)象。姚教授指出,建設“中國樂派”重要的不是這個概念能否成立,是否能得以實現(xiàn),而是要將其作為一個后現(xiàn)代“事件”去關注。“中國樂派”的意義在于提出這個概念本身,它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這種“事件”在音樂現(xiàn)代性時代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它應該被視為一個后現(xiàn)代標識,目的是跳出西方音樂為主的參照體系,建立具有鮮明民族性和時代性的中國音樂體系。
結(jié)語
在為期三天的會議研討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圍繞大會議題進行了熱烈而自由地討論。不僅有對西方音樂史上“樂派”的探討與分析,也有對“中國樂派”的反思與爭鳴;既有對西方音樂史發(fā)展及“中國樂派”建立的宏觀俯瞰,亦有對個案作曲家作品及流派的近距離觀察;既有對傳統(tǒng)話語的解構(gòu),亦有對于某一位音樂家及音樂作品的深入解讀;既有以古窺今的反思,亦有全球化視野下的觀照。
閉幕式上西方音樂史學會會長楊燕迪教授做了總結(jié)發(fā)言,他指出:“我們在以積極的姿態(tài)回應時代的需要和中國音樂發(fā)展的驅(qū)動,我們配合和支持中國音樂學院的辦學理念,從學理層面來切入中國音樂學院所提出的構(gòu)建‘中國樂派’的學術構(gòu)想和主張,我們希望以更為寬闊的視野和全方位的視角來開展音樂流派、樂派、風格以及內(nèi)在機制的研究。”
這是一次高效的學術成果的碰撞、交融與匯聚,是一場學術思想的盛宴。習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fā)展。”與會學者在對西方音樂風格流派及“中國樂派”發(fā)展的深入探討中所滲透出的創(chuàng)新性,必將成為中國音樂研究新的理論和方法的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