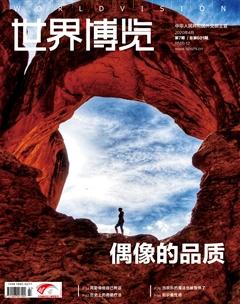口罩污名
施越

當地時間2020年3月22日,日本東京北之丸公園櫻花綻放,游人漫步櫻花林。
1月23日,除夕夜的前一天,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武漢宣布“封城”。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意大利的一家公司里上班,心思卻早已不在工作上。國內已經在大幅度宣傳佩戴口罩可以有效減少被病毒飛沫傳染的風險,需要買點口罩嗎?一整天,我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相比自己,我更多地擔心的是國內的親人,此時,國內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口罩短缺現象,不僅在電商上重金難求,真正能夠防御新冠肺炎病毒的口罩更是少之又少。我叮囑父母,只有戴了口罩才能出門,過年的聚會盡量取消。出于謹慎考慮,我還是在網上訂購了50個醫用外科口罩和20個N95口罩,在歐洲尚未有病例報告的情況下,口罩在歐洲已經出現了缺貨現象,貨運提示我,一個月以后才能收到這些口罩。現在想來,這真的是我今年迄今為止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
口罩難題
隨著國內的疫情發展愈發嚴重,歐洲各國也陸陸續續有病例報告,一些華人根據國內預防病毒的建議,率先戴上了口罩出門。沒想到,這種行為卻引發了歐洲當地人的不解和恐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居住在歐洲的華人和當地人之間的平和狀態。
歧視華人的現象在歐洲各地愈發多地涌現出來,華人被辱罵、被房東驅逐、商店拒絕華人進入、華人餐館客流大幅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無故的暴力行為。在米蘭,一個視頻在網絡上廣泛地傳播:在擁擠的地鐵車廂里,一個華人男孩坐在座位上四處張望,他的周圍空蕩蕩,沒有人敢坐在他邊上,也沒有人敢站在他周圍。所有的外國人都擠在離這個男孩一米遠的地方緊張不安地看著他,和這個男孩臉上浮現出的天真與不知事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說,新冠肺炎成為了一些道德敗壞的人實行種族歧視的借口,那么口罩就成為了這些人標榜種族歧視的佐證。不僅是華人,許多佩戴口罩的亞洲人都成為了歧視的目標。在意大利都靈,一個戴著口罩的華人女生被推下公交車;在米蘭,一個戴口罩的日本女生被人推搡。所有華人,或者所有深知這場疫情嚴重性的亞洲人都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果不戴口罩出門,就會有被病毒傳染的風險;如果戴了口罩出門,就可能會遭遇種族歧視。我們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呢?戴口罩這件事,怎么就不能被接受了呢?
盡管在中國,甚至包括日本和韓國,醫生普遍建議大家戴口罩來抵御新冠肺炎的飛沫傳染,但是在歐美國家,醫生卻認為戴口罩不一定能夠起到抵御病毒的作用。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只有在出現COVID-19癥狀(尤其是咳嗽)或照顧可能感染COVID-19的人時,才需要戴口罩。一次性口罩只能使用一次。如果未生病或未在照顧病人,那么戴口罩便是浪費。”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生病或者不會接觸到新冠肺炎病人,那就不用戴口罩。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怎么能夠確保我們在外出活動時,不會接觸新冠肺炎病人呢?更何況,許多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并不會出現任何癥狀,也有許多病人,將它和普通流感混為一談。正是這一點,被許多歐洲人所忽視,導致了他們認為戴口罩沒有必要的想法。
除此之外,由于歐洲的大部分口罩來源都依靠中國的工廠,本土口罩資源稀缺。在中國國內疫情暴發時期,口罩供不應求,大量的海外華人盡其所能采購口罩捐贈回國,大大影響了歐洲藥店里的口罩存貨;隨著歐洲疫情的暴發,歐洲的醫院也同樣面臨著口罩短缺的局面,因此政府呼吁普通民眾盡量把資源優先讓給醫院。
從文化角度上來說,生病戴口罩,在亞洲人眼里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在流感期間,戴口罩不僅可以防止被他人傳染,也可以避免自己傳染給別人。除此之外,冬天戴口罩可以防風、外出戴口罩可以防霧霾、臉上過敏了戴口罩可以遮瑕,甚至亞洲娛樂圈的一些明星,也會把口罩當成一種時尚來搭配。口罩,對于亞洲人來說有著豐富的功用和含義,但是對于歐洲人來說,口罩一般都只和疾病掛鉤。歐洲最早的口罩可以追溯到一世紀,當時的長老林普尼使用動物的膀胱皮來保護羅馬礦山的工人免受氧化鉛紅塵的侵害。到了14世紀,歐洲黑死病暴發,治療黑死病患者的醫生會佩戴一種鳥嘴面具來保護自己。這種面具在眼睛處裝有透明玻璃,用來隔絕患者的血液和飛沫;面具前段的鳥喙內會填充龍涎香、蜜蜂花、樟腦等散發芳香的物質,用來保護醫生免受瘴氣的侵害。
如今,在現代歐洲,在人們的普世價值觀里,只有醫生和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因此,當人們在大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人,就會下意識地把他當作是一名病患。如今,面對大量的亞洲人集體戴上口罩,他們出現了不安和恐懼的現象可以理解,但不幸的是,這種文化差異也進一步地加深了“亞洲人和病毒之間的關系”的成見。
至此,口罩被貼上了“社會污名化”的標簽,無論你出于何種理由佩戴口罩,所有戴著口罩的個人或者群體都被迫和新冠肺炎“聯系在了一起”,并且受到歧視和孤立。新冠肺炎是對于全人類來說都是一種未知的恐懼,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誕生的,也沒有人知道它什么時候才會結束,更沒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在不經意間被感染上。在歐洲,這種對于未知事物的恐慌很容易地就被轉化為了對戴口罩的人的恐慌。
許多華人為了避免被歧視、孤立,只能選擇脫下口罩。這種行為或許也能解釋為什么許多歐美人在明知新冠病毒感染性極強的情況下,依然不愿意佩戴口罩。為了避免遭受“社會污名”,許多密切接觸過感染者的球星、演員、官員,在公眾面前堅持參與公眾活動、堅持拒絕佩戴口罩,堅持表示無畏于病毒,而最后被證實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社會污名化”在這種情況下加劇了病毒在社會的傳播,最后只有面對現實的慘狀之后人們才遲鈍地蘇醒,但已經來不及了。
“社會污名化”的轉移
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當意大利成為歐洲首個疫情暴發的國家之后,歐洲針對華人的歧視轉變為了針對意大利人的歧視。作為一個天性自由、熱愛到處奔波社交的民族,意大利在疫情暴發初期并沒有重視病毒,也沒有意識到新冠肺炎可怕的傳染性,許多感染病毒卻不自知的意大利人在不經意間將病毒帶到了意大利的周邊國家,引發了歐洲國家的強烈反感。意大利早在1月就成為了全歐洲第一個禁止中國-意大利直飛航班的國家,令人想不到的是,它很快也成為了全歐洲第一個被其他國家禁止航班和火車入境的國家。有些人在1月用中餐編造低級的新冠肺炎段子,在2月就用意大利披薩編造了同樣令人惱火的段子。法國的一家電視臺制作了一個含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視頻:一個意大利廚師從烤箱里拿出了一塊意大利披薩,接著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一塊綠色的分泌物滴落在披薩上。隨即,視頻上出現了這樣的字幕:新冠肺炎披薩,在世界傳播的新型意大利披薩。在倫敦,一所中學突然宣布需要關門兩天,進行“深度消毒”,原因是“有些學生來自意大利”。一個意大利人在社交媒體上抱怨,她在倫敦的一座巴士上接電話,用意大利語說了幾句話以后,坐在她前面的乘客突然用圍巾蓋住了口鼻。

14世紀歐洲治療黑死病患者的醫生佩戴鳥嘴面具來保護自己。面具在眼睛處裝有透明玻璃,用來隔絕患者的血液和飛沫;面具前段的鳥喙內會填充龍涎香、蜜蜂花、樟腦等散發芳香的物質,用來保護醫生免受瘴氣的侵害。
然而,在意大利本土,也同樣出現了“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間的地域歧視。疫情初期,新冠肺炎僅在意大利北部暴發,一部分北方人逃往意大利南部,同時也將病毒帶往了意大利南部,引發了意大利南北方人之間的強烈爭端。僅在普利亞大區,就有15%從北方逃回來的學生將新冠肺炎傳染給了自己的家人。一邊是以經濟最發達的米蘭和威尼斯為首的北部,一邊是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為首的意大利資源最充沛、風景最秀美的南部。在南方人的刻板印象中,北方人勤奮傲慢;在北方人眼里,南方人自由散漫。北方人將南方人稱之為“農民”,南方人將北方人蔑視為“吃玉米糠的”。地域歧視問題本身就是意大利長久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在疫情的沖擊下,南方人終于在長久以來的經濟劣勢下揚眉吐氣,理直氣壯地拒絕擁抱從疫區出逃的北方人。“社會污名化”的影響也最終同樣出現在了意大利本土,那些接觸過確診患者的人們不敢聲張,隱瞞接觸史,在意大利完成了跨越全國的大遷移,最終將新冠病毒散布到了意大利全國。
意大利人一邊在網絡上和別國的網民爭吵,一邊終于開始反思過去的排華行為。我的一個同事分享了一家意大利媒體翻譯的武漢抗疫紀錄片視頻,在社交網站上寫道:“我們應該清楚兩件事:這個世界沒有邊界,新冠肺炎不是任何人的錯,沒有人有過錯。”只有真正在這場疫情中親歷過種族歧視與“社會污名化”的人,才會真正地、深刻地體會到,什么叫作“病毒沒有國界”。這場疫情帶來的不僅是世界性的人間悲劇,更揭開了虛偽者的面紗。疫情帶來的謠言和歧視的傳播速度比新冠病毒本身更加迅速,兩者如同病毒的左右副手一般瓦解著整個世界對于抵抗病毒的凝聚力。3月7日,意大利倫巴第政府拋開成見,成為了第一個呼吁民眾佩戴口罩的地區。一個星期以后,街上半數人都戴起了口罩。口罩終于擺脫了成見的標簽。
戰勝困難的共同力量

當地時間2020年3月19日,意大利米蘭,人們進行戶外運動。
3月12日,首批支援意大利的中國醫療團到達了羅馬機場,這則消息在網絡上受到了意大利網民的熱烈反響。這批醫療團,是來自四川華西醫院的醫護人員。他們向意大利人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88年,意大利政府曾經援助四川修建了一個急救中心;2008年汶川地震,意大利派了14名急救專家支援汶川,在專家的幫助下,有900名傷員轉危為安。這次馳援意大利,四川是為了報恩,并且做好了在意大利長期奮戰的準備。
許多意大利人表達了對中國的贊賞和感激,感謝中國在疫情面前向意大利伸出援手。在社交媒體上,人們找出一個月前中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的經驗和視頻,作為榜樣宣傳。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劇烈波動正在不斷地撞擊著所有地區、所有人的經濟、觀念、文化和生活的屏障,全人類應當攜手一起面對這場危機。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那可以引用一句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詩,這句話被寫在了中國支援意大利的物資貨箱上:“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