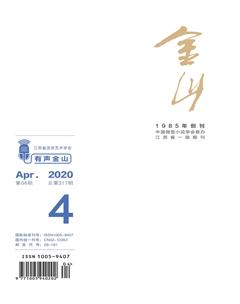夢溪園前的那條河
徐蘇
最近到夢溪園又轉了一圈,里面的變化不大。雖然規模上有了一些擴容的跡象,但想恢復到當年夢溪園的鼎盛狀態,可能不容易了。倒是出門時,腦海里突然想起了大運河申遺的事,想到這里也曾是大運河流經鎮江老城區的一個支流小段,流傳過許多動人的故事。
歲月滄桑,夢溪園門前那條碧波蕩漾、舟筏往還的河流,早已變成了車流不息的道路,兩邊的建筑也變得高大了許多。在對面江蘇大學夢溪校區的映襯下,當初雄偉的夢溪園門墻似乎被縮微了,路邊亦很難找到古運河的痕跡,只有憑記憶來想象那條曾是小舟戲水游歷,兩岸槐柳成蔭的河流了。
在我的記憶中,流經夢溪園前那段運河俗稱“上河邊”,河邊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道相沿。這里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宋代大科學家沈括的夢溪園。夢溪園的來歷頗為有趣,在沈括“自志”中說:他30歲時夢見過一個地方,山清水秀,花木似錦,古柏參天,心里一直向往到那里定居。過了20多年,他遭貶路過鎮江,見到一座小木橋畔風景秀麗,有山、有水、有石、有樹,宛如夢中所見,于是“吾緣在是矣”!放棄了去建陽安居的想法,落戶京口,修了夢溪園。夢溪園占地約10畝,整個庭園依山緣溪而筑,園中花叢翠竹環繞,亭臺樓閣點點,有夢溪泉、百花堆、殼軒、岸老堂、蒼峽亭、竹塢、杏嘴、蕭蕭堂、遠亭、深齋等景點,顯得十分幽雅。尤其是百花堆,艷而不俗,香氣四溢,被宋代詩僧仲殊推為京口十景之一。夢溪園旁邊的夢溪橋也曾是與運河相映成趣的好地方。
夢溪園與壽丘山相鄰,蕩漾的運河水從中間流過,山水相依,景色秀美。不僅沈括看上了這里的風景,北宋宰相陳升之也把宅園建在了離壽丘山不遠的地方。他的宅園華麗而靜幽,很有品位,就連沈括這樣有閱歷的人,見過后都發出了驚嘆。《夢溪筆談》中說:“公治第極宏壯,池館綿亙數百步”,可惜宅園建成后,園主已病重,不能行走,只是由家人們用轎抬上西樓一覽而已。后人趣談此宅園“三不得”,即住不得、修不得、賣不得。清代的大書法家王文治在沿河的小道踏青時,也喜歡上這里山光水色的美景,在河邊修建了一座“柿葉山房”,作為自己臨摹書法,撰寫詩文,創作劇曲的佳處。
到了清末時,這里運河沿岸的房屋還保持著過去的古趣,一排排青磚小瓦,高低不齊的建筑,在大小槐樹的點綴下,看上去卻也自然有序,只是附近的鄴林園找不到了。聽年長的人說,運河邊修建的鄴林園景色宜人,是文人雅集的場所。園主夏鄴林是鎮江一個頗有名氣的讀書人,貢生。他的詩和書法都不錯,著有《十硯齋詩抄》等。他修筑的鄴林園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獨立園林,里面山石水溪,古木名花,半亭短廊,參差錯落,整個園林顯得非常的秀氣。園中的水溪名曰“梅溪”,溪上建有一閣,題為“十硯齋”,里面存放著主人精心收集來的十方名硯。溪旁筑有桐蔭閣。鄴林園內相傳有八景,分別是“范橋春水”“花塢夕陽”“ 水榭觀荷”“平臺啄茗”“竹院秋風”“蕉窗夜雨”“梅溪晚煙”“蓬門積雪”。 主人還分別為園中的八景題了詩,如《范橋春水》詩云:“范橋跨東隅,一水年年碧。前沿沈括溪,后通刁約宅。照眼桃花鮮,早潮已三尺。” 清代京口“中七子”之一的張崇蘭就住在 “雨余溪水到門斜,恰好居鄰沈括家”的地方,他對鄴林園景色觀察很仔細,寫過有名的《十硯齋游記》,其中這樣描述:“夢溪南流,過范橋水漸寬,衍岸益平曠,有土阜叢木與民居相雜。夏君鄴林買廢宅而新之,疏泉編籬雜事蒔竹樹,面溪背市,結構疏簡,屋成取所蓄十硯實其中,命之十硯齋……余嘗月夜過之,月河西傾,極目寥闊,隔溪燈火遠出,深樹游魚唼波,與草蟲相間,忽忘其身之猶在城市也……”
這里從熱鬧的程度來看,雖不如過去的運河千秋橋段繁榮,有“青苔寺里無鳥跡,綠水橋邊多酒樓”的說法。但在我的記憶中,這段小道靠著東門坡,連著五條街,道上分布的小店小鋪也不算少,路人來來往往,只是到了晚上,這條小道就顯得荒涼,經常是漆黑一片,沒有路燈,很少有人行走。這段運河同千秋橋段差不多,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多看過河水的清澈,體驗過嬉水的樂趣。雖然當時河道變化,水面變淺,已不能適應運輸的需要,基本上看不到木船來往,但木筏子還是有的。有時趕上大潮,或是下大暴雨時,這里的水流仍較為湍急。
舊時的運河邊上多石階,一層一層地向水中延伸,方便岸邊的人們取水,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除了井水外,運河水就是附近人們飲水和用水的來源。過去運河的水用水桶挑回家后,若洗衣服一般都直接用;若飲用的話則有一個凈化的過程,先倒在水缸里,會放上一點明礬,用木棍輕輕地攪拌一下,水立刻清澈見底。經過凈化的水燒開后是沒有什么異味的,窮人家的孩子喝不起茶葉茶,但也有自己的享樂方式,他們會拿來一些刺槐樹上的花瓣放在碗中,注入開水后,一碗帶點甜味的大碗茶也能喝上個半天。
運河邊的石階上也曾是婦女和孩子們忙碌的地方。婦女們喜歡蹲在這里洗菜淘米、洗衣刷褲,棒槌聲此起彼落。那些常年用來洗刷衣褲的石塊,看上去非常的光滑,只要不是在烈日照射下,光腳踩上去是涼蔭蔭的,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孩子們把岸邊的石階作為游樂的地方,在這里盡情嬉水,他們中有人把手伸到石板下去摸螺螄;有人拿淘米籮到水中去撈小魚小蝦。有的稍大一點的孩子拿著竹竿,在竿頭粘上面筋去捕捉運河邊老槐樹上的知了;也有的孩子會借運河來比賽技巧和臂力,找來破碎的瓦片在河面上打水漂漂,看誰擊起的水圈最多、最遠,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在運河畔長大的城里孩子,同樣可以享受到鄉下孩子嬉水的樂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時運河邊水草茂盛,里面藏了不少青蛙、魚蝦等。人一到河邊,青蛙就像跳水的英雄,一個接一個地跳入水中。所以我們喜歡在運河邊小跑,看驚起的青蛙不停地跳躍取樂。河邊抓魚的人也多,常常看到有人光著腳丫在河邊水草中摸魚,而不會游水的孩子喜歡待在岸上看熱鬧,不過,如果運氣好,岸上的人也有收獲的機會,我就曾經捉到一只受驚嚇爬上岸的烏龜,得意洋洋地帶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