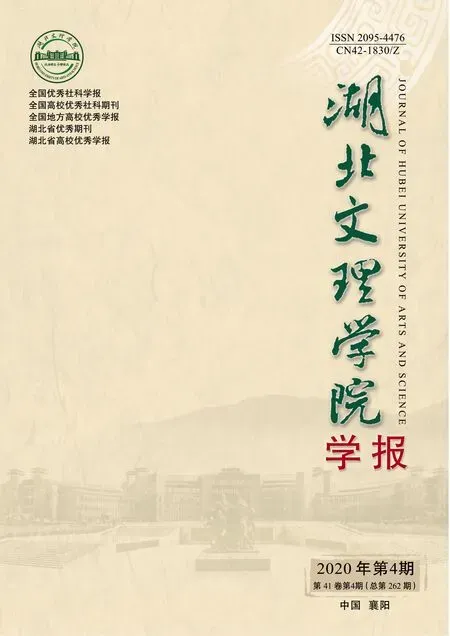疫情防控中志愿者的法律保護
牟糖醇
(北京理工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定義為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1]。在這其中,重大傳染病疫情以其傳染性強、傳播迅速、波及范圍廣、發病率異于普通病癥等特點,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重點關注。因此,本文以防控新冠狀病毒肺炎為研究背景,探析志愿者法律保護途徑。
一、疫情防控中志愿者法律保護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志愿者立法狀況
《突發事件應對法》主要明確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責,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規定為鼓勵積極應對并提供幫助。并未開展十分詳細的說明。
域外志愿者服務立法中,美國制定了志愿服務法[2]。日本在《志愿活動保險》中將“傷害事故”定義為突如其來的傷害,其中包括傳染病傷害,將“賠償事故”定義為造成他人損害提供的賠償。對比國外法律實踐,我國目前欠缺關于突發事件志愿者保險保障的立法[3],現行有效的法規中,只有志愿者服務條例對此做出了說明,缺乏高位階統一立法。
(二)非注冊志愿者的地位
武漢志愿者車隊一名成員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幸去世(1)參見澎湃新聞:武漢一志愿者感染新冠離世,曾稱“有一份力量就出一份力量”.ht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75060.,這種民間自發形成的志愿者團體是否在志愿者法律法規所保護的范圍之內?筆者選取國務院發布的《志愿服務條例》作為重點進行分析說明。
志愿者的定義分為廣義觀點和狹義觀點。廣義觀點包含非注冊登記和注冊登記的志愿者,而狹義觀點僅包含注冊登記志愿者。《志愿服務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志愿者可以參與志愿服務組織開展的志愿服務活動,也可以自行依法開展志愿服務活動。”[4]參與志愿服務組織的為注冊登記志愿者,而上文提到的武漢志愿者車隊,則是條文中自行依法開展志愿服務活動的非注冊登記志愿者。由此可見,我國在統一的全國性行政法規中明確了非注冊志愿者的地位。
(三)志愿活動中侵權責任歸責原則
2020年2月20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事司副司長段勇表示:“一線醫務人員臨時工作補助發放的人員范圍,不受編制、身份等限制,以具體參加實際工作為準。”[5]2020年3月5日,一份名為“我們也是醫護人員,武漢醫護志愿者尋求身份認可”的報道[6]訴說了來自民營醫院醫護志愿者的心聲,他們渴望獲得有關部門給與的“醫務人員”身份的認可以及工作補助。
那么醫護志愿者是否與醫護人員享有同等身份?疫情期間,患者入住公立醫院卻接受志愿者醫護人員的治療照護,若引起醫療糾紛,是否可以參照醫療侵權糾紛進行歸責?還是按照不當得利進行賠償?然而我國志愿服務條例尚未對侵權責任主體做出詳細清晰的說明。
筆者參照日本志愿者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做簡要說明。根據日本民法第709條,當發現志愿者有侵權行為時,該志愿者就是責任主體。若該志愿者是注冊登記志愿者,則根據日本民法第715條,志愿組織應對受侵害方負責。如果該志愿組織是非營利組織(即NPO公司),則由NPO公司對受侵害方負責。如果承擔侵權責任的志愿者是NPO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則根據日本《非營利促進法》第8條對侵權行為承擔責任。[7]
(四)志愿者保險購買情況
我國志愿服務條例規定志愿者在從事可能影響人身安全的志愿服務活動或大型社會公益活動時,應當為其購買保險。然而對于購買的險種、保險時長、保險繳費額度并未做詳細規定。
此外,在突發事件志愿服務活動中受傷或死亡的志愿者,志愿服務組織和突發事件發生地政府是否應該提供醫療費、喪葬費,亦或是將志愿服務納入社保體系?
《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視同工傷”[8]。然而我國目前沒有統一的突發事件志愿服務立法,志愿服務條例中也未明確說明。那么,醫護志愿者被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否能定為工傷,這一問題的解決可以參照域外法律規定。
法國將志愿者分為兩類:無償志愿者和帶薪志愿者。前者不被視為工人,后者根據志愿者法而受到約束。例如,如果帶薪志愿者被派遣到非洲進行國際合作,則可向帶薪志愿者提供長達6年的病假、產假等福利。匈牙利在2005年頒布了《志愿者活動法》,非營利組織和志愿者必須簽署合同并向主管部門登記。如果注冊受傷或發生意外,NPO也應賠償;如果志愿者在活動中對第三方造成損害,則NPO也應承擔責任。[9]日本工傷保險僅部分志愿者可適用,例如:在足球比賽中受傷的志愿者可視為工傷,并規定在18個月間可獲得失業保險,社會保險和工人賠償保險。
日本的志愿者保險中也有值得借鑒的地方。由日本社會福利理事會作為聯絡點的志愿者保險計劃于2004年提供的責任保險,每次事故的最高限額為5億日元。當前,存在針對受傷的志愿者的事故險以及對傷害他人的志愿者侵權責任的多種類型志愿者保險。[9]
(五)志愿者救濟途徑
《志愿服務條例》并未明確規定糾紛產生后,如何解決糾紛。志愿者活動中,如若發生摩擦訴至法庭,志愿者們可能會由于繁瑣的訴訟程序和令人望而卻步的律師費而忍氣吞聲不再維權[10],甚至不會再參與志愿者服務活動,這顯然不利于我國志愿服務事業健康蓬勃的發展。政府是否應為他們提供法律救濟,則是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二、志愿者權益保護的必要性
(一)憲法規定保障人權
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11]志愿者作為公民,國家應當保障其基本的權利,即: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以及其他私人權利,這些都是人權所涵蓋的內容。國家應當依法提供保障。
(二)基于無因管理的求償權
無因管理是指市民在沒有義務或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將助人為樂等優秀道德品質法律化的行為。筆者認為在衡量如何保護志愿者權益時應當參照無因管理的求償權來解決此問題。羅馬法中曾記載:“自己享有利益者,使他人負擔損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說,在無因管理活動中,如果管理人基于此受到損害或支付了必要的管理費用或替本人償還債務,則本人應當對管理人進行必要的賠償或補償。如果這些費用都由管理人承擔,這樣顯失公平。在志愿者服務活動中,志愿者為管理人,被服務對象為本人。雖然志愿者的志愿服務是出于自身意愿,但在志愿者服務活動中產生的費用和損失是無法預料的,全然不顧志愿者的支出與損失,長此以往難免會削弱志愿者投身社會服務的熱情,淡化疫情當前急速凝聚起來的正能量。所以基于無因管理的求償權,保護志愿者權利迫在眉睫。
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第1163條規定:管理人因管理本人事務遭受人身傷害的,如果管理行為是為了本人的生命健康利益,本人應賠償全部損失。[12]疫情期間的醫護志愿者是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而投身志愿服務活動中,若他們遭受人身傷害,筆者認為則患者有義務賠償其全部損失。
(三)基于侵權責任法的損害救濟權
侵權請求權是一種救濟權,當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受到侵犯時,應當予以優先救濟。設立侵權請求權優先權,能夠保障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幫助他們得到及時救濟,使之盡早恢復原狀,而且設立侵權請求權優先權還彰顯了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中的人道主義精神。
《民法總則》第183條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13]第三人對志愿者(管理人)的賠償義務,以及本人對志愿者(管理人)的賠償義務將成立不真正連帶責任。基于侵權責任法的損害救濟權,志愿者受損害時應當得到法律救濟。
(四)基于無因管理與基于侵權責任法的差別
首先,賠償條件成立前提不同。在無因管理中,只要管理人在管理活動中遭受損失,就可以向本人請求全部賠償。而《侵權責任法》第23條規定只有當第三人侵權行為成立且第三人存在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的情形時,受益人才承擔補償義務。
其次,兩者對于管理結果的要求不同。無因管理不要求管理結果一定利于本人,即使管理行為全無效果,管理人也可要求本人對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而《侵權責任法》第23條規定受益人承擔補償義務需以實際收益為前提,而且補償數額在收益范圍之內。《侵權責任法》第23條調整的只是有第三人侵權行為介入的類型,并不調整因自然原因發生損害的類型。疫情之下的志愿服務活動還可以依據《民法通則意見》第142條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5條的規定責令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
三、完善途徑
(一)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立法機制
在《志愿服務條例》的基礎上盡快出臺志愿服務法。根據志愿失靈理論,志愿者服務離不開政府的指引。第一,我國應將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服務列為未來突發事件志愿服務法的單獨一章,由此公共衛生事件中志愿者尋求救助便有了法律依據。第二,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應在未來立法中把志愿者分為日常生活志愿者和突發事件志愿者,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在疫情緊急時刻,民眾足不出戶,網絡媒體成為了大眾共享信息的平臺,應該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在網絡上召集組織擁有專門知識和醫護經驗的志愿者,由他們組成團隊,以應對不時之需。可根據突發事件的嚴重程度分成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級,并以此決定調用多少數量、類別的志愿者,這樣可以減少盲目性[14]。第三,應由立法規定建立一支相對穩定的應急志愿者隊伍。在召集組織有專門知識的醫護團隊之后,政府應定期組織醫護志愿者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演習訓練,系統上課,強化醫護專業知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緊急性、傳染性迅速等特點,為此我們理應未雨綢繆。
(二)著重強調非注冊志愿者的保護
完善對非注冊志愿者登記制度和途徑。充分利用社交網絡尤其自媒體平臺進行宣傳,對自發形成的志愿者組織微信群進行統一篩查登記,尤其微信實名制之后,更加便于管理。同時加強對非登記注冊者的心理關注,有突出貢獻者可適當給予其子女在升學考試中的優惠政策、授予本人榮譽稱號,對其工作升遷、考核進行一定嘉獎,逐步落實對非注冊志愿者切實可行的保護政策。
(三)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侵權免責制度
1.參照第三人侵權行為的歸責制度《侵權責任法》第37條第2款規定第三人在公共場所或者群眾性活動中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15]筆者依照楊立新教授的觀點將此條規定下的第三人侵權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適用第三人侵權行為的一般規則,免除實際加害人的侵權責任。

原因作用是否有過錯實際加害人間接原因輔助作用無第三人直接原因直接作用有
第二種情況:競合侵權行為,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不適用第三人侵權行為的一般規則。
概念圖模型的建立能夠幫助學生快速理清各概念之間的聯系,特別有利于聯系前后章節,建立大單元學習背景,在整體教育思想的指導下,高瞻遠矚地看問題。

原因作用是否有過錯實際加害人間接原因輔助作用有第三人直接原因直接作用有
第三種情況:當第三人的行為不是致使損害發生的全部原因的,應當分情況討論:

行為種類責任類型共同侵權行為連帶責任分別侵權行為按份責任競合侵權行為不真正連帶責任第三人侵權行為第三人責任
2.參照醫療損害責任制度目前尚未明確醫護志愿者是否屬于醫護人員,因此醫護志愿者引起的糾紛能否適用醫療損害責任制度也尚未明晰。筆者提議將組織醫護志愿者的機構擬制為醫療損害責任制度中的醫療機構,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1款規定的用人單位責任原則。或將醫護志愿者視為醫護人員,享有同等待遇,則可直接適用侵權責任法第54條醫療損害責任制度。
依照楊立新教授的觀點:侵權責任法第54條是第34條第1款的特別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志愿服務活動組織與醫務志愿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擬制為勞動關系,前者擬制為用人單位,后者擬制為員工,當醫護志愿者因志愿活動造成他人損害時,其后果應當由志愿組織(或醫療機構)承擔。[16]當醫護志愿者存在管理過錯時方可適用第54條,此時志愿組織(或醫療機構)才能夠承擔責任,這顯然對醫療機構更為有利。我國志愿服務條例并沒有對志愿活動中的侵權法律責任做出說明,應當在今后的志愿者服務立法中加以衡量。
(四)健全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的保障體系
抗疫支援過程中,若志愿者不幸被傳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甚至產生死亡后果,怎么辦?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司就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落實關心關愛一線醫務人員的人事激勵措施,提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的,應認定為工傷;已參加工傷保險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和單位按照工傷保險有關規定支付,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按照法定標準支付,財政補助單位因此發生的費用,由同級財政予以補助;開辟醫護及相關工作人員工傷保險綠色通道”。從身份上識別,這些救助措施似乎不適用于醫護志愿者。
針對以上情況,筆者認為應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保障體系,即通過保險、專項基金、社會保障的有機結合,全方位、兜底式確保醫護志愿者感染后能得到及時救助和賠償。
1.完善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志愿者的保險制度第一,在立法層面應設立強制保險制度,即強制要求用人單位或志愿組織為突發事件中的志愿者,尤其針對服務于公共衛生領域,面對散布快、傳染性極強的病毒而奮戰的醫護志愿者,必須為他們購買意外傷害保險和健康保險。第二,要明確規定財產險和第三者責任險。志愿者可能會遭受財產損失,僅僅規定人身保險是不夠的。如今醫患關系緊張,若意外事件或由于醫護志愿者疏忽大意的過失造成患者不可逆人身財產性損失的,可由第三者責任險進行兜底性賠償,有助于減輕醫護志愿者的賠償壓力、維護醫護人員形象[17]、減少社會醫患沖突。志愿組織應與金融保險行業合作,針對醫護志愿者的保險產品,來保障白衣天使的安全。第三,規定保險期限。一般以志愿服務活動之前雙方明確的期限為準,若實際操作中,時限與訂立時不同,則應當重新訂立保險合同。若志愿者想續保,則與保險公司協商。第四,對于志愿組織未購買保險的處罰。因志愿組織未購買保險而造成的損失,應由志愿組織承擔責任,產生嚴重后果的需要追究單位及其主要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初犯或情節顯著輕微的,當地政府或志愿者登記管理機關可給予其警告,責令改正;累犯或多次沒有為志愿者辦理保險業務的志愿者組織,可以令其限期停止活動并處以行政罰款[18]。
2.設立專項基金政府應鼓勵志愿服務組織開展設立專項基金,用來彌補意外保險賠償不到位的缺憾,盡量避免志愿者無法得到相應賠償的情形。專項基金的來源可由兩部分構成,在社會廣泛捐助之下,政府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財政補貼和撥款,以防出現資金不到位的情況。但同時志愿服務組織也應該定期公開專項基金的使用情況,用在哪,用多少,是否真正落實,后續進展等。要公開透明地接受社會群眾監督,讓愛心人士的錢花得明明白白,杜絕出現以公濟私的郭美美事件,以免對社會捐助產生不利影響,造成惡性循環。
3.將志愿服務保障同社會保障體系相結合例如,此次疫情當中,若醫護志愿者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則應該一視同仁地讓醫護志愿者也享受工傷待遇。此舉措合情合理,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護志愿者創造更強勁有力的保護措施。志愿服務具有公益性,社會保障是一種社會再分配方案。將志愿服務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此舉有利于促進公平,尤其體現在突發性事件之中。
(五)完善救濟途徑
志愿者權益受損的救濟途徑大致分為兩種,即非訴訟途徑和訴訟途徑。
1.拓寬非訟救濟途徑若在志愿服務過程中發生糾紛,矛盾雙方可自行協商解決。比如當志愿者和志愿服務對象之間發生糾紛,則可以引入志愿服務組織作為第三方協商主體,以期達到公平公正的效果。如果無法通過此種方式解決糾紛,還可以適用人民調解制度促使矛盾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解決糾紛,非訴救濟途徑并不妨礙矛盾雙方繼續采取其他救濟途徑捍衛自己的權利[19]。
非訟救濟,既可以是矛盾雙方采用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各自訴求,避免了矛盾雙方產生類似庭審程序中劍拔弩張的僵化關系,解決了訴訟成本,簡化了解決矛盾的程序,從而更加便捷高效地處理糾紛,有利于防止矛盾擴大,建立和諧社會。
2.完善訴訟救濟途徑筆者認為,應當將突發事件中的志愿者納入法律援助范疇。《法律援助條例》明確了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或失業救濟標準,或者能夠提供其經濟條件特別困難的公民可以無償獲得法律服務。突發事件中的志愿者無償幫助他人,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第一時間舍己為人、沖鋒陷陣,理應受到道德與法律的鼓勵和保障,擁有接受法律援助的正當性基礎。通過仲裁機構仲裁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是司法救濟的最后保護屏障,其維權所要承受的昂貴成本和不為民眾所熟悉的訴訟程序,成了民眾所謂的“打官司”,這讓老百姓望而卻步,此時則需要專業的律師協助志愿者進行維權。
目前我國的司法救助制度僅限于對減免訴訟費用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還可以考慮減免志愿者的執行費用,從而達到對整個訴訟過程的救助目的,為我國突發事件志愿服務活動的平穩發展披荊斬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