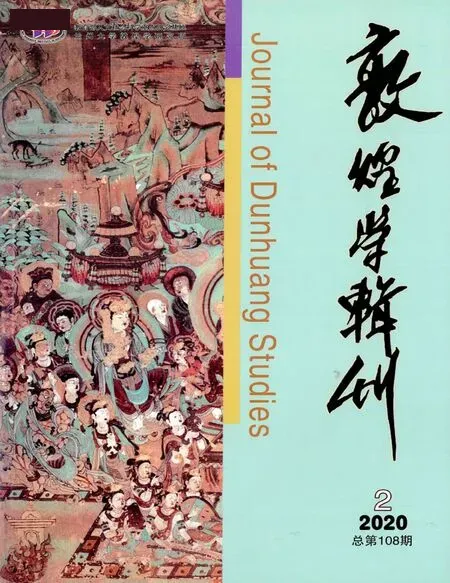唐前期西州鄰保組織與基層社會研究
——以吐魯番出土文書與磚志為中心
趙曉芳 郭 振
(淮北師范大學 1.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2.信息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貞觀十四年(640)唐滅麴氏高昌國,于其地建立西州,并根據該地特點采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張廣達先生總結為“在建立中原體制的州、縣之同時,推行整套的鄉里、城坊、鄰保制度,從而保證唐朝律令規定的均田、租庸、徭役、差科等制度的實施。”①張廣達《唐滅高昌國后的西州形勢》,《東洋文化》 第68 卷,1988 年;收入《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116 頁。這其中就提到了鄰保制度。但是,相較于學界在西州鄉里、城坊、均田制、租庸調制等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鄰保制的研究稍顯薄弱,尚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西州鄰保組織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與其他制度如何配合實施?鄰保與親人擔保有何區別?其實施的社會基礎是什么?以上問題,涉及鄰保制度與組織的功能及其演變情形,自然也是觀察唐律令制在西州貫徹落實效果的視角之一,理應予以足夠重視。因此,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①日本學者如增村宏《唐の鄰保制》,《鹿大史學》 1958 年第6 號,第40-59 頁。松本善海《吐魯番文書より見たる唐代の鄰保制》,《中國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77 年,第395-440 頁。仁井田升《唐代の鄰保制度——吐魯番發見の唐代官粟貸付(五保)文書》,收入《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 年,第663-682 頁。中川學《八·九世紀中國の鄰保組織》,《一橋論叢》 1980 年第83 卷第3 號,第122-136 頁。山根清志《唐前半期における鄰保とその機能——いわゆる攤逃の弊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史研究》 1982 年第41 卷第2 號,第57-93 頁。中村治兵衛《唐代の村落と鄰保——全唐詩よりみたる四鄰を中心に》,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國家·社會との關系——周邊諸地域の場合を含めて》,東京:刀水書房,1984 年,第116-122 頁。中國學者如羅彤華《唐代的伍保制》,收入刑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之《城市與鄉村》,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年,第88-117 頁。張國剛《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其演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年第5 期,第112-126 頁。,考察唐朝政府管轄下西州鄰保制度實施的具體情形。不足之處,懇請指正。
一、鄰保在唐代西州基層社會的運作
隋文帝即位之初,規定“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以相檢察焉”。②[唐]魏徵等撰《隋書》 卷24 《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第680 頁。唐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規定: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③[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 卷48 《食貨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2089 頁。《通典》 引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④[唐]杜佑《通典》 卷3 《食貨三·鄉黨》,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63 頁。學界一般稱之為伍保制或鄰保制。其主要目的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家庭與鄰里之間相互監督、糾察,從而形成彼此之間存在連帶責任的居民互助、互保組織。此即“諸戶皆以鄰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⑤[日]仁井田升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年,第138 頁。今就吐魯番文書所見其主要職能分析如下:
(一)警政治安,訪捉逃戶
鄰保制作為唐代的基層連保制度,其設置之初的主要職能是警政治安。中國古代社會人們比鄰而居、朝夕相見,鄉里社會內部信息的傳遞速度快,共享程度高,從而使該組織在防范非法流移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吐魯番出土《唐西州天山縣申西州戶曹狀為張無瑒請往北庭請兄祿事》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334 頁。文書,就體現了鄰保組織與里正在“按比戶口”方面的共同作用。由文書前5 行內容知,張無瑒欲前往北庭為其兄長張無價請祿,同行帶有“奴胡子年廿五”、“馬一匹駮草肆歲”及“驢貳頭并青黃父各陸歲”。自第5 行始抄錄如下:
5. 將前件人畜前往北庭請祿,恐所在不練行由,請處分者。責問上者得
6. 里正張仁彥、保頭高義感等狀稱:前件人所將奴畜,並是當家家生奴畜,亦
7. 不是詃誘影他等色。如后有人糺告,稱是詃誘等色,義感等連保各求
8. 受重罪者。具狀錄申州戶曹聽裁者。今以狀申。
9.令 停務 丞 使
本件文書無紀年,據整理者推測當在天寶、大歷年間。有朱印四處,印文為“天山縣之印”。第9 行應是天山縣官吏的署判,然該縣縣令“停務”,縣丞出使。唐朝政府嚴禁壓良為賤,以防戶口減少,規定攜帶奴婢外出者須“五人同保一事”,而馬驢等牲畜作為軍需物資,亦有嚴格管理,故“張無瑒”外出攜帶奴畜,須向西州戶曹報告。
文書第6 行以下是里正張仁彥及保頭高義感等的保證辭,即擔保張無瑒所攜帶之奴畜并是“家生奴畜”,非為“詃誘”。第6 行所見“保頭”即保長,《唐六典》 卷三“戶部員外郎”條云“保有長,以相禁約。”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73 頁。保頭作為群體組織的代理人,除在文書中保留姓名外,與保內其他保人并無不同,“唐律中似未見保長對保內事件擔負特殊責任的規定”“未見其具有特殊權能的形跡”。②[日]増村宏《唐の鄰保制》,第52 頁。日本《養老令·戶令》 云“凡戶皆五家相保……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并語同保知。”也就是說,若保內有人外出,須告知同保其他人知曉。故本件文書中,以保頭高義感為首的張無瑒的鄰保之人對其出行作出擔保,并強調“若后有人糺告,稱是詃誘等色”,義感等連保之人要接受重罪責罰。同時,保內之人很可能將人員流動情況上報給負有“按比戶口”職責的里正,以使其及時掌握里內人口的異動情況。雖然文書中出現了里正張仁彥,但“義感等連保”中是否包含里正,里正與同保之人是否承擔同樣的罪責,從文書中很難做出結論。
與上件文書相似者,如《唐開元十九年(731)唐榮買婢市券》 云“又責得保人石曹主等五人款,保不是寒良詃誘等色者”;《唐開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買婢市券》云“又責得保人陳希演等五人款,保上件人婢不是寒良詃誘等色。如后虛妄,主保當罪”。《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謙、薛光泚、康大之請給過所案卷》 載“保人宋守廉等得款:前件馬匹並是唐長史家畜,不是寒盜等色。如后不同,求受重罪者。”《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辯辭》 提及“但染勿等保石染典在此見有家宅,及妻兒親等并總見在。所將人畜,並非寒詃等色。如染典等違程不回,連□之人,並請代承課役,仍請準法受罪。”其中,石染典作為一名漢化的粟特人,不僅接受了更為規范、成熟的漢文契約,③楊際平《4-13 世紀漢文、吐蕃文、西夏文買賣、博換牛馬駝驢契比較研究》,《敦煌學輯刊》 2019 年第1期,第118 頁。而且也接受了來自唐朝政府的律法約束。以上四件文書無一例外地寫明“保人某某某等”,其中前兩件文書具體寫到“五人”,并在末尾處羅列了五位保人的姓名。筆者推測文書中的“等”應該都是指代“五人”。那么,五位保人擔保的事項是什么?首先是保證出行人所帶人畜非為強搶、誘盜;其次,《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辯辭》 提及保證代承出行人的課役。最后,保證所言真實不虛,否則“求受重罪”。
之所以要求鄰里之間連防相保,是因為若有人逃走,鄰保負有追訪之責。《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倉曹下天山縣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①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70 頁。中,天山縣安昌城人唐建進狀告該縣主簿高元禎耕種逃戶、死絕戶的田地,或者以此出租,或進行廻換。西州都督府受理此案后,在多次判下天山縣追訪唐建進未獲的情況下,遂下令“追建進妻兒及建進鄰保赴州”。可見,唐建進的家屬及伍保之人負有訪捉之責,可能也需要將訪捉結果向州縣匯報。
以上文書足以說明唐西州不僅實施了鄰保制,而且相互負責的群體內部監督被切實執行。即便是被一直堅持重農主義政策的唐朝各級政府視為異端的人口流動,因為鄰保制這樣百姓之間卓有成效的橫向監視與連帶責任,也處在井然有序的狀態中,足見唐政府布下的安全網絡是何等嚴密。
(二)代承課役,代輸稅賦
由于中國古代社會人口的流動性較弱,鄉里社會內部人員接觸多,溝通時間長,鄰里之間獲取信息較為容易,因此中國古代各級政府在充分利用民間信息資源的過程中,很容易將鄰保制度設立之初相互監督、檢舉的功能擴大化,從而延伸到賦稅和課役領域。
吐魯番出土中宗景龍三年(709)南郊赦文云:“所征逃人四保租調二年□諸色勾征,並宜者,委□□即分明勘會。”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59 頁。表明八世紀初期中央政府對全國范圍內伍保承擔逃戶賦稅、租調的情況是了解的,西州自然也在此列。至于其開始時間,學者推測“大概至遲在永徽年間即已行之。”③羅彤華《唐代的伍保制》,第107 頁。
與逃戶問題一樣,四鄰伍保的攤逃也是唐朝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如開元年間皇甫璟《諫置勸農判官疏》 指出:“州縣懼罪,據牒即征,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逃。”④[清]董誥《全唐文》 卷397,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影印本,第4055 頁。點明了逃戶與攤逃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均田農民逃走危害極大,直接影響唐政府的財政稅收和徭役征調,“非直課調虛蠲,闕于恒賦,亦自誘愚俗,堪為禍患。”⑤[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1843 頁。為了穩定鄉里秩序,強化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掌控力,唐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括戶運動。但是,在逃戶未回到原籍之前,仍舊需要有人代替逃戶承擔租庸調。故唐戶令云:“諸戶逃走者,令伍保追訪,三年不獲,除帳,其地還公。未還之間,鄰保近親(或四鄰伍保三等以上親),均分佃食,租庸代輸。戶內口逃者,同戶代輸,三年(或六年)不獲,亦除帳,地準上法。”①宋家鈺《唐代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44 頁。也就是說,在逃戶“未還之間”由近親(關于近親問題,下文論述)鄰保以“佃食”的名義耕種逃戶的廢棄土地、代輸租庸,這是國家的法律規定,也是鄰保代濟的理論基礎。
吐魯番阿斯塔那4 號墓出土《唐總章元年(668)西州高昌縣左憧憙辭為租佃葡萄園事》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221 頁。雖然不是鄰保代濟的直接材料,卻也從側面反映了這樣的問題。

由文書內容知,“左憧憙”曾于“趙廻□”邊租佃張渠葡萄園一處。文書第2 行小字部分標明“趙廻□”為“舊主”,推測趙可能在契約訂立后身死或逃亡。這就涉及三個方面:作為田主的“趙廻□”不在,那么其與“左憧憙”簽訂的契約是否仍舊有效?左又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呢?在此情況下,吐魯番租佃契約所言“租輸百役,仰桃主了”又由誰來具體執行呢?
有學者指出:“唐西州時期,該地區實行的主要是均田制,葡萄園被官府作為永業田授予個人。”③馬燕云《吐魯番出土租佃與買賣葡萄園契券考析》,《許昌學院學報》 2006 年第6 期,第91 頁。一般而言,永業田均傳之子孫,可以戶內繼承。那么,第4 行所見“屯桃(萄)人”可能就是本處葡萄園的繼領人。左在上呈給官府的報告中云“恐屯桃人并比鄰不委”,同時請求給予“公驗”(即官方證明)。其中“比鄰”應該是舊主趙廻□的四鄰,“不委”可以理解為不明原委。“左憧憙”之所以這樣做,在筆者看來,一方面在于促使官府承認先前訂立契約的有效性,以保障自身的經濟收益。當然這也意味著他必須履行契約規定,按時交納租價。另一方面,實際上明確了新的責任歸屬,即“園中租輸百役”將由“屯桃(萄)人”或者“比鄰”承擔,并不會影響國家賦稅征收。因為鄰人具有組織和幫助履行納稅應役的義務,故而出現在左上呈官府的報告中。
此外,《唐景龍三年(710)十二月至景龍四年(711)正月西州高昌縣處分田畝案卷》④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第562 頁。之其中一宗,也涉及逃戶稅錢的征收問題,茲抄錄如下:
113.右上件大女先已向北庭逐糧在外,死活不知。昨
114.被前里正左仁德逐追阿彌分地,入收授出給。比來
115.阿彌所有戶內□錢,恒是本里代出。其戶內更兩
116.人,戶見未絕,地未出,望乞處分。
本件文書系逃戶大女阿彌所屬里正上呈給縣司的請求牒文。大意為大女阿彌先前往北庭“逐糧”(即逃亡),其戶應交納的□錢一直由其所在之里代出,故前里正左仁德要求收回阿彌的土地,分配給他人。然現任里正認為阿彌戶內尚有兩人,非為絕戶,也沒有退還土地,因而請求縣司處理。究竟逃戶所欠錢是里正代出,還是鄰保代出?不太清楚。雖然兩種可能都存在,但按照唐朝法律規定應該是鄰保攤付。
(三)問訊擔保,協助司法
因為鄰保負有偵查四鄰動靜的義務,故經常作為問訊對象出現于司法案件中。“官司在審訊過程中,常需就當事人之陳述,責保人或證人問訊,以查其所言虛實,而伍保應是其重要的征詢對象之一。”①羅彤華《唐代的伍保制》,第114 頁。如《武周西州交河縣前倉督高歡貞牒為租田事》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第328 頁。,今轉錄如下:

本件文書整理者編為10 行,查看圖版,現第3 行文字內容雖無法識別,但依稀可見文字筆畫,故改為11 行。存朱印一方,殘剩“交河”二字。前端殘損嚴重,“地”“月”“日”均為武周新字,可判定其時間在武周時期。所述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似為民間因租種田地發生糾紛,從而訴至官府請求裁決。第7 行所見“召親鄰、伍”后所缺文字或為“保”;第10 行“付司”表明官府已經受理此案。顯然,親鄰五保作為原告或被告在血緣及地緣關系中最親近的人,在案件審問過程中被召集、查訊,證其公直過惡,是司法程序之一,也是鄰保被賦予的特殊治安責任。
發生于張玄逸家中的失盜案亦可見鄰保蹤跡,茲抄錄部分文書如下:
(2)《唐麟德二年(665)知是辯辭為張玄逸失盜事》

① 整理小組于此處漏錄“被”字,見《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第239 頁。
本件文書時間為麟德二年(665)五月,第1 行所見“張逸”即張玄逸,內容系官府審問知是的辯辭。知是是麴運貞家中的奴婢,不排除其與《唐麟德二年(665)畦海員辯辭》 中提及的一婢②曾柏亮、李天石《敦煌吐魯番漢文文獻中奴婢資料的再整理》,《敦煌學輯刊》 2019 年第1 期,第163 頁。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官府懷疑知是越墻偷盜,并質問其所盜之物現在何處。知是在辯辭中用鄰里來證明其長期患病,使得高昌縣官員做出“更問”的批示,這其中知是的四鄰很可能被帶至公堂問訊,最終促使司法官員重新審查案件,可見西州鄰保組織的證言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
除以上職能外,我們還在編造手實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鄰保的身影。《西州高昌縣下太平鄉符為檢兵孫海藏患狀事》 是一件唐西州高昌縣的公文書,上鈐“高昌縣之印”,該文書的核心事件是孫海藏患病及入疾問題,文書提及“波斯道行”,知時間為唐高宗調露元年(679)七月以后。孫海藏患有風癇(即癲癇),又“坐底冷漏”,卻成為波斯道行軍的一員。因在行軍中多次發病,最終被西州政府下符取消兵役。③關于孫海藏被取消兵役的具體過程,參考李興祥《論唐代前期軍隊與地方的關系——以患兵處理為視角》,《西域研究》 2010 年第3 期,第42-43 頁。其后,在地方政府編造手實時,為了弄清其是否符合“入疾”(成為正式殘疾人)的條件,不僅對軍方提供的病情證明文件反復核查,“又責保問鄉勒保人張丑是等五人,里正杜定護、醫(后缺)”,④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第488 頁。詢問了孫海藏的保人張丑等五人、里正杜定護及醫師等,證明其患有風癇及冷漏有些時間了。此處的保人張丑等五人應該就是孫海藏著籍之地的伍保,與伍保相呼應共同履行職責的是里正及相關人員。
二、與鄰保相結合的近親
由前文的論述可知,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與鄰里之間相互監督、相互糾察并負有連帶責任的鄰保組織在唐前期的西州地區是確實存在的。律文所見其制度設立之初的主要職能也僅限于治安、督察。但是,隨著則天朝小農逃亡、丁口虛掛等問題的逐步暴露,國家不僅逐步強化了鄰保代出課役、負擔賦稅的義務,而且地方官吏出于影響自己政績的顧慮,往往采取非常手段擴大連帶的范疇,波及近親,甚至已經到了國家無法容忍、不得不下令禁止的程度。
唐玄宗天寶八載(749)正月勅“蓋為牧宰等,授任親民,職在安輯,稍有逃逸,恥言減耗,籍帳之間,虛存戶口,調賦之際,旁及親鄰,此弊因循,其事自久……其承前所有虛掛丁戶應賦租庸課稅,令近親鄰保代輸者,宜一切並停。”①[宋]王溥《唐會要》 卷85 《逃戶》,第1854 頁。可見天寶之前由近親、鄰保攤逃租調、賦稅的處理方式已經非常具有普遍性。即便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攤逃的弊端,明令加以禁止,但效果未必理想。僅僅八年之后,至德二載(757)二月又下令“諸州百姓,多有逃亡,或官吏侵漁,或盜賊驅逼,或賦斂不一,或征發過多。俾其怨咨,何以輯睦。自今已后,所有科役,須使均平,本戶逃亡,不得輒征近親,其鄰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②[宋]王溥《唐會要》 卷85 《逃戶》,第1855 頁。。對近親的態度是不得征收,對鄰保則是“務從減省”,可見其中之差異。
盡管國家從律法層面上多次嚴令禁止近親攤征,但實際上由于地方政府的“恥言減耗”,代輸逃戶租課仍舊實實在在地落在與逃戶有血緣關系的近親身上。山根清志指出:在與代輸(代納·代出)相關的諸史料中,經常能夠看見以親鄰、近親·鄰保、鄰親、近親=鄰保、鄰近等表現的詞匯。③[日]山根清志《唐前半期における鄰保とその機能——いわゆる攤逃の弊を手がかりとして》,第73頁。如寶應元年(762)五月十九日勅“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征,不得率攤鄰親高戶”④[宋]王溥《唐會要》 卷85“逃戶”,第1855 頁。。這是對四鄰近親等高戶攤征租賦的正面回應。長慶元年(821)正月赦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離死絕。見在桑產,如無近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于官健中取無莊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便與公驗,任充永業。”⑤[宋]王溥《唐會要》 卷85“逃戶”,第1856 頁。雖然不是直接說明近親攤征的問題,卻提到了近親對逃亡戶留下的桑產具有優先承佃的權利,那么在優先承佃的基礎上代出課役,在理論上被強制地義務化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吐魯番出土《唐通感等辯辭為征納逋懸事》 云:“人人皆自輸納,亦不浪征百姓。被問依實。”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86 頁。通感辯辭中的“不浪征百姓”可能是真的,但從吐魯番出土其他文書看,頗具諷刺意味。地方官吏出于財政考量,或追求政績,在征納過程中可能存在浪征行為,其浪征的對象極有可能就是逃亡戶的親鄰等。
吐魯番阿斯塔那187 號墓所出文書《唐高昌縣史王浚牒為征納王羅云等欠稅錢事》,⑦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206 頁。突出反映了地方官吏處理民眾拖欠稅錢的程式,其中就涉及近親代納稅錢。茲抄錄部分文書如下:
6.尚賢鄉戶王羅云
7. 右同前得狀稱,被牒報稱,是王如珪妹,令征今年
9. 依問里正孫居,得款:□□女戶是王如珪妹,
10. 見隨兄在蒲昌城坐巷,名丑婢,請付橫管征者。
本件文書的背面是天寶三載(744)的名籍,推斷書寫時間可能在唐玄宗開元時期或天寶初年。由文書內容知,尚賢鄉王羅云是王如珪的妹妹,其兄不知何故,未交納該年稅錢。該鄉里正孫居證實王如珪與王羅云“在蒲昌城坐巷”,即確認二人的兄妹近親關系,因而建議“請付橫管征者”。也就是說,若王如珪果真未交納稅錢,則官府將強制王羅云代為繳納。
親鄰可能需代為承擔徭役。阿斯塔那178 號墓出土一件文書或許從側面反映了此問題,茲抄錄如下:

①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184 頁。
本件文書時間在開元二十八年(740),前端殘損嚴重,同墓所出 《唐開元十八年(740)土右營下建中趙伍那牒為訪捉交河兵張式玄事二》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185 頁。可供參校部分文字。由文書內容知,阿毛兄長張式玄于該年三月被分配到交河車坊上番,然至今未歸,不知死活。阿毛擔心其兄更有番役,牽扯到自己,故向都司說明情況。陳辭之中,阿毛一方面強調自己與兄“別籍”“不同居”,另一方面述說自己孤身一人,沒有丈夫,依靠給他人作傭勉強養活自己,以表明自己沒有義務、亦無經濟實力替兄上番。盡管本件文書并不是近親替代承擔徭役的直接材料,但是阿毛急于撇清自己的做法,恰恰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官府強制近親承擔徭役的普遍現象。
總之,鄰保組織作為唐朝最基層的地方組織,以維護地方社會秩序,建立集體安全網絡,鞏固統治者權威為最終目標。但是,鄰保與親保在保證對象及側重方面可能稍有差異。就鄰保而言,除協助里正按比戶口、檢察非違外,更側重于向官府保證其提供信息的真實性,而親保似乎無此職能,只在代納課稅、代承徭役等方面表現突出。這種責任的差異性在吐魯番文書中亦有完整體現。如阿斯塔那509 號墓所出《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 之“麴嘉琰請過所案卷”中,其保人麴忠誠等五人的保證辭為:“麴琰所將人畜,保並非寒盜誆誘等色者”;①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286 頁。其弟麴嘉瓚的保證辭則為:“兄麴琰去后,所有戶徭一事以上,並請嘉瓚祗承,仰不闕事者。”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肆,第287 頁。當然,西州人多地少,人口的活動能力相對有限,家族成員比鄰而居,血緣與地緣關系往往融合在一起,親屬與鄰里相互重疊的情形應該也是存在的。
三、從“昊天不吊”到“四鄰楚目”
西州成立之初,很多制度都受到麴氏高昌的影響,如高昌國時代通行的銀錢繼續使用,“遠行馬”制度以“長行馬”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繼承下來,高昌國的量制也在西州民間繼續沿用等。但是,現有材料尚未發現麴氏高昌國存在鄰保組織的蹤影。那么,唐西州鄰保制迅速實施的社會基礎是什么?
吐魯番地區自20 世紀初期至今已經出土的磚志共計300 余方,其中時代最早、有明確紀年者為《大涼承平十三年(455)沮渠封戴墓表》,沮渠氏雖不屬漢族,但深受漢文化熏陶,其墓表的出現無疑是中原喪葬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在此后的80 余年間埋葬衣物疏一直是當地流行的習俗,直到公元537 年才出現了有明確紀年的第二方墓表,即《高昌章和七年(537)張文智及夫人馬氏、鞏氏墓表》。石見清裕將麴氏王國的墓表形式總結為“ 〔元號〕 〇年〔干支〕 歲〇月〔干支〕 朔〇日〔干支〕 〔官職〕 〔姓名〕 春秋(年)〇〇〇氏之墓表”③[日]石見清裕《吐魯番出土墓表·墓志の統計的分析》,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9 年,第174 頁。,表明墓志的書寫具有固定化的程式,但仍舊能從中發現一些緩慢的變化,最典型者如磚志書寫詞匯從“昊天不吊”向“四鄰楚目”過渡。
“旻天不吊”“昊天不吊”“天不愍遺”“天不慗遺”等詞匯的出現,見于《高昌永平元年(549)田元初墓表》 《高昌和平四年(554)孟宣宗墓表》 《高昌建昌三年(557)任□□墓表》 《高昌建昌五年(559)田紹賢墓表》 《高昌延昌十五年(575)張買得墓表》 《高昌延昌十九年(579)畫儒子墓表》 《高昌延昌卌一年(601)索顯忠墓表》 《高昌延和七年(608)賈羊皮墓表》 《高昌延和七年(608)張叔慶妻麴太明墓表》 《高昌延壽十七年(640)醫人墓表》 等,時間從549 年-640 年。
“旻”又寫作“昊”,旻天即蒼天、上天、皇天;昊天不吊,即蒼天不吊唁,此語經常出現在墓葬文字中,流露出時人對命數由天的無可奈何與惋惜之情。麴氏高昌墓表中的“昊天”應該是擬人化的實體“天神”,它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和主宰人命運的權力。在既崇拜又畏懼的心理作用下,當地百姓很自然地把人的生死福禍理解為神明的安排,并在磚志中書寫出來,從而體現了最原始的“天命觀”。
但是體現這種樸素的“天命觀”的詞匯在公元640 年以后的吐魯番墓志中很少出現。其原因并不能簡單歸結于政治上的改朝換代,因為“墓葬的重大演變經常無法在一個王朝內得到最恰當的詮釋”。①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 2006 年第1 期,第71 頁。事實也的確如此,從西州建立到貞觀朝結束的十年間,磚志書寫中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使用唐朝年號和紀年方式這一點上,其他形式與麴氏高昌末期基本無二。與此同時,吐魯番磚志中出現了大量表示鄉里社會人際關系的詞匯,茲列表如下。

吐魯番出土磚志所見人際關系詞匯表

續表

續表
以上31 方墓志時間從麴氏高昌延昌十九年(579)至唐開元七年(719),其所有者有男性也有女性,絕大多數為漢人,也有一部分屬于昭武九姓粟特人。涉及人際關系的詞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詞匯,如四鄰、鄰里、鄉閭、鄉邦、鄰田、鄉里、鄉黨、鄉城、衢里、鄰伍、里民、閭里、鄉閈等;其二,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詞匯,如親屬、六親、九族、宗親、親族、親戚、室家、宗族、子息等;其三,綜合性詞匯,如友朋、合境、朝野等。歸納起來,這些詞匯大多以對仗的形式或用于表達生人對逝者離去的哀傷與悲慟之感,如宗族悲號、四鄰楚目等;或用于刻畫生人對逝者品德等的贊美,如鄉閭嘆其平恕、鄰里贊其無私、鄉閭稱為教首、宗族號曰慈仁等。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墓志的格式相對固化,“循守著固定一概的行文模式,充溢著千人一面的譽美之詞”,①鄧小南《六至八世紀的吐魯番婦女——特別是她們在家庭以外的活動》,《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4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16 頁。但這些充滿溢美的帶有情感傾向的詞語使用情況(雖然不是所有墓志中都有)仍舊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種變化,是我們可以感受到的。
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墓志中出現了“四鄰”,首次出現于高昌延和三年(604)鞏孝感墓志。這意味著該詞匯和前文討論的唐朝鄰保制中的“四鄰”并無關聯,而僅僅是一種泛泛的稱謂。雖然墓志中并沒有寫明四鄰的作用,但是鄰里以人力、物力相助營辦喪事應該是人之常情。敦煌出土喪葬文書云“儒風坊西巷村鄰等就馬興晟家眾集再商量”②劉傳啟《敦煌喪葬文書輯注》,成都:巴蜀書社,2017 年,第63 頁。、“右上件村鄰等眾就翟英玉家結義相和”③劉傳啟《敦煌喪葬文書輯注》,第64 頁。,表明在喪葬活動中鄰里互相幫助已經成為當地的鄉規民俗。若不助鄰里之喪者,將可能受到道德的審判,視為不義。如趙泉虬《對助鄰婦喪判》 判文曰“鄰婦時命先秋,生涯凋落,四德之名尚在,九泉之魄俄沉。存既寡于周親,沒亦感于鄰義。既而朱火不舉,俯兇事而無從;元璉未臨,仰生人而何托?聞人以蹈危為意,憂濟留心,爰行博施之恩,自合無喪之服。論其主斂,則親屬為先;語其科辜,則聞人無罪。”④[清]董誥《全唐文》 卷956,第9927 頁。要求鄰里之人“感于鄰義”,對鄰婦喪葬之事“行博施之恩”。
吐魯番出土文書《唐眾阿婆作齋社約》⑤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叁,第81-82 頁,整理小組命名為《唐眾阿婆作齋名轉帖》。郭鋒先生將之命名為《唐眾阿婆作齋社約》,見《吐魯番文書〈唐眾阿婆作齋社約〉 與唐代西州的民間結社活動》,《西域研究》 1991 年第3 期,第74-78 頁。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這件文書應該是社條而非轉帖。共34 行,其中第2-27 行書寫結構和形式一致,共羅列了26 位阿婆的姓名,如第19 行“□彌舉阿婆弟十九”,彌舉是人名,阿婆應是彌舉的母親。“弟十九”表示第19 位。茲將文書第28 行以后抄錄如下:

26 位阿婆除每月一次齋會外,“眾阿婆等中有身亡者”表明本件社約也涉及喪葬互助活動,考慮到阿婆的年齡因素及結交同性朋友伙伴的長時段性以及吐魯番地區的封閉性,我們認為她們是近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學者中村治兵衛對《全唐詩》 涉及四鄰及近鄰關系的詞匯內容的考察顯示:“四鄰是唐代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個組織……而五家為一保的組織卻幾乎沒有在全唐詩中出現過,或許是因為其不太適合作為詩的描寫對象”。①[日]中村治兵衛《唐代の村落と鄰保—全唐詩よりみたる四鄰を中心に》,第121-122 頁。值得注意的是,五家一保組織在吐魯番出土墓志中也幾乎完全未見。前列表1 《咸亨四年(673)史住者墓志》 雖然出現了“鄰伍悲傷,行路啼泣”,但此處的“鄰伍”很可能與“鄰里”“四鄰”等詞匯一樣,并無具體的指代含義。聯想到前文提及的保長要為朝廷控制人口,避免隱丁匿口,甚至還要替朝廷征發賦役,所做工作大多違背當地百姓的利益與愿望,實在算不上光彩的角色,因此他們作為朝廷的觸角在基層社會中是非常尷尬的存在,這樣的處境使得極少有人愿意將“保長”等職銜書寫在磚志上。
喪葬作為中國古代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埋葬的對象雖然是死者,但磚志的書寫、喪禮的主持等活動確是由生人操辦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和人們的價值取向。中國古代講求“蓋棺定論”,多揚善隱惡,吐魯番磚志所言“鄉城領袖,宗族軌模”“鄉黨稱仁,宗族稱孝”等,從表面上看是給予死者的評價、榮譽及懷念,實際上對死去之人并無任何意義與價值,但對活著的人卻非常重要。墓葬的大小、磚志的書寫、葬禮的規模、隨葬品的多寡、守喪期的表現等不僅寄托了生者加官進爵、延年益壽、光耀門楣等諸多期待,而且也是仁孝家風禮教的體現,在吐魯番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因血緣和地緣關系結成的熟人社會中,家族的良好口碑在當地盛行的借貸、租佃等經濟活動以及需要四鄰擔保等諸多事務中將使生者受益,是不難想象的。
出土磚志從表現人們敬畏天命的“昊天不吊”到鄰里守望相助的“四鄰楚目”,其中固然有中原墓志書寫方式的影響,但仍舊需要將之置于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考察——即高昌王國屢次請求內徙不獲,轉而著力經營吐魯番之地,進一步增強當地民眾的地域認同。高昌作為一個以內地漢族移民為主體的地方割據政權,長期孤懸磧外,周圍強敵環伺,其首次內徙始于馬儒統治時期,史載: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愿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麹嘉為王。”②[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101 《高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2244 頁。麴嘉被擁立為高昌王后,于永平元年(508)初,遣其兄之子麴孝亮出使北魏,“仍求內徙,乞軍迎援”③[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101 《高昌傳》,第2244 頁。,終因“失期而返”以失敗告終。其后,麴嘉仍舊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貢,請求內徙。僅永平二年(509)左右,就先后十余次向北魏請求內徙;④[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101 《高昌傳》 卷8,載“高昌曾于永平二年正月、六月、八月遣使朝貢。”第207-208 頁;同書《高昌傳》 亦載“於后十余遣使”,第2244 頁。永平三年(510)亦如是;⑤[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8 《世宗傳》,第209 頁熙平元年(516),麴嘉又遣使北魏,仍舊遭到拒絕。神龜元年(518)五月,又見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麴孝亮再次使魏“復表求援內徙”。①[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101 《高昌傳》,第2244 頁。這是史書所見高昌最后一次請求內徙,此后雖屢有朝貢,卻再不提內徙之事。內徙斷念,才有了麴氏高昌國獨立經營的開始。
馬氏、麴氏高昌積極向中原政權靠攏,尋求保護,頻表忠心,是當地政權意圖將地域認同與國家認同結合起來的表現之一,雖然在筆者看來這種國家認同的實質是借中原政權之名維護其在地方的統治。由于內徙不獲批準,加之中原政權更迭頻繁,此后麴氏王國與各中原政權之間雖偶有往來,但難以產生持久穩定的合作默契,在心理層面上再難以對中原政權產生國家認同感。所以,隋朝建立后麴伯雅、麴文泰父子雖先后來朝,亦不提內徙之事。②薛宗正先生認為麴伯雅入隋朝覲,并非出自單純的文化認同,而是其自我政策的調整。見薛宗正《麴伯雅生平析疑》,《敦煌學輯刊》 2007 年第2 期,第132 頁。及至唐朝建立,太宗發布《討高昌王麴文泰詔》,麴文泰的回應頗值得玩味,其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游于堂,鼠安于穴,豈不活耶!《唐永昌元年(689)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 亦載:麴文泰“阻漠憑沙,國有偷安之望”。③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第586 頁。就是這樣一位君主,高昌國人不僅給予其“光武王”的謚號,而且在唐軍瀕臨城下之時出城為其送葬。有學者指出“危在旦夕之際為亡君發喪,可以反映高昌國人對國君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態度。”④裴成國《論貞觀十四年以降的唐西州形勢》,《西北民族論叢》 2016 年第1 期,第94-95 頁。那么,高昌國人對國家是什么態度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從上而下強烈的地域認同感支配的共進退與同患難。事實也的確如此,高昌君臣不僅負隅頑抗到了最后才投降,而且在戰爭結束之初仍有部分人抗拒唐朝的統治。以上論述都說明,經過五胡十六國時代的不斷移民,加之麴氏數代經營,到公元640 年唐朝平定其地前,漢魏黎民對吐魯番之地形成了較強的地域認同。
這種地域認同就高昌而言在文化上具有很好的適應性。麴嘉屢次請求內徙不獲,轉而變內徙為內強,引進五經、諸史,充分利用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文化來加強內部凝聚力。此后,麴氏諸王堅持仁孝治國,利用漢人血脈相連、文脈相通的文化心理特征,進一步鞏固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關系和鄰里關系,其所求借的五經、諸史以及國子助教等很可能參與了麴氏高昌的國家構建。在此過程中,人們越來越重視周圍的鄉鄰關系,并將鄉鄰的美好評價視為衡量個人品德和家族聲望的標準之一寫入墓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吐魯番出土唐貞觀二十年(646)十二月《趙義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書》 寫道“巢寄他土,曉夜思鄉,粗得偷存,實無理賴”⑤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 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172 頁。,趙義深日思夜想的故鄉應該是吐魯番之地,而不是馬氏、麴氏所請求內徙的中原某地,是再清楚不過的。因為那里有義深的阿婆、姐妹、兄弟、友鄰,有他所有人際關系的總和。正是由于麴氏對吐魯番之地長達百余年的經營才形成了當地百姓強烈的地域認同,并滋生了這種故土難離的情感。而公元640 年太宗平定高昌,建立西州,采取方方面面的措施撫慰當地百姓和官員,使得他們在磚志中直書“高昌人也”,則是當地民眾自覺將國家認同與地域認同再次統一的表現。
四、余論
鄰保組織作為一種基于地緣的近鄰關系的小團體,到清朝已經發展為“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究、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的重要工具,基本涵蓋了鄉村生活的全部內容,成為古代國家控制基層社會的得力措施。現代學者在論述鄰保制的作用時,往往強調其負面影響,如“唐代伍保制的設計,明顯地是重官務、輕民務;重社會安定,輕個人權利;重財政收入,輕百姓利益……將導致伍保的負擔過重,甚至遭逢政府的無理摧殘”。①羅彤華《唐代的伍保制》,第117 頁。但是,從春秋戰國到民國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里,鄰保制非但沒有走向消亡,反具活躍的生命力,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作為一項統治手段,應該如何更客觀地評價其作用?
不可否認,鄰保制力圖利用百姓之間的橫向監視將其身份與土地等緊密結合,限制人們隨意遷徙、流動,以達到“編戶齊民”的目的。但是,從國家控制的角度而言,人與人之間的連帶責任克服了古代信息不對稱、技術和交通落后等制約因素,通過事前設定的責任范圍及適當的獎勵與懲罰,實現了小政府、大疆域前提下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就邊地西州而言,地方政府的軍政事務異常繁忙,不僅要統計人戶、分配土地、征收賦稅、征發兵役和徭役等,而且由于其地處東西交通之孔道,族屬成分復雜,商貿往來頻繁,人員流動性較大,加之州縣官府人力資源緊張,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親屬和鄰里之間的信息優勢,實施有限范圍的連帶責任,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治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