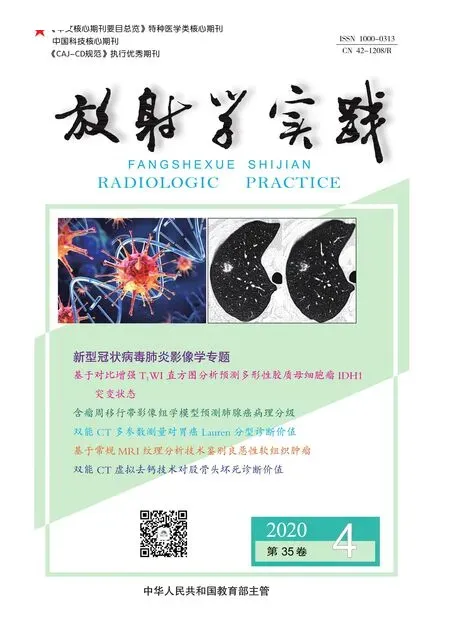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臨床特點及肺部CT變化模式
劉松,謝紅,余成新,聶陳
自2019年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陸續發現了多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隨著疫情的蔓延,中國其它地區及境外100多個國家也相繼發現了此類病例。2020年2月11日WHO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命名為COVID-19[1],同一天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Virus Taxonomy,ICTV)提議根據生物遺傳學分析,將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2]。影像學檢查尤其是HRCT對于評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肺部改變具有重要作用,是診斷COVID-19的重要檢查手段。筆者回顧性分析72例患者住院期間的病歷資料,總結肺部CT動態變化模式,對于全面了解COVID-19的疾病轉歸過程及指導治療有重要意義。
材料與方法
1.資料收集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3],搜集72例經PCR病毒核酸檢測確診為COVID-19患者于2020年1月26-2月27日在本院隔離治療期間的病歷資料,分析患者的流行病學、臨床癥狀、檢驗結果、影像資料、用藥信息及治療過程。
2.CT掃描
使用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16排CT機。檢查前訓練患者屏氣,于吸氣末期采集CT圖像。掃描范圍自肺尖至肺底,掃描參數:130 kV,100 mAs,層厚1.5 mm,間隔1.5 mm,骨算法重建。觀察圖像的窗位設置為-500 HU,窗寬為1500 HU。
3.CT圖像分析
將肺部CT按解剖部位劃分為5個肺葉,根據病變在每個肺葉中的累及范圍,采用6級評分法[4-5]。0分:無累及;1分:病變累及范圍<10%;2分:病變累及范圍11%~25%;3分:病變累及范圍26%~49%;4分:病變累及范圍50%~75%;5分:病變累及范圍>75%。CT總得分是各個肺葉得分的總和,取值范圍為0~25。
肺內病變分布分為3類。①胸膜下:主要累及肺的外周三分之一;②隨機分布:胸膜下和中央區域都有;③彌慢性:累及范圍廣泛,不局限于肺段。
肺內病變的主要征象記錄為:①磨玻璃影(ground glass opacity,GGO);②混合GGO;③實變;④混合實變纖維;⑤纖維條索影;⑥其它影像[6-8]。并記錄典型的特殊征象如鋪路石征、小支氣管空氣征、暈征、反暈征和白肺等。
所有肺部影像評估均由2位副主任醫師及以上職稱的放射科醫師共同判定。
4.統計分析
使用SPSS 26.0統計軟件對所有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對于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值±標準差表示,分類變量采用例數n(構成比,%)表示。歷次檢查中5個肺葉受累例數差異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5個肺葉受累范圍評分差異的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和Mann-WhitneyU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
本研究中72例COVID-19患者的基本臨床資料見表1。本研究中老年患者(>65歲)較多(29例),既往病史中患有高血壓(24%)和糖尿病(22%)病史者較多見。另外,本組中有2例產婦(在感染之后行剖宮產手術)。最常見的癥狀是發熱(71%)和咳嗽(43%)。38例(53%)患者有武漢旅居史或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觸史,其中12例為家庭聚集感染。

表2 各次CT檢查中各個肺葉受累范圍的CT評分
注:*為發病至首次CT檢查時間。

表3 所有肺部CT檢查中5個肺葉受累情況和受累范圍評分
注:#歷次檢查中5個肺葉受累例數差異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5個肺葉受累范圍評分的差異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
2.首次實驗室檢查結果
47例(65%)患者淋巴細胞計數減低,平均值(1.09±0.59)×109/L;48例(67%)嗜酸性粒細胞計數降低,平均值(0.04±0.08)×109/L;12例(17%)單核細胞計數升高,平均值(0.44±0.20)×109/L;41例(57%)C反應蛋白升高,平均值(25.21±31.03)mg/L;31例(43%)血沉升高,平均值(26.32±26.37)mm/h;32例(44%)D -二聚體升高,平均值(681.15±134.52)ng/mL,31例(43%)纖維蛋白原含量升高,平均值(3.80±0.80)g/L;22例(31%)乳酸脫氫酶升高,平均值(228.79±71.62)IU/L。
3.住院治療情況
本組72例患者中普通型57例(79%),重癥13例(17%),危重癥2例(3%)。58例(81%)接受了氧療,10例(14%)重癥及危重癥患者接受了高流量吸氧。所有患者采用中藥(連花清瘟膠囊、清瘟補肺湯等)及抗病毒藥物(奧司他韋、阿比朵爾、克立芝、磷酸氯喹、利巴韋林等)進行治療,34例(47%)患者使用不等劑量的激素(甲強龍、強的松等)進行治療,32例(44%)聯合使用了抗菌藥(莫西沙星、拜復樂、頭孢類藥物等);25例(35%)患者注射了增強免疫力的藥物(丙種球蛋白等)。住院期間18例(25%)出現肝功能異常,5例(7%)出現腎功能異常,3例(4%)出現皮疹,3例(4%)出現精神行為異常,1例(1%)出現左下肢靜脈血栓。截至2020年2月27日,46例(64%)患者出院,25例(35%)患者仍在院接受治療中,2例(3%)住進ICU病房,其中1例(1%)患者病變進展迅速,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4.肺部CT特點及評估
從發病到首次CT檢查時間為0~15d,均值為(4.44±3.06)d;第一次至最后一次CT掃描時間為6~31d,平均(21.15±5.65)d;相鄰兩次CT掃描間隔時間為1~15d,平均(4.67±2.14天)d。72例患者共進行了374次掃描,3~7次/例,平均(5.19±1.00)次。所有患者第一次至第七次檢查的時間間隔及每次CT檢查各個肺葉累及范圍評分見表2。5例患者首次肺部CT檢查未見明顯異常。
各次肺部CT檢查中5個肺葉受累情況和受累范圍評分見表3。歷次檢查中5個肺葉受累例數及受累范圍評分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采用Mann-WhitneyU檢驗對5個肺葉之間受累范圍評分進一步進行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有以下幾組:右肺上葉與右肺下葉(P=0.032),右肺上葉與左肺下(P=0.008),右肺中葉與右肺下葉(P=0.001),右肺中葉與左肺上葉(P=0.039),以及右肺中葉與左肺下葉(P=0.000)。各肺葉中,以右肺下葉及左肺下葉發病最多見,歷次檢查中總出現率分別為78%和77%(P<0.05),平均得分分別為1.84±1.05和1.94±1.15,以左肺下葉累及范圍最嚴重(P<0.05);右肺中葉發病最少,出現率為 52%,且累及范圍最輕,平均得分1.61±1.00。

圖1 進展-高峰-吸收模式:COVID-19患者,男,54歲,發熱4天伴咽痛、肌肉酸痛,家庭聚集感染,首診時淋巴細胞計數正常。a)發病4天后首次CT檢查,顯示左肺上葉胸膜下有斑片狀GGO;b)第7天復查CT,顯示病變沿胸膜下蔓延;c)第10天CT復查,顯示病變沿胸膜下繼續向背側進展,病變范圍擴大達峰值;d)第24天復查CT,顯示肺內僅殘留少許斑片影。
病變分布以胸膜下多見,可散在分布,重癥者可見雙肺彌漫性病變,甚至呈現“白肺”表現(2例)。在整個病程變化期間胸部CT可以動態觀察到的影像征象有GGO、鋪路石征(4例)、混合GGO、實變影、實性結節(2例)和條索影。1例合并肺不張,2例出現反暈征,6例吸收期可見少量胸水。6例合并慢支肺氣腫,3例陳舊性結核,1例腎積水,1例縱隔內少量積氣。
以CT掃描時間點觀察,病變高峰期約在發病后1~37d,平均(9.92±5.01)d,肺部病變嚴重程度的平均得分為6.15±4.96。根據每例患者病程期間多次(3~7次)肺部CT累及范圍評分百分比,將所有72例患者肺部病變的評分變化歸納為以下5種模式。①進展-高峰-吸收型(圖1):36例(50%)患者首次CT圖像上午異常改變或病變范圍較小,評分較低,隨后的CT檢查提示病變范圍擴大,評分達到峰值之后的CT掃描提示病變范圍逐漸減小,最后一次CT檢查提示病變完全吸收或殘留少許病變。②進展-高峰-緩慢吸收型(圖2):15例(21%)患者首次CT圖像上評分較低,復查CT檢查提示病變范圍進展,評分達到峰值之后多次CT復查提示病變較前少量吸收,最后一次CT胸部檢查時仍有較多的病變殘留,且評分大于5分;其中1(1%)例進展為“白肺”,隨后復查顯示病變略有吸收。③逐漸吸收型(圖3):12例(17%)患者首次CT掃描為評分達到峰值,在隨后的CT復查中提示病變范圍逐漸吸收,最后一次CT評分較低,病變基本吸收或殘留少許病灶。④平臺型(圖4):6例(8%)患者多次CT檢查提示肺部病變范圍評分變化不明顯。⑤持續進展型(圖5):3例(4%)患者胸部CT提示病變范圍逐漸擴大,評分逐漸增大,其中1例呈“白肺”。
肺部CT上病變進展方向的變化可以歸納為以下3種模式。①病變沿胸膜下蔓延(圖1):32例(44%)患者胸部CT顯示GGO進展,沿胸膜下向前后方向蔓延。②病變呈“攤餅”樣擴大(圖6):17例(24%)患者胸部CT上可以觀察到GGO向周圍片狀擴大,部分病變呈圓形擴大,類似于“攤餅”樣改變。③彌漫性進展(圖2、5):13例(18%)GGO范圍明顯擴大,并不局限于肺段,或與其它病變融合呈彌漫性病變,甚至白肺(圖2b)。
胸部CT病變密度的變化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模式:①密度增高-實變-吸收模式(圖2),51例(71%)胸部CT動態觀察可看到GGO病變密度逐漸增高,形成混合GGO或實變或實性結節,吸收過程中可出現或不出現粗大的、縱橫交錯的條片影或條索影。隨著病程延長,纖維條索逐漸變細、變小,最后完全吸收。②病變密度逐漸變淡吸收模式(圖3):23例(32%)患者胸部CT可以觀察到GGO或者混合GGO病灶密度逐漸減低,直至完全吸收,部分患者殘留下少許條索影。
其它征象:3例(4%)可見“沉降征”和“界面征”(圖2a,圖7)。在病變吸收期,72例患者中66例(92%)可見纖維化灶,其中11例(17%)可見胸膜下線(圖8a);19例(29%)可見條索帶(圖8b);43例(65%)可見粗亂條索影,少數病例表現為“柵欄狀”(圖8b)或“粗網狀”(圖8c)。6例(8%)患者肺部未見纖維化灶。
討 論
COVID-19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疾病,并且是致命的。本研究中男女比例各占50%,53%有明確接觸史而感染,其中17%為家庭聚集感染,因此做好防護、隔離是必要的措施。本組病例中最常見的癥狀是發熱(71%)和咳嗽(43%),嗜酸細胞計數(67%)和淋巴細胞計數減少(65%)可能對診斷有幫助,與Chen等[9]報道的數據接近。本研究中重癥占17%,危重患占3%,老年患者(>65歲)較多(40%),最常見的基礎疾病為高血壓(24%)和糖尿病(22%)。住院隔離治療期間部分患者(25%)出現了肝功能異常,是由于藥物作用還是SARS-CoV-2病毒感染所致肝損傷,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研究證據。但是這會導致住院治療時間延長,截至發稿前本組中仍有多例患者(35%)仍在住院治療。本研究中1例患者肺部病變持續進展,因呼吸衰竭死亡。由于納入的危重病例數較少,病死率為1.38%,低于其它的相關研究結果[10]。

圖2 進展-高峰-緩慢吸收模式:COVID患者,女,79歲,發熱5天伴咳嗽、咳痰、乏力和心悸,無明確接觸史,合并高血壓3級,首診時淋巴細胞計數減低,嗜酸細胞計數減低。發病5天后首次CT檢查在其它層面僅發現少量GGO。a)發病第10天,胸部CT顯示胸膜下大范圍GGO,后部病變被葉間裂限制,界限清楚,可見“界面征”(箭)和“沉降征”;b)第14天胸部CT顯示雙肺彌漫性分布的混合性GGO,密度較前不均勻增高,病變進展呈“白肺”表現;c)第19天復查CT,顯示病變密度進一步不均勻增高;d)第24天復查CT,顯示雙肺內可見粗亂的條片狀和條索影,部分形成實變結節,胸膜凹陷。 圖3 逐漸吸收模式:男,65歲,發熱4天伴氣喘,無明確接觸史,合并高血壓、冠心病和糖尿病。首診實驗室檢查淋巴細胞計數和嗜酸細胞計數減低。a)發病4天后(2月6日)首次CT胸膜下及中央區均可見多發不規則斑片狀GGO,主要位于胸膜下,部分病變呈“反暈征”;b)第8天CT 顯示病變范圍變化不明顯,密度減低,見少許條索影;c)第13天病變密度進一步減低,見少許條索影;d) 第23天CT見病變進一步吸收,仍見少許纖維條索影。 圖4 平臺型:女,77歲,發熱3天伴頭痛、乏力、活動后氣促、胸悶,有明確接觸史,首診時淋巴細胞計數減低、中性粒細胞計數升高,合并冠心病和糖尿病,伴有肺部細菌性感染及左下肢靜脈血栓。a)發病3天后首次CT,顯示右肺上葉胸膜下GGO(箭),雙下肺實變;b)第6天CT復查顯示原右肺上葉GGO呈實變表現(箭),雙下肺仍為實變;c)第12天CT復查,病變略吸收,但是評分沒有變化;d)第21天復查CT,病變變化不明顯,并可見右側胸腔少量積液。
COVID-19患者雙肺下葉受累最多見,病變主要位于胸膜下[7,11]。肺部CT表現大致可分為早期、進展期、危重期及緩解期[12]。以CT掃描時間點觀察,病變高峰期約在首次癥狀出現后約10天,此時肺部異常表現出最大的嚴重性,與Pan等[5]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CT病變累及范圍評分也呈現出了基本相同的變化模式,即進展-高峰-吸收模式(50%),這種模式大部分見于普通型患者。但是本研究中納入了臨床重癥型和危重型患者,與PAN等[5]僅選擇普通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不同,因此影像評分變化模式還呈現了另外4種:進展-高峰-緩慢吸收型(21%)、逐漸吸收型(17%)、平臺型(8%)和持續進展型(4%)。由于臨床重癥及危重患者以老年人較多,既往合并基礎疾病及住院治療中并發癥較多,免疫力低下,導致病變遷延不愈,病變吸收較慢,病程較長,此型患者目前均在院繼續治療中。17%的病例首次CT評分即達峰值,經過住院治療后CT復查顯示病變呈逐漸吸收型。平臺型中2例患者有較多合并癥,病變范圍吸收不明顯,仍在繼續治療中;另外4例患者病變范圍較小,多次CT復查評分變化不明顯,事實上病變在大小、形態或密度方面是略有改變的,但是CT范圍評分并不能反映出來,這可能是CT半定量評分的缺點,結合病變密度的變化,可以判斷病情好轉。尤其要重視持續進展型患者,本研究中4%的患者病情變化為這種模式,患者均為臨床重癥及危重患者,合并癥較多,肺功能較差,病情逐漸加重,其中1例死亡、1例行機械通氣治療中。

圖5 持續進展型:男,83歲,發熱5天,有明確接觸史,首診時淋巴細胞計數正常,嗜酸細胞計數減低,合并高血壓和慢阻肺。a)發病后5天首次CT檢查示雙下肺胸膜下有斑片狀GGO;b)第7天復查CT顯示GGO沿胸膜下蔓延;c)第14天CT復查示病變范圍持續擴大,呈彌漫性分布,仍表現為GGO,并可見網格影。患者第20天因呼吸衰竭死亡。 圖6 病灶呈“攤餅樣”擴大。a)首次CT檢查顯示右下肺有一類圓形GGO灶;b)首次CT矢狀面重組圖像,顯示肺內單發GGO病灶。c)3天后復查CT顯示病灶呈圓形擴大,類似“攤餅樣”改變;d)3天后復查CT矢狀面重組圖像,顯示病灶較前擴大。 圖7 COVID患者。CT顯示雙肺上葉內大片GGO,密度由上而下逐漸增高,可見沉降征(箭)和界面征。 圖8 吸收期CT圖像上3種不同形態的纖維灶。a)平行于胸膜的胸膜下線;b)右下肺內可見垂直于胸膜的條索帶,左下肺為形似“柵欄狀”纖維條索灶;c)左下肺為雜亂的纖維條索影,縱橫交織成“粗網狀”。
胸部CT顯示44%的患者可見GGO進展沿胸膜下向前后方向蔓延,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病變進展模式。24%的患者顯示病灶為片狀擴大模式,通常見于非胸膜下GGO病灶,因為沒有葉間胸膜或壁胸膜的阻擋,呈片狀向周圍蔓延,部分病例以小支氣管血管束為中心向四周均勻“攤餅樣”擴大,比較典型。18%的患者呈彌漫性進展模式,比較兇險,通常見于重癥患者,病變不僅沿胸膜下擴大,同時沿支氣管血管束向肺野內帶和中帶延伸,或與其它病變融合呈彌漫性病變,甚至呈“白肺”表現。
胸部CT動態觀察發現,大部分患者(71%)的肺部病變呈GGO-實變-吸收模式,進展期GGO病變密度逐漸增高,然后形成混合GGO或實變或實性結節,尤其是峰值期為彌漫性病變,在吸收期病變密度減低,邊緣固縮,隨后出現粗大的、縱橫交錯的條片影或條索影,隨著病程延長,纖維條索逐漸變細、變小,最后吸收。大部分患者(92%)在病變吸收期可見纖維化灶,主要表現為3種形態的條索影:第一種是平行于胸膜的胸膜下線,與胸膜粘連不明顯或較輕;第二種是垂直于胸膜的長條狀條索帶,尾部可延伸至肺野的中帶甚至內帶;第三種粗亂的條索影,最常見,通常可以引起多處胸膜凹陷,少數病例表現為“柵欄狀”或“粗網狀”。32%的患者肺部CT病變呈現密度逐漸變淡吸收模式,首檢CT表現為GGO或者混合GGO病灶,在動態觀察中發現密度逐漸減低,直至完全吸收,或短時間內殘留少許纖維條索。
本組中在3例患者的肺部CT上觀察到位于雙肺上葉的大片混合密度影,病變上部較淡、向下逐漸增密。組織學檢查為肺泡腔內充滿大量黏液及損傷脫落的肺泡上皮[13],可能是由于患者長時間臥床或者在仰臥位CT掃描時的重力關系造成的“沉降征”,病變的下部因靠近葉間裂附近而被葉間裂所隔斷,形成境界清楚的“界面征”。
患者在住院期間的病情變化不單單是體現在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查數據和影像變化,而且還體現在心理和精神層面。本研究中有3例(4%)患者出現明顯的精神或行為異常,1例患者有自殺傾向,1例患者明顯抑郁,還有1例患者煩躁不安、不配合治療。因此住院隔離期間患者的心理疏導也應該值得關注。
綜上所述,COVID-19肺部CT動態變化模式為評估患者的病情變化和及時調整治療方案提供幫助,結合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結果,對臨床治療具有指導意義。本研究不足之處在于樣本量較小,沒有對患者進行臨床分組研究;其次是所觀察的病程時間較短,接下來的研究方向就是擴大樣本量、密切追蹤患者的病情變化及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