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處是吾鄉
周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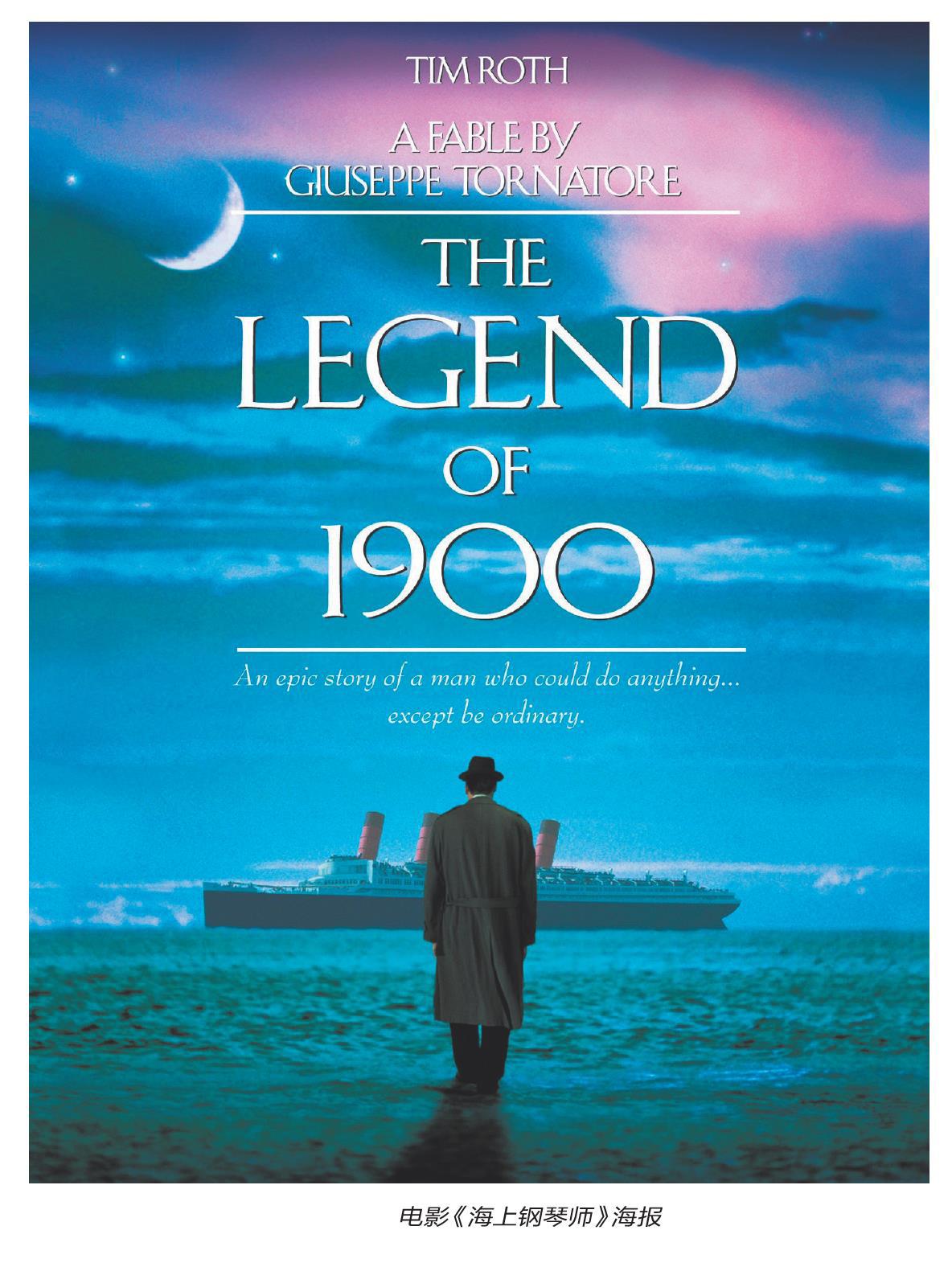

經典作品之所以經久不衰,在于其每個時期都能煥發出觀照當下的深刻意義。1998年,當意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托雷執導的《海上鋼琴師》首映時,人們已經領略到天才鋼琴家“1900”孤獨卻令人驚嘆的傳奇一生。時隔22年后的今天,《海上鋼琴師》以4K修復版重現于銀幕,人們得以發掘影片“更深一層”的“興味蘊藉”。
從羅蘭·巴爾特有關批評是“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創造性觀點,到“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展現出對于文本(本文)的自由式解構,再到伊格爾頓和杰姆遜等提出的穩定的歷史性定見,關于藝術作品的讀解一直沿著類似約翰·菲斯克提出的“受眾主體性”視角持續發展與演變。從受眾主體性的角度看,任何藝術作品其實都存在著一對相互對立的“雙重文本”(也即雙重本文),正如學者所述,“雙重文本”不僅可以作為“一切本文共有的特性,也可以被視為文化的一種修辭術……文本總是由意識文本(表層結構)和無意識潛文本(深層結構)組成的”[1]。
具體延伸到電影領域,這種解讀類似電影文化上的“修辭論闡釋”,亦即不再是“復述普通觀眾在觀影時看到的東西并對此提供闡釋”,而是“直接呈現在普通觀影時容易遮蔽或抑制,卻在電影文本中確實存在、更多地屬于無意識層面的東西”。可以說,這種從“電影文本與社會文化語境相互依賴”的關系角度,重新發現和合理化闡釋的對象,就是“第二重文本”。[2]本文將通過以下幾個部分的論述,在重映版《海上鋼琴師》中挖掘之前未被發現的“第二重文本”,以提供一種對《海上鋼琴師》的差異化解讀。
一、“世事如夢”與“鏡中窺人”——超越“自由”的自由
《海上鋼琴師》講述了天賦異稟卻孤獨憂郁的天才鋼琴家“1900”的傳奇經歷。對于絕大部分觀眾來說,無論是對世俗社交的漠不關心、對一見鐘情女孩的欲言又止、對繁華城市的惶恐無助乃至對于堅持一生“不下船”的執拗堅持,都讓他們讀解出“1900”性格中那份極度內向、孤獨、善良和敏感的“詩人”特質。面對光怪陸離的世界和形形色色的人群,“1900”選擇的態度是回避與逃離,他享受徜徉在自己所創造出的心靈世界中,并深信著如薩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獄”。因此,即使是愛情的本能沖動帶給了他前所未有的巨大勇氣,“1900”最終也沒能完成踏上陸地的“重要一步”。
這一層面看,觀眾從《海上鋼琴師》的“表層意識文本”中,得以解讀出“對自由的追尋”——主人公“1900”對于外在世界的恐懼與無助,對于名利的漠然與淡定,對于航行于大洋上巨輪的堅守,都更加反襯出“絕對的自由”在其內心占據的最為重要的位置。影片中以小號手麥克斯為代表的絕大部分人(包括觀看電影的受眾),囿于世間難以擺脫的情感糾葛、利益關聯、人情世故,往往被動選擇被生活逼迫著“負重前行”,而只有“1900”始終遵循內心的聲音,做到了一生都未忘“初心”。正因如此,觀眾于不知不覺中將現實生活的情境投射進《海上鋼琴師》,將自身對“絕對自由”的渴求移置到“1900”身上,即潛移默化地完成了銀幕與現實間角色隱性的“審美置換”[3]。因此,觀眾在這“第一重文本”中,解讀出了當下現實生活的困境與內心對于“自由”的無限渴望,同時這種強烈的渴望轉而在“1900”身上得到了“替代性滿足”。這也是絕大部分觀眾感到“1900”吸引他們的原因所在——他們在其身上讀出了自己孤獨的“影子”。
然而筆者認為,《海上鋼琴師》在對“1900”這一角色塑造的目的上,其實還隱藏著更深一層的“第二重文本”。“1900”作為角色本身,確實有如上分析的性格特質,但影片更加震撼人心之處在于,《海上鋼琴師》塑造的這位風度翩翩追尋自由的“肖邦”式人物,實則是一個符號化的象征——“1900”是一面用來照見人世間萬物的“鏡子”。《海上鋼琴師》由“1900”這面鏡子,映射出世俗社會中熙熙攘攘的眾生百態,觀照出桎梏在社會中的人所面臨的種種痛苦與束縛。鏡子本身是“如如不動”的,不存在所謂的喜怒哀樂,因此觀眾從“1900”的臉上看不到成人世界中那種由壓力導致的壓抑感,反而永遠呈現出少年般的純真;但由“1900”這面鏡子映射出的世間百態,卻飽含銀幕上眾生的顛倒執念,甚至呼應著銀幕外,當觀眾走出電影院后即將面對的苦楚煩惱和糾結人生。因此,“1900”的性格是否存在極度的“憂郁、敏感、執著”并不重要,因為“1900”作為影片表達的“想象的能指”,其背后的“所指”是獨立于世俗思維和蕓蕓眾生的如同鏡子般清醒的“旁觀者”。“1900”得以追尋無限“自由”的原因,就在于他如小說《死神的精確度》中的角色一樣,能以“旁觀者”的心態,帶領觀眾毫無心理負擔地對世間人生百態進行觀察,如“鏡子”般平靜而客觀地映現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影片前半段,幼年時期的“1900”是通過半透明的彩色玻璃去觀察船上形形色色的眾人的,他透過絢麗但模糊的玻璃觀察這一舉動,象征著由他所帶領的觀眾觀看的恰恰是“如夢幻泡影”的虛幻世界;他賦予船上客人由不同旋律構建出的精妙樂曲的行為本身,暗示著他如一名“編劇”,在通過細致入微的感知力,游刃有余地創造著銀幕中出現的不同人物、性格及其內心。因此,觀眾可以在《海上鋼琴師》“第二重文本”中解讀出這樣的意味——人生其實就如同“1900”構建的這“一場大夢”,世間的煩惱、糾葛、痛苦只是夢境中的“故事”,而“做夢者(觀眾)”應該如“1900”一樣清醒地看待一切的流變。“1900”又如放映著銀幕上這一切影像的“放映機”,在通過銀幕中的塑造提醒銀幕外正在觀看的觀眾,不要太執著于“故事”所構建的紛繁和苦痛,不要忘掉了初心,因為這一切只是一場“大戲”和夢中幻象。
《海上鋼琴師》從很多細節安排上暗示了確實存在這“第二重文本”。例如,片中麥克斯總是控制不住地不斷快速晃動自己的眼球,而實際上只有當人正在“做夢”時,眼球才會迅速移動,這似乎暗示著麥克斯和片中人們一樣,正活在一場“大夢”中;而大海、巨型輪船等具有“崇高感”“夢幻感”的特殊意象,以及“1900”傾慕的、從船艙窗戶看出去充滿神圣柔光的女孩,也都與“夢”有著很強烈的關聯意味。
“事如春夢了無痕”,當輪船上早已沒有鋼琴可以彈奏之時,“1900”仍然選擇張開雙手,于虛空之中彈奏想象中的88個琴鍵,這恰恰說明“1900”的心永遠是自由的,只要他想,他在腦中隨時都能彈起鋼琴。當人們在即將炸毀的輪船上無論如何都找不到“1900”的身影時,只有麥克斯能通過放起曾經的音樂將他“召喚”出來。這時“1900”所說的話很耐人尋味:“麥克斯,你是唯一知道我在這里的人,你要習慣這一點。”對于“1900”這個“筑夢者”來說,銀幕中的一切、包括麥克斯都只是他夢中的角色,正如張愛玲所說:“向來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劇中人。”影片試圖通過“1900”告訴觀眾,“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人生就如同夢境一般,本質上沒有所謂的別人對你的看法,事情帶給你的壓力和痛苦,本質上也沒有所謂社會關系、世俗壓力對于一個人的捆綁和阻礙,這一切都是感覺本身強壓給自己的一種“感覺”,因而沒有任何人和煩惱能進入一個人的內心去束縛他的絕對自由。
二、時間的綿延與專注的力量——活在當下的重要意義
《海上鋼琴師》中對觀眾沖擊力最強、讓觀眾印象最深刻的,非“斗琴”一段莫屬。“1900”以極高的音樂天賦震撼了觀看斗琴全程的在場觀眾,也讓銀幕前的觀眾大呼過癮,拍案叫絕,為“1900”的高超技藝所傾倒。當爵士樂大師傲慢地以演奏終了的鋼琴臺上仍能維持長長香煙煙灰,作為其“穩定”發揮的炫技資本時,“1900”則“技高一籌”,通過演奏完畢后的以滾燙的琴弦點燃香煙的瞬間,征服了對手,也震撼了全場。可以說,從斗琴一段的“第一重文本”層面,觀眾感受到了“1900”爐火純青的技藝、超群的應變能力、“人琴合一”的精湛功力與無與倫比的心理素質。這一切都體現出“1900”對于鋼琴技術和藝術非同常人的天賦,以及為藝術而生般遺世獨立的特殊魅力。
然而進一步看,“斗琴”片段其實還蘊藏著對于“第二重文本”的展現——影片展現了“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的強大力量,即“專注當下”的精神境界。哲學家柏格森提出的“時間的綿延”理論實際指出了一個道理:人們往往沒有真正“活在當下”,人們感受著一段一段時間的流動,但其實是每一個當下才是真正可以把握的瞬間。與“1900”比賽的爵士樂大師,在看似無出其右、登峰造極的技術背后,缺少的正是對于彈奏樂曲的每一個當下的絕對“投入”,他沒有真正享受“當下”每一刻的“無我”,仍然在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的境界游蕩;反觀“1900”,他只要開始彈奏鋼琴,就能做到如孩童投入游戲一般,全身心投入到每一個音符之中,享受著每一個當下瞬間的快樂,即使在無數觀眾營造出的關乎巨大顏面的斗琴比賽中,也能完全拋開他人賦予的關注和壓力,真正進入“物我兩忘”的狀態,步入同六祖惠能所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精神境界。
由此可見,斗琴一段戲中深藏的“第二重文本”展現了“活在當下”的力量。“1900”超越爵士樂大師彈琴之處,就在于王陽明所說:“饑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對于“1900”來說,彈琴這只是一件關乎自己快樂的事,它無關他人,無關比賽,無關觀眾。縱觀“1900”短暫的一生中,他的偉大就在于,真正做到了享受當下,永遠在體會著生命的流變過程。人的專注度往往如同蠟燭火苗一般脆弱,當外界有風吹動時,火苗往往不斷搖晃波動,即使在絕對封閉無風的環境中,火苗仍然會難以控制住地不斷搖曳。《海上鋼琴師》中,導演特別安排了兩個細節來證明“專注當下”的巨大力量——全身心沉浸在觀看“斗琴”當下的觀眾中,一位戴著假發的貴婦專注到假發掉下來丑態盡顯卻毫不自知,而另一位紳士專注到香煙燒著自己的衣服仍毫無察覺。
“1900”在斗琴結束時,他的極端專注導致鋼琴琴弦能夠產生巨大能量點燃香煙,而人心如若能像“1900”彈琴時一樣保持絕對的“投入”,就將“制心一處,無事不辦”。這就好比在火苗上來回晃動的手指永遠不會被灼傷,但如果維持手指在火苗上不動達到3秒鐘,手指就一定會燒傷一樣。已經完全忘記比賽本身的“1900”,他專注于當下后享受到的是“無我”的無限快樂——人活生生地“活著”的存在感。因此“1900”的一聲雖然短暫,但每當他“活在當下”的時候,片刻就成為了永恒。
三、對“不下船”的再思考——“生活在別處”與不存在的“別處”
每一名觀看過《海上鋼琴師》的觀眾,都會被一個問題縈繞心頭——為什么“1900”最終也沒有選擇下船?這在“1900”最后對好友麥克斯的一段話中或許可以找到解釋:“城市不斷蔓延,包含一切,除了盡頭,它是無窮無盡的,想到這一切難道不會崩潰嗎?”對于“1900”來說,他是輪船上的王者,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駕馭鋼琴鍵旁上的88個黑白鍵,但是到了陸地上,面對綿延不斷又繁亂復雜的人情社會,他沒有能力再去感受到那種“絕對的自由”。
因此,從《海上鋼琴師》的“第一重文本”來看,“1900”就如同大海中的鯨魚——鯨魚可以在廣闊的海洋里自由徜徉,但一旦登上陸地,鯨魚就會因感到內部“壓力”過大而“爆炸”而亡。對于“1900”來說,“下船”反而意味著失去了自由,城市對于“1900”這樣純粹的人充滿了看不見的盡頭。城市中物欲橫流,無限的欲望會將人們“牽著走”,那些因人而憑空制造出來的規則、產生的繁雜信息,壓迫著人們去處理各種繁重的關系,并徒增了無盡的苦惱(現代社會中那些時刻被手機信息和電子屏幕攫取著時間精力而被掏空的人同樣如此)。因此,“1900”才會本能地對船長喊出:“去他的規則!”也才會說出這樣充滿哲理的話語:“我覺得陸地上的人,浪費了太多時間去問為什么……冬天來了,你們渴望夏天,夏天到了,你們又害怕冬天再來。”可以說,《海上鋼琴師》充滿了一種對人渴望“生活在別處”的欲望投射,正如弗羅斯特的詩作體現出的意境一樣,“人們雖然有時也想逃避苦惱的現實,但若是真的讓他們離開世界,他們又會感到空虛與恐慌”[4]。
人們(包括銀幕外觀看《海上鋼琴師》的觀眾)永遠試圖尋找更加美好的“彼岸”,但是這種對“生活在別處”的想象背后,只是一種對于身份認同的“無地焦慮”。《海上鋼琴師》《出租車司機》等電影都是在展現都市中人們對于在地化“身份”的認同,大部分人都在通過對于自身身份的確認來明確自己的存在價值。“地點是人的生存的具體物質場所,是人的具體生存意念或理想的物化形態。正如海德格爾指出:“‘地點(place)把人放置在這樣一種方式中,以致它顯示出他的生存的外在鐐銬(external bond),并同時顯示出他的自由和現實的深度(depths of his freedom and reality)。”[5]而當對于自身所在“地點”的存在無法確認時,人們往往就會產生身份焦慮——例如長期漂泊在海洋上的船員們,會通過重新踏上陸地這樣的固定場所,感受到“依地生存”的踏實。同時,由于身體是“最具體而又細小的人的生存地點單位”,因此身體成了“強烈的無地焦慮的最后的解決場所”,“無地焦慮只能用地點流動去解決”。[6]
如學者所述,人們“恒定不變的可信賴的地點情結已經和正在被肢解,而代之以變動不居的處在風險中的無地生存。這種無地生存的一個基本標志,就是生存的流動性,即個人生活必然地時常處在從此地向異地的流動中”[7]。正因如此,“1900”才會說:“所以你們永遠不厭倦旅行,總是尋找遙遠的地方,永遠是夏天的地方。”這是一句對于人性殘忍而精確的總結——人們永遠都渴望尋求到更好的“別處”,他們看似雙腳踏上了穩定的大陸,實則窮其一生都在隨著欲望而“漂泊流浪”;“1900”看似一直沒有下船,實則他的內心早已真正安定下來,他決定不再隨著漂泊,因為生活在別處只是一種欲望的本能牽引,實際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別處”。
影片中當“1900”已走下舷梯但最終決定放棄下船的那一刻,導演安排“1900”形成了一個“凝視鏡頭”的畫面。拉康認為:“‘凝視是主體重返‘實在界的重要途徑,主體通過‘凝視現象,才能發現和認清自己欲望的深淵。”[8]如拉康指出的那樣:“‘凝視理論正是通過用電影中不同的角色來復制觀眾自己的欲望,才使觀眾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體,由此建立起真正的主體性,并讓每位觀眾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欲望的深淵。”[9]由“1900”的這一凝視,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揭開《海上鋼琴師》此處存在的“第二重文本”。當“1900”即將下船但最終凝視屏幕后,他并沒有邁出那一步,這源于他意識到,其實根本就“無船可下”。整個陸地乃至整個地球、整個宇宙,本質上都是那艘巨大的“輪船”,人作為其中的一個角色,永遠不可能做到“真正下船”,只有內心徹底感受到安定和解脫,才是真正的“下船”。因此,人們普遍意義上認為“1900”被那艘船束縛住了,但其實船也是“1900”的心中物;當陸地上的人們都被物質欲望、被世俗煩惱、被愛情痛苦以及被城市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規則束縛住的時候,不要忘記,只要內心不被所謂的規則束縛,才是真正的自由。正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
結語
很多觀眾或許會感到《海上鋼琴師》緩慢的節奏難以理解,感到影片情節冗長而不知所云,而這一點恰恰說明了發掘影片中“第二重文本”的重要價值。如學者所說,“每一部電影作品都不是封閉的完成體……呼喚著觀眾和評論家去做二度、三度,甚至更多的超常打量”“電影文化修辭闡釋的目標,正是通過借助于表層的意識文本來探測那暫時隱匿在深層的無意識文本”[10]。“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觀眾能夠從《海上鋼琴師》的淺文本層面讀出對自由的渴望、對藝術天賦的贊嘆以及對“生活在別處”的想象性滿足,但進一步可以從深層文本挖掘出“超越自由”的自由、“活在當下”的力量和實際“無船可下”的哲學思辨。應該說,第二重文本屬于“觀眾以特殊眼光才可以窺見的哪些隱秘的電影形式及其意義蘊藉”[11],這也許就是經典能帶給觀眾回味無窮的終極魅力。
參考文獻:
[1][3]王一川. 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 M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16,67-70,.
[2][5][6][7] [10][11] 王一川. 第二重文本:中國電影文化修辭論稿[ 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序)7,89,90,90-91,(序)7,(序)7.
[4]孫梅琳. 對羅伯特·弗羅斯特自然詩作的新認識[ J ].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6,(1):52.
[8][9]張竑.“凝視”的秘密——窺探齊澤克理論大廈的入口[ J ].黑龍江社會科學,2019(3):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