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霍爾奈:走出弗洛伊德陰影的女性心理學家
謝天海

談到心理學,人們會想到著名的德國心理學家、精神分析的奠基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他提出的夢的解析、自由聯想等心理研究和治療方法長期以來已成心理學研究的代名詞。然而,弗洛伊德理論很多觀點受到其歷史條件的限制,對人類心理的描述存在很多不準確甚至不科學的表述,但很多人自封為正統的弗洛伊德門徒,他們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堅守一定程度上成為當代心理學發展的障礙。有很多心理學家在挑戰和修正弗洛伊德理論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本文就向大家介紹一位勇敢走出弗洛伊德陰影的德國女性心理學家卡倫·霍爾奈(1885—1952)。
成長:女孩、醫學生、母親
1885年9月16日,卡倫·霍爾奈出生在德國漢堡附近布蘭肯斯小鎮上一個八口之家。父親布蘭德是一名船長,終年工作在南大西洋和合恩角地帶危險的水域,很少回家,他對子女非常嚴格,平時不茍言笑,卡倫的童年得到父親的關愛很少。盡管如此,卡倫從小就愛說愛笑,喜歡編故事,用洋娃娃當演員演出各種自編的小劇,她最喜歡扮演的角色就是印第安阿帕奇部落的酋長。上學以后,她學習努力,贏得了所有同學和老師的喜愛和尊重。從那時起,她就喜歡分析他人的性格,15歲時,她在日記里寫下了對自己老師的印象:“舒爾茨先生有趣,聰明而且安靜;迪特里希博士很英俊但非常不公平,可他在校外很活躍而且友善;班寧小姐像個天使,有魅力、聰明,惹人喜愛。”
一般來說,那個時代德國女孩初中畢業后就會離開學校,成為家庭主婦。但在世紀之交,這種情況正在悄然改變。1894年,在卡倫所在的小鎮不遠的巴登鎮建立了德國第一所女子高中。1900年,漢堡女子高中也正式開課。卡倫初中時萌發了學醫想法。父親對她的想法極其反對。與19世紀的絕大多數德國家長一樣,他認為女孩子應該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務,但卡倫的意志不可動搖。她在日記中寫道:“他可以阻止我上學,但無法阻止我求學的愿望。”在她的堅持之下,父親終于同意她繼續上高中,于是卡倫在1901年離開了家鄉去往漢堡,開始了她的求學之路。
1906年,卡倫通過了大學入學考試,具備了入學資格。但當時大學很少招收女生。幸運的是弗萊堡大學更改了招生政策,卡倫于是搬到了弗萊堡。弗萊堡位于德國的最西南端,距離漢堡有500公里,乘火車需要12個小時,小城古色古香,像個童話世界。學校里有上百個男生,卡倫是為數不多的女生。但她并不在意社會習俗,常常和男生一起喝酒、遠足。在一次舞會上,卡倫認識了未來的丈夫,同為大學生的奧斯卡·霍爾奈。奧斯卡為人安靜,是一個優秀的聆聽者,對于卡倫的想法和取得的成績由衷地贊賞。 1909年,二人正式結婚。奧斯卡在一家著名的煤礦能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二人一起來到柏林,開始新的生活。
婚后的最初幾年,兩人過著幸福的生活。奧斯卡職位不斷上升,工資也越來越高,兩人住進了柏林郊區的別墅,并養育了三個孩子。但卡倫并沒有甘于成為家庭主婦,她選擇了精神病學作為專業。在20世紀初,精神病學仍然作為內科學的一個分支,卡倫的教授們都對弗洛伊德認為精神原因是一些身體癥狀根源的看法不屑一顧,將他使用的催眠、解夢和自由聯夢等治療方法視為妖術邪法。但卡倫卻對弗洛伊德的觀點和方法心醉不已,白天學習傳統醫學,晚上研修弗式理論,閱讀了大量理論著作,而且參加了很多弗洛伊德學派的著名學者,包括榮格、蘭克和阿德勒的講座。同時,她還每周六次接受德國當時唯一一位專業精神分析師,弗洛伊德的學生卡爾·亞伯拉罕醫生的心理咨詢,在了解心理分析理論的同時對自己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卡倫過分醉心于工作,并與奧斯卡在育兒問題上產生分歧,兩人的親密關系逐漸產生了裂痕。尤其是“一戰”之后,德國經濟出現了通貨膨脹,使奧斯卡的公司遭遇嚴重的財務危機。卡倫最終選擇與奧斯卡離婚,自己帶著三個女兒獨立生活。
學術:“真理比權威更可貴”
與奧斯卡分手以后,卡倫通過了醫學博士論文答辯。在一次名為“精神分析療法技術“的講座中,公開宣稱自己為弗洛伊德陣營成員。她加入柏林精神分析學院,成為六名核心成員中唯一的女性,為市民進行免費心理咨詢,并為學生授課。學院制訂的學生培養模式包括聽課、自我精神分析以及在導師指導下對病人進行治療,這成為世界范圍內培養精神分析師的標準模式。同時,卡倫面向社會進行的講座不僅吸引了醫學從業者,而且受到柏林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卡倫性格和藹,對待所有人,包括學生們都像朋友一樣,因此很快就擁有了大批的擁護者。
卡倫雖然受到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卻對其理論并非盲目接受。她認為弗氏理論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帶有強烈的性別色彩,對于女性心理的描述失于粗暴和武斷。1922年,在國際心理學年會上,她提交了一篇有關于女性“閹割情結”的反思性文章。“閹割情結”理論認為女性對男性生殖器存在妒忌,將自身視為被閹割的男性,這一生物學上的錯誤認知會成為女性成長中的轉折點。雖然女性會糾正這一誤解,但心理影響久久不會消失。卡倫對于這一觀點提出了謹慎的質疑,認為女性對性別差異的認知與弗氏理論的表述不符,“閹割情結”缺乏事實根據。而在為紀念弗洛伊德七十壽辰出版的論文集中,卡倫再次表達了不同看法,她明確指出:“女性與其說對男性的身體存在妒忌,不如說是嫉妒社會賦予男性的特權。”卡倫的看法在一定范圍內受到了正統弗氏理論學者的反對,而弗洛伊德本人僅僅在五年之后一篇文章中回應道:“這一看法與我的印象不一致。”
1930年代初,民族主義的抬頭令德國國內反猶主義論調甚囂塵上。希特勒上臺之后,對于猶太人的排斥逐步升級。弗洛伊德是猶太人,精神分析也被稱為“猶太人學說”遭到禁止。他的著作被公開焚燒,很多猶太學者受到盤問和限制,被迫選擇逃往美國。卡倫雖然是雅利安人,不會受到傷害,但她的學術關系和圈子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她也興起了奔向美國的想法。1932年,卡倫接到了以前學生弗蘭茨·亞歷山大來自美國的電話。弗蘭茨在美國芝加哥建立了精神分析中心,邀請卡倫前往工作。卡倫的兩個大女兒已經獨立,于是她帶著15歲的小女兒蕾內于1932年9月跨越大西洋,來到美國。

到達芝加哥后,卡倫擔任了精神分析中心副主任,開始指導學生并接診病人。卡倫同時還和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成了好友,包括卡爾·麥辛格醫生和人類學家、以研究原始部落青少年女性聞名于世的瑪格麗特·米德,很快同為歐洲難民的埃里克·弗洛姆也成了卡倫的好朋友,一個圍繞在卡倫周圍的學術圈子開始形成。精神分析在美國尚屬于一個新生領域,卡倫由于和卡爾·亞伯拉罕的關系,被視為弗洛伊德學派的再傳弟子,卡倫和弗蘭茨出版了期刊并面向公眾舉辦講座,教育美國人民精神分析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卡倫在她所開創的女性精神分析領域繼續進行研究。1933年,她在美國心理學季刊上出版了《愛的超價值》一文,文中指出,雖然現代社會允許女性實現個人價值,但傳統的社會觀念仍然期待她們作為賢妻良母,如果一位女性放棄了自己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身份,就會被視為反常,這種社會觀念會導致女性內心的強烈沖突,為了解決這一沖突,女性會強迫自己尋找丈夫或者同性伴侶,將其他女性視為競爭對手,認為其丑陋或者不可愛,并將自己的婚戀關系視為獲得自我認同的關鍵。卡倫總結道:“她們認為只有通過愛情才能獲得幸福,而實際上愛情僅是幸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她們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會不斷減弱。“這篇文章不僅體現出卡倫對女性社會處境的敏感性,同時也說明她認為個體的發展受到個性和社會環境的雙重影響,與弗洛伊德的先天決定論產生了質的區別。
此文一出,引起了美國心理學界的爭論,尤其是在正統弗洛伊德學派擁護者當中引發了巨大反響。卡倫很喜歡這樣的爭論。她發覺很多的批評者來自紐約,于是離開芝加哥赴紐約工作。雖然在紐約舉目無親,但她對自己有著極大的自信。她申請成為全美影響力最大的紐約精神分析學院的會員。填入會申請表時,要求填寫其指導教師的名字,卡倫寫道:“自1920年心理學生采用導師制以來,本人一直在指導他人學習。”而在“所學課程”一欄,她同樣自信地寫道:“自從心理分析課程出現以來,本人一直在給別人上課。”這種霸氣外露的個人陳述令她順利加入了學院,當然也為以后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來到紐約后,卡倫過上了奢華的生活,她的住所位于紐約市中心,俯瞰中心公園。她很快結交了很多紐約市文化藝術界的名流,大部分都是來自德國的流亡人士,同時,弗洛姆也移居到了美國,卡倫與他共墜愛河。卡倫與這些新結交的伙伴一起喝酒談天,有時一直聊到深夜。與此同時,卡倫又與紐約社會科學研究院搭上了關系,這一學院由美國著名知識分子如約翰·杜威以及索倫斯坦·范伯倫建立,學院有一個名為“流亡大學”的項目,吸引了大批為逃避納粹來到紐約的猶太學者和藝術家。項目坐落于格林威治村附近,其迷人的藝術氣質令卡倫欲罷不能。自1935年起直到去世為止,卡倫每年至少在這里教授一門課程,并做了大量面對公眾的講座。她的性格和氣質吸引了大批的學生、病人和支持者,也形成了著名的“星象俱樂部”,除去卡倫之外,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還有心理學家哈利·蘇利文、克拉拉·湯普森和威廉·西爾伯格。四個人趣味相投,常常一起去酒吧,聽爵士樂,交流思想,這些朋友對她以后獨自單飛起到了關鍵作用。
1935年,卡倫開設了名為“文化與神經癥”的系列講座,旨在討論神經癥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卡倫認為,神經癥患者喜歡攀比,總希望超過他人,最終導致幻想破滅而身患疾病,而在注重競爭、努力、成功的美國文化中,神經癥特別容易產生。在講座中,卡倫對弗洛伊德的觀點進行了認真的批判,她指出“神經癥并非對嬰兒態度的重復或者故態復萌,而是早期人生經歷的后果產生了質變與量變”。卡倫并不想讓那些正統的弗洛伊德信徒們感到不快,因此她還是強調了童年經歷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當她試圖將講座開設為一門課程在學院講授時,她的提議被駁回了。因為有一些學院的教授們認為她的學術觀點、行事風格以及在學生中的名氣有可能把學生引上邪路。
面對這些阻力,卡倫勇敢地予以回應,1937年,她將講座出版成書,名為《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在序言中,她公開宣布自己離開弗洛伊德學派,提出新的心理治療方法。她還提出了對弗洛伊德的辯證看法:“對于弗洛伊德偉大成就最好的尊重應該是繼續發展他所奠定的基礎,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在將來充分實現心理分析作為一種理論和療法的各種可能性。” 和她事先預測的一樣,本書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她的擁護者們認為這種新的療法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而在正統弗洛伊德主義者眼中,這本書絕對是離經叛道,認為是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對于弗洛伊德科學觀念的無恥詆毀,尤其是這本書出版時,弗洛伊德已經風燭殘年,正在受到癌癥的折磨,這種做法是對權威的極大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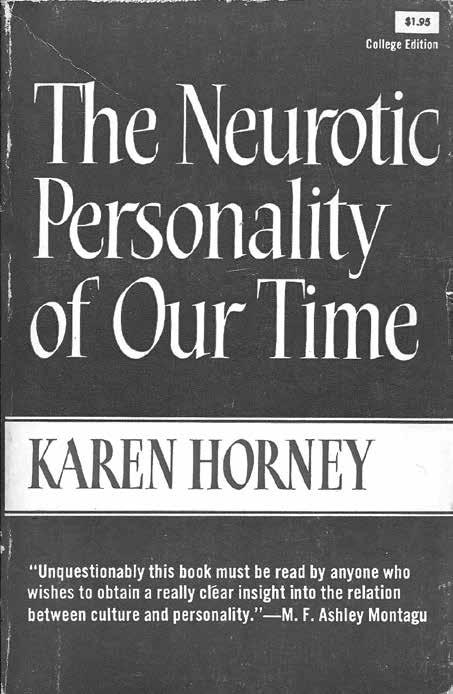
此后不久,卡倫就受到了來自正統弗洛伊德主義者的排擠。1939年,卡倫在紐約精神分析學會發表了《弗洛伊德思想中對創世記的強調》的講話,在此后的閉門討論中,卡倫受到了很多學會成員的批評,學術爭論漸漸演變成人身攻擊。卡倫呆坐在觀眾席里,流下了眼淚。1940年,學會發布了一系列新規定,要求所有會員在向學生講授新觀念和新理論時需要明確上報,由學會教育委員會決定哪些理論應該教給學生們。以前由學生挑選教授的方式也改為由教育委員給學生指定教授。不言而喻,這些規則的改變就是旨在減少卡倫在學會和學生當中的影響。而卡倫的學生也遇到了困難,很多由她指導并修改的論文被“以分析內容不足”的理由退稿。學生們覺得他們和卡倫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自發組織起來表示抗議,但在學術政治的干預下,并沒有什么效果。1941年,學會宣布將卡倫降格為講師。聽到這個消息,卡倫憤然離開了會堂,兩天后,卡倫以及四名同事向學會提交了一封短信,指責學會“日趨墮落,維護傳統思想取代了科學探索的自由精神”,并宣布退出精神分析學會。
晚年:“尋求心靈的終極安寧”
從精神分析學會退出后僅僅一個月,卡倫在“星象俱樂部”好友的支持下,自行成立機構,名為“高級精神分析”學會(AAP )。當年秋天,學會開設了精神分析課程,宣稱招收學生“應為聰明而且有責任心的成年人” ,課程宗旨在于“去除僵化觀念,本著科學與學術民主的精神,對來自各類源頭的思想作出回應。” AAP的成立可謂恰逢其時,1941年底,日本偷襲了珍珠港,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國內處于一片恐慌之中。卡倫抓住機會,發表了一篇名為《理解恐懼》的文章,指出個人對緊急事件的恐懼需要通過社會的方式加以處理。《紐約時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同時向幾百萬名讀者提供了應對恐慌的各種建議。在同一個月內,卡倫出版了她的另一部著作,名為《自我分析》,指出那些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可以在分析師指導下進行自我分析,從而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直面心理問題。一定程度上,這本書削弱了心理分析師的職業作用,因此也受到了專業人士的批評,有書評將其稱為“三塊錢的自我分析指南”,但無論如何,這種將心理分析從象牙塔中帶向公眾視野的作法,為卡倫贏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僅僅一年間,AAP 發展異常迅猛,不僅招收了很多學生,而且還開設了眾多的講座,擁有一眾學者朋友助陣,卡倫底氣十足,在1942年初召開了首次心理學年會。與紐約精神分析學會相比,AAP顯得更為寬泛,不僅研究精神分析,而且強調其跨學科性,將文化與社會學領域也納入研究視野。正如學會副主席、卡倫的朋友威廉· 西爾伯格所言:“心理分析不僅是一種治療手段,也是一個心理學科,滲透到每個需要研究人性的領域并為之提供啟示。”
AAP的發展令紐約精神分析學會非常不滿,他們決定要清理門戶。早在1941年底,學會會長勞倫斯·庫比在《心理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聲明,稱卡倫離職并非學術迫害,將卡倫和朋友們稱為持不同政見者,認為他們對于精神分析學會的指責混淆了視聽,影響心理學生做出正確判斷。庫比還在很多協會進行了一系列講座對卡倫進行批評。庫比的做法獲得了全美心理協會新任主席曼寧格的支持。在曼寧格的阻撓下,AAP沒能成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學生們無法獲得精神分析師資格,論文不被主要期刊接受,也不能參加全國性心理學會議。與此同時,AAP內部也發生了爭執,起因是卡倫拒絕讓弗洛姆成為學會成員,借口是他不具備醫師資格,但有內部傳聞是因為二人斷絕了戀愛關系。這一次,學生和朋友們站在了弗洛姆一邊,幾位核心成員退出學會。隨著與紐約醫學院合并談判告吹,西爾伯格也離開了AAP, 三年之后,卡倫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但她還是憑著鋼鐵般的意志,獨立支撐著學會和學校向前,直到人生的終點。
在辛勞工作之余,卡倫也在通過各種途徑尋求著她內心世界的平衡。她的心理診所開在自家的門廳里,很多病人都和她成了朋友,大家一起談天說地,制作烘焙。她在六十多歲時還有一個比她小很多的男朋友。小女兒嫁到了墨西哥,她每年都會去和小女兒同住一段時間,一起購物,打牌,享受休閑的時光,但即便是在游戲的時候,她也會像工作一樣把日程安排得滿滿的,沒有一刻能夠停下腳步。
晚年時,卡倫的作品中表現出對于東方禪宗哲學的關注。將她引向禪宗的人正是著名美國日裔心理學家鈴木大拙。1952年,鈴木大拙在紐約哥倫大學做講座時,卡倫邀請他到AAP進行演講,從而開啟了兩人的友誼。鈴木邀請卡倫和她的二女兒一起去京都參觀。卡倫在日本度過了五個星期,會見了日本心理學家近藤晃史,并在東京慈惠醫學院做了有關東西方心理分析理論比較研究的講座。在鈴木的帶領下,卡倫游覽了距東京一百五十公里處的廂根町寺院,并見到了珍珠島上的采珠人。日本的禪宗理念和生活給予卡倫很大的啟發,讓她對于自己的心理學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如何獲得內心的寧靜。在《我們內心的斗爭》一書中她寫道:“誠心等于專心。這一點和醫生的臨床觀察結論高度一致,如果人的內心分裂,就無法做到誠心。”
從日本回國以后,卡倫被診斷為膽囊癌,已經擴散至肺部,卡倫平靜地接受了生命的審判。在病床前,她依然關心著女性心理學家的教育事業。去世前不久,她與一名醫學生在病床進行了一次談話。她向那個學生回顧了她的一生,從一個村里的小姑娘一步步來到大城市并成為心理學界權威的生涯。她問道,他班里有多少女學生。當聽到一個百人班里只有三個女學生,她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后說道:“怎么會是這樣,心理學是一門關心人,培育人的學科,怎么能全都是男醫生呢?” 最后,她對那個學生說道:“你還年輕,也許當你到達我這個年齡時,世界會變得不一樣。” 兩個星期以后,卡倫·霍爾奈溘然長逝。
卡倫病榻前的預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應驗。2003年,美國心理學系女生人數首次超過了男生。作為一名走在時代前面的女性心理學家,卡倫最偉大之處就在于讓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意識到弗洛伊德心理學存在的局限性和男性中心主義的缺陷。70年前她提出的理論,現在已經變成了心理學界的共識,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能夠為女性心理辯護,世界應該感謝這位固執、堅毅、特立獨行的女性心理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