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現在黑我的人蠻多,不用理會
鮑安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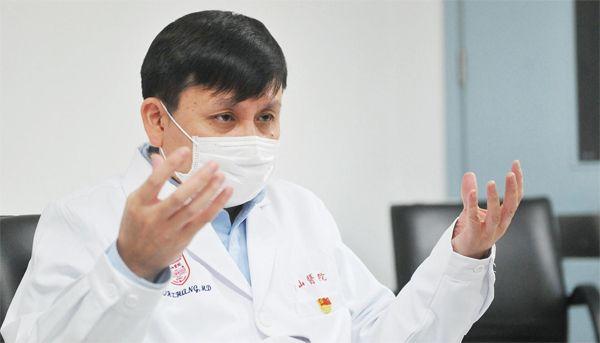

人紅是非多,真是喝粥都會塞牙縫。
自從張文宏“多吃蛋白質、不許喝粥”的言論引起新一輪的爭議,華山感染的公眾號幾乎二十多天沒有更新、沒有發布疫情分析文章了。張文宏的學生、疫情分析寫作群(疫情開始后他拉的一個群)成員艾靜文說,他們想低調點。
張文宏曾告訴記者,自己不用微博,華山感染也沒必要再弄個微博賬號了,有公眾號就行了。結果,形勢比人強。沒過幾天,“華山感染”重新啟用了幾年前注冊的微博賬號。他說,最近關于他的謠言比較多,他想有個渠道進行澄清。
“人活著很難的。”他感嘆。
“鐵嘴”
張文宏突然火起來,始于今年1月--29日“把黨員全部換上去”的發言視頻。嚴格說起來,實際情況跟他的表述是有出入的。
1月20日,上海市首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確診,當天華山感染科接到上級通知,要求騰空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當時科室主任張文宏在金山公衛開會,副主任張繼明在靜安區開會,是主治醫師虞勝鐳協調了當晚的騰挪病房、收治疑似病人。
由于新增了新冠肺炎疑似留觀病房,原來的正常排班被打亂了。國家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也密集更新,新流程一直在摸索。
1月29日上午,張文宏在科里召開了一個黨支部會議,首先表揚了非黨員在疫情前期的工作,還說接下來如有需要,會優先派黨員,直接派出,不允許推脫。之后,感染科確實換崗了,但并非“把黨員全部換上去”,而是梳理了新的流程,重新排了一個班。
張文宏真正考慮的,是接下來向疫區派人的問題。他心中已經規劃了一個優先順序:男性黨員、男性非黨員、女性黨員、女性非黨員。最終,感染科支、援武漢的5位醫生都是男性,要么有行政職位,要么是黨員。
不過對于他的這個發言,科室同事們都見怪不怪,因為都知道他說話一向是這個style。
不同于一些專家有意識地“放炮”,張文宏更像傳說中那種被本職工作耽誤了的超級段子手,“隨手抓哏”幾乎是他的本能。
10年前,他在醫療界就有“鐵嘴”之稱了。學生結婚時,他主持婚禮,逗得滿堂哄笑。2018年的一次學術活動中,張文宏大笑著說,自己最大的優點就是“自覺”,最大的缺點就是“跑火車”。看看他2016年在丁香園公開課的一個視頻就知道,如果他撒開了跑起來,簡直可以跟郭德綱“搶飯碗”。
疫情中,張文宏金句頻出,讓聽慣了“磚家”腔的公眾一下子耳目一新。“哪個正常人不想念他的母親”等反矯情視頻流出來,謔而不虐,更是圈粉無數。
張文宏紅了,不是一般的紅,而是紅得鋪天蓋地。
青年時代
九十年代,烏魯木齊中路38號是華山醫院的實驗樓。這是一座三層小洋樓,傳染病科實驗室在二樓,對面是中醫科的實驗室。傳染病科實驗室的條件比較好,有空調,有獨立衛生間,有沙發,還有電話。因為電話分機號是516,大家習慣稱這里為516號。年輕人很愛在這里廝混,有時還用煤氣爐做飯。
主廚通常是陳一平。他1988年起在華山醫院傳染科教授徐肇玥名下讀研,實際上由時任傳染科主任翁心華輔導,因此自認是翁心華的第一位弟子。翁師母說起他,至今仍是贊賞有加,說他很有凝聚力,把一幫兄弟聚到了一起。
不久,又來了一位年輕人,這就是張文宏。1994年,張文宏進入中醫科中西醫結合專業讀研,師從查良倫教授。由于離得近,他時常來傳染科串門,久而久之和傳染科的年輕人都混熟了,和陳一平關系尤其好。在陳一平的印象中,中醫科也只有張文宏常來串門。
這樣的日子并不太長。不久后,華山感染就進入了最艱難的歲月。1998年,華山醫院進行基建改造,傳染科病房被拆--除,只能租用上海市武警醫院和上房醫院作為病房。這一年,陳一平離開華山醫院,去了美國。張文宏接替他,跟著翁心華做結核病課題。
張文宏回憶,當時傳染病專業不景氣,一個月的工資獎金加起來不超過4000元,30歲出頭的他覺得難以養家糊口,也產生了辭職的念頭。是翁心華勸他再堅持一下,讓他留了下來。
2003年初,翁心華年滿65歲退休,由華山醫院黨委書記張永信兼任傳染科主任。張永信上任后,想提拔張文宏做副主任,但張文宏卻不愿意干。
張文宏坦言,自己要養家,經濟比較拮據,業余時間在做一個英文翻譯方面的兼職,精力上難以勝任。張永信體諒他的困難,轉而安排他當了主任助理(2004年后被任命為副主任)。
2006年,張永信退休。院里曾考慮,暫不設主任,由副主任主持工作。翁心華向時任華山醫院院長的徐建光建議,千萬不能如此,沒有主任會影響科室在全國感染學界的地位。最終,“一施(施光鋒)二張(張文宏和張繼明)”走馬上任。
2010年8月,五層的新感染樓正式啟用。感染科從居無定所的“角落科室”一躍成為華山醫院硬件條件最好的一個科室。感染科領導層也再次面臨換屆。當年,在新樓里,舉行了一次由全科室老教授、醫生、護士參加的民意測驗,醫院派人來監票。投票結果,張文宏當選為新一任感染科主任。翁心華說,是全票通過。
感染科主任
翁心華說,張文宏在科室利益分配方面做得很公平。“蛋糕做大了,大家都有得吃,這是他的一個原則。”
2010年時,科室僅有床位約70張。床位資源緊張,上一屆時,有的教授不被安排分管病床,翁心華很痛心地說,這等于浪費掉一個人。張文宏積極爭取病房,床位增加到近200張。
張文宏說,由于缺乏人手,很多科室都不愿意要或難以要到病房,但“在我這里我就不怕”。因為每年來華山感染進修的醫生近兩百人,全國各地的病人都會來,目前有85%為外地病例,不缺醫生,也不缺病人。
張文宏上任后,在科里帶頭不拿科室獎金,提出主治醫生比不擔任主任之職的教授多拿獎金。因為教授有資歷,可以通過會診等輸出醫療服務的形式獲得更多的合理收入。他還提出,出現醫患糾紛時,如果不是責任事故,需要賠償的話,低年資醫生不用出錢,而由科室賠償,相當于科室共同擔責。
研究生想留在頂級三甲醫院,競爭很激烈,一般有種不成文的傾向——主任的學生容易留下來,但張文宏設計了一種畢業生選拔機制:學生打擂臺,導師回避,由本科室和其他科室的教授、院領導進行評分排名。
在華山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外號“張爸”,副主任張繼明外號“張媽”。這次,張繼明是華山醫院第三批援鄂醫療隊的隊長,他與第四批的隊長李圣青、護士長張靜一道,成為了華山醫院的“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作為十多年的默契搭檔,“二張”經常保持著熱線。不過晚上十點后張繼明很少打電話,因為張文宏睡得早,一般早上四五點起床,每天早晨六點多就到醫院,開會時而打瞌睡,但疫情暴發后他的作息節奏亂了,有時候趕稿子睡得很晚,“所以經常出現黑眼圈就不足為奇了”。
“網紅”
疫情期間,張文宏典型的一天是這樣的。
每天早上六點多,他從家出發,開車一個多小時,來到位于金山區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查房,協調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會議室所在的防控東樓上有給他安排的房間,疫情初期他晚上常住這里。上海防控形勢好轉后,他才逐漸可以回家住。
下午如果沒有別的活動,他就開車回到位于靜安區的華山醫院。
時常,他要與艾靜文等幾位年輕醫生開會。疫情期間,主治醫師艾靜文可能是張文宏“抓差”最多的人,客串起他的文案、對外溝通、媒體等各項助理。
早在武漢疫情初露時,張文宏就拉了一個微信群,跟進、分析疫情。一直跟著張文宏做精準診治平臺的艾靜文與師姐喻一奇、其他6個師妹都在群里。
當時,全國各省首例病例的確診都要先做出全基因組測序,交國家衛健委審核。上海市疾控中心承擔了這項工作,同時讓華山醫院的感染科做平行實驗。華山感染做出測序后,交上海市疾控中心,最后上交國家衛健委的正是這個版本。
張文宏也帶著這個團隊開始在華山感染的微信公眾號上持續發表疫情分析文章。一開始都是他自己寫的,后來寫疫情復盤、國際疫情分析的文章需要大數據,就由張文宏出思路,艾靜文負責落地,組織師姐妹們找數據、資料,有時先寫出初稿,最后終稿大部分由張文宏自己執筆,因為其他人“沒有那個筆力”。
華山感染的微信公眾號,由虞勝鐳在2014年9月注冊。因為注冊為個人號,所以每次誰要發文章,都要讓她掃碼。公號維護沒有專人專職,王新宇、虞勝鐳等一些年輕醫生自己寫文章,自己排版,沒人干涉,也沒有報酬。有時,張文宏也來“投投稿”。
幾年來,這個號一直在穩定地更新,文章和排版都像模像樣,但閱讀量也就幾千而已。疫情前,關注數剛突破兩萬五千。張文宏的“把黨員換上去”的視頻流出的當天,關注數就新增13萬。迄今,已突破83萬。閱讀量最高的《WHO:大眾如何預防新型冠狀病毒》,閱讀量達2043萬。
閑聊時有人說起,現在微信上有篇文章對他不利。他說,“現在黑我的人蠻多的,我現在微博基本上都不看,不用理會”。過—會兒,還是拿來對方的手機翻看起來,邊看邊說,這種文章大家一看就知道荒謬,沒事。
3月31日,他上午照例去金山查房。下午參加了兩個連線活動。他的博士生、去年剛畢業的李楊跟著他,幫他設置網絡連線。
做完與復旦大學學生的連線,他從碩大沉重的雙肩包里掏出領帶系上,準備與臺灣中天新聞連線。近年來,他參加活動基本都是那件金色紐扣的深藍色西裝,這次還是這身行頭,西裝左前襟邊沿處和雙肩包的拉鏈都磨舊了。
連線后,他又去上海市疾控中心開了一個會。開完會已六點多了,他開車回華山醫院,一邊開車一邊用外放打電話。路上遇到輕微堵車,他點踩剎車,抓緊看手機上的文檔。堵車路段過后,他把手機交給李楊,要李楊讀給他聽。
很快遇到一處紅燈,他打著哈欠,靠在方向盤上,左手抱胸,右手揉捏著兩眼之間的睛明穴,看上去十分疲憊。他低頭閉眼,問李楊“無癥狀感染者”的研究進度,追問要聯系的人是否已經聯系。
將近7點,他回到華山醫院。
有人問,關于無癥狀感染者的微信公號文章寫好了,當天是否推送?他說題目敏感,他要仔細看過,還要先了解鐘南山院士、李蘭娟院士等各方說法。“網上老傳言說我跟鐘南山院士之間有矛盾,實際上我們關系很好,經常通通電話。”
華山醫院感染病中心和復旦一所實驗室一起,向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捐贈了1萬個咽拭子。張文宏需要將一首蘇轍的詩寫在一張A4白紙上:“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他握著黑色馬克筆,一筆一畫、從右到左地慢慢豎寫。
中途,他囑咐一位年輕醫生,明天要么將他給崔大使(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的回信親手交給上海外辦,要么讓外辦的人來拿。信已擬好、謄抄好,在信的結尾,他邀請崔大使在世界抗疫勝利后回家鄉,“一起在老上海,您老家附近的小酒館里把酒言歡”。
如今的張文宏,越來越如履薄冰。再看2月27目的視頻上他懟女記者時那種靈動和談笑風生、嬉笑皆成文章,才不過兩個月,已然有判若兩人之感。
就像人們所說,世界分為新冠肺炎疫情前和新冠肺炎疫情后。他說,自己不是一個公眾人物,疫情結束以后,在專業領域還可以繼續發聲。
摘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