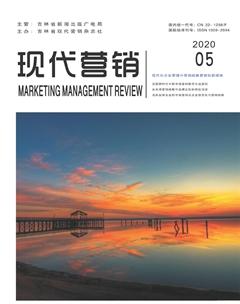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與完善措施
陳萍萍
摘要:七次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既滿足了公眾降稅減負、稅收公平的期待,又實現社會收入分配效應的目標,是個人所得稅制完善的重大一步。但是,新一輪改革也仍有遺留的與伴隨產生的問題。稅制的改革,應該始于分析各稅制要素的不足之處,再結合稅制在不同國情下的根本目標,對納稅人與稅制雙管齊下地改革。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改革;個人所得稅問題;個人所得稅完善建議;“互聯網+稅務”
一、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內容
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在2018年10月1日與2019年1月1日分步實施,本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有: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四項所得納入綜合所得計稅;綜合所得項目按月預扣預繳年終匯算清繳;免征額上調為5000且調整優化綜合所得稅率結構;新增加專項附加扣除項目:增加反避稅條款。這些改革措施不僅順應了新時代下國策的要求與民眾的期盼,在減稅減負、實現公平、提升征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新個人所得稅改革后存在的問題
(一)征稅范圍:高收入來源不夠細化,收入差異化有待提高
我國高收入者收入更多是是財產性收入、資本性收入,收入來源多,逃稅空間大。而我國對高收入者主要的收入劃分并不詳細,監管也就缺乏針對性,導致了稅收流失嚴重。例如高收入者的資本性收入,可能涉及了金融、房地產、工業等行業,沒有對這些收入進行細分稅務機關在監管上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沒有方向。
沒有對高收入者主要收入類型進行細分帶來的問題還表現在稅率的制定。為了調節高收入同時又不打擊投資者的積極性,就要對需要鼓勵投資的活動收入適用低稅率,對需要調節的收入采用高稅率。沒有細分的情況下,為了國內經濟的穩定,普遍采用低稅率,這就犧牲了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所以征稅范圍的設定還制約著稅率的合理制定。
稅收一項很重要的原則是量能課稅。部分所得綜合征收是為了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平效應,但是不同的所得根本上的差異是仍然存在的。比如,綜合所得中,相比于擁有工資薪金所得的人,僅僅持有其他三項所得的人群全年收入變化幅度較大,這類勞動者承擔著一定的風險,所以其他三項收入不全額計稅是考慮到個體差異的體現。在瞬息萬變的發展環境中,各種收入的質與量的差異,對稅務機關的合理計稅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二)費用扣除:費用分配機制不完善,制定標準不合理
1.免征額的公平效應不足,制定方法不合理
新增專項附加扣除,個人的稅收扣除考慮了納稅人個體的家庭情況,會引導人們趨向于以家庭為單位的公平比較,標準化免征額在公平效應上因此有了爭議。家庭組成結構不同,納稅人實際應該負擔的基本生活開支會因此產生差異,標準化免征額對于養老撫幼負擔重的納稅人顯然是不公平的。養老撫幼的負擔一致的條件下,標準化免征額對在崗人數多的家庭顯然是一種眷顧。既然要考慮個體差異征收個人所得稅,標準化免征額就必然會引起質疑。再觀察往年免征額調整的情況,免征額的調整較為被動,呈現累積性調整[1],每次調整都要反復征求意見。
以上情況出現的原因就在于稅法個人所得稅相關條例中并沒有為免征額規定調整的標準以及調整頻率。物價不斷變動也就決定了基本生活開支也在時刻波動。累積性調整會導致免征額并不能隨時適應納稅人的實際納稅能力,反復征求意見與修訂不僅耗費大量成本還會導致調整不及時無法跟上公眾的需求。
2.費用分配問題影響征稅效率,標準制定方法不合理
專項附加扣除項目大多是家庭成員共同承擔的費用,一旦隨著贍養形式多樣化、相關行業情況復雜化,會加劇家庭成員分配的復雜程度,征納雙方都要承擔征繳稅的復雜化,稅收行政效率將得不到保證。
以個人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在扣除家庭共分攤的費用時就要考慮家庭納稅人之間分配的合理性,規定越復雜逃稅空間越大,會造成稅收流失,也不利于征收管理。在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納稅人為了避免子女教育扣除費用分配的復雜手續都采用了家庭申報或夫妻聯合申報。像在我國這種家庭觀念根深蒂固的人口大國,以個人為單位申報納稅在有了年終匯算清繳手續后會大大增加稅務機關的工作量,使分配問題更加棘手。
專項扣除標準化費用存在和免征額一樣“無標準”的問題。這類費用水平是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沒有時間標準、數額標準容易導致稅制改革陷入面對不合理征兆與公眾壓力再調整的境況。
(三)稅率結構:稅率結構不合理
對于個人所得稅中的稅率結構,綜合所得適用的累進稅率仍然存在級次過多,邊際稅率偏高的問題。我國的高收入者收入主要來源是資本性所得和財產性所得,即這類所得是引起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因為沒有分清“高勞動收入”與“高收入”,我國適用于勞動所得性質的綜合所得的累進稅率,過多級次、邊際稅率過高,僅僅對對勞動所得施加了過大的力度,不僅起不到真正調節收入差距的效果,反而會導致納稅人產生逃稅動機,進而造成稅收流失,加大征管難度。
首先,通過數據分析,低收入群體收入分布較為集中,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分布較為廣,僅有不到1%的人適用超過10%的邊際稅率[2]。由此可以推測,適用35%以上稅率的群體占比很低。其次,高稅率級次額主要作用是在于調節高收入者收入,但我國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中綜合所得占比較小,而是資本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占比較高。所以,目前稅率結構中的最高稅率級次并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國目前對資本性收入采用比例稅率計稅,但稅率卻不高,承擔的平均稅負低于勞動所得承擔的平均稅負,所以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不大,也就無法對收入調節起到作用。但是稅率無法上調又是因為考慮到投資者投資積極性,所以這也一定程度上與收入不夠細分有關:高稅率無法對可以調節的資本性收入進行重點調節。
(四)稅收征管:納稅人的繳稅水平、稅務機關的征收水平不足
首先,我國的納稅人自主申報意識普遍較低,對稅收知識的掌握度不高,改革之后年終匯算清繳工作的推進將會伴隨著許多問題,如最終的匯算清繳率可能很低,造成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秩序的混亂、納稅人在計稅時與稅務機關產生矛盾等。其次,我國納稅人在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質上并沒有深切的體會,稅痛因此難以減緩,納稅意識就無法提升;再次,我國稅收知識宣傳途徑并不完善,給納稅人造成了在納稅上“有心無力”的困難。
從征稅方來看,改革之后征稅工作工作越來越需要納稅人的參與,征納雙方更緊密地接觸交流。個人所得稅稅痛最強,征稅時最易產生摩擦。在這種形勢下,給予納稅人更多的便利性、親和力來提高納稅人納稅的自愿性、潤滑征納雙方的交流、保證兩方關系質量是稅務機關需要進一步提升的。
三、個人所得稅制完善建議
(一)課稅模式: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收制度
目前,適應我國明確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的目標一致,我國應繼續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征稅模式過渡,但需要有幾點突破:先在個人層面分類計算所得額與優惠,再匯總以家庭為單位扣除共同承擔的可扣除的費用,最后按家庭匯總對應累進稅率表計繳個人所得稅。
在這種模式下,是在原來分類的基礎上對可以綜合征收進行綜合計稅,符合我國簡化稅制的方向;將個體收入按收入性質分類計算所得額能在考慮差異的基礎上最小化籌劃空間;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更有利于量能課稅、實現公平與提升管理質量。這種模式還可以彌補減少了“分類計稅再綜合計稅”這種兩次計稅的弊端,也可以彌補我國暫時無法達到綜合征收制所需的高征管水平的缺陷。
(二)征稅范圍:高收入者征稅范圍細化,不同收入所得額占比差異化
在個人層面,應針對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進行收入細分,爭取將高收入者的收入均納入征稅范圍。隨著收入差距縮小、其他收入調控機制逐步產生和完善,就可以對收入細分降低要求,甚至運用反舉例法擴大征稅范圍,同時降低稅率。
當前可將征稅收入劃分為三大類型:勞動收入、經營收入和資本利得收入。在有必要細分的大類中再進一步細分,如資本利得收入,實現稅收模式的“大綜合,小分類”。在取得資本利得收入的行業一般會與國家金融經濟相關,而當前的國家經濟局面還并不穩定,有需要鼓勵的投資活動也有需要嚴格限制的投資活動,依據行業性質對資本利得收入進行分類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管理國家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能進一步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
量能課稅要求征稅應該考慮個體差異,而差異的來源不僅包含個人、家庭還有收入本身,稅務機關要最大限度地量能課稅就需要全方位地考慮個體差異來計算所得額與稅收,使其既能對個人合理征稅又能對收入所屬行業起到調控作用。
(三)費用扣除:扣除費用指數化,謹慎設定稅收優惠,以家庭為申報單位
(1)從個人與家庭兩個層面扣除,以家庭為申報單位
在個人層面對各項收入按比例計算所得額是為了考慮收入在當前經濟、社會背景下的差異性;在家庭層面計算各項扣除是為了考慮個體在微觀環境下的差異,充分遵從量能課稅的原則。從兩個層面進行費用扣除可以結合免征額與專項附加扣除的優點,在量能課稅上將是一大改進。
家庭是國家管理的最基本單位,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能提高征收管理效率;其次,通過學者的實證分析,新增專項附加扣除后對家庭征收個稅的收入分配效應會大于對個人征收的效應[3],所以在新的改革形勢下以家庭為申報單位是一個提升征收管理質量、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的手段。
(2)扣除標準指數化,稅收優惠合理化
個人層面的優惠扣除和家庭層面的專項附加扣除等項目的扣除標準應該有成文規定,并且設置指數化標準[3],保證各項扣除費用能隨著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更好起到量能課稅的作用,又能避免累積調整對稅收收入產生的巨大變動。
高收入者通常是對國家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的群體,所以對其征收的個稅不應打壓到其勞動積極性且不導致資本大量外流[4]。但稅收優惠又不應設計過多,否則會影響收入調節。所以應對高收入者主要收入進行細致劃分,謹慎把握其費用扣除。
(四)稅率結構依照收入分布現狀定制累進稅率結構
為了優先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按家庭計稅時采用累進稅率并且擴大中低收入級距。隨著其他調節收入的體制完善之后,就可以逐步擴大級距、減少累進稅率級數,逐步向單一稅率靠近。單一稅制可以減少逃稅避稅空間,提高征稅效率,這也是個人所得稅向增加財政收入功能不斷過渡的一個過程。
同時,要讓稅收的累進性達到最優狀態應該基于我國家庭收入整體情況,如結合現經濟水平對我國的收入水平劃分出不同的等級,每個等級再確定適用的稅率,最終定制出合適的稅率結構。個稅收入調節的結果應該是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5],所以在稅率結構上對中等收入應更注重級距擴大,對低收入應注重級距擴大與稅率的設計。
對于高收入者資本利得收入,在建立健全的分類體系的基礎上應該采用差異化稅率。應該考慮到投資積極性的相關收入予以低稅率征收,而應該嚴格限制的活動相關收入予以高稅率打壓,同時為了在取得這些收入的人群中實現縱向公平,也可考慮采用超額累進稅率。
(五)稅收征管
從納稅人的角度看,首先納稅人納稅意愿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納稅環境的公平感知。應引導納稅人感知公平,如通過稅務信息公開,將稅收去向公開化,向民眾展示他們享受公共服務多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己繳納的稅收。其次,讓征稅管理成為“征稅服務”,比如賦予納稅人一定的權力,在稅務辦理時給予納稅人親和的態度、便利與援助等。
從征稅方入手則可以加強納稅信用與征信體系的結合,提高納稅人警惕性,抑制不誠信行為發生。將不遵從稅法的威懾與遵從的激勵結合在一起會大大提高對納稅人的激勵效果[6],所以可以重點對高收入者的監管與懲處,對誠信納稅人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或實質性獎勵,從威懾與激勵兩方面入手提升征稅效果。
參考文獻:
[1]曹桂全.我國個稅免征額調整的稅收效應——基于應有免征額、免征額累積性調整方式的分析[J].經濟學報,2018,(2).
[2]李銘,李立(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優化個人所得稅稅率、級次與級距的設定——基于基尼系數的分解和組間基尼系數變動[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2):24-30.
[3]王曉佳,吳旭東(東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基于微觀數據的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9,第41卷(9):83-86.
[4] 曹桂全(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J]. 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20卷(3):202-209.
[5]黃聰聰(中央財經大學).淺議我國工薪累進稅率和免征額的功能[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第31卷(6):41-43.
[6]李林木等.高收入個人稅收遵從與管理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社,2013,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