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天津市立美術館展覽的視覺邏輯
民國時期天津市立美術館之頻繁開辦且內容豐富的展覽與陳列,使其成為中國現代美術館早期實踐中的代表。其展覽陳列方式呈現出琳瑯滿目的視覺效果,并且館方針對不同展品調整排列方式,試圖營造出秩序感。展覽中不時出現復制品的情況,則折射出時人對“原作”的認識與物質條件的局限。臨時展覽與長期陳列之龐雜內容呼應著寬泛的“美育”概念,但作為被啟蒙者的觀眾卻被給予了能動的思考與批評反饋。透過研究展覽的多個層面,本文試圖分析展覽陳列與觀看的視覺邏輯。
民國時期;天津市立美術館;展覽陳列;視覺邏輯
民國時期天津市立美術館(1929-1948,簡稱天津美術館)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博物館建設浪潮中美術館的代表。在其開辦的近20年時間里,這里舉行了百余次臨時展覽,籌備并幾次調整長期陳列展。無論在展覽內容還是展陳形式上,這些展覽都有特定時期的特點。
本文圍繞民國時期天津美術館的展覽—藝術展覽與其他展覽,臨時展覽和長期陳列1.在天津美術館的官方文獻中,“展覽”與“陳列”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所指。前者指短時間的展覽,展品往往部分來自本館、部分借自美術館以外的機構或個人—到抗戰結束后的艱難時期,展品則更多來自本館收藏;而后者則指長時間的展覽,陳列物品從美術館自己的收藏中選出。當然,這也是博物館學中的分類慣例。—從博物館學關注的經典論題“展陳方式”談起,再探討藝術展覽中復制品使用的問題,最后從“美育”的具體歷史語境切入到展覽藝術品的分類、博物館展覽氛圍及其對觀看行為的影響、被啟蒙者的能動性等論題,剖析美術館展覽中呈現與觀看的實踐及其背后的邏輯。
一、“琳瑯滿目”與有限的秩序感
天津美術館的展覽報道標題中,“琳瑯滿目”是一個高頻詞。同時期對全國范圍內其他展覽的報道也會使用這個詞,并配合給出展品總數以顯示數量繁多。可見,民國時期各種展覽常常追求呈現出密集繁多的視覺效果。不過,在天津美術館的案例中,館長嚴智開是眼界開闊的藝術留學生,非常了解同時期國外美術館的展陳樣貌。所以,展示空間的狹窄應是導致“琳瑯滿目”現象的重要原因—天津美術館本身是一個“小型美術館”2.有關天津美術館展示空間的具體狀況,可參見筆者拙文《為現代城市而設:民國時期天津美術館的主樓建筑與空間的敘事》。該館主要參照了當時在日本新建立的小型美術館“黑田紀念館”。它的主樓只有一層加上半地下室。后來又加了一間畫室和用于長期陳列的平房。總體而言,它的規模非常局促,很難與今天體量龐大的博物館、美術館相比。。而對展品不嚴格取舍,也是原因之一3.陳端志就指出過陳列上常見的缺點。第一條就指出:“尤其在吾國,便是貪多務得,來者不拒,終致成為勸工場式的陳列。……主要點不易捉摸,不但可使參觀者注意力散漫,且可發生一種不快之感。所以陳列品務須精密選擇,寧缺毋濫,且須多留空隙部分,格外顯示陳列品的珍貴,集中參觀者的興趣。”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第173頁。。
然而,“琳瑯滿目”不代表展陳方式完全沒有規律。從留存下來的天津美術館展覽照片來看,藝術展覽中的二維展品—西畫、照片、圖片等—被分為兩到三層展示于墻面(圖1、圖2、圖3)。比較另外兩種展示方式,則可了解天津美術館這種懸掛方式的“過渡性”。第一種,以沙龍展為代表的歐洲公共美術展覽4.同為“琳瑯滿目”式的展陳樣貌,沙龍展與博物館前身奇珍屋的陳列相比,已有不小的變化:貯藏與陳列空間分離之后,展示空間變得相對舒朗。且每次展覽展品的材質、門類可以更為統一。。它沿襲歐洲皇家畫廊的普遍做法,將眾多作品密集地懸掛在寬敞大廳的高大墻面上(圖4)。但這種展示方式的缺點是,無法保證展出的每件作品都被觀者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那些比視平線高出很多的作品。

① 約1940年的天津美術館建筑陳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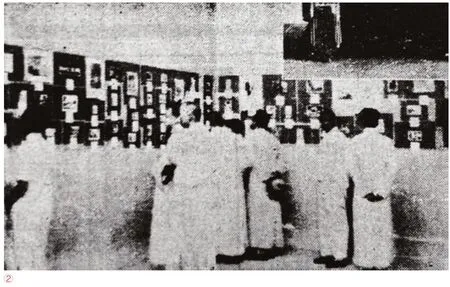
② 1933年天津美術館第三次攝影展覽會現場

③1934年12月的天津美術館內部展陳

④ 于貝爾·羅貝爾,《盧浮宮大畫廊》,1801-1805年
第二種可作為參照的展示方式誕生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白色立方體”模式(圖5)。因為希望觀眾關注藝術品個體,這種方式將作品相對舒朗地置于觀眾的水平視線上。如此,多數作品都可以被平視和凝視。有時,某件重要的展品甚至會占用一整面墻壁或一個展室,寬松的布置反而比沙龍式的密集更強化出稀少、珍貴的感覺,但其缺點也很明顯,即對展示場館的空間體量有所要求。

⑤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1936年的展覽“New Horizons in American Art”展覽現場
無論從發展時間還是形式上考察,天津美術館的攝影作品、西洋繪畫、圖片等的陳列都介于沙龍展式樣與白色立方體式樣之間。相較于白色立方體的模式,天津美術館為了更充分地利用空間,將“平視區域”的上下邊緣擴寬,使之能夠容納兩到三層的二維展品。或者說,沙龍式的整面墻壁的利用范圍被縮小了區域,盡量壓縮到觀眾比較容易看清的范圍之內。1934年發表的一張天津美術館內部陳列狀況的照片(圖3)顯示了一種極端情況—展品實在太多了,右側墻上,視平線之上還有兩排更小的畫框。可見的兩面墻的墻根也都立放著展品。當然,整體看起來還算排列有序。天津美術館對美術館展覽中的二維展品的展陳方式盡量平衡了空間的有效利用與觀看的舒適程度。
當然,這種兩到三排的展示方式并非天津美術館獨有,同時期西方的美術館不乏兩層排列的油畫陳列方式(圖6),民國時期的藝術展覽也常常采用類似的方式,比如:1929年藝術運動社的展覽(圖7)和1931年上海藝專的學期展覽(圖8)。后者乍看是類似的展陳方式,但如果照片中的人站立起來,則下面一排作品處于視平線之下。1937年北平歷代建筑展覽會中,最高一排的照片與人視線基本齊平,其他照片也都在更低的位置(圖9)。攝影展覽一類,比如光社的展覽,則類似于天津美術館的情況,盡量在視平線上下鋪展為兩到三排(圖10)。

⑥1930年代瑞典國立博物館的18世紀陳列室

⑦1929年藝術運動社的展覽現場

⑧1931年上海藝專的學期展覽

⑨1937年北平的中國歷代建筑展覽會

⑩1929年攝影社團光社的作品陳列
對于陳列物品的高度,同時代的專業書籍《博物館》中有所論述:“物品能安放適當,使觀者不必伸頸屈腰,得以極舒適極自然的姿勢,以觀察物品,可減觀覽人的疲勞,在博物館的技術上,亦為一極重要之事。……普通成人的眼,平均離地約高五尺,而眼與物體的距離,不得超過一尺五寸以上。根據這個條件,陳列小物品。以離地三尺五寸(注:1.17米)乃至六尺五寸(注:2.17米)間為適當的陳列范圍。但這個尺寸對于兒童尚嫌太高,所以最適當的,應在三尺三寸(注:1.1米)至五尺(注:約1.67米)間。惟較大的物品,則較此區域或高或低均可無疑。”5.費耕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中華書局,1936年,第162頁。顯然,本文討論的幾例,展品基本都陳列在規定的1.1米至2.17米之間的區域。
天津美術館中的中國書畫作品有自己的展示規律。在1930年10月開幕展覽時的國畫陳列室中(圖11),國畫以中心點為橫向對齊的基準,取尺幅較為接近者并列。每幅畫之間也有比較均勻的間距。此外,從照片來看,每幅畫旁邊有一個白色小方塊,應該是每幅畫的題目或簡介。1935年3月的歷代名家墨跡展覽的報道中記者提到“每一作品,均附以作者之簡略,及其事跡,俾觀眾得以一目了然。”6.《市美術館歷代名家墨跡展》,《益世報》,1935年3月30日,第二張第六版。這說明天津美術館會用展簽對展出的書畫作品進行介紹。

?1930年天津美術館開幕展的國畫陳列室
葛斐爾曾在《中國早期公立美術館之當代性研究—以天津市市立美術館個案為例》中針對這張照片的展示場景指出,這些畫距墻面有一定距離,像在毛筆架上懸掛毛筆的方式,因而將這種陳列方式描述為“筆屏”。但實際上,天津美術館對國畫的陳列并不都是這種“筆屏”,很多作品仍是直接掛到墻面(圖12)。從目前的有限資料判斷,就國畫展示而言,“筆屏”式的展示方式可能僅出現在該館早期的臨時展覽中,而直接貼墻懸掛的情況出現在長期陳列當中—但尺幅并不規整。

?1940年天津美術館的繪畫陳列室
從天津美術館進行長期陳列的繪畫陳列室和1931年1月的書畫與石刻展覽的照片來看,書畫作品之間的距離明顯比開幕展要緊湊。可見,館方也會根據每次展覽作品的多寡來調整作品之間的距離、懸掛的密集程度。不過,從這些僅有的書畫展覽照片來看,無法確定天津美術館展覽的書畫作品,除了垂直展開的條幅,是否還有橫向裝裱的手卷或冊頁。
就三維展品而言,天津美術館也提供了不同的展陳方式。在1930年的開幕(臨時)展上(圖13),雕塑按照一定區域排布陳列,以立柱和繩子劃分。1935年之后,在長期陳列的西洋雕塑陳列室中,雕塑被置于高度相當的架子上,再被整齊地排列在過道兩邊。而在同時期的中國雕塑陳列室里,佛像、佛頭等被散落攤放在桌面上。一些石刻被立在桌子側面。背后還有拓片立在墻根。如此的布置,較西洋雕塑的陳列而言,顯得相對混亂—可能因展品尺寸、材質的差異造成。
與上述具有一定秩序性的展陳相比,1935年在天津美術館展覽的小學算數教具展(圖14)是雜亂而缺乏規律的典型案例。這類為中小學教育服務的展覽多為學校教師自己布展。面對既有三維又有二維、大小參差不齊,且展品數量多達九千多件,非專業人員自然無從下手。這次布展的凌亂,堪比“勸業場式的陳列”7.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第173頁。—源自陳列并推銷商品的勸業場。

? 1935年天津美術館小學算數教具展
天津美術館展覽陳列的秩序是有限的。除了上述雜亂的案例,對展品順序的考慮不足也妨礙了秩序感的顯著性。從觀眾反饋可知,1936年郵票展覽的布展順序就“尋不出社會歷史的痕跡,地理人文的概念”8.《郵展觀后記》,《大公報》,1936年3月6日,第四張第十三版。;1935年黑白影展需要“改良陳列次序”9.《關于黑白社影展》,《益世報》,1935年1月28日,第四張第十四版。。
同時,對說明性文字的忽視是有限秩序感的另一個原因。觀看了1936年的博物館展覽會的記者質疑:“不知是否直到現在還沒人知道那些東西的詳細,或者是認為市民們只要看看花樣,根本沒有知道那些事的必要?”10.《博物展覽會印象記》,《北洋畫報》,1936年9月24日,第1456期,第3版。
不過,關于說明文字的問題,即便同為1936年的文獻,也體現出了認識的差異。有人想要更多更詳細的文字。《博物館學通論》的作者陳端志則在討論陳列時認為:
但在事實上對于藝術品方面,觀眾仍非先有充分理解的程度,不能感到愉快的享受……所以任何物品的陳列,都應顧到此,展覽與說明的兩大目標,各視物品的性質,施以適當之處置……
藝術品的陳列,當然注重在欣賞方面。但在知識傳達上,只要不妨礙物品本身在藝術上的價值,也應相當的注意……在科學博物館中缺乏美的要素,在美術博物館中,對于教育上的工作每不注意。11.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第163-164頁。
相反,也有一種鼓勵美術館要節制使用文字說明的認識,以防干擾審美:“博物館中陳列物品的目的,第一須將物品映于觀者的眼前,而覺愉快,第二便于利用物而傳達知識。……美術館陳列,大多以合上述第一種目的而行之。故能配置優雅而注意于采光的調和、色彩的配合,并避去用太觸目的說明為最要。”12.參見費耕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中華書局,1936年,第161頁。
民國時期,國內對博物館理論的研究相當不足。無論對展品的排列順序,還是對說明文字等展覽闡釋的標準,都有待進一步明確和改進。此時的天津美術館之展覽實踐也只能達到“有限的秩序感”。
二、復制品展示、“原作”觀與條件局限
今天,我們往往要求美術館展示藝術品“原作”,但民國時期天津美術館的展覽出現了大量復制品。
首先是大量的雕塑復制品。正如學者李軍曾指出,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收藏中有豐富的古代雕塑復制品,以服務于專業藝術教育。它們影響到學院派和古典主義創作的“理想美”以及西方人的藝術趣味。13.參見李軍:《可視的藝術史:從教堂到博物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0頁。不僅天津美術館有一批西方雕塑復制品,同時期的蘇州美術館更以其雕塑復制品的數量龐大而聞名。兩家美術館的創辦者,嚴智開和顏文樑都接受過法國的專業美術學院教育。1931年到1933年,1935年到1947年,天津美術館開展了專業的西畫培訓。這批雕塑復制品在展覽之外,還被用于教學。
其次是“圖片”。館方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向教育局請專款作收藏、藝術品照片、復制品模型和拓片等”14.《琳瑯滿目之美術館》,《益世報》,1930年10月24日,第二張第六版。。其收藏范圍包括了原作和復制品。1931年的雕塑展覽中,中國古石刻照片“系采自日本書籍中所有而加以鏡框者”,“歐洲雕塑品原物照像,則又采自德籍而懸諸鏡者也”15.《美術館之雕展》,《北洋畫報》,1931年10月27日,第695期第3版。。彩色圖片很多直接取自國外書籍,版權問題此時還不在考慮的范圍內。
盡管復制品的藝術“靈韻”消失,但圖片在早期美術館的使用還是有助于美術的傳播。國外的美術館,如英國的博物館中就有設立專門的印刷品陳列室案例16.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大量地使用圖片作為藝術品原作的替身使天津美術館的展示內容得以豐富和拓展。通過翻拍印刷的圖片,天津的觀眾可以看到“德國歷代名畫展”、“法國藝術圖片展”、“西洋名畫圖片展”等。“博物館展覽會”中的大量圖片還讓他們有機會看到國外博物館的建筑和豐富的館藏。
然而,天津美術館“德國歷代名畫展”的報道中卻暴露出繪畫圖片“頂替”原作的情況。1936年12月11日,《大公報》的短消息《德國名畫市立美術館十八日展覽》說“德國歷代名畫展”展覽作品“均為精印品”,且強調“與原作無異”17.《德國名畫市立美術館十八日展覽》,《大公報》,1936年12月11日,第二張第六版。—但之前的報道也沒有提到展品是復制品。相似的,1948年天津美術館向上級匯報舉辦郎世寧畫展的檔案顯示,雖展覽名稱為“郎世寧真跡展”,但展示內容實際為真跡的圖片。顯然,這兩次展覽都被冠以“畫展”之名,卻主要利用復制的圖片。
此做法是否說明,民國時期人們有將圖片視為原作的普遍觀念?1934年10月的歷代名畫展報道中,署名為“榮”的作者識破了明人仿宋人的畫作,但仍抱以欣賞的眼光。中國人自古對高質量的國畫贗作并不太排斥。這種傳統可能也影響到時人對各種繪畫復制品的寬容態度。而且機器復制的圖片可能會比手工復制品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原作。不過,觀眾因為復制品與原作的差異產生對原作錯誤認知的情況,在當時還沒有被廣泛意識到。
此外,用繪畫的圖片復制品代替原作是一種情況,用二維圖片代替三維原作則是另一種狀況:雕塑、建筑、石刻、青銅器等展品的圖片,不僅像繪畫原作與復制品那樣跨越了媒介,還跨越了平面與立體的維度。安德烈·馬爾羅就認為:“……無論是細密畫、壁畫、彩色玻璃鑲嵌畫,還是壁毯、塞西亞飾板、油畫、古希臘瓶畫的‘細節’甚至雕像,都成為‘彩色底片’。在照片沖印過程中,它們失去作為物體的屬性;但同樣的,它們可能獲得的最大的意義是在風格方面。”18.安德烈·馬爾羅:《沉默之聲》,轉引自道格拉斯·克林普:《在博物館的廢墟上》,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0年,第45頁。圖片的轉譯事關藝術史在20世紀的構建方式。19.巫鴻也在《美術史十議》中的第二章“圖像的轉譯與美術的釋讀”討論過這一話題。他特別指出,沃爾夫林的風格研究從中受益。它使得藝術史可以論述的范圍得到巨大的拓展,過去不可能完成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接受過專業訓練,具備國際視野的首任館長嚴智開了解圖片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也知道它為展覽帶來的可能行。
不過,照片與實物存在巨大差異。觀者只能通過圖片中的視覺“符號”,調動想象力以盡力還原實物的三維形態。礙于技術發展的局限,圖片難以精確記錄原作的質感、色澤等信息,它也很難幫助觀看者想象出實物的尺寸及其空間感。
物質條件的局限是造成圖片替代原作的最大原因。對于美術館而言,雖然三維雕塑復制品比二維雕塑圖片的展示效果會好些,但制作精良的雕塑三維復制品往往要從國外購買,花費不菲。圖片的價格相對原作便宜,還可節約展示和收藏的空間。當然,民國時期,想要獲得精美的美術品圖像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到美術館看這些復制的圖片,也不失為一種間接了解原作之道。
三、寬泛的“美育”與能動的被啟蒙者
天津美術館的各類展覽—藝術的和非藝術的—以實物或圖像對觀眾進行涉及現代都市生活各方面內容的教育。它們屬于民國時期廣義“美育”的范疇。
其中,有關現代藝術新門類的臨時展覽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攝影展覽和郵票展覽為代表。它們反映、傳播并引導了城市中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市民的視覺文化潮流和趣味。從建立到天津淪陷之前,天津美術館堅持每年舉辦一到兩次美術攝影展覽。除了傳播藝術觀念,這種持續的展覽還反向影響到攝影的發展。20.請參見筆者拙文《民國初期天津市美術館的美術影展與美術攝影文化的早期建構》。而1937年的郵票展覽是華北地區最早的一次,引領收藏潮流。從媒介本身而言,攝影是新近流行的藝術創作方式,但其藝術性在當時存有爭議;郵票也屬于“圖案”的范疇。它們都不是傳統藝術門類。第二類則包括木刻版畫和漫畫展覽。它們在天津美術館中各舉辦過一次,但展現著新時代藝術的大眾化發展方向。木刻版畫和漫畫,都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重要藝術媒介,肩負著宣傳的功能。1935年在此舉辦的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更成為這種藝術媒介經歷波折后加速發展的里程碑。第三類,推動工商業發展的設計展覽,包括圖案和建筑。“圖案設計”即今天所說的“平面設計”。它在民國時期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也不受重視。而天津美術館的圖案展覽旨在提高設計水平,進而促進工商業發展。該館涉及建筑的六次展覽涵蓋古今,在現代建筑設計之外,也展示了我國傳統建筑模型。這三類新興藝術的展覽回應著都市環境中經濟、政治與藝術的互動和相互影響,也提示著與普通人生活更為緊密的視覺藝術門類的拓展。當然,這也折射出天津美術館館方人員對藝術發展和社會需求的敏銳觀察。
而對中西經典藝術門類的展示也是天津美術館臨時展覽的重要內容。“西畫”和“國畫”的相關展覽在天津美術館中時有呈現。觀眾可以通過展覽見證它們在相互張望中取得發展的過程。西方的雕塑和中國的石刻也在展覽中有所亮相,但兩者未必能夠直接對應,則臨時展覽中兩者雖同場出現,但并未作為同類一起展示。
無論哪種藝術門類,天津美術館的美術展覽反應了一個國際范圍內博物館展覽的發展趨勢:“從前每多以古代珍品陳列的,近來亦多改注重近世繪畫及現代藝術。”21.費耕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中華書局,1936年,第149頁。新興的現代藝術門類自不用說,該館也展示時下國畫家和油畫家的作品。首任館長嚴智開曾輾轉學習于日本、美國和法國,并關注各地博物館的發展狀況,在注意陳列現代藝術展品的做法上也與國際接軌。
此外,天津美術館中非藝術類的臨時展覽覆蓋了多樣的內容:既有進行公民教育的展覽,包含如衛生教育、拒毒宣傳、科學、尊孔等內容;又有培養“國家未來”的兒童珍玩、教具、書畫、工藝等與兒童教育相關的內容。以公民教育為目的的展覽試圖使參觀者可以理解圖像傳達的政治、經濟、歷史、科學等多方面信息。而學校的學生們參與程度更深,他們的作品在天津美術館的一系列兒童教育展覽中展示。此舉調動了學童繪圖和圖解概念的能力。這些非藝術展覽的舉辦符合蔡元培倡導美育的目的,即美化社會,改良社會。他在《美育代宗教》中說:“至于美育的范圍要比美術大得多,包括一切音樂、文學、戲院、電影、公園、小小園林的布置、繁華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靜的鄉村(例如龍華)等等,此外如個人的舉動(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談)、社會的組織、學術團體、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種種的社會現狀,是美化。美育是廣義的”22.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60頁。。
在臨時展覽之外,民國時期天津美術館的長期陳列以一種更具結構性的方式,體現出對展品,特別是藝術品類型的劃分思路。并且,因為長期陳列經歷了調整,其歷時性的變遷也可資比較。首先,其利用館藏舉辦的1930年的開幕展中的分類是長期陳列的雛形。其分為“雕刻部”“繪畫部”和“模型部”23.《美術館今日開幕》,《益世報》,1930年10月24日,第一張第二版。三類。1933年,長期陳列包括了建筑陳列部、金石書畫部、雕型、西畫部、中國雕塑陳列部共五個部分。1935年,分類變為歷史文物、古代石刻、工藝美術、建筑模型、古今書畫、東西繪畫、中外雕塑、古今拓照、美術攝影,共九種。1946年,其類型又縮減為古今繪畫(附書法)、古今中外建筑、古今中外雕塑、古今中外工藝品、美術攝影共五類。
顯然,第一個分類自世界首家藝術博物館烏菲齊宮建立就已產生,且在法國的藝術教育體系中被繼承的“繪畫-雕塑-建筑”分類。第二個分類方法,在前述西方美術(或美術品)經典分類體系之基礎上,把中國傳統的金石書畫和中國雕塑納入。顯然,中西方藝術還是割裂著,只是雕刻被冠以“雕塑”之名。第三次分類的標準就相對比較統一。首先將歷史文物與美術品區分,再在美術品中大致按照媒介分出八個門類。它比第一次分類增加了比較新興的攝影和工藝美術兩類。不過,此分類仍有問題。歷史與美術的價值可能存在于同一物品;古今書畫與東西繪畫也有重疊。第四個分類雖然縮減,但劃分標準很明確,即完全按照藝術媒介分為五類,古今時代也都被囊括進來。從1930年采納的西方美術經典分類方式,到1933年、1935年和1946年的三次調整,天津美術館美術陳列品(收藏品)分類之調整,折射著“藝術”這一概念從外引入我國,再進行中西融合并逐漸擴大媒介類型的本土化、現代化趨勢。同時,這個過程也顯現出以藝術為最高文明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機器對應分類結構的強勢。
實際上,蔡元培提出的廣義“美育”涵蓋了更為廣泛的領域,包括現代生活,特別是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需要通過各種感官,特別是視覺來獲取信息,追趕上社會文明的步伐,讀圖能力的重要性愈發顯現。天津美術館涉及各方面的展覽,就以各種說明式圖片和實物,輔以文字,讓觀眾了解信息與知識,同時鍛煉著對圖像的認知能力。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文明的產物博物館、美術館中仍存留著類似于神廟的氛圍效果。天津美術館也通過園林和建筑來營造藝術神殿的氛圍。24.請參見拙文《為現代城市而設:民國時期天津美術館的主樓建筑與空間的敘事》。天津美術館的參觀者就描述過這種一種體驗:“全華北的幾個特別市,物質文明大概要列天津為第一等了,可是除去數不盡的警察、橫沖直碰的汽車和煙塵,以為真就沒有什么可以代表了。市民在這樣的環境里討生活,的確可稱為精神上的無期徒刑……這次市立美術館開第十次攝影展覽會,記者以為這是一次絕好的增進美術觀念的機會。所以盡先趕去看了,并且順便到對過的公園,去逛了一遭……希望讀者抽時間自己去看,無論如何比走四馬路有趣。”25.《走出煙塵的鬧市,到美術館去》,《益世報》,1931年8月9日,第三張第十版。在美術館和公園,這位參觀者感受到了與日常生活非常不一樣的氛圍。
正如卡羅爾·鄧肯在《儀式的文明化:內觀公共藝術博物館》中指出,日常行為的法則因為美術館的審美空間具備的“閾限性”(Liminality)被暫停。這是美術館觀眾進入“審美”儀式的重要條件。進而這位觀眾認真地以“增進美術觀念”的審美態度品評了攝影展覽中的展品,仿佛完成了對神廟般的藝術殿堂中的物品的“膜拜”儀式。
在美術館“神圣”的非日常空間中,建立者期待著美育的、啟蒙的內容可以自然流溢,浸潤參觀者。這就類似于傳播學中刻板的“皮下注射”理論的假設,即觀眾對于傳播的內容是無力抵抗的。無論美術的還是社會教育的內容都是以美育之名,借美術館之特殊空間呈現給觀眾。
不過,在一個預設了非日常的、凝視的觀看的美術館空間里,社會生活中的圖像—比如報刊中常見的攝影圖片和漫畫,商業環境中的廣告“圖案”,革命運動中用于宣傳的木刻版畫圖像—特別是在某些如“勸業場”般失序的布展情景中,是否真的可以在美術館中被凝視?還是說,在琳瑯滿目的展陳中,凝視不得不改變為掃視?
掃視著的展覽參觀者將可能規避閾限性的誘惑。他們不再是被動接受者,而可以是一個個有獨特感知能力和反饋行為的個體。他們有選擇地觀看展覽,對展覽發出自己批評或贊美的聲音。他們不僅會關注展覽的內容,還會對展覽的陳列方式“指手畫腳”。他們或是驚喜于1930年的開幕展中,雕刻的展示背景是“紫絳色的布”26.《美術館之初瞻》,《大公報》,1930年10月26日,第二張第七版。;要么認為黑白影展更需要“添置批評簿子”、“改良陳列次序”、“準許翻照”;再就是嫌棄博物館展覽會的文字說明太少,等等。
而觀眾的反饋得到了美術館方面的部分回應。館長嚴智開在接受采訪時認為,觀眾不應注意布展狀況:“有人脫離像片而轉注意于場所之布置及懸掛之方法,是更非題中應有之義”27.《天津美術館之影展》,《北洋畫報》1930年11月29日,第3版。。這種精英式的強勢態度將美術展覽的不足推脫到觀眾身上。其實質是對于博物館、美術館“神廟”般的閾限性之迷信。似乎只要場所的閾限性“魔力”在場,展覽的陳列設計、敘事邏輯、展品間相互關系、現場對展覽的闡釋說明等引導觀眾進一步理解展品、獲得展覽希望傳達之信息的工作都不再重要。事實卻是,閾限性需要上述工作以營造。至于天津美術館是否根據觀眾的意見而進行過展覽的改動,筆者不得而知。博物館作為論壇的功能,倒是在展覽的內容之外,意外顯現出來。28.學者徐堅認為,博物館的“常設展是神廟,而臨時展是論壇”。不過,他是從展覽對展品闡釋的層面來討論,本文則是以臨時展覽引起的觀眾與舉辦者之間的對話來考察的。參見徐堅:《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10頁,第25頁。報刊文字協助權利在博物館與觀眾間流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