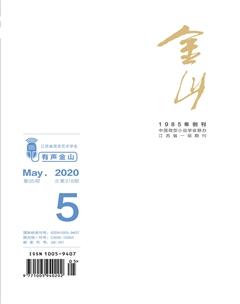鏡芙先生的師道
趙金柏

趙蓉曾,字鏡芙(1852.3.13—1924.11.1),江蘇丹徒大港鎮(今鎮江新區)人。趙蓉曾學識精深,無意功名,在家宅“天香閣”設館授業,培養出大批杰出的人才,人們尊稱他鏡芙先生。
鏡芙先生課徒有何獨到之處呢?
懷古勵志? ? 醍醐灌頂
鎮江東鄉大港古鎮有一則“天香閣”軼聞:鏡芙先生帶著將要畢業的弟子到大港東岳廟,拜謁廟中的岳飛、韓世忠塑像,寄語弟子日后成為有用之材。禮畢,先生指著廟東頭的田家村對弟子出一上聯:“東岳廟東田家田里田雞叫”。弟子們撓頭搔耳一時對不出如意的下聯。先生說:“不著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后你們行走天下,對來不遲。”后來弟子王家駒在北京做大學校長,也效法先生懷古勵志。有一次,當他與學生登上長城,突然一拍腦袋叫道:“有了!”面對驚訝的學生,他說明原委,脫口對出:“北京城北燕國燕山燕子飛”。鏡芙先生看了此聯十分滿意,遂將小女兒趙芬許配給這個得意門生。
鏡芙先生引導弟子“自強不息”“行天下大道”做“大丈夫”,不作抽象說教。他帶領弟子走出課堂,利用歷史文化遺跡與民俗文化,對弟子進行身臨其境的教育。東鄉一帶有登圌山的習俗,清明過后登山節(黃明節)來臨,弟子們就貓子抓心地想著要爬山。鏡芙先生因勢利導把登圌山當做天香閣的入門課程。他帶著弟子登上山頂,從自然風光到江山社稷,從張煌言的《師次圌山》詩到圌山軍民抗倭的史篇,從圌山的抗英炮臺到韓世忠抗金的遺跡,進行振聾發聵的歷史講解與亦歌亦泣的詩詞吟誦。
越國公張世杰率部屯駐圌山抗戰的歷史與宋末三杰的愛國氣節是每次登山必講的重點內容。
圌山報恩塔下,一江春水,萬古山魂,鏡芙先生講授中華民族最大的文化災難、歷史危機與愛國氣節,使弟子醍醐灌頂,激發弟子發憤圖強,樹立遠大的人生目標。憂患滄桑的歷史與頂天立地的精神是“天香閣”地靈人杰的注腳。
形象啟迪? ? 玄妙之門
鏡芙先生充分利用藝術形象啟迪弟子的悟性。“天香閣”教學始終伴隨著詩詞、書法與音樂。他讓弟子組織“清音隊”,音樂伴奏的詩詞吟唱是“天香閣”課余的風雅娛樂;先生尤其重視書法,書法是“天香閣”的修養課。鏡芙先生教書法不拘泥于法,而是由法入道,由道化人,一筆一畫都關乎悟性、道行、審美、智慧、學問、人格、胸襟、氣息。在先生這里,書法與音樂也像詩詞一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著啟迪悟性、修身養性、格物致知的作用。
鏡芙先生通過藝術培養弟子卓有成效。當年,趙聲與趙紹甫從“天香閣”投考江南水師學堂,在全國700多個考生中分別以第一名與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弟子們說“鏡芙先生不搞灌輸、不用戒尺,在‘天香閣很快樂”。
怎樣快樂地取得好成績?可惜弟子們沒有留下詳細的記載。弟子趙紹甫用先生的這套辦法,教愛孫趙無極詩詞、書法,為無極后來的藝術發展拓展了廣闊的空間。趙紹甫的教育實踐或能說明問題。
趙無極在《回憶錄》中說:“祖父對書法美的要求,從不馬虎,盡管對這個學書法的學徒要求十分嚴格,但在他的監護之下,并不真的苛求,反而成為他快樂的泉源。”“為了教我認字和寫字,祖父不停地在一些物體上寫上標明這些物體名稱的正楷字……四面八方畫了許多棕色和綠色的彎彎曲曲的線條……逗引我創造出一種有意義的東西來。”
原來書法教學意在形象,知識傳授不離生動的形象,知識轉化為能力也靠形象的想象。難怪“天香閣”大廳掛滿書畫,先生講解抽象的理性知識不離感性的藝術形象,這不僅使弟子增強學習興趣,使知識的理解更有厚度,使弟子更牢固地掌握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弟子們的想象力與直覺的領悟、創造能力。
先生的師道博大精深,通達無礙,藝術與智慧、藝術與興趣、藝術與知識、藝術與能力都是相關的。
因人施教? ? 授之以漁
趙聲在推動辛亥革命的緊要關頭引用《易傳》的“需卦”之理,致信孫中山說:“需,德之賊也。成敗關頭不在巧拙,而在遲速。”《易傳》是“天香閣”的基礎課,“易道”不但是先生教學的法寶,也是授與弟子們的寶笈。
先生教學,重在理解與融會貫通,不要求弟子死記硬背,而是簡易功夫,授之以漁。先生用《易傳》之道傳授知識,以天地間“不易”的基本道理,“一以貫之”于各相關知識,讓弟子全面綜合地理解文化,做到觸類旁通,自主學習;從“變易”的規律上把握各種知識的內在理性,開闊視野,聯系社會背景與自然環境,交代前因后果,提出思考問題,促使知識轉化為能力與素質。
黃花崗起義總指揮趙聲是鏡芙先生的兒子,自幼跟父親學習。1900年19歲的趙聲走出“天香閣”,入學軍校、考察日本;1903年擔任三江師范學堂國文教師;1904年擔任長沙實業學校的兵操、歷史教師。趙聲的國文和歷史知識來自于“天香閣”的學習。1905年趙聲打入新軍后,由一名知識分子迅速轉化為一名能“扎硬寨,打死仗”的軍事家;他將新軍改造為武裝革命的主力,為辛亥革命奠定堅實的基礎,而成為同盟會組織、領導、指揮新軍武裝革命的領導人。他過人的能力與過硬的綜合素質來自于“天香閣”的開發培養。
鏡芙先生在全面綜合教育的過程中,根據弟子的天分因人施教,鼓勵個性發展,他的弟子走出天香閣,或進一步接受專業深造或在社會實踐中歷練,多在不同的方向上成才。從武的解朝東留學德國,授少將軍銜,任江蘇都督府軍務司副長、江蘇陸軍小學校長與武漢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校長;從文的王家駒留學日本,任北京法政大學校長、安徽教育廳廳長、中英庚子賠款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從事實業的夏伯安任丹徒十八縣市總董事。銀行家趙漢生,復旦通才趙宋慶、國醫大師章次公、留洋英才趙俊庠、南大學者趙俊欣也都踏著父輩的足跡在“天香閣”啟蒙,他們受到的教益遠在讀書識字之外。
師道傳承? ? 寶貴遺產
鏡芙先生傳道、授業、解惑,弟子多成棟梁之材,特別是李竟成、趙念伯、解朝東、趙啟騄、趙光、趙芬、夏伯安、趙紹甫、章哲亭、趙文湘等弟子在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深明大義,投筆從戎,跟隨趙聲參與辛亥革命,為推翻封建制度、創建共和立下不朽功勛。著名學者趙醉侯將鏡芙先生與中國著名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并列,贊為:“龍頭咄咄馬相伯,麟角崢崢趙鏡芙”。值得重視的是:與出自西學的馬相伯不同,鏡芙先生的師道完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大港《趙氏文翕分譜》記載:鏡芙先生的先祖趙希真倡導后人“有大志慷慨尚義氣延師儒訓”,鏡芙先生“肅然應之而不辭”。深諳國學精髓的他堅守道義,效仿先祖“設義塾以教之”的做法,將先祖“讀書窮理”“以詩書禮樂相承”“以修身為本”的師道與注重整體的傳統文化加以揚棄,形成自己全面而深刻的整體式教育方式,這種整體式的教育既與只管教書識字的一般私塾不同,也與西方分別教育德、知、體、美的做法大相徑庭。鏡芙先生的師道是一筆值得后人研究的寶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