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良知與真知
——伍鐵平先生的學術精神
周流溪
(四川大學/ 北京師范大學)
伍鐵平先生(1928-2013)是中國當代學術界和教育界的知名學者和堅強戰士,其事跡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雖然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榜樣和教導將永遠啟發后學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前進。下面從幾個方面談談我在與伍先生交往中的受益和體會。
一
伍先生出生于湖南湘潭,1945-1946年曾在昆明就讀于西南聯合大學;1946-1947年就讀清華大學(化工系)時,最后越過封鎖線進入冀東解放區參加了革命(投入土改工作)。1948-1950年他在哈爾濱外國語專門(科)學校——黑龍江大學前身——學習,后留校工作(曾主編外專校刊——后名《俄語教學與研究》)。他一生中秉持堅定的思想和信念,而理工類的教育也有助于他養成尊重科學的品格。他對祖國的語言和文化充滿熱愛,但絕不走極端而表現出沙文主義傾向;因為他具備良好的外語修養和國際眼光。他早先曾是個俄語專家;但他對英語、德語、法語等語言也很熟悉,一般學過的和了解的其他語言還有很多。他收集的各種語言辭書達200多部,那怎么也覆蓋上百個語言了吧。從事語言研究,如果不去盡量多了解一些語言,那就不可能具備通達的眼光,甚至連那些旁征博引眾多語言的外國有關專著也讀不下去,并容易僅憑自己的有限知識就信口開河而動輒出錯。
伍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擔任過國外語言學研究室主任、主編過《語言學資料》(后改名《語言學動態》);大量譯介國外語言學著述的日常工作,使他不斷擴展了語言學理論的視野。但是后來其進一步加強普通語言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并不曾受到研究所領導的足夠重視(那個小刊看其名稱就不像個雜志,1980年才改為公開發行的雜志《國外語言學》)。他在所里只是副研究員(連研究員也未曾當上),在恢復研究生制度后的第四年才招收了一名碩士生(姚小平)。我在此處不是要批評我的老師和諸位前輩;語言所沒有在普通語言學研究方面帶頭,實在不是哪一任特定所長的工作有多大欠缺。它在這個方面的投入始終還不如一般高校;也許高校畢竟有教學的緊迫需要吧,反正現有的幾部“語言學概論”(或綱要)之類的書都是高校教師寫成的。1985年伍先生轉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工作,是語言理論教研室的領頭人,為學科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種種原因,他主持的語言學理論方向也還是沒能獲得長足的發展。他在來師大第三年、快60歲時當上了教授(這比我當教授的年齡晚了十年;不過我當教授的年齡又比我的一些學生晚了十年,世道如此也不是人所能預料的);但他沒能當上博士生導師。他曾想在我們外語系加盟帶博士生,而竟被外語系的人拒絕了。當然,一個人能否有所作為也不完全取決于他是否當上“教授”、“博導”。但就伍先生的情況而言,那畢竟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他的學問。
伍先生早年在哈爾濱外專(外院)跟蘇聯專家學習俄語理論語法時閱讀了蘇聯語言學大師們的著作,加上在社科院多年主持譯介國外語言學理論,因而對普通語言學理論和語言學史都比較熟悉。他在語言所跟丁聲樹學過音韻學(反切法)。后來因為探索比較詞源學,又通讀過楊樹達的著作(楊氏是既通國學又能了解西方語言學的學者)。來到師大這個語言文字學重鎮后,他與陸宗達、蕭璋、俞敏、王寧等學者同事接觸多了,在漢語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面的知識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對中外歷史語言學的了解,使他在普通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能有寬廣的視野和足夠的學術素養;這也為他日后識別各種學術觀點準備了良好的基礎。伍先生在語言學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一大批論文(如“語言詞匯的地理分布”[1984] 、“開展中外語言學說史的比較研究——兼論語言類型學對漢語史研究的意義”[1989,1990])和結集的《語言與思維關系新探》(1986,1990)、《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1981年首發論文,1994年編著成書)、《模糊語言學》(1999)、《比較詞源研究》(2011),主編的《普通語言學概要》(1993,2006);此外還有《語言和文化評論集》(伍鐵平1997/1998)、《語言文字學學術批判和批評文集》(伍鐵平2010)等。他在雜志編輯和國外語言學的譯介工作中也留下了大量著述。《普通語言學概要》是一本廣受歡迎的教材。伍先生在中國首倡模糊語言學研究,影響深遠。他也是最早把語言類型學引進中國并運用于漢語研究的人,其論文“男性直系親屬名稱的類型比較”(載于北京市語言學會編《語言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5)就是這種研究的成果。伍先生曾經長年下了極大的功夫要編撰一部《俄語詞源詞典》;但出版社由于俄語地位在中國的下降而取消了出版合同,該書的編撰不能得到后續支持便夭折了。這是極為可惜的事。
二
我在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研究生畢業后沒有留在研究室做語言學研究,而是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當了英語教師(這主要是基于生活的考慮而做出的選擇)。后來我不想教英語了,就調到北京師大外語系來。在這里我的工作是講授語言學的相關課程(我講課都用英語,但我不是教英語)。從此我與伍先生的交往便日益密切起來了。伍先生本是我在社科院的師長輩,但他從不以師長自居,見面都稱我為“老周”,這使我有點惶恐(他夫人稱我為“小周”我還覺得好些)。我們每逢見面(多是我去拜訪他,他住西郊時我就去過他家),我們談的都是學問。伍先生披覽既廣、交游也多,從他那里我獲得了不少知識、信息和聯系。我們在語言學問題上有很多共同見解,也在經營這一學問中互相支持(在我們這里中文和外語兩個陣地并非老死不相往來——當然這也取決于雙方人員的學業基礎和交往意愿)。伍先生和我都重視普通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力求準確把握其精髓,連術語的使用都很注意。當然我們也都想為語言學的學科發展做出一些貢獻。我在教學生涯的最后十年招收過30多名博士生,他們幾乎都是研究語言學的,涉及該學科的不同路線和各個部門。伍先生非常歡迎我的學生前去請教,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學生看待,總是給予耐心細致的指導,并以自己的學風對他們進行熏陶。
在改革開放中,伴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學術的發展,也出現了學術腐敗現象。當學術騙子和行為不端者恣意妄為時,很多人都視而不見、甚或姑息放縱。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早就呼吁要開展學術批評(參看楊玉圣 1998 [該文“九十年代中國的一大學案——學術規范討論備忘錄”原載于香港《中國書評》1998年復刊號])。這時伍先生挺身而出,以最實在、最堅定的工作大力進行學術打假和學術批評。中國近現代史上屢見的“湖湘骨氣”在伍先生身上又表現出來了。(當然別的因素也會發生作用。他嘗云在學習法語時得知pillage [掠奪、搶劫] 的轉義是“抄襲、剽竊”時,那極大地加深了他對這種現象的鄙視。人講德義,中西皆然;伍先生可謂善于從人類德性中汲取力量。)他自言“眼睛里揉不進沙子”,決不能容忍歪風泛濫,在天降大任時更是當仁不讓、義無反顧。魯迅所云民族精神的脊梁,就是這種人物。伍先生在為國家有關部門提供語言學科研規劃咨詢報告時普遍查閱各種書刊來全面了解和掌握國內語言學研究現狀,于中發現了學界的很多假冒偽劣產品;他從批評申小龍的抄襲剽竊克隆和揭露徐德江的假冒教授兜售偽科學開始了學術批評、學術打假的漫長斗爭。為此他遭遇重重阻力;他的文章固然有在較高級別的刊物發表的,但也不止一次被一些刊物退稿,有的文章只能在級別較低或地處邊遠的刊物登載。他在家庭經濟和身體健康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他不屈不懼、堅持到底,把生命的最后年華都奉獻于此,甚至在住院臨終前的日子里還念念不忘。其行動得到了學界的普遍響應支持,支持者中不但有伍先生的同事及校內外的朋友,還有外國學人。伍先生一些弟子也積極上陣。徐德江冒稱黎錦熙的“不一般的弟子”、自吹或雇托兒吹捧他創造了“新階段”的人類語言文字理論。袁曉園、安子介寫過錯誤百出的文章與徐德江呼應(在袁、安、徐、申“四維架構”中徐之“公式”妄稱“普通語言學”);他們偷換概念歪曲事實來誤導學界和群眾,夸大漢字的“優越性”和被簡化的“百年冤案”,從而或明或暗反對國家的語言文字規范化政策。但語文不規范化則無法走向現代化和信息化!呂叔湘先生任《中國語文》主編時,曾拒絕發表袁、安的文章(伍鐵平2010:86)。伍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則從各個方面把徐德江的“理論”批駁得體無完膚。可惡的是徐德江1995年11月向法庭控告伍先生侵犯其名譽權而竟獲法院受理(1996年1月),出現了中國法政史上假教授狀告真教授的丑惡例子。這激起學界人士的義憤。以呂叔湘、周有光等為代表的148位語文工作者簽名發出呼吁支持伍先生。王寧教授聯絡主持正義的律師為伍先生辯護。而徐德江的律師竟然對簽名者進行恫嚇;但那遭到了被恫嚇者的反擊,并導致更多的人們支持伍先生。我在呂先生病榻旁向他報告情況并請得了他的簽名號令;他一呼百應使簽名聲援伍先生的學者最終多達708人。法院面對這種情勢不得不于1998年7月宣布徐德江此案“不宜受理”,從而客觀上宣告了伍先生事實上的勝訴。
我的一些友生也積極與伍先生站在一起投入這一學術打假和學術批評的行動。比如周利娟寫了“不爭不‘明’——讀伍鐵平《語言和文化評論集》”(《北方論叢》1997/6),文旭寫了“《語言和文化評論集》(重印本)述評”(《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1);又李京廉有“學術批評和學術打假的意義——讀《語言文字學辨偽集》”(《人民政協報》2004.8.9)和“學術批評的意義——評《語言文字學辨偽集》”(《中華讀書報》2004.12.8);李美霞有“一部正本清源的學術著作——評《語言文字學辨偽集》”(《學術界》2006/5)。龐建榮和伍鐵平合寫了“模糊語言=文學語言?——評何南林文的一些錯誤”(《渤海大學學報》2005/5);王慶和伍鐵平合寫了“正確的翻譯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前提”(屠國元主編《三湘譯論》第6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王慶又寫了“追求學術公平,弘揚社會正義——批駁《漢字文化》2009年第2期的部分言論”。(以上三文收錄于伍鐵平2010。)王慶還有《推進學術批評 純凈學術環境——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伍鐵平先生訪談錄》(《社會科學論壇》2010/10)以及《論文字的本質及文字與語言的關系——評張朋朋文章中的一些言論》(《當代外語研究》2011/7)和別的學術批評文章。《語言和文化評論集》出版后,我在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中加進了學風教育的內容,以此書為主要參考。我也為它寫過一篇書評,但未能發表。
伍先生對學界一些長輩、平輩和晚輩,對一些名流或顯貴,于其偏頗觀點或過頭言論以及著述和學風的粗疏之失,還有圍繞著他們的一些不實吹噓,都進行過中肯的批評。這些批評并不是針對“私敵”,而是從原則出發的嚴諫或勸勉;其中處處體現了他治學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的作風,其意見(包括批評的觀點以及批評所涉及的理論和語言材料)實可供當事者和后學參考。伍先生還說:“我們呼吁并非專門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人在沒有深入研究語言文字、語言文字學和我國當前語言文字學界的狀況時,不要再就語言文字學胡亂發表意見,須知幾乎每個成年人都會的語言和文字絕不等于語言文字學。要想成為語言文字學家,往往要皓首窮經,付出畢生的辛勤勞動。”(否則,這些非語言文字學工作者就一定會說出許多外行話,受人批評。他們甚至會起到干預或阻撓反對偽科學之斗爭的作用。)針對有些非語言文字學界的人隨便同意在民間刊物擔任顧問和學術委員會職務,伍先生指出:“須知不做實事,僅掛虛名,以擴大自己的聲望,聽任他人利用自己的名聲為所欲為,是我國當前學風不正的表現之一。”(伍鐵平2010:69。)現在國家有關部門已經要整頓這種情況了。
三
在和伍先生的多年交往中,我的教學和研究都得到過伍先生不少啟發、鼓勵和幫助。
我在上高中時讀過王宗炎著《英語語法入門》(那是一本普及型的書,講述的是教學語法),從此在高中和大學時代都不必再看英語語法書了。到了在中學教英語的時候,我讀到國外學者寫的好幾種語法書(大部頭的學術型著作),很受啟發和鞭策。但讀這些書已經越出了學習和講授英語的需要,是研究的需要了。王力先生說過:他喜歡文學和語言學,但更愛語言學,因為語言學是科學。我也有這樣的看法。文革后在報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時候外文所和語言所我都曾考慮過,最終還是上了語言所跟從呂叔湘先生。國外多位語法學家都是英語教師出身,呂先生也是從英語教師而成功為語言學家。王力是中國語言學的集大成者(周流溪2001b: 89-91)。但我的學術志向,第一步是“兼王呂而有之”,此外還有更高的理想。這不是狂妄,是后學要站在前輩巨人的肩上向前遠眺的態度。我在自己的論文集《語言研究與語言教學》開篇(周流溪2001a:1-3)談的是自己步入中年時的體會和認識:“語言研究的學術層次”。就語法研究而言共有四層:教學語法、學術語法、理論語法、語法理論,最后的“語法理論”就是升華了的語言學理論。王力早在1957年就指出(《中國語文》第3期):“中國語言學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普通語言學的落后。這一個薄弱的部門如果不加強,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前途就會遭受很大的障礙。”我在清華大學紀念王力百年誕辰的“21世紀漢語語法及語法理論研究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重申了他的這一觀點(周流溪2001a:276)。伍先生2002年對申小龍談“西方語言理論”表現出盲目排外的情緒提出批評時,也引用了王力這段話(伍鐵平2010:164)。
我們在讀研究生時有語言學基礎的課程(呂師安排從美國回歸的廖秋忠先生來講授)。我曾把美國一本《語言導論》(Fromkin & Rodman,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的一章譯出刊于《國外語言學》。畢業前后我們在呂師指導下集體翻譯了帕默爾的《語言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一版)。伍先生很關注這本書,他發現我們有幾處譯錯了,還被申小龍照抄了去(甚至反復地抄)。我們已經錯了,但申小龍把錯誤擴散了。在該書第九章附注10里(1983:149)帕默爾引de Laguna的話說:“這個世界里有‘赤色分子’和‘反動分子’,有 flappers(黃毛丫頭)和lounge lizards(在時髦場所鬼混的男子),有live wires(生龍活虎的人),也有morons(白癡)。”伍先生(1997/1998:92)指出譯文的不妥處;我在校閱《語言學概論》第二版(2013/2016:179)時已經改正為:“……有服裝奇異舉止輕浮的少女( flappers)和在時髦場所鬼混的男子(lounge lizards),有生龍活虎的人(live wires),也有‘呆笨’的人(morons)。”又,原譯第六章有這樣的譯文(1983:99):“在中國,一如在埃及,文字不過是一種程式化了的(stylized)、簡化了的圖畫的系統。……書面語言是獨立于(independent of)口頭語言的各種變化之外的。”此處譯文有誤,尤其是stylized一詞,應譯為“線條化了的”,因為style在這里指的是古代刻寫用的鐵筆之類工具。由于該詞用的是古代的本義,我們太粗心而弄錯了。伍先生很細心,又具有詞源學的功底,所以能辨析出來(伍鐵平2010:226-227)。在《語言學概論》第二版(2013:117),我已將此處改譯為:“在中國,一如在古埃及,文字不過是一種線條化了的、簡化了的圖畫系統。……書面語言并非總是受制于口頭語言的各種變遷和變異。”
2000-2001年我曾為外研社引進的《語言學教程》(Radford等編)、《歷史語言學》(Trask著)、《語言學綜覽》(Aronoff 和Rees-Miller編)寫過導讀。我力圖不負出版社所望拿出最好的成績。歷史語言學很多人視為畏途,我要給出可讀的準確引導。《綜覽》是一部800多頁全面介紹語言學各部門的巨著,名為“手冊”而實不易對付;我要正確引導讀者養成全面關注語言學眾多分支學科的態度,既要培養對語言學的興趣樂于探索,又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孤芳自賞。《教程》是一部以生成語言學觀點編寫的語言學入門書,我有準確評價它的義務。我與沈家煊、林書武合譯過喬氏的《支配和約束論集》、《形式和解釋論文集》;我們承認他在當代語言學上的貢獻也愿意介紹其新觀點,但我們幾個翻譯者都沒有成為喬派的信徒。Radford等編《教程》的導讀已先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上發表過。在肯定該書之優點的同時,我列舉其不介紹語言學各種重大問題的缺陷并對之作了最嚴厲的批評(那肯定是所有幾十部書的專家導讀中僅見者):“一部語言學概論應該寫入一些什么內容?……像這部書,對新成果的介紹大部分是生成學派方面的或能與該派相當地兼容的東西。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既需要有重點、有見解的新的語言學概論書,也需要更客觀的、涵蓋面更廣的新的語言學概論書。”編者們應該看到這個導讀及其批評,所以第二版做了一些增補和改進。外研社又引進了該版并讓我再寫導讀;我因事忙而拖延了一年左右,但出版社很寬容仍采納拙文把比第一版導讀篇幅翻倍(達19頁)的文本照單全收。這次我也肯定了編者做出的修改并詳細論述了國內開課教師應該注意的問題,但又再次嚴肅批評了該版的不足之處。比如編者在談語音的第二章劈頭就問:“英語里有多少個音?”這是非常不合適的寫法。你哪怕只做個樣子也總得拐個彎才提到你偏愛的英語吧?我引了布龍菲爾德《語言論》的例子:他在前面有一章介紹世界上的語言,講語音也不限于英語,連梵語的四類爆破音都講了(斯足以祛除很多人的迷誤痼疾——那很大程度上是漢人學英語養成的壞毛病,以為送氣的就是清音、不送氣的一定是濁音!)。這種大家手筆才是撰寫語言學概論的應有作風。針對喬派的句法分析我指出:那里還有不易對付的問題,比如杜牧《阿房宮賦》結尾那個四次用了“后人”的半真半假循環結構的長句以及《莊子·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那個復句(此處若無馮友蘭的英譯,原文頗難理解!);漢語句法靈活又無形態束縛,我們諒必需要在語法的形式分析前[及分析中]考慮語句的意義內容[及其思想精神]。至于像俄語那樣形態豐富詞序多變的語言,要按大體上從英語歸納出來的生成分析法去析解大概也不容易。
前蘇聯有些語言學家曾蔑視和狠批生成語言學,這固然太過偏頗。但蘇聯人為何敢這樣做?那是因為俄蘇自有可以屹立于歐洲和世界學林的語言學;看看波鐵布尼亞、庫爾德內、福爾圖納托夫、沙赫馬托夫、謝爾巴、維諾格拉多夫、雅柯布遜等等名字就可以知道了。庫爾德內創立了喀山學派,他和他的學生克魯舍夫斯基對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曾采用他們著作的觀點并加以改造和發展。但庫爾德內對布拉格學派也有很大影響。謝爾巴等人(庫爾德內的弟子)創立了列寧格勒音位學派。而阿瓦涅索夫與列弗爾馬茨基等創立的莫斯科音位學派,早在1930年代(比喬姆斯基和哈勒的生成音系學早30年)就把音位看作由位置上交替的具體音素表現出來的、具有單純功能作用的抽象單位(《國外語言學》1981.3:68)。蘇聯以語言學大國自許,很重視普通語言學的研究和普及;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曾把撰寫一部代表蘇聯學派主張、概括本國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協調業內觀點作用]的大型系統著述作為重點[國家]科研項目來攻關(1970-1973年出版了三卷本《普通語言學》,隨后又譯為幾種外語對外宣傳)。蘇聯高校俄語系和外語系本科一般在幾年里開設三門與普通語言學相關的課程:語言學引論(一年級就開課,介紹普通語言學的起碼知識和基本概念)、語言學史(系統介紹國內外語言學理論思想的更迭和各個流派的縱橫)、普通語言學(該課在最后一年開設,系統闡明蘇聯學派的語言觀和方法論)。從1963年起普通語言學作為必修課在高校語文系普遍開設。在此前后出版了多種普通語言學教程,其中最著名者為茲維金采夫的《普通語言學綱要》(1962年莫斯科大學出版,中譯本1981年出版[伍鐵平參與翻譯和校對])和柯杜霍夫的《普通語言學》(莫斯科1973,中譯本1987)。柯氏曾參與科學院三卷本的編寫,他的這部書分為(兼有)史、論、法三部分,一體承擔了前述三門課的任務。以上所述蘇聯的普通語言學研究和教學,與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詳見俞約法“蘇聯普通語言學教材建設沿革——兼評柯杜霍夫的《普通語言學》”一文,《語言教學與研究》1988/4)。誠然,中國也有很好的學術;但一來學人素無創立獨家思辨體系的“野心”(或興趣),二來學術范式也難與國際“接軌”,加上政治運動的干擾,故而總體上我們在學科上還是落后了。每當國外出現新理論,我們多只顧“進口”。我們“出口”的東西太少。呂先生本來很早就提出句子分析的“動詞中心”說;但因為上述原因,那功勞卻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國學者特尼埃爾獨占了。今天一談起動詞中心觀,人們就只提到特尼埃爾的依存語法。這豈不可惜?
我在北京師大外語系開設的普通語言學課程不大正規(這與我看到的美國類似院系開設的“Linguistics I”、“Linguistics II”那種分步升級的課程頗有距離),因為英語專業研究生的主要方向被定為“英語語言與教學”,后來竟然一度被篡改為“英語語言教學”(本校研究生院也沒有發覺和質疑)。在那種環境下,更沒有什么正規的語用學、語義學,課程名稱只是“意義與交際”!總之多數課程只有一些實用主義的泛泛名稱。這也難怪:我們單位的默認目標只是培養外語教師,所以決策者的眼睛只盯住外語教學。更有甚者,以前有一位校領導說過:“外語系還能運轉,系領導工作做得不錯。”而直到外語系改為外文學院之后,一次學校某個分管學科工作的領導人還說:“外文學院的工作開展得很好,現在公外的教師再不來學校鬧事了。”在他們心目中,外語院系能得過且過就算大善、萬幸。外語教師反正不[用]搞學問!外國語言、文學、文化、教育,尤其世界上的語言學是什么東西,他們既不知道,也沒有興趣去了解。——誰叫那“語言學”是沒有用的東西呢?因此說來有趣:盡管我瞎猜伍先生上課第一句話可能會說“語言學是領先的科學”,但我上課第一句話卻是“語言學是沒有用的”!這叫做當頭棒喝的說教。(而這還是大實話:靠語言學并不能生產面包,更不能造出大炮。)但我馬上會安慰學生道:“你們也別太喪氣,因為有人還要學習更沒有用的東西——哲學。(學生滿堂大笑。)不過話說回來,許國璋指出: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兩百年來有一種持之以恒一貫不變的強國哲學!這樣看來,哲學應該是有用的。……那么我們學習語言學應當做的事情便是要找出它的‘無用之用’。”——然而總的說來,由于外部環境對我的開課要求不高,這就助長了我的惰性: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能把語言學這門課講得更好更透,自己也沒有把講義編成高規格的教材。外文學院建立后我當了分管研究生教學和科研的副院長,我便主持修訂了培養計劃而第一次明確地在我校外語學科設立語言學、語法學、語用學等課程(我們也設立學科教學論、西方文論等課程)。但工作仍不無阻力而且好景不長,我推行的學科發展計劃未能實現。我自己在學科研究中也只能默默地積聚力量。我還要繼續在語言學研究中有新的作為。伍先生的榜樣一直在激勵著我不斷前進。
至今我在語言學研究中的心得多在宏觀問題上。首先,我很注意當代語言學的路線。這是要結合語言學的歷史和現狀才能逐步看清的,路線也與研究旨趣和方法密切相關。我的長文《近五十年來語言學的發展》(《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1998年分三期連載)主要談結構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已隱含這是兩條路線之意;該文也涉及“認知語法”,但其勢頭當時還不夠大,我也未曾從獨立路線的高度來評說它。不管怎樣,它重視語義和語言的心理現實性之特點還是得到中國學人較多的認可,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也很迅速。在外研社引進的《語言學教程》(2000)導讀里我就指出:編者沒有介紹認知語言學(也沒有提及認知語用學)是不妥的。我在進行認知語言學的探索和指導博士生的過程中,逐步明確形成三條路線(結構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并大力宣傳之。現在三條路線似乎是客觀存在的簡單事實,為何吾說仍不失為一家之言的“創見”?因為在各派自大門戶者看來,別派的路線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可以宣稱把它納入自家路線的范圍,或者雖似存在而無甚價值即形同不存在。比如結構派有人就稱現在搞認知語言學的人盡是胡說。(雷柯夫是從結構派叛逆出來另立山頭的,他的東西自然是“胡說”了。不過仍然待在結構派陣營里的杰肯道夫現在倒坦然承認:到頭來證明了過去被他們批判的雷柯夫的語義學觀點還是正確的。)功能派在克服結構派的極端方面有所貢獻;但它又認為功能語言學可以囊括認知語言學,這卻不對(過去就有過功能語言學可以取代語用學的說法)。這后兩條路線的一個主要區別是:功能派關注什么因素促成人們選擇某個語言形式,認知派則解釋人們為何能在心理上接受某個形式。其實任何一條路線都不能包打天下。在如何認識研究路線的問題上,人們會有不同意見,而且看法也會因時而異。國外學者亦非人人都有很正確的路線觀念,例如萊普希《結構語言學通論》(1970)就將韓禮德的功能語言學歸入結構語言學(那也與韓氏體系還處在初期階段有關,其實60年代后期韓氏已受布拉格學派影響)。我們承認韓禮德也研究語言的結構(其學說初稱“階與范疇語法”,后稱系統語法和系統-功能語法,現稱功能語言學);但其理論基點與新老結構派都不一樣。拿功能派和結構派相比, 就能看出:喬姆斯基一派(以前曾稱轉換生成語言學, 現稱生成語言學,尤喜稱形式語言學)不從功能入手, 它只能是結構語言學,盡管它研究的“結構”可能是高度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形式;所以我把它歸入解釋性結構語言學(新派),以便與其先行者描寫性結構語言學(舊派)相區別。喬氏以數學和邏輯學為指導改造語言學,其勇于創新的精神是可嘉的,其學說對語言學的領先地位也有貢獻。但他標榜其說為“笛卡爾語言學”,卻未必討好;笛卡爾再偉大,其哲學在今天也已風光不再。又:喬氏曾認為語言學是心理學的分支(他說其學是認知性研究;但那多停留在口頭上),現在他又要搞生物語言學了。我在外研社《語言學教程》第二版(2014) 導讀里肯定了他的生物學方向探索是有價值的;但同時也指出那不可能是語言學的主要方向。總之不管怎樣,語言學自身都不會變成一門技術科學(或自然科學,呂師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序言中早就下了這一結論)。
我在最近10年為一些友生之書所作的序言以及商務印刷館《語言學概論》(第二版)譯校后記和外研社《語言學教程》(第二版)導讀里,也明確地提及語言學研究之三條路線和四種旨趣(描寫、比較、解釋、計算)的觀點。我還對語用學、語篇學(text-linguistics)、語風學(stylistics)、社會語言學、國際語學(interlinguistics)等學科進行不懈的探索。在語用學里我提出過“規避準則”和“最大信息[量]原則”;我提出了區分語用學和社會語言學的一個標準;我還提倡發展中國傳統的辭章學(textology),用語篇學來增強辭章學的理論色彩、又用辭章學來拓寬語篇學的范圍和提升其品位。我也從術語學的高度來看待術語及其翻譯問題,對一系列術語提出了改進的建議(周流溪2015 b:14,2017)。就術語使用而言,伍先生也是我們的榜樣。比如他把雅柯布遜的書Kindersprache,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英文譯名Child Language,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細心而準確地譯為《兒童語言、失語癥和語音普遍現象》,而非《兒童語言、失語癥和音系的普遍特征》,就很難得;誤譯是源于一看見phonological便以為一定指“音系的”(其實這是后起的詞義)。伍先生還糾正了不少人把genealogy(譜系學)譯為“發生學”的不當做法。至于有人連German(德國的、德語[Deutsch])和Germanic(日耳曼的germanische)這樣起碼的區分都不懂而動輒混淆,他就要嚴厲批評了(伍鐵平2010:262,260,358)。
我認識到:要從總體上提高學習語言理論的自覺性并打好扎實的基礎,必須從史、論、法三方面下功夫。所以我規定博士生要在其選題的閱讀范圍之外在史、論、法方面各讀10部書(大都是他們不愛讀的),書單中就有柯杜霍夫的《普通語言學》。也有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該書的長處是全面兼顧,既有歷史比較語言學史又有普通語言學史,還包含了中國語言學史的內容。一個學生如果不耐心強啃幾本自己不愿意讀而卻又非讀不可的書,總難以避免偏狹的毛病。我一直鼓勵學生以積極主動的心態和兼容并包的精神來學習新的知識。
四
伍先生從1980年在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開始曾多次宣揚并發揮國外幾位學者的一個觀點: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所謂領先,是指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經常處于領先地位(現今對自然科學某些部門也有影響,并催生了語言學與多種學科交叉的研究)。伍先生長期研究語言學基本理論和語言學史;他來倡導這一高屋建瓴的觀點正當其宜,而這對很多語言學工作者在各地方開展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伍先生的《語言與思維關系新探》在學術界也引起很大反響,是國內比較全面地論述思維和語言關系問題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伍先生還寫了一文,論“從語言學的領先地位談到它在方法論上對哲學研究的意義”(《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8/3,后收入上引書的增訂本)。]
八十、九十年代不少學者也開始關注這類問題尤其是語言哲學問題。許國璋先生就很注意闡發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中的哲學眼光,因為許先生從青年時代就受到哲學家(如金岳霖和外國哲人)的思想熏陶。他還有專文探討《馬氏文通》和《說文解字》里的語言哲學。我本人對中外哲學都有興趣。我在《易經》和《老子》研究中都已有自己的心得。但伍先生的上述著作,直接推動著我從哲學的角度來審視新興的認知語言學,寫成“認知語言學使語言學繼續成為領先學科”一文(周流溪2005)。該文指出: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體驗主義(experientialism,又稱embodied realism)。那就是說,人對世界的認識從身體經驗開始,并且把這種認識用語言表現出來(即體現在語言之中)。Embodied realism“體現性實在論”或稱embodied philosophy,宜稱為philosophy of embodiment(體現[性]哲學)。謹按:embodied/embodiment曾經被譯為“體驗[的]/體驗[性]”。然今謂不妨遵從該二詞的通常意義改譯為“體現……”,此‘體’循其本義,即仍解釋為身體的‘體’;“體現”是身體經驗的理性表現或表征,它與experientialism乃一物二面:experientialism是從主觀上說,embodiment是從客觀上說。 這種認識[論]帶有經驗主義的基礎,但不是簡單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當然那也不是先驗主義(apriorism)或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體驗主義是把客觀對象和主觀感知結合在一起的,人必然在體驗的基礎上進行思辨和抽象;換言之,人首先認識自己的身體,然后由此出發去認識其他事物。以此觀點回頭來看以《易經》和《老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那也是體驗主義(體現哲學)。經驗主義是機械唯物論,先驗主義是唯心論;體驗主義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人對世界的認識,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性。認知語言學對語言的擬象性(iconicity)、隱喻(乃至廣泛的比喻或“類喻/ figurative analogy”[周流溪2001a: 319])、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等方面尤其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透徹解釋。以認知語言學和體現哲學來觀照中國傳統文化,很多現象也已獲得了可信的合理解釋。
體驗主義的認知觀和心理語言學緊密相關。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心理語言學家施坦伯格(Danny Steinberg)來北京師大訪問,對心理、中文、外語專業師生演講《語言學的認知方面與心理語言學》,由我擔任翻譯。其講座的要點我已譯為中文,載于我的論文集(周流溪 2001a: 183-188)。以1987年雷柯夫(G. Lakoff)和約翰遜(M. Johnson)的認知語義學以及郎厄科(R.W. Langacker)的認知語法學為代表而崛起的認知語言學,建立在認知心理學的基礎上(也可以說,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都是認知科學群的分支學科)。這與喬姆斯基以“笛卡爾語言學”為標榜的那種“認知”研究大不一樣。雷柯夫提出“要糾正兩千年來我們關于心智的錯誤觀點”(包括喬氏唯理主義/rationalism 和客觀主義/objectivism)。我很贊同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念。我招收的首批兩名博士生(1997-2000)就研究認知語言學:一位研究認知語用學,另一位研究語法化。我指導博士生、碩士生的基本方針是“弟子各從其志”;我容許和鼓勵他們依照自己的意愿去選題,只在個別情況下加以調控。后面還有很多博士生研究認知與隱喻、轉喻、仿擬、關聯、推理、語篇、語言習得等方面;也有一些碩士生研究與認知有關的問題。我自己也探討英語認知語法,是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英漢對比來做的;此外我也關注認知語篇學、認知詩學。當然我宣傳認知語言學也不走極端,我不像一些同志那樣漫天談認知語言學(包括過度闡發擬象性),好像語言學只能是認知語言學。
五
現代語言學成為領先科學,索緒爾有很大功勞。伍先生不同意徐德江“胡批索緒爾”,他也指出過高名凱在翻譯索緒爾《教程》中的失誤。我并體會到:對索緒爾的思想既不能漠視,又需要仔細研究。在這方面許國璋先生也是我們的榜樣。其“論索緒爾的突破精神”、“關于索緒爾的兩本書”(1983,從兩本書看索緒爾的語言哲學)、“布龍菲爾德和索緒爾”諸文都能發前人所未發之見。上述關于索緒爾的兩本書是“索緒爾研究”版本校勘的成果。我們在學習和研討中無疑必須求助于它們,但我們更需要一個不同于《教程》初版的、能更好地展現索緒爾思想的版本;那就是其第三次開課的講稿,現在有法英雙語對照本《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第三教程》(Pergamon Press,1993)。可惜至今很多人還沒有依靠和利用這個版本。
我有“索緒爾的辯證語言觀新探”一文,即重點依據索緒爾研究版本校勘的成果和第三教程。我還注意到雅柯布遜的觀點(見“談語言研究和文學研究的結合——語言學巨匠雅柯布遜的治學一瞥”)。有人曾譏評我現在還講索緒爾;其實他是錯誤地采取了一種漠視前人的態度。我們當然不能止步于索緒爾的學說;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還沒有真正領會其著作的真諦,而且有些基本概念由于種種原因還在被不準確地使用著。那都不得不辨。在上述“新探”和“一瞥”二文(分載于周流溪2001a、周流溪2001b兩部論文集,也曾先后在雜志發表)我指出:《教程》確為語言學成為獨立學科做出了貢獻;但其舊版結尾所標榜的“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卻不是索緒爾的原話——此話太極端,他其實說過“語言”研究和“話言”研究都屬于“言語科學”(sciences du langage)。我確認索緒爾對人類語言持有三分觀點(langage言語、langue語言、parole話言)而非學界以往認定的二分觀點(langue語言、parole‘言語’)。索緒爾精辟地論述過語言符號的二重性,即signifiant~signifié(高名凱譯為‘能指~所指’)。這個說法(包括漢譯名)長期被視為圭臬;其實它易孳歧解,甚至造成很大的流弊(還波及其他學科)。這種符號二重性沒有包括符號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我們不妨這樣理解:索緒爾應該知道有那種關系,不過他只著重論述語言符號本身的二重性而無暇兼顧那另一個方面了。但符號的三重性畢竟是不能忽略的,那第三個方面(即符號所指向的客體,不管是現實世界、可能世界還是虛擬世界里的事物)可以用拉丁詞denotatum來表示。依據雅柯布遜的闡釋,我們必須在談索緒爾語言符號觀點時采用三分術 語 (signifiant施 指 ~ signifié受 指 ~ denotatum 所指)。這里三個漢譯名是我確定當用的。“所指”按一般人的漢語語感,應該是符號所指向的事物(英語名referent),而非符號的意義(sense)即其表示的概念(或曰符號的“指稱”reference)——但這恰是索緒爾二分術語的另一面。高譯‘所指’本當謂reference,卻容易被理解為referent!再說,碰到真要表示referent的場合卻又沒有一個合用的術語和譯名。[注意:不應把英語詞reference理解為符號所指向的事物(那應該是referent)。] 故我們不宜繼續使用含糊而不敷應對的、又容易造成誤導的高氏舊譯名了。容我再說一遍:符號本身(形音統一體)是signifiant“施指”(英語名signifier),它指向某個概念(具有某種意義);符號攜帶著的該概念(或意義)是signifié“受指”(英語名signified);而此概念(或意義)所體現于其中的、即符號所指向的事物才是符號的“所指”denotatum(英語名referent)。其實,西方自古就有人探討符號(詞)~ 意義 ~ 事物之間的關系;近的說來,美國人皮爾斯(Peirce)、奧格登和理查德(Ogden &Richards)、莫里斯(Morris)都比較明確地提出符號學和語義學(韓禮德合稱“意義學”semiotic [參看周流溪2017: 7])的三分術語,后兩家的名稱一家用的是symbol符號 ~ thought or reference思想、指稱 ~ referent所指,另一家用的是sign [vehicle]符號[載體] ~ significatum意義 ~ denotatum所指。這樣看,三分術語是很清楚、很合用的了。
雅柯布遜還注意到語言的美學功能(poetic/aesthetic function)。我很重視他這種見解,并大力弘揚之。經過反復比較諸家在語言功能上的觀點,我形成這樣的看法:在語言的眾多功能中我們只要抓住三個基本功能(交際功能、認知功能、美學功能)就掌握了全局。這又是我關于語言的基本觀點之一。它已經被采納而寫進了《普通語言學概要》第三版(伍鐵平、王慶2014)。我直接從事詩歌創作和翻譯數十年,對語言的美學功能有深刻的體會。所以我不僅在理論上認識這一點,在實踐中更力圖使自己的作品發揮應有的美學功能。
伍先生是很勤快的人;“文革”中他在干校勞動時還努力學習外語,也注意閱讀德文版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披覽各種文本的《國際歌》并了解其作者鮑狄埃的生平。這使他能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出版了《漢法德俄英西文對照“國際歌”(注釋和研究)》一書。我從中受惠不少。我覺得《國際歌》已有的英美人譯文不夠完美,就大膽把此歌細按法語原文重新譯為英語(就中我參照伍先生的研究而準確譯出了歌中表達的思想:不能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資產階級政客,無產階級需要建立自己的政黨)。我雖然并不掌握法語,但仍然有信心通過縝密的校勘拿出更好的英譯文。而且我也順手就將法語的《馬賽曲》重新譯為英語。我自信這兩首歌的新譯都更準確也更優美(包括合樂方面)。那么伍先生指出了《國際歌》各種譯文的優劣,而我提供了新譯可說是在其研究基礎上把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或者說,他做了研究工作而我將那研究成果付諸實際應用了);總之,這是一個后學繼承和取法前輩而應有的作為。(這兩首歌的配曲新譯載于周流溪主編《中國中學英語教育百科全書》。)
1974年國家為出版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向全國外語專家征求意見的時候,我在廣州(當中學教師)從暨南大學詩友處得見其稿本。拜讀之下,我發現譯文中有很多不足,我也不能認同其散文化譯法。所以此書出版后,我在很艱苦的環境下(當時既有一般課堂教學,又經常帶學生到農村分校種地)還是不揣冒昧動手重譯毛澤東詩詞;但只譯了10首詞(收錄于《流溪詩外編》,華人出版社2002)。有些詞我按照英詩韻律去譯,有些詞我就摹仿唐宋詞的格律去譯。幾年后我學習和掌握了世界語,也用它來譯詩寫詩(比如重譯了德國海涅的《孤松》,也譯了《義勇軍進行曲》和楚辭的很多篇章),直至最后參與了“中國風”的創作活動(在詩作中以一個世界語音節對應一個漢字、幾乎100%復制唐宋詞牌的格律)。有了這方面的實踐經驗,再回頭來看毛澤東詩詞的英譯,我更加強了決心和信心要把它譯為盡量完美的詩體文本。近年得到一個機會,我就把毛澤東 40 題 43 首詩詞都譯為漢英合璧的格律詩(韻式全依原作,詩行內的平仄節奏則換成英詩各種音步的正規格律)。詩的部分發表于《當代外語研究》(2016/4);詞的部分次年載于同刊第 5期。前文訂補稿轉載于2017 年暨南大學《外語論叢》。后文訂補稿將待機轉載。在這一特殊領域我攀上了中外毛詩譯者都未曾涉足的險峰。重譯毛澤東詩詞的心愿已償,但可嘆的是 40 年一晃就過去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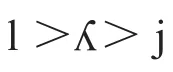
伍先生認識丹麥語言學家維爾弗里德·舒馬赫(W. Wilfried Schuhmacher),也介紹他和我認識;我后來從他那里獲得了一些難得的資料。1999年舒馬赫來我校訪問時我們邀請他到外語系作報告介紹丹麥的語言學研究概況。我寫成“國小未必等閑看——略談丹麥的語言學”(《俄羅斯文藝》 2002年北京師范大學百年校慶外語系學術論文集;又題為“略談丹麥的語言學研究”載于《外語與翻譯》2002/3)。其實,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能把普通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兼而治之卓有建樹,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至于維爾弗里德·舒馬赫,我曾有專文介紹他的學術觀點(周流溪2001b: 278-281),其中談及他的論文“瑪雅語的 na’與美洲人之定居”——它指出由瑪雅語的 na’(智利復活節島的一種印第安語言之 na’a 是其同源詞)與波利尼西亞所羅門群島一個語言的 na’a 及其詞族相通、可以推想是巴布亞人2000年前橫渡太平洋把這個詞帶到美洲(1992年他與人合著的《南島語言和巴布亞語言的歷史》已在尋找證據)。我覺得其言有理,還補充道:幾年前我看到一條短訊說太平洋島嶼上的人在上萬年前就橫渡大洋去到美洲了;我認為在人類進化史上時間因素比空間因素更重要,在漫長的時間跨度內什么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做成的。(舒馬赫還有學術批評集《赤子語言學家》,他自己有反抗社會流俗的赤子之心,時時捍衛學術尊嚴;他也支持伍鐵平先生的打假斗爭。)
七
伍鐵平先生認識德國學者庫爾馬斯(Florian Coulmas),也希望我介紹庫氏的文字學著作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他請庫氏把書寄給我,我讀后便寫成“《世界的文字》評介”一文(《語文建設》1990/3[周流溪2001a: 150-152])。我指出:“本書的最大特色是它的語言學觀點。作者哀嘆現代語言學導論教科書把文字放到最后一章甚至附錄中。這些書不承認沒有文字就根本不可能有語言學。作者認為,文字絕不只是語言的外衣,更不能說只有剝掉這層外衣才能著手研究語言。”此書論述了文字有六大功能,它擴大了語言的表達能力。文字可能分別在詞、詞素、音節、音位幾級單位上映現語言。但“文字單位和語言單位并非完全是一對一的關系。某種文字應該以傳達什么信息為佳,是由其使用者決定的。”
1990年前后有個青年人“發明”了用漢字“六書”解釋英語拼音文字之法,不止一次試圖拉攏伍先生和我為他作鑒定和捧場;那自然被我們拒絕了,因為他的“發明”里沒有任何詞源學根據,純屬亂猜胡說。他想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書沒有成功,倒是中國世界語出版社給他出了。還有報紙、電視臺輕率報道胡亂吹捧他的偽科學。這都是那些單位的奇恥大辱(另請參看伍鐵平2004: 26-28)。
伍先生在批評《漢字文化》引“俗詞源學”為安子介破解 (cracking) 漢字之謎的所謂“俗形義學”(實為亂拆亂講)辯解時詳細指出:語言學中根本不存在“俗詞源學”這樣一個學科。我國個別譯著如《語言與語言學詞典》將folk etymology譯為“俗詞源學”是不對的;那指的是一種現象,應譯為“流俗詞源”。它又叫false etymology(偽詞源)。[見伍鐵平1997:363-364。——其實,我們在帕默爾《語言學概論》第一版也曾使用了不當的譯名“通俗詞源學”;在第二版里已經改正為“流俗詞源”。]
德里達說:“漢字破壞了西方的整個哲學系統和基本范疇。”這言過其實。(當然我們不是否認德里達的一切觀點,對于非語言專業的語言文字研究我們還是要冷靜審察、取其可取之處。但像這句話,如果把它奉為圭臬則肯定要出問題。哲學界對此自有公斷。)我上文說過漢字的造字原理有體驗主義的依據;但漢字并不能完全表現體驗主義,而且體驗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也不是唯一正確的和萬能的(《易經》和《老子》的體驗主義后來就都被人參用外來的、思辨性更高的佛教哲學而重新闡釋并加以發展,形成玄學、理學等流派)。所以若抓住德里達這句話就把漢字神化、認為 21世紀是漢字發揮威力而使西方文化讓位于東方文化的世紀,那就是盲目樂觀的意見、甚至是文化沙文主義了。
我們應該尊重中國傳統語文學,但也不能說過頭話,比如說:“《爾雅》成書時,西方人還在草昧階段。”[伍評:]當時希臘已出現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伍鐵平2010:276)。周按:所謂“西方”常常不免要包括“西天”(印度,歷史上長期主要是印歐民族統治的松散國家);我們必須知道印度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經出現耶斯迦(Yāska)所著的《尼祿多》(Nirukta),而該書之作是為了解釋一部更古的書《尼犍豆》(Nighantu)。《尼祿多》已經比《爾雅》古老,更別說《尼犍豆》了。還要注意:《爾雅》或托名周公所作、或云經孔子增益,那都不靠譜;它成書應在戰國到秦漢之間。《尼祿多》是有明確作者的(耶斯迦生活在相當于子思即孔子之孫那個時代),而且它比《爾雅》具有更高深的解釋結構——因為它提供的是詞源解釋。中國到東漢劉熙的《釋名》才出現詞源著作。當然對《說文》、《釋名》等書里的詞源解釋也要細心研究,甄別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又不為那些不可靠的說法所誤導。在這方面,比較詞源學有一定的作用。伍先生說到:他發現俄語的бес(鬼)和бояться(害怕)是同源詞而與漢語“鬼”和“畏”也是同源詞竟不謀而合,感到十分興奮,于是萌生了做比較詞源學研究的想法。我用體驗主義分析漢語顏色詞時也發現了一個問題。《說文》云:“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段注:俗言信若丹青;謂其相生之理有必然也。援此以說從生丹之意。)但是要說顏色和“信”有關,那是扯不到一塊的。現在有人則說:植物萌芽時下部本是紅色,長出來后則變為綠色。這樣企圖把丹和青的關系說圓,也太勉強。我指出:“關鍵在于‘從生丹’的丹字沒有說準。丹,古字寫成井字形。按傳統說法,那是因為井出丹砂。這沒有根據。實際上‘井’不是義符,是聲符。‘井’,切韻在清韻,上古音與‘青’字同韻;因而‘井’可以作‘青’的聲符。這樣,青字的準確解釋是:從生井;青,生也,草木生長之色也。比較一下英語詞 grow(生長)和 green(青綠):可巧 grow和green 這兩個詞也是同源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見我們的新解從認知的觀點來看是能成立的。”(詳見周流溪 2005。)
為了弄懂聲明學,我花了約10年來研讀[和注釋]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西方學法”一章以及參閱中外學者的有關著作。通過多年學習語言哲學和西方哲學(包括“西天”哲學),我在《西方哲學史歌》希臘哲學的多處注解(周流溪2007:80-82, 90-92, 94-97)及補注(“Logos與律格”和“西洋與‘西天’”[同前: 158-170])中,初步探討了logos和ontologia (=英語ontology)的問題。后來又寫成論文“Ontology 及其中譯名探討”(《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1)和“淺談古印度的語言哲學思想”(《外語學刊》2015/5)發表。我尤其試圖參與解決中西哲學家長期探索和爭論的問題:ontology的真義。通過比較中外幾個主要的語言,我挖掘出漢語的潛力,把ontology譯為“諟論”并做了解釋。我認為漢語同族詞“是、諟、寔”足以包涵外語(首先是希臘語,那是此論所從出的語言)環繞著ontology的由一個詞(on[t])之各種形態變化所表示的多重意義(周流溪2015a)。
* * *
我們中國學者應該學習外國一切有用的東西,但也應該自尊、自信、自強。我在外研社《語言學教程》第二版導讀里說到:“語言學概論可以有各種寫法。中國學者編寫的一些語言學概論(有些書名曰普通語言學綱要),能集蘇俄語言學、歐洲語言學和美國語言學之所長,甚至能結合中國傳統語言學,所以對基本知識和主要觀點的敘述一般比較全面而不太偏頗(今按:我這樣說,就有肯定像伍鐵平主編的《普通語言學概要》那樣的書之用意);總體說來,中國學者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只需不斷完善自己的工作。”北京師大的學者們為捍衛漢語語言文字的尊嚴、堅持研究的科學性,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們也和國內學界的很多同人在戰斗中結成了同盟軍。在這條戰線上,我們還任重而道遠。我們要積極參與國家的語言文字工作,也要隨時識別各種似是而非的觀點,為提高廣大群眾的認識、為教育青年一代多做普及性的宣傳。在這些事業中我們都要學習和發揚伍鐵平先生的精神,他是一位既有良知、又有真知的學者。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的復興。我們從事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外語研究以及各人文學科研究的學人們要以天下為己任,在科研和教學中努力做出新的成績,為振興中華而獻身,為弘揚中國文化并參與國際新文化的構建而不斷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