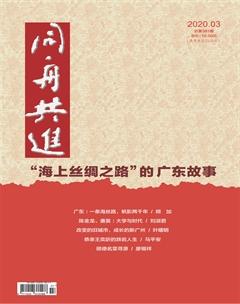外國人眼中的唐朝廣州
郭曄旻

“廣府是一個(gè)大城市,位于一條大河的岸上,這條大河是流入中國海的。城與海之間,相距六七日的途程。從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島和其他國家的船只,載運(yùn)各種商品開進(jìn)這條大河,一直開到廣府附近。廣府城人煙稠密,僅僅統(tǒng)計(jì)伊斯蘭教人、基督教人、猶太教人和火襖教人就有二十萬人。”
——阿拉伯歷史與地理學(xué)家麥斯俄迭
從巴士拉到廣州
公元八九世紀(jì),正是西方歷史上的中世紀(jì)。那時(shí)的西歐國家正處于“黑暗時(shí)期”,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也沒有一座像樣的城市。天主教會的神學(xué)是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觸犯了教會的教條,不是被燒死就是被砍頭。就在這時(shí),文明的花朵燦爛地開放在東方大地上。中國的唐朝與阿拉伯的哈里發(fā)國家,是當(dāng)之無愧的兩個(gè)中古文明高峰。
將這兩大帝國連結(jié)起來的,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哈里發(fā)朝廷在商路上為客商設(shè)置了宿舍和驛站,開掘了水井,設(shè)立換馬站,引得無數(shù)商隊(duì)涌向東方。僅根據(jù)漢文史料的記載,從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798年(貞元十四年),先后來到長安的阿拉伯帝國(大食)使節(jié)就有39批。在怛羅斯戰(zhàn)役(751)后被俘,流離阿拉伯帝國12年的杜環(huán)在他的《經(jīng)行記》里記載,當(dāng)時(shí)中國的綾絹機(jī)杼已經(jīng)通過“絲綢之路”流入阿拉伯帝國。
可惜一場“漁陽鼙鼓動(dòng)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亂(755-763)”結(jié)束了“陸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時(shí)代。唐朝的軍政勢力退出了西域,使得“絲綢之路”陷于“道路梗絕、網(wǎng)絡(luò)不通”的困境,就連詩人杜甫也發(fā)出了“乘槎消息斷,無處覓張騫”的哀嘆。
公元762年,杜環(huán)終于得以乘坐商船從阿拉伯半島啟程,回到廣州。他從“陸上絲綢之路”進(jìn)入阿拉伯半島,卻從海路返回故國,恰是極富象征意義的舉動(dòng):“陸上絲綢之路”在這一時(shí)期固然盛極而衰,但東西方的聯(lián)系并未因此中斷——未來屬于海上。更值得玩味的是,同時(shí)期的阿拉伯帝國哈里發(fā)曼蘇爾選中原本籍籍無名的村落巴格達(dá)(今伊拉克首都)作為京城的理由之一,就是“這里有底格里斯河,已經(jīng)把我們同遙遠(yuǎn)的中國聯(lián)系起來”。
當(dāng)時(shí)的巴格達(dá)在底格里斯河的碼頭長達(dá)數(shù)英里,停泊船只成千上萬,有巨艦,有游艇、木筏、牛皮舟,還有中國帆船。“市場上有從中國運(yùn)來的瓷器、絲綢和麝香……城里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至于地處巴格達(dá)以南,底格里斯河與幼發(fā)拉底河交匯處附近的巴士拉,更是因成為大批中國貨物上溯美索不達(dá)米亞平原的中轉(zhuǎn)站而被阿拉伯史家稱為“中國商港”。這與巴士拉因河網(wǎng)密布被日后的西方人稱為“東方的威尼斯”真是相映成趣。作為中世紀(jì)美索不達(dá)米亞平原的主要出海口(但因地理變遷海岸線淤塞外推現(xiàn)已遠(yuǎn)離波斯灣),《一千零一夜》中充滿了有關(guān)巴士拉的故事,辛巴達(dá)就是從巴士拉出發(fā)周游世界的。
當(dāng)然,巴士拉與中國之間遠(yuǎn)隔萬水千山,海路往來談何容易。好在唐代中國的造船能力可以說是傲視世界,造船工場遍布各地,僅揚(yáng)子(今江蘇儀征)一地就有造船場10所。唐代的中國商船大者可載600人至700人,載重萬石。其船舶之龐大、堅(jiān)固以及運(yùn)輸量之多,都是當(dāng)時(shí)的洋船無可比擬的。時(shí)人盛贊,“只有龐大堅(jiān)固的中國海船,才能抵御波斯灣的驚濤駭浪,而暢行無阻”。法國學(xué)者J·索瓦杰因此就說,“波斯灣的商人乘坐中國人的大船才完成他們頭幾次越過中國南海的航行”。
因此,在《漢書》里,中國商船航行到今天的印度“苦逢風(fēng)波溺死,不者數(shù)年來還”的悲慘記載已經(jīng)成為陳跡。成書于8世紀(jì)末的《廣州通海夷道》詳細(xì)記錄了商人們利用中國造的海船從廣州啟航,穿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海岸西上,再沿海岸線西行至波斯灣,航行到波斯灣的盡頭,全程最短時(shí)間僅僅只需驚人的89天。無獨(dú)有偶。阿拉伯地理學(xué)家伊本·胡爾達(dá)茲比赫(約825-912)在《道里邦國志》里也記載了從阿拉伯到中國的海路交通,即從巴士拉出發(fā)沿波斯海岸航行,途經(jīng)印度境內(nèi)各口岸,途徑南海到達(dá)廣州。阿拉伯人商人“穿過‘中國之門,向著漲海前進(jìn)”,“船只通過中國之門后,便進(jìn)入一個(gè)江口,在中國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該地拋錨,此處即中國城市(廣州)”。
長達(dá)萬里的古代海上航行主要借助季風(fēng)。阿拉伯商船“于9月從波斯或美索不達(dá)米亞出發(fā),駛?cè)牒常竽鏂|北季風(fēng)行使到達(dá)印度南端。然后順西南季風(fēng),于12月到達(dá)孟加拉灣。接著利用南中國海的南風(fēng)于次年4月至5月到達(dá)中國廣東。進(jìn)入秋季后,他們借助北風(fēng)離開,趕上印度洋的東北季風(fēng),并于來年4月至5月回到波斯灣。1980年阿曼蘇丹曾卡布斯倡議并資助了一艘仿古雙桅三帆船,由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直航東方大港廣州的考察巡游活動(dòng)。該船以阿曼古都“蘇哈爾”命名,不裝備現(xiàn)代動(dòng)力設(shè)備和科學(xué)儀器,僅憑借季風(fēng)鼓動(dòng)風(fēng)帆、羅盤針、牽星術(shù)以定方位航程。當(dāng)年11月23日,“蘇哈爾號”帆船從馬斯喀特啟航,沿著唐代海上航線駛向中國,途經(jīng)中外歷史文獻(xiàn)記載的多個(gè)海域,總航程6000英里,歷時(shí)216天,于1981年7月1日順利進(jìn)入珠江口,停靠在廣州的洲頭咀碼頭。這一壯舉,無疑更加證實(shí)古代阿拉伯世界與中國的“海上絲路”交通的真實(shí)存在。
商人們的“廣州夢”
在唐代的阿拉伯商人眼中,“廣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貨物和中國貨物的集散地”。為什么他們會選擇廣州而非其他中國城市呢?這是因?yàn)椋?dāng)時(shí)的廣州稱得上是唐朝海外貿(mào)易方面當(dāng)仁不讓的橋頭堡。
廣州城瀕臨南海,上接西江、北江、東江,三江由此匯入珠江,再流入南海。考慮到在古代,水運(yùn)是唯一具有經(jīng)濟(jì)效益(運(yùn)量大、運(yùn)費(fèi)低)的貨物運(yùn)輸方式,作為海運(yùn)和河運(yùn)的交通樞紐,廣州的地理?xiàng)l件可謂得天獨(dú)厚。另一方面,大庾嶺因其地勢險(xiǎn)要、環(huán)境惡劣,一度成為南嶺南北交通的障礙。公元716年,“大庾嶺新道”的開通更加改善了廣州的陸上交通條件,打通了中原與嶺南交通的咽喉。從此之后,從廣州出發(fā),從北江經(jīng)過嶺南重鎮(zhèn)韶州(韶關(guān)),再越過大庾嶺,進(jìn)入江西境內(nèi),經(jīng)贛江水系輾轉(zhuǎn)到達(dá)當(dāng)時(shí)大運(yùn)河中心——揚(yáng)州,再經(jīng)由大運(yùn)河便能到達(dá)大唐東都洛陽。這樣一來,唐代中國的心臟地帶就成了廣州港的經(jīng)濟(jì)腹地。比如一位生活在9世紀(jì)的阿拉伯人曾說,“中國最好的麝香來自廣府”。可見,本地其實(shí)并不出產(chǎn)麝香的廣州,卻成了麝香的最主要的集散和輸出地。
交通上的優(yōu)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唐朝政府對廣州海外貿(mào)易的鼓勵(lì)態(tài)度。當(dāng)看到“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船,以珍貨與中國交市”的盛況之后,唐朝政府在廣州首次設(shè)立了市舶使,掌管海上往來的船舶貿(mào)易、接待蕃客和征稅。唐政府對外國商人之來貿(mào)易,只要是按規(guī)定依數(shù)交付價(jià)值(貨稅),和官市(官買)之后,就任百姓貿(mào)易(私人經(jīng)營買賣)不加干涉。對此,公元9世紀(jì)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佐證,“海員從海上來到他們的國土,中國人便把商品存入貨棧,保管六個(gè)月,直到最后一艘海商到達(dá)為止。他們提取十分之三的貨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還商人”。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對外國商人進(jìn)行敲詐,唐朝中央政府還三令五申,禁止對他們?yōu)E征各種雜稅。上面提到的蘇萊曼還曾記載了這樣一個(gè)故事:有個(gè)呼羅珊(今伊朗東北部一帶)的商人,在伊拉克采購了大批貨物來到廣州交易,與唐朝宦官發(fā)生了一場糾紛。宦官也就是俗稱的“太監(jiān)”,其職責(zé)原本是在宮中服侍皇帝。但從開元年間以后,宦官經(jīng)常被派到各地充任監(jiān)軍,其中在廣州任職者又往往兼任市舶使,稱得上是權(quán)勢熏天。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貨品的交易上,那位呼羅珊商人與宦官發(fā)生了爭執(zhí)。商人拒不出賣,宦官竟采取強(qiáng)制手段,把商人帶來的好貨拿走了。誰知那位倔強(qiáng)的商人并不罷休,悄悄地從廣府起程,花了兩個(gè)多月光景,來到長安告狀。按蘇萊曼的說法,此時(shí),如果呼羅珊商人取消控告,要被罰五十大板,再遣送回廣州;如果堅(jiān)持上訴,就要直接面君,并相應(yīng)承擔(dān)掉腦袋的風(fēng)險(xiǎn)。呼羅珊商人選擇了后者,于是他被押到皇帝面前。好在經(jīng)過調(diào)查,皇帝證實(shí)呼羅珊商人所講屬實(shí),于是那個(gè)貪婪的宦官被召回,免去職務(wù),沒收財(cái)產(chǎn),并派去管理墓地。
這樣的公正處理不能不讓蘇萊曼感嘆,“往時(shí)中國在行政上的卓著成效”以及“中國人打心底里尊重法制”,自然也使得唐代的廣州成為海外商人趨之若鶩的地方。當(dāng)時(shí)的另一個(gè)外國人,日本文豪真人元開在公元779年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中就描述了當(dāng)時(shí)廣州市舶貿(mào)易的繁榮景象:“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shù)。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阿拉伯、波斯商人遠(yuǎn)涉重洋來到廣州,當(dāng)然是因?yàn)榭梢詮馁Q(mào)易中獲得大利。公元903年,阿拉伯地理學(xué)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中就將中國絲、中國瓷器和中國燈列為三大名牌產(chǎn)品。阿拉伯人不惜一切代價(jià)訂購中國精美的瓷器,或陳列于皇宮,或裝飾于清真寺等建筑上。公元10世紀(jì)的忽魯謨斯(今伊朗霍爾木茲)商人本·沙赫里耶則在《印度珍聞集》里記述了這么一則軼事:一位白手起家的猶太商人到中國做買賣,公元913年自廣州從海路攜帶大量中國絲綢和瓷器而回,發(fā)了一筆橫財(cái)。他將一件精致的中國青瓷壺獻(xiàn)給了阿曼城的統(tǒng)治者,從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盡管他是一個(gè)猶太“異教徒”。其影響所及,直到中世紀(jì)后期,著名的波斯詩人薩第(1208-1291)在《薔薇園(Gulistan)》一書里,還曾記載了一個(gè)巴格達(dá)商人向作者傾訴他的計(jì)劃,“我準(zhǔn)備把波斯的硫磺運(yùn)到中國去賣,據(jù)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價(jià),然后我再把中國的陶器運(yùn)到希臘……回到波斯。此后,我將放棄國外貿(mào)易而退居于一所大商店里”。毫無疑問,這就是當(dāng)時(shí)阿拉伯、波斯商人心中的“廣州夢”。
“阿拉伯商人薈萃之地”
每年春夏之交,唐代的外商借著東南信風(fēng),從西亞、非洲運(yùn)來了珍珠、象牙、犀角及香料等商品,在廣州叫賣,同時(shí)又購得瓷器、絲織物、紙、鐵器、金銀等回頭貨,在廣州度過一個(gè)炎熱的夏季,等到秋冬時(shí)分,乘著東北風(fēng)離開廣州。
如此眾多的中東商人來到廣州,展現(xiàn)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gè)高度發(fā)達(dá)的文明。阿拉伯商人因此很容易發(fā)現(xiàn),唐代廣州是嶺南地區(qū)無可爭議的中心城市。“廣府是個(gè)港口,船只在那里停泊,另有其他近二十個(gè)城市歸于廣府管轄。”盡管它不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但繁榮的貿(mào)易帶來了滾滾財(cái)源,“納入國庫的錢每天可達(dá)五萬迪納爾”。
唐朝的廣州已經(jīng)居住著幾十萬居民,他們“無論貴賤,無論冬夏,都穿絲綢”的習(xí)慣讓阿拉伯商人大為震驚。那些在西方身價(jià)百倍的絲綢,在廣州不過是尋常用品,王公穿上等絲綢,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財(cái)力而衣著不同”。中國絲綢高度精湛的工藝,更是讓這些“老外”目瞪口呆,以至于由衷承認(rèn),“真主創(chuàng)造的人類中,中國人在繪畫、工藝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嫻熟的,沒有任何民族能在這些領(lǐng)域里超過他們”。蘇萊曼記述道,一位阿拉伯富商去拜會廣州城里的宦官。他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長著一粒黑痣,這是透過穿在身上的絲綢衣服看見的。商人推測那宦官至少穿著兩件衣服,里外重疊在一起。結(jié)果卻發(fā)現(xiàn),他竟然穿了五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過這些衣服顯現(xiàn)出來。然而,這甚至不是中國最好的絲綢。起碼,“(廣府)都督穿的絲綢,比這還更精美,更出色”。
廣州的飲食習(xí)慣也給遠(yuǎn)道而來的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蘇萊曼寫道,廣州人的“糧食是大米,有時(shí),也把菜肴放入米飯?jiān)俪浴M豕珎儎t吃上等好面包及各種動(dòng)物的肉”。廣州人“自己用發(fā)酵稻米制成的飲料(米酒)”,而不是西亞流行的葡萄酒。當(dāng)然,蘇萊曼接下來的判斷——“中國人既不知道這種(葡萄)酒,也不喝這種酒”,其實(shí)并不準(zhǔn)確。畢竟王翰早就寫過“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或許這只是因?yàn)槲饔蚴⑿械钠咸丫拼藭r(shí)尚未傳到嶺南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蘇萊曼提到了“泡開水喝的一種干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此前他可能尚未見識過茶葉,因此對茶及唐人飲茶的嗜好還充滿了新奇感。
相比衣食而言,來自海外的商人更關(guān)注的自然是廣州的經(jīng)商環(huán)境。阿拉伯客商驚喜地發(fā)現(xiàn),“在商業(yè)交易上和債務(wù)上,中國人都講公道”。財(cái)務(wù)通過契約文書約定,“放債人和借債人之間總是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盡管他們之間的交易沒有證人,也不需要什么誓言的保證,但哪一方也不會背信棄義”。為了保障外商的財(cái)產(chǎn)安全,朝廷甚至發(fā)放專供他們使用的“過所”,上面注明持有者的姓名和父名、所屬宗族、到達(dá)廣州日期以及隨身攜帶的白銀、物品。“如果出現(xiàn)(物品)丟失,或(其人)在中國去世,人們將知道物品是如何丟失的,并把物品找到交還他,如他去世,便交還給其繼承人。”
所謂“近者悅,遠(yuǎn)者來”。盛唐時(shí)期,法度清明。走南闖北見識頗廣的西亞商人在心中比較了所經(jīng)之地,終于還是得出了順理成章的結(jié)論——“中國更美麗,更令人神往”。于是,海外商人云集唐代廣州,其數(shù)量多至十余萬,乃至在廣州城里形成了外國人居住區(qū)——“蕃坊”。
廣州蕃坊的范圍,大體上包括今廣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東、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帶,以光塔街及其附近為中心。當(dāng)時(shí),珠江江面比現(xiàn)在要遼闊得多,懷圣寺以南還是一片汪洋,適合海舶停靠。各國人都可在此定居經(jīng)商,保持他們的風(fēng)俗習(xí)慣和宗教信仰。來自印度的佛教徒居住在屬于他們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內(nèi)的池塘中還點(diǎn)綴著芬芳的藍(lán)睡蓮。而穆斯林也在這里停留下來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懷圣寺。據(jù)說,它是中國的第一座清真寺,其建立是為了紀(jì)念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先知,因此才得名“懷圣寺”。
這些外國人在廣州的生活受到了地方當(dāng)局的優(yōu)待和尊重。唐廷在法律上有明確規(guī)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就是說,來華貿(mào)易的外商中,如有犯法,在同國人之間(如阿拉伯人與阿拉伯人之間)依本國法律論處;在異國人之間(如阿拉伯人與日本人,或阿拉伯人與中國人之間)則依中國法律論處。在廣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準(zhǔn)許他們自治,按伊斯蘭教的法律行事。廣州蕃坊設(shè)有蕃長或都蕃長,其辦事機(jī)構(gòu)叫蕃坊司。蕃長由蕃坊的外商推選,并經(jīng)唐政府的認(rèn)可,主要職責(zé)是管理蕃坊事務(wù)。此人同時(shí)也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領(lǐng)導(dǎo)和穆斯林間爭議的裁決者。蘇萊曼就此寫道,“在商人云集之地廣州,中國官長委任一位穆斯林,授權(quán)他解決這個(gè)地區(qū)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這是按照中國皇帝的特殊旨意辦的。每逢節(jié)日,總是他帶領(lǐng)全體穆斯林作禱告,宣講教義,并為穆斯林的蘇丹祈禱”。
如此一來,唐代的廣州成為“阿拉伯商人薈萃之地”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當(dāng)時(shí)外國人的心目中,廣州”甚至成為整個(gè)“中國”的代名詞。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里就提到,“支那(Cina)即廣州也,莫訶支那(Mahacina)即京師也”。在梵文里,“Cina”就是“中國”的意思,而“Mahacina”則可意譯為“偉大的中國”。唐代廣州作為海洋貿(mào)易中心的顯赫地位,就此也可窺豹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