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豈可無詩
肖瑞峰
自從高曉松發出“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感嘆后,“詩和遠方”便成為時尚人士經常掛在嘴邊的一種生活指向。盡管將“詩”與“遠方”相并列,未免不恰當地拉大了詩與生活的距離,但把詩定義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卻不失為一種深刻感悟,對崇尚名人金句的萬千粉絲發揮了啟沃作用。而當余秀華以農婦的身份,依循“饑者歌其實,勞者歌其事”的古老定律發為歌吟,在媒體的合力報道下,一夜間成為紅遍大江南北的詩壇新秀后,人們益加覺得詩歌離我們并不遙遠,通過詩歌來暴得大名似乎也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
其實,要像余秀華一樣“以詩名世”,畢竟概率極小,那需要多種機緣促成,是一種不可復制的成功。但把詩歌僅僅視為成名的工具,這本身就是對詩歌的曲解,甚至是褻瀆。詩歌對于人生的意義實不在此,而另有可以縷述者。要言之,詩歌是人生的反光鏡,可以折射人生;詩歌也是人生的教科書,可以指導人生。借助詩歌,我們可以認識人生,體會人生,甚至改變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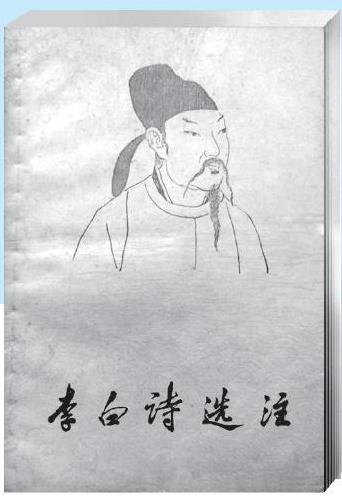
李白像〔明〕王圻《三才圖會》

《李白詩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對于詩歌的功能與作用,孔子曾經做過一個非常精辟的概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管語焉未詳,卻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的路徑和發揮的空間。由此生發開去,我認為詩歌與人生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加以考察。
一、言志與理想
古人說“詩以言志”,首先是說它表達了抱負與志向,就是現在所說的理想。唐代詩人李白便屢屢用詩歌來激勵自己踏平人生坎坷;他以“安社稷、濟蒼生,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為己任,卻因權奸當道而仕途不通、壯志難酬。在《行路難》一詩中他雖然對“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現實處境深致不滿,并感嘆再三:“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但篇末卻以擲地有聲的詩句表達了對理想前途的高度自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仿佛奮力一振,便將滿腹牢騷像灰塵般盡數撣落。當他痛感懷才不遇的厄運已成為不可擺脫的魔咒時,仍然在《將進酒》中不甘沉淪地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
赴京“待詔翰林”期間,他盡管有過“御手調羹、貴妃捧硯”的恩寵,并因此而名滿天下,卻不滿僅僅被當作一介御用文人,公然挑戰“君君臣臣”的封建統治秩序,始終高昂著驕傲的頭顱,乃至被統治者以“賜金放還”的名義驅逐出京。痛定思痛之際,他依舊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的篇末慷慨激昂地表態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執著地保持自己蔑視權貴、追求自由的本色。
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為人生奮斗目標的杜甫,同樣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懈跋涉,不因險阻而卻步,不因挫折而動搖,而詩歌則負荷起為其理想助推的使命。有別于李白對科舉制度的不屑,他期望按部就班地通過科舉考試來步入仕途,一點點向終極的理想目標逼近。但出師不利,首次進軍考場便鎩羽而歸。此時,他沒有沮喪,沒有氣餒,不僅登臨泰山以拓展自己的胸襟,而且吟出了鼓舞后代無數有志青年的勵志詩篇《望岳》:“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其后因權奸李林甫等從中作梗,他又有過兩次科場慘敗的經歷,困居長安十年之久,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屈辱生活。盡管如此,他仍然熱切守望理想,堅信自己的才志終將沖破重重阻力得以伸展。《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歷述人生際遇的種種不堪,分明心有慊慊,但結穴處卻示以掃蕩六合的昂揚姿態:“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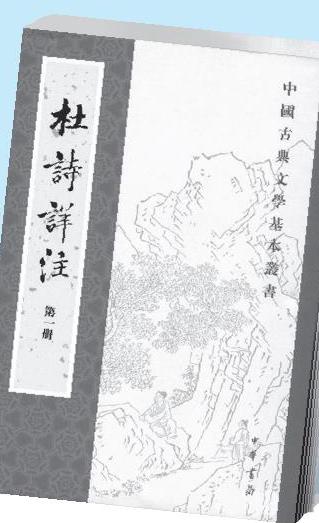
《杜詩詳注》(全八冊)〔清〕仇兆鰲注中華書局 2015 年版
同理,當我們在事業上小有所成而不想故步自封時,讀一讀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或可平添繼續奮進的精神動力。反之,假如我們不幸蒙冤受屈、無可告白時,反復吟誦劉禹錫的《浪淘沙九首》 (其一):“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也許就能積聚起勇氣與力量。詩人對“讒言”報以蔑視,暗示最終被歷史長河中的大浪淘去的將是那些“狂沙”般的進讒者。
二、現實的晴雨表
優秀的詩歌必然感應時代潮汐、折射時代精神,必然融入詩人對社會現實的真切體驗。因此,閱讀詩歌,就是閱讀現實,從中可以感受到現實生活的陰晴風雨,有利于我們把握人生方向,主導生命流程。
將王昌齡的《從軍行》和李益的《受降城外聞笛》這兩首唐人邊塞詩加以比較并讀,我們就可以體會到這一點: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王昌齡《從軍行》)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清照集校注》王仲聞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版
同樣駐守在遠離故鄉、黃沙漫漫的邊關,環境之惡劣、征戰之殘酷毫無二致,但前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內心充滿為國戍邊的豪情壯志,全然不以“黃沙百戰穿金甲”的艱苦遭際為意,慨然發出“不破樓蘭終不還”的鏗鏘誓言。鄉關萬里,他們當然也渴望還鄉與親人團聚,但那必須是在剪滅強虜、平定邊患之后。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抱定必勝的信念,毫不懷疑有可能出現不利的戰爭結局。而這又緣于對強盛國力的高度信賴。這便是后人所津津樂道的“盛唐氣象”。
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則為思鄉情緒所裹挾而無法自拔、斗志頓失—突兀而起的幽怨的笛聲把他們本就難以抑制的懷鄉思歸之情勾逗得更加濃烈,在這個輾轉難眠的月明之夜,他們無休止地重復著“望鄉”這個機械而又深情的動作。字面上不見“憂傷”,但其低回掩抑、吞聲飲泣之態卻宛然在目。抒情基調由前詩的高昂一變而為后詩的低沉,原因何在?這絕不能歸因于詩人氣質與性格的差異,而是因為經歷了“安史之亂”這一滄桑巨變后,唐王朝的國勢迅速由盛而衰,外夷侵擾與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傾軋交相為患,戍邊的將士們既痛感前途暗淡、勝負難料,又不愿為腐敗朝廷戰死沙場、埋骨塞外,厭戰與思歸之心便與日俱增,借笛聲而軒露無遺了。
這也就是說,是時勢的變化導致了詩人抒情基調及敘事風格的變化。那么,以此反推,由不同詩人創作于不同時期的同一題材的作品,不是也可以捕捉到判然有別的現實投影與時代折光嗎?人生風雨無定,時代陰晴難料,而這都會在詩歌中留下或深或淺的痕跡,讓我們得以體認特定時代的復雜性和特定人生的豐富性。
由同一詩人創作于不同時期的作品,也能發現社會現實的激變如何左右著詩人的情感指向并影響著他們的抒情方式。宋代女詩人李清照的創作可以劃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的她過著養尊處優的貴婦生活,唯一的憾恨是身為朝廷命官的丈夫趙明誠或不免異地任職,乃至兩人無法長相耳鬢廝磨。因此她此時的詞作以抒寫相思之情為主,如《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所謂“愁永晝”,其實是有些夸張的,作者心里縱有一些不爽,也是因短暫的別離所造成,既不深刻,也不沉重,而淺若流云,淡如輕煙,一旦丈夫歸來,便煙消云散,重現光風霽月。
后期的她則在顛沛流離中咀嚼著國破、家亡、夫喪這三重深哀劇痛,發為歌詞,也就哀婉欲絕、近乎嗚咽了。如《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此詞亦于篇末托出一個“愁”字,這種愁遠非詩人前期詞中那種稍縱即逝的春愁、離愁可比,它融合了亡國之痛、孀居之悲、淪落之苦,底蘊顯得格外深廣與厚重。
將這兩首詞作相參讀,社會的動蕩變遷,現實的風雨晦明不言自明。
三、安置心靈的意境
詩歌可以為人們提供心靈的慰藉。當寂寞的靈魂在現實中感到孤獨無依時,無妨把詩歌當作休憩的驛站。一旦契合于詩歌那高邈的意境,你的心靈就會得到安撫與安頓,寵辱不驚,陶然忘機,不再糾結于仕途的失意或其他種種人生的不快,至少在閱讀的瞬間如此。
古代的高人雅士都把詩歌當作生活中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缺少的東西,是和物質消費同樣重要,有時甚至更加重要的精神需求。

賈島像 ,〔明〕王圻《三才圖會》
中唐詩人賈島在《戲贈友人》一詩中感嘆說:“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似乎失去了詩歌這股甘泉的滋潤,他的心田立刻就會干涸。唯其如此,他才會片刻不敢停歇地以“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綆”來保持心靈的水分,也才會糾結于“僧敲月下門”(《題李凝幽居》)一句的措辭,反復比較“推”“敲”二字的優劣,長久地為之舉棋不定,乃至給后人留下“推敲”這一具有多重啟示意義的典故。“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題詩后》)這是他的自道甘苦之辭,與盧延讓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苦吟》)意思相近。這既映射出其創作態度的認真,也可借以發現詩歌是怎樣牽系著他們的悲歡,制約著他們的情感世界。
對這類以“苦吟”而著稱的詩人,后世頗有不以為然者,譬如蘇軾就形容與賈島齊名的詩人孟郊說:“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讀孟郊詩二首》其一)金人元好問似也語含不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論詩三十首》其十八)但他們其實都已注意到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至少在吟詠之際,詩歌是占據著賈島、孟郊的全部心靈,并使其生命得以燃燒的。
與賈島、孟郊約略同時卻崇尚平易通俗的白居易在《北窗三友》一詩中說:“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將詩、琴、酒相并列,認定為自己遞相循環、永不離棄的摯友。
而在奉白居易為偶像、奉白居易詩為經典的東瀛,當它處在漢文化的籠蓋之下時,與中國古典詩歌同根同源且同貌的漢詩應運而生。以風雅自命的日本漢詩作者,和他們瓣香的偶像白居易一樣,對詩歌極度癡迷。藤原為時《春日同賦閑居唯友詩》有句:“閑居希有故人尋,益友以詩興味深。”由詩題可知,作者把詩歌視為閑居生活中唯一的友人,更加突出了它對心靈的慰藉作用,較之白居易的“北窗三友”說,又提升了一大步。不僅如此,“春日同賦”云云還昭示我們:這并非獨是作者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一同吟詠這一詩題的所有文友的共識。“若不形言兼杖醉,何因安慰陸沉心。”這同樣不只是藤原為時作為個體的感慨,而代表了整個創作群體對詩歌之靜心、清心、暖心功能的認知。

《白居易詩集校注》(全六冊)謝思煒校注中華書局 2017 年版
唐代長才短命的詩人李賀則將詩歌與自己的生命扭結在一起:所有的生命熱能都在詩歌中消耗,因為只有詩歌能給予他希望與光明,而創作詩歌也就成為他生存的全部意義。這個本來想經由進士考試而步入通衢的有志青年,卻因為才高見妒,被無恥小人用“避諱說”硬生生剝奪了考試資格:他的父親名叫李晉肅,而“晉”字恰好與“進士”的“進”同音。如此荒唐的理由居然大行其道,最終迫于輿論的壓力,他只好放棄登龍之想,轉而傾全力于詩歌創作,立下“唯留一簡書,泥金泰山頂”(《詠懷二首》其一)的宏愿,不惜為之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乃至老母親心疼不已地驚嘆:“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但他自己卻甘之如飴,因為詩歌不僅激活了他當下的生命、消釋了他胸中的塊壘,還將他的心靈世界與藝術世界合而為一。
四、情感與人生況味
詩歌是抒情藝術,以真實而又藝術地傳導人們的喜怒哀樂為第一要義。在詩歌中,人們可以自由地歡唱,也可以毫無顧忌地呻吟;可以直率或含蓄地說出自己的愛,也可以不加掩飾或曲折有致地表達自己的恨。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是最適合、最方便抒情寫意的藝術載體。
它可以用深婉之筆表現愛情的忠貞、熱烈及難言之隱。如李商隱《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相見不易,離別時才格外難分難舍。這就暗示男女主人公之間橫亙著一座有形或無形的壁壘,以致無法自由交往。但這卻無妨他們兩情深篤、至死不渝。“春蠶”二句作為最經典的愛情盟誓,遠勝《長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曉鏡”二句懸想對方別后應容顏不整、寂寞難耐,亦見深情繾綣。最后寄望于“青鳥”頻繁往來,為他們傳遞愛的信息,聊慰如饑似渴的相思之情。曲折婉轉的情感音波,借由精嚴的韻律和優美的語言的傳導,感動了后世多少癡情男女!而“春蠶”二句還被轉用來形容對事業及信仰的忠誠。

蘇軾像,〔明〕王圻《三才圖會》
它也可以千回百轉地抒寫“悼亡”的無盡憂傷。如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這是蘇軾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幽明永隔的痛苦與仕途蹭蹬的悵恨融合在一起,使這篇作品具有了一種沁人心脾的感染力。“不思量”,貌似無情;接著說“自難忘”,則見出死生契闊而未嘗一日忘懷。“塵滿面,鬢如霜”,暗示暌離十年來宦海浮沉,南北流徙,從容顏到心境都顯得特別蒼老,早已無復當年模樣。悼亡之情與身世之感在這里已水乳交融。“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夢境中的意外重逢,使兩人不僅失態,而且失語,悲喜交集之際,對視良久,淚下如雨,彼此的心聲就流溢在這積聚了太久的淚水中。
當然,最值得贊賞的那一類抒情詩歌,是將一己的情感與祖國的盛衰和人民的悲歡緊緊聯系在一起。杜甫的詩歌就是這樣。他的心律始終呼應時代脈搏的跳動,當血雨腥風彌漫時,他的詩歌旋律就無比滯重,情感基調也哀婉欲絕。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當時作者被安史叛軍羈押在淪陷后的京城長安。春天花開鳥鳴,本是賞心樂事,作者卻看花濺淚、聞鳥驚心,那是因為觸景傷情:鮮花著錦般的盛唐氣象已消散殆盡,花好月圓的幸福時光也已一去不返;連天戰火使得家人如鳥獸四散,而身為戰俘的自己則似鳥入樊籠。正所謂“以我觀物,則物皆著我之色彩”。全詩吞聲嗚咽,極沉郁頓挫之致。
當國家即將走出泥濘、走向新生時,他的詩歌旋律就變得無比輕快,情感基調也就變得喜氣洋洋了。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甫像,〔明〕王圻《三才圖會》
聽到官軍收復失地的喜訊,“漂泊西南天地間”的作者欣喜欲狂,不僅放聲高歌,而且陡然產生了“縱酒”的愿望。他的家人也洗去憂愁,盡現歡顏。他甚至已經開始設計返鄉路線,想象一路春色相伴、笑語盈耳的情景。突然而來的勝利消息,觸發了他內心久已塵封的喜感,使他唱出這樣奔放歡暢的心曲。《春望》中寫到了“淚”,此詩中也寫到了“淚”,同樣是“淚”,前詩是悲極而流,此詩則是喜極而飛。
此外,詩歌可以廣泛地介入我們的生活,成為現實生活中的敲門磚與試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