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地域的地域文學研究
周松芳

日前重讀陳建華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學林出版社1992年),深感這是一部優秀的明代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著作,而且由于集中到一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地區,并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為分析基礎,就比一般的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著作更深刻、更生動,也更富啟迪。許多年以后,陳教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的開篇也夫子自道:“我博士論文做的是明代江浙地區的文學,做文學的地域研究很有趣,也很有價值。”并說:“在我的筆記本里還有不少這方面的課題,卻沒有繼續做下去。”這里提出的“文學的地域研究”,竊以為基本可以有效避免“地域文學的研究”的身份代入感和方法民科化,即一味鼓吹自身所在地域的文學及其歷史的輝煌成就,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宏觀的文學的歷史)。而其未能繼續做下去,頗為遺憾,好在陳廣宏教授“繼續做下去”了——近作《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而我更感興趣的,乃是陳橋生博士新出的《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從來討論嶺南古代文學,對于唐代以前,或語焉不詳,或干脆從張九齡說起,雖然顯系失當,應該也是無計可施——對唐前嶺南文學的探求研究,無論努力與方法,都太嫌不夠。而從嶺南文明與中華文明的關系角度,此一階段,意義或許更大。考古研究表明,史前文明嶺南獨立發展,“在新石器時代是自成一中心,有光輝的歷史,起于當地,源遠流長,與黃河、長江流域各文化中心相比,互有長短”(曾昭璇語)。進入文明時代后,很長一段時間仍是獨立發展,建立了不少土邦小國,蘇秉琦先生曾說過嶺南有“自己的夏商周”,但真正有文字敘述的歷史,也可以說真正進入中華文明的歷史,主要還是始于秦征南越之后。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后廣東文學或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嶺外入中國”——嶺南融入中華文明,或中華文明擴展至嶺南——的歷史,征伐、遷徙、宦游、貶謫都是重要的觸媒,特別是作為書寫文明大大滯后于中原的嶺南,外來的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在唐以前更是成為書寫主體。而張九齡之所以能“橫空出世”,也正緣于其成長地始興與內地密切交流所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積淀。但是,這是怎樣一種文化積淀,又是如何形成的?陳橋生《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主要從文學的角度,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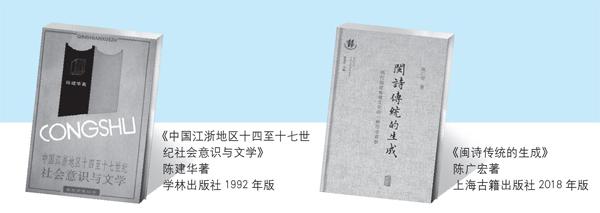
比如該書第七章“始興在南朝的迅速崛起”,先特別討論了范云(451~503)的個案,通過諸多流官謫宦的共同努力,以及范云的典型示范,不僅將嶺南創作融入了永明詩歌的主流之中,更以《三楓亭飲水賦詩》(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邪階流)等最早吟詠嶺南風情的佳作等,形成后世足資取徑的文學積淀。這是“嶺外入中國”的一種文化形式。而嶺外入中國的另一種形式,則是借由“中國”之人的栽培而進入“中國”,并在政治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者。再如號稱“南天一人”并入傳《陳書》的侯安都(519-563),便助推始興的發展達至前所未有之高度。侯安都早年曾被始興內史、南齊高帝蕭道成之孫蕭子范辟為主簿,后“招集兵甲,至三千人”,追隨陳霸先起事,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并在陳武帝陳霸先駕崩后,果斷擁立文帝繼位,居功至偉,影響深遠。特別是在京都建康招集文士品評詩賦,一爭高下,不僅有功于南朝文化的發展,當然更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嶺南文化與文學的發展。而所招聚的文士如陰鏗、徐伯陽等,不少都是剛剛經歷侯景之亂從嶺南回到建康,沾被著嶺南文化的雨露,把嶺南與首都建康的江南文化自然緊密地牽連交融,無形中更有力地促進了嶺南文明與中土文明的溝通對話,從而推動著整個南朝文學的融合發展。因此之故,屈大均《廣東新語》“詩始楊孚”條在追溯張九齡之前的嶺南詩史時,便對侯安都的招聚文士之舉給予了“開吾粵風雅之先”的高度評價;也正是因為有了侯安都等人的開風雅之先,才可能在盛唐出現張九齡這樣的本土著名政治家和文學家。
當然,更早承擔始興這一角色而且地位更為重要的,當屬嶺外入中國的第一個交通重鎮和文化交流中心——交州州治和蒼梧郡治的廣信(封川);直到唐以前,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海洋的世界,番禺(廣州)固為一都會,文化卻未有相應的昌明。故屈大均《嶺南新語·粵人著述源流》正是從廣信的陳元說起:“漢議郎陳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后有士燮者,生封川,與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余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后進若王范、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為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粵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須知,無論陳元抑或士燮,他們雖生于封川,但都無不是中原移民的后裔;這種中原文化的嶺南在地化,是嶺外入中國的另一種形式。
再往前推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的合浦與徐聞(兩港相距甚近),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朝貢貿易以及作為最早的南貶的集中地——從來貶謫之地,終須有基本的生存條件,以及相對健全的行政機構,才足以安置貶謫官員——更多地與中原保持著文化的交流往來,“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就是這種文化交流的生動寫照。又因海上絲綢之路首發港的原因而有諺曰:“欲拔貧,詣徐聞。”史上有名有姓的首貶嶺南的官員——西漢末京兆尹王章,雖死于踏上貶途之前的獄中,但家屬卻照貶合浦,并在其妻子的率領下,借其地利,通過兩年的經營,“采珠致產數百萬”而“榮歸故里”。在這些精彩的故事背后,陳橋生總結說:“抹去歷史、個人的恩怨情仇,流徙所及,便是文化的流播所及。流徙者以其滿腹的才華,就像一座流動的圖書館,被迫遷徙到了帝國最僻遠的文化角落,愈行愈遠,無遠弗屆,譬若陽光,不遺忘任何一個角落,譬若文明的種子,播撒一路,從而在荒遠的土地上也開出鮮麗的花來。”
陳橋生的論述還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如果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傳統的中原文化以外其他各個區域,莫不存在一個先后次第的“文化入中國”過程;“粵越一也”,在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過程中,后來成為新的文化中心的江南,曾經也是與嶺南一樣的斷發文身蠻夷之地,卻后來居上,成為新的文化中心。而晚近以來,嶺南也漸漸有成為新的文化中心的契機。如陳寅恪在讀了陳垣推薦的岑仲勉的論著后說:“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稍后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寫的審查報告中所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可謂對此的補證——晚近的嶺南,正處于這種吸收輸入外來學說而又不忘民族本位的樞紐地位,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對此實早著先鞭、論證甚力。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張君勱在《歷史上中華民族中堅分子之推移與西南之責任》中,更直接提出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與時次第為文化中心之說;朱謙之、郭沫若也都有近似的說法。而陳序經的《東西文化觀》《中國文化的出路》等著作,則可謂對梁、陳諸家之說的理論化系統化的闡述,認為輸入西來新知的東西文化問題,其實正是南北文化的真諦。也就是說,我們所爭論的以嶺南為代表的南方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的關系,其實可轉換為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南方文化的成長,一面接受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一面接受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進而影響著北方文化與傳統文化,形成一種非常重要的良性互動關系,不斷促進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與時俱進。
其實誠如葛曉音教授在序中指出:“作者同時又特別關注了嶺南文明如何反過來滲透、影響于中原文明。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互動,是貫串全書一條鮮明的主線,也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創見所在。”循著陳橋生的論述,我們發現,隨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互動,漸漸地更多地表現為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的互動。特別是在明代以后,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地域文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參見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這種區域間文化的共生與互動,顯得尤為重要,深具意義。偏居一隅文化相對落后的嶺南,從明初以孫蕡(1337-1393)為代表的“南園五先生”開始,在廣州南園結社唱和,開創嶺南詩派,一躍而成為國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不僅建立起了嶺南文學發展的自信,更確立了嶺南文學的新傳統——后世稍有影響的文學團體,多集于南園,且每以“南園后五先生”“南園十二子”“南園今五子”等相稱,以示文脈相承,嶺南文學,自此漸由附庸蔚成大國,如康熙時主盟詩壇的王士禎說:“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當代文史大家謝國禎也說:“廣東地方雖然僻遠,但文化極為昌明。在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等人,以文章聲氣與江南復社相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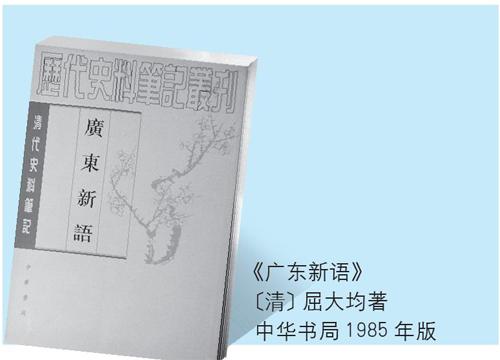
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嶺南文學的這種發展,與江南文學的共生互動有莫大的關系,也可以說主要淵源系于江南。今人常引洪亮吉論清初嶺南三大家詩句“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表稱嶺南詩歌的中原傳統,竊以為純屬誤讀;王士禎既已指出嶺南詩歌“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鄧之誠也說:“大均與江南畸人逸士游,未改故步,佩蘭與中原士大夫游,俊逸勝而雄直減矣。”這種雄直、古雅的傳統,正沿自南園詩派及其首席代表孫蕡——“五古遠師漢魏,近體亦不失唐音”(朱彝尊語),也正與相對軟媚的江左也即吳中詩派相區分,而更接近以其師宋濂、劉基為代表的奇崛雄肆、駕宋元而上的浙東詩風。孫蕡師事宋濂,最為虔敬,如在《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二十五首》中說:“二十余年侍禁闈,趨朝常早晚歸遲。春坊一掬臨分淚,記得垂髫受業時。”今檢《宋濂全集》,諸生之中,孫蕡也是向宋濂獻詩最多的,達三十一首之多,尤其感激宋濂的另眼相看青眼有加:“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蕡眼尚青。幾度背人焚諫草,風飛蝴蝶滿中庭。”嶺南文學的江南淵源,于此可見一斑。更有意味的是,從此之后,嶺南作家交游,多尚江南,且每以蒙受教誨、品題等為榮,即便到了清代,嶺南文化已經相對昌明,仍復如是。比如大名鼎鼎的屈大均,因先后得到兩位文壇盟主錢謙益與朱彝尊的獎掖而感念不已,同時也倍感自豪:“名因錫鬯起詞場,未出梅關人已香。”后來江蘇吳縣人惠士奇雍正間提學廣東六年,嶺南詩人何夢瑤、勞孝輿、羅天尺、蘇珥等入署從學,人稱“惠門四子”或“惠門八子”,蔚為文化盛景;阮元總督兩廣創辦學海堂并親任山長,網羅張維屏、譚瑩、陳澧、朱次琦等俊彥,更是極一時之盛。
但是,以江南為師,并不妨礙堅守自己的特質。在明初嶺南五子的作品中,大量反映嶺南風物的詩篇,就是一個象征。對此,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總結道:“百川東注,粵海獨南其波;萬木秋飛,嶺南不凋其葉。生其土俗,發于歌詠,粵之詩所以自抒聲情,不與時為俯仰也。”(《征刻廣州詩匯引》)借此更可發展到互為師表的境界:“三吳竟學翁山派,領袖風浪得兩公。”(屈大均《屢得友朋書札感賦》)錢仲聯先生的研究也作如是觀。如說“清中期廣東詩人黎簡,受浙派的影響,反過來他又影響浙派”(《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良性互動的區域間文學生態,應當值得關注和思考。事實上也日漸引起關注和重視,二○一九年先后在粵滬兩地舉行的“江南文化·嶺南文化”論壇,就是這方面的重要體現。推而廣之,江南文化與中原文化、嶺南文化與荊楚文化、齊魯文化與中原文化等之間是怎樣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共生互動形態?而這種共生互動關系的研究,也極有助于打破地域文化研究的地域桎梏,成為中華文明的嶺南研究、江南研究、齊魯研究、荊楚研究等的推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