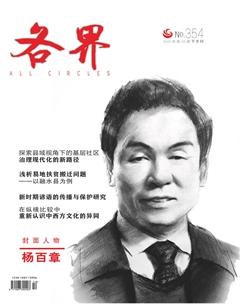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問題探究
李典
摘要:隨著科技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人工智能、物聯(lián)網(wǎng)、云計算、大數(shù)據(jù)、3D打印技術(shù)等新型技術(shù)層出不窮,并且在各自的領(lǐng)域快速發(fā)展形成了一定產(chǎn)業(yè),進而又蔓延滲入其他領(lǐng)域,與其他領(lǐng)域發(fā)生交叉關(guān)系。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角度出發(f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逐步蔓延到文學(xué)領(lǐng)域,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音樂、藝術(shù)作品進入群眾視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與著作權(quán)法律的關(guān)系也成為業(yè)內(nèi)熱議的話題。本文基于技術(shù)革新和著作權(quán)保護相平衡的原則出發(fā),通過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定性等方面來討論人工智能技術(shù)和著作權(quán)法律制度的沖突與聯(lián)系。
關(guān)鍵詞: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
一、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由高度互聯(lián)的機器、軟件或由人類勞動創(chuàng)造并基于算法的系統(tǒng)所顯示的類人和非類人智能。人工智能領(lǐng)域與各個學(xué)科均有一定的交叉聯(lián)系,例如計算機科學(xué)、心理學(xué)、哲學(xué)、神經(jīng)生理學(xué)等。隨著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等高級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工智能技術(shù)逐漸進入人們生活中并占有一定的地位。例如,智能翻譯器、指紋識別、人臉識別、智能家電家居、無人駕駛汽車技術(shù)等。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當(dāng)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中均屬于人們熱議的話題。人工智能技術(shù)目前處于初步發(fā)展階段,其探索的空間還很大。另外,該技術(shù)的出現(xiàn)對人類產(chǎn)生了一定的效用,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人們通過發(fā)展研究人工智能技術(shù)以使促進社會進步,形成新的人類文明。
二、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人工智能是否屬于法律所規(guī)定的權(quán)利主體,學(xué)界有著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主張人工智能不是“人”,不能賦予其法律主體地位,它只是以計算機技術(shù)為依托執(zhí)行人類命令的工具,并不具有人類的獨立思考和自主處理問題的能力;另外一種觀點主張,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和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進步趨勢,其自主性和學(xué)習(xí)型會逐漸接近人類,甚至超越人類,人工智能在此時擁有法律地位就是必然。只有明確人工智能的主體性質(zhì),才能進一步討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否具有可著作權(quán)性。只有明確人工智能屬于著作權(quán)人,才有資格禁止未經(jīng)授權(quán)的侵權(quán)行為。要確定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首先要明晰人工智能的發(fā)展現(xiàn)狀,針對不同階段的人工智能來分別討論其是否具有法律主體地位是比較合適的。
(一)初級人工智能是否屬于法律主體
初級階段的人工智能大多數(shù)屬于符號性知識表達。該階段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使用專業(yè)語言(如計算機語言)進行程序編碼,通過運行一系列的程序來實現(xiàn)目的,對于信息的收集與處理依賴于計算機系統(tǒng)。常見有的家用掃地機器人、“天貓精靈”、實時翻譯器等。此階段的人工智能顯然不能作為享有相關(guān)權(quán)利的法律主體,他們更像是一個基于計算機技術(shù)的高科技工具,不具有人的內(nèi)在屬性和生命特征,無法獨立處理事務(wù),因此賦予其法律主體地位難免有些牽強。
(二)高級人工智能是否屬于法律主體
目前發(fā)達國家正在極力推進著第二類人工智能即非符號性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發(fā)展,此類人工智能不同于第一類的特點在于,該類人工智能不是利用專門語言來編碼轉(zhuǎn)譯龐大的知識信息,是在更深層次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模擬人類大腦的工作原理,以創(chuàng)造類似于人類的神經(jīng)元來收集處理信息,即“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那么我們假設(shè)在未來的高級階段人工智能技術(shù)不僅僅是執(zhí)行人類命令,其擁有理性、情感、獨立思考等人類特有特征,甚至超越了人類的智慧,是否應(yīng)該賦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主體地位。傳統(tǒng)法律人格賦予標準顯然已經(jīng)不能滿足技術(shù)發(fā)展的未來,根據(jù)當(dāng)前標準,我們無法將人工智能精準定位為一個法律人,但是將其作為“物”對待,對于高級人工智能是不合理的。美國早在1983年就出現(xiàn)了將人工智能列為作者的情況,將小說《警察的胡須剃了一半》的作者登記為一臺計算機;在2014年,香港的一間公司就將計算機算法任命為董事會成員;2017年沙特阿拉伯政府授予人工智能機器人Sophia公民身份;歐盟議會法律事務(wù)委員會針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也提出了立法提案,擬賦予機器人法律主體地位。因此,結(jié)合當(dāng)下國際上對于此問題的看法以及未來人工智能技術(shù)發(fā)展的趨勢,我們應(yīng)該打破傳統(tǒng)法律人格賦予的禁錮,緊跟技術(shù)發(fā)展的潮流趨勢,在發(fā)展中逐步確認人工智能獨立的法律人格。
三、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地位
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打破了人類在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壟斷。同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其創(chuàng)作物是否屬于作品,是否屬于著作權(quán)保護的客體等一些問題也引發(fā)了學(xué)術(shù)界的熱議。在現(xiàn)有的著作權(quán)制度下,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均明確要求作者必須為自然人。這也是我們要討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權(quán)屬問題無法躲避的問題,正如上文說道,目前技術(shù)背景下的人工智能還不能被認定為“法律人”,那么我們在討論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屬于作品的同時就會陷入一個邏輯循環(huán),即“因為著作權(quán)法所要求的作品的主體必須是人,而人工智能不是人,所以其創(chuàng)作物就不是作品;因為該創(chuàng)作物不是作品,那么就沒有作者,則無須認定其著作權(quán)歸屬問題。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無法得到法律定性,那么是否就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未經(jīng)授權(quán)的使用這類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法律對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來說,應(yīng)該是激勵其設(shè)計生產(chǎn)更多的符合人類需求的智能產(chǎn)品,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否認他們。
(一)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否為作品
考慮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否是作品時,暫時不考慮主體因素,只考慮相關(guān)內(nèi)容的形式要素,那些不符合原創(chuàng)性要求的內(nèi)容,則可在“與人類作品相同形式的內(nèi)容”中識別并排除在版權(quán)保護范圍之外。而滿足作品的形式要件且具有獨創(chuàng)性,就有可能被認定為作品。故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在相關(guān)內(nèi)容的表現(xiàn)形式上是否符合作品的形式要件,而是否具有內(nèi)容上的獨創(chuàng)性是下一步應(yīng)該討論的問題。例如對于由人工智能繪制的畫是否屬于作品的判斷,首先我們分析如果是人類創(chuàng)作的畫,判斷其是否屬于著作權(quán)法上規(guī)定的藝術(shù)作品如果其形式滿足“以線條、色彩或其他方式構(gòu)成的審美意義的平面造型藝術(shù)”的形式要件,就可以將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具有相同形式要件的繪畫納入考慮范圍中,進一步分析其是否具有獨創(chuàng)性。
(二)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獨創(chuàng)性
學(xué)界對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獨創(chuàng)性判定也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不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理由在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所體現(xiàn)的“創(chuàng)作力”實際上是計算機的應(yīng)用法則、規(guī)則等計算。而《著作權(quán)法》所要求的獨創(chuàng)性的體現(xiàn)是作者獨立的、富有個性的創(chuàng)作,是作者精神和思維的外在表現(xiàn)。例如上文中所說繪畫作品,我們都知道以一個相同的參照物,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因為每個人對于參照物的理解不同,使用的筆觸,顏色的不同,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是不同的,并且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繪制的作品也無法一模一樣,這正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獨創(chuàng)性的體現(xiàn)。有別于人工智能嚴格根據(jù)算法、規(guī)則,執(zhí)行一系列命令而產(chǎn)生的輸出物。因為這些先置的命令是自主運行的,使用人無法干涉或者加入自己的個性表達,其由任何人執(zhí)行,獲得的結(jié)果都是相同的,排除了執(zhí)行者發(fā)揮自己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從而不符合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主張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具有其獨創(chuàng)性的學(xué)者,他們是基于具有“學(xué)習(xí)”能力的人工智能來展開的,前文所述利用“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通過模擬人類大腦的任務(wù)處理,在設(shè)計者完成初步的設(shè)計之后,通過計算機網(wǎng)絡(luò),大數(shù)據(jù)來自主學(xué)習(xí),這種學(xué)習(xí)是脫離了設(shè)計者最初的預(yù)先算法規(guī)則,在處理任務(wù)中發(fā)現(xiàn)更細的規(guī)則來進行創(chuàng)作,在該人工智能得出結(jié)果以前,任何人都無法預(yù)測到。因此我們可以以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深度學(xué)習(xí)能力,即內(nèi)容生成的自主性來劃分,如果產(chǎn)品的內(nèi)容是基于設(shè)計者預(yù)先設(shè)定的內(nèi)部程序和算法,則不是原創(chuàng)的,可以定性為創(chuàng)作的輔助工具;如果創(chuàng)作物的內(nèi)容是基于提供的素材且根據(jù)自主學(xué)習(xí)生成的,并且生成結(jié)果不具有同樣性,根據(jù)不同的環(huán)境、時間因素結(jié)果不同,那么此種意義上的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就具有獨創(chuàng)性。
四、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保護的意義及可行性方法
當(dāng)前,人工智能技術(shù)還處于發(fā)展階段,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保護面臨著作者界定、可著作權(quán)性判斷、權(quán)利歸屬等待解決問題。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保護是企圖在“私權(quán)”和“公眾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是實現(xiàn)著作權(quán)法“利益平衡”精神的有效途徑。著作權(quán)法是為了賦予權(quán)利人一定期限的獨占權(quán),以激勵更多的創(chuàng)作物產(chǎn)出和傳播,這也是我們需要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進行著作權(quán)保護的原因。
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進行著作權(quán)保護,不同的學(xué)者專家也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方法。易繼明教授提到了劇本模式,即將人工智能技術(shù)作為“劇本”,人類是表演者,在此種模式下,可以借鑒參考著作權(quán)法中有關(guān)演繹作品的規(guī)定進行保護。吳漢東的看法是在不參考該創(chuàng)作物的來源的前提下,只要其符合創(chuàng)作物的表現(xiàn)形式和獨創(chuàng)性,就可以作為著作權(quán)客體來保護,即使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主體地位,但是可以視為是人類利用計算機系統(tǒng)進行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內(nèi)容。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不能包容概括為人的創(chuàng)作,既不能簡單劃歸為程序編寫者的智力成果,也不能將其籠統(tǒng)歸為使用人的智力成果,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中的作品只能是人類創(chuàng)作的作品,即使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是原創(chuàng)的,也不能簡單地將其列入著作權(quán)法的作品范圍并加以保護,故有的學(xué)者提出了制定單行法律對其進行特別保護。未來人工智能技術(shù)占據(jù)人們生活,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也會越來越多,人們會更多地了解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應(yīng)用,所以制定單行法是可取的。同時,基于目前學(xué)術(shù)界熱議的問題,也必然要在法律中規(guī)定清楚以何種方式對其保護。
五、結(jié)語
人工智能技術(shù)與著作權(quán)法的聯(lián)系與沖突,一方面促進了法律順應(yīng)社會的發(fā)展,不斷地發(fā)現(xiàn)漏洞,彌補漏洞,以更好的調(diào)整社會關(guān)系;另一方面,因為這些權(quán)屬爭議,使人工智能更多的展現(xiàn)與公眾視野,通過爭議解決來反推動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法律是滯后的,立法者不能預(yù)先根據(jù)自己對社會發(fā)展的猜想來預(yù)設(shè)法律。具體到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正是因為科學(xué)技術(shù)與法律的交叉,其發(fā)展進步是由一次次的技術(shù)革新推動,技術(shù)的高速發(fā)展不斷挑戰(zhàn)著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這正好也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制度發(fā)展革新的原動力。
【參考文獻】
[1] 程夢瑤.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保護問題研究[J].圖書館,2019(03):41-42.
[2] 尹國金,支果.人工智能“作品”權(quán)屬問題研究[J].法制博覽,2019(07):40-42.
[3] 曹源.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獲得版權(quán)保護的合理性[J].科技與法律,2016(03):488-508.
[4] 田瑞.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問題分析[J].現(xiàn)代商貿(mào)工業(yè),2018,39(26):137-138.
[5] 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nèi)容在著作權(quán)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7,35(05):148-155.
[6] 易繼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作品嗎?[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7,35(05):137-147.
[7] 吳漢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制度安排與法律規(guī)制[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7,35(05):128-136.
[8]許明月,譚玲.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鄰接權(quán)保護——理論證明與制度安排[J].比較法研究,2018(06):42-54.
[9]徐文.反思與優(yōu)化:人工智能時代法律人格賦予標準論[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18,39(07):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