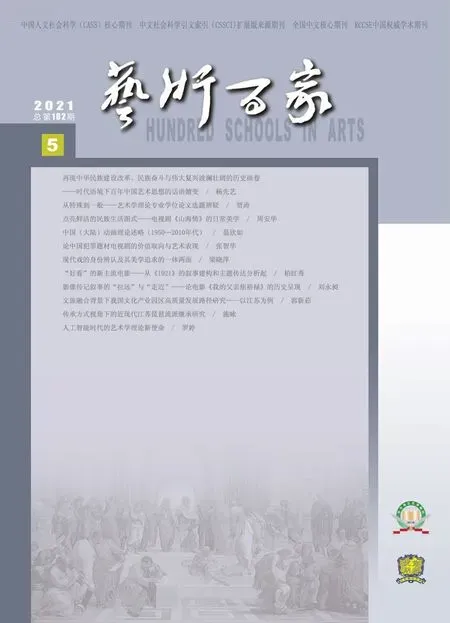門類藝術間通感激發的具體審美動因分析*
——以跨門類視角下的《聽琴圖》圖像形態中的幾組關系為例
韓 波
(曲阜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山東 曲阜 273100)
每個人對藝術作品的欣賞都有其獨特的心理經驗,但欣賞的深入程度又與欣賞者的知識素養緊密相關。就一般的欣賞過程而言,有這樣幾種層次:最為基礎的欣賞層次是僅著眼于藝術作品的顯性形態。顯性形態欣賞的主要機制是建立在直接感官的基礎上,此時人們獲得的審美愉悅是直接的或言為淺表的。進一步地欣賞則是對于藝術作品內在結構的學理性的分析,諸如題材、技法、類型、形式、趣味等;最深層次的賞析和解讀則需要接受者具備更為深刻和寬廣的人文科學的知識和修養,方可窺其堂奧,捕捉到作品的話外之話、弦外之音。
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基礎在于各門類藝術之間跨門類的規律和分析研究。事實上,美術與音樂兩個門類藝術形式之間存在著相互溝通的內在規律性聯系,而絕非風馬牛不相及。藝術通感是欣賞者面對藝術作品進行欣賞過程中產生的深度審美體驗,也是各個門類藝術之間相互溝通、關聯的橋梁和紐帶。藝術欣賞層次在理論建構上的明晰化離不開美國著名藝術史論家潘諾夫斯基,他提出在藝術作品的題材或含義研究方面的三個層次:一是基本的或自然的題材,又分為事實性或表現性題材;二是從屬性的或約定俗成的題材;三是內在含義或內容[1]36。他將這三個層次的研究應用于圣像學的研究,依次為:前肖像學描述、肖像學分析、圣像學解釋。盡管這種方法最初應用于對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宗教畫的研究,但其蘊涵的學理性內核即便在其他地區、時代或民族的藝術作品分析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適用性。東方藝術從來不缺乏隱喻和象征,這就決定了對之研究同樣可以借鑒潘氏學說的理念。尤其在對于第三層次“內在含義或內容”的分析時,諸如心理學、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的介入,無疑會使得研究走向深刻。
一、美術與音樂間的藝術通感
美術和音樂作為藝術的兩種形式,在創作機制和接受機制上有著很大的不同。美術主要提供給人視覺形象上的感知,其視覺形象的形成源自于創作者在腦海中累積的形式表象,這些形式表象最終經過藝術家大腦的整理、分析和提煉,借助技巧和媒介的表達,以一種明確的視覺形態也就是畫面提供給欣賞者。而音樂提供給人們的則是聽覺的感知,是創作者心靈沖動下對聲音的情感化表達,依循對音聲的高低、節奏快慢的秩序化組織,從而形成音樂旋律。
日本學者黑田鵬信曾對藝術構建的材料進行過論述,認為存在兩種意義上的藝術的材料,一是“感覺的材料”,二是制作藝術的“物質的材料”。他指出:“藝術的感覺的材料,和美的材料相同,也有色、形、音三者。建筑、雕刻、繪畫、工藝美術等的材料,是色和形。音樂的材料,是音。”[2]6至于“物質的材料”,易于理解,即藝術作品呈現所使用的物質實體材料。對美術而言,無外乎是各種物質材料,對音樂來說,除物質制作的樂器外,還包括人體的發聲器。在創作階段,無論是美術還是音樂,要想建構一件完整、和諧的作品,都要有效地組織“感覺的材料”和“物質的材料”,即促進色、形、音的秩序化和可感知化的實現。美術作品對“感知材料”和“物質材料”的組織表現為同時性、混融性,如畫家在用畫筆驅使顏料的過程中同時完成了色與形的組織;在音樂創作階段先是完成了對“感知材料”——音的組織,其次通過演奏或歌唱才能實現作品的可感知化。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后治其飾。”[3]27《樂記》中這一段對音樂的本質和特征的闡釋,很好地借用造型藝術特別是美術常見的特征語詞,講明了其中的道理。這也就是說,美術與音樂絕非風馬牛不相及的藝術形式,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溝通的規律性的東西。有學者認為:“音樂,作為一門以聲音為媒介反映宇宙萬物和人類心靈運動節律的藝術,雖然不能直接描述客觀事物,但也可以做到聽聲類形,以耳為目。這種通過聯覺獲得的“非音樂性內容”可以是其他類型的聽覺形象,也可以是視覺性的形象,甚至可以是動覺、觸覺、味覺、嗅覺等無所不包的內容,使得音樂不僅可以用耳朵聽,而且可視可睹、可聞可嗅、可品可嘗、可感可觸,它遠比音響本身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內容要廣闊得多。”[4]163這說明音樂所能激發的其他的感官聯覺是多方面的,音樂感染力的源泉即根源于此。欣賞音樂作品時,人們除了沉浸在旋律的氛圍中,也可能伴隨著形象的聯覺即在欣賞者的腦海中出現畫面感。
反過來,道理也是一樣。人們在欣賞美術作品時,在瞬時全局地或連續不斷地觀看視覺形象的同時,有可能產生一定的樂感體驗。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藝術通感”①現象。朱光潛先生是這樣描述藝術的通感體驗的:“各種感覺可以默契旁通,視覺意象可以暗示聽覺意象,嗅覺意象可以旁通觸覺意象,乃至于宇宙萬事萬物無不是一片生靈貫注,息息相通……所以詩人擇用一個適當的意象可以喚起全宇宙的形形色色來。”[5]]70那么藝術通感究竟緣何而生呢?朱立元主編的《美學大辭典》中解釋為,“藝術通感的客觀基礎是當前感知的事物與以往經驗過的或思考中的事物在形、質、量、度上客觀存在的相似性被人認識以后在大腦中的溝通、關聯,是藝術與社會生活以及各門類藝術之間的內在聯系被激活和溝通。其生理機制是諸感覺器官之間的關聯性和大腦皮層視、聽、觸等區域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激活。其心理基礎是主體在審美創造美實踐中所積累的生活經驗、審美經驗、創作經驗被喚起和在此基礎上展開的聯想、想象活動,情感活動,創造活動,其中尤以審美需要、審美記憶、創作動機、創作探索、審美感受力、藝術想象力和飽滿的情緒狀態為直接動力,并制約著通感的豐富性、創造性和獨特性。”[6]87
依據上面關于藝術通感的生成機制的論述,我們知道藝術作品接受對象的過往感官經驗被作為一種記憶儲存在大腦之中。而能調動起所儲存的經驗記憶的前提是當前感知對象在形、質、量、度上所具有的相似性。所以欣賞一幅繪畫,若要獲得音樂的通感,則這幅作品的畫面要素排布特征和畫面意境的營造一定能夠激發對音樂經驗和記憶表象的喚醒,從而產生聯覺。當然藝術通感的體驗因人而異,因為個體的經驗記憶的儲存有著必然的差異。略通文藝常識,我們都能明白這種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道理。
藝術通感是中國書畫欣賞中的一種深度審美體驗。本文所關心的是在美術作品欣賞過程中,音樂通感體驗所賴以生發的基本動因問題,這些動因與作品畫面結構形態的設計存在怎樣的邏輯關聯。通俗地說,畫面的結構形態好比酵母,沒有酵母不會引發更大程度上各種各樣感官聯覺發酵和通感體驗的形成。下面我們以宋代繪畫中以聽琴為題材的繪畫作品,也即傳為宋徽宗趙佶所作的《聽琴圖》為例,從畫面本體角度來探討其激發音樂通感的可能性。
二、琴與人:典故激發通感
在《聽琴圖》畫面中,琴與人是誘發音樂通感生成的第一組關系動因。古琴與中國其他傳統的樂器一樣,最初都是用于祀神,其后漸次變為娛人。從這個意義上看,樂器皆是仿擬天籟之聲的“道器”。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古琴與人的節操和修為之間關系密切。琴最初雖然不是士大夫的專屬,但在魏晉以后逐漸與高人逸士聯系在一起,成為雅樂樂器。
在中國古代的文化生活中,舉凡圣賢哲人對音樂的教化作用都甚為看重。對于令人欲望泛濫、萎靡放浪的音樂,斥之為“淫”樂,觀照宇宙自然、寓意人倫教化、比德克己修身、抒發心志情懷的清朗、莊穆之樂,視之為“雅”樂。尤其自魏晉之后,隱逸之風興起,古琴成為文人抒發自我心性的樂器之一,意在表達對天地人生感悟之情懷,而非用于嘩眾取寵。隨著文人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趣味影響的深化,古琴的演奏、創作、欣賞等音樂習得方式,也逐漸擺脫了民間大眾的審美趣味,形成了古琴的專業化演化路徑。魏晉時期的南北分立的社會現實、文人化的哲學化、精神化的思想文化語境也為文人們培養出悠游不迫、坦然自適、富有彈性的處世態度。[7]80
知音難覓,膾炙人口的伯牙與子期的故事,為我們呈現了琴、人關系的典型化例證。操琴者伯牙和知音者子期,一方面對應了音樂創作和接受關系中的兩個主體,另一方面也印證了琴音與高士之間關系的超凡脫俗。《列子》中云:“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伯牙志在流水,鐘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海。’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伯牙曰:‘善哉,子之心而與吾心同。子期既死,伯牙絕弦,終身不復鼓也。”[8]69演奏者的心象注入琴曲,聽音者的體驗意象與之高度契合。高山與流水分別對應著仁者和智者的志趣偏好,昭示著伯牙、子期心中所追求的德范來自于超越普通民眾志趣和情懷的圣賢。嵇康在《琴賦》中對操琴者的德范表達非常明確,“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恡;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9]111在嵇康看來,琴音潔凈端理,至德和平,因此舉凡圣賢,皆于琴聲有悟,“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9]111良琴更是可堪比擬人的高尚德操,能遇見真正的操琴之人,無疑是琴之幸事。然而能夠在琴技和個人德行上雙雙達到巔峰的人實在是太少了,鼓琴者能遇到真正知音也殊為幸事。惟其稀缺,方才為世人所尊奉。這也恰如嵇康所發出的感慨那樣,“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9]111
無獨有偶,精于琴道的唐代學者蘇易簡,在其所撰《琴訣》一書中亦曰:“琴之為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心亂神濁,則聽者難辨矣。常人但見用指輕利,取聲溫潤,音韻不絕,句度流美,但賞為能。殊不知志士彈之,聲韻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聽之則壯氣益增,孝行節操者聽之則中情感傷,貧乏孤苦者聽之則流涕縱橫,便佞浮囂者聽之則斂容莊謹。是以動人心,感神明者,無以加于琴。蓋其聲正而不亂,足以禁邪止淫也。……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難也。”[10]162這段話清楚地闡述了古琴之樂音所具有強烈而豐富的藝術感染力,但該藝術感染力與鼓琴者的德操修為有著密切的關系。高妙的演奏境界非志士高人不可達到,而如果聽者修養不高,自然也是無法在欣賞過程中與鼓琴者達成藝術共鳴的。這種至善的演奏和欣賞境界只能存在于極少數人之間。至此,古琴與鼓者及知音者漸漸在后世人們的藝術表現中形成了一種彼此關系的定格,即琴之品格必定對應人之品格。
《聽琴圖》中,居于畫面中心的操琴者乃是九五至尊的當朝皇帝,貴為人主的社會地位無人企及。但畫面引人入勝的,卻并不是通過華麗的衣飾來渲染宋徽宗在世俗社會中的崇高身份。相反,對其服飾的刻畫卻刻意回避世俗性。不同于畫面中兩位聆聽樂音的官宦,趙佶內穿白色交領衫,無中單,下著裳,外披玄色鶴氅,腳踏玄履,一派仙風道骨。其時,他正頷首正襟,撫琴啟弦,目光游離世象之外,超然恍惚,似入無我之境。徽宗的這種裝束并非偶然,其意在昭示精神信仰中對于道家思想的尊崇,甚至于表現出對道教的支持和袒護。徽宗即位后,棄佛奉道,幾近于癡迷。政和七年,甚至冊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在政治上十分昏聵平庸的他任由蔡京和童貫之流操持朝堂之事,以至政廢民怨。道教那種無為而治,率意自然的思想與其即位前形成的耽于藝術、修養身心的一貫作風達成了契合。筆者查閱《宋史》,摘錄出其尊奉道教的一些事項羅列于下表,讀者由此可見一斑。宋徽宗在畫面中被塑造成這種道家形象,無疑會令觀者聯想到古之高人逸士,其視線神游于天外,思緒料已進入玄妙的天籟境界。
左右對坐的兩位侍臣則為文官裝扮,頭戴展腳幞頭,腰間革帶下插,身穿圓領長袍。一人綠衣,籠袖膝上,仰首凝思,心馳神往;一人朱袍,手執團扇,俯首靜聽(胡敬《西清札記》認為穿紅衣者為蔡京②);另有藍衫童子兩手交叉,凝神注視撫琴之人。
演奏者和聽琴者的人物排布,加上正前方的假山瓶花,共同形成了一個閉環,是否象征道氣圓滿充盈,也未可知。君臣之間通過音樂的交流,豈不酷似古之伯牙、子期,觀者耳邊難免不會隱約浮現“高山流水”之樂音。

表1 《宋史本紀》載宋徽宗尊奉道教事跡
三、琴與境:空間激發通感
畫面中,鼓琴行為與所在環境關系的建構是激發琴音通感的又一組關系動因。正如伯牙、子期在山水間相遇一樣,操琴需要與之相契合的環境。凌瑞蘭在《中國古琴文化》一文中認為:“古代,中國琴人視古琴為修身養生之道,而非謀生之路,所以將琴、棋、書、畫、酒、茶、金石、古玩、園林、建筑、園藝等一并作為文化修養納入生活天地。”[11]35從漢代始,古琴漸成為文人所鐘愛的樂器,其作為獨奏樂器,具有清、微、淡、遠的審美特質,因而操琴者在演奏環境上有所苛求。“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靈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常思。”[9]108這是嵇康在《琴賦》中為我們勾畫的一幅美妙的場景。
在嵇康心里,適合的環境會對鼓琴的狀態產生出很好的輔益,“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燦,纓徽流芳,于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觸如志,唯意所擬。”[9]101-102司空圖在其《二十四詩品》中有三品(第六品、第九品和第十八品)③中涉及到了鼓琴與環境的關系。《白居易全集》中也有“聽彈古《淥水》”“對琴待月”“和《順之琴者》”“朝課”等數條文字有關于這一方面的感悟。④明代文人屠隆在《考盤馀事》中具體描述了作為琴室的環境條件:“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達。如平屋中,則于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于喬松修竹,巖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此外還有關于演奏時環境的描寫,諸如對月、對花和臨水⑤等。至清代,文人程允基在其所著《誠一堂琴談》之“琴有所宜”條中援引《太古遺音》說:“凡鼓琴,必須明堂靜室、竹間松下,他處則未宜。”[12]11
文人靜修的自然林水或縮微自然的園林被視為與古琴音韻相和諧的彈奏場所。上千年來,這種意識作為文化傳統一直傳續在文人的音樂生活中。小說《紅樓夢》第八十六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寄閑情淑女解琴書”中,作者曹雪芹借黛玉之口道出了撫琴與環境的關系,“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樓層的上頭,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崖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才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13]1240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1939年出版的《琴道》一書,其中也提及中國文人對鼓琴之境的選擇,“除了在戶外美麗的風景之中,文人學者的寓所也是最適合撫琴的地方。學者們理想的寓所要有隱士的氛圍:寓所為園林所環繞,以松竹與外界相隔離,幽幽曲徑蜿蜒于別有意趣的假山或是蓮塘旁邊,通向一個樸素的樓閣,在那里他們可以作詩、讀書。”[14]57他甚至不惜筆墨,援引《何氏語林》中對元代畫家倪瓚居所的描述,以佐證自己的論斷,“倪云林所居,有清秘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舒繚繞。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攜杖履自隨逍遙容與,遇會心處,鼓琴自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
高羅佩書中還提及了楊表正所著《琴譜》中對于彈琴的一套清規戒律的描述,即所謂“十四宜彈”和“十四不宜彈”。[14]57在“十四宜彈”中明白地指明彈琴所宜的環境條件,如“處高堂,升樓閣,在宮觀,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氣清朗,當清風明月。”
據言宋徽宗珍愛天下之琴,曾搜集天下名琴陳列于萬琴堂內,其中最出色的是唐朝雷威所作的“春雷”琴。后金章宗得此琴,鐘愛有加,并指定以此琴殉葬。而后又有更愛琴者將其掘出,由耶律楚材贈與當時的著名琴師萬松老人,才致使其流傳民間。
《聽琴圖》(圖1)中為觀者營造了這樣的一處環境景象,畫面構景極為簡潔,超越了宋代一般院畫的寫實傾向,更強化出一種與琴聲的精神抽象特質相匹配的空靈、玄淡之感。作者已將本系蕪雜的宮苑園林景觀給予了高度的提煉和簡化。樹木、花草、山石近乎一種符號化的表達。一棵欹曲的孤松,點明了林下松風的環境,雖只一株,卻讓人聯想到萬壑松風的藝術意象。筆者以為,畫家之所以有節制地控制樹木的數量,并非苦于對更多樹木枝丫描繪的繁瑣,而是點到為止,以一當十。處于畫面下端操琴人的正前方,置放一座極盡曲折變化的太湖石,上置銅鼎,鼎中插花。這顯然又是以假山石的符號性表現,暗示觀者,此處乃是一處園林。事實上,在中國園林的營造技巧中,假山石的疊放大多三五成群,成團成簇,給人縮微的山體之意象。獨樹園中的太湖石情況雖然也有,但往往選擇面積不大,不能大片疊石的院落空間,且石材應具有相當的尺度,以便給人危峰獨立的奇峭之“象”。很顯然,如果在一片空曠平坦的園林院落中,孤立的放置一座巨型假山,是十分突兀的。畫家如果去寫實性描繪其尺度,必然又會對人物所應占有的畫面中心空間產生沖擊和破壞。所以,在這里聰明的畫家會依然將其視為一種象征性符號,縮小其體量,協調整體畫面空間。再看其他景物元素,正值花期的凌霄花在松樹上攀援而上,樹旁點綴著幾竿青竹,四向伸展搖曳。至此,我們會發現表征園林空間的建構要素基本齊全了,只欠水體了。但從空間表征的角度,這些要素已經足夠了。我們大可以依據園林營造的規律想象,湖面可能就在畫面沒有展現開的不遠處。這樣的符號化的園林空間敘事,其實并不是畫家的首創,因為在五代畫家周昉的作品《調琴啜茗圖》中,我們不難發現相似的處理技巧。畫面中呈現的簡率空靈的美感意境,正如魏晉至唐代墓室壁畫中慣用的高度提煉手法一樣,畫家僅僅以一株桂花、一棵梧桐樹就寓意了人物生活的環境——宮苑園林。《聽琴圖》的這種處理手法,與簡潔表意的唐代墓室壁畫的形式語言可謂一脈相承(圖2)。

圖1 〔宋〕趙佶《聽琴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唐〕周昉《調琴啜茗圖》,絹本設色,縱28厘米,橫75.3厘米,〔美〕納爾遜·艾京斯藝術博物館藏
因為僅僅依賴對于環境真實性的強調,并不足以讓觀者獲取更強烈和豐富的通感共鳴。相反,樹木和山石多了之后反而弱化了對人物形象和神情風貌的強調,密密匝匝的林木反而阻礙了與樂音相適合的縹緲淡遠的空間意境的呈現。而這種意境恰恰是以視野上的虛空烘托出無形的樂音所引發的空靈回響之聯覺。“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道家思維在畫面中得到了巧妙的詮釋,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
我們或許無法真正準確地推斷畫家在畫面經營上的用意。但至少,畫面中有限的信息和我們透過歷史考證宋徽宗當時生活行為,可以讓我們獲得這樣一種審美判斷——即畫面中洋溢著一種超逸之“象”。這必定與徽宗當時的信仰傾向息息相關,畫作創作的意圖在于隱喻以“樂”就“道”。高羅佩關于描繪鼓琴一類的中國繪畫有這樣的闡釋:“坐在生長于飛瀑懸掛的峭壁邊的一棵古松下,沉浸在薄霧繚繞、只見遠山之巔的冥思中,這幅圖景就是中國畫家在丹青中樂于描繪的琴人撫琴的環境。乘著超然的、寧靜的琴聲,琴人的思想得到了凈化并且升華至神秘的境界,他的靈魂可以與面前凹凸不平的巖石和潺潺的流水相通,這樣他就會體驗到與‘道’完全地融為一體。琴人應當置身于這種開闊的自然環境之中;‘雖身列廊廟,必意在林泉’。”[14]53
在老子那里,道是不可描述的,是一種最高意義上的抽象存在。老子曾說,“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具體到藝術來說,極盡鋪排描繪之能事的藝術形式是等而下之的,至高的藝術境界是簡,是縹緲、是虛空。但從繪畫角度來說,《聽琴圖》畫面又要體現“道”的宏旨,又要記事載物,顯然又不可脫離具體形象,畫家那就只能將畫面減到至簡。
四、音與色:意象引發通感
畫面表現中,色調氛圍與樂音之間構成了另一組通感動因。古琴作為雅樂樂器,雖然曾經也被用于伴奏,但由于其所具有的“清嚴”之特性,還是成為文人士大夫寵愛的獨奏樂器。琴音又被糅合進自然超脫,逍遙清凈的美學特質,在藝術直覺的審美層面上安撫心靈或平衡心境。文人們“主張由恬淡之中求得個人生命的超越與精神的淵默寧靜。在琴樂之中,他們所洞悉的是生命與藝術的真髓。是以老子有‘大音希聲’之說,莊周有‘至樂無聲’之說。‘天人相和’的哲學觀念在此已沉淀為一種自然恬淡、虛靜純真的美學理想。這是一種超乎世俗情感之上的精神理念的體驗”。[15]3-4
《聽琴圖》畫面的色調韻味也是引領觀者感官和思維聯動,并以此獲得飄逸的音樂審美通感的原因之一。作品以流暢的線條勾勒形象,然后施以渲染。但渲染控制有度,雖然人物服飾色彩有別,但僅僅是平涂處理,不去強調其明暗和體積變化。人物和樹木所在的水平地面環境僅以淡墨示意性的表現,在絹本固有底色基礎上與豎向的天空空間融合在一起。作品在設色上也顯得自成一格,取墨色為主要輪廓基調,淡彩輔之,使畫面色彩沉著典雅而具書卷氣。畫家對色彩的運用優雅而得體,在絹本載體本色的基礎上,沒有過多的背景渲染,尤其在松樹以上留出近三分之二的空白空間,使得畫面清朗、通透,給人以空寂、寥遠之感。陳振濂如此評析道:“這完全是一種士大夫的格調,雖然畫的是皇帝,而畫風之端嚴也是畫院中的手段。但整個畫面卻沒有絲毫富貴奢華之氣。恰恰相反,是一種深遠、幽靜、簡約、清謐的氛圍。就連設色,也是艷而不俗,……但畫面卻以神態的展現、技巧的精工、構圖的嚴謹與對稱諸因素,更以色彩的皆偏深暗為基調,有效地沖淡了原色組合所帶來的耀眼。更以高松綠竹、靈霄垂掛,設色淡雅,作為色彩的鋪墊層次,凡此種種,都是有著精心處理的痕跡的。”[16]410
這樣的一種追求簡潔清淡的畫面色調,強化出一種與琴聲的精神抽象特質相匹配的一種空靈玄淡。作者意在以琴聲為渲染的主題,巧妙地借助筆墨傳達出“大音希聲”的琴道意境。
五、跋語與意寓:詩文啟示通感
關于這幅《聽琴圖軸》的作者,學界說法不一。由于畫幅有宋徽宗題名與畫押,此作一度被認為是趙佶所畫,后經學者考證,實為宣和畫院畫家描繪宋徽宗趙佶宮中行樂的作品,而圖中撫琴者,正是趙佶本人。陳振濂先生認為《聽琴圖》當然不會是宋徽宗的御筆,最大的可能是畫院高手對景寫生,也對御容寫真,然后上呈睿覽,龍顏大悅,信筆作題;不但御題,還囑蔡京這位權相也作題。[16]409中國畫的獨特文化屬性也體現在詩、書、畫、印的綜合視覺建構上,從多個方面為藝術欣賞通感的實現提供了動因。書畫題跋一方面可以作為平衡畫面視覺結構的手段,另一方面則具有十分明確的主題強化作用。盡管此畫面中已有了作品名稱的題字或作者印鑒,但畫中這些與畫面意境相配的詩句的題寫無疑又為觀者深化對作品的理解展開了空間。位于畫軸正上方松樹之上的這首題詩寫到:“吟徵調商灶下桐,松間疑有入松風。仰窺低審含情客,似聽無弦一弄中。”至少,蔡京的題詩首先有效地表達出一種信息,即畫的作者和題詩者之間的親近的知音關系。其次,詩文在字面意義上以文人間平等交游的層次對宋徽宗的琴藝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如果將這四句詩文單獨拎出來,用在其他文人間撫琴交游題材的畫作中似乎也不會太突兀。可見,所強調的是一種相知相交的文人間的融洽關系,而非等級森嚴的君上與臣仆之間的關系。文字信息中似乎并未有曲阿之嫌,反而洋溢著文人詩文唱和的輕松氣氛。這樣的題跋對于一向以任意率真的處事態度與文人畫家頻繁互動的道君皇帝來說,并不會反感,反而可能正合圣意。
題詩內容顯然體現了蔡京本人的觀畫感受,“松間疑有入松風”“似聽無弦一弄中”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已經進入了從視覺到聽覺的通感體驗之中。當后世之人面對此作時,如果沒有此題詩,人們對于畫面寓指可能還會停駐于相對模糊的審美意象和藝術聯想層面,但一經閱罷詩文,無疑將使得人們洞悉畫面形態所蘊含的寓意,大大延伸了樂音聯想的維度。
六、結語
藝術通感產生的動因隱藏在畫面形態的不同要素之中,但最終依賴于觀者感知過程中對于諸多動因的感知綜合并形成聯想。由藝術通感分析的維度,展開對《聽琴圖》此類畫作的分析,只是藝術賞析方式的門徑之一。或許這種嘗試不可避免地會帶有鑒賞者自身的觀念局限,甚至結論難免存有偏頗之處,但不能不說,這對藝術理論研究方法的豐富是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潘諾夫斯基指出:“‘藝術問題’當然不僅僅限于純形式的價值,它還包括主題和內容的‘風格結構’,詳細闡述它并使之系統化,由此建立一個‘藝術科學范疇’的體系乃是藝術理論而不是藝術史的課題。”[1]25事實證明,即使如潘諾夫斯基這樣著名藝術理論學者,其理論建構也難免被他人質疑對圖像象征意義過度闡釋。但筆者認為,借助多維度的研究視角回歸對于藝術作品結構本體的審美分析和理論闡釋,不失為一種務實的方式,它的確能夠有效地拓展藝術理論研究的深度,使之逐步實現美學闡釋的系統化。
① 藝術通感(Artistic Synesthesia):藝術鑒賞中由對某一門類藝術的感受連帶引起對其他相關門類藝術的感受;藝術創作中由于外界事物的啟發、誘導而引起對藝術構思、藝術手法的感悟。
② 蔡京(1045—1126),字元長,仙游(今屬福建)人。熙寧三年(1070)進士及第。后以奢侈迎合帝意,受徽宗寵信,官至尚書右仆射、太師。金兵入侵時,率家南逃,被欽宗賜死于潭州。
③ 第六品“典雅”:“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蔭,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若可讀。第九品“綺麗”:神存當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虜深。霧余水畔,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蔭。金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第十八品“十鏡”: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唐〕司空圖著,羅仲鼎、蔡乃中注《二十四詩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4、69頁。
④ “聽彈古《淥水》”:“聞君古《淥水》,使我心和平。欲識漫流意,為聽疏泛聲。西窗竹蔭下,竟日有余清。”“對琴待月”:“竹院新晴夜,松窗未臥時。共琴為老伴,與月有秋期。玉軫臨風久,金波出霧遲。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和《順之琴者》”:“陰陰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泠《石泉引》,淡寧《風松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朝課”:“平甃白石渠,靜掃青苔院。池上好風來,新荷大如扇。小亭中何有?素琴對黃卷。《蕊珠》諷數篇,《秋思》彈一遍。從容朝課畢,方與客相見。”以上諸條分別見:張春林編《白居易全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47、471、474頁。
⑤ “對月(鼓琴):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咸寂,月色當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對花(鼓琴):宜共巖桂、江梅、榮莉、檐葡、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艷者為雅。”“臨水,鼓琴偏宜于松風、澗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漪芳沚,微風灑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以上諸條見〔明〕屠隆著《考盤余事》,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