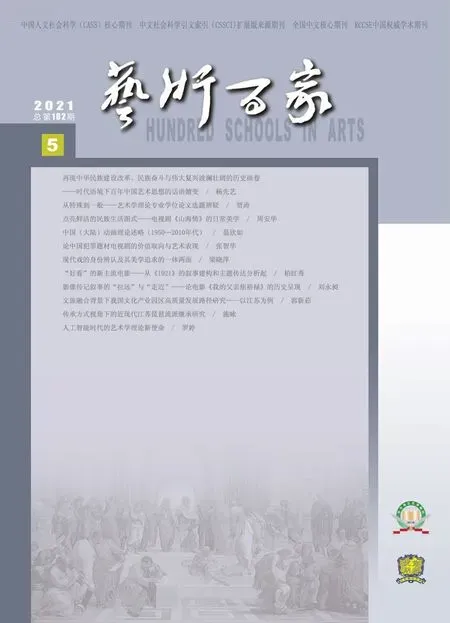中國傳統藝術創作中“詩意”的美學精神追求及其意境表現*
——以南宋院體花鳥畫藝術作品《枇杷山鳥圖》圖像分析為例
姚遠,金納
(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北京 100081)
中國傳統藝術在其發展歷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中國傳統藝術的核心審美價值觀,即融詩心、詩境于藝術創作中的“詩意”的美學精神追求。在中國畫諸門類中,花鳥畫藝術的興盛與繪畫藝術對詩意融入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中國花鳥畫藝術,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以動植物為主要描繪對象的畫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而完整的形式體系和表現體系,成為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典型代表。兩宋時期,花鳥畫因迎合了帝王的審美品位以及宮廷裝飾的需求,成為了宮廷繪畫的主脈,成功地將宮廷生活的奢華富貴形諸于名花異草。而伴隨著宋室南渡,社會政治、文化特點的轉變促使各個領域的藝術都發生了審美趣味上的轉變。南宋院體花鳥畫也在繼承北宋精致華貴的美學表現的基礎上,更趨于內斂與含蓄,強調表意。在花鳥形象的刻畫、筆墨情趣以及造型空間的布局上,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婉約清新的“詩意”追求,以一花一鳥表現自然的無限生機、生命律動,呈現出了具有時代特征的詩意美學精神追求。
這種具有詩意審美的藝術創作風格,體現了中國式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樣貌,見證了中國傳統藝術不同于西洋藝術作品之形式美學特征的構建歷程。
一、中國傳統藝術“詩意”審美觀的構建
(一)詩“意”內涵
中國詩與中國畫是中國傳統藝術中最重要的兩大門類。詩是古代文學的重要體裁,是“耳所聞的時間中表現的音調藝術”[1]4。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奠定了中國詩以抒情為主的基本美學特征。中國古人十分重視詩中的精神審美境界即“意”的表達,“意”包含了“志”與“情”。漢代《毛詩序》將詩、歌、舞蹈、音樂的本質都歸于心志與情感,其中談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2]45詩是人心志的表達,在心里是意志,形成語言便是詩。情感萌動于心中,用語言表達出來,無法言盡則不禁吟嘆,吟嘆也不足以表達便放聲歌唱,歌唱仍感不滿足便不知不覺地舞蹈起來,最終匯聚成音樂。無論是語言的藝術還是聽覺的藝術,心志與情感的表達都是其核心價值觀。
畫,是“目所見的空間中表現的造形藝術”[1]4,初被視為記錄事物形象的方式。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云:“無以見其形,故有畫。”[3]1“存形莫善于畫。”以記錄視覺圖形的功能為伊始,到描繪情節、動態、感受,由“圖”至“繪”,畫承載文化內容與精神內涵的功能也逐漸凸顯。漢代畫像磚,表現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現實生活、禮教孝道等內容,如伏羲女媧、倉頡造字、荊軻刺秦王、孝子趙荀,都是對中國文化的敘述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與文學作品的聯系更加緊密,如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根據漢魏曹植的文學作品《洛神賦》而作,表達了對神話愛情的向往與歌頌。同時期總結繪畫創作思想與規律的論點與專文,如顧愷之所崇尚的“傳神”論;南齊謝赫《六法》中將“氣韻生動”列為品評繪畫的標準之首;南朝王微《敘畫》強調山水畫創作要以“竟求容勢”“寫山水之神”“明神降之”為中心,追求“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的自由的精神審美境界;唐代張璪在《繪境》中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些論斷足見中國繪畫對于自身作品精神內涵的表達以及表情達意作用的愈加重視。
由此,中國詩與中國畫雖為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但無論以文字的形式亦或圖像的形式,二者都不是機械地模仿、照搬現實,而皆是藉自身的藝術“語言”去創造意象,表達心志、傳遞情感,即皆歸于對“意”的追求。
(二)宋代士人自我意識的覺醒
任何民族性格與文化心理結構以及思想傳統的形成與發展,都有現實的物質生活為根源。畫與詩這兩種藝術的關系熱化自北宋末年、南宋初年開始凸顯,這主要歸因于11世紀后半葉文人士大夫詩文書畫活動的日益活躍。而這種現象的產生,從根本上是兩宋社會翻天覆地的經濟變革、科技文化的極其繁榮、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以及漢族政權的異地南遷共同作用的結果。
宋初,太祖為了抑制武將權力,施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才為國家所用,宋王朝大力發展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的社會風氣業已形成,具有文人和官人雙重身份的士大夫階層逐漸出現,一批貴族之外的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制度登上了國家的政治舞臺,士人佐政的同時也成為了文化的旗手。宋王朝特別重視加強思想統治,宋代皇帝都不斷抬高孔子地位,倡導儒學,積極宣揚儒家倫理的忠孝節義,同時提倡儒、釋、道三家的互補與互鑒。由此,受孔儒“隱居以求其志”思想及佛禪“空”的宗旨影響,淡泊名利、放逸自然的人生觀逐步為士人所認同,他們追求高雅的生活,渴望從禮教中解脫。因此,士人以“游于藝”之修養,使風雅成為一時之風。正如趙佶《文會圖》、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等名作中所描繪的,吟詩作畫,談禪論道,賞花望月,都是文人追求精神生活多樣化的形象體現。在這些文人名士眼中,畫與詩皆是尋求個性舒展和精神解放的方式,他們更注重畫中“士氣”即一種“逸格”與“神韻”的表達,而非主題性的闡釋。蘇軾更以“與之可文,其德之糟粕。與之可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4]1057,揭示了德、詩、書、畫之間的關系,這種以心性修養為中堅的“士人畫”概念也由此誕生。蘇軾作為一代文豪以及“士人畫”的舵手,“詩畫結合”是其主要的思想理論之一,具體則體現于下列四段記載: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5]26
“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6]629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6]47
“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7]
這四段記載是蘇軾所指出的一個明確以“詩意”為內核的、詩與畫共通的審美精神體系。在這個體系空間里,繪畫的特征是“無常形卻有常理”、超脫于自然卻更抓住自然的本質,即用繪畫來表現詩歌的時間與空間意象。詩的特征是營造“畫面感”、貴在有言外之旨,即用詩歌來表現繪畫的空間意象。如蘇軾《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賦予動植物之靈性,無聲、靜態的畫面被轉化成有聲、活動的場景,活脫脫就是一副生動的花鳥畫。詩與畫建立起友好的互補關系,這實則是宋代士人自覺意識的體現。士人們想要避免過度卷入自然和物質世界之中,試圖從世間萬物的表象直接跳躍到萬物普遍適用的法則——“理”上,宋代詩與畫就此在“表意”上找到了共通點。文學與繪畫開始相互融合滲透。從形式上,中國畫逐漸出現詩、書、畫一體的形式,詩詞和書法成為畫面形式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畫既具有畫面、書法、印章的視覺美感,又在題畫詩對畫意起到點睛作用的同時,也因其可詠讀而具備了聽覺美感。從內容上,實則為后人開啟了一條以文人思想入畫的坦道,中國畫藝術的審美內涵由此變得更加多樣化、綜合化。宋人在繪畫藝術創作中追求詩性的意向契合,表達情感、抒發心志,“詩意”美學理想、藝術趣味就此被帶入繪畫領域,成為主導的美學標準。
(三)“花鳥”寄興寓情對單純審美的突破
在中國畫諸門類中,花鳥畫中“詩意”的萌芽發生得最早。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很早就已將花鳥剝離了自然屬性而賦予其更多的人文色彩及文化寓意。《宣和畫譜》有曰:“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間,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揪斂,則葩華秀茂,見于百卉眾木者,不可勝計。”[8]310百卉眾木的芬芳艷麗被宋人視為“五行之精”的化身,可見人們在感受其外在美的同時,更深信其內在的力量,這點在詩詞文學作品之中有最直接的反映。戰國時期的屈原、宋玉最初以香草比喻君子的美好人格與神采。唐人齊己《早梅》“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贊頌梅花不畏嚴寒,以此比喻君子高潔堅忍的品格。李白《孤蘭》:“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詠蘭而歸于懷才不遇。兩宋時期,花鳥“比德”“載情”的內涵在被延續的同時,宋人的趣味更加著眼于情節意境的描繪。宋人劉克莊《蘭》:“開處何妨依蘚砌,折來未肯戀金瓶”,明示折蘭而賞已是文人的習慣。林逋《<山園小梅>二首》中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形象地描繪了梅花的優美姿態及其與周圍環境共同構成的美妙情境,折射出宋人對于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即“意境”的關注。
隨著“花鳥”突破了美的范疇,上升到精神層面,花鳥畫也開始步入自覺表現審美感受的階段。《宣和畫譜》的“花鳥敘論”就提出為表現“覽物有得”而“寓興”:“繪事之妙,多寓興于此,與詩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藥,禽之于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于鶴之軒昂,鷹隼之擊博,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于圖繪,有以興起人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8]310強調畫家在花鳥畫創作中也應和詩人一樣寓興于其中,把“奪造化”與“移精神”聯系起來,在表現自然美的同時賦予自然萬物人性的關懷,體現在畫面里便是具有詩性的情趣和語言,幽柔婉轉、細膩耐賞。
(四)以“立意”為重的院體花鳥畫品評標準
隨著士人畫風影響力的擴大以及“花鳥”文化內涵的逐漸凸顯,北宋中后期花鳥畫的品畫風尚開始發生轉變。院體花鳥畫也開始一反前代驕奢浮華的審美追求,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化流露、詩詞韻味以及畫面意氣神韻的詩意表現。
自宋初以來,以精致富貴、刻畫求真為特點的“黃氏”風格一直被視為宮廷遴選繪畫人才的唯一標準,《宣和畫譜》記載:“自祖宗以來,圖畫院為一時之標準,較藝者視黃氏體制為優劣去取。”[9]351直至宋徽宗趙佶時期,將“畫學”納入畫院的美術教育制度中,宮廷在選拔繪畫人才方面有了明確且客觀的考核標準。關于“畫學”取士的內容與標準有兩處記載:“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10]102“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11]3688由此可知,考核以古人詩句為題,將作品的“立意”作為品評作品優劣的首要標準,而以古人詩句為題的考試形式,也正是文人注重詩畫共性的結果。鄧椿《畫繼》記載,文人名士米芾、宋子房先后被徽宗授予“書畫學博士”。畫學博士是畫學選拔環節的主考官,因此他們于繪畫創作的審美取向對考試標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導向性作用。米芾的詩文書畫以不蹈前人為標準,認為山水畫“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12]157,這正與畫學所要求的“不仿前人”即“格法”的觀點不謀而合。史料記載,畫學曾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亂山藏古寺”“踏花歸去馬蹄香”為題。題一“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大多數考生都畫空船停泊在岸邊,或拳鷺于弦間,或棲鴉于船篷上,只有奪魁者畫了一位撐舟人,橫臥在船尾,吹著孤笛,通過描繪舟人的“閑”表“無人渡”之意。“亂山藏古寺”一題之奪魁者畫荒山滿幅,只在山間露出一幡竿以表“藏”意。題三“踏花歸去馬蹄香”奪魁者則通過描繪一群蜂蝶圍繞在馬蹄周圍,巧妙地傳達出“香”這一嗅覺體驗。以詩句命題,表明考核首先檢驗的是畫者的文學素養與創新思維,是否能在創作中恰如其分地營造畫面意境,這種考核方式從客觀上促進了詩與畫的融合,同時也推進了院體花鳥畫詩意化的進程。如何準確而含蓄地表現富于詩意的繪畫境界,使詩性入畫而畫也入詩,已逐漸成為宋代畫家們追求、揣摩的中心課題。
二、具有文學氣息的審美理想和藝術趣味追求: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創作中體現“詩意”的“以形寫神”
對自然與生活的體驗是所有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在繪畫藝術領域,無論是中國畫還是西畫,“寫生”都是繪畫創作的基礎。然而中西方繪畫寫生觀又有所不同,西畫的寫生是將客觀放在首位的寫實藝術觀,追求真實地再現客觀物象,強調結構、透視、光影的準確和諧。相對于西方繪畫,中國畫的寫生講求“以形寫神”,認為形是手段、神是目的。唐代畫家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說的也是在親近自然的同時又超越自然,以達到自然與心靈的完全合一。花鳥畫藝術所表現的亦復如是。
(一)忠于“物理”
中國花鳥畫藝術自五代已具備了堅實的寫實基礎,花鳥畫宗師黃筌是寫實技巧的卓越代表與集大成者。從黃荃所作的《寫生珍禽圖》(圖1)中可見他精湛的寫實技巧,在僅70厘米的絹幅上,畫滿了麻雀、桐花鳳、大山雀、龜、蟬、蜜蜂等20多種動物,禽鳥草蟲的造型與刻畫嚴謹細致、一絲不茍。

圖1 五代 黃筌《寫生珍禽圖》
北宋初期,在“勾勒填彩,旨趣濃艷”的黃氏畫風影響下,花鳥畫寫實美學的地位被更加重視。評論家郭若虛就曾提出畫花果草木應知“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后先,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且畫鳥類應當“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必須融會,闕一不可”[13]34。花鳥畫家趙昌為了掌握花的情態,常于清晨朝露未干時,圍繞花圃,仔細觀察花卉的形態,及時記錄摹寫,人謂其畫“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14]69。另有以畫猿猴著稱的易元吉,曾跋山涉水到荊湖地區的深山里觀察猿猴獐鹿的生活習性。與此同時,宋代畫院的設置為花鳥畫創作提供了無比優越的人文環境,畫家能在皇家園林中潛心觀察四季花草樹木、珍禽異卉的千姿百態,探究花草珍禽的物種特性。宋徽宗酷愛書畫,對花鳥畫的寫實性要求極高,要求畫家們重視對生活和自然細致入微的觀察與表現,描繪對象要力圖做到符合自然法則。據記載,龍德宮建成后裝繪壁畫,他獨欣賞壺中殿前柱廊拱眼間所畫斜枝月季,認為“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日正中者,無毫發差”,另有對“孔雀升高,必先舉左”的深入觀察,使“眾史駭服”的故事已口口相傳。追求細節的真實、對自然的忠實一度成為宮廷畫院的重要審美標準。此時花鳥畫的寫實能力已達到空前絕后的水準,但仍停留在對直觀感相的寫實,并未完成對于生命精神的傳達。
(二)體會“物情”
至南宋,花鳥畫的創作秉承了北宋“精微于物理”的寫生觀,畫家們在創作時依舊秉著“窮理盡性,事絕言象”的理法精詣,對生活和自然進行極其精細入微的觀察體驗。在此基礎上,又將客觀形象與主觀的情感、意念聯系起來,畫家們筆下的花鳥形象不僅做到寫形,更寫花卉鳥蟲禽獸生動之狀、生意之態。畫面生機盎然,生命意志蘊含其中,從而使形象具備了某種意象的指向以及抒情的體驗。
《枇杷山鳥圖》(圖2),絹本設色,縱26.9厘米,橫27.2厘米,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南宋孝宗淳熙年間畫院畫家林椿所作,是南宋院體花鳥畫精品。《圖繪寶鑒》記載:林椿,錢塘人,孝宗淳熙(1174—1189年)時畫院待詔,工花羽翎毛,“師趙昌,傅色清淡,深得造化之妙”[15]858。清人吳升在《大觀錄》中評價林椿:“花細勾染,竹夾葉綠,嵌草蟲,描摹生動。具有天趣,氣韻奕奕古潤,絕無院體。”[16]303“絕無院體”說明林椿的花鳥畫已呈現出與北宋“宣和體”“勾勒填彩,旨趣濃艷”畫風完全不同的新風貌,這些新的風貌則體現在“生動”“天趣”“氣韻奕奕古潤”。而這種活躍在作品中的生命律動、天趣盎然以及神采風韻,正指向一種高級的、具有文學氣息的審美理想和藝術趣味的追求——“詩意”。

圖2 南宋 林椿《枇杷山鳥圖》
《枇杷山鳥圖》繪初夏時節,枇杷樹的一株枝干上結滿碩果,相鄰的枝干上站立著一只繡眼鳥,正在專注地看著枇杷果上的兩只蜂蟻。畫面中,不同物象的造型與質感都得到了逼真的描繪。繡眼鳥身姿小巧,外形的蓬松圓渾被凸顯出來,造型十分可愛。鳥周身的羽毛用細筆勾勒,硬挺的翅羽、蓬松的軟毛以及纖細的鼻須,面面俱到,皆勾畫得一絲不茍、質感逼真,眼圈周圍白色絨狀短羽的刻畫更見神功。葉子的正面用深草綠分染、再用草綠色罩染,突出其褶皺與光澤,蟲眼枯損處的缺合也描繪精細。樹干用濕筆淡墨烘染,再用濃墨和石色多次積染,細致而巧妙地描繪出樹皮斑駁的肌理及樹干的結構轉折。物象的生動刻畫以及精微熨貼的表現,都歸功于畫家在創作中秉著“窮理盡性,事絕言象”的理法精詣,重視對生活和自然細致入微的觀察與表現,孜孜不倦地踐行著一絲不茍的寫實精神。
而南宋院體花鳥畫在繼承北宋寫實精神的基礎上,更是把對“寫實性”的研究與實踐發展到了極致。將林椿的《枇杷山鳥圖》與北宋黃氏風格的作品作一比較,即可見南宋院體花鳥畫對“形”的研究與實踐,具備更寬廣的圍度。《枇杷山鳥圖》中的枇杷果鮮嫩飽滿,被枇杷果壓彎的枝干隱然有搖曳的動感。樹葉有巧蠹,彰顯著四季的輪回、生命的周轉。離近仔細觀察畫面,發現枇杷果上還趴著兩只蜂蟻,寥寥幾筆點綴而成,實在妙哉。蜂蟻垂涎于鮮嫩飽滿的果實,卻被剛停落在枝頭的繡眼鳥發現了,它定眼注視著枇杷果上的兩只蜂蟻,瞳孔的點法神靈活現,實為“點睛之筆”。繡眼鳥靈巧的身體微微前傾,好像正等待時機要“有所行動”,畫家對物象神情動態的刻畫惟妙惟肖,充分再現了自然之態的生動,畫面處處滲透著蓬勃的生命朝氣。
相較于北宋院體花鳥畫“以形寫形”的寫實方式,在詩意化影響下的南宋畫家們更強調“以形寫神”的寫實精神。以自然為參照物,從“我”的角度去觀察體驗對象。對“形”的塑造已開始擺脫北宋過分嚴格的寫實要求,花鳥草蟲的形象已不再只關注于“翎毛諸禽形態名件”的精準描繪,也不再是嚴格遵循自然常態的標本式,而是具有本真的、情緒化的特征。在“形似”的基礎上,趨重于物象“精神”的表達,更加關注畫面所要傳遞的情緒與氛圍,從而使形象多了一份自由活潑。正如《枇杷山鳥圖》畫面里撲面而來的鮮活的生命感,觀畫的同時,仿佛能聞見初夏里彌漫在空氣中的甜果香,聽見鳥兒動聽的鳴聲,正所謂“花如欲語,鳥如欲飛,石必崢嶸,樹必挺拔”[17]33。畫家不僅是表現動植物的生態,更是抓住了對象神態、動態的微妙之處,憑觀照自然之心,由對物象“物理、物態”的概括總結逐漸升華至對“物情”的體會,以花鳥形象的“生姿”寫花鳥之“生機與生意”,進一步拉近“我”與對象的距離,進而直探此情、此景下的生命本質,以花之枯榮、葉之向背、鳥之啼笑鑄成詩一般的語言。
三、“筆情墨韻”: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創作中對于筆墨語言的意境美學韻味追求
“筆墨”是“形”的載體,魏晉南北朝謝赫《古畫品錄》中提出“六法”,其中有二法“骨法用筆”“隨類賦彩”,強調的則是“形”(用筆)與“色”(用墨)的問題。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中提到象物在于形似,形似須全骨氣,而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運墨而五色具,是為得意”[18]。“形”與“色”歸于“意”,而終落實到“筆”與“墨”。五代山水畫家荊浩評王維的水墨畫“筆跡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反映出他認為用筆的好壞與畫面氣韻格調的高低之間具有一致性。如同在文學創作中,好的文筆、詞藻決定了作品的感染力,杜甫就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贊嘆李白的妙筆。而筆墨正是繪畫層面的語言表達,筆墨本無情,畫者能傳情,在中國畫創作中,筆墨的好壞決定了畫面格調的高低。
花鳥畫對于“筆墨”的探索可追溯至五代花鳥畫家徐熙,宋人曰“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不似黃筌嚴謹精細的用筆,“落墨”是徐熙繪畫的最大特點,下筆自然不作謹細描摹,頗能表現動植物之風神情狀,畫面洋溢著野逸情趣。可以說,“徐熙野逸”為花鳥畫對于“筆墨”的美學關注播下了種子。至北宋崔白、吳元瑜在創作中超越院體范囿,“稍稍放筆墨以出胸臆”,表明院體花鳥畫已開始關注筆墨語言的情感表達。南宋院體花鳥畫在不偏離法度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了對于筆意的要求,其中包含了行筆勾勒的豐富變化以及在著色渲染中對“水”的把控。
(一)行筆勾勒,妙趣橫生
縱觀《枇杷山鳥圖》整幅畫面,用筆工整細膩、敷色明麗,是黃氏風格的延續。然而黃氏風格用筆工整規范,刻畫精細逼真,但過分刻意求工,使造型顯得拘謹,也有萎靡柔媚之嫌。相較于黃氏風格的嚴守法度,《枇杷山鳥圖》中的筆墨章法雖嚴謹卻也變化豐富。線條由細膩中求疏朗,遒勁中見溫潤,枝干、果實、葉以及繡眼鳥通身不同區域毛色的質感,處于情節之下的姿態,均有不同的行線與力度,既嚴格地把握物像,又在筆鋒筆力的運用上出神入化。繡眼鳥以纖細的筆法勾勒輪廓,鳥周身羽毛的勾勒虛入虛出,柔軟的絨毛與堅挺的尾羽一并躍然紙上,在質感上形成對比,而鼻須的勾勒更是簡勁勻凈,絲毛的筆觸及羽片的層次清晰分明。鳥嘴的線條用筆堅定,線條刻畫干凈利落、挺拔而有力度,嘴部堅硬的質感呼之欲出。
樹干輪廓的勾勒用側筆中鋒,粗細有變化,行筆頓挫有力,留有飛白。特別是在枝干轉折結痂處,注重用筆的提、按、頓、挫,充分表現樹干蒼勁、干澀的質感。枇杷葉外緣的用筆挺拔有彈性,波浪線凸起處提筆線條細,凹陷處頓筆線條粗,極富節奏變化。通過葉子莖脈線條走向的勾勒表達出葉面的凹凸起伏、卷皺斜出,同時又符合透視原則。枇杷果的線條用筆更加精妙,不是用毛筆簡單地畫一個圓圈,而是表現為線條靠近果子根部與枝干的連接處時較粗,在靠近果子頂部時則較細,畫面通過一根線條即神奇地表現出果子的球體結構,已完美詮釋了中國畫用線表現體積、空間的獨到之處。
(二)色彩渲染,濃淡相宜
院體花鳥畫的筆墨變化不僅施用于勾勒輪廓,色彩的渲染同樣要求體味筆意。《枇杷山鳥圖》中對色彩的渲染,以自然的色彩為寫照,力求表現自然之美。21個枇杷果被分為三組,畫家充分考慮到環境色的影響以及色彩冷暖對比,用深淺不同的淡赭墨分染果子之間接觸的部位,緊鄰葉子的枇杷果又以石綠分染呼應綠葉的顏色。枇杷果均用黃褐色罩染,豐滿有光澤,且近處顏色淺,遠處顏色稍重。冷暖、明度的變化使21個枇杷果之間產生前后、上下的空間關系,繁而不亂,錯落有致。
整幅畫面的色彩渲染,畫家對于石色及“水”的運用與控制恰到好處,最應稱嘆。樹枝先經濕筆淡墨烘染后,再以濃墨積染,趁濕沖入石綠,在墨、水色、石色的碰撞與渲染中,枝干于粗糙斑駁中見秀潤。樹葉的渲染更加得體自在,正葉用深草綠沿著葉脈的線條進行分染,草綠罩染,葉的厚度及溫潤被凸顯,而后用石綠提染,則為綠葉又添生氣。此時,若石綠過濃,畫面生硬少滋潤,缺乏生氣;過薄,則不能表現樹葉在夏日里的翠勁有力、生機勃勃。在這個過程中,對“水”的掌控極為考驗畫家的功力,需要在節制與縱容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同時,在樹葉的設色技巧上,葉尖及邊緣部分刻意洗淡一些顏色,這便在密致的層染中留出一絲輕松,更顯夏葉的疏放之美。
畫家對鳥體結構的渲染同樣十分精彩,鳥羽的暈染熨帖,用筆步步精湛。背及頭部的絨毛經過草綠分染打底,再罩染草綠色,色不壓線。黑色的翎毛用濃墨層層渲染。胸及腹部之間的銜接處用淡赭石暈染,再以薄白粉渲染,顏色邊緣的處理幾乎不著痕跡,虛實精當,色澤豐盈秀潤毫無滯礙,妙不可言,詮釋了“淡妝濃抹總相宜”的美妙境界,更足見畫家對于用筆及物象結構的嫻熟把握。
整幅畫面中,用筆的豐富變化、色的渲染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對“水”的節制或縱容,使畫面中的元素避免了“匠氣”的單調與刻板。對個體精微熨貼的生動描繪,以及個體與整體在筆墨關系上的統一與對比,突破了院體花鳥畫最初勾勒填彩的裝飾意味,也表明畫家對于繪畫語言內涵的理解更趨成熟。藝術作品豐富的筆墨語言包含了物象內在的韻律表達,更包含了畫家的人格修養,當二者兼備時所詮釋出的筆情墨韻,便是一股無形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精神氣質,也是一種鮮活的、具有生命感的詩意律動。
四、“布景致思”:在藝術空間布局上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詩意境界的精神表達
每一種藝術都可以表現出一種空間感。中國園林藝術在這方面有最典型的表現,“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1]187這同樣是中國書法、繪畫、詩歌、音樂、舞蹈等一般藝術的特征。就繪畫領域而言,空間的布局是中國畫作品意境構成的重要因素。中國畫里的空間構造,并非西畫中常運用光影的烘托之法或是幾何透視法,而是一種具有詩性、樂感的節奏安排。隨著花鳥畫這一繪畫門類的不斷深入發展,加之南宋特殊的時代背景與地域特色,南宋院體花鳥畫開始專注于獨到的構圖形式語言,在畫面空間的布局結構中努力探索新的形式法則,展現了中國畫特有的空間意識。總體而言,南宋院體花鳥畫在空間的布局上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意境界,呈現出“小景”布局的特點,具體表現在畫面空間形式的精簡以及空間內容的剪裁取舍兩個方面。
(一)空間形式的精簡
南宋院體花鳥畫畫成屏壁上的巨幅較少,而裱在屏風上的小幅花鳥以及冊頁、扇面之類的小幅作品形式更為流行,畫作均尺幅不大,玲瓏可愛,《枇杷山鳥圖》即為典型的冊頁形式。畫幅偏小,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市民文化的勃興,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日益多樣化,使南宋社會更加呈現出世俗化平民化的趨勢,這種世俗化的趨勢同樣存在于繪畫領域。繪畫的重心逐漸開始下移,由廟堂、佛窟、寺院、宮廷融入平民日常活動的場所,與通俗文化相觸碰,被人們用來收藏、贈禮或裝飾。作品大多為形制靈活小巧的畫幅如扇面、冊頁等,與傳統長卷、立軸繪畫大異其趣,并由此而盛行。南宋詩人陸游就曾感嘆:“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另一方面與當時社會的治世思想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北宋,在佛教和道教的沖擊下,儒學思想家們開始重新認識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儒家思想中蘊含的人文主義和理性精神,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也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義,開創了中國古代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格局,朱熹的理學開始逐漸顯露出來。至南宋理宗朝時,理學即被欽定為封建正統思想和官方哲學,確立了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之后便開啟了對中國思想與學術領域長達千年的影響。理學家們探討“性微精一”,在美學觀上崇尚“真”與“淡”,以簡樸為尚。以至于在這個時期,無論是詩詞還是繪畫,其風格都漸趨于內斂,開始變得理性、精致,處處透著佛家的自省,“以方寸之心去牢籠天地,以一花一葉看浩瀚宇宙”。
(二)“以小觀大”的空間語言
與北宋院體花鳥畫整體且豐滿的構圖不同,南宋院體花鳥畫選擇“以小觀大”的視角,在構圖上極有剪裁、有取舍地從場景的某個角度或物像的某個局部出發,著意經營布局。在畫家筆下,自然被馴服、被理想化,除了展現最吸引目光的景致之外,其他現實中本應存在的元素都被畫家摒除。題材、場景、對象、畫面都變小了,一株臘梅、半截樹枝便可組成畫面的主體內容,也占據了畫面的大部分,呈現出一種“特寫式”的“小景”描繪。這使繪畫更具概括性、象征性,畫面所展現的抒情性也更加濃厚。繪畫創作不再是著眼于博大的精神與恢弘的氣勢,而是更關注于物象的本體描繪及生命內涵。
《枇杷山鳥圖》是典型的特寫式小景構圖。枇杷的枝干由畫面右上方向左下方呈“S”形延伸,枝干末梢結了一串成熟的枇杷果,枇杷果的體積占據了畫面的主體。為了不使畫面的重心偏移下沉,枇杷果的整體勢態微微抬起向左上方,與右上方繡眼鳥低頭的姿態相互輝映。而近處的左右兩片大葉子與繡眼鳥形成一個穩固的三角形,這樣,畫面整體的氣韻得以流動起來并聚焦到畫面的中心點,既突出了枇杷枝干的生長之勢,也襯托出了繡鳥已成為畫眼在吸引觀者的視線。
畫面中每片葉子的形態和朝向都不盡相同,老葉、新葉、側葉、反葉、正葉巧妙地穿插于果實與樹干之間,不僅使葉子在造型上豐富多彩,同時通過利用每片葉子的位置與朝向,為畫面作出了空間上的拓展與延伸。葉子指向不同的方向,實則為畫面打開了多個方向上的空間,畫家還利用蟲蝕葉之洞,透過洞看見了被遮擋的樹枝(圖3),增加了含蓄的空間感,正所謂“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萬里可論”[19]396。畫家通過對畫面元素有章法的排列組合,巧妙地布置了畫面的均衡得勢。平穩中不乏勢的變化,借勢傳情,以小見大,以少見多,以極其精煉的形式語言精心捕捉到了近景中所蘊藏的美,做到了“狀難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盡之意溢出畫面”。咫尺畫幅,卻得以以此畫作觀照畫外的無限天趣。

圖3 南宋 林椿《枇杷山鳥圖》(局部)
這種特寫式的構圖表現,實際是畫家在藝術創作過程中主動實現的對自然之景由宏觀到微觀的再認識。與此同時,南宋院體花鳥畫還出現了以馬遠的“馬一角”構圖樣式為代表的花鳥與山水相結合的小景構圖。如馬遠的《梅石溪鳧圖》(圖4)中,作為畫面主體的石崖及梅樹被置于畫面的邊角處,畫面中留有大片的空茫用以訴說言外之意,蘊涵著朦朧且神秘的美學意象,由此把畫面的主題籠罩在一片感性之中。這種構圖方法貼合了江南山水煙雨迷朦的自然之景的實際表現需求,也是對于宏觀與微觀之間相互關系的微妙處理。

圖4 南宋 馬遠《梅石溪鳧圖》
南宋院體花鳥畫簡約、純粹的布局,是畫家自覺意識的流露,體現著畫家的匠心獨具。看似是對自然景象的客觀描繪,實則在表達一種人生理想,即把人們審美感受中的理解、情感、想象引向一個無限飄渺的境界,類似于美學家李澤厚先生曾談到的詩、畫及各類藝術都具有的一種美的類型和藝術意境——“無我之境”。這便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造境,藝術家與觀者都在這種模糊的、隱晦的情感中,在這個永恒的空間里,進行著無窮無盡的自由想象,正可謂意在言外。
五、結語
不同于西洋美學以“和諧、秩序、比例、平衡”為中心,中國傳統藝術作品以構建“詩意”的美學精神和個人價值追求為中心,由此突破了自然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片面性,以華夏土地所孕育的獨特的審美方式和中國式的賦、比、興手法,形象化地展現了東方世界的宇宙觀和自然觀,創造了中國式的現實主義藝術創作思想和藝術作品表達形式,實現了藝術作品中形式(造化)與內容(心源)的高度統一。宗白華的《美學散步》中曾就“藝術的定義和內容”談到:“藝術家創造一個藝術品的過程,就是一段自然創造的過程,并且是一種最高級的、最完滿的、自然創造的過程。因為藝術是選擇自然間最適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使他成了人類最高精神的自然的表現……藝術本就是人類——藝術家——精神生命的向外發展,貫注到自然的物質中,使他精神化、理想化。”無論是中國繪畫、書法、詩歌、建筑、戲劇等各種藝術門類之中的哪一個,中國傳統藝術“詩意”的創作手法都貫穿其中,始終以抒發人的情感與心志、展現“生命的律動”為目標,并依此使中國藝術以獨特的姿態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
中國傳統藝術創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了不同的風格面貌,并承載了特定的文化內容。在南宋時期,畫家們自覺意識、主觀情感的喚醒與投入,使院體花鳥畫在承襲北宋院體花鳥畫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統一契合的同時,更進一步擴展為自然主義、理想主義與個人主義相統一、相契合的肇端,使花鳥畫不僅成為一種寫實的藝術,更是成為最空靈的精神表現形式之一,使心靈和自然完全合一。“細節的真實和主觀繪畫元素間關系的協調同時并舉,使南宋畫院花鳥畫超越庸俗和呆板(匠氣),也沒有流于抽象和虛空(書卷氣)。相反,從形似中求神似,由有限(畫面)中出無限(詩情),與詩文發展趨勢相同。”[20]241形神兼備的造型、豐富飽滿的筆墨、簡約純粹的布局,共同匯聚成為南宋院體花鳥畫清新婉約、含蓄內斂的美學格調。在畫面中,畫家以精妙的手法、巧妙的構思給觀者構建了一個充滿情調、思緒、想象的詩意空間,正所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由此探入了生命節奏的核心。在審美情趣方面形成了富有詩意的審美觀,這促使南宋院體花鳥畫從眾多繪畫門類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一朵爭妍斗芳的奇葩,并以其特有的美學境界創造了中國花鳥畫藝術的歷史高峰,促使中國傳統藝術創作中“詩意”的審美追求及其意境表現在這一時期有了典型的體現,此后,這種“詩意”的美學精神追求也日益成為了中國藝術的基本美學準則和民族特色。
近觀當代藝術創作,許多藝術作品雖然在題材、表現手法上日趨豐富,但已很難從中追慕到它在古典時期曾經有過的品格與神采,這正是因為創作者們僅僅沉迷于技巧層面倫理的延續,卻忽略了對客體生命價值進行視覺形式轉化及其深刻表現的探究。因此,中國傳統藝術創作中的“詩意”美學留給后人的不僅是技法問題,更是文化層面的思考。在當代,藝術創作要在繼承中不斷創新。但對于傳統的繼承,并不是取其貌,而是需要理解蘊藏在藝術形式語言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內涵,體會這一藝術形式對于生命的思考和自然的關注。同時,中國傳統藝術所表達的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所展現的“詩意”特征,是根基于中華民族文化品格的基本哲學。因此,我們身處在這個經濟飛速發展、全球日趨融合的時代,面對著“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傳統藝術的文化價值標準和美學精神追求,充分認識中國傳統藝術發展的路徑,努力創作出以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形式、內在美學精神和價值追求為核心,且符合時代特征與審美趣味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