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醫(yī)生到“大”醫(yī)生
韓萌

學醫(yī)的愿望促使我在高考志愿的填報中清一色選擇了臨床醫(yī)學專業(yè),同時放棄了所有調劑的可能。正是這份對臨床醫(yī)學的執(zhí)著,使我有幸被南昌大學臨床醫(yī)學與生物醫(yī)學的中英聯合培養(yǎng)項目錄取,現在我是一名醫(yī)學專業(yè)的大二本科生。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這學期的所有課程,包括微生物、藥理、發(fā)育及免疫等都開啟了線上教學模式,當“核酸檢測”“瑞德西韋”以及“RNA”等與病毒有關的專業(yè)詞匯出現在我的課堂時,使我覺得自己離疫情戰(zhàn)場那么遠,又那么近。
這個長長的寒假加春假使我有時間認真思考、沉淀自我。
“權威醫(yī)生”
童年的小孩子總是幻想自己成為大人的樣子,我小時總幻想自己成為醫(yī)生的樣子。在與小伙伴的游戲中,我總是要扮演醫(yī)生的角色,而我們的游戲內容幾乎總是醫(yī)生和病人那些事。
為了滿足角色的真實性,我的道具來自于從媽媽科室里拿到的紗布與拔了針頭的針管和聽診器。小伙伴們則從家里拿來常用的藥品和用來固定針管的膠帶。我笨拙地穿上從媽媽那里淘來的廢舊白大褂,將頭發(fā)梳成大人模樣。百試不厭地打針情景與奇形怪狀的包扎造型是我童年回憶的典型代表。
作為“資深演員”的我深知,游戲要逼真,少不了專業(yè)名詞的“扶持”。我瘋狂翻找母親的各種工具書,其中的《胎兒畸形診斷學》是我作為“權威醫(yī)生”的撤手锏。這本書中會有一些有略帶恐怖的圖片,他們的背后可能是一個個不幸家庭的縮影。我時常會在我們的游戲中說出書中的一些專業(yè)名詞,然后再頗有自信地翻出對應的照片,“病人”看到照片后的反應都是無一例外地全部跑開。這時的我則會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照著母親的樣子向她們一一講解。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游戲開始被貼上幼稚的標簽。雖然后來不再扮演醫(yī)生,但是那種“偷師”和模仿帶給我極大的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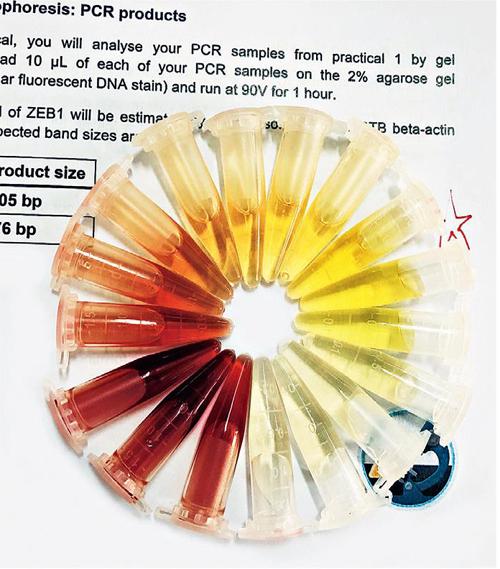
從幼兒園到小學,我的生活里總有新事物不斷出現,但唯一不變也不可或缺的是在媽媽所在的科室“陪伴”她上班。其實說陪伴也有些牽強,說是等待可能更為恰當,但一些時候的等待則悄悄拉近了我與醫(yī)生的距離。
一次,一位阿姨帶著一個貌似跟我年齡相仿的小朋友來看軟骨。我偷偷得聽到路過的實習醫(yī)生說到,“那個小朋友感覺真的和正常的小朋友的軟骨不一樣”。小朋友的軟骨其實與成年人的軟骨有很大的區(qū)別,因此治療小朋友的軟骨癥狀就需要對照小朋友的標準。于是,一個想法在我心里萌生,我和那個小朋友差不多大,我不就是最好的參考標準嗎?找了一個媽媽休息的間隙,我偷偷溜過去問:“媽媽,我可以當作正常孩子軟骨的對照嗎?”
媽媽當然拒絕了我的,原因是作為醫(yī)生她們明確地知道小朋友正常軟骨的標準。“醫(yī)生可真厲害!”當時我的腦子里只有這一個想法。
小小的我,心里描繪的對照應該就是是一會兒看看我的,一會兒看看那個小朋友的才可以進行比較,卻殊不知醫(yī)生對于人體的熟悉早已超過了我的認知。
一種我連參照物都做不了的無力感席卷全身,有點小失落。但這次之后,我對醫(yī)生的崇拜程度早已榮升到了與哈利·波特同一級別的程度。
患者等候區(qū)里掌握電視遙控器的“霸
在醫(yī)院呆久了,總會為自己找點事情做,所以那時的我在患者等候區(qū)里承擔了一份極為重要的任務——操作電視遙控器。我成了患者等候區(qū)的“霸主”。
等候區(qū)電視的存在是為了讓患者在漫長的等待中打發(fā)時間,其實遙控器也并不是由我掌握在手,只是由于長期呆在這里的緣故,對這里每一個物品的位置擺放都無比熟悉。
小小的我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和媽媽同一科室的醫(yī)生總會開玩笑道,說我總是讓許多病人陪著我看動畫片。其實不然,對于電視的掌控我其實有自己的小秘密。當看到有漂亮姐姐無奈等待時,我會把電視頻道調到湖南衛(wèi)視讓肥皂劇與她作陪;當看到和我同齡的小朋友,我會調到少兒頻道,其余時間調到中央一臺,調和大眾口味。
如果問我的童年剪影是什么?那就是在密密麻麻患者中間坐著那個拿著遙控器的安靜的我。
與其說我在控制著遙控器,不如說我在觀察著這里的人。每一個患者都有屬于自己的故事,但如此不同的他們卻坐在這里為了同一目標——健康。我見過帶著孩子心懷忐忑、坐立不安的母親,我也見過為陪伴老人難忍淚水、不知所措的子女們。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八十多歲病重的老人由自己的兒子背到等候區(qū),因為疼痛難忍只能用輕哼來表達。
我至今都無法忘記這位老奶奶的臉色,那種異于常人的土黃色是我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了痛苦的存在。
不管先前對醫(yī)生是角色扮演也好,是崇拜也罷,但如果說想成為醫(yī)生的想法確實是在某一特定時刻爆發(fā)的,我想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刻。
成醫(yī)則勇
醫(yī)學生考試月常以背誦為伴,醫(yī)學生的周末常以上課為主,盡管過得辛苦,但一直以來,我對當醫(yī)生這件事從未動搖過。
醫(yī)學專業(yè)課更是出了名地不輕松,那一本本厚厚的“藍色生死戀”是我醫(yī)學小書包里的全部內容。當然醫(yī)學生的世界不僅僅有“藍色生死戀”,與之相伴的探索性動物實驗也是培養(yǎng)未來醫(yī)生重要一課。
我在高中階段曾有幸走入實驗室,在那里我見到了小白鼠的腦缺血模型。作為腦缺血模型的小白鼠會呈現出不斷追捕自己尾巴的奇特現象,我對之印象深刻。這一次與小白鼠的初相遇,使我在日后作為醫(yī)學生時與小白鼠再見面時,比我的同學都多了一份熟悉感。這種熟悉感也讓我在醫(yī)學實驗中更加得心應手。
小白鼠的恐懼并非人人都可以克服,與我同組的伙伴對小白鼠就有一種先天的恐懼。她原本有低血糖,在一次練習給小鼠灌胃操作時,因操作不當,她手中的小白鼠突然開始口吐鮮血,而受到驚嚇的她突然因低血糖而昏倒。從那以后,同時抓捕兩只小白鼠到實驗臺以及適時處死兩只小白鼠成為了我的常規(guī)操作。
其實這次疫情對于醫(yī)學生的我們來說也是一次隔空仿真考驗,這種考驗既關乎醫(yī)學技能,也關乎從醫(yī)勇氣。幾個月里,無數的“醫(yī)護逆行者”奔赴武漢,援鄂醫(yī)療隊離開武漢后,各地機場以民航界最高禮遇“過水門”迎接援鄂英雄們凱旋,為他們“接風洗塵”。我在想,醫(yī)生真的是無所畏懼嗎?有人說為母則剛,我說成醫(yī)則勇。哪有人天生勇敢,只是心中有信仰則會大不一樣吧!
作為現在的“小”醫(yī)生,盡管我還在攀登醫(yī)學的路上,但我將永葆信仰,勵志成為日后危機事件沖到最前線的“大”醫(yī)生。
責任編輯:鐘心
作為現在的“小”醫(yī)生,盡管我還在攀登醫(yī)學的路上,但我將永葆信仰,勵志成為日后危機事件沖到最前線的“大”醫(y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