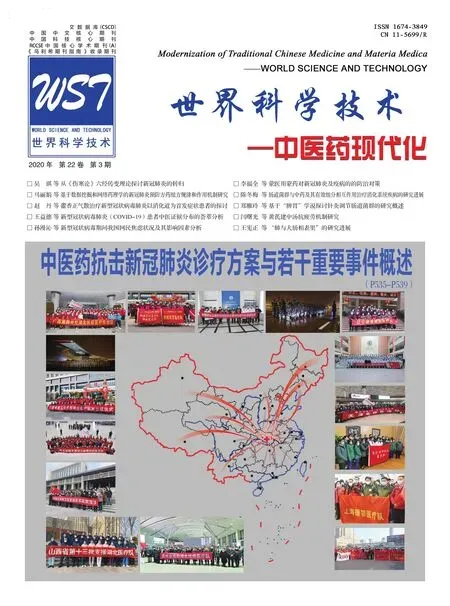中西醫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研究進展*
臧明泉,任建琳,張瑩瑄,毛發江,張 功,陸鑫熠,靖 琳,左 玲,史雯妍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市中醫醫院 上海 200071)
新型冠狀病毒屬于β屬冠狀病毒,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命名為2019-nCoV,2019-nCoV直徑在60-140nm,基因組含有約29.8 kb核苷酸,其中擁有14個開放閱讀框(ORF),可以編碼27種蛋白,2019-nCoV與SARS-nCoV(SARS冠狀病毒)在氨基酸水平上較為相似,同時存在差異,二者差異主要體現在輔助蛋白種類和氨基酸數量等方面[1-2]。COVID-19與SARS均有較高傳染性,COVID-19可通過飛沫經呼吸道傳播或密切接觸等方式傳染,COVID-19原始傳染源仍未確定,COVID-19患者是主要傳播源。患者早期可有發熱、干咳、乏力等表現,部分患者出現流涕、咽部不適、腹瀉,血細胞分析提示早期患者常有白細胞正常或降低,淋巴細胞數量減少,C反應蛋白增高;COVID-19患者體液或者分泌物、排泄物標本進行2019-nCoV核酸檢查常提示陽性。胸部X線或者CT檢查以多發斑片影和間質變化常見。在當前防治中,COVID-19確診需要2019-nCoV核酸檢測陽性或者基因測序高度同源的報告支持。
1 COVID-19流行病學相關研究

圖1 COVID-19患者治療前后胸部CT圖
流行病學研究有助于明確COVID-19潛伏期、掌握常見癥狀、排除疑似患者。前期流行病研究發現,COVID-19潛伏期通常在14天內,但鐘南山團隊領銜的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有一例患者的潛伏期可能長達24天,盡管該研究多數患者的潛伏期在3天內。該研究納入1099例COVID-19確診患者,其中患者在入院前出現發熱的比例約43.1%,而入院后出現發熱患者的比例升高至87.9%,這提示對于未發熱的疑似病例仍不能掉以輕心。確診患者中常見癥狀是發熱、咳嗽、乏力、咳痰、惡寒、關節不適等。需要注意的是,COVID-19患者除了針對肺炎治療外,還需要對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急性腎損傷、膿毒癥性休克提早干預,因為三者是該研究中COVID-19引起的常見嚴重并發癥。該研究進一步確認了2019-nCoV發生人際傳播的能力,明確了多數COVID-19患者出現的癥狀和體征以及影像學和實驗室異常的意義,為當前疫區加速確診COVID-19提供支持[3]。Zhang MQ等對北京發熱門診的9位COVID-19患者進行回顧研究,發現9例患者當中有8例出現發熱,5例出現干咳,而具有咽痛、疲勞、身體酸痛患者的比例均是44.4%,約66.7%的患者出現外周細胞計數異常,其中以單核細胞增多,淋巴細胞減少為主。而該研究樣本中有7位患者的HRCT顯示異常,主要表現為雙肺毛玻璃滲出[4]。針對COVID-19患者胸部影像改變,姬廣海等收集并研究了湖北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收治的45例COVID-19患者胸部CT資料。該患者樣本群體中,在發病3天內進行CT檢查的29例患者CT提示:約有72.41%的患者胸部CT出現磨玻璃密度影,約89.66%的患者胸部CT出現不規則形或扇形病灶。45例COVID-19患者中有38例患者在10天內進行了CT復查,結果提示:約65.79%患者病灶范圍縮小(示例見下圖1)[5]。根據最新解剖研究,COVID-19患者胸部CT所示的磨玻璃密度影在解剖上對應肺部炎性病灶,呈現為灰白色斑片狀,在該解剖研究提示“COVID-19主要引起深部氣道和肺泡損傷為特征的炎性反應”(示例見下例圖2)[6]。上述研究,初步介紹了COVID-19的潛伏期、早期癥狀、影像和解剖表現,后續科研人員進一步分析患者實驗室指標與病情發展變化之間的聯系。
1.1 COVID-19患者實驗室檢測與病情危重分組相關研究
Huang C等對武漢地區41例COVID-19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人員發現發熱和咳嗽、疲勞是患者的主要癥狀,高達66%的患者曾有到華南海鮮市場的記錄,并且出現家庭聚集性發病樣例。所有患者均有肺炎的CT癥像,其中約55%患者出現呼吸困難,病程發展中位時間約8天;此外,患者血漿檢測提示,入住ICU患 者 與 普 通 患 者 相 比,IL-2,IL-7,IL-10,GSCF,IP-10,MCP-1,MIP1A和TNF-α含量更高,這八種因子含量的差異可能與患者病情進展相關[7]。然而,通過檢測白細胞介素等生化因子含量差異來鑒定COVID-19患者的危重程度卻有結果不一致的研究。Chen L等收集了武漢地區的29例COVID-19患者,并依據臨床綜合標準,將29例患者分為普通組、重癥組和極危組,對患者的臨床樣本分析發現,只有IL-2R和IL-6滿足統計學差異,即隨著癥情加重,IL-2R和IL-6含量依次遞增;與此同時,三組間TNF-α、IL-1、IL-8、IL-10、hs-CRP、淋巴細胞計數及LDH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8]。
1.2 COVID-19患者并發癥

圖2 COVID-19患者解剖圖
Nanshan Chen等集中研究了武漢市金銀潭醫院99例COVID-19患者,在該樣本群體中,有49%的患者曾有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患者平均年齡為55.5歲,有51%的患者有基礎慢性疾病,提示健康人群也容易感染2019-nCoV;盡管有70%以上的患者,接受了氧氣支持、抗生素、抗病毒治療,但難以阻止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導致11%患者因治療無效去世,這提示COVID-19的危重性。令人鼓舞的是在研究結束時,已有約31%的患者治愈出院。此外,研究者關注MuLBSTA評分,該評分被用于預測病毒性肺炎患者的死亡率,而在該項研究中,有兩名去世患者的病情變化適合納入MuLBSTA評分系統進行危險性評價;研究者希望臨床一線進一步考慮采用MuLBSTA評分系統以評估COVID-19患者病情的動態變化,從而提前干預或調整治療措施[9]。相比Nanshan Chen等人的研究,Dawei Wang等人開展研究中COVID-19患者的治愈率上升至34%,死亡率降低至4.3%。該項研究一共納入138例COVID-19患者,盡管上述兩項指標有所轉好,但是約有26.1%患者因病情加重而不得不轉入ICU治療。此外,該標本中的COVID-19患者從首次出現癥狀到發展成ARDS的中位時間僅為8天,提示COVID-19病情進展迅速,而并發癥ARDS、急性心臟損傷、心律失常、休克,尤其應當引起一線醫生重視[10]。
2 抗擊COVID-19的藥物研究現狀
隨著疫情的發展,許多治療COVID-19的新藥正在加緊研發,而一些已經上市藥物的新作用也正被挖掘。磷酸氯喹屬于氨基喹啉類抗瘧藥物,該藥物通過干擾瘧原蟲的DNA轉錄而抑制瘧原蟲增殖,曾主要用于防治三日瘧、單日虐[11-12],該藥亦有多篇臨床報道證實其用于治療風濕病、口腔扁平苔蘚、紅斑狼瘡等[13-18]。2020年2月15日,中國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張新民介紹,科研人員經多輪篩選和進一步研究發現,磷酸氯喹能夠在體外較好的抑制2019-nCoV,而且多個地區醫院開展的臨床試驗初步表明磷酸氯喹能夠在治療COVID-19中發揮一定作用[19]。受限于疫情和研究的進展,目前,仍未有論文性質的報道闡釋磷酸氯喹抑制2019-nCoV的明確機制。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除了利巴韋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抗病毒藥物外,磷酸氯喹已經正式納入治療方案[20]。
沙利度胺能夠鎮靜、止嘔、抑制血管生成、調節免疫,臨床上主要用于抑制麻風反應癥;鑒于沙利度胺具有免疫調節作用,夏景林教授將該藥用于重癥COVID-19患者。該患者入院時主要表現為焦慮、嘔吐腹瀉,同時存在呼吸障礙(氧飽和指數為142左右),狀況危重。因為沙利度胺具有改善患者焦慮,止嘔的作用,故夏景林教授力主在本醫案中使用沙利度胺;沙利度胺干預近4天后患者癥情明顯改善,連續使用該藥14天后患者好轉并順利出院。夏教授認為沙利度胺是促進該患者康復的關鍵因素;經過研究發現,患者在使用該藥后IL-6和IL-10含量降低,故夏教授認為沙利度胺逆轉該重癥COVID-19患者病情可能是通過抑制IL-6和IL-10并增強免疫功能實現[21]。
一項包含99例武漢地區COVID-19患者的研究發現,高達43.4%的患者出現肝損傷,主要表現為患者血樣中丙氨酸氨基轉移酶和(或)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含量升高[9]。針對該情況結合前期研究,丁虹教授認為,COVID-19患者出現包括肝損傷在內癥情惡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COVID-19促發的人體炎癥瀑布,基于該構想丁虹教授提出將具有抑制炎癥的甘草酸類藥物應用于COVID-19的治療[22]。該構想認為,新冠狀病毒入侵人體后引起免疫系統大量釋放多種免疫因子,免疫因子在對抗COVID-19的同時對人體多種器官組織產生免疫傷害,這種難以控制的傷害即炎癥瀑布;根據以往經驗依靠以激素為主的綜合治療并不是最理想方法,所以丁教授采用能夠有效抑制肝炎的甘草酸二胺搭配維生素C和蘆丁作為新的COVID-19治療措施,該方案優勢在于清除自由基、抑制炎癥瀑布、保護肝臟;得益于有個例反饋該方案有較好臨床效果,目前該方案已經在武漢中南醫院開啟正式臨床試驗[23]。
3 COVID-19患者圍手術期治療
3.1 COVID-19患者圍手術期調整
在COVID-19疫情得到控制前,周太成等將疝和腹壁外科疾病依據其輕重緩急分為擇期手術、限期手術、急診手術。對于適合擇期手術的患者,應當建議其待疫情結束后來醫院就診;對于適合限期手術的患者,應當適當處理穩定病情,待疫情結束或患者病情穩定后再行根治性治療,例如腫瘤合并腹外疝氣、切口疝的患者可以先行輔助性化療,之后再行腫瘤根治術;對于使用手法等非手術方式治療無效的急癥性疝或腹部疾病,應當做好及時手術的準備。對于手術方式的選擇,周太成認為,應該充分考慮麻醉及手術醫生的暴露時間和面積。對于疝和腹壁外科門診上出現發熱或者疑似或確診COVID-19的患者,如在轉至定點醫院之前需要急性手術,應該在有負壓條件的手術室進行[24]。
3.2 圍手術期腫瘤患者合并COVID-19的治療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胸外科開展一項腫瘤患者感染2019-nCoV的病例研究。一位61歲因“咳嗽1周,加重伴咳痰2天”入院的男性患者,入院后胸部CT提示:“左上肺軟組織團塊影,未見明顯磨玻璃樣改變”,考慮診斷:左上肺腫瘤性病變(cT2bN0M0),在順利完成左上肺葉切除術+系統性淋巴結清掃術后(術中冰凍病理示:非小細胞肺癌)的三天內未有異常不適,術后第四天以及第六天體溫分別升高至39.2℃、38.2℃,其中第五天體溫降至正常,伴隨乏力,咳少許黃膿痰,無嘔吐腹瀉等癥狀。血細胞分析:白細胞4.97×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5.7%,淋巴細胞百分比10.3%,中性粒細胞4.26×109/L,淋巴細胞0.51×109/L。雖然患者無華南海鮮城相關暴露及發熱人員接觸史,但是發熱后兩次查胸部CT均支持:左肺術后改變;左余肺及右下肺感染。在增加使用更昔洛韋抗病毒和鹽酸莫西沙星抗感染的基礎上,患者體溫雖稍下降,但處于37.8℃水平。隨后進行的病毒核酸檢測提示2019-nCoV陽性,而肺炎支原體IgM抗體和流感病毒A、B型以及其他常見流感病毒IgM抗體檢測均為陰性。隨即患者轉院,在改為鹽酸阿比多爾片抗病毒和靜脈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增強免疫等治療后患者體征暫平穩。該病例提示患者術后3天的出現異常發熱,患者雖訴無華南海鮮城相關人員及發熱人員接觸史,但是患者處于武漢疫區,又有實驗室檢查和影像檢查支持肺炎診斷(高度懷疑病毒性肺炎),即便未拿到核酸檢測報告前,仍然應該迅速做好醫護以家屬人員的隔離及防護工作,及早進行經驗性抗病毒治療,防止病情傳染擴散[25]。
目前COVID-19治療中,患者病情變化較快,可能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血糖嚴重紊亂等,發展為重癥COVID-19。糖皮質激素治療病毒型肺炎干擾糖代謝、引起血糖紊亂,在抗擊SARS已有研究證實[26-27]。羅偉等報道了一例重癥COVID-19合并糖皮質激素誘導的糖尿病病案。患者為43歲的中年男性,有武漢居住史,患有乙肝及早期肝硬化1年史以及高血壓2年的個人史。患者在出現發熱、咽痛、頭痛咳嗽自行服藥未緩解的情況下入院,入院后呼吸困難加重,并持續高熱,隨機血糖9.76 mmol/L,影像胸部CT平掃提示雙肺多發磨玻璃樣滲出影增多。給予頭孢呋辛,利巴韋林后呼吸困難和咳嗽等癥狀未緩解;結合咽拭子2019-nCoV核酸檢查陽性、再次影像學檢查(雙肺滲出面積增加)和血氣分析(PaO261 mmHg)等情況,專家組作出患者當前屬于重癥COVID-19的診斷。隨后采用新的治療方案,該方案包括α-干擾素、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及胸腺法新、甲潑尼龍、免疫球蛋白、莫西沙星,停用頭孢呋辛。但是新方案采用兩天后患者呼吸困難加重,并出現多尿多飲,血糖高達23.8 mmol/L,治療方案又再次微調,調整后的糖皮質激素用量為80 mg(較前之前用量增加一倍),此時患者常規胰島素控制不佳,改為門冬胰島素及甘精胰島素后血糖控制亦不理想(血糖水平處于15~20 mmol/L)。值得關注的是,患者糖皮質激素用量增至80 mg并維持使用三天后,癥情緩解,隨后降低糖皮質激素的用量至40 mg、20 mg各維持使用3天后停用,后患者胸部CT提示病灶明顯吸收,癥情明顯改善,而且隨著糖皮質激素的用量降低患者血糖亦得到有效控制。患者呼吸困難緩解,可能與甲潑尼龍的用量增加后抗炎作用增強相關。因患者沒有糖尿病病史,且其他因素導致血糖升高的可能性較低,故羅偉等認為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是導致血糖升高的主要因素。本病例提示,在治療COVID-19過程中,糖皮質激素的短期服用可能有利于肺部炎癥控制,同時可能是引起血糖紊亂的潛在因素。由于血糖長期升高可能使患者氣道分泌糖增高,不利于肺部感染的控制,故研究者認為,在重癥COVID-19治療中,應該嚴格控制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時間和用量[28]。
4 中醫藥防治COVID-19
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將COVID-19納入中醫“疫”病范疇,并提示感染“疫戾”之氣是病因[20]。中醫對疫病具有深入的認識,并具有豐富防治經驗。《素問·刺法論》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即中醫認為“疫”有較強的傳染性,患者感染后癥狀有相似之處。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提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即吳又可認為瘟疫的病因是一種特殊的異氣,這種異氣與外感六淫不同,并在該部著作中總結瘟疫在致病性、傳染性、危重程度上比普通外感疾病更強。戴天章在《廣瘟疫論》述溫病和傷寒在辨證的異同,同時提出“時疫見證,純表純里者少,表里夾雜者多”,即瘟疫單純表現為表證較少,為使用解表和里治療瘟疫的治法指明方向[29]。
4.1 COVID-19病因病機
當前許多學者根據疫情發展變化,從不同角度提出對COVID-19病因病機的認識。戴敏等人對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收治的五位COVID-19患者病情分析,認為COVID-19屬于中醫“濕毒疫”,而“濕”是關鍵發病因素。結合五位COVID-19患者癥情動態變化和當地嶺南較高的氣溫特點,研究人員認為,當地COVID-19病機更容易發生“濕從熱化”和“濕隨熱化”。值得注意的是,五位患者初期均未有風寒征像,而且在病程中均出現消化功能異常的表現(嘔惡、腹瀉、腹脹、水樣便),所以研究者認為“濕邪”體現于COVID-19的病因病機和病勢[30]。楊華升等收集了北京地區27位COVID-19患者舌像等資料,經統計發現舌象中有表現為舌紅和舌暗紅的患者比例分別為55.56%、33.33%;而所有患者均有苔膩現象,其中表現黃膩苔的比例高達62.96%;經研究人員進一步辨證后發現,疫毒襲肺證患者占比達55.56%(熱重于濕);而濕毒郁肺證患者占比不足50%,共有12例。故研究人員認為北京地區的COVID-19患者病性以“濕熱證”為主,且熱重于濕[31]。上述兩項研究均支持“濕”毒在COVID-19發病中的關鍵作用。
唐德志等認為,COVID-19在老年人當中發病率偏高與老年人常有“腎精虧虛”的生理特點密切相關,主張從“邪伏少陰”或“肺腎相生”的角度理解COVID-19,即疫戾或溫病,濕寒之邪或者陽邪皆易導致傷腎,進而導致腎精虧虛。此外,研究人員在曾經對涵蓋多個省市的1059例普通人群樣本調查,通過分析樣本血的B細胞以及T細胞亞群CD3+、CD4+、CD8+細胞的比例和TGF-β1分子濃度,發現與40歲以下成年人相比,60歲以上老年人更容易處在免疫功能低下狀態,這與老年人“腎精虧虛”特點吻合,所以研究人員建議通過調節“腎精”防治老年人COVID-19[32]。姜良鐸教授在診治四位COVID-19患者后結合多地疫情實際情況,提出應該通過“氣不攝津”的角度認識COVID-19病機。COVID-19耗損肺脾之氣,肺脾氣虛則上焦“肺中陰液化為痰濕”,肺脾氣虛則“水液外滲,肺中如大水泛濫,勢不可擋”,同時肺實變這一病理變化也是COVID-19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和全身癥情惡化的關鍵[33]。
4.2 COVID-19治療經驗和建議
范伏元教授、金朝暉教授等對湖南地區50余例COVID-19患者的中醫藥診治方法和經驗進行總結:該50余例患者具有到武漢生活、學習或者出差的個人史,大部分患者具有發熱、乏力、干咳等癥狀,其中干咳癥狀比較典型,結合發病時節和武漢的地域氣候特征,專家認為COVID-19發病易傷肺陽,其病變本質是“濕毒夾燥”,特點為“燥濕相兼”;患者的癥狀主要為發熱、乏力且熱勢不高,部分患者有腹瀉,故認為“濕毒”是該病的病理基礎,病變內傷肺、脾,外部癥候以“肺燥脾濕”為主。辨證分型及治療上,主張分為四期:初期、中期、極期和恢復期。初期以羌活勝濕湯、達原飲等方藥祛除表證,解除“濕毒郁肺燥傷肺陰”;中期以宣白承氣湯、麻杏石甘湯等方藥抑制“疫毒陷肺”;極期(危重癥)用四逆加人參湯、生脈散、安宮牛黃丸等方藥阻止“疫毒壅肺,內閉外脫”;恢復期選清暑益氣湯、生脈散、竹葉石膏湯等方藥祛除余邪,恢復正氣。對于COVID-19的防護,該研究強調維護正氣,尤其側重顧護脾胃,兼以潤燥養陰”[34]。
姜良鐸教授防治COVID-19的用藥思想體現在因人而異,主張分期辨證施治,并且將服藥群體分為以下五類型:易感、輕癥、普通、重癥和極危。針對易感人群提倡采用“生黃芪9 g,北沙參9 g,知母9 g,連翹12 g,蒼術9 g,桔梗6 g,水煎服,每日1劑,或兩日1劑,連用6 d”方劑,主要體現補肺氣、宣熱邪的思想;針對COVID-19輕癥患者,宜選中成藥,“偏熱者選用金花清感顆粒或連花清瘟膠囊”“偏濕者選用藿香正氣膠囊”,針對虛證之氣陰兩虛的輕癥患者可選擇生脈飲,而偏實者可選擇防風通圣丸或連翹敗毒丸;對于普通型COVID-19患者,姜老主張使用“炙麻黃6 g,杏仁9 g,薏苡仁30 g,甘草10 g,蒼術15 g,桔梗6 g,黃芪20 g,麥冬15 g,五味子6 g,北沙參30 g,知母10 g,玄參10 g。”以“宣肺達表、祛濕清熱”;當患者發展至重癥時,可用“麻杏苡甘湯宣肺、麻杏石甘湯、平胃散、黃芩滑石湯加減”,即逆轉正虛邪陷;若臨床上患者病情危急,則急予“炙麻黃9 g,杏仁9 g,薏苡仁30 g,蒼術15 g,知母10 g,厚樸15 g,生石膏60 g,紅參30 g,西洋參30 g,山萸肉30 g,赤芍20 g,牡丹皮15 g,郁金10 g,萆薢15 g,蠶沙10 g,豬苓30 g”,同時可搭配涼開三寶如安宮牛黃丸等,為益氣固脫、開竅醒神挽救危情[35]。
項瓊等認為,COVID-19主要發生在風寒盛行又濕氣綿長的武漢及周邊地區,結合該病發病潛伏期較長,病程漫延又有較強的傳染性等的病變特點,首次提出“濕毒疫”概念。在認為COVID-19與SARS的病因均屬于疫戾之氣的前提下,研究者側重“宣肺利濕、芳香化濁”治療COVID-19。針對陰虛精虧體質易感人群的防治,總結多年溫病學研究和臨床經驗,提倡服用“強身扶正方(黃芪、枸杞子、黨參、當歸、熟地、女貞子、炒白術、茯苓各10 g)”[36]。
4.3 COVID-19治療新藥物和措施
孫國祥等在大量查閱中醫藥防治瘟疫史,結合“以毒攻毒”的用藥理念,提出將毒性中藥砒霜運用到治療COVID-19臨床救治中。早在260年前張宗法在《三農紀》中就留有砒霜治療瘟疫的記載,砒霜卡耳法應用亦頗有歷史,并且20多年前中國曾用砒霜治療豬瘟,故研究人員認為亞砷酸具有殺死多種惡性病毒的作用。研究者認為,上述砒霜運用于人類與動物瘟疫的治療史,為砒霜(以亞砷酸氯化鈉注射液的形式)治療COVID-19提供了一定的依據。此外,研究者在前期研究基礎上,提出在臨床醫師可以在嚴格謹慎態度下,根據具體病情,考慮亞砷酸氯化鈉注射液治療劑量不超過0.16 mg/(kg·d),用藥時間1至6周。該研究尚未進行嚴格的臨床試驗,亞砷酸氯化鈉注射液治療COVID-19的效果及安全劑量以及毒副作用有待進一步基礎和臨床研究證實[37]。
張晉國等回顧了中藥香囊被用于在我國抗擊疫病的歷史經驗,結合中藥香囊可能通過提升流感患者血清中IgA、IgG水平防治流感,倡導使用顧植山教授建議的辟瘟囊預防COVID-19。辟瘟囊來源于清代吳尚先所著的《理瀹駢文》,由羌活、大黃、吳茱萸、柴胡、蒼術、細辛組成,該方藥芳香化濕行氣避穢,能解六經之邪或可在防治COVID-19中發揮作用[38]。
4.4 部分地區COVID-19病癥和治療特點
目前,中醫對COVID-19發病和治療各地區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總結,本文根據氣候和地域位置主要劃分為南部區域和北部區域(黃河或長江以北為北部區域,黃河或長江以南為南部區域)。北京、天津、河南、甘肅劃為北部區域,湖南、湖北、上海、南京廣東劃為南部區域。北京三面環山,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寒冷干燥,此次COVID-19發病多以“濕熱證”為主,且“熱重于濕”,舌象均可見苔膩[31]。天津臨海,地處海河五大支流匯合處,此次發病以納呆、腹瀉、低熱為最常見中醫癥狀,苔膩為最常見舌象[39]。河南地勢西高東低,冬季多寒冷,雨雪相對較少,今冬雨雪相對較多,以“濕邪疫毒”論治,病程可分為初期、進展期、危重期、恢復期四個階段,以藿樸夏苓湯、荊防敗毒散、銀翹散、宣白承氣湯等予之[40]。甘肅省西南-東北走向,地形狹長,以山地型高原為主,地貌復雜,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傾斜,氣候類型多樣,故而病例自西南向東北呈階梯狀分布,輕癥為主,危重較少,主張三焦辨證,立足肺脾,祛濕為先,方以藿樸夏苓湯、三仁湯、麻杏薏甘湯等[41]。
湖南、湖北為長江流域,湖泊眾多,冬季寒冷潮濕,結合地域及時令,此地區COVID-19發病以“濕毒夾燥”為主,特點為“燥濕相兼”,病變內傷肺脾,證候以“肺燥脾濕”為主,倡宣肺利濕[34,36]。上海臨海,長江入海口,今冬雨水甚于往年,濕邪較重,COVID-19發病屬中醫“濕瘟”范疇,早期“濕毒郁肺”,予以藿樸夏苓湯、梔子豉湯;若其后熱甚,發展為“邪犯膜原”,以達原飲、宣白承氣湯予之[42]。南京毗鄰上海,濕氣較盛,發病初期多為“濕困肺衛”,以咳嗽、發熱、乏力為主癥,膩苔多見[43]。廣東地處嶺南,氣候潮濕,氣溫較高,易發“濕毒疫”。以“濕”為重,易“濕從熱化”和“濕隨熱化”,常以腹瀉、嘔惡、水樣便起病,病程分為早期、中期、極期、恢復期,早期多以小柴胡湯、藿樸夏苓湯為主方,熱甚可用麻杏石甘湯合達原飲加減治療[30,44,45]。
結合各方各論,目前中醫對COVID-19的認識有許多共性:病位在“肺”,病機以“濕”為主,病程可分為初期、中期、重癥期和恢復期,證候隨病程深入演變各異;針對COVID-19的治療,應該分期隨證辨治,同時COVID-19發病并非單純熱毒或虛證,故慎用清熱解毒及補益方藥;隨證可選方:達原飲、藿樸夏苓湯、麻杏石甘湯、宣白承氣湯等[46-48]。
5 討論與總結
現代醫學著重于病源結構認知和治療標準化。在結構方面,現代醫學通過分子生物學和病理學,篩選并明確定COVID-19的病因是患者感染具有傳染性的2019-nCoV。根據基因測序和核酸檢測從分子層面揭示2019-nCoV與SARA病毒、其他常見流感病毒在核苷酸序列、編碼蛋白種類和結構的異同,為搜尋2019-nCoV的最初感染源和中間宿主提供證據。同時,依據前期流行病學調查,為COVID-19疑似患者隔離和觀察時間提供依據,指導一線人員和群眾的防控措施和防控用品使用,節約醫藥資源,發揮資源配制最大化。此外,已經開展的研究闡釋患病人員的基礎身體狀況和發病關系,指導人們改善生活方式。在臨床前期研究中,診斷標準的不斷調整也顯示了現代醫學靈活性和準確性。COVID-19發病短,抗擊疫情的形勢較為嚴峻,臨床重癥治療的研究較少見刊。據相關報道,已經有COVID-19患者遺體解剖和病理實驗的開展,相關研究結果值得關注。
中醫藥曾在SARS防治中貢獻突出,本次抗擊COVID-19中醫藥積極介入整個防治流程。中醫藥在抗擊瘟疫中優勢明顯,如耐藥率低、毒副作用小(比如SARS防治中,中醫藥的干預有效降低了激素沖擊治療引起的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等)。當前多個地區和醫療機構積極開展中醫藥治療COVID-19,其治療有效率得到提升,病死率降低,比如方艙醫院。這需要后續嚴謹的研究支持,但中醫藥客觀、明顯的療效提升社會各界戰勝COVID-19的信心。目前的防控工作中,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共存共融并肩抗擊COVID-19。中醫藥領域對COVID-19的認識未有完全統一,但是在COVID-19的病因病機、病性、病機轉化、治療上有許多一致的認識,這種一致性是中醫治病整體觀思想的體現。此外,對COVID-19預防和預后,中醫預防側重避邪氣,增強正氣。恢復階段,重視補益氣陰和顧護脾胃,增強后天之資。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已發表文獻研究,其病例多為臨床觀察和回顧,缺少嚴謹的前瞻性基礎和臨床研究;目前報道提示已有標準化、多中心、隨機對照、雙盲相關試驗開展。現代醫學和中醫藥共同目標是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降低COVID-19發病率,增加治療有效率,降低死亡率和縮短病程,減輕毒副反應。現代醫學和中醫藥應該相互取長補短,高效融合于COVID-19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