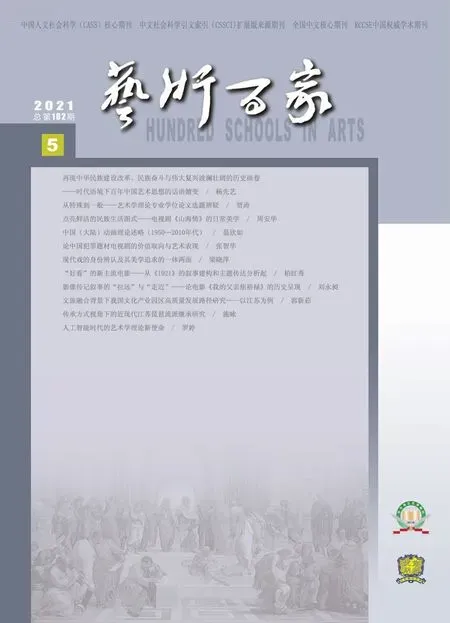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力挽頹波”的華喦*
——評劉毅《華喦花鳥畫研究》
孫 磊
(山東藝術學院 美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華喦花鳥畫研究》[1]一書不僅從繪畫本體角度還原了華喦在“揚州八怪”畫家群體中“力挽頹波”之功,而且通過對他所處時代藝術生態的研究再現了華喦游離于“謀食”與“謀道”困境中的精神內質,不失為近年來關于“揚州八怪”個案研究的典范之作。
有影響的關于“揚州八怪”的研究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顧麟文主編的《揚州八家史料》(1962)以及卞孝萱撰寫的《關于汪士慎的幾個問題》(1962)、《“揚州八怪”之一的高翔》(1964)等。更多相關研究成果的涌現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段時期,該時期付梓的一系列關于“揚州八怪”的個案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個案研究有助于在細致深入的剖析中揭示“揚州八怪”諸家的個性特質,有效避免因學術的慣性認知與“后見之明”而陷入概念化的陳見與誤讀中。同時,個案研究也有助于在文化藝術日益繁榮的新時代進行藝術史的重構,重塑“揚州八怪”這個以“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2]356著稱且極具創新意識的畫家群體的藝術地位。作者劉毅所著《華喦花鳥畫研究》便是頗有學術創見的個案研究。
首先,劉毅為知名中中、青年畫家,擅長花鳥畫、人物畫。因此他在該著作中能夠游刃有余地從繪畫藝術本體還原華喦這位“揚州八怪”中堅人物的歷史地位,尤其是其他“八怪”諸家所未及的“力挽頹波”之功。
通常而言,“揚州八怪”以“怪”名世,所謂“另出偏師,怪以八名”,正如鄭板橋“六分半書”的“亂石鋪街”,金農筆如帚刷的“漆書”,黃慎書畫蒼藤盤結的用筆,汪士慎的淡寫梅花,無不呈現出“奇”與“怪”的審美趣味。然而事實上,今日看來,華喦的繪畫卻很難符合“怪以八名”的標準。與鄭板橋那樣的“揚州八怪”諸家一樣,華喦的繪畫成就同樣體現在花鳥畫方面。不過,其主要的不同點在于華喦花鳥畫的傳統內蘊極其深厚,研究者若對其視而不見,便很容易對其獨到的藝術史貢獻進行“消耗性的轉換”。[3]6
緣于對花鳥畫史研究的長期積淀,劉毅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更為客觀、立體的花鳥畫家身份的華喦。前人寫華喦要論雖多,但通過研究作品本體語言變化來尋繹其內在美學理路,兼以花鳥物象剖析者并不多見。劉毅的研究精準抓住了華喦花鳥畫之典型意象,并得以在歷史滔流中細分其啟承淵源,尋繹本質,將華喦花鳥畫之精髓娓娓道來。雖談不上研究華喦花鳥畫之嚆矢,但論述翔實系統,實為可觀。就意象分析而言,劉毅發揮了一名花鳥畫家在研究視野、視角上的專業特長,深入闡述了自己對華喦花鳥畫敏銳的感受方式與思考方式。
“揚州八怪”以“怪”名世,一味彰顯與眾不同的“前衛”意識,本無可厚非,但因此也很容易陷入“率汰三筆五筆……胡謅五言七言,打油自喜”[3]的誤區。故而,王原祁謂其“廣陵惡習”并非沒有道理。然而華喦卻改變了此種關于“八怪”書畫的不良認知。對此,清代汪鋆《揚州畫苑錄》卷二“虞蟾”條對華喦予以高度評價:“幸來閩叟力挽頹波,豪拈則魔障一空,紙落則煙云四出,空中有畫,著處無痕,會冥契于天倪,參微茫于大造;化俗為雅,寫生即生,寓繁于疏,不古而古。”汪鋆所言華喦有“力挽頹波”之功并非言過其實,而是基于一名書畫精鑒者理智的價值判斷。
劉毅的研究表明,華喦的拯弊之功緣于其自身系統而深厚的藝術研習,這恰恰是大部分“八怪”諸家所未盡處。對此,劉毅對華喦與石濤、惲壽平以及元、明諸家的承襲關系予以了細致闡述,并對華喦寫意花鳥的個性化審美追求同樣予以學理剖析。此既揭示了華喦與“八怪”諸家敢于創新的共性特征,又有力回答了華喦自我成就的立身之本。清代花鳥有沒骨、寫意兩大流派,華喦出于其中卻不泥于其中,略帶夸張的小寫意畫風“繼南田殆無愧色”,誠為獨樹一幟。華喦花鳥畫力追古法,不求妍媚,又恪守氣韻,契合元明以來文人花鳥之意蘊,師法廣大且特立獨造。
在劉毅看來,華嵒入揚州之前是其風格初步形成之時間段,往返揚杭之后,則是其風格主要定型時期。其人物遠取李公麟、馬和之,近承陳洪綬、王樹榖。其花鳥畫精髓則大體師出惲南田,但能一改南田纖細柔媚之寫生為跌宕瀟灑之寫意,而這種寫意則是在其完備的寫生基礎上升華而來的;進而又發展寫意為寫趣,并變惲壽平畫面之靜為物象之動,發展了惲壽平對“形”和“意”層面的理解,其畫面意象生動傳神,將自然界天然情趣與自己的藝術思想相融合,創造出活靈活現的雙鴨形象,那種宛若天成的韻趣,顯示出其小寫意花鳥畫的精湛技藝與獨特思想,展現了華嵒對“形”和“意”的獨特認知。對此,作者通過畫面的意象剖析告訴我們,華喦總能將惲壽平“筆筆實卻筆筆虛”的自在“虛靈”轉變為“筆虛卻物實”的自適“虛靈”。“無我”到“有我”,是華喦花鳥畫所呈現的特殊韻味。這當得益于華嵒對自然物象的長期觀察。他在杭州寓居處,便種植各式花卉,每日澆灌修養,不僅培養了生活情趣,同時亦通過仔細觀察植物細微變化、探索生命成長姿態,提升花鳥畫作之境界。
而就花鳥畫風的演進而言,華喦取法趙孟堅、王淵、陳琳、張中,變元人質樸為輕靈,仿效林良、呂紀、唐寅、陳淳,改明人清剛為秀逸。秉承石濤“一畫論”之思想,與鄭板橋、金壽門、李復堂、黃恭壽“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尤為同調。“八怪”各家,要求不同,境界不一,安靜急躁各有性格。但當遇到所“愛”之事,則都自我滿足,欣然為之,于畫中有所期待,有所鉆研,幾十年成就各自之畫風,不知老之將至。對華嵒來說,鬻賣書畫是其生存之必需,得悟感言是其天性使然。華喦于筆墨、色彩銳意創新,于構圖、布置更見功夫,結果就是情趣、意境上的升華。對色彩的敏銳捕捉是華嵒的優勢所在,從其詩詞中便可看出他對色彩的把握十分精到。華嵒對色彩的追求更趨向于視覺的感官呈現,于物象表現則注重色彩的復合和混融。身為花鳥畫家,劉毅總能從技法的微妙處與華喦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
該著作多有類似的闡述,實為獨具慧眼之見。如此看來,較之華喦花鳥,其他“八怪”諸家即便是鄭板橋,往往顯得銳氣有余而內蘊不足,因而華喦在“八怪”群體中不容漠視的存在價值自是一目了然。此為劉毅《華喦花鳥畫研究》給我們的重要啟發之一。
其次,該著作在還原當時揚州畫壇的藝術生態中,揭示了華喦游離于“謀食”與“謀道”困局中的真實心境及其品格追求。“揚州八怪”畫家群體盡管人員身份不盡相同,但在鬻畫為生方面卻殊途同歸。華喦生活的揚州鹽商云集,如汪中《廣陵對》所言:“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故而,當時的揚州對書畫有著較大的藝術消費力與獨特的審美趣味。由此,吸引了華喦等眾人前來以畫謀食。不過,在劉毅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華喦等人雖是以畫謀食,但仍不乏“謀道”之渴望,此為其作品注入了高蹈之精神內質。“八怪”屬于一群失意文人的聚合體,不過他們雖遭遇人生窘境,卻總能在守望真性中坦然面對。況且,這里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
華嵒是一個善于交際的人,初入揚州便與員果堂“有若琴瑟和,心照復神視”。與“八怪”之金農、高翔、李方膺、李鱓、黃慎、鄭燮等同樣惺惺相惜。如其曾以“乾坤浩浩人如虱、誰識英雄在布衣”之言贊譽李方膺,此雖為對李方膺灑脫出世之刻畫,但實為自況。華嵒出身布衣,卻能不囿于命數安排,奮力進取。其年少時在家鄉曾一夜偷畫出四幅壁畫,隨后遠赴他鄉,不懼別人冷眼,勇于追求內心向往之生活。至揚州后,華嵒很快與“揚州二馬”、汪應庚等富商交往甚密,深入了解當時揚州儒商階層的喜好,為其作品進入揚州書畫市場做好了鋪墊。然而,就其生存狀態而言,貧困似乎總是如影隨形,此與大多數苦于謀食的“八怪”諸家一樣時運不濟。值得肯定的是,華喦總能寄情書畫,怡然自足。由是觀之,《華喦花鳥畫研究》正是在當時揚州藝術生態的復現中,為我們勾畫出以華喦為主角的“八怪”諸家的內心世界。
基于此,劉毅的研究對華喦“解弢”“隱逸”“離垢”等精神內質作了全面解讀。“解弢”,一意,解得天弢,透過現象看本質;二意,恪守儒家之道,追尋真正的自己。華嵒對人生的態度即如此。正如書中所言,在與摯友的交往中,他們的言行思想影響了華喦,由最初的被動接受、隱逸心態到后來主動追求“解弢”“離垢”的思想,使得他的繪畫最終形成鮮明而含有隱逸品質的藝術風格。這種思想影響了華嵒的繪畫取向,他學習師法的對象是惲壽平,究其原因,還是惲壽平的畫中有著濃厚的隱逸情結,畫品契合人品,他所選擇學習的元明時期繪畫中的隱逸成分也很濃重。
通過劉毅的研究,我們發現無論是畫風還是人生,“逸”均為華喦藝術史價值判斷的核心。在作者看來,“簡”等同于“逸”,而其中包含兩種含義,一是畫面呈現的簡逸審美韻致,二是以簡淡的筆墨呈現出來的造型。華喦能將惲南田之“高簡”轉化為一種意態和意趣,此為其對“簡”的獨到把握。華喦對逸趣孜孜以求,以簡逸之筆墨寫“趣”與“態”,長期以往,逐漸成就其繪畫的常態與風格。正所謂“畫為心聲”“崖懸百丈藤,鶴下千年樹”“陰山一丈雪,萬里月孤懸”,從其畫面款識見出,華嵒具有冷逸的內骨。但此并不是說其性格僻傲,不與人言,而是指其志氣孤高。其雖受生計影響,卻并未一味沉溺于鬻畫、討好買家口味之中,而是在以畫“謀食”中隱忍著“謀道”的遠志,故而形成其獨特的雅俗共賞的藝術境界。由此看出,其藝術之“雅”為其天性使然,畫中“俗”的成分并非華嵒的主動迎合,而是他作為職業畫家的無奈選擇。劉毅對此展開的相關表述頗有見地。
再次,該著作對華喦后世影響的闡述頗有藝術史的啟發意義。藝術史總是在發現中得以不斷重構。顯然,華喦便屬于被重新發現的那一位。從其對后世尤其是對海派的影響中就可見一斑。對此,作者的研究同樣很有藝術史研究上的啟發意義。歷史車輪輾轉向前,事物終將湮滅,華喦花鳥畫之影響卻歷久彌新。對海派畫家而言,當他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日益消逝,當前朝優游山林的閑情逸致不復存在,華喦卻給了他們重要的藝術參照。在作者看來,取法華喦已成為海派畫家群體的一種集體策略,海派人物畫或者著色花卉畫上往往題有“仿新羅山人”,此便為重要的圖像佐證。經過圖像的梳理,劉毅發現,無論是審美風尚,還是物象呈現與處理,好多海派畫家皆曾對華喦的花鳥畫進行過學習揣摩,進而完善、發展,達到新高度。身為一名擅長花鳥的青年畫家,劉毅此種發現顯然得益于自身的藝術接受經歷。正如書中所言,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華喦的藝術影響并未成為過去,即使在當代,他那種以日常所見之題材表現物趣意態及其對真、善、美,理、趣、法的追求,在當代寫意花鳥畫的發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訪一個畫派或一個畫家,不僅能打破線性歷史觀之桎梏,也有助于在傳統藝術的研究中彰顯文化的厚度與自信。尤其是在共襄盛舉的新時代,我們更需要對華喦這樣才華橫溢又很容易被歷史所遮蔽的藝術家予以重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