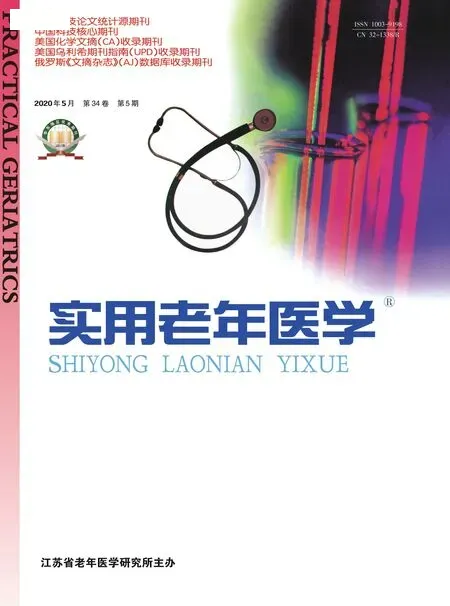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衰弱的相關因素分析
潘穎 李伏超
衰弱是老年人因各種應激及功能障礙引起的生理儲備下降,進而導致機體易損性增加,可作為預測摔倒、感染、失能、住院、死亡風險的指標[1]。骨質疏松病人輕微摔傷即可發生骨折,且多為髖關節骨折,其中約50%為股骨頸骨折[2]。老年股骨頸骨折后因疼痛制動、手術創傷、術后臥床等危險因素也易導致新發衰弱。衰弱是老年髖關節術后近期并發癥的獨立影響因素,且顯著延長病人住院時間[3]。本研究通過應用衰弱量表對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病人進行衰弱評估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旨在為臨床股骨頸骨折術后衰弱的預防提供更多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2015 年1 月至2017 年12 月入院的股骨頸骨折手術復位及內固定術后滿1 年的老年病人256 例,年齡60~98歲,平均(77.8±8.7)歲,其中男90例,女166例。納入標準:(1)年齡≥60 歲;(2)術前無衰弱,Fried 衰弱量表<2分(步速除外);(3)同意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合并脊柱、顱腦骨折及內臟多發傷;(2)處于疾病急性期、終末期;(3)合并嚴重腦梗死、癡呆及惡性腫瘤;(4)輔助工具協助下仍不能行走;(5)溝通障礙。
1.2 研究方法
1.2.1 評估工具:在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自行制訂問卷,問卷內容包括病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職業、子女參與照料情況、基礎疾病、髖關節骨折類型、有無合并上肢骨折、術后并發癥、術后是否長期臥床(>1 個月)、缺乏營養支持(口服營養補充<400 kcal/d 或<3 個月),并采用Fried 衰弱量表對病人衰弱情況進行調查。
1.2.2 研究過程:8 名調查員經標準化培訓后,對股骨頸骨折術后滿1 年的老年病人進行訪視并對受試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和觀察測評,調查時2人1組,便于核對和補充。
1.3 老年衰弱的診斷 本研究采用Fried 等提出的衰弱量表對老年衰弱進行定義[4]。量表包含以下5個指標:步速、虛弱、低體力活動、體質量下降及疲乏,以上5個指標中具備3個及以上則診斷為衰弱。
1.4 統計學方法 利用Epidata 3.1建立數據庫并雙人錄入。采用SPSS 20.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 二元逐步回歸分析衰弱的相關影響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老年術后衰弱與非衰弱病人臨床特征比較 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1 年衰弱的發生率為27.7%,術后衰弱組和非衰弱組在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合并COPD、合并心律失常、股骨頸骨折類型及有無合并上肢骨折、肺部感染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在性別、有無子女照料、T2DM 患病率、高血壓患病率、合并下肢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術后臥床>1個月、缺乏營養支持方面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見表1。

表1 股骨頸骨折術后衰弱與非衰弱病人臨床特征比較(n,%)
2.2 衰弱的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衰弱狀態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結果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二分類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男性、T2DM、DVT、術后長期臥床均為衰弱的影響因素,見表2。

表2 Logstic回歸分析衰弱的影響因素
3 討論
股骨頭、股骨頸、髖臼共同構成髖關節,是軀干與下肢的重要連接裝置及承重結構,其中股骨頸骨折后對人體影響極大。股骨頸骨折不易愈合,恢復緩慢,容易致畸致殘,1 年內死亡率達14%~36%,約1/3 病人不能恢復到傷前功能狀態[4]。研究顯示,老年髖關節骨折病人中約1/3 術前存在衰弱,其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較無衰弱者增加18.88%,且病死率增加8.51%[3]。髖關節骨折與衰弱關系密切,但由于衰弱的評估方法和標準不同以及選取人群差異,衰弱的發生率在各項研究間不一致,我國老年人衰弱的發生率普遍高于10%[5]。本研究發現,股骨頸骨折術后老年病人衰弱發生率為27.7%,顯著高于一般老年人群衰弱發生率。因此,及早發現衰弱并給予預防和干預顯得極為重要。
衰弱過程涉及到多個系統的生理變化,其原因也有很多。以往研究表明,性別是影響衰弱的因素之一,衰弱患病率隨增齡而升高,女性高于男性[1]。但本研究發現,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男性發生衰弱的風險高于女性。原因考慮部分骨折病人可能存在肌少癥或肌少癥前期,而EWGSOP將肌少癥定義為衰弱前期,也是衰弱的病理生理核心[6]。研究證實,男性為肌少癥好發人群,其雄性激素睪酮為促進肌纖維蛋白合成激素,而血液中睪酮的水平在40 歲后每年下降1%,約有20%老年男性睪酮激素處于正常低限,它的減少會增加老年人衰弱、肌肉無力和跌倒的風險[7]。一項隨機試驗對274例處于衰弱的老年人進行6個月睪酮注射,試驗組注射睪酮50 mg,1 次/d,對照組注射安慰劑,結果提示睪酮可顯著改善衰弱[8]。
多種疾病共存是衰弱重要的危險因素之一,慢性疾病和某些亞臨床問題與衰弱的患病率強烈相關[9]。研究表明,DM 和衰弱的病理生理機制具有相關性,故老年DM 病人衰弱發生率較高,其發生率為15.1%~46.3%[10]。目前,國外對老年DM 合并衰弱的機制研究較為深入,認為DM可通過高血糖水平、高胰島素抵抗、高炎癥反應、強氧化應激、周圍神經退行性病變等機制共同導致衰弱。另外,由于老年糖尿病病人存在胰島素抵抗,致使骨骼肌細胞攝取葡萄糖受限,進而導致肌少癥的發生并加速機體發生衰弱[11]。研究發現,衰弱對老年DM病人不良結局具有重要預測作用,是老年DM 病人失能和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12-13]。本研究同樣證實了T2DM 是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發生衰弱的獨立危險因素,究其原因考慮系股骨頸骨折及手術應激等導致血糖大幅波動,并可能通過上述機制導致衰弱的發生。因此,對該類病人術前術后積極管理血糖,對預防衰弱有著積極意義。
股骨頸骨折術后因患肢制動、疼痛導致下肢肌肉主動運動受限,部分老年病人因此長期臥床。肌肉功能的維持有賴于正常收縮及運動,當肌肉處于制動或無負荷狀態時,肌肉纖維即開始萎縮。長期臥床導致肌肉蛋白合成減少,尿氮排泄增多,肌肉分解增強,肌肉質量尤其是下肢肌肉質量明顯減少。研究發現,老年病人因活動不足10 d 可導致下肢骨骼肌質量下降10%,因住院制動3 d 可導致下肢骨骼肌質量下降大于10%[14]。本研究提示,長期臥床系股骨頸骨折術后發生衰弱的獨立危險因素,故術后即使不能負重,也應盡早行功能鍛煉,可維持肌量或減少肌肉萎縮,防止衰弱的發生。
另報道顯示,超過70%的下肢骨折病人會有不同程度的DVT 形成,術后DVT 發生率為20.0%[15-16]。DVT 主要臨床表現為下肢腫脹、疼痛、行走困難等,其降低了病人的生存質量,重者甚至還會致殘或危及生命。本研究發現,衰弱組DVT 發生率為19.7%,是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發生衰弱的獨立影響因素。因此,對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病人進行有針對性的集束化護理及家庭延伸護理,能更好地預防股骨頸骨折術后DVT及衰弱的發生。
老年人因各種原因,營養不良發生率較高,而營養不良是衰弱發生、發展的重要生物學機制[17-18]。本研究發現,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缺乏營養支持的病人衰弱發生率高,雖本研究缺乏營養支持并非術后衰弱的獨立危險因素,但研究顯示營養支持可通過補充能量、蛋白質、維生素D 及鈣等顯著增加肌容量,改善下肢肌力和功能,進而改善衰弱狀態[19]。故而老年病人股骨頸骨折術后積極進行營養支持治療,對維持病人肌肉功能及預防衰弱也有重要價值。
本研究仍有以下不足。首先,衰弱影響因素眾多,限于病例數量有限,此次僅針對部分重要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同時無法對衰弱前期進行分組分析。有待后期進一步收集病例并行前瞻性研究,為預防老年股骨頸骨折術后衰弱的發生提供更多臨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