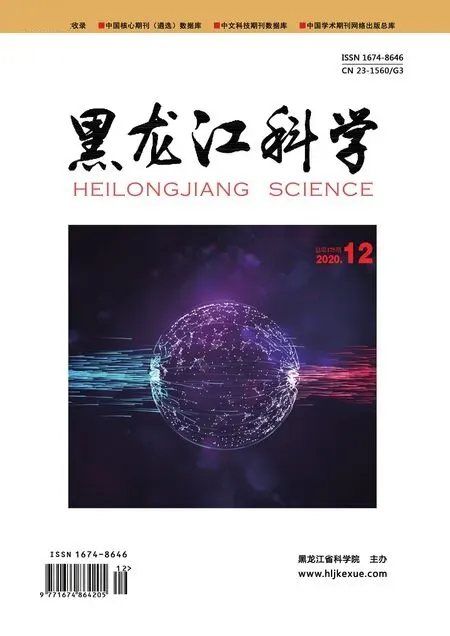貝葉斯公式的應用推廣
陳曉旭
(青島濱海學院,山東 青島 266500)
在概率論與統計學中,與頻率學派不同,貝葉斯定理是在確定某事件發生的概率時,加入了該事件歷史經驗先驗概率,通過實踐結果不斷調整先前的認知。
1 貝葉斯公式
假設A1,A2,…,An為事件樣本空間Ω的一個完備事件組(即一事件發生的所有可能的假設),結果發生為事件E,則:
公式中的P(Ai)為事件發生前的先驗概率,往往是主觀概率,而P(Ai/E)則為加入了結果之后的后驗概率,是對主觀概率的一種調整。
2 實際案例分析
例1:突發性疾病診斷。
新冠肺炎患者的診斷核酸檢測是目前主要參考,但不乏有患者數次檢測為陰性或者檢測為陽性卻沒有任何相關的癥狀表現。本例中采用貝葉斯公式,從數學角度分析核酸檢測的準確率。
首先做以下假設:事件E為“核酸檢測呈陽性”;事件A為“患者確診患新冠肺炎”。99%的新冠肺炎患者能通過核酸檢測確診(這一數據是通過新聞以及相關數據通告估計),誤診率為1%。

然而上式得出的確診概率非常低,與直覺認為的99%確診率貌似相悖,原因是P(A)值計算為所有人群。因此,想要提高準確度,可以將P(A)的值提高。方法有提高核酸檢驗條件,如出現某些臨床癥狀(咳嗽、胸悶、發燒等癥狀)時再做檢測,檢驗準確度則會大大提高。假設在有相關癥狀的人群中確診率為P(A)=15%,則結果為P(A/E)=94.6%。配合胸部CT掃描,結果也會更加準確。
因此,通過在檢測前對患者進行初步診斷能夠有效提高核酸檢驗的準確度。
例2:刑事偵查決策。
在未掌握完全信息的情況下,根據有限證據對嫌疑人做犯罪概率的推斷有時顯得尤為重要。假設有這樣一則案例,認為嫌疑人甲有大約50%的把握犯罪。審訊過程中,尋得一位現場目擊證人,該證人肯定罪犯做事時為左撇子。若嫌疑人確實為左撇子,是否就可以認定其為罪犯?若不能判定,則目擊證人提供的證據有多大價值?用貝葉斯定理的思路進行分析:

模型中用到的初始概率p(A)其實為相對主觀的先驗概率,這一先驗概率的合理性也會直接影響后續的推斷,因此在假定先驗概率時,盡可能地客觀和考慮充分信息會使得模型更具有參考性。在避免案件誤判方面,貝葉斯的后驗概率也能提供更客觀的信息。在本例中,嫌疑人被中度懷疑的情況下,有線索表明罪犯為左撇子,若不假思索,則很容易陷入直覺誤區,繼而肯定此人確為罪犯。但實際的模型計算并沒有100%認定這一點,可見主觀概率一定是不斷根據實踐經驗修正才能更趨向于客觀。
例3:誠信度下降。
“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從數學角度來講,諸侯對周幽王的信任度不斷下降,并且這個信任度可以量化。

第二次周幽王無故點燃烽火,這時用0.36代替原先的0.7,代入公式計算,得P(A/E)=0.12。可見諸侯對周幽王的信任已經所剩無幾了。
從歷史故事中挖掘很多,像韓非子著作中的“三人成虎”的故事,用貝葉斯分析魏王對謠言從疑到信的背后理論;或者伊索寓言中狼來了的故事,代入估計概率模擬村民對小男孩的信任如何降到冰點[2]。
例4:投資風險規避。
近期股市很多意外波動,很多人認為經濟危機又將會出現,有的公司在投資市場有很多算法預測股市漲跌。對于投資人,如何理性應用各種理論模型避免誤判則尤為重要。以美股為例,歷史上大約2000個交易日出現一次股指單日下跌10%的狀態。假設目前已有算法預測大跌的概率達到90%,如投資人收到算法預警明天股市大跌,則是否選擇緊急拋售?

可見實際發生的概率非常低。如果每次都僅僅按照算法進行操作則大多時候是誤判的。因為在歷史上,結果出現的可能性極低,為小概率事件,這就造成了歷史經驗的欠缺。主觀概率在未經實驗檢測的情況下準確率往往存在較大偏差。
3 小結
本研究選取了4個典型的應用案例,其中突發性疫情的診斷符合當下的社會形勢,但由于精確數據的統計有很多的臨床復雜性,上述新冠肺炎的數據是根據新聞估算,存在不足之處。臨床研究中,可以對數據和假設做更多的調整優化。案件偵破的線索價值判斷,可以結合專業領域更多的場景進行推廣使用。“烽火戲諸侯”的故事是現代人社會信用的量化模型,在信貸機構或平臺有一定的使用價值,也可作為教學中案例探索,潛移默化影響學生,熟悉歷史典故,提高人文素養的同時,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誠信美德。投資誤判的規避可給普通投資人一些決策參考。在投資市場中,散戶常會加入一些決策群或者收到很多不可靠的內參消息。參考上述思路,在分析時加入貝葉斯定理的后驗概率,要比人們憑直覺的先驗概率要更加明智。雖然無法每次都得到事件背后的充分信息,但從數學角度來講,已知的越多,就能為了解未知的東西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方法支撐,這正是貝葉斯的通俗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