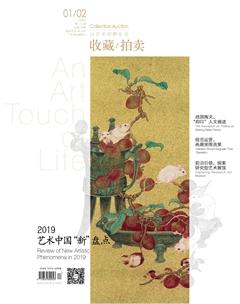林旭輝 創(chuàng)作,一個進(jìn)山與出山的反復(fù)過程
張小雪



他穿著一身合體的休閑裝,說話慢條斯理,沒戴眼鏡。坐在布面沙發(fā)上,雙手?jǐn)傞_,整個人舒展又松弛,笑起來還有點不好意思。你很難把眼前這樣一個身材精瘦,平靜溫和的人跟《未知——第6房間》和《向世界求愛》這樣充滿強烈情感和沖擊力的畫作的創(chuàng)作者聯(lián)系起來。一體中的兩極性,也許正是藝術(shù)的張力和魅力。
隨性,沒那么復(fù)雜
走進(jìn)林旭輝在宋莊的工作室的時候是冬日下午,工作室外幾棵梧桐樹的葉子已經(jīng)快落盡了,顯出幾分北方冬天的孤潔蕭瑟。下午的陽光穿過落地窗從西邊照進(jìn)來,灑在他正在創(chuàng)作的畫面上。林旭輝的工作室非常空曠,和他本人非常理性的外表一樣,有條不紊。北面是他平時工作的地方。架子上顏料筆刷擺得整整齊齊,南面放著沙發(fā)、扶手椅、茶幾、朋友送的木頭櫥柜,顯得疏疏落落。最特別的是沙發(fā)背后的墻上,掛著莫蘭迪、畢加索和弗朗西斯。培根的裝飾畫。也可以看出他在工作狀態(tài)里琢磨著什么。
林旭輝,1978年在浙江溫州龍港出生,畢業(yè)于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爺爺是老校長,在他童年時親自教他書法。無心插柳柳成蔭,他不喜寫字,卻對文房四寶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愛上了手握畫筆的感覺。畢業(yè)后他曾開過設(shè)計公司,也曾經(jīng)營過蠟燭廠。最后出于對藝術(shù)的赤誠來到北京,成為了一名職業(yè)藝術(shù)家。這段從商的經(jīng)歷,加深了林旭輝對整個社會的理解和對人性的思考。
印象很深的是他拿出濃而不澀,口感醇厚的巖茶來做招待,茶杯質(zhì)感粗糲卻古拙。桌上放著冰糖桔的果盤,白色的陶器表面點綴藍(lán)色的銀杏葉形狀的花紋。后來他說,這些都是他去小集市上淘來的,我們的茶杯原本是盛放醬油醋的小碗。他還興致勃勃地把自己發(fā)現(xiàn)的兩個小工具展示給我們看。林旭輝十分真誠地說:“這份溫柔敦厚,對古樸質(zhì)感的器物的喜愛,對瑣碎生活的熱情,是我骨子里自帶的東西。很小的時候生活在農(nóng)村,那時候經(jīng)常會撿牙膏殼和泥土做雕塑玩。許多東西其實沒有那么復(fù)雜,喜歡就買了來。就像喝茶,想怎么泡就怎么泡,想怎么喝就怎么喝。真情流露,就有禪味。喝茶就這么簡單。簡單,就是道。”
失去邊界的曾經(jīng)世界
從他2015年創(chuàng)作的系列油畫《有機面孔》《向世界求愛》,2016年的《未知——第6房間》再到2017年的《密室》,林旭輝的色彩和筆觸都發(fā)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顯示了他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不斷摸索和突破。今年林旭輝正在創(chuàng)作的畫作,完全除去了對現(xiàn)實世界中具體實在地指涉,直面人的非理性。
《有機面孔》和《向世界求愛》由一系列面目模糊甚至扭曲的人像組成。這些人像只有靠輪廓才能辨認(rèn),仿佛身處一個不斷劇烈震動的世界中,周圍的切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擠壓過來,他們的雙眼緊閉,外形在持續(xù)地分離,破碎直至崩潰瓦解。《未知——第6房間》則呈現(xiàn)了密閉幽暗的房間,主人公無助又絕望,有種近乎舞臺劇表演的癲狂。林旭輝用非常大膽又自由的筆觸幾乎將顏料直接扔在了畫布上。明顯突出于畫布的筆觸,似乎要將我們拉進(jìn)這個滿足悲觀情緒的空間中。這個階段的創(chuàng)作,林旭輝模糊了“抽象”和“具象”的界限,各種具體對象形象邊界的模糊,表面色彩的流動之下,是人潛意識里的孤獨和恐懼。在他的畫面上,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棍子在攪拌著一桶顏料,它們已經(jīng)逐漸失去邊界,開始互相融合。而我們無法控制這一切,就像畫面上的主人公伸出手來,也注定什么都觸碰不到,林旭輝創(chuàng)造的“空間”原本就是大片的虛無。最后丑陋,骯臟,焦慮,迷茫,吶喊,掙扎……構(gòu)成了野蠻而無情的現(xiàn)實,我們只能照單全收,無處可逃。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自我是脆弱的。
在揭露世界真相,面對自我的探索過程中,英國藝術(shù)家弗朗西斯·培根給了林旭輝很大的啟發(fā)。林旭輝用了一個非常精妙的比喻來形容培根試圖揭露的隱喻:現(xiàn)代社會機器生產(chǎn)對人的壓迫和人對死亡的恐懼。他說:“培根畫面里的人物似乎被扔進(jìn)了絞肉機,整個人在機械化的巨大力量壓迫下皮膚被剝?nèi)ィ骞俦慌で踔聊X漿進(jìn)裂。”他幾乎直面了所有的人性陰暗面:暴力,欲望,恐懼和性。坦誠地面對自己是需要勇氣的,把真實的自己暴露在外是很危險的。
《密室》系列,林旭輝用了非常具體的形象——椅子。他的色調(diào)更柔和,筆觸更細(xì)膩,椅子的形態(tài)也穩(wěn)定了許多,不再充滿矛盾和激烈的掙扎。但畫面中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我們?nèi)滩蛔〔孪耄旱降资钦l會走進(jìn)這個空曠的、無聲的、靜止的房間里,在這樣一把椅子前坐下。年歲漸長,林旭輝的畫面從試圖在人心里激起驚濤駭浪,到平靜之下暗流洶涌。他講很多情緒藏了起來,留給觀賞者更多的思考空間。歐洲游歷后歸來的他感嘆道,“其實許多藝術(shù)家傳達(dá)的都是人本身的孤獨,無論是愛德華。霍普大蕭條背景下的人,喬治亞·歐姬芙的花朵,路易斯‘布爾喬亞的大蜘蛛,還是莫蘭迪彼此孤立的靜物”。
進(jìn)山出山,循環(huán)往復(fù)
2019年的油畫,林旭輝完全放棄了具體的形象,畫面整體更加溫和克制,又充滿生命力。那是一個花火爆炸的世界,在漫天斑斕的碎屑里,遠(yuǎn)方有光,而且正在延伸。于是有了他的新作《預(yù)言》系列。
這幾年林旭輝經(jīng)歷了父親的病逝,時間的流逝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緊迫感和危機感,這一切都逼著他不斷地以生命體驗繼續(xù)探索藝術(shù)的前行之路。回顧自己這一路,林旭輝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既是不斷吸收、梳理和思考的過程,也是自己跟自己較勁兒的過程,就好像爬山。進(jìn)山與出山,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一個反復(fù)的過程。不斷前進(jìn)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有種快感。爬到平臺或者到自己體力的極限時,又特別的焦灼,每一步都很煎熬。意識到想要達(dá)到的效果或者探索的目標(biāo)和自己目前的差距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熬過平臺期,堅持下去,就能豁然開朗。希望以后能更深入地探究圖像背后的懸疑和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