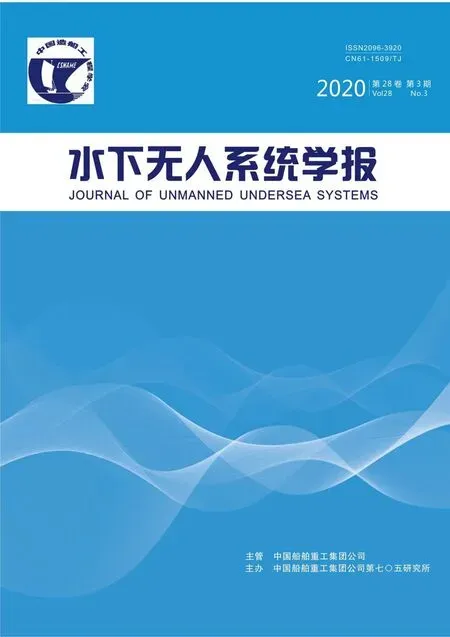海上實兵作戰實驗綜述——概念、案例與方法
錢 東, 趙 江
海上實兵作戰實驗綜述——概念、案例與方法
錢 東, 趙 江
(海軍研究院, 北京, 100161)
實兵作戰實驗是作戰概念開發、戰法開發、兵力運用和兵力結構優化中的關鍵環節和軍事轉型的重要支柱。文中對作戰實驗及其相關概念進行了解析, 闡述了作戰實驗的科學及軍事意義; 簡述了美海軍的主要作戰實驗機構和作戰實驗活動; 介紹了實兵作戰實驗的歷史案例和現代案例, 重點介紹了美海軍著名的“艦隊問題”演習和二戰水下戰的實驗探索; 討論了實兵實驗設計和實施中的有關問題。指出: 應明確實驗目的和目標, 通過發現新現象和探索機理來獲得新知識; 建立相對完整和合理的問題框架是實驗成功的先決條件; 應對系列化實驗進行系統規劃, 避免針對某些孤立問題、缺乏基礎的“跳躍式”實驗; 應合理選取實驗因素及水平數, 把握作戰想定的粒度和特異性, 以保證實驗結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在實施中應注意與演訓的結合, 適時運用模擬兵力, 以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獲得最佳效益; 應建立專業化的分析評估隊伍和專家隊伍, 采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對結果和證據進行分析, 以揭示出問題的本質。指出實兵實驗是發展現代作戰學說的必要途徑。
實兵作戰實驗; 演習; 水下戰
0 引言
過去研究戰爭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經驗的定性分析和戰例分析, 但在現代技術飛速發展、長期未發生大規模戰爭的今天, 這些傳統方法的局限性日益顯現, 作戰實驗已日益成為研究現代戰爭的主要手段之一。
作戰實驗的作用主要體現為超前實踐——提前進行戰爭預演, 揭示和認識未來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找到對策和方法。作戰實驗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不同層次和方面, 例如: 作戰概念開發, 作戰條令開發, 戰術、技術和程序(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s)開發, 兵力結構優化, 裝備運用等。作戰實驗本身就是重要的創新途徑, 因此美軍將作戰實驗視為軍事轉型的重要支柱、發展未來作戰理論的溫床、實現任務能力群的重要途徑。例如: 雖然網絡中心戰、分布式作戰及無人化作戰幾乎已成為共識, 但是具體到指揮控制、組織結構、作戰原則和戰術流程等細節, 都還有待深入研究, 須經過作戰實驗驗證。
作戰實驗是研究作戰問題的軍事科學活動, 旨在運用科學的方法來檢驗作戰概念、理論和方法, 為軍事決策和戰爭實踐提供科學依據。實驗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本身所產生的知識, 更在于它在科學知識發展進程中的作用。
關于作戰實驗問題, 由于各種原因, 目前絕大多數文獻研究的是實驗室中的建模與仿真——基于構造仿真和虛擬仿真的作戰實驗, 較少涉及實兵實驗。文中主要討論基于實兵的海上作戰實驗問題。
1 作戰實驗的概念、分類及意義
1.1 概念
“實驗”( experiment)一詞源于拉丁語experiri, 意為“嘗試”(to try)。在英語中, experiment是指“A test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that is made to demonstrate a known truth,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a hypothesis, or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something previously untried”, 即在受控條件下為演示一個已知真理、檢驗假說的正確性或確定以前未嘗試過的某些事物的效能而做的試驗[1]。《辭海》中給出的定義是: “實驗是根據一定的目的, 運用必要的手段, 在人為控制條件下, 觀察研究事物本質和規律的一種實踐活動”。實驗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研究對變量進行操縱的結果”的過程[2]。有人則將實驗(基本要素)定義為: 一個問題、一組可能的答案、一個事件、一組可能發生的結果, 以及事件結果與問題答案之間的關聯關系[3]。
嚴格地說, “實驗”(experiment)與“試驗”(test)是2類目的不同的科學活動。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 實驗是“為了檢驗某種科學理論或假設而進行某種操作或從事某種活動”; 試驗是“為了察看某事的結果或某物的性能而從事某種活動”。英語中的解釋與此類似。一般而言, 實驗是一種探索性活動, 用來證明理論或發現新現象、推導新結論; 而試驗是一種檢測性活動, 用來檢測正常或臨界運行過程及結果, 如工業產品的各種試驗。例如有人認為, 從事物理化學研究的人主要是在做實驗, 目的是探求化學現象背后的道理, 主要進行科學研究; 而從事分析化學的人主要是在做試驗, 主要目的是進行化學鑒定和分析, 主要從事技術工作。從某種角度看, 實驗是評估系統對某些事物的影響, 而試驗(測試)是評估系統自身的特性。
有時, “實驗”(experiment)和“試驗”(test)會同時出現, 用于表達不同層次的測試活動概念, 例如美國報告中出現“proof-of-concept experiment test plan”的表述, 顯然其中的experiment代表實驗項目或活動的大概念, 而test表示其中一系列分解后的具體試驗子項目和實施活動, 即實驗中相對較小的技術驗證子過程。在此場合, 多少有些類似mission(使命)與task(任務)之間的關系[4]。
“作戰實驗”(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是研究作戰問題的科學實驗活動。在作戰實驗中, 實驗者運用科學實驗的原理、方法和技術, 在可控、可測的近似實戰或模擬對抗環境中, 根據特定實驗目的, 有計劃地改變實驗中的兵力、戰法和作戰環境等因素和條件, 考察各種因素和條件影響下的作戰進程和結局, 從而深入認識戰爭規律, 為軍事決策和戰爭實踐提供科學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2011 年版)將作戰實驗定義為: “在可控可測近似真實的模擬對抗環境中, 運用作戰模擬手段研究作戰問題的實踐活動。包括作戰實驗的規劃設計、組織實施、分析評估等環節。”有人將作戰實驗概念表述為: 探索對特定作戰能力或條件進行操控所帶來的影響或效果。美國和北約已將“作戰實驗”一詞納入軍語[5]。
在西方出版物中先后出現過一些類似的術語和概念, 主要有: 防務實驗(defense experimentation)[2](泛指國防領域內包括正規作戰和非戰爭軍事行動等所有沖突類型的實驗方法)、艦隊實驗(fleet experiment)[6]、戰斗實驗(battle experiment)、艦隊戰斗實驗(fleet battle experiment, FBE)以及實驗戰役(campaigns of experimentation)(一系列相關實驗的集合)[7]等。這些術語的內涵大同小異, 文中引用時尊重原文的表達。
作戰實驗主要運用于作戰實踐上升為作戰理論和方法的科學認識階段, 通過實踐、分析和歸納, 完成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 以此來完成對作戰概念和TTPs[8]的開發, 達到設計作戰樣式和方法、設計未來戰爭的目的, 如: 澳大利亞“游隼”系列作戰實驗就是為武裝偵察直升機配合營連級戰斗而開發條令和TTPs的一系列人在回路的綜合實驗[2]。本質上, 作戰實驗是戰術和技術開發工作的一部分, 而不僅僅是試驗驗證。有些國家將能力開發和建立原型系統的過程稱為“概念開發和實驗(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CD&E)”[2], 應該也是基于這種認識。總之, 作戰實驗是為了探索和檢驗作戰理論、方法及技術而進行的研究活動和預實踐活動。
與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實驗比較, 作戰實驗有其特殊性, 主要體現在軍事問題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對抗性和不可控性等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 有些探索研究中的測試活動兼具實驗和試驗的目的和特點, 許多演習同時包括實驗和試驗的內容, 如美軍近年來將“超重型兩棲連接器”(ultra heavy-lift amphibious connector, UHAC)和“機器驢”等新概念裝備投入部隊演習和實驗, 既探索和驗證新的作戰概念, 也同時考核裝備原型的性能和能力。
1.2 分類
根據不同的視角和理解, 對作戰實驗有不同的分類方法[2-3,5,7,9-16]。總體上看, 下面幾種分類得到廣泛認同, 基本形成了目前的主流觀點。
1.2.1 按實驗目的分類
從實驗目的看, 作戰實驗主要可分為3種: 發現型實驗、驗證型實驗和演示型實驗, 這是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認可的一種分類方法, 但DoD也指出, 幾乎不存在“純粹”的某類實驗, 實驗活動幾乎都是多類實驗的混合體[5,11-12,14,17]。
1) 發現型實驗——也稱探索性實驗, 主要目的是發現新現象、探索新知識、揭示新特點、開發新概念。受這類實驗的次數限制和精度影響, 一般難以推斷明確的因果關系, 不足以形成對戰法的清晰認識。
2) 驗證型實驗——即假設驗證型實驗, 是以分析、檢驗和證實為核心, 對已有的經驗、設想或預測進行驗證和評估。在軍事領域, 這類實驗主要是指為驗證作戰理論、戰法或作戰方案的正確性和可行性而進行的實驗。實驗主要用于檢驗戰法中的假設, 發現錯誤假設或發現假設中的限制條件, 對一些因果關系進行驗證, 以此來形成對作戰概念和戰法的深刻理解。在實際作戰實驗過程中, 對象復雜, 各種因素交織, 因此實驗設計十分重要。
3) 演示型實驗——主要目的是向決策部門和部隊展現已有的科學方法和結論, 展示和傳播新思想、新戰法和新技術, 以期推動實戰應用。
概括地說, 發現型實驗旨在發現現象, 驗證性實驗旨在揭示機理, 演示型實驗旨在傳播思想和概念。
1.2.2 按實驗方法和手段分類
從實驗方法和手段看, 主要可分為3種: 仿真、推演和實兵實驗(演習)。在國內, 當不特指“實兵”時, 通常將作戰實驗理解為基于仿真或推演的作戰實驗。
1) 仿真——作戰仿真包括數學仿真和半實物仿真, 是作戰實驗中最基本、高效的方法。仿真實驗的突出優點是, 能夠通過大量計算給出統計結果, 可進行敏感度分析, 也能進行詳細的因素分析和過程分析, 從而揭示仿真結果與關鍵因素間的因果關系和規律。因此, 仿真已成為對抗推演和實兵演習方案設計的基礎。但受模型、數據和假設等的影響, 仿真結果畢竟與客觀實際之間存在差距, 且對人行為的解釋有很大困難, 所以仿真方法仍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按照現在較為流行的觀點, 仿真主要可分為3類[11, 18]:
①實景仿真(live simulation)——指真實的人員在實際條件下操縱真實的裝備, 主要指試驗和訓練。
②虛擬仿真(virtual simulation)——真實的人員操縱仿真的裝備(模擬的系統), 主要手段是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 如飛行模擬器。
③構造仿真(constructive simulation)——仿真的人員操縱仿真的裝備, 例如全數字仿真。
LVC仿真是指同時具有實景(live)、虛擬(virtual)和構造(constructive)仿真的綜合仿真活動, 主要用于軍事訓練和試驗, 也可用于初級作戰實驗。越戰后, 美空軍調查發現, 飛行員參加約10次作戰任務后, 其戰場生存能力顯著提高, 于是設立了著名的“紅旗”軍演。飛行員在貼近實戰環境中進行對抗, 積累經驗。這類實兵演習雖可提供寶貴的練兵機會, 但成本過高、保障復雜, 于是提出了將實裝嵌入仿真網絡的需求, 由此出現了LVC集成系統。LVC集成中的實兵部分通常包括真實的作戰平臺、任務系統和受訓人員; 虛擬部分則包括部分人員、裝備、系統及其接口, 支持人在回路的實時交互; 構造部分是計算機生成的實體, 表征裝備和人員的能力和行為, 并根據預定規則和行為模型來決定實體的行動。
在水下戰領域, LVC集成的典型代表是美海軍水下戰中心(naval undersea warfare center, NUWC)構建的戰術集成綜合環境(synthetic environment tactical integration, SETI)。SETI利用水下跟蹤遙測系統和網絡, 將高置信度的魚雷仿真能力與實航狀態下真實潛艇上的聲吶和火控系統集成在一起, 實現了在真實潛艇上發射模擬魚雷, 使艇員可利用NUWC的硬件在回路(hardware- in-the-loop, HWIL)模擬的魚雷來攻擊真實或虛擬的目標。潛艇能在水下實時“感知”到所發射的模擬魚雷, 并可進行線導。這種能力可用于早期戰術開發和實驗、對抗訓練和武器試驗。1998年, 美海軍利用“洛杉磯”級潛艇上的建制作戰系統, 完成了對1枚MK48 ADCAP模擬魚雷實施線導導引的演示驗證[19]。
2) 推演(wargame) ——亦稱兵棋推演, 指對抗雙方按演習問題的順序和戰役、戰斗可能發展的進程而連貫進行的模擬對抗和劇情化博弈。早期的推演形式一般是研討會式的決策演習和桌面或圖上作業, 現在都采用計算機輔助推演方式, 加入實戰或實兵演習數據, 交戰各方運用作戰模擬手段, 對作戰方案和行動進行“人在回路”的模擬, 對決策和方案進行評估與優化。這種對抗模擬實際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實驗, 適合于研究決策的過程、原因和影響因素, 探索與人相關的不確定、難以量化的非裝備因素。推演在裝備效能評估及其相關研發決策上的作用日益顯現, 例如, 有人在推演中引入無人水下航行器(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 UUV), 以研究其對交戰雙方作戰決策和對抗過程的影響, 促使人們從新的高度來審視UUV在兵力結構中的地位。
推演主要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博弈過程的對抗模擬, 重點著眼于作戰決策及其后果, 而不是裝備和操作細節。雖然“人在回路”的仿真也有人介入, 但一般多指針對具體裝備運用過程的模擬, 關注的重點是“人-機-環”及其基于武器裝備的戰術對抗策略和武器運用方法, 如為開發TTPs而進行的仿真。
3) 實兵演習/實驗——是指動用真實兵力(人員和裝備)在近似實戰環境下的演習。許多演習同時兼顧訓練、考核、試驗和實驗研究等多個目的。在實驗設計完善的情況下, 實兵演習/實驗所得結論的可信度高, 但組織復雜、成本高、重復難度大。今后將主要依托大型專業訓練基地(中心)借助現代化手段來組織實施。
仿真分析的優點在于能夠提供對作戰過程的基本理解、模型和定量結果, 可作為推演的基礎; 推演的長處在于能夠用于探討決策過程, 可體現出一些非軍事和非技術因素對決策的影響, 有助于從更廣闊的視角發現問題和提出建議; 實兵演習/實驗通過運用真實裝備和作戰人員來測試有關戰術和技術概念, 獲取真實數據, 既能檢驗決策的合理性, 也能近似模擬實戰過程, 從而驗證一些假設和預測, 發現問題, 為下一步仿真分析、推演以及后續實兵演習提出更多更有價值的建議。完整的作戰實驗應將運籌分析、作戰仿真、推演和實兵演習結合在一起, 在理論指導下進行實踐, 用實踐結果來完善、修正理論和模型, 經過不斷交互循環, 不斷逼近“合理解”, 科學引導作戰條令和戰法開發及新裝備研制。只有綜合這些功能互補的方法, 才能對真實作戰中的問題獲得完整和全面的理解。
1.3 實兵作戰實驗與作戰試驗、演習、技術演示驗證試驗的異同
1.3.1 實兵作戰實驗與作戰試驗的異同
在DoD的裝備采辦過程中, 試驗與評估(test & evaluation, T&E)主要分為3類: 研制試驗與評估(development test & evaluation, DT&E), 作戰試驗與評估(operational test & evaluation, OT&E), 實彈試驗與評估(live fire test and evaluation, LFT&E)。
OT&E主要目的是解決武器系統的關鍵使用問題, 在作戰試驗設計中應關注“是否以正確的方式做該做的事”和“評價是否有意義”這2個基本問題[20]。實際上, 作戰實驗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區別在于評價的對象已不限于武器裝備, 而是擴展到作戰指揮、編制和戰法等更高層次的內容。
作戰試驗與作戰實驗關注的對象不同。前者主要關注的是武器裝備在現有作戰理論和實戰條件下的作戰能力; 后者主要關注的是軍兵種以及軍隊未來發展、建設和作戰等方面的關鍵環節, 如新的作戰概念、新的作戰思想、組織結構, 以及重大技術的運用對作戰的影響等。
1.3.2 實兵作戰實驗與作戰演習的異同
作戰演習是部隊戰備訓練的高級形式, 是在想定下進行的作戰指揮和作戰行動的演練, 主要用于檢驗部隊的戰備程度與作戰能力、武器裝備技術狀態和實際能力, 以及戰術的合理性。作戰實驗和作戰演習都可以驗證武器裝備的作戰性能、戰場環境對作戰行動的影響以及組織指揮在作戰行動中的作用, 區別主要在于: 作戰實驗側重于研究, 用于探索作戰問題; 而作戰演習側重于訓練, 用于鍛煉和提高部隊戰斗力。所以, 二者在目的、目標、組織方式、實施方法以及技術手段運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別。但在實踐中, 兩者經常穿插在一起進行, 在作戰演習中進行部分項目的作戰實驗[1]。
1.3.3 實兵作戰實驗與先期概念技術演示驗證試驗的異同
在預研階段, 美國利用先期技術演示驗證(advance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TD)和先期概念技術演示驗證(advanced concept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CTD)來實現先進技術向裝備型號的快速轉化。ACTD是面向新型系統概念或方案的演示驗證試驗, 目的是加速成熟技術向新系統的過渡, 在接近真實的作戰環境中進行, 一旦技術性能和實用性得到驗證, 即可啟動正式研制或采辦程序[21]。ACTD強調的是對成熟技術的集成, 而不是技術開發, 其目標是提供原型作戰能力、體現軍事價值、形成新裝備使用概念。
盡管有某些相似之處, 但ACTD與一般意義上的作戰實驗的區別是明顯的: ACTD試驗主要面向裝備技術(盡管有時也會涉及到有限的作戰概念和組織結構), 目的是為裝備采辦決策提供依據; 作戰實驗主要面向作戰概念、條令、戰法、兵力組織結構、新型裝備, 目的是考察各種條件影響下的作戰進程和結局, 認識戰爭規律, 為軍事決策和戰爭實踐提供依據。兩者出發點不同, 這也體現出“試驗”和“實驗”的區別。
但在另一方面, 有些引入了新概念裝備的小規模作戰實驗與ACTD的界限有時變得比較模糊, 經常是兩者聯合進行, 一次活動同時達到多個目的。如美軍近年來將UHAC和“機器驢”等新概念裝備直接投入部隊演習, 并將其稱為作戰實驗。但從傳統觀念看, 它們更像是典型的ACTD或作戰試驗。
總之, 實驗主要是評估系統對某些事物的影響, 試驗則主要是評估系統特性[2]。
1.4 作戰實驗的科學及軍事意義
過去研究戰爭的主要方法是依靠經驗進行定性分析, 以局部經驗或歷史戰例分析、邏輯推理、反復研討形成對戰爭規律的認識。這種依靠戰例研究未來戰爭的方法在歷史上曾發揮了很大作用, 指導了人們對戰爭的認識, 但在軍事科技現代化的今天, 已遠不能滿足現實需求。限于當時有限的觀察條件、片段的記憶和記錄等因素, 并不能清楚地了解歷史戰例中一些事件的細節、原因和戰術決策等, 從而使許多戰例被摻入了大量文學創作成分, 從而影響到實際啟示效果, 特別是人機結合問題, 僅通過理論和歷史研究常難以得出結論[17]。
如果認為戰爭研究既是科學也是藝術, 則作戰實驗的價值就主要在于對戰爭的科學問題進行實證。許多人僅滿足于從表象上尋找一些能說明現有理論的現象和案例, 而不愿進行深入、嚴謹、系統的實驗探索, 對于新的現象, 總是習慣性地歸結于某個未知的偶然因素。例如: 在戰例研究中, 軍事史學家們往往不自覺地去為一些偶然事件尋找依據并進行解釋, 常將原因歸結于特定環境, 這就難以進行科學、全面的概括和發現其中的潛在規律和機理, 也難以有新的發現。而通過反復進行的作戰實驗, 可合理地解釋常見和偶然現象, 認識因果關系和主次因素。因此, 在現代科技條件下, 沒有先進的作戰實驗基礎就不可能產生先進的軍事理論。
美軍將作戰實驗視為軍事轉型的重要支柱, 認為未來作戰理論的發展與作戰實驗密切相關, 實驗的目的在于評估和完善新的作戰理論, 必須通過作戰實驗開發與實驗新的作戰方案、編制體制、程序和技術。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美陸軍開始了一項長達十年的作戰實驗行動計劃, 相繼成立了多個功能性實驗室, 進行以作戰概念開發、驗證、演示和傳播為主的作戰實驗活動, 美陸軍幾乎所有院校和師級單位都劃入實驗掛靠單位。美軍在多次局部戰爭中的許多戰法實際上都源于作戰實驗。
作戰實驗的作用體現在作戰概念開發、條令開發、TTPs開發、兵力和裝備結構優化, 以及裝備運用等各個方面, 作戰實驗本身就是重要的創新途徑。在歷史上, 美軍利用作戰實驗開發了航母及特混艦隊運用方法,德軍利用作戰實驗驗證了“狼群”戰術和“閃電戰”戰法。在大量UxVs不斷涌現的今天, 顯然必須通過作戰實驗來摸索新的交戰形式, 開發新的聯合作戰方法。實兵實驗除了可為仿真、建模、驗模提供真實數據外, 更重要的是, 只有通過實兵實驗, 才能更真實地展現戰斗人員在近似實戰條件下的行為表現, 揭示出裝備、方法和程序中的潛在問題。
戰爭手段的每一項重要發明, 都要求重新檢驗和評估戰略和戰術的思想、兵力結構、裝備和條令, 這種評估要求對戰爭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進行定量或定性分析, 這是作戰實驗乃至現代軍事變革的原動力。作戰實驗將催生對現代軍事領域的新的認知[17]。
2 美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主要作戰實驗機構及作戰實驗活動
2.1 主要作戰實驗機構
美海軍的作戰實驗機構主要有: 海軍分析中心、海上戰斗中心、海基戰斗實驗室(sea based battle lab, SBBL)、系統技術戰斗實驗室(system technology battle lab, STBL)等, 還有空間和海軍作戰系統司令部(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ommand, SPAWAR)、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NPS)、海軍空戰中心訓練系統分部(naval air warfare center training systems division, NAWC TSD)下屬的作戰實驗室。海軍陸戰隊下屬的作戰實驗機構主要有: 海軍陸戰隊作戰實驗室(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laboratory, MCWL)、海軍陸戰隊戰術系統支持行動中心(marine corps tactical system support activity, MCTSSA)等。
美軍的作戰實驗機構并非都設置在軍隊中, 一些科研和教學機構、甚至民企也參加作戰實驗活動, 如美海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CNA), 盡管是一家民間機構, 卻是作戰實驗的重要參與者。
1) CNA
CNA是美海軍的重要思想庫, 有“海軍的蘭德公司”之稱。作為獨立的非營利組織, 主要服務于美海軍和國防部門, 聚焦于海軍戰略、戰役戰術、作戰評估和資源分析等問題研究[11]。
美海軍的戰爭及作戰分析可分為3個層次: ① 戰略分析, 由海軍學院和海軍作戰部進行; ②戰役級分析, 主要是海軍兵力結構分析, 由海軍學院和CNA進行; ③ 作戰分析, 主要研究海軍裝備性能和戰法, 由CNA、海軍實驗室及研制方進行。CNA主要從事海軍戰略戰術、武器裝備、編制體制和后勤建設等各方面的研究, 尤以研究水下戰技術和戰術著稱。通過技術和系統分析、作戰分析, 協助海軍生成作戰需求和開發新的作戰概念; 通過作戰實驗和試驗、分析和評估, 協助部隊改進作戰、訓練和保障方法及組織結構[22]。
CNA常年保持數十人在海軍及陸戰隊各指揮部和機關擔任顧問, 另通過戰場項目(field program)派人深入一線部隊提供支援。現場分析人員從各個角度觀察實際作戰、訓練和實驗過程, 收集第一手數據, 然后與中心的研究團隊共同分析和評估。這種常態化交流使研究部門和部隊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促進了新的作戰概念和戰法的開發。
2) 海上戰斗中心與SBBL
美海軍的作戰實驗一般由海軍各艦隊輪流承擔, 因此各艦隊都是事實上的作戰實驗室。除此之外, 還成立了專門的作戰實驗機構——海上戰斗中心, 由一名中將領導, 實際上是艦隊作戰實驗的協調和管理機構, 也是聯合作戰實驗中的跨軍種協調機構。2000年, 在第3艦隊“克羅拉多”號上又正式組建了SBBL, 該艦為各種海上作戰實驗活動提供技術支援。海上戰斗中心下設概念研究、技術評估和行動協調3個小組, 分設在海軍學院、SPAWAR等單位, 主要通過仿真和艦隊戰斗實驗2種形式對海戰方案和相關技術進行驗證[5,11,13,23]。
3) 其他戰斗實驗室
“戰斗實驗室”(battle lab)的概念于20世紀90年代誕生于美軍, 其目的是“能夠迅速和深入分析由新興技術產生的作戰思想和作戰方法”。戰斗實驗室本身也可被賦予某些作戰能力, 如指揮控制。多數戰斗實驗室并非獨立機構, 而是某一部門和機構下的研究組織, 或是現有組織被冠以新的名稱, 如海軍研究生院、海軍空戰中心下都設有這類實驗室。許多戰斗實驗室規模不大, 且針對某些具體專業方向, 如: 美陸軍的“火力戰斗實驗室”和“情報戰斗實驗室”等,其主要任務一般是: 規劃和實施各種實驗、提煉作戰概念、評估潛在解決方案、審查想定、提供決策支持等。戰斗實驗室并不一定以戰斗實驗室標榜, 許多研究機構本身從事相關研究和實驗, 也被視為戰斗實驗室, 如關塔那摩基地就被視為是美軍從事心理戰和情報挖掘的“戰斗實驗室”, 他們利用關押的對象和工作環境獲取數據、訓練審訊者、開發情報審訊TTPs[24]。“戰斗實驗室”這一名稱現在也開始被推廣到其他非軍事領域, 如: “霍普金斯大學戰斗實驗室”實際上僅是一個利用仿真和數據分析手段進行生物系統研究的實驗室。
2.2 主要作戰實驗活動
美軍的作戰實驗著眼于未來5~10 年需求, 通常分為一般實驗和高級實驗, 實驗周期1~5年。海軍的高級作戰實驗主要通過艦隊海上戰斗實驗來進行, 每年組織2次, 每次賦予不同的主題和目標, 由各艦隊輪流承擔實驗任務。
艦隊戰斗實驗(fleet battle experiment, FBE)是美海軍最主要的實兵實驗, 美海軍利用FBE分別進行了“火力圈”及“武庫艦”概念和方案的驗證, 聯合火力支援TTPs, 以及極淺水反水雷特遣隊(very-shallow water mine countermeasue, VSWMCM)運用高速艇(HSV-X1)、無人水下航行器(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 UUV)REMUS(Re- mus remote environmental measuring units)和戰場準備自主水下航行器(battlespace preparation autonomous undersea vehicle, BPAUV)等UUV的反水雷作戰實驗。美海軍還每年舉行“三叉戟勇士”(Trident warrior)實兵作戰實驗, 分別演示了部隊網、海域感知與遠征作戰等能力。MCWL開展的實驗有: “獵人勇士”開闊地帶作戰實驗、“城市勇士”城市作戰實驗、“干練勇士”機動作戰與戰役欺騙實驗、“千年龍”登陸奪港與城市作戰實驗、“海盜”分布式作戰實驗、“遠征勇士”海上基地概念驗證、“聯合城市勇士”聯合城市作戰概念開發實驗等[5,11,23]。
3 實兵作戰實驗案例
在歷史上, 航母及特混編隊作戰概念的產生, 以及二戰中一些水下戰和閃電戰等戰術的產生, 都直接來源或曾借助于作戰實驗。戰后60年后的今天, 實兵實驗與作戰仿真相結合, 正催生網絡中心戰、無人作戰等新型作戰概念的產生和發展。
3.1 歷史案例
3.1.1 美海軍“艦隊問題”系列演習——作戰概念和戰術的開發平臺
歷史上最經典的作戰實驗案例應是美海軍在1923~1940年間舉行的21次“艦隊問題”(fleet problem)演習。演習名稱表明, 其目的不僅是訓練部隊, 更重要是通過演練發現艦隊作戰中的問題, 探索和驗證新的作戰概念和戰法、兵力編成與組織、指揮協同及裝備運用方法等。因此, “艦隊問題”演習實際上是“實兵演習+實兵實驗”。軍事史學家給予了“艦隊問題”系列演習極高的評價, 因為它孕育、孵化了航母裝備和使用的諸多概念。通過一系列作戰實驗, 使美海軍一步步認清和理解了航母設計和運用中的一些未知問題, 逐步形成了航母及特混艦隊作戰運用的完整概念和實際作戰能力, 其基本概念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面對21世紀的各種顛覆傳統的戰爭形態, 美海軍又于2015年重啟了“艦隊問題”演習, 可見“艦隊問題”演習的深遠影響力。
“艦隊問題”演習是美海軍用于描述27次海軍演習的名稱。原定于1941年舉行第22次艦隊問題演習, 由于二戰爆發而取消, “艦隊問題”演習就此中斷, 以后的演習采用了其他名稱。然而, 在海軍上將Swift的倡導下, 這一名稱在2015年又恢復了使用, 第23~28次“艦隊問題”演習相繼舉行。該演習通常每年舉行1次, 有時舉行多次。
“艦隊問題”演習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的作戰實驗和超前實踐。每次演習聚焦1~2個重點問題尋求答案, 在特定作戰想定下探索作戰概念和戰法, 檢驗能力。通過早年的“艦隊問題”演習和二戰實踐, 逐步確定了航母在美海軍兵力結構中的定位, 明確了其角色、任務和目標, 成功牽引和驅動了航母技術和戰術的發展。
1) 航母作用與地位的確立

為探索航母的運用方式, 美海軍充分利用1923~1940年間的年度艦隊演習進行了一系列近似實戰條件下的作戰實驗。雖然演習并非專為航母設立, 但美海軍在不斷開發、提煉海軍艦隊戰術的同時, 也逐步確立了航母在海軍中的地位。因而, 一系列“艦隊問題”演習也就成為航母發展的里程碑。
1923年, 美海軍在巴拿馬運河區太平洋一側舉行了第1次“艦隊問題”演習, 圍繞運河攻防展開對抗, 雙方用其他艦船來模擬航母。“敵機”在美軍未察覺的情況下, 用10枚模擬炸彈“炸毀”了“卡通”泄洪道。這次簡單的演習引起了很大震動, 美海軍開始意識到, 航母絕不僅僅是偵察艦或者護衛艦, 它是一種有效的新型攻擊平臺。雖然那時飛機能否戰勝戰列艦隊尚無定論, 但大家都已認識到, 航母的出現必將改變未來海戰規則[25-26]。
在航母出現的最初10年里, 各國海軍從零開始摸索, 逐漸明晰了任務和目標, 航母的作戰運用概念和方法逐步成型。1929年, 剛服役的“列克星敦”(CV-2)和“薩拉托加”(CV-3) 2艘航母首次參加演習就引起了軍事界和媒體界的轟動, 這就是日后被軍事學者們反復提及、十分著名的“第9次艦隊問題演習”。人們普遍認為, 此次演習是海軍史上的一次飛躍, 演習所獲的經驗和結論, 對于艦隊戰術和海軍整體戰略, 尤其是對海軍航空兵的戰略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此次演習的想定是藍方(美國)同時與2個敵國交戰, 分別是太平洋上的黑方和大西洋上的棕方。為將美國分割在兩洋, 黑方要對巴拿馬運河發動突襲, 而藍方則要保護運河。黑方兵力中配屬有“薩拉托加”號航母, 用掃雷艦“阿盧斯圖克”號代替正在大修的“蘭利”號航母, 用搭載的1架水陸兩用飛機代表“蘭利”號上的18架戰斗機和6架偵察機。藍方兵力中配屬了“列克星敦”號航母。棕方則只是一支無實際人員和裝備的虛擬兵力, 配合黑方夾擊藍方。黑方此次行動的基本策略是戰列艦隊的常規攻擊和航母的突然襲擊并舉, 這一戰術安排完全體現了此前美海軍對航母的理解: 既要利用速度優勢離開主力艦隊執行先期作戰任務, 完成任務后又要伴隨主力艦隊行動。1929年1月26日, “薩拉托加”號放出了由83架各型飛機組成的歷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艦載機攻擊群, 對巴拿馬運河太平洋一側的兩處船閘發動了大規模“空襲”并大獲成功。第2天, 黑方掃雷艦“阿盧斯圖克”號又放飛了1架水陸兩用飛機, 用以模擬“蘭利”號上的機群, “摧毀”了大西洋一側的船閘和機場。黑方最終以徹底摧毀巴拿馬運河而取得了勝利。當年由海軍戰爭學院提出的一系列相關問題得到了解答, 航母的威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體現[25-27]。
第9次“艦隊問題”演習的結果震驚了各國海軍, 引發了各方激烈的討論。由于“薩拉托加”號的卓越表現, 美海軍完全確定了大甲板、大載機量和高速航母的價值, 隨之放棄了已開展的建造小噸位航母的計劃。同時, 航母的運用也成了隨后幾次艦隊演習的主要內容。第9次“艦隊問題”演習標志著美海軍取得了巨大成就, 航母不但能與其他水面艦協同作戰, 也可成為一支獨立的打擊力量。這一變化很快對美海軍的航母作戰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下一年度的艦隊演習中, 以航母為中心的戰術編隊首次出現, 這一戰術組織形式在此后的一系列演習中得到了不斷檢驗和完善[25]。
2) 航母特混艦隊的形成
特混艦隊的概念產生于第9次“艦隊問題”演習之后。通過一系列“艦隊問題”演習, 美海軍對航母及其戰術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演習中的教訓使美海軍開始意識到, 航母不能靠自身大口徑艦炮與敵方戰列艦展開對攻。一些經歷了演習的軍官認為, 航母必須由多艘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艦隊來護航, 以免遭對方水面艦隊的打擊。這一觀點被視為是美航母特混艦隊的最初萌芽。經過第9次及隨后的系列“艦隊問題”演習, 美海軍的作戰/偵察艦隊編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 傳統的戰列艦隊繼續擔當海戰核心, 以重型巡洋艦為核心的偵察艦隊則逐漸演化成了多支以1艘航母為核心, 由多艘重型巡洋艦和驅逐艦提供保護的航母特混艦隊。美海軍二戰前的重型和輕型巡洋艦有明確的分工: 重型巡洋艦主要編入偵察艦隊和航母特混艦隊, 獨立執行偵察等任務; 輕型巡洋艦則主要伴隨作戰艦隊, 負責近距離掩護和戰術偵察[25]。
第9次“艦隊問題”演習中, 雖然“薩拉托加”號航母攻擊運河成功, 但在隨后的行動中被判因遭敵反擊而被“擊沉”了3次。這一結果使美海軍意識到, 航母具有強大的攻擊力, 但獨自作戰時自身也面臨著極大危險。于是, 美海軍內部對航母應獨立作戰還是與主力艦隊協同行動的問題形成了兩派意見。激進派認為, 航母平臺應獨自作戰以發揮速度優勢, 與主力艦隊分進合擊以形成有利的戰場態勢。但脫離主力艦保護的航母一旦遭遇對方戰列艦會十分危險, 幾次演習結果都證明了這點。為此提出, 應為航母建立一支由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護航艦隊(戰列艦的速度不夠), 護航軍艦在遭遇敵方時要舍身而出。保守派則認為, 只有讓航母和戰列艦共同行動, 相互掩護, 才能發揮出最大效能, 但其代價是犧牲航母的速度優勢。帶著這樣的問題, 美海軍在1930年接連舉行了2次艦隊演習——第10和第11次“艦隊問題”演習[25-26]。
第10次“艦隊問題”演習的想定是: 藍方(美國)在加勒比海被黑方打敗, 于是派太平洋艦隊進入加勒比海, 消滅黑方艦隊。雖然基本任務相同, 但雙方采取了2種截然不同的航母運用方式: 航母兵力較強的藍方選擇了保守派的方案, 讓航母伴隨主力艦隊行動; 而僅有1艘航母的黑方則采納了激進派的意見, 首次組建了以“列克星敦”號航母為核心的特混艦隊, 多艘驅逐艦部署在前方, 任務是搜索敵方艦隊, 摧毀敵航母, 支援己方戰列艦作戰。特混艦隊正式亮相。在這次演習中, 藍方的2艘航母因遭到“列克星敦”號航母的襲擊而癱瘓, 表明快速空中攻擊兵力能夠打破海上力量平衡。演習的結局令人意外: 在演習的大部分時間里, 雙方都是在竭力搜尋對方, 一旦某一方先機發現對手, 立決勝負。此次演習使美海軍澄清了第7次演習中得出的、但不能十分肯定的結論: 航母面臨空中攻擊時非常脆弱。幾乎可以斷言: 航母決戰中能搶占先機的一方必取勝。黑方航空兵指揮官給出了形象的比喻: “航母對決就像是兩個蒙住雙眼手持大棒的人在一個小圈子里打架, 只要其中一個人眼前的眼罩被摘掉, 另一個就死定了。”根據這一結果, 美海軍得出結論, 如能利用突然性優勢并用航空兵發動先敵打擊, 則完全可能扭轉兵力上的劣勢。這一結論在后來的中途島海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25-26]。
單獨成立航母艦隊會對原有相對固定的編制體制帶來很大影響, 實施難度大。因此, 美海軍決定借用陸軍“臨時特遣隊”的概念, 在海軍中組建一種不占固定編制的臨時性編隊。與陸軍特遣隊不同的是, 海軍特遣隊不會隨某一任務的結束而解散, 它們將相對固定地編組在一起, 共同訓練和作戰。這就形成了最初的“特混艦隊”(task force)[25]。
3) 航母作戰理念和戰術的孵化、開發和實踐檢驗
“艦隊問題”演習為航母作戰理念形成、戰術開發與驗證提供了實驗平臺, 形成了一系列戰術成果。
在航母發展早期, 存在“戰列航母”(battleline carrier)與“全能航母”之爭。前者是指編在戰列艦編隊中的航母, 以較慢速度伴隨編隊行動, 噸位較小, 不需裝甲和重炮。后者則是指具備獨立作戰能力的航母, 航速不低于巡洋艦, 噸位較大。在第10次“艦隊問題”演習中, 這2個概念進行了面對面的較量。演習中, 美海軍第一次將摧毀對方航母作為己方航母的首要任務和主力交戰的先決條件, 結果是“全能航母”取勝, 證明了航母具有很強的對海獨立作戰能力。隨后的第11、12次艦隊演習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戰列航母”連續3次失敗顯然不是偶然現象, 這表明它很難適應未來海空戰[25]。
明確了航母的進攻角色、組建了獨立的航母特混艦隊后, 美海軍開始探究航母與戰列艦對抗問題, 將此作為第12次“艦隊問題”演習的主題。演習表明, 雖然受當時航空兵能力所限, 航母尚無法有效摧毀戰列艦, 但其本身并未受到戰列艦的任何攻擊, 航母特混艦隊完全可獨當一面, 成為海軍主力。后來戰爭實踐證明了這一點[25]。
此后的第13次“艦隊問題”演習表明, 海戰不會是單純的航母對攻, 各種兵力交戰交織在一起, 使得海戰十分復雜。對抗結果表明, 單航母不足以完成艦隊攻擊和區域防御任務,因此在以后的戰爭實踐中, 2艘以上航母在一起共同作戰成為基本戰法。
在對航母的運用概念已基本了解后, 美海軍在隨后的第14~21次“艦隊問題”演習中, 進一步開展作戰實驗, 逐步摸清了航母的主要使用場合、最佳使用方式等問題, 使自身逐步發展成為能夠熟練運用航母遂行機動作戰和艦隊決戰的強大海軍。珍珠港事件并未給美海軍航空兵以實質性打擊, 反而帶來了新的契機: 航母不得不擔當起了海軍第一主力的角色。
3.1.2 二戰時期的水下戰——與作戰實踐相結合的作戰實驗
在很多情況下, 受兵力資源、時間等各種條件的限制, 難以通過精心設計的作戰實驗來驗證作戰概念和構想, 只能結合戰爭實踐進行實驗和檢驗。戰場是最好的實驗室和試驗場, 即使一些戰法在理論上是合理的, 也須在真實戰場環境下進行實驗驗證, 這是因為戰法的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些未知因素的影響和假設前提是否成立。在兩次大戰和一些戰后局部戰爭中, 許多戰術實驗是在實戰中完成的。
1) 潛艇戰——“狼群”戰術
二戰期間德軍精心設計的許多潛艇戰術是通過作戰實驗/試驗進行驗證和提煉, 并最終應用于戰爭的。其中的“狼群”戰術最早由德軍潛艇指揮官鮑爾提出, 而海軍元帥鄧尼茨基于當時的裝備水平, 通過創新研究和大量的作戰實驗及演習, 將這一戰術逐漸開發成熟和完善。在早期缺乏潛艇的年代, 他們用魚雷艇代替潛艇進行“狼群”戰術實驗。

鄧尼茨認為, 集群作戰幾乎是歷史上所有戰斗的基本形式。由于指揮困難, 潛艇以前幾乎都是單艇作戰, 為實現集群作戰, 他進行了大膽的探索, 并指出: 潛艇兵力運用的基本設想、新戰術等都必須經過實驗/試驗的驗證[32]。
“狼群”戰術在結合實驗的訓練過程中攻克了許多難題。起初, 最先發現“敵艦”的潛艇在報告后立即攻擊, 其他潛艇再追上圍攻。演習證明, 這種戰法只能對付航速較低的船隊。后來, 在戰術巡邏線后面又配置1個或者數個艇群來對付運輸船隊, 使“狼群”戰術進一步完善。在大量的實驗和演習中, 潛艇部隊嘗試了各種隊形, 最后發現環形配置方式的效果最好: 敵艦進入環形配置海域后, 位于環形海域弧線上的其他潛艇能夠迅速趕到。演習中取得的所有經驗不斷加進條令中, 條令篇幅不斷擴大[30]。
在1937年舉行的德國大規模“國防軍演習”中, 鄧尼茨在1艘護衛艦上用無線電指揮潛艇群成功地搜索、跟蹤和攻擊了“敵方”艦隊和運輸船隊, 初步驗證了“狼群”戰術的有效性。后又分別在北海、大西洋、波羅的海等不同海域舉行了“狼群”戰術實驗。經過大量演習, 全面驗證了“狼群”戰術在不同海區的有效性, 并基本解決了“狼群”戰術的具體細節問題[30]。
2) 反潛戰
戰時護航戰是針對潛艇破交行動的作戰, 主要作戰樣式是“被動反潛戰”。由于條件所限, 很難在戰前進行規模性實驗, 盟軍主要通過結合實際戰斗, 在實踐中進行作戰實驗/試驗和檢驗。
護航船隊早在一戰期間就已出現, 英法試驗性地采取護航船隊方式后, 效果顯著: ①據計算, 潛艇發現一支護航船隊的概率與發現一艘獨行船只的概率相差很小。在良好條件下, 水面潛艇發現單艘船只的距離約為16 km, 而發現20艘艦船規模的船隊(寬約2 mile)的距離(距船隊中心)則約為17.6 km。顯然發現20艘單獨航行船只的累積概率要大得多, 護航船隊的優點明顯。②沿某一航線獨行的商船會形成綿延不斷的目標, 潛艇攻擊機會多; 而護航船隊雖龐大, 但攻擊窗口是有限的, 被攻擊的只是船隊中少數商船。③用有限的反潛兵力掩護船隊比掩護整個航運交通線效益更高。實驗/試驗成功后, 英國立即將護航體制推廣到90%的商船[28,33]。也有人認為, 護航體制使每次約有1/3的商船滯留在港口, 等待編入護航船隊, 影響運輸效率, 僅憑想象就認為應該用主動反潛取代被動護航。受此影響, 在二戰早期, 英國在實行護航制度的同時, 將大量反潛艦編成多支獵潛編隊, 在大洋上搜尋德國潛艇, 但如同大海撈針, 效果不佳。實際上, 戰時護航船隊是一種有效的“守株待兔”式的反潛方式, 事半功倍。戰爭時期的實踐表明, 護航反潛的戰績遠高于主動反潛大隊[31,33]。
結合各種裝備和戰術的實驗/試驗始終貫穿于護航反潛的戰爭實踐之中, 融入了實戰, 催生了一些被實踐證明有效的戰術戰法, 對盟軍在大西洋戰爭中最終獲勝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反潛困難時期, 英國軍方要求大家獻計獻策, 此后相繼出現了航空反潛深彈、機載雷達、無線電測向儀、“利式”探照燈、磁探儀(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s, MAD)、聲吶浮標以及機載反潛火箭彈等新式裝備。
MAD出現后, 美國運籌小組提出了以下戰術: 飛機進行“屏障巡邏”, 即在航道最窄處設置1個6.4 km×1.6 km的矩形區域, 2架飛機保持在長方形兩對邊線的相對位置上, 同時以184 km/h的速度繞圈飛行。這樣, 長方形上的每一點均能每隔3 min被“訪問”1次。即: 1艘60 m長的潛艇在2 kn流速下以2 kn航速潛航通過“屏障巡邏”區時, 機載MAD能有2次機會對其進行探測。發現磁擾信號后, 飛機進入“螺旋8字”跟蹤飛行, 依次用發煙彈連續標示目標位置, 以此可粗估出潛艇航向和航速, 然后與水面艦進行協同攻潛。經過實驗證明這種戰術有效, 英國將這種戰術投入使用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8]。
在封鎖英吉利海峽時, 為有效使用30架裝備雷達的巡邏機每30 min將2萬平方海里的海區搜索一遍, 英海軍設計了一套方案: 根據不同巡邏機的能力將巡邏區劃分為12個大小不同的長方形框, 框的周長等于飛機30 min或60 min飛行的距離, 如周長等于60 min的航程, 就派2架飛機以30 min的間距繞圈飛行。方框的寬度及與相鄰方框的距離大約是機載雷達發現水面潛艇距離的2倍。這就解決了速度、雷達各不相同的飛機之間的協同問題。可將這一嚴加封鎖的狹長水域看作是一個堵在英吉利海峽上的巨大軟木塞, 因此這一戰術以“軟木塞”而著稱。飛機沿長方框飛行時, 每隔30 min對整個區域搜索一遍。德國潛艇如發現雷達信號即行下潛, 很快就會耗完電量。為驗證“軟木塞”巡邏戰術的可行性和檢驗實際效果, 英國在愛爾蘭南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實兵實驗/試驗。英國“海盜”號潛艇奉命盡快在水面或水下完成90 n mile航程, 任務是躲避飛機的攻擊, 同時確保潛艇到達目的地參加戰斗。在28 h內, 潛艇只是間斷性地在水面航行了2 h。潛艇曾9次浮出水面, 每次上浮的時間平均約13 min, 這顯然不夠充電或補充壓縮空氣之用。在距目的地還有5 n mile時, 潛艇因電量將盡而不得不上浮認輸。在實際“參戰”的19架飛機中, 只有2架飛機發現了潛艇, 且都未能在潛艇下潛前實施“攻擊”。這次實驗/試驗回答了一個許多人長期質疑的問題: “飛機日夜巡邏, 卻很少發現潛艇, 航空巡邏反潛意義何在?” 19架飛機中只有2架發現了潛艇, 卻使潛艇自顧不暇, 完全喪失了作戰力, 這一事實對上述問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28]。
盟軍還根據實際作戰需求, 進行了一些帶有軍事背景的科學實驗。如: 英國通過海上實驗證明, 白色飛機被發現的距離比黑色飛機近20%。于是將反潛飛機的下面都噴了白漆。事實上, 海鷗等海鳥就是以白色為掩護色[31]。
時至今日, 反潛戰仍然是世界公認的難題。由于水下環境的復雜性, 許多因素對裝備效能的影響程度并不清楚, 因此一些戰術設想在不同條件下的有效性和適用范圍也不十分確定, 需要通過大量的作戰實驗、試驗、演習、甚至實戰來摸索和驗證。
3.1.3 二戰時期的水面戰和兩棲戰
僅靠新裝備并不一定能保證取得優勢, 還需開發與之相適應的戰法并進行實驗/試驗驗證。二戰初期, 美海軍并未認識到應針對新出現的雷達采用新的戰術, 而是采用密集單縱隊占據“T”字形陣位以充分發揮艦炮火力的傳統戰法, 因而在所羅門群島的早期夜戰中屢遭日本“長矛”遠程魚雷的齊射攻擊, 損失慘重。本來美軍擁有火力和信息優勢, 但卻沒能充分利用雷達來掌握戰場態勢和引導攻擊, 將密集縱隊暴露在敵方魚雷攻擊扇面內, 使己方的傷亡增加了4倍。后來美軍嘗試了新的策略, 組成了幾支分別由3~4艘驅逐艦組成的小分隊, 借助雷達保持分隊合理位置, 艦艏對敵, 事先不再進行炮擊, 協調轉向, 實施魚雷齊射。美海軍通過結合實戰的試驗找到了利用己方雷達優勢抵消敵方魚雷優勢的戰術, 從而轉敗為勝[34]。
二戰前, 美海軍陸戰隊通過每年一度的登陸演習和相關作戰實驗, 開發和檢驗了《登陸作戰試行手冊》, 摸索出了火力、近距離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方面的經驗, 并在演習中結合技術試驗, 推動了新型登陸裝備的服役[3,35]。
在其他作戰領域, 作戰實驗在德國著名的“閃電戰”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3,17,36]。中國地空導彈部隊則是通過戰前作戰實驗不斷驗證新的戰法, 在復雜對抗條件下接連成功擊落敵機[37]。
這些戰例展示了作戰實驗在戰法創新和優化中的作用。
3.2 現代案例
現代作戰實驗通常包括作戰概念開發、構造仿真、推演和實兵實驗等環節。通過實兵實驗, 可驗證作戰概念和模型、評估軍事技術及能力, 驗證戰術、組織和流程。如: 美海軍曾組織了長達5年的“海龍”系列作戰實驗, 從TTPs的基礎性驗證實驗開始, 以大規模的綜合性高級作戰實驗結束。
3.2.1 “寂靜鐵錘”實驗
“寂靜鐵錘”實驗于2004年進行, 其主要目的是驗證“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艇改裝為戰術巡航導彈核潛艇后納入打擊群的可行性。在實驗主要對象“佐治亞”號潛艇上臨時加裝了“戰斗管理中心”原形系統, 采用分布式情報監視偵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資源網絡。2架有人飛機分別模擬中空和低空無人機(unmanned aircraft vehicle, UAV), 提供光電傳感器功能; 一架波音707飛機搭載多任務ISR試驗床(testbed)系統, 模擬星載傳感器功能, 提供合成孔徑雷達和地面移動目標指示; 陸上無人值守傳感器提供地面態勢感知; 另一艘潛艇潛望鏡提供水面艦船光-電圖像。前沿指揮單元、戰斗管理中心的參謀人員、后方地面指揮單元及其參謀人員都可以通過一個“元數據架構”訪問所有ISR信息。實驗想定中還包括UAV、UUV的運用[5]。
3.2.2 新時代的“艦隊問題”演習和實驗
面對新的威脅, 經過數年的討論和推演, 美太平洋艦隊近年來已重新恢復了“艦隊問題”系列演習, 結合航母打擊群(carrier strike group, CSG)的部署與訓練, 探索和實踐先進戰術, 力圖激發新一輪戰術創新和變革。美太平洋艦隊司令Swift上將認為, 盡管艦隊具有基本戰術素質, 但由于訓練制度問題, 在例行訓練中, 指揮官個人難有機會演練復雜的作戰程序和發揮主觀能動性, 從而限制了訓練效率和TTPs的實際效能。因此, 應營造出能激發指揮官自身創造力和主動性的環境, 探索作戰藝術和檢驗各種假設[38]。
首先要提出“艦隊問題”演習中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 可通過推演來識別問題。在美海軍戰爭學院的幫助下, 提煉出了友方兵力部署、敵方態勢、作戰任務(mission)及雙方損失等關鍵要素, 將其作為“艦隊問題”的輸入,并設計了有助于發現問題的想定。美海軍認為, 只有進行近似實戰條件下的自由對抗, 才能發現問題中的關鍵因素, 從而找到解決方案。
當在潛艇威脅區運用CSG時, 傳統做法是進行反潛, 而在“艦隊問題”演習中, 艦隊并不直接向CSG下達為完成某項作戰任務(combat mission)而要執行的具體行動任務(task)(如“NLT 01100Z, 對……進行打擊”), 而是在時間和進程上給指揮官以最大的靈活處置權。CSG的作戰任務(mission)不是反潛, 而是在潛艇強威脅環境下執行核心作戰任務——打擊, 以支援聯合作戰。管控潛艇威脅是達到最終目的(打擊)的手段, 若消滅了敵潛艇且己方也未受損失, 但未能完成所賦予的作戰任務——打擊, 則行動是失敗的。演習組織者認為, 指揮應是基于作戰意圖而不是僵硬地執行計劃, 因此并未事先規定CSG司令應如何管控潛艇威脅, 他可選擇各種方案。在演習中的任務命令十分簡單, 只體現了基本作戰意圖, 而開發(develop)具體行動任務(task)的任務由各作戰單元或編隊自行完成[38]。
每次“艦隊問題”演習結束后, 主要指揮官都參加對抗部門(通常在艦上)的復盤, 在時間軸上來回移動, 仔細分析和討論從傳感器到射手的每一個事件, 自我檢討, 總結技術和戰術中的具體錯誤。通常由艦隊外的高級軍官充當雙方的裁判和觀察員。有時“艦隊問題”演習與海軍戰爭學院的推演并行進行, 隨時相互通報和比較。每個“作戰開發中心”和航母戰斗群常派出十多名參謀參加演習, 他們在各作戰部隊中觀察和學習, 將經驗教訓直接反饋到艦隊訓練部門, 有的參謀甚至在現場邊觀察學習邊形成戰術文件[38-39]。
2015~2017年共進行了超過6輪的“艦隊問題”演習(第23~28次)。美海軍認為, 恢復該系列演習是近年艦隊作戰中最重大的變化, 為學習作戰提供了一個戰斗實驗室, 促使艦隊全員共同思考作戰問題, 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完成作戰任務(mission)的關鍵推動者(enabler)。目前的一些標準TTPs并不完善, 需要通過作戰演習和實驗來摸索[40]。
在2017年舉行的第28次“艦隊問題”演習中, “羅斯福”號航母率第9 航母打擊群擔任藍軍, 數艘驅逐艦組成偵察監視編隊, 各艦拉開超出以往的間距, 前進到敵方能夠發現CSG的安全距離之外, 引導CSG的飛機和艦船搜索目標, 并提出攻擊建議。多個編隊分散配置兵力可避免因一輪偵察或打擊而全軍覆沒, 并有助于減小編隊總體目標特征, 提高生存力。最新型“標準”導彈的射程已達350 km, 可在一體化火控-防空系統(naval integrated fire control-counter air, NIFC-CA)的支援下攔截各類空中目標, 為CSG提供有效的保護傘。顯然, 海上分散部署是在針對遠程反艦導彈和高超聲速導彈出現后的海戰進行作戰實驗和準備[41]。
盡管美海軍一直未公布重啟后的“艦隊問題”系列演習的內情, 但高層透露的信息清楚地表明, 美海軍正在重拾“光榮傳統”, 將“艦隊問題”演習作為學習戰爭的作戰實驗室和海軍戰術的開發平臺, 驅動海上作戰體系的優化重構, 開啟對未來海戰模式的新一輪探索。
3.2.3 海上無人裝備的作戰實驗
美海軍在2016年“海軍技術演習”(ANTX)期間, 實驗演示了“潛艇-UUVs-UAV” 母子式(mother-daughter)協同作戰能力。潛艇先發射中型UUV, 中型UUV又發射2枚小型UUV和微型UAV, 執行偵察及通信中繼任務, 實現了母平臺(潛艇)對二級子平臺(小型UUV)的直接指揮。
英國在2016年的“無人勇士”演習中, 實驗演示了50多個UAVs、無人水面艇(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USVs)、UUVs等各類無人系統的偵察、反潛和反水雷能力。在反潛演習中, 首次運用4艘波浪滑翔式USV——傳感器密集型自主遠程艇(sensor hosting autonomous remote craft, SHARC)組成的持久機動探測網絡來搜索和跟蹤水下機動目標[42]。
3.2.4 “馬賽克戰”(Mosaic warfare)及其實驗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下屬戰略技術辦公室(strategic technology office, STO)在2017年公布了獲取非對稱優勢的新概念——“馬賽克戰”。馬賽克是由無數個“馬賽克碎片”組成的系統, 具有單元簡單、功能多樣、可快速拼裝等特點, 且缺少部分片段并不會對全局造成很大影響。DARPA將未來戰場描繪為: 低成本傳感器、多域指揮控制節點、有人和無人系統等“碎片”實時靈活組合, 構成任務不同、靈活機動的作戰網絡。即使局部被毀, 系統也能及時反應, 基本維持整體作戰效能。大量簡單系統集成后具有很高的生命力, 可在戰場上快速規劃和構建作戰資源網絡, 配置兵力與后勤, 快速變換作戰體系和交戰環境, 使對手陷入判斷和決策困境[43-45]。
為推動“馬賽克戰”概念和能力的發展, DARPA提出要發展“馬賽克實驗能力”。雖然“馬賽克實驗”目前仍處于概念開發階段, 但美軍已超前進行實驗/試驗技術研發和部署, 將利用各種實兵演習的機會, 針對作戰規劃、分布式作戰、對抗環境下的通信和動態適應網絡、低軌道星座、快響系統、無人裝備和預置武器、多域指揮控制、智能系統等技術及集成系統, 進行一系列作戰實驗。
4 作戰實驗設計和實施中的若干問題
由于軍事系統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人們對其規律的認識十分有限, 難以完全進行定量描述,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還需借助經驗和直覺。但經驗性的認識往往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 其客觀性和穩定性較差。因此, 規范的實驗方法十分重要。實驗一般分為設計、實施、評估3個主要階段, 美軍在這3個環節所占時間比約為4∶2∶4[5]。對于大型實驗, 一般需要數百人用1~1.5年進行計劃。
作戰實驗設計和實施需關注如下要點。
4.1 規劃與設計
4.1.1 目的與目標
實驗設計應圍繞目的及某項核心內容展開, 如: 開發或驗證某種理論、評估某類裝備或戰法等。實驗結果應能回答實驗提出者所關心的問題。如前所述, 根據實驗目的, 實驗主要可分為3種: 發現型、假設驗證型和演示型實驗。一般而言, 發現型實驗用于開發新概念和新方法; 假設驗證型實驗用于證偽(if-then形式的假設)或發現其限制條件; 演示型實驗是對已知原理的重現, 其目的在于說服和傳播[7]。
發現型實驗往往開始于相對粗糙的新思想或新問題, 只是一些尚無法精確定義的概念性“命題”, 主要是對事件進行觀察、定義和歸類。需要通過深入的創造性思考, 將原始想法轉化為有意義的變量、關系和條件。假設驗證型實驗的基礎是發現型實驗的結果, 實驗的目的是形成說明性或因果性的知識, 從僅僅描述“發生了什么”(what)擴展到能解釋“為什么發生”(how)。這類實驗需清晰地表達一系列相關假設、確定合理可信的準則、明確一系列具體的限制條件[3]。
不同實驗的區別之一在于實驗的逼真度和對實驗的控制。發現型實驗的環境一般都是人為專門構設的, 目的是聚焦少數關鍵變量。需仔細選擇觀察對象, 確定合理的觀察過程。為達到實驗目的, 實驗者可視情況制定新的規則、流程和組織方式。許多實驗, 尤其是發現型實驗, 都可能產生意料外的結果, 正是因為實驗結果和預期不同, 所以往往更有意義。它們可能揭示某些理論缺陷或實驗缺陷、發現新的現象和未預料到的限制條件、獲取未知的因果關系等新知識。有時實驗的目的就是發現問題, 而不僅僅是尋找答案。
4.1.2 問題設計
實驗問題設計是對軍事需求和實驗目的的直接體現, 建立問題框架是實驗設計的核心, 也往往是最困難的環節。
應明確基本實驗問題、命題與假設、指標和準則、實驗中的變量及其可能的關系。實兵實驗關注的問題既可以是基于現有裝備和兵力組織形式的戰法開發問題, 也可是未來作戰概念和思想的探索研究問題。隨著實驗研究的深入, 對作戰問題的認識會逐步深化, 從而發現新的問題和影響因素。例如: 美海軍陸戰隊為期2年的“城市勇士”系列實驗表明, 城市戰術在諸多方面很不理想, 于是開發出一套新的戰術和訓練課程, 并通過相關實驗來考察其有效性。因此, 系列化實驗、問題的逐步聚焦、相關概念的形成等, 是一個循環迭代過程[1]。
建立問題框架需要確定: 問題及其背景、問題分析目的(如概念驗證、戰法研究、能力評估)和目標、實驗范圍、實驗對象、實驗因素、評判準則及問題的形式化描述等。例如, 若對武器防御問題進行實驗, 需確定: 實驗目的是系統概念方案驗證還是戰法研究, 是針對單武器(如軟、硬武器)系統還是綜合防御系統, 若是硬武器, 評判指標是取攔截成功率還是平臺總體生存率等等。這一系列相互關聯問題都需在問題框架設計中完成, 這樣才能達到實驗目的。
實驗組織者一般都希望通過實驗獲知: 新裝備及其使用方法的效能和優勢, 新戰術的可行性、有效性、優勢和適用范圍等等。要回答這些抽象問題, 就須針對具體對象設計一些分解后的詳細問題。例如: 要通過實兵實驗來探索和驗證“海床戰”等作戰概念, 就需對系統及功能結構進行分解, 針對用戶關心的投送、感知、目標指示、通信、載荷、響應速度及持久力等關鍵能力設計問題, 進而指導實驗詳細設計。鑒于軍事問題的復雜性、關聯性, 應避免過早縮小關注的問題, 也要盡量避免提出一些簡單、孤立、模糊的問題。
4.1.3 實驗規劃
最初的想法和觀點往往比較粗糙, 戰爭問題十分復雜, 僅靠有限的單項實驗不足以產生和驗證完整的作戰概念, 難以完全發現全局性的問題, 為形成完整的理論和方法, 加深對作戰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并獲得相關性、有效性、可重復性和可信性, 統籌規劃、有計劃地開展相互關聯的系列化實驗和綜合性實驗十分必要。
應避免針對某些孤立問題、或僅僅是為了響應上層意圖而匆忙進行的“任務式”實驗, 不應進行缺乏前期實驗基礎的“跳躍式”實驗, 防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低水平重復。還要避免對某項特定實驗期望過高, 超出了單項實驗的能力范圍。在單項實驗里涵蓋過多的內容, 易導致顧此失彼, 無法得到有效信息。
4.1.4 方案設計
作戰實驗設計是指, 根據實驗目的和要求, 針對實驗問題, 對實驗要素、想定、方法和程序, 以及實施方案進行設計, 以達到預期目的。實驗設計質量直接決定了實驗結果及其事后分析的有效性。作戰實驗設計需部隊、研究部門和實驗機構共同參與。不同的目的會導致不同的實驗思路和方法, 對水下戰而言, 分別關注隱蔽攻擊、遠程引導攻擊、水下防御等不同主題的設計者, 會設計出不同的實驗, 使之能回答(或部分回答)決策者、部隊和分析人員提出的問題。
實驗設計的主要內容有: 實驗目標、分析框架、關鍵輸入(自變量)、重點觀察變量(主要因變量、關鍵中間變量)、輸出、約束條件、實驗指標及測量方法、實驗想定、控制無關變量的措施、實驗部隊、評估人員、數據采集方法、實驗步驟、統計方法, 以及評估方法等。
實驗的主要風險有: 1) 在情況不明和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匆忙啟動實驗; 2) 在不成熟的情況下草率確定實驗方案; 3) 采用試錯法, 而不是依據理論指導實驗; 4) 忽視部隊的經驗和創造力[7]。因此, 實驗前應周密考慮和分析每一個步驟和可能的結果, 即進行“思想實驗”。
實驗指標反映了人們對實驗問題的認識程度, 其主要選取原則: 1) 能表征問題的本質特征; 2)聚焦, 排除次要因素; 3) 客觀公正性, 直接來自于實驗, 避免引入主觀因素, 不偏不倚, 最忌為某一預設結論尋找論據。
實驗因素以及水平的選取——實驗因素即實驗變量。實驗者應選擇與研究目的有關的“控制因素”, 并闡述選擇理由, 以便讓實驗人員能充分理解其對實驗的影響。原則上應選取那些對實驗結果影響大、相對獨立、便于觀察和數據收集的因素。水平是因素在實驗中所取的狀態, 即“實驗點”。對于成本高昂的實兵作戰實驗, 難以承受水平數過大的實驗。即使是作戰仿真實驗, 也盡量控制水平數。例如: 美國蘭德公司在針對2005年臺海軍事沖突的仿真實驗中共選取了7個因素, 其中有5個取2~3水平, 只有美軍介入的部隊數量這一項取6水平, 從實際分析結果看, 美軍部隊介入的數量取3水平(不介入/少量介入/中等介入)也會得出相似的結論[17]。
為保證效益, 在實兵實驗之前, 應通過充分的仿真實驗來確定關鍵因素、揭示理論上的關聯性、分析敏感性和敏感區間, 從而指導實兵實驗方案設計。
4.1.5 想定設計
北約《指揮控制評估準則》(2002版)將“作戰想定”定義為: “根據一定的研究目標和符合作戰原則的情況假設, 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對與作戰行動有關的作戰區域、作戰環境、作戰手段、作戰目標和其他事件進行的假想描述”。可見, 作戰想定由以下基本要素構成: 地域/海域, 參與方, 各方作戰企圖和目標, 各方兵力規模、作戰能力和作戰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 以及事態發展的時間表等。實驗設計中制定作戰想定的目的是為綜合考察各種作戰變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提供合適的條件, 確保分析的客觀性、全面性[17]。簡言之, “想定”是在演習和作戰實驗/試驗中對交戰雙方的企圖、態勢以及戰斗發展情況的設想和假定。實驗想定應具有典型代表性, 從而能夠從實驗結果得出廣泛意義上的結論。
想定所需的詳細程度取決于實驗的目標, 應合理把握想定的粒度。想定過細, 喧賓奪主, 可能會掩蓋問題的本質, 難以對數據進行有效的歸納; 想定太粗, 實驗將無法獲得足夠的數據來支持結論[17]。
想定決定了實驗的約束條件, 合理的想定是確保實驗結果可信性的關鍵之一。在想定設計中, 應注意避免對實驗結果先入為主的成見, 避免過早地排除可變因素。在實兵實驗中, 為保證實驗進程的可控性, 一般應給參與者以明確的提示, 如須采取的行動、不得采取的行動、何時可自行決策和行動等。
應提煉出實驗的關鍵點和難點, 給予重點關注, 進行有針對性的想定設計。一般不應脫離實驗目的套用“通用”想定, 應設計能突顯問題的想定, 使實驗能聚焦問題, 得到預期成果。例如: 若實驗是為了探索或驗證某種攻潛戰術, 所設計的想定就不應讓海上兵力花大量時間去搜潛。
4.2 實施
4.2.1 實兵作戰實驗與演習、訓練、試驗的結合
從形式上看, 實兵實驗非常類似于演習, 但實驗在目的、內容、方法及規則等方面畢竟不同于常規演習。必要時應說明兩者的區別, 使參與者充分理解實驗的目的——要解決什么問題。
應盡量結合訓練、演習和OT&E進行作戰實驗, 因為平時難以獲得這樣豐富的兵力和保障資源。大多數國家沒有專職于實驗的部隊和編制, 因此就需考慮如何利用常規訓練、演習等活動。實驗和訓練、演習、試驗相結合的意義不僅是節約資源, 更是可利用關聯的實踐活動相互支持、豐富內容, 通過實驗與實踐相結合, 達到探索、研究和驗證的最佳效果。
4.2.2 實兵作戰實驗中的模擬兵力
模擬兵力主要可分為2種: 計算機虛擬兵力和替代兵力。
在美軍“千年挑戰2002”聯合軍演中, 非野戰參演人員超過2000人, 野戰演習有13500名官兵參加, 虛擬兵力達到7萬人。演習中80%的戰斗都是模擬的, 分布在17個計算機網絡和模擬器上進行。該演習是美軍史上規模最大、最復雜的實兵與模擬相結合的演習, 檢驗了美軍許多新的作戰思想和作戰原則[46]。NUWC則是利用SETI生成海上虛擬兵力和兵器, 與實兵一起進行海上作戰訓練、實驗和試驗[19]。
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 可用替代裝備和原型裝備進行作戰實驗。如: 美國在當年的“艦隊問題”演習中, 由于航母數量不夠, 曾用其他艦只代替航母, 用一架飛機代表一個機群。再如: 受“凡爾賽條約”的制約, 德國二戰前很長時期沒有潛艇, 鄧尼茨便使用驅逐艦和魚雷艇替代潛艇進行“狼群戰術”的作戰實驗。德軍在“閃電戰”作戰實驗中, 則是用運輸車代替坦克。
4.3 分析與評估
4.3.1 分析和評估隊伍
應建立包括實驗需求開發者、實驗設計者、部隊人員、裝備設計師以及專業實驗/試驗人員在內的分析評估隊伍。作戰實驗最忌虎頭蛇尾、簡單總結、匆匆收場。實驗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得出結論, 更重要的是通過深入細致的分析, 找到解決問題、改善能力的途徑。這需要得到更大范圍的專家智囊隊伍的支持, 常需要跨領域專家、科學家、軍事運籌專家及數學家的協作。
專家智囊在作戰分析中的作用有目共睹,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Blackett教授(后獲諾貝爾獎)及其團隊在二戰反潛戰中的重要貢獻。他和助手們組成了運籌(operations research)小組, 在對軍方提供的作戰報告和大量作戰數據進行仔細分析研究后, 總結出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從而大大提高了英軍的反潛效率。例如: 經過對護航船隊數據的分析, 布萊克特認為護航船隊規模越大, 效能就越高。根據圓面積和周長的數學關系, 船隊中的商船數目每增加一倍, 護航艦艇的數量只需增加33%即可。此外, 擴大護航船隊規模, 減少出航次數將會減少總體被發現概率。一支護航船隊所受損失到了一定程度后便不會再增加, 這是因為被“狼群”擊沉的船只數量受限于潛艇數量、魚雷攜載量和再裝填能力。因此, 一支艇群攻擊一支大型船隊所能擊沉的船只數量與攻擊一只小型船隊時基本相同, 而一支大型護航船隊的規模相當于2~3支小型護航船隊, “狼群”卻只有1次攻擊機會。該建議在付諸實施后收到了巨大成效[33]。運籌小組還為英海軍改進了航空深彈攻擊方法, 提高了命中率; 甚至還和戰術開發小組共同提出了一種將聲吶浮標與MK 24自導魚雷相結合的攻潛方法[28]。
美國的一些部門和機構有專門的分析評估團隊, 他們將作戰分析與實驗評估、戰場評估結合在一起, 為美海軍提供廣泛的支援。例如CNA就是從早期美海軍反潛戰運籌小組發展而來, 下屬部門中包括先進技術和系統分析部門和作戰評估組(operational evaluation group, OEG)。后者主要針對戰場項目(field program)分析和探索作戰問題, 研究部隊訓練程序和技術, 評估新的作戰概念及其效能。在重大軍事任務期間, OEG派分析人員深入到各地指揮部和一線作戰部隊。
4.3.2 實驗結果分析
實驗的目的并非僅是獲得結果, 而是要找到原因、摸清機理和規律, 這就涉及到對實驗結果的分析與解釋問題。對實驗中發現的現象做出理論解釋并得出結論, 是整個科學研究中的理性認識階段, 也是作戰實驗中最深刻、最有指導意義的部分[17]。
實驗報告應包括: 實驗想定、模型、假設、限制條件、主要數據源、作戰過程分析、實驗結果及其意義、主要影響因素及敏感性等。與常規試驗報告不同, 實驗報告不僅是對實驗過程和結果的客觀描述, 更要注意闡述現象及其意義、分析原因、提出下一步實驗建議[47]。有些作戰實驗可能得到意外的結果, 這常可產生更大的啟發作用, 促使作戰分析人員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 激發新思路。
實驗分析大都采用統計分析方法, 但目前存在的普遍現象是對數據變化分析、原因分析等工作做得不深入, 即: 重一般數據統計和平鋪直敘, 輕關鍵變量分析和深度解釋。問題分析流于簡單化、表面化, 一些所謂的“綜合分析”變成了模糊、粗糙、“八股文”式的定性分析的代名詞, 這往往導致對數據背后的含義解釋不清, 難以發現真正的規律, 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作戰實驗作用的發揮。這種浮于表面的實驗分析所導致的一個現象就是: 各次實驗總結報告除一些具體數據外, 內容雷同, 建議空洞, 更像是情況通報, 而不是有啟發意義的研究報告。
作戰實驗就是發現問題、尋求因果關系, 但在現實世界中許多因果關系并不明晰, 大數據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將因果分析轉化為相關性分析。在現實中, 這種方法能解決許多工程應用問題, 許多現代人工智能方法秉承的也是這一思路。水下作戰實驗十分復雜, 人們對許多現象的物理機理及因果關系尚未掌握, 大數據分析可在某些場合下發揮作用, 幫助人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實際上, 大數據分析的意義在于其多維度和完備性, 這2個特性使得看似無關的現象聯系起來, 形成對客觀事物全方位的完整描述。
4.3.3 關于效能評估問題
雖然上層通常最關心的是裝備或戰法的作戰效能, 但要通過有限幾次實兵實驗和演習對作戰效能做出準確評估是不現實的。作戰效能應建立在足夠數據量的統計分析之上, 一般而言, 仿真是主要分析手段, 實驗和演習是主要驗證手段。
效能分析和評估主要有2種途徑: 1) 采用形式化的效能評估模型。如: WSEIAC(weapons systems effectiveness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模型、指數(index)法、SEA(system effectiveness analysis)法、層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等。但迄今為止, 各種效能評估模型都存在一個致命缺陷——理論上沒有得到證明, 這就使其科學性大打折扣。此外, 這些模型一般都是靜態的, 很難反映出動態作戰過程。2)基于仿真的統計評估方法。這種方法更直接, 相對客觀、可信, 是國內外效能評估的主流方法, 當然還需結合各種實驗、試驗和演習對模型進行驗證[48]。
4.3.4 評估結論
實驗評估階段要回答“實驗收獲了什么”的問題, 這是從感性到理性的知識升華過程。須避免依賴試錯法和“就事論事的評估”, 而應在理論指導下進行實證性評估。
不應完全按嚴格的學術標準得出實兵實驗的結論, 也不應以少數幾個實驗作為重大決策的依據。僅憑個別實驗就大膽給出重大結論報告的現象經常出現, 有些研究者往往聲稱已掌握“證據”證明某重要概念或思想具有重大軍事價值, 但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風險很大[7]。實驗結論在多數情況的普適性和在對抗條件下的適用性值得重點關注。
對實驗結果的分析不能僅靠直覺, 而要靠嚴密的理論分析。這樣的教訓很多, 如: 二戰中美潛艇艇長擔心暴露而不愿使用對空雷達, 這是由于使用雷達時發現的飛機數量確實增加了, 然而, 分析表明潛艇周圍敵機的密度并未增加, 而發現敵機數量的增加完全是因為雷達的探測距離增大。再如: 1943年, 德國對潛艇在比斯開灣經常到飛機夜襲一直迷惑不解——盟軍飛機為何能在夜間對德國潛艇準確定位?為何曾十分有效的“梅托克斯”雷達偵察機不報警?起初, 德國情報軍官曾正確地猜測出盟軍使用了厘米波雷達, 于是加裝試用了新型雷達接收機, 但因產品不成熟而效果不佳, 德國人轉而誤認為是老式“梅托克斯”接收機本身的電磁輻射暴露了潛艇位置。盡管大多數無線電專家對此不認同, 鄧尼茨還是下令停用, 這成了二戰中“電磁輻射恐慌”的大笑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 只要千方百計去尋找, 幾乎任何觀點都可能找到論據加以證實。鄧尼茨竟將“梅托克斯”接收機的輻射現象同過去許多難以理解的事情聯系起來。巧合的是, 在該型接收機停用的時段內, 德國潛艇在比斯開灣的損失為零, 這使希特勒信以為真。而實際原因是, 德國潛艇通過該區域的數量減少了, 且采取了夜間在水面沿雷達不易發現的海岸航行的措施[28]。另一個例子是1940年德國V2導彈對倫敦的大轟炸。從報紙上公布的標記有遭轟炸地點的倫敦地圖中, 人們發現轟炸點分布很不均勻, 于是引起了各種猜疑, 軍方擔心V2導彈具有很高的精度, 以至于德軍能夠選擇攻擊目標; 民眾則以為那些未遭攻擊的地區是德國間諜居住地, 有人甚至開始搬家。更有甚者, 有人根據導彈落點更多散布在倫敦東部平民區而推測, 德國是故意激發英國的階級對立, 影響民眾的抵抗意志。直到戰后, 有人用網格法從數學角度分析了轟炸數據后發現, 雖然落點不均勻, 但完全符合特定隨機分布。事實上V2導彈在當時是精度很差的武器。可見, 依據事實的深入科學分析和僅憑表象的主觀臆斷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要使評估結論具有說服力, 就應給出充分的證據。但正如上例所述, 對于任何觀點, 只要有目的地去竭力尋找, 幾乎都可能找到支持的論據, 這往往來源于人們先入為主的“選擇性偏倚”。這就提出了證據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問題, 具體涉及到證據的真實性、相關性、穩定性和時效性等。盡管有些證據是真實的, 但可能并非主要因素, 且與主題的相關性弱、重要性低。穩定的證據應具有可重復性, 對于多平臺、多區域、多時段具有一致性。應關注證據的時效性, 有些證據強度會隨時間減弱。對證據本身的評價是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可嘗試根據置信程度對證據進行分級, 如詢證醫學中的5級證據分級方法。同樣的事實用作不同領域的證據時, 有效性是不同的。對于軍事領域而言, 數據來源的權威性直接決定了證據的質量, 可作為證據分級的參考依據。總之, 證據是科學評價的基礎, 證據質量決定了評估結論的置信度。因此應對實驗證據問題高度關注。
5 結束語
作戰實驗作為現代軍事科學的助推器, 正受到廣泛重視。西方在進行實驗活動的同時, 也在進行作戰實驗問題的理論研究。1999年, 美軍指揮與控制研究項目組(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program, CCRP)發布了首版《作戰實驗法規》及“實驗程序清單”, 此后又根據實踐不斷更新; 2002年, 北約發布了《指揮與控制評估法規》。這些文件的發布規范了作戰實驗活動, 推動了作戰實驗向科學、有效的方向深入。
實兵作戰實驗之所以重要, 其中一個原因是作戰過程中的“涌現性”。涌現性(emergent properties)是指系統具有各構成要素所不具備的性質, 即“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一般認為, 系統結構、環境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決定了系統整體性能, 有些性質只有在高層次系統中才會出現, 即所謂“涌現”。在自然界中, “涌現性”典型的例子有: 螞蟻和蟻群、神經元和大腦等。作戰過程顯然具有涌現性, 尤其是復雜的水下戰, 往往會因各種未知要素的交互作用而出現意料外的情況。正如美海軍Fitzgerald將軍當年為一個水下戰研究項目在美眾議院聽證時的形象比喻: “反潛戰是一個取決于環境的、巨大的復雜問題。只靠買潛艇和飛機解決不了這一問題。它就像一個拼圖, 需要100拼塊才能構建出完整圖像, 而我們可能只掌握了45塊……。某一天運氣好, 我們可能又掌握了30塊……。”[49]。水下戰的復雜性正是源于環境的復雜性和諸多因素交織而產生的涌現性。因此, 現有許多理論模型往往是不很可靠的, 僅靠理論分析和仿真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需要通過近似實戰條件下的作戰實驗來發現現象, 為下一步揭示機理、利用現象和制定對策提供輸入。
作戰實驗是作戰開發及驗證的主要手段, 西方國家將作戰概念和戰法創新建立在實驗科學的基礎之上。近年來, 美軍對未來作戰概念進行了大量開發和早期實驗。如美軍提出了可用于支援未來多種作戰行動的信息引誘戰, 其目的是誘敵機動—開啟主動傳感器—使用武器。其下的一系列戰術概念與美AUV發展規劃中的電磁機動戰(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maneuver warfare,EMMW)、“欺騙戰”、“海床戰”等概念一脈相承。例如: “獵手-殺手”概念是指用低成本的非隱身平臺喚醒敵方目標, 如使用可模擬潛艇或魚雷特征信號的UUV, 誘使敵方潛艇做出反應, 再由殺手平臺摧毀目標; “武器海綿”戰術是指用多譜誘餌和信息欺騙技術, 引誘對手向假目標發射武器, 使敵方浪費武器和暴露位置, 增加敵方目標識別的負擔, 通過信息過載造成反應滯后, 從而使本方獲得主動權; “虛擬佯攻”戰術是指使用多譜誘餌和其他欺騙技術, 誤導對手, 使其將ISR資產投入到錯誤方向上; “信號特征增強”戰術是指通過在敵平臺上附著某些信標或浮標進行“標記”。此外, 還有“通道作戰”、“反堡壘區”、“水下打擊模塊”等其他作戰概念。美國正在開發一系列與這些作戰概念相關的新型水下戰裝備和技術, 并將進行相關作戰實驗和試驗[50]。
在軍事科學領域, 軍事理論研究、技術開發和作戰實驗是相輔相成的3個基本支柱, 作戰實驗的主要作用在于對軍事科學問題進行實證[51]。要想避免“坐而論道”、“紙上談兵”, 就要勇于進行實兵實驗, 通過不斷實踐, 逐漸發展出順應時代潮流的、科學合理的作戰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而“預實踐”是探索真理、尋求真諦的必要途徑——這就是實兵實驗的意義所在。
[1] 曹欲華, 管清波, 白洪波, 等. 作戰實驗理論與技術[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3.
[2]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Guide fo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Defense Experimentation[R]. US: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2006.
[3] McCue B. Military Experiments before World War II[M]. US: Wotan’s Workshop, 2009.
[4] 錢東, 趙江, 楊蕓. 軍用UUV發展方向與趨勢(上)——美軍用無人系統發展規劃分析解讀[J]. 水下無人系統學報, 2017, 25(1): 1-30.Qian Dong, Zhao Jiang, Yang Yun.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UUV(Ⅰ): A Review of U.S. Military Unmanned System Development Plan[J]. Journal of Unmanned Undersea Systems, 2017, 25(1): 1-30.
[5] 李輝. 美軍作戰實驗研究教程[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3.
[6] Shephard News Team. SeaFox Takes Part in US Navy Fleet Experiment[EB/OL]. (2012-09-10)[2015-05-29]. http://www.shephardmedia.com/news/uv-online/seafox-takes-part-us-navy-fleet-experiment/.
[7] Alberts D S, Hayes R E. Campaigns of Experimentation: Pathways to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Code of Best Practice)[M]. US: DoD CCRP, 2005.
[8] 錢東, 趙江. 關于戰術、技術與程序的思考與啟示[J]. 魚雷技術, 2015, 23(4): 241-256.Qian Dong, Zhao Jiang. Discussion on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J]. Torpedo Technology, 2015, 23(4): 241-256.
[9] 王凱, 趙定海, 閆耀東.武器裝備作戰試驗[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2.
[10] Kass R A, Alblerts D S, Hayes R E. 作戰試驗及其邏輯[M]. 馬增軍, 孟凡松, 車福德, 等譯.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0.
[11] 呂廣躍, 方勝良.作戰實驗[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7.
[12] 江敬灼.作戰實驗若干問題研究[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0.
[13] 陳建華, 李剛強, 傅調平.艦艇戰法實驗與分析[M].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0.
[14] 卜先錦, 張德群. 作戰實驗學教程[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3.
[15] 戰曉蘇. 作戰實驗工程基礎教程[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3.
[16] Albers D S(美). 軍事實驗最佳規程[M]. 郁軍, 周學廣, 譯. 北京: 電子工業出版社, 2009.
[17] 王本勝, 趙子海. 戰法實驗理論與方法[M].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7.
[18] 周玉芳, 余云智, 翟永翠. LVC仿真技術綜述[J]. 指揮控制與仿真, 2010, 32(4): 1-7.Zhou Yu-fang, Yu Yun-zhi, Zhai Yong-cui. Review on LVC Simulation Technology[J]. Command Control & Simulation, 2010, 32(4): 1-7.
[19] 錢東, 唐獻平, 崔立. 美國海軍預研中的魚雷新技術[J]. 魚雷技術, 2003, 11(1): 1-5.
[20] 廖德力, 錢東, 高軍保, 等. 魚雷及其武器系統的作戰試驗與評估(OT&E)[J]. 魚雷技術, 1998, 6(4): 39-43.
[21] 錢東, 崔立. 美軍的先期概念技術演示驗證[J]. 魚雷技術, 2002, 10(4): 1-5.
[22]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NA 1942~2017[EB/OL]. 2017[2017-08-12]. https://www.cna.org/.
[23] 胡斌, 王曉彪. 美軍作戰實驗室發展綜述[J]. 軍事系統工程, 2000(3): 32-36.
[24] Leopold J. How Guantanamo Became America’s Interrogation ‘Battle Lab’[EB/OL]. (2015-01-12)[2015-05-10]. https:// news.vice.com/article/how-guantanamo-became-americas-interrogation-battle-lab.
[25] 譚星. 全甲板攻擊——戰火中成長的美國航母[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26] Wadle R D. United States Navy Fleet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rrier Aviation, 1929-1933[R]. US: Texas A&M University, 2005.
[27] Ensign Hederman. Blocks up the Panama Canal[EB/OL]. (2018-07-04)[2018-07-04]. http://www.strategypage.com/ cic/docs/cic127b.asp.
[28] 普賴斯A(英). 空潛戰[M]. 韋晉光, 李安林, 譯.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0.
[29] 安東尼·普雷斯頓(英). 潛艇發展史[M]. 李加運, 譯. 北京: 中國市場出版社, 2009.
[30] 劉桓. 大西洋上的狼群——希特勒的狼群[M]. 哈爾濱: 哈爾濱出版社, 2013.
[31] 王志強. 護航大海戰[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32] 卡爾·鄧尼茨(德). 德國海軍戰略[M]. 上海外國語學院,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33] 戴維·喬丹(英). 大西洋潛艇戰——希特勒的狼群[M]. 張國良, 胡偉, 謝伏婭, 譯. 北京: 中國市場出版社, 2010.
[34] 韋恩·休斯(美). 艦隊戰術和近岸戰斗[M]. 易亮, 譯.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6.
[35] 伊恩·斯佩勒, 克里斯托弗·塔克(英). 搶灘——兩棲戰的戰略、戰術和戰例[M]. 張國良, 谷素, 譯. 北京: 軍事誼文出版社, 2010.
[36] 富勒J F C(英).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戰略與戰術[M]. 胡毅秉, 譯. 北京: 臺海出版社, 2018.
[37] 陳輝亭. 中國地空導彈部隊作戰實錄[M].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8.
[38] Swift A S H. Fleet Problems Offer Opportunities[J/OL]. Proceedings, 2018, 144/3/1, 381. (2018-07-05)[2018-06- 16].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8-03/fleet-problems-for-opportunities.
[39] Rielage D. Bring Back Fleet Battle Problems[J/OL]. Proceedings, 2017, 143/6/1, 372. (2017-06)[2018-08-04].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7-06/bring-back-fleet-battle-problems.
[40] Eckstein M. Fight to Hawaii: How the U.S. Navy is Training Carrier Strike Groups for Future War[EB/OL]. (2018-03-22)[2018-08-04]. https://news.usni.org/2018/03/ 22/fight-hawaii-u-s-navy-training-carrier-strike-groups- future-war.
[41] 羽旌. 決勝未來海戰場——美海軍重啟“艦隊問題”演習原因淺析[J]. 艦船知識, 2018(6): 34-39.
[42] 錢東, 趙江, 楊蕓. 軍用UUV發展方向與趨勢(下)——美軍用無人系統發展規劃分析解讀[J]. 水下無人系統學報, 2017, 25(2): 107-150.Qian Dong, Zhao Jiang, Yang Yun.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UUV(Ⅱ): A Review of U.S. Military Unmanned System Development Plan[J]. Journal of Unmanned Undersea Systems, 2017, 25(2): 107-150.
[43] Bellamy W. DARPA Seeks ‘Mosaic Warfare’ Approach to Future Conflicts[EB/OL]. (2018-09-06)[2019-09-15]. https://www.aviationtoday.com/2018/09/06/darpa-seeks-mosaic-warfare-approach-future-conflicts/.
[44] Magnuson S. DARPA Tiles Together a Vision of Mosaic Warfare[EB/OL]. (2018-01-08)[2019-09-15]. https:// www.defensemedianetwork.com/stories/darpa-tiles-together-a-vision-of-mosaic-warfare/.
[45] Williams B D. DARPA’s ‘Mosaic Warfare’ Concept Turns Complexity Intoasymmetric Advantage[EB/OL]. (2017- 08-14)[2019-09-15]. https://www.fifthdomain.com/dod/20 17/08/14/darpas-mosaic-warfare-concept-turns-complexity-into-asymmetric-advantage/.
[46] 柯林. 作戰模擬與伊拉克戰爭[J]. 軍事運籌與系統工程, 2003, 17(3): 54-57.
[47] 王劍飛, 張輝, 岳秀清, 等. 關于加強我軍作戰實驗結果分析和解釋的思考[J]. 軍事運籌與系統工程, 2007, 21(4): 59-61.
[48] 錢東. 關于戰術、對裝備論證中有關問題的認識[J]. 魚雷技術, 2006, 14(4): 1-6.Qian Dong. An Understanding of Equipment Demonstration[J]. Torpedo Technology, 2006, 14(4): 1-6.
[4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dvanced Submarine Technology and Antisubmarine Warfare[M]. US: Uni- 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50] 黃承靜, 魏佳寧, 姜百匯, 等. 預己從嚴: 兵棋推演及其應用[M]. 北京: 航空工業出版社, 2015.
[51] 王輝青. 作戰實驗若干基本理論問題探討[J]. 軍事運籌與系統工程, 2008, 22(1): 3-8.
作者.題目(年-卷-期)
1. 黃穎淞, 葛輝良, 王付印, 等. 蛙人探測聲吶系統發展綜述(2020-28-1)
2. 孫芹東, 蘭世泉, 王超, 等. 水下聲學滑翔機研究進展及關鍵技術(2020-28-1)
3. 何心怡, 陳雙, 陳菁, 等. 國外反潛訓練靶標應用現狀與啟示(2019-27-6)
4. 錢洪寶, 盧曉亭. 我國水下滑翔機技術發展建議與思考(2019-27-5)
5. 吳尚尚, 李閣閣, 蘭世泉. 水下滑翔機導航技術發展現狀與展望(2019-27-5)
6. 文海兵, 宋保維, 張克涵, 等. 水下磁耦合諧振無線電能傳輸技術及應用研究綜述(2019-27-4)
7. 劉偉, 范輝, 呂建國, 等. 超高速水下航行器控制方法研究熱點綜述(2019-27-4)
8. 嚴浙平, 劉祥玲. 多UUV協調控制技術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2019-27-3)
9. 黃玉龍, 張永剛, 趙玉新. 自主水下航行器導航方法綜述(2019-27-3)
10. 胡橋, 劉鈺, 趙振軼, 等. 水下無人集群仿生人工側線探測技術研究進展(2019-27-2)
11. 王延杰, 郝牧宇, 張霖, 等. 基于智能驅動材料的水下仿生機器人發展綜述(2019-27-2)
12. 魏博文, 呂文紅, 范曉靜, 等. AUV導航技術發展現狀與展望(2019-27-1).
13. 張萌, 譚思煒, 張林森. 美海軍三型魚雷最新研發進展及技術途徑(2019-27-1)
Summary of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at Sea——Concepts, Cases and Methods
QIAN Dong, ZHAO Jiang
(Naval Research Academy, Beijing 100161, China)
The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is the key part in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 concept and tactics, force application and forc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 scientific and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main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U.S. Navy. Some historical and modern cases of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s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famous “Fleet Problem” exercise of the U.S. Navy and th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undersea warfar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Some issues abou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periment are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objective of the experiment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iming at discovering new phenomena and mechanisms. A reasonable problem frame is a prerequisite for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Systematic planning should be made for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avoid isolated and “jumping”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factors and levels, and the partitions and specificity of operational scenarios should be considered properl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nfidence of experiment results. A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should combine with exercise or training to achieve best results in limited resources condition. Professional teams of analysts and experts are need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evidence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is a necessary way to develop modern warfighting theory.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military excise; undersea warfare
E0-03; E112; E139
R
2096-3920(2020)03-0231-21
10.11993/j.issn.2096-3920.2020.03.001
2018-12-06;
2019-01-04.
錢 東(1958-), 男, 高級工程師, 長期從事魚雷武器系統總體技術研究.
錢東, 趙江. 海上實兵作戰實驗綜述——概念、案例與方法[J]. 水下無人系統學報, 2020, 28(3): 231-251.
(責任編輯: 陳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