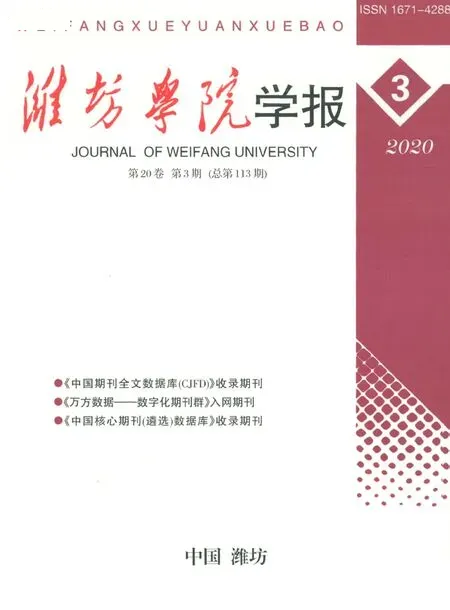淺談王石經的篆刻藝術
遲星飛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王石經(1833~1918),濰縣城里(今濰城區)人,字君都、郡都,號西泉,別號甄古齋主,是清末民初名揚齊魯聲及天下的篆刻家。他一生愛好金石文字,善書篆隸,他的篆書高古博深,多取法古籀、石鼓文字及秦李斯篆,于金石意味中兼有端莊儒雅的氣質;隸書博采漢碑佳作,風格規整,筆畫沉厚樸實,強調內斂之勢而少外拓之姿,以古樸渾厚見長。當然,王石經最為世人稱道的還是他的篆刻藝術,他的篆刻主要取法秦漢印,也從秦權、詔版、量、瓦等處有所借鑒,從集字到鐫刻,筆筆見法,字字有據,不失秦漢之風,被看作是晚清璽印派工整一路的代表性人物。
王石經一生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清末五朝以及民國初期,這也正是篆刻學大盛的年代。篆刻藝術形式在經過明清之際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突破之后,作品形式基本趨于穩定,成為了專門之學,文人領域掀起了金石創作的熱潮,其學術水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皖派、浙派為代表的篆刻藝術流派如雨后春筍般的建立起來,諸派名家風格林立、各領風騷,篆刻創作和藝術交流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另外,編制印譜也成為一種風尚,這為篆刻藝術成就的記載和傳承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清末印學領域的興盛景象,在數量、質量以及歷史影響等方面,之前的歷朝歷代都少與之比肩。
濰坊地區有著淵源流長的篆刻傳統,自明末崇禎年間,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河南開封人,篆刻理論家,集有《賴古堂印譜》《賴古堂藏印》)在濰任知縣起,后至清初著述家、篆刻家張貞(原籍濰縣,后居安丘南門里)、張在辛一族家傳,影響逐漸擴大。1746 年(清乾隆十一年)著名書畫家鄭板橋知濰縣,同一時期的濰縣人郭偉、譚云龍、韓秀歧、王右民、郭起隆等受鄭板橋的影響,酷愛書畫篆刻,形成了濰坊篆刻早期較為穩定的陣容。至十九世紀中葉,濰坊地區金石學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當地的四大名門望族郭、陳、丁、張富甲一方,族內昆仲子孫多有學術功名,多人自幼嗜學好古,孜孜以求,終生不墜其志,出現了一大批的行家里手。王石經雖不是名門子弟,但青年時期就與其中諸人交往頗深,使其在金石文字方面具備了相當能力。而對王石經篆刻成就影響最大的是清末公認的金石學大家陳介祺先生。陳介祺出身名門,早年游學京師,中年厭倦仕進而辭官歸里,專心收集金石文物進行考證研究。陳氏有著深厚的傳統經史之學素養,又兼當年甚得知名高官學者阮元的欣賞指點,故于金石之學獨具慧眼。他的鑒賞眼力很高,收藏金石多而且精,門類也非常廣泛,對于青銅、璽印、陶文、封泥、畫像磚等的收藏研究都有卓越之處。陳介祺在咸豐四年(1854 年)回到故里濰縣,落戶城郊來章村,其時四十二歲。而王石經與其初識則在1860 年遷居濰縣城內之后。當時的王石經對于書法印學的理解都已具雛形,但苦于沒有名家前輩指點提攜,所以初見陳介祺即有久旱逢甘霖之感,而陳介祺也非常欣賞王石經的才學見識,兩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陳介祺對于后輩悉心指點,寄予厚望,王石經則有幸得到金石前輩的悉心教誨,并能夠近距離研習上古金石,凡陳介祺所藏商、周、秦、漢之鐘、鼎、尊、彝、敦、洗、盤等,他都朝夕觀賞臨摩,加之勤勉刻苦,孜孜不倦,所以藝學日進,深為陳介祺贊賞器重。
王石經早期就擅長篆刻,聞名鄉里,在與陳介祺的長期交往過程中,他對秦漢文字耳濡目染,功力日增,后又受陳氏力薦,得以同全國金石名家王懿榮、盛昱、徐坊、宮本昂等有所交往,在為他們刻制印章的同時也能夠交流學術,擴大眼界,這使得王石經的篆刻藝術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影響力逐漸擴大。能夠標志王石經篆刻藝術前期成就的是《甄古齋印譜》的編制完成。1870 年,將近不惑之年的王石經匯集自刻印成《甄古齋印譜》一書,其書共收王石經為陳介祺、王懿榮、端方等名家治印118 方,章法各異,方方珠璣。一代名家匡源、陳介祺、潘祖蔭、盛昱、吳大澂、王懿榮等皆有題贊,陳介祺、張士葆、吳重意、吳大澂還分別為其作跋,贊賞之詞疊加有余,在篆刻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陳介祺為本印譜的題詞是:“王君追隸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機妙,多材雅士詳。印摹鐙照漢,帖撫搨追唐。何日編鐘鼎,同登叔重堂。”金石學家徐坊見此印譜后更是稱贊其“自有金石以來,未有如先生者”。
1874 年,王石經以簠齋藏印為主、兼及吳世芬、李璋煜、葉志詵、劉喜海、鮑康、李佐賢、潘祖蔭、吳云等各家所藏鈐集成冊,取名《集古印雋》,陳介祺為之題詞曰:“王西泉弟,余歸里來文事友也。能刻印,見余所藏三代秦漢璽印而益進;能作篆隸,見余所藏泰山二十九字、漢二楊碑、郭有道碑真本而益篤;能嗜古文字,見余所藏吉金而能讀;且善氈墨,能鑒別,見余所藏宋元以來書畫而更精審。朝夕過余討論,已二十余年矣,識見日上,藏弆日富,時人已多推之,殆右丞所謂‘天機清妙’者歟。”是年年底,陳介祺推薦王石經為潘祖蔭治印,并寄示王石經新編制印譜《西泉印存》(錄印248 枚),潘祖蔭見后譽為“天下第一”。1875 年王石經為王懿榮刻“劍泉”印兩方,受到王氏稱贊,后又為潘祖蔭刻“伯寅寶藏第一”大印和“潘祖蔭印”“伯寅”章,為吳云刻“退樓乙亥后改號愉庭”正方白文印和“乙亥改號愉庭”正方加框白文印。1890 年,王石經又匯集他和田镕叡、高鴻裁、劉善穎等人藏印編輯《古印偶存》一書。王石經一生輯有古印7 冊,是中國篆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在篆刻界關于晚清印壇的評價當中,王石經大都是被歸為璽印一派的,與之風格相近的有同時期的胡钁和之后的羅福頤、馬衡等人。璽印派的核心理念是“印宗秦漢”,自元朝到明清的長期印學實踐中,受吾衍之《印學三十五舉》的影響,印人多以“規秦模漢”相標榜,治印也幾乎可以與“摹印”劃上等號。然而大部分習印者受困于金石學研究的滯后,再加上自身識見不廣、學養不深,所以很少有人真能得秦漢遺韻,就更別說各出己意、另辟蹊徑了。整個明朝,除朱簡、汪關等寥寥數人外,能得秦漢遺規者甚為罕見。清朝中葉以后,先古文物的大量出土引導了金石學研究逐漸興盛,當時的達官貴族、文人墨客大都愛好收藏、鑒古,這也在篆刻學的領域為“印宗秦漢”提供了實際操作上的可能。而在清末民初的整個印學領域,王石經無疑是在追摹秦漢道路上卓有成就的一位大家。
王石經所處的時代,皖浙諸派已經注重了篆刻創作的入古出新,走向了“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復合型藝術創作道路。就風格而言,篆刻家所考慮的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藝術面目。王石經治印,則不染時人,更傾向于摹仿秦漢以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徑從漢鑄入手,求沉靜肅穆氣息,然后上窺先秦璽印,融合吉金古文爛熟于胸,在刀法、字法、章法乃至于作品意境方面呈現出不求古而自合于古的藝術面目。
王石經從游陳介祺近三十年,得以見到陳氏家藏璽印近萬方及各種金石拓本,眼界大開,學識也是日漸豐厚。經過日積月累的眼見耳聞和王石經本人的勤勉苦學,之后其所作印章,漸見秦漢風范,更合篆籀規矩,“逼肖古人”基本上成為了其篆刻藝術的主要特點,這與晚清其它篆刻流派求新、求變、追求個人風格的主張截然不同,大概也是與陳氏印學思想的影響有關的。關于古篆對于治印刻章的重要性,陳介祺有相當精彩的理論著述,曰:“凡作印:篆居其六、七,刻居其三、四。篆佳而刻無力,則篆之神不出。刻有力而篆不佳,則野矣。穆倩之篆猶未免野人不識字之憾,松雪、三橋以下,篆亦未能至古,而秀則近於弱矣。”對于時人流行的敲邊破角以追求古穆之趣的作印風尚,陳氏不以為然,嘗言:“至漢印,人止知爛銅,而不知銅原不爛,得其刀法愈久愈去痕跡則自佳,此所常與西泉共論者也。”類似的思想見解極大的影響了王石經的治印風格,王石經心追手摹,所作印章跬步不失古人面目,佳者往往置諸古譜中而莫辨,并世名流。另外,他也力矯浙派的切刀營造破碎而求“古樸”的習慣,刀法追求整飾,于莊重中尋求清雅靈動的氣息,他的作品吸引了當時許多金石學家爭相收藏。陳氏反對印人學古不深,在他的眼中,即使趙之謙印章中的“個性、風格”也都在“時人習氣”之列,因此他以為“西泉似不讓拻叔也”(《秦前文字之語·致潘祖蔭書》),潘祖蔭在見到王石經自輯印冊后大加推崇。能夠將王石經的篆刻水平與晚清四大家之一的趙之謙相提并論,雖有提攜后進之嫌,但是能夠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可,也足以說明王石經篆刻的藝術高度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在當時篆刻各派各家尚未得到歷史定論的情況下,追摹秦漢應該還是比較正統的篆刻風格。
故宮博物院現藏有王石經的大量印章,整體來看印風清雅雋永、端莊大方,工穩而不離古法,功力極其深厚,特別是近人屢有紕漏的篆法方面,王石經的作品做到了幾無絲毫之失,令人嘆為觀止。這與他苦苦臨摹秦漢之印分不開,也是其遵循古人嚴謹治學的必然結果。正是在觀摩璽印萬方及各種金石拓本的基礎上,才練就了他頗為正統的璽印風范,而大量的臨摹也夯實了王石經的布局、技法和刀工,使其所刻印章爭奇斗妍,令人賞心悅目,艷羨不已。仔細觀賞他的作品,構思奇異,布局巧妙,其光潔整飾的藝術效果與浙皖等派的沖切結合迥然不同,成為了晚清印壇的一道靚麗風景,閃閃奪目,令人難以忘卻,帶給觀賞者以無窮的意味。
以現在的篆刻美學理論來看,追摹秦漢一路印章,似乎不應在流派之中。原因有二:一則此路印人并不以風格、個性相標榜,而專以得秦漢形神為上,特別又受限于當時學術交流、綜合素養的局限性,導致作品的個人面目不甚明顯,僅能做到在此風格上愈精愈熟而已。二則此路印人對于師承相授的依賴性較小,只要是在治印上的觀點相同,最后的作品意味大都會殊途同歸,這也可以看作是璽印派篆刻在創作方面難以突破的瓶頸。在這方面,王石經也不例外,他的篆刻雖能學古入微,但卻遜于出新,陳介祺嘗教其“以金文入印,自有過漢人處,辟一蹊徑”,而王石經在這方面卻突破甚少,陳氏將其歸之為學力不足,多次對友人說“惜讀書少耳”。近代篆刻家馬國權對于王石經的篆刻藝術有過相對比較客觀的評論:“平心而論,石經之印,功力可謂精到矣,然端整有余,流麗不足,稍欠生動之致,或其稟賦有以限之耶?”當代評論家王家葵也在《近代印壇點將錄》中有類似的說法:“規秦模漢是治印家基本功,而既能入古,則當出新。以秦漢法度,寫我胸臆,此石濤上人所謂‘筆墨當隨時代’也。今論西泉篆刻,于其摹古功力,余無間言,而終生以逼肖古人為追求,縱能無毫發之爽,亦不過為陳簠齋萬印樓中多添幾枚偽印耳,此西泉雖享高名,終不能與吳黃共爭妍也。”
瑕不掩瑜,作為晚清印壇璽印一派的先驅人物,王石經篆刻藝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其篆刻風格對當時和后世的印學領域特別是齊魯印壇的發展軌跡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理應得到重視和進行深入研究。
晚年時期,王石經在鉆研藝事之余,也樂于提攜后輩、傳播文化,濰縣地區民國時期很多書畫篆刻名家如陳君藻(陳介祺五世孫)等都受益頗深,現當代的濰坊篆刻也有著明顯的王石經篆刻風格的痕跡。王石經卒于1918 年,享年85 歲,在藝術家中算長壽的。王石經有三子:長子王宗彝,字幼泉,擅長拓墨,亦工篆隸、印學;次子王丙彝,字子常,由附貢任涼城知縣,曾任康保設治局局長;幼子王尊彝,字子重,工繪畫。其中王幼泉和王石經侄王松甫也曾在陳氏門下從事拓墨。
其后代最能繼承家風的是其孫王端(王幼泉之子)。王端(1908-1996),字扆昌、之端、孝善,別署五士草堂主。他繼承了祖父王石經、父親王幼泉的篆刻藝術精華,篆刻風格在古璽秦漢印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創新,對制作古銅印藝術有獨特的研究。另外他喜歡畫竹,其所畫之竹灑脫自然、飄逸清新、圓勁挺拔、氣勢軒昂,自題詩曰:“竹未出土先有節,昂首凌云總虛心。”王端曾任蘇州美專教授、滬校教務長,他和郭味蕖一起討論治印,也是西冷印社早期社員之一,和唐云、胡亞光、張炎天等都是社友,當時盛名遠播。一九四七年與國畫家蔣孝游、史良猷等組織成立上海市美術茶會,其創立并主編的我國第一部《美術年鑒》研究,在我國藝術史上有著重要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