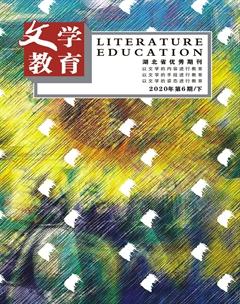莊子和惠特曼的詩學精神比較
桂永才
內容摘要:莊子和惠特曼在追求逍遙于世和人性解放的自由之境時,莊子信奉個人通過祛欲、心齋、坐忘、齊物于道等方式來摒除一切違背個體天性的外在羈絆,力求達到與世無爭、天人合一的澄澈之域;惠特曼則回應時代的要求,對歷史和人性進行不斷的探索和挖掘,對詩人本人和美國民眾現代主體性思維進行細致入微的關照。莊子反對科技文明,信奉在無為中舒張人性。惠特曼卻倡導發展科技理性,并在情理激蕩中釋放人性,兩者詩學精神的差異受到了林語堂的誤讀。
關鍵詞:莊子 惠特曼 詩學精神 審美感知
莊子和惠特曼作為時代的叛逆者,皆對各自的社會文化傳統和倫理價值體系作了深刻的反省和徹底的批判。雖然兩者是處于不同國度的著名詩人,但是兩者的詩學精神也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然而,這些審美思想的相似和差異卻被很多作家所誤讀,林語堂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之一。筆者發現,林語堂在以下三個方面對惠特曼詩學精神造成了誤讀,而這些誤讀至今沒有引起評論界的重視。
一.“道法自然”與“自然之子”:個性自由的實現途徑
在《美國詩人惠特曼對林語堂的影響》的文章中,王小林先生揭示出林語堂曾以贊賞的口吻說:“在這混亂場(指西方哲學的混亂)引者中,有幾個人是矯立不倚,形神俱足的,一是George Santanaya因為他是主張妙悟的,叫人無法歸類。一是美國詩人Walt Whitman,他說“我就是我”,不像笛卡兒乞求哀憐于他的Cogito來證明其有我相。”[1]5這段話反應了林語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現了莊子和惠特曼有諸多相似之處,進而提倡中國人要如同惠特曼和莊子倡導的那樣,在個人化的私密的空間中無拘無束地享受人生樂趣,其實,林語堂混淆了莊子和惠特曼對自然看法的差別。
莊子把生于萬物、主宰萬物的“道”視為自然和社會運轉的根本規律和基本法則,萬物都是在“道”的循環演化中產生、生存、運行和發展的。《莊子 大宗師》中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級之下而不為深。生天生地,在天地而不為久,長與上古而不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終。[2]111莊子強調“道”是孕育萬物的主體存在,是自然無為的,人應該順應道行,不能因自己的主觀隨意的需要違背自然。他在《齊物論》中這樣寫道:“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惡乎可?可于克。惡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2]71
殘酷的社會文化背景迫使莊子與惠特曼都向往和憧憬自然。但他們在對自然的審美態度上截然不同。林語堂把惠特曼對自然的看法和自然中個體的表現,和中國詩人莊子的自然和自然中表現的個體的審美姿態混為一談。雖然惠特曼和莊子都呼吁人要順應自然,享受自然帶來的人生樂趣,但他們在理解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莊子認為,自然是沒有意志的無為的被動存在,個體應該順應自然的發展;而惠特曼則認為,自然是有為的主體,是完全可以激發個體蓬勃力量的大自然。當個體和自然融為一體的時候,惠特曼筆下的抒情人物的情感就具有相當強烈的主體意識和自我個性,而不像莊子認為的那樣,個體只是無意識、無目標、無節制的被動的順應自然的存在。
二.“至者”與“志者”:塑造理想人格的形態特質
莊子認為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秩序已經內化到民眾的個體無意識中。民眾彰顯出的對人性的追求、生命的呵護、自由的追求,都必須嚴格服從以儒家血緣體系為核心的價值標準。莊子的《逍遙游》對理想的人格做了這樣的闡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2]59在他心中,極具人生智慧的“至人”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人和自然合一相融的狀態,至人的特性“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2]61,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去做有為之事。
人們而要達到莊子提出的“至者”狀態的最好方法是:守一去欲、秉虛心齋、坐忘無待。莊子對守一去欲這樣解釋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生長。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慎守汝身,物將自正……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2]91就是以虛靜的方式集中注意力,秉虛心齋中。莊子認為:“虛者,心齋也。[2]91如何達到虛,莊子認為:“無聽之以耳”,“無聽之以心”,“聽之以氣”[2]91,要忘記所有的感官活動和生理需求,尤其是功名利祿等外在和內在欲望,“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惡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2]87功名利祿是不一定會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快樂的,相反,可能帶來消極的影響,成為人們相爭互斗的目標,也是禍害形成的根源。“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宜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2]85莊子極力鼓勵人們掙脫一切外在的物質誘惑和精神枷鎖,平和漠然地看待世間一切功名和生死,最終以心靈的安寧愜意來反抗和解構傳統的倫理本位文化。莊子塑造出很多傲立于宇宙間超越生和死、進入逍遙之境的個性形象,這種“齊生死”、“齊萬物”的至人形象極其閃亮動人。
馬克思曾這樣表達過,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使自己的自然中沉睡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的控制。”[3]202在《自己之歌》中這樣表達道,“我是巨大的,我包羅萬象,”[4]103在《巴門諾克開始》中,詩人表達道“我愿意使我的問題、思想、關涉到全體。”[4]100著名評論家約翰布羅斯曾經指出:欣賞《草葉集》時,你必須抱著一種寬宏的氣度,一種與它本身相稱的博愛和信念去接近它。”[5]534
林語堂卻忽視了惠特曼和中國莊子關于理想人格的區別。林語堂這樣認為:“我以為人生不一定要有目的或意義。惠特曼說:‘我這樣地做一個人,已夠滿意了。所以我也以為我現在活著———并且也許還可以再活幾十年———人類的生命也存在著,那就已經夠了。這樣看法,這個問題便變為極簡單,而不容有兩個答語;這是人生的目的除了去享受人生外,還有什么呢?”[6]245
總體來看,“至人”是以消極避世的方式來祛除個體的一切欲望,推卸一切社會責任,順應天命;而“志人”是以積極入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釋放天性,發揮自己的獨立意志,積極肩負起建設社會的責任,創造理想的生存環境。
三.“游世”與“游技”:感悟人性自由的實踐模式
莊子和惠特曼雖然采用理想的形式對世俗社會主流意識所推崇的人格給予了徹底的拒絕,但都希冀于人性獲得自由。莊子極力彰顯的是人們清靜無為的精神狀態,而惠特曼則奮力呈現的是具有獨立意志的、并在自我實現和社會建設時能迸發出昂揚奮進的、具有生命激情的人的性格,
“夫弓弩,畢戈,機變之知多;削格、羅洛,置罘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2]130(《胠篋》),人類使用各種技術制作工具來捕捉動物,既擾亂了日月的光華,又破壞了山川中的精靈,造成生態平衡的紊亂。他認為要“決勝棄知,大盜乃止,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2]139人們對科學技術知識的認知水平和把握能力越強,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科技發明擾亂國家秩序,蠱惑民心,尤其當科技主宰一切時候,可能會嚴重地擠壓生物的自由和發展空間,天然生物就可能被無情地征服、掠奪和絞殺,會造成生態失衡、物種滅絕、資源銳減等嚴重而又的棘手問題。
游世者表現出的神清氣爽的精神,是醫治煩悶抑郁、迷茫惶惑等精神疾病的苦口良藥。游世者們的瀟灑飄逸的自由意識,成為詩人賴以支撐的心理依靠和精神屏障,而飽有這種游世精神的人,才會享受真正的人生。
惠特曼在《草葉集》中借助游走各地的經歷來實現對理想人格的實踐。他的詩歌中的主人公,在游走過程中表示出了對既定傳統規范的厭惡和激烈的反叛,以游走路上所感受到的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科學技術作為生活養料來豐富自己的情感和情操,因此,不妨把他筆下主人公的游走謂之“游技”。
林語堂忽視了莊子和惠特曼詩歌中的個人游走的實踐內涵的區別。雖然兩位詩人都是以“游”來體認人類獨立自由的精神內核,但惠特曼詩歌中的主人公們,以激情擁抱時代,始終緊跟建設時代的步伐,用游走的姿態來對抗個人自主性被剝奪的傳統教義的束縛。他們游走背后內隱著熱烈豪放的生命活力,掩藏著灼熱感人的青春激情,彰顯著對強烈生命的渴望。而莊子作品中的主人公們留給我們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對自己才干的淋漓盡致的展現,而更多的是在不停的游走中那種對于傳統倫理道德秩序的漠視和鄙夷的態度,以及對脫離時代節奏,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人生理想的堅定呵護和為自己渴望無為、怡然澄澈境界的執著追求。
惠特曼和莊子都以詩意的語言追求自然的回歸,描寫自己憧憬的人性舒展和自由的狀態,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林語堂.林語堂自傳[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5.
[2]洪鎮濤.老子 莊子[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111,71,59,61,91,91,91
,87,85,85,130,138.
[3][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2.
[4][美]惠特曼:草葉集[M],楚圖南、李野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103,100.
[5]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M].Oxford Publishing House 1998:534.
[6]林語堂.林語堂文集(第七卷)生活的藝術[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245.
項目號:2015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振興計劃重大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應用型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形勢下的大學英語綜合改革——以淮南師范學院為例(項目編號:2015zdjy134)
(作者單位:淮南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