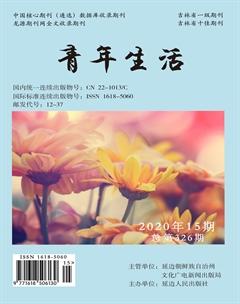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對立與共生
馬曉陽
摘要: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在電影史上一般是相互對立的兩極,前者代表著工業化制作,后者則代表著藝術創作。但隨著電影實踐的深入發展,二者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共生關系。在電影創作蓬勃發展的今天,如何化解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兩極對立的難題,以及如何在電影工業和電影藝術二者之間取得平衡點成為了當代電影人避之不去的議題。本文將以希區柯克電影為例,全面探討類型電影以及作者電影之間的聯系,以此審視新時代下電影創作的新視角、新路徑。
關鍵詞:類型電影;作者電影;希區柯克;藝術創作
一、概述
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往往是電影史上互相對立的兩極,類型電影主要是商業電影,而作者電影即為藝術電影等非商業性電影的代指。其中,類型電影源于好萊塢全盛時期,此時期的好萊塢創造了一種將藝術產品標準化的規范以提高制片效率與收益的穩定性。在依照不同類型的既定要求而制作影片的規制背景下,類型電影具備定型化的人物、公式化的情節以及圖解式的造型,娛樂性強又通俗易懂。在電影實踐中,類型電影受眾面廣,產量大,喜劇電影、動作電影、科幻電影是最為常見的類型電影,普通觀眾在商業院線內接觸到的電影絕大多數也都是類型電影。
而作者電影源于20世紀60年代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新浪潮電影代表人的“作者論”主張。作者電影與“作者論”一脈相承,其共同高度肯定導演個性、貶抑電影流俗化創作,在作者理論的影響下,一系列具有濃烈個人風格特質的作者電影登上歷史舞臺。隨著電影實踐的深入發展,作者電影的含義與藝術電影的含義在當代幾近重合,二者共同站在商業電影的對立面鼓勵電影藝術創新并強調電影的藝術性而非商業性。歐洲電影節上的電影作品就是當代最常見的作者電影,其最注重的即是導演的個人化表達且排斥工業化的流水線型創作方式。
但是,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對立關系并非是絕對,二者之間的對立關系是相對的。隨著電影制作的深入發展,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呈現出了某種共生的格局,這種共生關系在《寄生蟲》、《蝙蝠俠:黑暗騎士》等當代電影中充分體現。而希區柯克的電影則是最能體現上述二者共生關系的,他習慣用商業化手法創作,其本人又生活在“作者論”興起的時代。因此,欲考究并深入理解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關系,則有必要對其作品加以審視。
二、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對立
(一)類型電影與希區柯克作品
類型理論是文藝創作中較為古老的理論,古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就曾經把文學作品劃分為史詩、悲劇、喜劇三大類型。直到19世紀末電影被發明,類型理論也深入到電影創作領域當中而逐步形成類型電影,類型電影作為一種拍攝方法,實質上是一種藝術產品標準化的規范。在《電影藝術詞典》中,類型電影被界定為 “按不同類型的規定要求制作出來的影片”。
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生于英國,1920 年開始在倫敦拍攝電影。直到1940 年,希區柯克前往好萊塢拍攝了影片《蝴蝶夢》并大獲成功。希區柯克也因此融入到了好萊塢大制片廠體系之中,他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里廣泛吸取美國大型壟斷電影公司的工業化制片模式,創造了一系列經典的懸疑電影。希區柯克的作品以犯罪片為基礎,往往圍繞某一具體的犯罪活動或罪案來架構故事,作品中嵌套一層又一層懸念以此抓住觀眾的好奇心和恐懼心理并在電影中營造出能使觀眾產生緊張感與恐懼心理的藝術氛圍。之所以將其作品歸為類型電影是因為希區柯克的電影設定符合經典犯罪片的常見范式,故事中的犯罪和罪犯被特定化、符號化。以其經典作品《迷魂記》為例,男主人公是勇敢又充滿正義感的偵探,總是穿著筆挺又正經的西裝;反面人物則狡猾奸詐、心思縝密,處心積慮地設置陷阱并實施犯罪。可見,作品中具體的人物特征與形象只是犯罪電影、懸疑電影中的符號化元素,不附帶任何的藝術創作性質。其次,電影情節也是依照罪案發生-偵查與懸念-揭露真相的順序推進,這已完全符合同類電影的創作標準規范。標準化創作、類型化策略讓希區柯克在移居美國后迅速深度融入以制片廠為核心的好萊塢電影體系并成為了類型電影的領軍人物。
當然,這種公式化、定型化與圖解式的創作模式是不值得全面提倡的,畢竟電影創作本質上仍應當屬于藝術創作的范疇。然而從觀影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種類型的特征可以滿足觀眾的獨特訴求,創造類型的愉悅,從而滿足觀眾的期待心理,引起觀眾的觀賞興趣,頗受歡迎。對于制片廠而言,類型更是一種經濟策略與商業運營模式,類型電影主要能以構建相似性的方式來吸納穩定的觀眾群并抵御藝術創新的風險。
(二)作者電影與希區柯克作品
新浪潮電影之父巴贊在文章《論作者策略》中對作者電影的重要性進行了總結: 在藝術創作中,作者的身份是清晰與明確的,對作者的重視在美學與藝術理論中是一個慣例。但因為電影藝術以工業的和流行作為先決條件而形成了某種整體的束縛,致使電影作者的身份在長時間內都是缺席的。換言之,作者電影的核心是要求電影像其他藝術作品一樣要具備明確的個人風格,強調電影的主要創作人和負責人是導演而非制片廠或制作人[王家東:“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視域下的希區柯克”,載《電影文學》2018 年第3期,第58頁。
]。但在電影高度商業化的大背景下,電影的多數藝術語言都是基于慣例的,而富于獨創性與新穎性的藝術表達與電影的商業化是背離的,因此很少被使用,這一切從整體上讓作者和電影漸行漸遠。
雖然希區柯克一生中最主要的創作時期都在好萊塢大制片廠的束縛下渡過,但觀眾仍能在希區柯克的作品中感受到作者創作的激情和生命力。其電影在手法上大量運用標準化程式,但其精神內核卻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其創造的“希區柯克式”懸念機制[史文杰:“淺析希區柯克電影情節中的懸念機制”,載《影視》2018 年第1期,第109 頁。
]極大地提高了自身作品的審美價值。以希區柯克自己的話來解釋其作品中特有的懸念機制便是“懸念在于給觀眾提供一些劇中人所不知道的信息。劇中人對許多事情不知道,觀眾卻知道,因此每當觀眾猜測結局如何時,戲劇效果的張力便產生了。”具體而言,他制造懸念的核心方法有三種:第一,希區柯克為觀眾提供全知的視角,而主人公均只具備限制的視角,二者相互映襯增強了情節發展變化的不確定性。以《電話謀殺案》為例,男主角萌生了殺妻謀財的念頭。經過周密的策劃,他雇用殺手執行他的殺妻計劃,并將執行過程中的細節對殺手作了詳細交代。這一切觀眾都一清二楚,而妻子卻沒有絲毫察覺,更無戒備。第二,設置多條互相穿插的時間線索平衡戲劇矛盾的沖突與緩和,每當淺層意義的矛盾被解決,更為深層的矛盾也隨之被引發,例如《狂兇記》中人為地造成尖叫聲遲緩的效果。第三,其廣泛利用打破第四面墻、主觀鏡頭等視聽語言增強觀眾的心理體驗與代入感,戲劇懸念也因此在主觀方面得以強化,《驚魂記》中的浴室行兇便是其視聽語言高度風格化的凝練表達。因此,希區柯克實際上是開辟了一套富有個人特色的懸念機制,故完全可以將其作品加冕為作者電影。
三、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共生
希區柯克的電影風格存在著類型電影的創作手法,又具有濃烈的個人特色和風格,他堅定地發展了好萊塢懸疑片類型的同時,又在他的電影中呈現出作者電影的特征,此即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的共生。類型電影重視模式,作者電影重視創造。因此,二者建立共生關系的關鍵在于調和模式化特征與藝術創造力之間的矛盾。在制片廠流水線生產模式的背景下,通過固化類型電影特定模式會使同類型作品不斷出現,令電影作者的風格不再只屬于導演一個人,而成為特定的“類型”。但希區柯克率先實現了突破,他創造的懸念元素只屬于其一人,他人只能模仿、挪用其作品中類型化的模式與創作手法,而作為核心的懸念機制則永遠是是具有創作者色彩的個人命題。
依照傳統的觀點,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似乎是對立的兩極。前者代表公式和工業化制作,后者代表創新和藝術構思,這種差異似乎讓電影創作面臨不可協調的矛盾。但當代類型電影往往面臨著內容固化、形式死板以及創作靈感匱乏的難題;而作者電影卻越來越小眾化,雖然其在內容和形式上極度創新,但其表達的高度和深度令一般的觀眾群體難以明白和接受。
所以,為了化解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兩極對立的難題,嘗試不同類型電影的勾兌和混合,成為了目前電影作品發展的新趨勢。也就是說,類型電影與作者電影共生是可以實現的。以希區柯克為例,他成為作者導演的同時創造了一種電影模式,縱觀希區柯克的創作,完全讓我們看到了類型電影和作者電影的完美共生。希區柯克的電影值得我們深思與研究,如今的電影發展也需要充分借鑒各種成功經驗。若當代導演積極展現出對電影新的認知視角和表達方式將有利于開拓電影的邊疆,所以保持一種開放包容和謙遜的態度對待類型電影和作者電影,將對導演和電影的發展都更加有益。近年來,在我國紛繁復雜的電影市場中,有一批青年導演群體,憑借自身對電影的理解,已經開始了多樣化的嘗試。從《心迷宮》到《老獸》,從《路邊野餐》到《八月》,從作者電影到類型電影,許多導演在當下不斷探索著電影創作的多種可能。
四、結語
類型電影經常被視為一種工業化的流水線的生產模式,這似乎是與體現個體獨立精神的作者電影的宗旨相背離的。然而,類型電影也不是僵化的、死板的或一成不變的,類型電影自身也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其內部機制得以在遵循模式的同時,不斷地破除舊模式與創造新的模式。觀眾的需要被類型電影視為頭等大事,其也就會根據觀眾的審美需要來自我調整,創造審美上的新鮮感,重塑類型。可以說,類型電影的系統是商業體制中非常成熟的一種體系,但若能及時融入作者導演獨特的創造力還將進一步增強其生命力并提高其藝術性。
另一方面,作者電影作為藝術的象征也并非絕對代表著“曲高和寡”,藝術化的表達與類型化制作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絕對沖突的,作者電影完全可以在保留藝術性的基礎上適當吸取類型電影的優勢以促使二者相互調和,以此不斷開拓電影的邊疆與認知視角。
參考文獻
[1]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Z].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2][法]安德烈·巴贊.論作者策略[A].楊遠嬰,主編.電影理論讀本[C].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3][美]大衛·波德維爾,克里斯汀·湯普森.世界電影史[M].范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48.